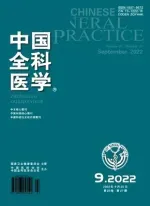国内外社区卫生服务经费分配与绩效管理体系的情况和分析
陈 虾,陶红兵,罗乐宣,张英姬,罗东辉
我国的社区卫生服务进入了 “规范化发展阶段”,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社区卫生服务的地位和方向已经明确,同时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所面临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社区卫生服务必须保持公益性,并在保证公益性的同时,提高绩效和避免 “吃大锅饭”和 “养懒人”情况的发生,为此我们在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组织下,派出 10名骨干赴美国、澳大利亚进行为期 1年的访问学习,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考察及访谈等方式,分别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沿海地区等国家或地区针对卫生经费政策及绩效考核进行了解和分析,并对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经费分配与绩效管理体系的建立提出设想与建议。
1 卫生绩效的 “4E指标”
“4E指标” 是指:Equity(公平性)、 Economic(经济性)、Efficiency(效率性)、Effect(效能性),是 WHO推荐评价卫生绩效的指标。
1.1 公平性 即无论人种、肤色、性别、年龄、社会和经济地位,都能公平地享受到国家为国民所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包含了 “公平性”和 “可及性”两个方面。
1.2 经济性 由两方面组成:一是政府投入的经济性 (即政府用较少的投入可以为居民提供足够的基本卫生服务),二是居民享受服务的经济性 (即居民以较少的费用即可享受到必须的基本卫生服务)。
1.3 效率性 即卫生系统提供服务的效率。
1.4 效能性 即卫生系统完成政府指令或社会职能的程度。
效率性是个 “单位数量指标”,如每位医生每天提供多人次的诊疗服务,或者患者享受到服务的速度 (如预约等候就诊时间);而效能性是 “定性指标”或 “等级指标”,如卫生系统在执行政府要求落实的某项政策或任务的程度 (如优、良、中、可、差,或达标、基本达标、不达标)。
4E指标往往是一组不可调和的矛盾,目前世界上很多的发达国家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 4个指标的矛盾,如美国的卫生系统在公平性、效率性和效能性较高,但经济性不高 (即政府支付了很多的经费);英国在经济性、公平性、效能性较高,但效率性不高 (居民需要很长时间的等候);我国现阶段的效率性是全世界最高的,但公平性和经济性的排名却很落后,而且效能性也不高。
2 国外卫生经费分配与绩效管理体系的情况
2.1 卫生经费的付费机制及模式
2.1.1 以 “服务包”成本核算的付费机制 美国、澳大利亚、法国等发达国家以及墨西哥、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并与医疗保险相结合的付费机制。
2.1.1.1 “服务包”的发展 “基本卫生服务包” (Package of Essential Health Service或 Packageof Basic Health Service)的概念是由世界银行首先于 1993年在 《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来的,是指包括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 (Essential Public Health Package)”和 “基本医疗服务包 (Essential Clinical Package)”在内的基本卫生服务项目。
之后各国进行服务包的概念性研究,1995年美国、英国等专业机构提出公共卫生的功能应该包含:健康监测与分析、对疾病暴发流行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调查和处理、建立并管理或实施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项目、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和效率等 10项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的内容也相应包含以上 10个方面的内容。在此期间美国的 “卫生系统协会”(Institute of Health Systems,IHS)提出了 “基本医疗服务包”的内容,并指出:要想使服务包能够负担得起,政府必须对经费分配、筹资和保险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
国际组织提出的基本卫生服务包内涵及研究情况是在对服务包的概念性研究之后开始的。在 《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提出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括以下六类活动:(1)计划免疫;(2)以学校为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3)计划生育和营养的信息及某些服务;(4)减少烟草和乙醇消耗的计划;(5)为改善居民环境而采取的行为调控和信息服务;(6)防治艾滋病。
1997年 WHO组织了 67个国家 145位专家在全球范围内就 “基本公共卫生”功能和内涵进行研究,并于 1998年确定“基本公共卫生”功能的框架包括:(1)健康状况监测;(2)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监测和控制;(3)健康促进;(4)公共卫生立法和管理;(5)对弱势人群和高危人群的个人卫生服务;(6)职业卫生;(7)环境保护;(8)特定公共卫生服务。“泛美卫生组织”在此期间对 “基本公共卫生”功能框架除了以上 8项外,还增加了:健康的社会参与、提高公共卫生政策与机构进行公共卫生规划与管理的能力、评估和提高必要卫生服务的公平可及性、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个人和人群卫生服务的质量保证等多项内容。
2.1.1.2 发达国家、地区提出的基本卫生服务包内涵及付费机制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提出的 “基本卫生服务包”包括:(1)生殖保健;(2)儿童保健;(3)有限医疗服务;(4)传染性疾病控制;(5)行为改变的交流 (行为干预)等5项内容[1]。根据服务包内容由不同的服务机构或家庭医生提供服务,政府向保险公司购买服务,保险公司根据服务情况向提供者付费。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卫生项目主要有四类:(1)国家卫生项目 (包括:健康促进项目、医疗服务项目、家庭和儿童项目、老年服务项目、残疾人服务项目、协调服务项目等六项);(2)口腔服务项目;(3)老年服务项目;(4)国家其他卫生项目。这些项目由基本医疗机构 (家庭医生或集体化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医生联合体)提供服务,费用由联邦政府购买。采用的是类似 “分灶吃饭”的承担模式,即国家承担基层医疗 (即社区卫生服务或家庭医生联合体所提供的服务),州一级的政府承担本地区医院的基本医疗,所以在澳大利亚当地政府愿意将患者流向社区,这样可以减少地方财政的支出[2]。
法国的公共卫生项目与上述相似,但更加细化。
2.1.1.3 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基本卫生服务包内涵 墨西哥于2003年把卫生服务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 “纯公共卫生产品和服务”,包括: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疾病预防与控制和明显外部性的个人卫生服务等,具有普遍覆盖、公平和社会保障性特点;第二类为 “一般性的个人卫生服务”,包括: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等。第一类由联邦财政提供经费,向全体公民免费提供;第二类通过大众健康保险负责筹资,按规定进行免费或部分自费服务。
泰国于 2001年提出了一项名为 “30铢计划”的全民健康保险,即公民在每次看病中只要交 30铢后,将获得所有公共卫生项目及大多数指定范围的免费诊疗项目。
印度政府用一个 “综合服务包”的形式来界定基本卫生服务内容,包括:(1)核心服务包 (包括公共卫生项目);(2)基本服务 (基本医疗项目);(3)二级服务包 (专科医疗项目)。
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均根据各个国家不同的卫生状况,制定了相应的卫生服务包。
2.1.2 纳入国家福利体系提供全民免费基本卫生服务的付费机制 英国、瑞典、丹麦和我国的香港均采用此模式,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卫生经费是根据上年度使用情况和人口发展情况进行预算,虽有预算但实际上是 “使用多少支付多少”。为了控制开支,这些国家或地区对提供的免费卫生服务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制度:一是 “守门人”制度,二是 “计划经济统筹管理”,即居民要得到政府提供的免费卫生服务,需要进行 “统筹管理”。在英国除急诊之外,所有门诊服务都要通过家庭医生进行首诊,如需要医院服务必须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转诊、预约和排队;如果想享受快速的服务,则到个体诊所或非免费的医疗机构,但由患者自费,所以这些国家或地区公平性高,但效率性低。
在以上这些国家或地区,居民的医疗保险购买率较低,其中香港是世界上惟一没有强行推行医疗保险的发达地区。
我国于 20世纪 70年代以前曾经执行过类似的模式,当时曾经被 WHO评价为 “用世界上最少的钱,解决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卫生难题”,是 WHO推荐的几种成功模式之一。但在 20世纪 80年代后,由于经费不足和市场经济思维的冲击,已经消失殆尽。
2.1.3 采用单病种医疗保险、总额控制和 “包干”的付费机制 这种模式在我国的台湾地区比较典型。台湾于 1995年推行 “全民健康保险” (强制性),目前医疗保险率接近100%[3],其支付及卫生经费控制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医疗保险付费方 (即健康保险局,也是卫生系统的管理者)与医院机构的结算和包干付费。
其模式为:(1)政府制定了每种疾病的单病种费用标准;(2)每年根据上年度经费及人口情况进行卫生经费总额、保险支付总额的预算;(3)居民到医疗卫生机构接受服务 (分四级),按服务项目 (包括疾病诊疗和保健服务)及其规定由医疗保险账户支付费用 (即挂账);(4)健康保险局与提供服务方结算时,采用 “单病种费用总额包干”和 “视全地区单病种数量进行费用标准的调整”,如:对于 “肺炎双球菌引起的肺炎”这种疾病,其单病种费用标准为 1万新台币/例次,全年预算用于此病的全台湾保险支付总额为 1 000万新台币(即估计全台湾全年有 1 000例次),但某一年全台湾此种病只有 500例次,那么每例次就有 2万元新台币,反之,如果此病例增加到 2 000例次 (公共卫生应急和突发性灾害等除外,由另外应急资金支付),那么治疗每例次病例就降到 5 000新台币,根据每个机构对此病例所提供的服务量进行经费分配。
此模式的优点是:(1)政府对卫生经费额度控制性好、预算执行力强;(2)降低单病种费用的方法由医疗机构自己掌握,有效控制了 “小病大治”的情况和医疗费用的过快上涨;(3)保持合理的医疗市场竞争,促使服务机构根据自己的技术优势和水平采取合适的经营策略;(4)引导医疗卫生机构重视预防和公共卫生工作、减少疾病发生,从而提高人群健康水平;(5)居民的就医虽也要分级医疗,但受限不大、费率低,公平性、可及性和效率性高。这些恰是我国目前所面临和亟需要解决的问题。
2.2 国外医疗卫生服务及社区卫生服务的绩效管理体系 国外的全科医学发展较早,所以其绩效评价体系的发展时间也较长,且相对完善,而真正意义上的绩效考核体系是从现代管理学理论快速发展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分支后才开始的。
从政府在绩效管理中的角色和绩效评价的目的,绩效考核体系可分为多种模式,各种模式往往由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阶段、卫生体制和国情所决定。往往一种模式在发展初期占主导,在经历多个发展阶段后,重新回归到初始模式,评估体系往往也是从简到繁,再从繁回到简的 “循环式上升”特点,同时每一种模式也并不是纯粹、单一的,而是多种模式兼并,只是某种模式占主导而已。
从管理的角度和行业发展规律,各种模式一般从 “政府直接管理”到 “间接管理”或 “托管 ”,再到 “行业自律管理 (自管)”,从 “被动约束”到 “自我约束”,所以,我们认为行业自律管理是一种较高级的绩效管理模式,当行业自律管理出现偏离、自律无法达到目标或需要进行改革时,又可以回到政府直接管理或间接管理的模式。
2.2.1 从政府的角色来看医疗卫生的绩效管理模式
2.2.1.1 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参与或主导的绩效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出现在:(1)在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各项行业标准尚未出台和不够完善,需要引导和规范行为,同时无其他监管部门代其职能,需要政府部门独立承担;(2)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政府为了加强某项功能管理 (如经费控制)、职能转变 (如 “管、办分离”,“政、事分开”),以及在行业管理和市场调控失灵的情况下而采取的模式。
我国的台湾地区现在实行的绩效管理模式就是这种模式,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卫生经费和建立良好的医疗秩序。在 20世纪 60—80年代,台湾曾经实行 “行业管理模式”,但造成了无序就医和居民负担过重的情况,当时的状况与我国大陆地区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基本相似。1995年开始台湾进行医疗体制改革,成立 “健康保险局”和推行 “全民健康保险”,并由“健康保险局”直接进行卫生经费分配和医疗机构的绩效管理,使台湾的医疗卫生服务走出了困境。目前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市场调控失灵的情况下,企图加强政府的监管来改变目前的状况。
目前采取此模式的国家或地区有:英国、台湾以及印度等,我国大陆地区也采取此模式,但与英国和台湾相比,在体系上仍存在较大差距,所处阶段也是不同的。这种模式往往体现了 “计划经济统筹管理”的特点,政府既是主办者,同时也是管理者、考核标准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2.2.1.2 以付费方 (第三方)进行绩效管理的模式 这种模式是目前较多发达国家或地区采用的模式,一般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医疗卫生已经步入稳定的轨道,政府对医疗卫生的业务监管由 “直接监管”转向 “间接管理 ”或 “托管”,这种模式同时也存在于为了加强卫生经费的控制而推行的时期。
目前采用此模式的有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管办分开,政府负责制定规划和标准,购买服务,由第三方 (直接付费方)进行业务绩效的考核,形成了 “政府 -付费方 -提供服务方”的三角关系,这个三角的中间是人群的健康,这就是他们所说的 “公共卫生的系统思维论”[4]。
2.2.1.3 以行业管理、行业自律为主的绩效考核 这种模式是政府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管理,如制定卫生规划、人群健康目标、卫生经费预算等,具体的管理行为和绩效评估由行业协会进行。从管理的角度实现行业自律管理是管理更高一级的模式。
目前采用此模式的有香港、瑞典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如我国的香港,医生行业自律性非常高,医学会具有资质审核、准入和医疗行为鉴定的权力,并可以对行业内的成员和机构进行质量的评估和最终评级。
此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业内人员的职业操守高、自律性强,行业组织完善,提高服务质量成为行业发自内心的要求,质量评估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行业组织有很高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政府的微观指令往往只能是 “建议”而不是强制性要求。
2.2.2 从绩效管理的目的来看医疗卫生绩效管理模式 医疗卫生的绩效管理可以分为: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绩效、进行卫生经费分配与经费管理、评价目标的实现情况等三个方面,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绩效管理均采用这三个方面目的的综合模式。
2.2.2.1 为提高服务、经费管理和评价目标情况的绩效管理模式 除香港和瑞典外,其他国家对医疗卫生的绩效管理均采用这种模式,它是根据质量管理的评估结果与经费的关联和渗透程度分为:经费额度是根据质量评估总结论进行经费拨付、经费额度是根据各服务项目的质量和数量进行核拨计算两种模式。
(1)总体经费额度是根据质量评估总结论进行经费拨付的绩效考核:这种方法的表现形式主要以 “每服务 1人口为每年拨付经费单位”和 “根据考核结论进行经费拨付参照”的方式进行考核的。这种方法早期多用于公共卫生项目的“服务包”和 “包干制”的付费机制,后来应用于 “单病种付费”的方法也是此方法的发展。
采用此方法的典型是美国的家庭医生契约服务,在美国家庭医生往往需要签约一定数量的居民,保险公司就以每人每年规定额度的经费进行 “包干”,保险公司每年考核后,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全年经费的结算。
这种方法往往存在一些缺点,没有充分考虑服务数量和服务对象的情况,如:一名家庭医生签约的人群老年人居多,而另一名家庭医生以青年人居多,这样在同样经费标准的情况下,第一位家庭医生的负担重、获利少。我国目前社区卫生服务经费分配与绩效管理就存在这个问题。
(2)经费根据各服务项目的质量和数量进行核算的绩效考核:这种绩效方法的表现形式主要以 “每服务 1人次,根据该项目的考核质量给予经费”,而经费总额是各项服务项目的经费累加。这种方法是在上述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完善发展而来。采用此方法的典型就是我国的台湾地区。
2.2.2.2 为提高服务和评价目标实现情况的绩效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绩效管理一般不考虑卫生经费分配政策,只针对服务质量和目标的完成情况,多在行业管理对业内服务情况进行评价,也在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或地区采用,同时专业的独立质量评价也采用此方法,如目前 ISO-9000系列的质量认证。
香港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例子,由于香港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政府负责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所以行业组织没有经费管理的委托任务,行业只管服务质量和各种资质审核、鉴定等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我国在 1996—2000年社区卫生服务常规性经费没有出台之前,由于无经费可分配,所以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考核基本上也是以质量考核为主。
3 国内社区卫生服务经费分配与绩效管理体系的情况
目前我国 3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有 82.1%的城市和70.0%的县都开展了社区卫生服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达到了27 308个[5]。
从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体系建设和发展来看,可以分为:(1)探索阶段 (2000年以前);(2)快速发展阶段 (2001—2005年);(3)规范发展阶段 (2006年至今)。
目前全国所有开展社区卫生服务的省、市、县 (区)都出台了相应的社区公共卫生经费和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考核方案。
3.1 国内社区卫生服务的经费及补偿政策及相关研究情况
3.1.1 社区卫生服务的经费及补偿政策情况 1998年,全国各地区相继出台了社区卫生服务的补偿经费政策,至 2010年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出台了相应的经费政策,在已经出台的社区卫生服务补偿经费标准中,均以 “服务每人口每年”的单位标准出台政策,标准为 5~45元[5]。
3.1.2 相关研究与发展的规律 国内社区卫生服务经费政策研究,基本上呈现这样的一个规律:从 “定性研究”开始、到 “定量研究 ”、 再到 “定向研究 ”。
开始提出设想后进行 “定性研究”(即 “要不要给经费”,进行可行性研究)、到 “定量研究” (即 “给多少”,“以何为准”)、再到 “定向研究”(怎么给、给到哪里)。社区卫生服务的经费政策也是呈现相似和对应的规律。
3.1.3 社区卫生服务经费政策的研究情况
3.1.3.1 概念及定性政策的研究 从查阅到的资料来看,郭清、鲍勇、顾杏元、李士雪等[6-9]于 1997年在我国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早期,就提出了社区卫生服务补偿及经费政策的思考,并建议出台相关的 “常规性补偿经费”的政策,实际上应该还有人在更早的时间提出相关的论题。
相关的研究也是从 1998年社区卫生服务补偿经费出台之时开始的,在此时期内,全国的学者及政策制定者与财政部门在出台经费标准的依据上存在疑问,于是在 1997—2000年,全国学者争论的焦点集中在 “要不要拨经费”这个定性问题上,多数以建议、呼吁、思考和可行性研究为主[6-9],因此,2000年以前只有少数地区出台了较为明确的补偿方案,其他地方的政府在出台经费补偿政策方面仍然持观望态度,直至2000年十部委 《关于加快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若干问题》的文件下发,这个 “要不要”的定性问题才得到共识。
3.1.3.2 定量经费政策、筹资机制和服务包的研究 在定性问题达成共识后,“拨多少”这个定量问题困扰着各地社区卫生服务经费的出台和细化。2001年复旦大学的蔡卓等[10]以上海的社区卫生服务为对象,率先对社区卫生服务的经费成本进行研究,得出现阶段 “每成人每年补偿总额 12元” (即每人每年 12元的补偿标准)。深圳市唐瑛等[11]于 2002年利用宝安区社区卫生服务的现经营成本,以成本分析法进行研究,得出每人每年 15元的标准。之后云南、四川、浙江等地学者除了研究拨付标准外,更多的是从筹资机制上进行探讨。
在进行补偿标准研究后,相关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思考:之前所做的成本核算研究全都是基于 “现有财务运行支出”来测算的 (即核算的结果就是:“政府补偿”等于 “实际亏损”、“项目成本”等于 “运行支出”),或者是基于 “六位一体”功能来测算的,而这个 “六位一体”只是一个 “模糊的概念性界定”,并不是社区卫生服务的具体实施项目,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所有成本测算方法 (无论作业成本法还是项目成本法),其前提是:必须有明确的服务项目和服务流程,否则所有的成本测算结果只能是 “针对过去的亏损进行补偿”,并不能完全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依据。
有关学者就社区卫生服务的项目进行界定和研究。2005年许速等[12]就上海 2001年开始实施的 “预防保健经费项目管理”进行研究和分析;2006年天津、山东等地出台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项目服务包;在服务包的系统研究上,罗乐宣等[13]于 2004年通过 “项目界定法”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服务项目进行界定和研究,深圳市于 2007年制定了 “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包”,并于 2008年针对服务包项目,利用成本作业法和项目成本法进行了成本测算,得出人力成本为 48.49元·人-1·年-1的标准,这是全国范围内首次以服务包的形式对经费政策的拨付标准进行的较为系统的研究。
3.1.3.3 定向经费政策的研究 在社区卫生服务经费政策“定性”和 “定量”问题得到解决后,汪潮[14]、王丽芳[15]就当时的社区卫生服务经费政策与社区卫生服务质量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经费政策并不能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绩效充分挂钩,认为 “干多干少一个样”,并提出设想:如何运用经费分配的杠杆来提高社区卫生服务的绩效。之后,全国各地的学者与专家也就社区卫生服务经费如何合理分配以及如何通过绩效管理,建立公平、合理的经费分配制度提出了看法,其中上海于 2001年实施了预防保健经费的项目管理,对原来 “以每人口 15元包干”的经费拆分到每个大项目,即 “走了半步”,但也无法充分体现 “数量”与 “质量”的挂钩,存在着种种弊端[12,16]。
之后,社区卫生服务经费的研究转向 “定向”的研究,即 “怎么给、给到哪”,如何充分体现 “数量” 与 “质量 ”公平的经费分配政策研究,目前尚没有能够充分体现 “数量”与 “质量”充分挂钩的研究报告或政策出台,即目前的研究尚处于一个 “概念性研究”阶段,并未进入实施阶段或没有出台相关政策。
3.1.3.4 目前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经费政策存在的不足 一是原有公共卫生经费与社区卫生服务公共卫生经费有重叠,影响社区卫生服务经费的出台与额度:在此之前,疾病控制、妇幼保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治等均有专项经费,也包含了落实的经费,在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后,很多的公共卫生工作放到社区落实,这部分往往存在重叠,财政部门因此而推后社区经费的出台或额度不足。二是因为经费重叠导致社区公共卫生经费 “到位不到账”:从一个地区的整体财政额度来看,总体人均公共卫生虽然不足,但在地区公共卫生经费额度有限的情况下,落实到社区的公共卫生经费仍然掌握在原有机构的手上,存在截留的现象,导致 “到位不到账”的情况出现。
3.2 国内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考核管理体系的研究情况及特点
3.2.1 国内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考核管理体系的研究情况 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考核体系的研究最早是在 1996年,郭清[6]提出了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评估的大框架,鲍勇等[7]首次提出了社区卫生服务综合评估体系的框架、项目指标、评估标准架构以及相关的经费分配结合方法,之后全国各地学者也纷纷进行了指标体系方面的研究。在 2000年以前,主要的研究方向在 “工作质量”上居多,2003年以后,主要以 “经费与质量”的综合研究为主,但这种主要集中在考核评价指标与经费的挂钩为 “总质量与总经费额”的考核体系研究,而且很多的研究局限在细化指标、合理化指标上,没有将经费分配与细化指标进行充分融合。有关学者对绩效考核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提出设想[17-26]。
2008年,汪云等[27]提出了 “综合绩效”的设想,之后周树迪、张力、周长强等[28-30]利用层次分析法、系统论的观点提出了社区卫生服务的绩效管理评估体系的设想;与此同时,深圳、上海、江苏等地分别于 2007年和 2008年在评估框架上加入了满意度评估,这标志着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绩效管理体系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相关绩效评估政策也是伴随相关研究相继出台的,最早颁布实施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评估标准是在 1997年[31],深圳市出台了第一个社区卫生服务的绩效评估标准,共 11个大项目和237条评估标准;到 2010年,全国开展社区卫生服务的各个地区都颁布实施了社区卫生服务的绩效评估实施方案[5]。
3.2.2 国内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考核管理体系的特点及不足
3.2.2.1 规范和标准欠缺,导致绩效考核依据不足、评估标准权威性不够和多变 任何一种评估标准的制定,都需要有足够的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为基础和依据,全科医学和社区卫生服务在我国发展的时间比较短,至今我国在社区卫生服务及全科医学服务的规范上仍然存在较大的空缺而且不统一,目前全科医学仍然沿用或参照医院、专科医学服务的规范,因此在制定和应用社区卫生服务评估标准时,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导致了同一个地区多层评估标准,如:在社区卫生服务综合考核时是一套独立的评估标准,但每个公共卫生专业机构 (如妇幼保健机构、疾病控制机构等)又是一套不同的标准,并分别进行考核,这不但加重了不必要的负担,同时其最终的结果和权威性也受到了质疑[5,14],而且其评估结果在地区间没有可比性。
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全国的绩效评估标准差别不大,或者是基本统一的,因此他们可以利用各种信息化和网络技术进行全国或州际联评,并在地区间进行对比和结果互认[32]。但在我国,同一个地区仍然在使用多套标准,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服务规范的缺失和不统一。
3.2.2.2 多从内部机制的角度进行研究 一直以来,卫生系统的绩效考核都被当成是一个内部机制的问题,所以在社区卫生服务的绩效考核体系上,把社区卫生服务当成一个 “小系统”独立出来,大部分的研究基本上都围绕这个 “小系统”内部进行。没有充分考虑 “财政体制”和涉及财政经费分配与绩效考核挂钩的平衡与制约。
因此,国内的绩效考核体系研究的重点大多数集中在“细化指标”和 “优化指标”上,在细化指标中没有充分考虑“质量评估与结论挂钩”和 “数量和质量与经费挂钩”的综合考虑。最近几年来,有关学者也就此发表设想[5,15,27-28]。
3.2.2.3 指标体系多以 “定量指标”为主,与现实和公共卫生的定性目标有冲突 一是我国公共卫生项目的目标多以“定性指标”为主,如:在公共卫生项目的很多指标中,均以“达到什么程度以上为合格”等为目标;二是我国的考核指标体系惯用 “定量指标”为主,如:多数为 “得多少分”为评价结论,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
从项目管理的观点,在项目发展早期,应该以 “定性指标”为主,才有利于目标的进一步推进和提高,待完善到一定程度才考虑以 “定量指标”下结论。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评价指标和结论中,仍然较多的采用定性指标[33],而目前我国一开始就采用定量指标下结论往往会导致拔苗助长的情况发生。所以,现阶段在评价指标体系的各项细化指标中,我们应该多一些采用 “定性目标”,而少用 “定量指标”。
3.2.2.4 与经费分配结合不充分,不能充分体现公平与效率
目前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绩效考核结果是与社区卫生服务经费挂钩的,但这种挂钩是以 “总经费额度”与 “评估总结论”,如总分达到 90分以上给予全额经费。
社区卫生服务的项目多、复杂性高,没有充分考虑每个项目的 “服务数量”与 “服务质量”的结合,不能单从总体上与经费进行简单的挂钩。假设有两个人口数相等、但年龄结构不同的社区,如按目前社区公共卫生经费的拨付标准为:每人口每年 20元,如果一个社区一年的产妇有 200人,另一个社区一年的产妇只有 50人,很明显前一个社区的工作负荷大而出现工作质量下降,在这种经费标准下,后一个社区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这一项目上的得分要比前一个机构高,将导致“多做的反而经费少”。
因此,绩效考核必须与经费拨付充分融合,使经费拨付的参照细化到每一项数量上,并以 “数量 ×评价质量”的方法进行经费的拨付与绩效考核。
4 建议与思考
由于社区卫生服务的绩效管理具有提高服务质量、进行经费分配和评价目标三种目的,因此,从系统论的观点[34]和“公共卫生的系统思维论”观点[4],社区卫生服务的绩效管理体系不但是卫生系统机制问题,同时也是体制问题,所以必须与经费分配一并考虑和充分结合,才能建立起公平、高效的绩效管理体系,以经费和绩效管理这个杠杆促进社区公共卫生和社区基本医疗的实施[33,35],这个体系我们把它称为 “做蛋糕”、“分蛋糕”和 “切蛋糕”三个方面。
4.1 建立以社区服务人口为基数、以公共卫生项目和服务包的成本核算为标准,进行社区公共卫生经费项目总额的经费预算方案。在以服务包及各项公共卫生项目测算研究的基础上,以辖区服务人口为参照进行经费的总额预算,经费总额度 =服务包成本 ×服务人口数,如某辖区上年末总服务人口数为20万人、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包成本测算的结果为 “每人口每年 40元”,那么该辖区本年度社区公共卫生经费总额为:20万 ×40元 =800万元,这种以人口为参照进行社区公共卫生经费的预算方法叫 “做蛋糕”。
4.2 根据公共卫生项目的重要性及艰巨性,设立公共卫生项目的经费系数、难度系数,建立可灵活性调节的经费分配与绩效考核机制。在经费总额确定后,根据公共卫生项目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对每个项目进行设定 “经费系数”(即占经费的比例)、难度系数,确定每个项目的经费额度,即在大蛋糕下进行 “分蛋糕”。而且每年可根据当年公共卫生的情况进行经费系数的调整,以促进和加强重要公共卫生工作项目的完成。
4.3 细化和优化经费分配细则,以工作质量为评估结论与经费分配等级系数、以工作数量为经费分配参照,建立经费分配与绩效充分结合的社区卫生服务绩效管理体系。在每个服务包(公共卫生大项目)中,将每个公共卫生项目的每一项工作量都作为经费分配的参照,每细项目都有评价结论,并以此为“质量系数 ” (如 “优秀” 的经费系数为 1.2、 “优良 ” 为1.1,以此类推),将每个细项的质量和数量挂钩进行每个细项的经费分配,即 “切蛋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总经费为各个细项的经费累加。
4.4 设立 “标准服务量单位”(标准工作当量),对各项公共卫生项目的服务量进行标准当量转换标化,建立鼓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更多开展工作、提高满意度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绩效管理体系,以及多劳多得的机构内部激励机制。由于社区卫生服务项目众多,而且每个项目都有差别,这会对整体机构的绩效和内部绩效带来困难,所以,应该设立一个标准单位和中间转换单位,通过成本测算和基线调查,对不同项目进行转换,如:通过成本测算,1人次的常见病诊疗服务 =1.415人次的预防接种服务 =0.201人次的产后访视 =……,由此可以设立一个标准当量对各种服务进行转换,无论从各个机构间的绩效比较,还是机构内部个人的绩效评价,都可以有一个直观和简单的指标进行比较和分析。
4.5 根据社区卫生服务的实际情况和公共卫生目标,建立与公共卫生目标相适应、以定性评价结论为主的指标体系。对于指标体系的建立,应该与公共卫生项目的目标一致,并考虑当前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情况,可以采用五等级评价方法 (如:“优秀”、 “优良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对每个指标进行评价,整体质量评价参照各个项目的评价,逐级汇总为机构的最后评价。
4.6 社区卫生服务基本医疗经费的购买与补偿需要进一步明确。目前社区卫生服务的公共卫生项目大体上已经明确,但社区基本医疗方面的补偿和购买服务尚未明确,当前,我国社区卫生服务从总体上,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仍然占主要部分,从相关的服务数量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5],将社区基本医疗纳入公共卫生体系来考虑目前仍然在讨论之中。
1 USAID.Essential Service Delivery(ESD)Package[EB/OL].http://www.usaid.gov/bd/files/esd_package.pdf,1998-5-9.
2 Laura CL,Laura KK,Debra R,et al.Evaluability assessment to improve public health policies,programs,and practices[J].Annual Review of Public Health,2010,31:213-233.
3 (台湾)中央健康保险局.中华民国九十八年全民健康保险统计[R].台湾台北:中央健康保险局,2009.
4 Leischow SJ,Best A,Trochim,et al.Systems thinking to improve the public′s health[J].American Journal of Preventive Medicine,2008,35(2):196-203.
5 卢祖洵,李永斌.全国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重点联系城市试点工作进展、成效及值得关注的问题——基于基线调查和常规监测数据的综合分析 [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09,26(6):321-325.
6 郭清.社区卫生服务管理模式研究 [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1997,13(4):14-16.
7 鲍勇,龚幼龙.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综合评估体系、促进社区卫生服务健康持续发展 [J].中国卫生经济,1997,5(15):30-31.
8 顾杏元.关于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经济补偿机制的建议 [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1998,14(4):172-173.
9 李士雪.关于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一些思考 [J].中国卫生经济,1998,17(6):20-21.
10 蔡卓,程晓明,于跃.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补偿总量测算 [J].社区卫生保健,2002,1(2):79-81.
11 唐瑛,彭晓明,陈金华,等.深圳市宝安区社区卫生服务成本构成分析 [J].中国卫生经济,2004,23(4):20-21.
12 许速,倪政.闵行区预防保健经费项目化管理模式及效果分析[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9,23(10):2-4.
13 罗乐宣,周勇,张亮.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特征与项目界定原则 [J].医学与社会,2006,19(7):8-9.
14 汪潮.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考核管理的若干思考 [J].社区卫生保健,2009,8(5):338-339.
15 王丽芳.对台湾全科服务和社区卫生工作的考察及思考 [J].社区卫生管理,2010,9(3):168-169.
16 景琳,李玉强,张媚.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偿绩效评价机制研究 [J].中国卫生经济,2009,28(4):42-44.
17 周良荣,江鹏 .湖南省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成本测算与经费保障机制探讨 [J].中国卫生经济,2009,28(8):26-29.
18 杜丽君,水黎明 .宁波市江东区社区卫生服务经费绩效管理改革的成效分析 [J].中国全科医学,2009,12(18):1741-1743.
19 张媚,景琳,李玉强 .城市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偿资金绩效:基于投入与产出问题探讨 [J].中国卫生经济,2009,28(4):46-48.
20 曹丽娟,刘金宝,崔冰.乌鲁木齐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J].中国全科医学,2010,13(7):2089.
21 蒋汉武,王丽芬.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内容、运营、补偿及其考核的探讨 [J].中国卫生资源,2008,11(2):79-80.
22 张忠田.山东: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 [J].中国医学理论与实践,2007,17(11):1045.
23 熊昌娥.我国城市社区卫生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和分配机制的政策分析 [J].中国全科医学,2009,12(23):2176-2178.
24 张丽芳,党舅,刘玉华.我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绩效管理的探索[J].中国卫生经济,2009,28(12):55-57.
25 韩琤琤,冯亿,刘向红.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行绩效考核与分配制度对社区卫生机构激励的效果分析 [J].中国全科医学,2009,12(1):71-74.
26 江一民,杜兆辉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绩效评估体系构建与实施的探索 [J].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2008,21(3):147-149.
27 汪云,陈霞,程勇.社区卫生服务系统绩效评价框架构建 [J].医学与社会,2008,21(2):29-31.
28 周树迪,范莉,冯泽永.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社区卫生服务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J].社区医学杂志,2009,7(6):11-13.
29 张力,潘小红,张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建立的研究 [J].中国全科医学,2009,12(5):400-405.
30 周长强,李士雪.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评价概述 [J].中国全科医学,2007,10(19):1640-1642.
31 深圳市卫生局.关于进行社区健康服务年终评估的通知 (深卫发[1997]187号)[Z].广东深圳,1997年 9月.
32 Fiscella K,Geiger HJ.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for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J].Health Aff,2006,25:405-412.
33 Bar YY.Improving theeffectiveness of health care and public health:a multiscale complex systems analysis[J].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06,96(3):459-466.
34 Peter Checkland[英].系统论的思想与实践 [M].左晓斯,史然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35 Doran T,Fullwood C,GravelleH.Pay-for-performanceprograms in family practices in the United Kingdom[J].NEJM,2006,355:375-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