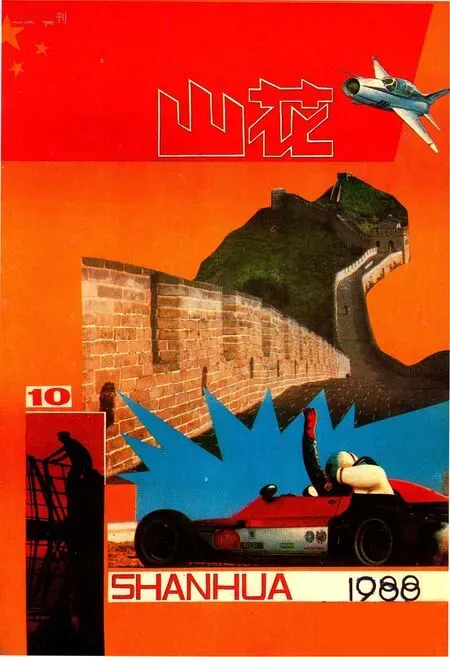生活与自然的诗意寻觅
——诗人金铃子访谈
张德明 金铃子
生活与自然的诗意寻觅
——诗人金铃子访谈
张德明 金铃子

金铃子,70后,原名蒋信琳,曾用笔名信琳君,籍贯重庆,家居山水之间。80年代末期开始发表诗歌,曾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大家》、《作品》、《散文诗》等纯文学刊物发表诗歌和随笔。作品入选多种诗歌年选,诗歌代表作《越人歌》全诗371行入选《2010年中国诗歌精选》(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散文诗代表作《当太阳普照》32章,前10章选入《2009年中国散文诗精选》。著有诗集《奢华倾城》、《香水》。曾参加第24届青春诗会,获2008中国年度先锋诗歌奖,第二届徐志摩诗歌奖,第七届台湾薛林青年诗奖。
生命的记忆
张德明:你的诗歌里面常常提到故乡,讲讲你对家乡的印象吧!说说那里的山光水色,一草一木,以及那片土地上令你难以忘怀的亲朋好友。
金铃子:海德格尔说:归乡,是诗人的天职。一个诗人若是对自己的故乡都不加以礼赞,那么,这个诗人是不成熟或者不合格的。我的故乡是很美的,比我的诗里的故乡要美得多。诗人的故乡除了山水、炊烟,更多的是一个人童年的记忆。在城市居久了,对山更是眷恋不已。山水诗文之乐,必是人生一桩快事。前些日子与友说到陶诗,称他为中国诗歌第一人。今越读越感到老陶遥不可及。这两日,我仔细翻读陶诗,觉得他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越发喜欢。这个时代的确不会有陶渊明了,想起《桃花源记》里的“不足为外人道也。”心里不免怅怅的。陶老不知他的精神家园增加了好多人的怅惘痛苦呢。好多年没回故乡了。想起来一切都那么的灿烂绚丽,云净天空,娇美而空灵。与大山的感情是最高尚、最甜蜜的感情。我对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有一种深深的遗憾和同情。心里想的是:他们怎么知道山的乐趣呢?他们不知道山的乐趣,又怎么知道我的乐趣呢。因此,他们是不知道我的。
作诗前,没有一次思绪不是先回到故乡那片山坡。无所事事,没教养,粗鲁,说大话,偷桃花,与爷爷一起想念古人。我的诗歌道路始于那片开满杜鹃花的山坡,一个只有风声水起的孤独的中午。只要我开始写诗时,我发现,我已经在那里了。
张德明:你在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诗歌?是出于什么原因而爱上诗歌的?诗歌给你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金铃子:我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爷爷是个饱读诗书的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读到了一些古典的格律诗词。很小就开始模写,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半临摹半创作了许多格律诗词。后来读到一些现代诗,我认为现代诗是最美的文学式样,我被诗歌所传达的情景、情绪所感染,无比的钟爱。现代诗歌创作是我精神释放的通道,是其他生活方式无法取代的。
张德明:第一次投稿大概是什么时候?处女作又是何时发表的?拿到第一笔稿费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金铃子:八十年代末期,我就开始了诗歌的书写。相对新诗,我更爱旧诗。很累很辛苦的时候,读一两首感觉恢复了生气;很快乐的时候,读它更是觉得美妙无比。开始填词,像所有初生牛犊一样,直接向诗刊投稿,也总是石沉大海。我的处女作发表在1992年的《诗歌报》,第几期我记不住了,写些什么我也完全记不得了。因为编辑把“琳”写成“陵”,我又不愿意去证明我是我,就没有取,15元稿费,汇款单现在还收藏着。我对诗歌的感情一直是偷偷的、涩涩的感情,不管是90年代初期,还是现在,除开与圈里的人说起诗歌。很难得与生活中的朋友说起这些。这就是我对诗歌的情感,是独享或者是肃静的,是一想着它就幸福的情感。
张德明:你于2008年参加诗刊社举办的第24届青春诗会,谈谈你参加诗会的感受吧!你觉得参加这次诗会对你的诗歌创作具有怎样的意义?
金铃子:参加青春诗会是每个青年诗人所向往的。我有幸参加第24届青春诗会,一方面是诗歌前辈对我作品的肯定;另一方面也是对我创作的激励。我想青春诗会其实就是青年诗人的加油站。每一个荣誉的后面都是压力,我离我心中真正的诗歌还远着呢。
新诗与传统
张德明:你的诗歌里边有比较浓郁的古典诗意氛围,这说明你对古典文学的学习较深入。你如何看待新诗与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能谈谈哪些古典文学作品对你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启发吗?
金铃子:我认同这个说法,中国新诗的传统既独立,又关联着整个中国从古以来的诗歌传统。或许可以说,催生中国新诗的,是闻一多所说的“中西艺术的结婚”。西方诗歌是父亲,古典诗歌是母亲。我们从母亲那里得到奶水。诗经和楚辞,李白和杜甫,仍然在滋养着今天的诗人。我愿意将新诗看作是整个中国诗歌传统在现代的延续,新诗是这个中国诗歌大传统内部的小传统,是中国诗歌这一伟大传统最晚近的转型。新诗的位置与古体诗、近体诗、词和曲的位置一样,其相对独立的发展推进着整个中国诗的发展。新诗是现代汉语取代古代汉语,但不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取代旧的语言体系,所以,新诗的传统并不能独立而自足。如果说我们今天诗人们的感性形式已经与古典诗人差别巨大,我们却仍然使用着古人赋予我们的文字和词汇,这些会像基因一样刻录在我们身上。
我是用汉语写作的中国诗人,我所汲取的营养是中国的,也就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营养。一个不懂传统文学或者不读古典诗词的诗人在我看来是不可信的,或者不可理喻的。传统的中心词是“传”,中国新诗的时间很短,还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是新诗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审美取向一直没有离开传统的审美取向。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一个民族自身的特点,把好的长于其他民族的优点“传”下去。唐诗宋词是我的基础课,而对我帮助更大的是屈原,他的宏大与内敛,深邃与张扬都是我喜欢并值得我终身学习的。
张德明:“五四”以来,西方诗歌尤其是翻译诗歌一直是中国诗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诗的传统。在你的创作过程中,哪些西方诗人对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你认为当代诗人应如何向西方学习?
金铃子:学习西方诗歌是近当代诗人的必修课,我不认为这会构成中国新诗的传统。借鉴是学习,模仿也是学习。学习是拿来主义,但是不可能取代本民族的传统。我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已有五百年,而欧美诗歌进入中国不到百年。
西方诗歌的抒情方式是中国诗人应该好好学习的。中国传统的诗歌大多内敛而羞涩,内敛和羞涩往往会遮蔽诗歌的饱满。我喜欢拜伦和雪莱的奔放、直抒胸臆的表达。中国人说一声“我爱你”一定是在无人的角落,而拜伦和雪莱可以在广场高呼。
诗人没有不敢说的话,没有不可表达的情绪。如果总有难以言说的隐秘,诗必然会受到伤害。诗人表达隐秘,可以借用修辞手段,但能不使用修辞的诗人才是让我敬仰的诗人。
张德明:在近百年的新诗发展史中,诞生了许多诗人。你比较喜欢哪些诗人的诗歌?你在诗歌创作中曾受过哪些现代诗人的影响?
金铃子:在中国近百年的新诗史上,我很喜欢穆旦。穆旦的诗读几遍以后,我甚至觉得我的诗歌表达是无力的。我想,我还年轻,还有许多学习的时间,我不会因为读到好诗而给自己设置障碍。恰恰相反,好诗使我兴奋,更能激发我创作的欲望。
张德明:有时候,一个诗人周围的朋友对他(她)的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新时期以来,重庆一直是新诗创作和研究的重镇,据说你身边的诗人朋友很多,你觉得哪些诗人朋友对你的诗歌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和触动?
金铃子:重庆诗人是团结的,是相互借鉴和学习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别人无法替代的优点,都有让我学习和借鉴的部分。虽然诗歌创作是个体劳动,但是创作环境和氛围是个体劳动能否获得最佳成果的重要因素。古人说:看你的朋友就知道你如何。重庆的诗人们就是这样一个互助、相互激励的群体。我非常喜欢诗人李元胜说的这句话:“我们需要同样的营养,我们需要确知生存的处境和真相,我们还需要相互竞争、照耀和鼓舞,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短暂的生存中更加生气勃勃。”
创作与自我
张德明:有人说,小说家需要丰富的生活经历,而诗人更需要天分和灵感。你同意这种观点吗?你觉得你的诗歌与你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关系?
金铃子: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生活的反映,小说和诗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诗歌要凝练,小说要铺陈,但殊途同归。
任何人的诗歌作品都是生活经历与个体经验的反映,我的也不例外。
张德明:据说你喜欢旅游,喜欢大自然。能谈谈旅游经历对你诗歌创作的帮助吗?
金铃子:一个优秀的诗人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有丰富的阅历和多种生活体验。大自然蕴藏着丰富的诗意,向大自然学习是每个诗人的必修课。我是个青年习作者,正在向优秀的诗人学习,正在努力完成优秀诗人的必修课。
张德明:诗歌中的“我”虽然并非作者本人,但一定与作者有着非常大的联系。你如何看待诗歌中的这个抒情主体?写作中你是否有意识地将诗中的“我”与现实中的“我”区别开来?
金铃子:我认为任何一首诗的抒情主人公一定是作者本人。没有“我”在场,诗歌的情感会流于虚假,所以,诗里首首有“我”,“我”就应该是我。一个没有“我”的旁观者,我不相信会写出有感染力的诗。
张德明:你一般在什么时候写作?你怎样看待诗歌创作中的“灵感”?
金铃子:什么时候写作这是个问题,关键是写什么更是一个问题。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吧。
灵感这东西,我认为确实存在,没有灵感,难以写出好作品。有朋友说灵感是上帝伸出手来抓住你,上帝之手不是灵感。对,上帝伸出来抓住你的手是灵感,关键问题是“抓住”。既然是上帝之手,是神的启示,那么它是不会凋零的,它是存在的。那么它在哪里?柏拉图说:“无论是谁。如果没有诗人的狂热而去瞧诗神的门,他尽管有极高的艺术手腕,诗神永远不让他升堂入室。”其实,灵感是诗人情感经验的瞬间爆发。就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就是最感人的爆发。
活动与颁奖
张德明:最近一些年来,每年国内举办的大小诗会非常多,诗歌活动非常频繁,你喜欢参加诗歌活动吗?你觉得诗歌活动对诗人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金铃子:我会有选择地参加一些诗歌活动。诗歌活动是诗人交流的场合。但我认为诗歌活动不能代替诗歌艺术的发展、探究。如果把诗歌活动搞成诗歌事件,我就不喜欢了。
张德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你连续获得了几个诗歌大奖,当时还有人说你是获奖专业户。最近两年,我感觉你在有意回避一些诗歌大奖赛。你能谈谈这样做的原因吗?当代诗歌奖项很多,你觉得这对诗歌的发展能否起到促进作用?
金铃子:获奖总是一件高兴的事。但是目前的诗歌奖项五花八门,让人觉得不够庄重、严肃,就不好了。虽然,我获过一些奖,但没有哪一项是我积极准备去得的。我更喜爱老诗人傅天琳说的:奖项就是天上掉馅饼。一个诗人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荣誉背后是压力。我认为真正的奖是人口皆碑,是对诗歌的责任。
张德明:现在诗歌刊物很多,不少刊物也在不断扩容,这对促进诗歌发展来说应该说是好事。但刊物一多,发表太容易,而且一个诗人一旦有了些影响,刊物的约稿也不断。你觉得这种现象对一个诗人的创作到底有利还是有弊?诗人应该如何与创作中的浮躁作斗争?
金铃子:刊物多了,对文学爱好者是好事。就像花园多了,各种花都有展示自己风姿的舞台。但是诗人最难得的是自审。一个诗人的影响再大也是有范围的。小圈子的“影响”未必真有影响。中国现在有十几亿人,知道牛汉的人不会超过三亿人。你能说牛汉没有影响吗?诗人愿意扎堆,就是因为诗人在人群中是少数人。在少数人中有点知名度,还不能说是影响吧!浮躁是社会的弊病,诗人是社会中的自然人,染病是正常的,但这种病只能自己医治。若是一个诗人认不清自己是谁,称不出自身的重量,那就无药可治了。
张德明:互联网出现后,诗歌创作一度显得很活跃。有人从中看到了新诗不断走向繁兴的希望,也有人认为网络会使诗人走向浮躁的误区。你如何看待网络与诗歌创作的关系问题?
金铃子:网络给我们表达自由带来了释放。而诗歌是一个心灵自由表达的产物。所以,诗歌写作和网络自由表达有高度的契合。网络的开放性使得人们在袒露心扉时不再娇羞。网络既是平台也是舞台,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平台或者舞台上展示自己。认为网络会使诗人走向浮躁,是一种杞人忧天的想法,诗人是否浮躁与网络没有什么关系。浮躁是来自于本我,而非外界。尽管网络上诗歌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但是我相信泥沙下面一定埋藏着闪光的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