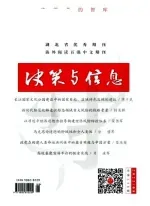东欧剧变二十年前后
文/张维为
二十年前的东欧
中国人关心东欧,因为东欧国家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东欧的剧变是怎么发生的?东欧剧变后的情况怎么样?东欧与今天的中国比较谁更胜一筹?我二十年前去过东欧,二十年后又去过不少东欧国家,所以有一些实地观感和思考。
1989年的东欧剧变震惊了世界,当时我正好有个机会去维也纳开会,便顺道走访了近在咫尺的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捷克和斯洛伐克尚未分家)和匈牙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年11月的一个夜晚,我从维也纳客运总站乘捷克的大客车启程,穿过维也纳灯光璀璨的繁华街道,半小时后就抵达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边防哨所。进入了东欧,进入了布拉迪斯拉发,但从这一刻开始,我发现路灯暗了、道路窄了、人的穿着土气了,这种强烈的反差,至今还记忆犹新。
布拉迪斯拉发市是斯洛伐克的首都,它的汽车总站很像中国过去的县城长途车站,灯光昏暗,厕所污浊。在这里,我第一次发现欧洲还有这么多看上去如此贫穷的人,十来个衣着不整的斯洛伐克男人挤在空气混浊的餐厅里喝土豆汤,啃黑面包,他们一边吃,一边目不斜视地盯着饭厅的黑白电视,并不时跟着电视节目激动地说话。电视里播放着反政府示威游行,还有此起彼伏的口号:“要人权”,“要自由”,“要戈尔巴乔夫”。第二天,我获悉捷共领导人已经辞职,新的领导人开始了与反对派“七七宪章”代表哈维尔的谈判。
布拉迪斯拉发是一座毫无生气的城市,到处是灰色单调的“斯大林式”建筑,市中心主要街道的商店空空如也。我口渴了,想买瓶饮料也买不到,走了几条街,最后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铺子买了一瓶汽水,但细看了一下,里面竟浮着一层霉。女营业员见状有点不好意思,马上给我换了一瓶,“这瓶应该,应该,没有问题。”口气中还有点犹豫。当时苏联和整个东欧轻、重工业大都严重失衡,消费品匮乏,而且质量低劣。
1986年我曾随一位中国领导人访问过罗马尼亚,住在罗马尼亚国宾馆。但国宾馆提供的肥皂不起任何泡沫,屋里的电视机是罗马尼亚自己生产的,只能“雾里看花”,声音也会突然消失,然后得拍它几下,才有声响。在布加勒斯特最繁华的百货商店,我看到人们排着长队购买上海生产的美加净牙膏,街上跑的是罗马尼亚和东德生产的甲壳虫小汽车。我1990年还访问过解体前的苏联,当时苏联的市场比1986年的罗马尼亚还要萧条。
这种局面使苏联和东欧的老百姓怨声载道,也给了西方很大的心理和话语优势。我曾看过一部美国人当时拍的纪录片。一个美国记者问苏共宣传部门的负责人:“美国的制度为人民提供了高水平的物质生活,你们的制度能够提供吗?”那位苏联宣传干部哑语了,不知如何回答。当时的苏联和东欧都有很多关于物资匮乏的政治笑话。其中一个是这样说的:一天,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对妻子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妻子说:“没有油啊。”“那就煮!”“没锅。”“那就烤!”“没柴。”伊万气得把鱼扔回河里。那鱼在水里游了一会儿,跳跃了起来,激动地高呼:“勃列日涅夫同志万岁!”
二十年前的东欧国家,虽然有“铁饭碗”和各种福利制度(现在不少人怀念那个时代),但整体物质生活水平和经济竞争力明显低于西方。反对派人士也利用这种局面不断地提出激进政治变革口号,波兰团结工会的智囊人物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就说过:“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是把‘要面包与要自由’结合在一起,把政治要求和物质要求结合在一起的。”
三天后我坐火车抵达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布达佩斯火车站是一座很有气势的古典建筑,人群熙攘,商铺热闹,小贩在吆喝,倒卖外币的“黄牛”很多,还有老头老太拉你租他们的公寓,这种鲜活的景象在当时的东欧很另类,说明这里的经济生活更加自由。其实匈牙利是东欧国家中最早推行经济改革的国家之一。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发,大批示威者冲击党政部门,纳吉总理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苏联随后出兵镇压,44岁的卡达尔出任匈共最高领导人,但遭本国许多老百姓的责难,说他是“卖国贼”。卡达尔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不动声色地推动了许多改善民生的改革措施,扭转了他前任拉克希奉行的极左政策。到了1970年代,匈牙利似乎已经由丑小鸭变成了金凤凰,成了东欧为数不多的相对繁荣的国度,布达佩斯也被誉为“东方小巴黎”。
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改革已停滞不前,加上持续的能源危机和过分举债等原因,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党内外对卡达尔的批评指责日益增多。1986年中国外长吴学谦访问过匈牙利,我当时在外交部工作,曾听过吴外长本人私下聊过他会见卡达尔的情景。那天,吴学谦向卡达尔转达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问候,并谈到卡达尔受命于危难之际,领导匈牙利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听后显然有点激动,”吴学谦说,“卡达尔在他最困难的1956年和1957年两次访华,见过毛主席、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他和中国的关系非同一般。”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十月事件爆发,布达佩斯市中心的斯大林像被拉倒
1987年10月卡达尔再次访华,邓小平和卡达尔两人一直携着手,慢慢步入中南海的会见厅,这对邓小平同志也是一种不寻常的举动,可见他们之间的相互敬重。邓小平与卡达尔的谈话很有针对性,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邓小平似乎已经预感到东欧要出事,他告诫卡达尔“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谈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强调“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并说我们“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卡达尔本人赞成邓小平的观点,但他党内的激进派与他意见截然相反,他们主张匈牙利立即推动“彻底的政治改革”,把匈牙利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室”。
在1988年5月的党代会上,卡达尔与党内激进派就政治改革问题进行了一次激烈辩论。他坚持必须在现有的体制内进行改革,而不是推倒重来。但他身体状况已欠佳,整个苏联东欧的大环境对他也非常不利,匈牙利党内分裂愈演愈烈。卡达尔本人身心憔悴,1989年5月终因健康原因辞职,7月6日与世长辞,享年77岁。

匈牙利前社会主义工人党主席、前总理卡达尔
在激进派的主导下,匈牙利党中央通过了一个比较激进的纲领,提出“国家社会主义使匈牙利陷入危机,要尽快改变模式”,匈牙利“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已经不可避免”。与波兰、捷克不一样,匈牙利没有像团结工会、“七七宪章”那样强大的反对派组织,也没有像瓦文萨、哈维尔那样影响力较大的反对派头面人物。匈牙利党是自己内部先分裂,然后分裂出来的派系与党外势力合作,最后瓦解了政权。
晚上我和H君夫妇共进晚餐,H君曾在日内瓦大学进修政治学,我们是老相识。他们夫妇现在布达佩斯一所大学任教。H君告诉我:“匈牙利已经改了国名,‘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中已经去掉了‘人民’两字,国旗上也没有红星了,我们的宪法也已修改,实行了多党制。”他还非常兴奋地告诉我:“我们一个月内,已经有了50多个政党登记参政。”他谈到政治变革的必要性:“现在匈牙利经济一路下滑,一个人打两份工才能生活,大家都认为经济改革已经走入绝境,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带给人民希望。”他夫人补充说:“我们匈牙利其实一直比其他东欧国家自由,我们几乎人人都有护照,只要有钱,随时可以出国,但我们珍视国家的独立,现在苏联军队还占领着我们国家。”H君点头:“他们必须滚回去,这是我们的国家。”这使我想起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他们也谈了对卡达尔的看法,H君不容置疑地说,“卡达尔落伍了,他讲的话都是老生常谈。匈牙利需要的是戈尔巴乔夫这样具有新思维的领导人,或者是捷克哈维尔这样的自由派领导人,否则人民看不到希望。”
东欧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有诸多原因:这些国家传统上受西方文化、政治和宗教的影响很大;他们的政权在自己国内的根基较浅,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几乎都是“二战”后靠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扶持上台的;很多东欧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还被苏联占领和控制着,还没有真正取得独立,波罗的海三国就是到了“二战”时才被苏联吞并的。苏联很多做法也使东欧小国耿耿于怀。例如,捷克共产党曾考虑接受美国“二战”后提出的“马歇尔计划”,但遭到了斯大林的严厉批评;1968年苏联大举入侵捷克;匈牙利在“二战”时站到了纳粹德国一边,后来遭到了苏联的强烈报复。匈牙利一位政府高官曾对我说:70多万匈牙利人被流放到苏联西伯利亚,其中30万有去无回。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可靠,但民族感情之对立是显而易见的。
东欧国家后来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改革都是断断续续的,即便是走得最远的匈牙利也未能突破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个意识形态的紧箍咒,结果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引起了本国老百姓的强烈不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变,从物资严重匮乏到市场空前繁荣和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善,其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邓小平说过:不发展经济,不搞改革开放,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这确实是东欧走上这条死路的一个主要原因。随着经济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再加上西方强大的话语攻势,这些国家的执政者自己都丧失了自信。到了1980年代中期,连控制东欧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自己也被西方话语征服,结果苏联的解体和东欧政权的垮台,就成为意料中的事了。
今日的东欧
东欧剧变至今已经二十年了。这些国家现状怎么样?人民的生活是否更好了?他们的民主转型效果如何?这些也是我关心的问题。从2000年开始,我陆陆续续地走访了近十个东欧国家,各种感受一言难尽。东欧国家中,阿尔巴尼亚和摩尔多瓦还相当落后,只能算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上采用了西方的制度,经济上还是发展不起来,这两个国家至今还属于欧洲最穷的国家。
东欧其他国家的起点要高得多。加入欧盟的八个东欧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中,大部分在1989年以前已属于中等工业化国家,其特点是农村人口都低于30%(至2007年,中国农村人口仍为56%),其中最富裕的是捷克、匈牙利,比较穷的是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
我也只去了这些国家的首都,所以很难和中国作一个全面的比较。总体上看,这些城市的商业也算繁华,欧盟的各种援助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中产阶级都有一定的规模。但如果拿这些城市和上海等中国的一线城市进行比较的话,我觉得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商业繁华程度、消费与时尚、新建筑的规模、式样和质量以及人的精神面貌方面,都落后不少。像华沙、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布拉迪斯拉发、索非亚、里加等城市与上海的差距还很大。
东欧城市有一个特点,漂亮的建筑几乎都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留下来的古典建筑,而新建的民居和城市改造的规模远远小于中国发达板块的任何一个城市。当然这也可能说明他们在旧的体制下已经基本解决了住房问题,而中国过去欠账太多,所以城市改造规模之大,新的民居之多,质量和外观之好,都是东欧这些城市所无法比拟的。
总体来看,三十多年前,中国与东欧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但是通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这个距离已明显地缩小了。从我走过的东欧城市来看,二十年前,像华沙、布达佩斯这样的城市领先上海至少十年,但现在我的感觉是他们落后上海至少十年。总体上,我认为我们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东欧的平均水平。但要使整个中国达到东欧今天的水平,还需更长的时间。
我们与人家差距最大的是市民文化这一块。从办事排队到开车讲规矩等,人家做得还是比我们好。东欧国家的市民文化形成历史比我们长,特别是像布拉格、布达佩斯、里加等城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有相当庞大的中产阶级,已建有大批高级公寓、别墅和咖啡馆,市民文化的底蕴迄今犹在。我记得捷克著名诗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在他的名著《世界美如斯》中,就回忆过自己1920年居住过的布拉格日什科夫区,回忆那里咖啡飘香、绅士互相脱帽敬礼、盛装舞会等贵族的传统。欧洲贫富差距当时也很大,达官贵人也遭人忌恨,但贵族的生活习俗和方式却一直被普通人模仿,这是欧洲市民文化比较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贵族留下的古堡、庄园、花园、艺术品至今还是这些国家的文化精品,这种源远流长的市民文化,我们要赶上真不容易。
重返匈牙利
近二十年后的2008年8月,我又有机会沿着老路从维也纳坐大客车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访问。维也纳还是那么雍容大气,只是机场显得陈旧了,刚从北京机场过来,一下子还真不习惯,真有点到了第三世界的感觉。机场的商店还是1980年代的装潢。红黄绿标记的三家出租车公司在机场拥有柜台,一字排开,里面的工作人员做出夸张的表情,争相拉你坐他们的车。二十年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维也纳夜景,今天看来是如此平淡,跟上海璀璨迷人的夜景相差太远了。西欧的特点是几十年不变,反正是发达国家了,可以固步自封了;中国的特点是一直马不停蹄地追赶发达国家,整个国家面貌日新月异。
我们的大客车很快就进入了斯洛伐克,现在斯洛伐克已是欧盟成员,所以不再设边界关卡,一块矗立在高速公路旁的“欢迎来到斯洛伐克”的英文标牌提醒我们,车子已进入了斯洛伐克。这些年来,斯洛伐克因为劳动力便宜,又加入了欧盟,吸引了不少外资。布拉迪斯拉发市的老城大有改观,修复了大片的步行商业街,很多名牌精品店纷纷入驻,但人气不旺。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布拉迪斯拉发火车站竟然还是和二十年前一样的简陋,连个像样的候车室都没有,旅客大都席地而坐。车站也没有一个像样的餐馆,只有两家夫妻店,七八张摇摇晃晃的饭桌,几十把塑料椅子,经营着不敢恭维的斯洛伐克匹萨饼和俄罗斯罗宋汤。真不知道这个当时人均吸引外资最多的东欧国家怎么不投资改造一下火车站、汽车站之类的基础设施。
斯洛伐克虽然已是欧盟成员国,但2005年选出的新政府很令欧盟头疼。因为新内阁包括了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可以公开谩骂该国的匈牙利和吉卜赛两个主要少数民族,骂这些人“丑陋、罗圈腿,是骑在令人可憎的马上的疑似蒙古症患者”。斯洛伐克前副总理伊万·密克罗什对我说:“亏得上面有个欧盟,使这些激进分子在国家政策方面还不敢走得太远,否则麻烦大了。”密克罗什曾在斯洛伐克推动了不少市场化改革方案,在西方广受好评,但2005年他的政党在大选中被击败。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搞改革,最好就是只做不说,先说了,最后什么也做不成,还被人骂。”

布达佩斯火车站
火车开了3个小时,我又来到了久违的布达佩斯火车站。但一下车,我最大的感觉也是这里与二十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些热闹的小铺子还在,出售各种廉价的旅游纪念品、箱包、打火机、DVD之类;那些兑换外币的私人钱庄也在,有十来个,边上还有几个“黄牛”,但人数比二十年前少;那些出租房屋的老头老太还在,惟一的变化是一位老头用中文在吆喝:“房间、房间。”我后来还抽空去了布达佩斯的劳克西商业大街,商品倒是不少,但从物业装潢到服务设施,都陈旧了,与中国大都市的繁华和时尚差距甚大。但布达佩斯的城市布局雍容大气,古典建筑端庄典雅,绿树成荫的宽阔街道令人赏心悦目,登上多瑙河边的城堡山眺望,更是令人心旷神怡,全城的景色一览无余。
我又见到了老朋友H君夫妇。他们约我在繁华的瓦茨大街终点的Gerbeaud咖啡馆见面,这是布达佩斯最精致的咖啡馆,家具都是古色古香的。他们夫妇这次给我最大的惊讶是,二十年前的政治激情荡然无存。我们聊起了这二十年匈牙利的变迁,H君说:“一言难尽,有得有失,但感觉有点苦,就像这个咖啡。”他接着说:“苦,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变革是如此不易,你说我们政治独立了吗?我们现在被北约控制了……我们的经济现在都被外国人控制了。”
我们聊到了戈尔巴乔夫和卡达尔。H夫人指着窗外热闹的瓦茨大街对我说,1986年6月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在他们夫妇的陪同下曾在这条街上散步,这里眼花缭乱的广告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使戈尔巴乔夫很惊讶。随后他多次表示苏联要借鉴匈牙利的经验来解决苏联的经济问题。现在看来他有点浮夸,不如卡达尔那么踏实。我知道现在匈牙利有不少人怀念卡达尔。H夫人说:“卡达尔那个时代,大家都有工作,全民医疗保险,还有带薪休假,我们的生活也比周边的国家都好。”

布达佩斯的瓦茨大街
她还说:“卡达尔非常廉洁,连他的政敌都不否认这一点,这与现在的权贵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一代的人做事有原则。卡达尔在1950年代曾被诬告而投入监狱长达四年,他夫人也受牵连,被开除党籍,人无居所,后来布达佩斯一个普通百姓家庭收留了她,卡达尔夫妇至死都和这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H君此时插话:“你知道我们现在怎么形容我国的政客吗?这些人见面互相打招呼,已经不再说‘你好’,而是说‘你是千万富翁了吗?’”想起H君当年对卡达尔的不满,我此时也只能唏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台湾地区民主化也二十年了,民望最高的还是亲民强势的领导人蒋经国,南斯拉夫各国也民主化二十多年了,但威信最高的政治人物还是意志如钢的铁托,历史是公道的,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
我们聊到匈牙利的选举政治,H君坦承:“看来我们当时是天真了,以为只要举行自由选举,一切都会变好。但二十年过去了,左派右派都执政过了,都是政客,没有出现过政治家。整个二十年东欧都没有产生过政治家,这是欧盟的结论。”他问我:“你听说过我们‘骗子总理’的事情吗?”我点头,这是指匈牙利总理久尔恰尼2007年5月在执政党一次内部讲话中说:“我们搞砸了……在我们执政的四年里,政府拿不出引以为傲的业绩。我们该如何向选民交代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保证使这个秘密在大选之前不被泄漏出去。过去两年里,我们一直在撒谎。”这段话后来在网上被披露出来,匈牙利举国哗然,随后就是二十年来匈牙利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和警民冲突。
“坦率地说,我现在很悲观,”H君说,“我们不是在‘好人’与‘坏人’之间作选择,而是在‘坏人’与‘更坏的人’之间作选择,他们之间争权夺利,分裂了整个社会。”他还引用了匈牙利学者海斯勒的评论:匈牙利人缺乏“政治文化和妥协的智慧”,所以今天的匈牙利是“一个深深分裂的社会”。我认识不少东欧朋友,他们原来都以为,只要政治制度一变,一切都会变好,但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革命是浪漫的、兴奋的、热血沸腾的、充满希望的,但革命后人们突然发现旧的习惯和行为方式依然根深蒂固,一切宛如昨天,甚至更糟。
我还见了匈牙利一位资深的政治学者,他的谈话更直率:“你看,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吗?匈牙利一半的资产卖给了外国人,还有一半给贪污了。什么是‘休克疗法’?那就是把能卖的公司都卖给外国公司了,最大的石油公司卖给了美国人,美国人又把它卖给了德国人,现在德国人又把它卖给了俄罗斯人。今天控制我们经济的主要是德国人,连媒体也都给德国公司控制了。你大概不能想像,我们的出租车公司也卖给外国人了,一家英国公司,还有一家土耳其公司,他们垄断了价格。”我这些天常坐出租车,注意到这里出租车价格贵得有点离谱,接近瑞士。
他给我展示了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作的最新民调结果:2008年62%的匈牙利人认为现在的生活不如二十年前的卡达尔时期,2001年时,这个比例是53%。今天只有14%的人认为现在是“最幸福的时期”,而60%的人认为卡达尔时期是“最幸福的时期”。他带有感叹地说:“很多东西,只有失去了以后才知道珍贵,就像空气和水,一旦没有了,才知道它们是多么的珍贵。现在少部分人的生活确实比过去好了,但大部分人生活得更糟了。物价上涨太快,货币贬值太多,工资涨了五六倍,但煤气、水、公共交通等都涨了20倍到100倍,受害最大的是我们这些拿退休金的老年人,退休金根本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还有就是年轻人,匈牙利就业机会太少,失业率已达10%。”
早在1980年代中期,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就积累了不少经验,当时中国派出不少代表团考察匈牙利经济改革的情况。我问这位学者:“如果坚持当时卡达尔的改革路线的话,匈牙利能否走出一条更好的路?”他说:“匈牙利本来的改革模式很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也许会走出一条类似中国的渐进改革的成功之路。但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不喜欢,他们不想让这种改革获得成功。而我们精英阶层完全跟他们走,放弃了渐进改革,转向了激进革命和彻底的私有化,最后把能卖的公司,包括银行,统统卖给了外国人,我们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了。”他叹了一声。匈牙利中央银行前行长也对我说:“我们把自来水公司卖给了法国公司,本来期待他们能投资开发我们的矿泉水资源,结果他们却在匈牙利推销法国的‘依云’矿泉水。”不过他也告诉我:“不能夸大卡达尔时期的繁荣,那是靠借外债维持的,结果弄得匈牙利债台高筑,新政权上台后只能靠变卖国有资产来还债。”
一位匈牙利朋友还与我谈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尽管制度变了,但旧制度的许多东西仍在运作,特别是原来按照前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安全系统至今在匈牙利,在许多东欧国家仍然影响巨大。“旧安全系统的人与政党、政客、黑社会联系密切,表面是多党制度、媒体自由,实质上是这些人继续控制着政治经济等各种资源,继续进行各种利益的私下交换。独立的司法体系根本没有建立,也没有一支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任人惟亲的现象广泛存在。”连《经济学人》杂志也载文感叹匈牙利过去的二十年是“令人失望的二十年”。
东欧的“两个激进”
东欧的变革可以用“两个激进”来概括:政治上激进转型,由原来的共产党体制迅速转变为西方式的多党制;经济上采用激进的“休克疗法”,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迅速地转向私有化、市场化。其核心也是一个梦:只要进行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些国家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所有的问题。结果政治激进带来的是政治参与突然爆炸和持续混乱,一个新体制从建立到良好运作谈何容易。“休克疗法”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有时高达2000%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失业人数剧增。匈牙利还是受灾较轻的,因为匈牙利在卡达尔时期就尝试了不少改革,一般老百姓对市场并不陌生。但对于多数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等于是一场浩劫,导致了既无政府干预又无市场制度的混乱状况,为非法掠夺提供了可能。使一批原来的官员获得了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的机会,也使腐败(特别是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不能说大部分东欧人都想回到过去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也有很多问题,更何况世界上愿意自己国家历史倒退二十年的人恐怕总是少数。但我可以说,如果东欧人民有机会重新选择变革的话,大部分人绝不会选择这种“两个激进”的变革方法,而会选择更为温和理性的改革,因为东欧普通百姓为激进变革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
匈牙利,乃至整个东欧经济经过“两个激进”的变革之后,全都变成了高度依赖外资的经济,而且普遍负债过高,贸易逆差过大,金融自由化使很多银行被西方银行控制。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又使多数东欧国家遭受了一次劫难。匈牙利货币对欧元的汇率半年内就下跌了20%,匈牙利人买房大都采用外币按揭:赚的是匈牙利的福林,还的是欧元,但现在福林大幅贬值,对按揭者是雪上加霜。拉脱维亚、乌克兰、塞尔维亚已接近破产,它们的债券评级已经被评为“垃圾”级别。
东欧经济形势不佳也反映在其经济竞争力的普遍疲软。据2007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报告,加入欧盟的八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都落后于中国。中国在该报告中排名第15位,爱沙尼亚第22位,立陶宛第31位,斯洛伐克第34位,匈牙利第35位,保加利亚第41位,罗马尼亚第44位,波兰第52位。从这个报告来看,一个13亿人的中国,在政治稳定性、政策一贯性、社会凝聚力等方面的得分都明显高于这些国家。政治上,东欧也困难重重。二十年过去了,尽管有欧盟大量的资金投入和专家指导,这些国家宪政的架子都有了,民主的形式也存在了,就是没有产生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一大批自私自利的政客在那儿争权夺利,导致百姓对政府的普遍失望。
奇怪的是我们国内一些学者至今还认为我们应该走东欧的道路。例如,不久前,国内一位教授说:“向市场经济转型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苏东国家的激进式转型,是把两个改革放在一块进行。我们的渐进式转型是先进行经济改革,再进行政治改革。但第二个改革的相对滞后,使第一个改革难以彻底。当前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加强政治改革,在此基础上再彻底完成经济改革。”幸亏这些人无权指导中国改革,否则的话中国早就成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翻版,国家大概都四分五裂了,中国的资产也早就被西方资本席卷一空,哪还有今日之崛起。中国当然要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但我们要汲取东欧的教训,汲取西方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的教训,超越西方模式。我们的目标,严格地讲,不是“转型”,而是“创新”,即使我们使用“转型”这个词,指的也是“制度创新”,而非效仿东欧。
这里还要谈谈东欧民主的质量。2008年初,欧洲权威机构Eurobarometer公布的民调发现,大部分东欧国家人民对自己政府的信任度均非常低:保加利亚为16%,波兰为17%,拉脱维亚为19%,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为21%。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下属的EIU发表了一个2006年世界民主质量评估指数,认为东欧国家民主的品质普遍还不如我国的台湾地区。这个评估把台湾地区民主排在第32位,而上述的八个东欧国家中只有捷克超过台湾地区,排在第18位,其他均排在台湾地区之后:爱沙尼亚第33位,匈牙利第38位,斯洛伐克第41位,拉脱维亚第43位,波兰第46位,保加利亚第49位,罗马尼亚第50位。如果这个评价是公正的话,人们就可以想像这些东欧转型国家民主的品质了。
即使是相对表现比较好的捷克,其民主质量也大有问题。捷克前外长伊日·丁斯特比尔曾于2006年10月9日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撰文,坦率地承认:“捷克公民不满情绪到处都在蔓延,参加投票的人数锐减,公众对政府、议会和整个政治进程的信任度日益走低。”他说,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时候,“我们期待得太多而不现实”。捷克政治人物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贪污丑闻。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顾问佩赫说了一句中肯的评论:“今天的捷克共和国,仍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独立捷克国家的奠基者、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所说的情况:‘国家已经民主了,但不幸的是,还没有民主主义者。’”
波兰2005年的大选,选出了卡钦斯基当总统,不久他孪生的哥哥也当了总理。兄弟俩奉行的政策很令欧洲头疼:他们先是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向欧盟的主要成员德国叫板,要算二次大战还没有算完的账。后又提出了在波兰禁止同性恋、恢复死刑、加强天主教会影响等主张,使欧盟老成员觉得很尴尬,欧盟不少国家现在已经把保护同性恋的权利作为重中之重的大事来抓了。卡钦斯基总理下了台,当总统的弟弟不高兴,认为哥哥遭到媒体的陷害,与新总理经常闹别扭。
2010年4月10日,卡钦斯基总统在赴俄罗斯卡廷吊唁“二战”中被苏联杀害的2万多波兰精英时飞机不幸失事,魂断俄罗斯。中国国内网上有文章称波兰是穷政府、烂飞机。这些文章的作者太不了解东欧了。依我之见,这个悲剧正好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波兰国家治理的混乱。波兰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也变成了选举社会。多数政客们忙着争权,没有用多少精力来治国,波兰时至今日连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尚未划分清楚。卡钦斯基乘坐的图-154型飞机,中国早在2002年就淘汰了,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权的尊重。而波兰总统的专机还在用如此简陋的机型,连波兰空军司令本人和波兰各界精英都坐在这架飞机上,这只能说明国家的治理很不专业。但是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波兰还算好一些,因为它尚能掌控自己的银行,否则波兰将很难渡过这次金融浩劫。英国《经济学人》2010年4月载文评论卡钦斯基总统亡命时这样写道:他是一个不懂外交的人,他只知道美国好,俄罗斯和德国不好,但波兰需要更为精明能干的领导人。他死前在波兰的支持率连25%都不到。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虽然也加入了欧盟,但距离欧盟的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罗马尼亚发展不顺利,从布加勒斯特机场到市中心的路上,还可以看到很多破旧的房子和汽车,腐败亦很严重,去医院看病住院一般都要行贿,各种政治丑闻也不断。一位罗马尼亚学者告诉我一个最新的政治笑话,老师问学生:“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把自己的手伸到别人的口袋里,这个人是什么人?”学生齐答:“罗马尼亚财政部长。”
保加利亚的问题更为严重。索非亚的一位NGO负责人告诉我:“我们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官员腐败,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人才外流。现在连称职的中小学老师都很难找。一旦学会了外语,就走了,以后只有傻子还待在这个地方。我看我们的国家要完了。”她的话可能夸张了一点,有一种南斯拉夫人常有的悲剧情结。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前,进行了很多面子上的改革,加入之后,改革派就被赶下了台。但保加利亚警察、司法体系都与黑社会勾结,使之成为欧盟新成员中最腐败的国家。我在2006年曾去索非亚参加一个会议,了解到保加利亚的各个级别的选票在街上均可以买到,总统选举的选票最贵,开价是100列弗(约60美元)一张。
在所有东欧国家中,对欧盟支持率最低的是拉脱维亚。这还是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情况。一位当地朋友对我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这儿的说法是,一到9月份,问题都来了。”9月就是议员们休假结束,议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像拉脱维亚这样的东欧国家,采用了西方竞选制度,老百姓前三天新鲜,之后就是普遍的厌倦,而厌倦的原因是竞选上来的基本上都是政客,空谈多于实干。“政客的特点是内斗,不是大事化小,而是小事变大,越大越好,他们可以浑水摸鱼,最后牺牲的是公众的整体利益。”她对我说。
德国明镜国际新闻在线对东欧的政局作了如下的评论:“虽然共产主义政权已经在东欧倒台将近二十年,但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迄今仍然在为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而挣扎。这些国家的政治缺乏中心,从极端右翼到后共产主义的威权主义形形色色,贪污腐败、极端主义横行,一片混乱。”克罗地亚作家德古丽琪曾是一位反对铁托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南斯拉夫解体后,她写道:“我们当时错把自由与民主当作是到西方随便采购的自由,但最终我们为此付出了三场战争的代价。我们的孩子在战争中被杀戮,我至今都感到对此负有责任。”
东欧国家本来的经济都相对发达,人口远远少于中国(除了波兰和罗马尼亚人口超过2000万,捷克是1000万,其他国家的人口都只有几百万,少于中国任何一个中型城市),教育程度不低,与西方文化的同质性也明显高于中国,欧盟和美国还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指导。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二十年后的结果竟是如此不如人意,确实值得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民主建设中深思。前面提到的“有民主而没有民主主义者”、“不会妥协”、“深深分裂的社会”、“没有出现真正的政治家”、“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没有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等问题,也是我们在民主建设中必须注意的。这也可以使我们更加坚定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信心,照搬西方模式,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历史文化传承与西方的差异远大于东欧的超大型国家只会是一场灾难。
不久前,我给匈牙利的H君发了电子邮件,问他一些匈牙利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也希望他和家人安然无恙。他很快给了我回信,写得很简单:“整个匈牙利正在等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济,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等待中国的救济。”他夸张了,但他似乎也道出了一定的真理。1989年东欧剧变震惊了世界,当时整个西方都看好东欧,不看好中国。但头脑十分清醒的邓小平对他的美国客人说了14个字:“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他让中国人继续走自己的道路。中国一路走来,不能说没有跌宕起伏,不能说没有坑坑坎坎,但中国最后拿出的成绩单比东欧亮丽得多,中国人也从东欧的经历中悟出了不少有益的东西。
作者: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春秋综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兼职教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一百多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