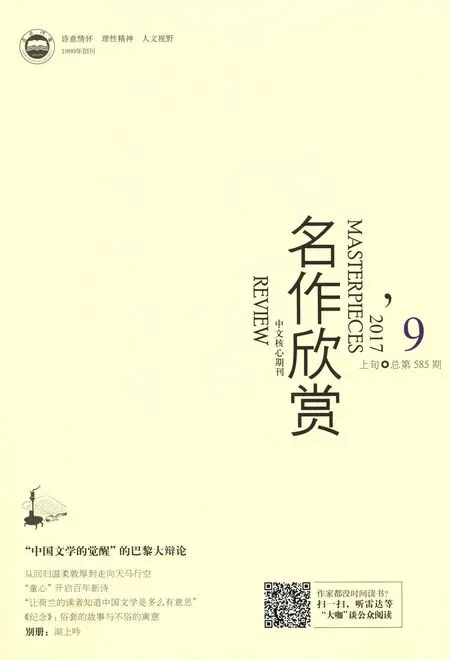宋词声音与两宋之夜
[江苏]白帅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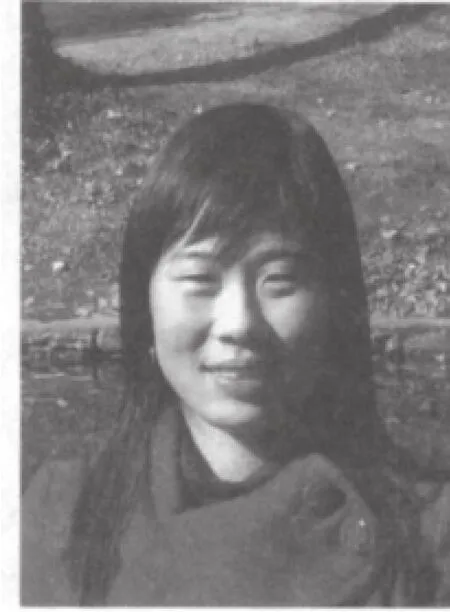
夜幕降临,本是万物俱息、万籁俱寂的时刻,然而也正是这黑夜的帘幕和无边的寂静,凸显了某些在白日里不起眼的光明和微弱的声音。黑夜模糊了白日里五颜六色的视觉刺激而只剩下世间万物的主体轮廓,它同样沉寂了世间喧嚣嘈杂的声音,而只留下特别清晰的一两种,在特定的时段供人玩味。声音与夜,天生地越是背离,越是相亲。透过夜的声音,我们有时反而能更轻松地“遗貌取神”,直达词人内心。
夜对声音的“自然相亲”
夜对声音的“自然相亲”,主要是指暗夜对声音的凸显作用。夜沉寂了众多声音嘈杂的合奏,而烘托出个别声音的清晰与响亮。
夜对声音的“自然相亲”源于暗夜的天然帘幕效应,而这与视觉和听觉的相互背离有关。套用哲学术语,人的五感是“对立统一”的,拿视觉与听觉而言,当你看到一张琴,如果你曾经听过琴声,你则大致能判断出这张琴能发出怎样的声音,但如果你要听一位琴师抚琴,那么闭目倾听的效果往往要强过眼耳并用,这其实就是视觉受阻对于听觉的促进作用。古时称乐师为“瞽”,虽并非意味着乐师全是盲人,但至少说明了古人较早注意到了盲人的乐感比普通人更好。春秋时晋国著名的乐师“师旷”就是一位盲人,庄子说:“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①由此可想象盲乐师师旷的耳力之聪。诗人们显然也敏感地注意到了视觉与听觉的这种背离关系,如唐代柳宗元《渔翁》的“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宋代梅尧臣《鲁山山行》的“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都以寻人不见、视觉受阻而突出声音的响亮和一方山水的清幽。词中如“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李煜:《浪淘沙》),“花影乱,晓窗明。莺弄春笙柳外声”(陈著:《捣练子·晓起》),“人悄。人悄。隔叶数声啼鸟”(李仲虺:《如梦令·石门岩》)等,也同样自觉或不自觉地选用“帘外”、“柳外”、“隔叶”等词语,以视线的阻隔来凸显声音的不凡。就这点而言,夜的优势就在于它有天然的帘幕效应,可以适当地模糊或阻隔人的视线,从而使人的感觉更集中于声音。如李清照的《添字丑奴儿》: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
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这首词上下两片分别写了芭蕉在白天和晚上给人的两种印象,白天的视觉效应和夜晚的听觉感受。白日里光线充足,人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就集中在了芭蕉宽大而舒卷的叶子上面,所谓“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而夜里,黑暗笼罩了一切,“雨滴芭蕉”的细碎响声,反而更能触及人心之幽微处。更何况一个经历了国破、家亡、夫死的“北人”,面对“夜雨芭蕉”这一典型的南方景致,其凄楚更是不言而明。“‘伤心’二句,对‘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杜牧:《雨》),‘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温庭筠:《更漏子》),‘薄暮投村驿。风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里人,分明叶上心头滴’(无名氏:《眉峰碧》)等等诗词佳句,可能有某种借取或隐括”②,但难以否认的是,正是这夜的帘幕效应才给了他们适当的契机,去感受这恼人的“雨声”。
当然,上述也只是夜效应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夜的寂静对个别声音的特别凸显,也是夜对声音“自然相亲”的重要原因。
暗夜与白昼相比,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静谧。莫砺锋先生在论述杜甫的“暮夜诗”时曾言:“缘情和体物是诗歌的两大功能。这两个功能都淋漓尽致地发挥,就形成了情景交融的好诗。暮夜诗也不例外。然而暮夜诗在‘体物’也就是写景方面,却有着先天的不足,因为黑夜在‘声色’两方面都不具备白天那样的丰富性。”③夜幕降临,万籁俱寂,声音在丰富性上确实不及白天。然而声多则杂,白天声音众多,个别声音往往会湮没无闻,反而给人纷乱破碎之感,如“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欧阳修:《临江仙》),“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秦观:《千秋岁》),“春将半。莺声乱。柳丝拂马花迎面”(吕渭老:《惜分钗》)。白昼里声音无疑要更加响亮,甚至要众音合奏、众鸟和鸣,才能被人感觉到。而与此相反,静谧的夜里,即使很细微的声音也一样清晰地传达人耳,触及人心。如曹组的《品令》:
乍寂寞。帘栊静,夜久寒生罗幕。窗儿外、有个梧桐树,早一叶、两叶落。
独倚屏山欲寐,月转惊飞乌鹊。促织儿、声响虽不大,敢教贤、睡不着。
关于此词,吴世昌《词林新话》言:“蕙风赞‘促织儿、声响虽不大,敢教贤、睡不着’曰:‘至今不嫌其俗,转觉其雅。’吾不觉其雅,转觉其酸。”④这里无论是况周颐赞其典雅,还是吴世昌言其酸,都是静夜与声音的组合造成的。只有静谧的夜,才能凸显出“梧桐落叶”、“月转惊乌”、“促织微鸣”这样细微的秋声,也正是夜里这细微而又清晰的鸣奏,才更能衬托夜的宁静和词人心中的忧思。鉴于此,我们可以说,虽然在夜里声音的丰富性大不如白天,但其表现力却大胜于白昼。
所以,我们要研究声音,离不开夜晚。同样,研究两宋之夜,也离不开声音。
声音对夜的“叛逆”背离
以上我们以宋词为例,解读了暗夜对于声音的凸显作用。那么宋词声音对于宋人之夜又有怎样的表达呢?恰与“相亲”相反,声音对夜,无时无刻不想着叛逆与打破,叛逆夜的包围,打破夜的静寂。声音与夜就像是一对闹别扭的母子,夜不断地为这个不听话的孩子清除掉了视觉、听觉上的其他阻碍,而声音却只想不断积蓄力量,来对抗这位看似严厉的母亲。
声音对夜的“叛逆”,首先表现在对人睡眠的扰乱上。夜是休息的时间,夜的黑暗与宁静原本为劳累一天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契机,让他们暂时放下肩上的包袱,安稳地睡上一觉,但并非所有人都有幸得到夜的这份慈爱与馈赠。“耿耿不寐,如有隐忧”(《诗经·邶风·柏舟》),“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范仲淹:《苏幕遮》),午夜时分,幸福的人都睡得安稳,而怀抱忧思的人则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所谓“风雨牢愁无著处,那更寒蛩四壁”(文天祥:《酹江月》),内心忧思与愁苦才是根本,人心理的平静一旦打破,周围的环境即使再宁静也是枉然。更何况此时声音总会适时地见缝插针,助人凄楚,如周邦彦的《蝶恋花·商调秋思》:
月皎惊乌栖不定。更漏将残,轣辘牵金井。唤起两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棉冷。
执手霜风吹鬓影。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楼上阑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
黄苏在《蓼园词选》中评这首词道:“首一阕,言未行前闻乌惊、漏残、辘轳响,而惊醒落泪。第二阕,言别时情况凄楚,玉人远而唯鸡相应,更觉凄婉矣。”⑤明确指出“声音”贯通全词的效应。俞平伯《清真词释》又具体分析说:“一叠起首三句是由离人枕上所闻,写曙色欲破之景,妙在全从听得,为下文‘唤起两眸’张本。乌啼、残漏、辘轳皆惊梦之声也。” 在分析“唤起”一句时又言:“此句实是写乍闻声而惊醒。乍醒眼应曰蒙眬,而彼反曰‘清炯炯’者,正见其细腻熨帖之至也。若夜来酣睡早被惊觉,则惺忪乃意态之当然,今既写离人,而仍用此描写,则似小失之矣。”“此处妙在言近旨远,明写的是黎明枕上,而实已包孕一夜之凄迷情况。”⑥俞先生对夜里的声音分析得非常细致,敏锐地看到了“梦醒”与“两眸清炯炯”的矛盾之处,但将这些声音归结为“惊梦之声”,则让人难以苟同。其实从“清炯炯”的“两眸”看来,词中的主人公其实是彻夜无眠的,乌啼、残漏,皆是长夜闭目“假寐”时所闻。辘轳声响起,则代表长夜已逝,因为只有天亮了才会有人起来汲水。这也意味着夜里短暂相聚的时光已经结束,离别时刻真的来了。也因此,她才会睁开被泪水浸润了一夜的眼眸,泪滴红枕。这里“辘轳声”唤起的不是梦,而真的就只是眼睛。这“一夜之凄迷情况”,也不是声惊梦醒,睡不安稳,而是“强装安睡”却又“彻夜难眠”。声音在这里的作用自然也不是“惊梦”,而是“扰眠”。
“惊梦”则是声音对夜“叛逆”的第二个表现。梦,是熟睡的产物;夜梦,可以说是夜的一个“衍生物”。“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大凡人思虑至深,在白昼清醒时刻难以实现之理想,就会以梦的形式在夜里呈现,这也是夜给人的第二个舒解压力的恩赐。在古典诗词中,梦往往是自由自在的,“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晏几道:《鹧鸪天》);梦也可以是酣畅淋漓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破阵子·为孙同甫赋壮语以寄》);梦过分美丽以至于人往往会“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晏几道:《鹧鸪天》),把美满的现实当成是梦的错觉。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对现实的“超越性”,“梦,就是突破一切社会秩序而进入无法无天的绝对自由的新天地,它可以最大限度地超越现实”⑦。而声音对夜梦最大的作用,则是“惊醒”,把词人从梦境中拉回现实。如“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秦观:《如梦令》),词人到底做了什么梦,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声音对词人现实中“迁客罪臣漂泊沦落之悲”的重新唤醒,则是可以想见的。又如辛弃疾的《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在古典诗词中,“蛩响幽窗”、“鼠窥寒砚”等常于夜间响起的细碎声音,往往成为人“梦枕频惊”(柳永:《倾杯》)或“夜枕不眠”的引线,如“半夜灯残鼠上檠。上窗风动竹,月微明” (吕渭老:《小重山》),“心事悠悠芳草歇。不眠听鼠啮”(石孝友:《谒金门》),“夜枕不眠憎鼠辈”(李弥逊:《蝶恋花》)。而辛弃疾此词,开篇即用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松风吹急雨”、“破纸自语”等一系列杂乱之声,打破了夜的宁静,也惊醒了睡梦中的词人。词人到底做了什么梦,词中同样没有直言。也许是“塞北江南”的征旅生涯,也许是又一次“梦回吹角连营”,但不管他梦到了什么,一旦被声音唤醒,眼前需要面对的则是自己“华发苍颜”,终将无缘复我“万里河山”的残酷现实。而那些“惊梦”的破碎响声,依然在寂静的夜里鸣奏,助人凄凉。夜梦给予你的短暂快乐和轻松被声音无情地打破,而剩下的则是无法改变的残酷现实与永夜无眠的寂静长久相伴。
正是“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入若邪溪》),声音对夜的“叛逆”,本来是为了打破夜的平静,却往往更反衬出夜的无边寂静,甚至会唤醒人们对夜的其他感觉,比如说茫然与冰冷。如前引周邦彦之“泪花落枕红棉冷”,又如苏轼《永遇乐》的“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吴潜《秋霁·己未六月九日雨后赋》的“飞鼠扑灯还自坠。展转惊寤,才听禁鼓三敲,夜声寥阒,又般滋味”。当词人被细碎的声音从梦中唤醒,他们更多感受到的不是声音之闹,反而是长夜之静和夜的茫然与凄冷。至此,声音对夜小打小闹般的“叛逆”,最终融汇于夜的沉寂与冰冷。但声音也并不是全无用处,它虽然撩拨不了长夜,却成功撩拨起了长夜无眠的词人的心,让他们在声之碎乱、夜之冷寂与现实之无奈“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心绪纷乱、孤苦无助,也让词境之悲苦力量成倍增长。
然而宋词中声音对夜的“叛逆”远未停留于此,它还时不时地将白天的欢闹场面延续到夜里,在“不夜”之夜,用疯狂的激情“彻底”打破了夜的沉寂(至少在一定范围能如此),比如说假日夜游与平常夜宴。亲朋高寿,同僚升调,抑或是佳节来临,总免不了觥筹交错地庆贺一番,所谓“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⑧。此时,声音就会展现其力量,一度要与夜分庭抗礼。据载,北宋宰相宋庠之弟宋祁极喜夜宴,每每“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⑨。据《宋稗类钞》:
宋子京好客。尝于广厦中外设重幕,内列宝炬。百味俱备。歌舞俳优相继,观者忘疲。但觉更漏差长,罢席已二宿矣。名曰不晓天。⑩
“不晓天”一词,彰显了宋人宴饮之疯狂状态。宋词中对于夜宴也是屡有触及,如毛滂的《忆秦娥·冬夜宴东堂》、陆游的《夜游宫·宴席》、吴文英的《烛影摇红·麓翁夜宴园堂》等,届时“乍莺歌断续,燕舞回翔”(万俟咏:《明月照高楼慢·中秋应制》),“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在夜宴中,五花八门的乐器轮番上场,“红牙双捧旋排行”(王安中:《小重山》),“琵琶拨尽四弦悲”(周邦彦:《浣沙溪》),“公宴凌晨箫鼓沸”(柳永:《玉楼春》),“满斟醽醁笑声哗”(崔敦礼:《西江月·寿词》),歌声、乐声、笑声、闹声充斥在长夜的某个封闭空间,尽情宣泄。这里烛光璀璨,欢声动天,声与色都彰显出了它们别样的美,哪里还有夜的丝毫踪迹?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声音对夜突破成功,这种喧闹还是被拘束在某个有限空间,一旦超越这个空间,夜的寂静与寂寞又会铺天盖地地迎面而来。如吴文英《西江月·丙午冬至》的“五更箫鼓贵人家。门外晓寒嘶马”,贵人家箫鼓喧闹,一旦跨出了门槛,便声势顿减,此时夜的寂寥与冰冷在门内喧闹的映衬下加倍凄楚。
值得注意的是,宋词(连同唐五代词)中的声音,在表达其欢情快意的同时,还以其大胆而直接的话语形式,再现了宋人夜生活的浪荡不羁,这是以前其他文体都鲜有表现的。柳永的词中就曾屡次写到床帏间的“山盟海誓”,如“缱绻。洞房悄悄,绣被重重,夜永欢余,共有海约山盟”(《洞仙歌·佳景留心惯》)。更有无名作者的言语表达更为直接:“告你休看书,共我花前饮。皓月穿帘未成寝。篆香透、鸳衾双枕。似恁天色时,你道是、好做甚。”(无名氏:《花前饮》)有类这种私密的话语,一旦被写入词中,公之于众,其遭人诟病的后果可想而知,柳永也因此被指为“词语尘下”⑪。在此,笔者无意对这种现象作任何道德上的评价,只是想从夜的角度,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诱因。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⑫宋词对于这类“私密”之事如此大胆的表达,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夜特别赐予的,与夜给他们带来的视听上的帘幕效应密切相关。这种帘幕效应一旦内化为人心理上的认同,大胆而直接的表达也会随之而来。包括前文所引宋祁宴饮“不晓天”之称谓,同样暗示了夜幕的这种“潜在激励”作用。在白日里,人的行为总是更多地要受到道德、伦理和法律的约束;在夜里,人往往会暂时地忘却一些东西,而去疯狂地享受另外一些。就这点而言,伴随夜而来的自由思想,有时也会闪现点点亮光。
总之,声音与夜有太多的牵缠,二者都喜“遗貌取神”,直取人心,这又与宋词善于表达人的幽微之情暗合。因此,研究宋词中声音与夜的关系,对于进一步推动宋词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①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7页。
②陈祖美:《李清照词新释汇评》,中国书店2003年版,第253页。
③莫砺锋:《穿透夜幕的诗思——论杜诗中的暮夜主题》,《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
④吴世昌:《词林新话》,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页。
⑤黄苏:《蓼园词选》,惜阴堂刊,庚申仲春(1929),第34页。
⑥俞平伯:《清真词释》,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35-36页。
⑦陶尔夫:《晏几道梦词的理性思考》,《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⑧孟元老、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页。
⑨钱世诏:《钱氏私志》,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页。
⑩潘永因、刘卓英点:《宋稗类钞》,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⑪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54页。
⑫鲁迅:《夜颂》,《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