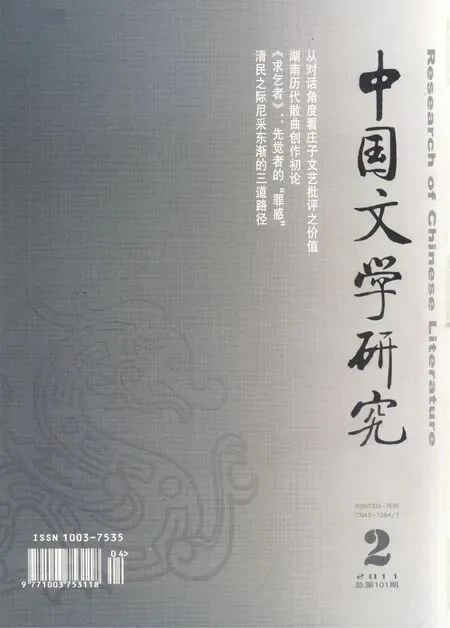隋代道教文学创作倾向的仙圣合一和神仙意象化
蒋振华 邓 超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隋代是道教由南北朝的成熟向唐代的繁荣而过渡的时期或中间环节。诚如卿希泰先生所指出:“隋代道教处于一个转折点,为唐以后道教的兴盛与教理大发展作了准备。”〔1〕隋代道教主要表现出南北道派逐渐融合,南北道教之教理教义相互渗透的趋势。具体来说,就是北方道教古朴雄浑的风格特征与南方道教华丽典雅的风格特色相互融合,相互兼容,在修道炼理等学养方面就是主张仙圣合一,道儒并存。这种道教修炼追求,对于道教文人影响所致则是主张道教文学创作的内圣外王的整体合一,追求神仙信仰和神仙境界的意象化、审美化和艺术化。
一
唐魏征曾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谈到南北朝文学存在很大的差异时指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贵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辞,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2〕魏征所指南北文学的差异,到了南北朝后期开始出现南北文学融合的趋势,差异渐渐淡化,合流渐趋明显。不但文学开始出现南北融合,在隋朝统一天下前夕,南北文化也开始出现合流兼容的趋势。在这样一种南北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道教的发展也必须走南北道派互相宽容互相渗透融合的道路。隋统一天下之前,道教的这种融合趋势已显端倪。据《仙苑编珠》引《楼观传》和《西岳华山志》记载,北周武帝时,南方茅山派道士前往华山传授三洞秘诀真经给北方楼观道派王延,之后王延就集南北道教之特点于一身。隋统一天下后,南北道教互相交流和互相融合的历史步伐大大加快,道教的地域性界限愈益被打破,例如茅山派就兼取南北道教之优长,在南北两方均有强大的势力范围。这种南北道教合流的趋势实际上把两个风格传统融合了起来,一个是北方道教古朴豪放浑厚的传统,一个是南方道教由注重教理教义而形成的经典制作之华丽典雅浓重的传统。从学术渊源上来说,前者源自道家老庄的自然简朴,后者源自儒家圣人的雅重典丽。隋代道教南北合流之势反映在道教文学创作倾向上则是对仙圣合一和内圣外王的追求,在文学主张上提出这种追求的是著名文人王贞。
据《隋书·文学·王贞传》载:“王贞字孝逸,梁郡陈留人也。少聪敏,七岁好学,善《毛诗》、《礼记》、《左氏传》、《周易》,诸子百家,无不毕览。善属文词,不治产业,每以讽读为娱。开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为主簿,后举秀才,授县尉,非其好也,谢病于家。炀帝即位,齐王镇江都,闻其名,以书召之。及贞至,王以客礼待之,朝夕遣问安否,又索文集。”〔3〕由传可知,王贞为儒生,但又是对道教极为信仰的道人,所撰文集三十三卷,表现出仙圣并主、道儒合流的文学创作倾向,即将儒家经世为用的文学思想和道教信仙成仙的文学观念结合起来,集中体现了隋代道教文学创作仙道统一和道儒融合的特征。这种倾向集中反映在其上齐王杨暕书《谢齐王索文集启》中,其书曰:
属贺德仁宣教,须少来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艺,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与天道,雅志传于游、夏,余波鼓于屈、宋,雕龙之迹,具在风骚,而前贤后圣,代相师祖。赏逐时移,出门分路,变清音于正始,体高致于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谁许独为麟角?
孝逸生于争战之季,长于风尘之世,学无半古,才不逮人。往属休明,寸阴已昃,虽居可封之屋,每怀贫贱之耻。适鄢、郢而迷涂,入邯郸而失步,归来反覆,心灰遂寒。岂谓横议过实,虚尘睿鉴,枉高车以载鼷,费明珠以弹雀,遂得裹粮三月,重高门之馀地,背淮千里,望章台之后尘。与悬黎而并肆,将骏骥而同皂。终朝击缶,匪黄钟之所谐;旦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顾想平生,触涂多感,但以积年沉痼,遗忘日久,拙思所存,才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见学仙之远;窥而不睹,始知游圣之难。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龙之降,渐过白豕之归。优纸陈情,形神悚越。〔4〕
该文是为其三十三卷文集所作之启,其阐述的关于文学创作倾向和文学思想的基本内涵包括:
一是对文学艺术的功能作用之认识。
文艺之功能作用或是“能事鬼神”,或是言“性与天道”,其影响历久不衰,代代相传,文艺创作必须遵循这种恒定不变的规则,且对此规则需铭刻隽永,如此则能志向高远,造就出贤哲圣人以万古承传,故“雅志传于游夏,余波鼓于屈宋”。这明显反映了儒家文艺观“立言之不朽”的经世致用思想,具有鲜明的儒学色彩,属于儒家文艺思想之范畴。
二是体现了对文学风格发展变迁的认识。
文学风格的发展变化决定于社会历史和时代之变迁,故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王贞对此一文学发展演变之规律有较深刻的认识,“赏逐时移,出门分路,变清音于正始,体高致于元康”,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其主要内容无非是对作家创作意旨的把握,对作品风格的品评,这种意识形态活动必须根据文学创作和作家所处的历史背景、时代风格去开展,即所谓“赏逐时移”。当然,文学批评又要根据具体的文学创作主体类别予以区别对待,不能一个标准一个尺寸,必须因人而异因作品而异,故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又云:“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文学批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以批评者的主观好恶为标准,即如王贞所谓“出门分路”,就是强调要分别对待,因地制宜。此外,一个作家或一代文学之风格的形成是时代气息的表现,“变清音于正始,体高致于元康”,正是王贞对文学风格之成因的具体阐述。正始时期,政治的急剧变化,紧张逼仄的生存环境,对生命前途的忧心忡忡,知识分子人格意义的淡化消弥,使一代文学、一代文人一改此前建安文学的激昂奋进而呈现出苦闷孤独彷徨的心理,在文学表达上则是谨慎含蓄隐晦,故刘勰评正始文学之代表人物嵇康、阮籍时指出:“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变清音于正始”,就是指的这种时代文风。元康(291—299)诗歌是太康(280—289)诗歌的余响,正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王贞所谓“体高致于元康”是指元康诗风体格高标,风流倜傥,诗人气质,高步迈举。
三是反映了作家经历,生平遭际与文学成就高低之关系。
一个作家文学成就之高低与其生平经历密切相关。大体来说,历经坎坷、遭遇磨难、身处逆境往往能成就文学创作。对此,司马迁曾站在历史高度予以指出:“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就是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的文学观,后来欧阳修将之阐发为“诗穷而后工”的诗学理论,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就是说的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王贞在这篇书启里,也谈到自己“顾想平生,触深多感,但以积年沉痼,遗忘日久,拙思所存,才成三十三卷。”意谓自己创作的三十三卷文集,都是自己坎坷多艰有感而为的。
四是关于文学创作的主旨倾向问题。
文学创作的内容主旨问题,是文学思想、文学理论首先要解决的文学的根本归宿问题。刘勰主张“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认为至高无上的道,乃是由圣人来阐明的;记载圣人之道的圣人之文,是文章之极致。历史以来,对于文学之道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主张儒家之道的,有主张道家之道的,有主张佛教之道的,有主张生活之道的。而道教界在认识文学之道时,则又提倡道教之道,即仙道、老庄之道等等。王贞在这篇书启里,在阐述了前述三个方面的文学思想之后,最终落到文学的根本归宿上来,既主张文学要承载儒家之道,又提倡道教仙学之道,是一种兼综儒家文艺思想和道教文学观念的圣仙合一的文学观,所以他指出:“仰而不至,方见学仙之远;窥而不睹,始知游圣之难。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龙之降,惭过白豕之归。”王贞向往道教神仙,为文三十三集,多写对仙道的渴望和企求成仙的信仰,表现的创作主旨是宣传神仙道教,但是,当一旦在狂热的宗教信仰之梦破碎之后便跌入清醒的现实之中,儒家圣道才是他建功立业以求生命不朽、英名垂世的依托之所。由此可见,王贞的文学思想在隋朝代表着一种仙圣合流道儒融合的趋势,为后来盛唐道教文学思想的儒学化、宋代道教文学思想的理学化开创了先河。这就是王贞仙圣合一内圣外王的道教文学创作倾向的重大意义。
二
隋代道教南北合流之势反映在文学创作倾向上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则是追求神仙意象化、审美化和艺术化。在这里先有必要提及一下神仙道教。
神仙道教是经晋代道教领袖葛洪以及南北朝许多道教学者的改进改造后繁荣昌盛起来的,到隋代仍然处于发展变化的状态。以上清派茅山宗为例,就能说明神仙道教在隋代的发展情景。茅山宗从南朝开始极其推崇神仙信仰,如在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里,设置了神仙的各种等级,把元始天尊摆在最高的地位,是至尊至上的神仙首领。这种神仙等级观念到了隋代,演变成以元始天尊为最高、以太上老君为次的道教神团系统。据《隋书》载:“天尊生于太元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所以说天地沦坏,劫数终尽,略与佛经同。以为天尊之体,常存不灭。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穷桑之野,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然其开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是其年号,其间相去经四十一亿万载。”〔5〕在这里,元始天尊被奉为最高品位的神,是万物之始原,宇宙之主宰,显示了道教关于神仙之神秘、万能的宗教色彩。不仅如此,隋代神仙道教还表现为对仙界仙境之美妙的涂饰、夸张和铺陈以作为吸引信徒的手段,神仙世界的美好与快乐也成了信众追求向往的目标,也是道教文士反复描写的对象,虞绰的道教文学创作表现的对神仙意象的浓笔重彩的描绘,就是这种道教信仰背景的产物,体现了隋代独特的道教文学创作的意象化、审美化和艺术化。
虞绰,据《隋书·文学·虞绰传》载:“虞绰字士裕,会稽余姚人也。父孝曾,陈始兴王谘议。绰身长八尺,资仪甚伟,博学有俊才,尤工草隶。陈左卫将军傅縡有盛名于世,见绰词赋,叹谓人曰:‘虞郎之文,无以尚也。’仕陈,为太学博士,迁永阳王记室。及陈亡,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绰所笔削,帝未尝不称善,而官竟不迁。初为校书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迁著作佐郎,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恩盼隆洽。从征辽东,帝舍临海顿,见大鸟,异之,诏绰为铭……帝览而善之,命有司勒于海上,以渡辽功,授建节尉。”据此可知,虞绰曾得到隋炀帝杨广赏识。而杨广是一个对道教尤其是神仙道教有浓厚兴趣的皇帝,他宠信道士,广读道书,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载他“自晓占候卜相”,迷信神仙术数,参与佛道之争,又建造宫殿,仿照仙山琼阁建成“西苑”,设置“神仙境”。炀帝的这些道教信仰之行事,对虞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他沉溺在这种气氛的包围之中。因此,当大业八年(612)炀帝征辽东舍临海顿见大鸟而异之,乃诏虞绰作赋以呈时,虞绰于是欣然命笔,赋得《大鸟铭并序》,其辞曰:
维大业八年,岁在壬申,夏四月丙子,皇帝底定辽碣,班师振旅,龙驾南辕,鸾旗西迈,行宫次于柳城县之临海顿焉。山川明秀,实仙都也。旌门外设,款跨重阜,帐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跸,下轻舆,警百灵,绥万福,践素砂,步碧沚。同轩皇之襄野,迈汉宗于河上。想汾射以开襟,望蓬瀛而载伫,窅然齐肃,藐属殊庭,兼以圣德遐宣,息别风与淮雨,休符潜感,表重润于夷波。璧日晒光,卿云舒采,六合开朗,十洲澄镜。少选之间,倏焉灵感,忽有祥禽,皎同鹤鹭,出自霄汉,翻然双下。高逾一丈,长乃盈寻,靡霜晖于羽翮,激丹华于嘴距,鸾翔凤跱,鹊起鸿骞,或蹶或啄,载飞载止,徘徊驯扰,咫尺乘舆。不借挥琴,非因拊石,乐我君德,是用来仪。斯固类仙人之骐骥,冠羽族之宗长,西王青鸟,东海赤雁,岂可同年而语哉!窃以铭基华岳,事乖灵异,纪迹邹山,义非尽美,犹方册不泯,遗文可观。况盛德成功,若斯懿铄,怀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镌名山,安用铭异!臣拜稽首,敢勒铭云:
来苏兴怨,帝自东征。言复禹绩,乃御轩营。六师薄伐,三韩肃清。龚行天罚,赫赫明明。文德上畅,灵武外薄。车徒不扰,苛慝靡作。凯歌载路,成功允铄。反旆还轩,遵林并壑。停舆海澨,驻骅岩址。窅想遐凝,藐属千里。金台银阙,云浮岳峙。有感斯应,灵禽效祉。飞来清汉,俱集华泉。好音玉响,皓质冰鲜。狎仁驯德,习习翩翩。绝迹无泯,于万斯年。〔6〕
从文中发现,虞绰用汉代以来的天人感应思想作为考察天地自然现象的方法论,从宗教的万物有灵观念来解释所谓呈现吉祥的大鸟出现的原因。为了附会这种解释,他借用了道教世界的神仙典故、神仙意象作为文章立论和创作的触发点,反映了他对于以道教神仙信仰为核心的道教文学创作在宣教功能方面的深刻认识。
“想汾射以开襟,望蓬瀛而载伫”,这里援引了《庄子》、《史记》中有关神仙的典故。《庄子·逍遥游》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下焉。”“想汾射以开襟”,就是说一想起《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的神仙风采,就心旷神怡、胸襟舒畅,从而表达一种强烈的羡仙意识以及对神仙世界和神仙生活的渴望。又《史记·封禅书》云:“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仙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焉,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琊,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土,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望蓬瀛而载伫”就是引用历史以来帝王至渤海求神仙不老之药的典故,蓬即蓬莱,瀛即瀛洲,相传为渤海中之神山,山中仙境优美,仙人长生不老,是人世间向往的神圣之所。虞绰在这篇《大鸟铭》里描写隋炀帝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对神仙道教的信仰,把他置于有感于神仙传说故事和面对大海触景生情止步不前的宗教信仰环境中,从侧面抒发了祈祷帝王万岁长命的歌颂之情。显然这种情感的抒发是以构建汾射和蓬瀛两个神仙意象为前提的,也就是说神仙的意象化是其创作立意的聚焦点。
着意涂抹和描绘神仙意象,使作品蒙上更浓厚的道教神仙色彩,体现强烈的神仙信仰意识,是虞绰道教文学创作的一种理论或观念。而在神仙意象方面,主要通过描绘出两种意象类型来表现,一是景物意象,一是生命意象。
所谓景物意象,是指道教领域中那些象征神仙境界之妙、神仙世界之乐、神仙生活之美的风景物象,如霞光、彩云、瑞气、紫霓等等。如虞绰《大鸟铭》所描绘的那样:“璧日晒光,卿云舒采,六合开朗,十洲澄镜。”这里的景物意象有:如白玉般洁亮的阳光,舒卷自如色彩斑斓的云朵,澄澈如镜、朗练明彻的宇宙大地……这样的景致,正是神仙道教神往的对象,它们强烈地吸引信徒们摆脱现实追求理想。正由于有如此神奇的效用,所以,一般来说,道教文学创作都要浓笔重彩地描绘仙界意象、物象、景象的神奇美丽以作为宣教的手段。在这里,宗教的实用目的与文学的艺术效果得到了有机的交融或水乳般的溶合。
所谓生命意象,是指自然界生命有机体中那些与道教神仙特征如长生不老、童颜不衰等极为相似的动植物形象,如白鹤、鸾凤、青鸟、赤雁、灵芝、松柏等等。虞绰在其《大鸟铭》中对此类意象的描写是这样的:
少选之间,倏焉灵感,忽有祥禽,皎同鹤鹭,出自霄汉,翻然双下。……鸾翔凤跱,鹊起鸿骞。……斯固类仙人之骐骥,冠羽族之宗长。西王青鸟,东海赤雁,岂可同年而语哉。
其中,鹤、鹭、鸾、凤、鸿、骐骥、青鸟、赤雁,都是象征人类生命长久,也是道教神仙世界经常借用来比况生命不衰的动物形象,以至形成了固定化的神仙意象。如西王青鸟,就是神话中的仙女形象,是西王母身边的一种长寿的象征物。虞绰在文中借此类神仙意象来修饰文彩,一方面说明道教神仙信仰对人们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神仙题材对于文学创作的借鉴、取材作用。
以虞绰为代表的隋代道教文学创作所刻划的两类神仙意象,其宗教的宣教功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从文学的审美愉悦与艺术化角度来看,无论是景物意象,或者是生命意象,都有诉诸欣赏者视觉感知而求得审美快慰的心理满足。所以,隋代道教文学创作在道教逐渐神仙化的过程中,更追求宗教的现实性与文学的审美性、艺术性的统一,神仙的意象化更是把信仰者从精神安慰的层面提升到了艺术安慰的高度,其价值在于把宗教升华到更高的形而上的品位。
〔1〕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修订版,第二卷第 2页
〔2〕唐·魏征等撰《隋书·文学传》,中华书局 1973年版,第 1370页
〔3〕〔4〕唐·魏征等撰《隋书·文学传·王贞》,中华书局 1973年版,第 1376—1377页
〔5〕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 1973年版,第 1091页
〔6〕唐·魏征等撰《隋书·虞绰传》,中华书局 1973年版,第 1739—17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