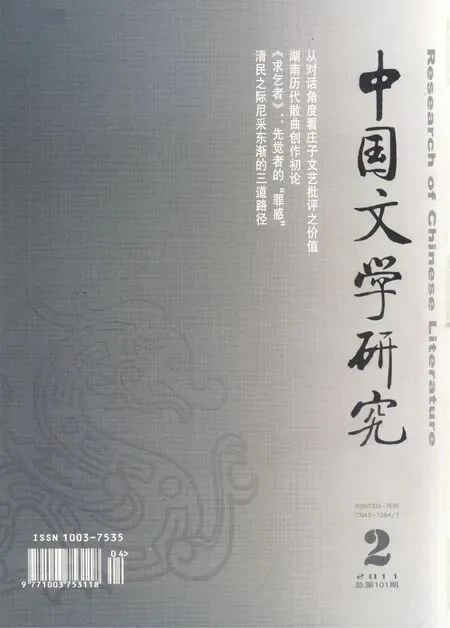20世纪 80年代“匪性文学”与侠文化
石志敏
(贵州铜仁学院初等教育系 贵州 铜仁 554300)
一
传统文化中,儒、道、佛文化是主流,长期雄踞于主流意识形态之中,侠自韩非子给它定性为“侠以武犯禁”以来,就受到主流统治文化的排挤。随着侠的活动由现实空间转向文学空间,侠文化就只以文化的支流形态被下层百姓接受和推崇,存在于民间中,带有民间文化的特征。在侠文化的流传过程中,虽然受到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文化的影响,是大小传统文化碰撞的结晶,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文化概念。“侠文化是一种缺乏精确的话语外延及严格的语义规范的文化构成类型,以致在传统文化结构中长期处于若即若离、若隐若现、乃至有形无相的状态。”〔1〕侠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概念被人接受和研究,是从 20世纪 80年代才开始的。
“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古代“士”阶层中逐步演变而来的,“士”根据专长的不同逐渐出现了文武的分化,并最终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文者为儒,武者为侠”〔2〕,“侠”的出现背景和社会政治现状决定了“侠”的游动。所以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称“侠”为“游侠”,并为“游侠”列过传。“游侠”自汉因其“以武犯禁”的不可调和的反抗方式受到统治阶级的打击。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侠”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却以文人想象的姿态出现在了文学文本中。侠作为一种精神形态的文化现象在流变过程中,它经受了大传统各种文化的浸润和碰撞,是文化融合交集的产物。但侠文化作为一种流传千年的已渐渐明晰和独立的文化系,它的场域、核心价值的渊源还是以墨家学派的影响为最深。墨家的社会出身多为从手工业者而上升为士的,墨家的社会理想是建立在小生产者的利益和精神、文化愿望之上的。他们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平等互助的社会交往和生活范式,这完全符合下层民众的意愿;人格理想上,他们提倡“任”,即“士损已而益所为也”,“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意思是,损己利人,为了挽救他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了解救他人的急难而不惜做自己厌恶的事情。这恰是侠的行为准则,也是侠义人格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任”在后世中成了侠道伦理观念的核心。所以后世把侠也称为“任侠”。墨家还站在弱小者的一方,不惜“杀己以存天下”,愿意为了自己的主义和理想而慷慨就死。这种为了道义献身的精神和侠的精神一致。墨家“尚同”的主张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这和侠文化的场域——理想化的、民间化的乌托邦的江湖世界有相同之处。自汉以后,墨学被统治阶级所排斥和打压,但墨学的精神和理想却借文人的笔在民间得到接受和传承,来自于民间的侠接受了民间化的墨家的思想,侠文化就有了思想的内涵。
在“侠”的发展中,侠义精神也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不断的被扩充、被整合,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最早对“侠”进行评述的是战国法家学派的韩非子,他在《五蠹》中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对“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同时也对“侠”的特征和精神进行了界定。第一次为“游侠”列传的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侠”的人格和品行进行了新的评定。“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第一个正面肯定、表彰了游侠的品质和行为,为“侠”的基本特征画了一幅素描画。他肯定了侠以弱小者为本位的利他伦理观念,表扬了他们信守诺言、急人之难、救人困厄而不惜牺牲自己利益乃至性命的勇力和气度。司马迁的这一论断为后世侠文化确立了占主流和中心地位的侠义观念,救人困厄、扶弱锄强、信守然诺成了“侠”的核心价值观。也成了后世文学作品塑侠、论侠的标杆和依据。
在中国几千年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发展的侠文化为中国人构建了一个远离庙堂的民间话语秩序;营造了一个和主流政治不一样的带有理想性、乌托邦色彩的江湖世界;其行侠仗义、扶危济困、舍生取义、追求自由自在的人格等精神内涵早已成为集体无意识存在于中国人的文化和心灵里。侠文化以“潜文本”或显或隐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言说着中国人的心理诉求,表达了对人的人文关怀,抚慰了现世的焦虑和忧伤。
二
如果说侠文化在发展流变过程中以显性的方式存在于古代侠义小说和近代武侠小说中的话,那么到了文学的现代时期,侠文化就以“隐性”、“潜文本”的方式存在于现代文学的某些严肃文学中、存在于某些作家的性格气质中,比如鲁迅、郭沫若、萧军等等。1949年以后,革命英雄传奇小说应运而生,其作品一般有民间思维和民间话语的特征,其人物形象有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其人物形象的成长模式与侠有着相似之处,其主题与侠文化的内涵有相通之处,比如“复仇主题”等。自此,英雄和侠找到了对接点,江湖中的侠演变成了革命战斗中的英雄。侠文化就以“潜文本”的方式进入了英雄传奇小说,进入了当代文学的文本中。从 80年代开始,文学又进入了新的时期,其中有一点特备值得强调,“在 80年代前期文艺界所热衷的‘现代派’热,在这一时期已逐步降温,文学有了强烈的本土意识,不是在向西方学习中获取生机,而是意欲立足民族现实而实现文学对过去的超越。”〔3〕很多学者也试图从传统文化中找取营养来建构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精神体系。在这种文学潮流之下,80、90年代文学创作出现了一股“匪性文学”创作潮流。
中国现代“土匪”活跃于民国时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消失于历史舞台。然而它却并没有随着历史而消逝,它依然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活跃在文学文本中。“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他将土匪对于中国人文化人格的影响和儒道文化的重要性等量齐观。”〔4〕现实中的土匪已不复存在,我们将研究进入当代文化、文学体系的“土匪”,或称之为“土匪文学”,或称之为“匪性文学”。尤凤伟认为,“‘匪性文学’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妨把外延放开一点,除了落草为寇的正宗土匪之外,还有在心情上极为靠近的乡村浪人、无业游民、三教九流等,从广义上都可以扯在一起”。〔5〕
为什么要写土匪?因为“富有象征意味的‘江湖’和‘土匪’实际上已经与官方政治对立而成为人们进行精神探险的心理需要,匪行与规定的社会行为作为理性与兽性这两种终极指向的表征,其间有异常巨大的张力空间,人的意识和行为会不断在这两极之间位移,并因此释放备受压抑的自然人性。”〔6〕作家写“匪”是因为“匪”有较大的自由度,写“匪”可以回避许多现实的、具体的需要答案的问题,从而使作家进入精神相对自由的空间;能够从容的多方面的展示文化的诸多层面。“匪”的文学意义在于“‘匪’是某种带有掠夺性又带有某种反封建色彩的复杂人物,从这些人身上透视整个的人文状态、生存状态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如果能抓住这些人内在的、深层的东西,就能写出比较厚重的东西。”〔7〕
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文化的侠文化是以怎样的形态进入到“匪性文学”的话语系统的呢?首先它们有着基本的共同点,都是民间话语系统,都具有民间思维的特征;都具有不和世俗的野性思维特征,有着自己一套独立的伦理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行事方式;都显示着创作主体和创作对象主体的理想主义倾向。只不过“侠”是进步的、理想的美好愿望,是对理想、美好人性的正面表达,是一种人们渴望而现实又不能实现的生命样式和精神风度。“匪”是反叛的、掠夺的,甚至是丑陋的(在很多文学作品中),但是从另一层面看,“匪”也有“信诺”也有“仗义”,也有一点老百姓的“公道心”,他们对人对己都是一套原则,自己今天杀人,明天也有可能被人所杀,是再公平、自然不过的事情,“匪”也有成“匪”的现实的逼迫和逃遁。所以“匪”是对理想的一种隐晦的表达,是对现实的一种间接的反抗。其次,当代“匪性文学”都不是为写“匪”而写“匪”,而是作家在“匪”这类人身上寄托着自己的人格理想、文化理想的,是通过写“匪”来表达对生命、人性、生存的思索和探秘。也就是把传统题材写出现代意味,而“匪”“侠”的生存方式带有比较多的原始色彩,他们身上带有最本真最有力量的人的“自然之性”。在这里,“匪性文学”与侠文化也就找到了对接的通道,“匪”虽是“匪”,但也不是现实中的“匪”,他们的人格和精神是作家乌托邦理想中的“侠义之匪”“力量之匪”,是现实的反讽者。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作家写了很多涉及到土匪的“匪性文学”,如贾平凹的《白朗》、《五魁》,苏童的《十九间房》,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张炜的《家族》,田中禾的《匪首》,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尤凤伟的《石门夜话》等等,形成了当代文学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现象。“他们塑造的土匪形象基本属于‘社会土匪’即‘好的土匪’系列,作者揭示他们为匪的社会合理性以及他们的反抗、愤怒和无奈。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叙写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行侠仗义、善良刚毅的品质。”〔8〕下以尤凤伟、莫言、贾平凹为范本阐释“匪性文学”中侠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三
(一)、穿着“侠匪”外衣的人性探秘——尤凤伟和他的《石门夜话》
《石门夜话》由五个相对独立的章节构成。讲一个美丽且苦命的女人与她所遭遇的几个男人的故事。五个章节虽然男主人公各不相同,但是前四章有一个牵连全篇的人物:匪首二爷。“这一个(《夜话》)故事中独特奇崛的部分使我看到故事之外的风光,使我看到这个俗而又俗的故事中的不俗之处。当写出来之后,我先自被感动了,我审视着那个喜欢在女人面前赤条条(也包括灵魂)的二爷站在面前,我简直说不清对这个‘怪物’是该恨还是该爱,但不管怎样,他是站住了。他站住了,作品大抵也站住了。因为这篇小说(《夜话》)只有一个人物,那就是二爷,其他人物用评论家的说法只是些‘符号’罢了。”〔9〕这是作家精雕细刻一个人物,也是小说揭示创作主体意旨和倾向的一个人物,更是作家“爱”的一个人物。面对这份“爱”,丁帆评道:“尤凤伟眼中和心中的土匪被小说家的道德情感极大程度的宽容,作者似乎失去了评判的勇气和锐利。”〔10〕这是小说家浓厚的宽容和包涵,也是小说家理想主义情怀的一种表现。他“身材高大,面皮白净,英俊如书生,手里把玩一把折扇。驹子从这人的长相装束也看不出是哪行当人,只是从那高傲自得的气派上推测他是这一伙人中主事儿的,大概便是‘二爷’了”。从对“二爷”的外貌修辞中我们简直看不出他是一个土匪。按以往“匪性小说”对土匪外貌描写的常规思维,这些“匪”他们要么是滑稽可笑的,比如曲波《林海雪原》中的刁占一、一撮毛,胆小、猥琐、干瘪;要么就是凶恶残暴的,比如《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同是匪首,座山雕凶狠残暴,“二爷”儒雅从容,外貌修辞的差异彰显了十七年文学作家和当代文学作家对待“匪性文学”创作的不同政治文化态度。十七年文学作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对土匪的文学想象充满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外貌描写烙上了道德因素,形成了好与坏、道德与非道德的模式化面孔特征。而当代文学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土匪成了他们所肯定的乡村文化的一部分,莫言《红高粱》式充满生命力的土匪;张炜《家族》中土匪头子李胡子、小河狸的信诺、人性;贾平凹《晚雨》中人性“善与恶”的两极的对立与转化;尤凤伟《石门夜话》的人性探秘等莫不如此。
在人性探险上,尤凤伟的《石门夜话》是有先验意味的一篇。作者借助人物主人公“二爷”的土匪身份、侠性性格,以“性”“情欲”为支点,展现了“奔腾于血液中最原始最有力量的因素”。他是这样阐释自己生活的现实和行为方式的,“见女人任不吭声,二爷又说:‘你听我说,凡事都有个定规,忠是对明君,孝是对慈长,仁是对高士,义是对良友,要是这世上再见不到明君慈长高士良友,那这忠孝仁义还有什么用场呢?相反,在一个混沌世界里,所有好东西都成了喂养达官贵人和恶人的酒肉宴席,把这伙人喂得肥头大耳,喂得脾气越来越大。我发现这样酒肉宴席上的位子被这伙人站得满满,于是便做了强盗。强盗干的是抢食吃的勾当,一边抢食一边为这世界主持点公道。你只要在山上住个一年半载,就明白我说的这些都是真的……’”〔11〕这样犀利的思想,这样入木三分的清醒的现实剖析,哪里还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土匪所言,分明就是一个揭竿而起的侠士,一个有着自觉选择的理性的造反者、一个要用自己微弱的个人力量为这世界主持公道的行侠者。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寄寓了作家对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诉求。表达了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是完完全全沉入民间的,是“龙泉汤镇”秩序的代言人。
《金龟》中的马汉子更是个知恩必报、侠肝义胆、慷慨悲歌的侠义之士。“报”是侠文化精神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怨分明,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更是侠士的品行。马汉子为了报答驹子,逃跑时邀上了驹子,结果因为驹子的害怕、怯懦和自私,逃跑计划失败,驹子逃脱、马汉子被抓。被抓的马汉子保住了驹子的命,独自慷慨赴死。除了马汉子,贪生怕死的驹子也有“侠义”之举的时候,老土匪寨主匡老头为了自家弟兄的性命花多少钱爷在所不惜。在“江湖”中匪也是“有情有义”的人。“匪性”和“侠义”的交织显示了作家民间话语的姿态,对“匪性”极大程度的宽容和包涵是作家理想主义情怀的表现,也是作家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回归。
(二)、“农民/土匪/英雄”模式与江湖侠义情境的结合——莫言《红高粱》的自由生命之歌。
莫言 198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他创作最大的灵感,不是别的,是他故乡高密的一景一物,他要从他故乡的民间大地中捕捉原始的生命力的冲动。正是“他得天独厚的把自己的艺术语言深深扎植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土壤里,吸收的是民间文化的生命元气,才得以天马行空般的充沛着淋漓的大精神大气象”。“用本土的文化之根来表达现代性的观念”,“如果以莫言创作中的民间因素来立论,莫言在 80年代的创作就是一标志。从《透明的红萝卜》到《红高粱》,莫言小说的奇异艺术世界有力解构了传统的审美精神与审美方式,他的小说一向具有革命性与破坏性的双重魅力。”〔12〕从陈思和的这几段话中,我们可以抓住几个关键的词语,“民间”、“革命”、“破坏”。对“民间”一词陈思和在《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中为民间文化形态作的定义是:“一、它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了相对活泼自由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的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虽然在权力面前民间总是以弱势的形态出现,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被迫接纳权力,但它毕竟属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而且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13〕民间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拘束的、充满原始生命活力的特征在莫言的《红高粱》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被称为“一曲生命辉煌的赞歌”。
这糅合了乡野传奇与英雄演义的作品的主人公们,是高密东北乡的农民,说他们是农民,因为他们祖祖辈辈躬耕在高密东北乡的广袤的黑土上,种的是高粱、吃的是高粱,喝的是高粱酒、甚至“睡”的也是高粱,他们健壮、剽悍,勤劳实忱,有山东汉子的朴拙憨直;可他们又不是真正的农民,他们没有整天在地里刨食,没有看天吃饭,没有逆来顺受,而是自由自在地穿梭在高粱丛林里,奔放的“野合”,不要命的跟鬼子干,流淌的鲜血把高粱地都“和稀”了,大块的吃“拤饼”,大碗的喝高粱酒。他们是土匪又不是土匪,“我爷爷”为了自家喜欢的女人不受蹂躏之苦杀了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财主单廷秀和他的麻风病儿子单扁郎,毫无畏惧和内疚之心,说他们不是土匪,他们一生却是“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14〕他们的身上有着“天生的英雄气质,遇到外界的诱因便转化为英雄的行为”。所以,在这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里、在这段现代革命历史舞台上出演的主人公们我只能说他们是农民中的英雄,是“农民英雄”。他们的精神上有着“人生一世,不过草木一秋,豁出去一条命,还怕什么?!”的放达、无畏无惧的特质;犹如火红的高粱般的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生命意识。“英勇无畏,狂放不羁的响马精神”是他们精神上最主要的特征。
《红高粱》以我的父亲,一个 14岁男孩的眼睛描摹了与其说是关于抗日的故事,不如说是以高密的莽莽野地为“历史空间”的英雄传奇故事。“所谓的‘历史空间’却不限于传统那种时与空、历史与原乡的辩证话题。‘历史空间’指的是像莫言这类作家如何将线性的历史叙述及憧憬立体化,以具象的人事活动及场所,为流变的历史定位。”“莫言的纸上原乡原就是叙述的产物,是历史想象的结晶。”〔15〕。在这样的“历史想象”中,作品以广袤狂野的高粱地为舞台,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在高挺茁壮的红高粱中,演出了一场场任情侠义的壮歌与悲歌。
“我爷爷”是“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作家将他放在“农民/土匪/抗日英雄”的模式中来叙述,因为土匪作为齐鲁大地雄强型人格的典型代表,他们身上的侠义精神——精忠报国、快意恩仇、尚武轻生、自由不羁等——一经和民族主义情感的碰撞和交集就构成了抗日英雄的基本素质。那么作者莫言把这个农民土匪、抗日英雄放在一个怎样的“江湖”中,或者说一个怎样的侠义情境中来表达的呢?。
作者莫言把余占鳌分别放在了情欲、“江湖”的快意恩仇和“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等“江湖”侠义情境中来表现。在虚拟化的场景中以情欲这一生命的原点及外化展示了人性的张扬和雄强,显示了自由不羁、蓬勃茁壮的生命力。快意恩仇本既是“江湖”的规则也是“江湖”的魅力,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命为自己的吃喝拉撒、爱恨情仇,为自己的欲望冲动,为自己的名誉尊严负责,这样以生命为原点衍生出的人生是直接而充实的,又是真实而快意的。余占鳌的经历正是展示了“江湖”人生的快意和自由。“精忠报国”是我爷爷“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表现。在一个特定的充满“历史想象”的空间——抗日战争,实体就是“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16〕在这样一场惨烈的战斗中,余占鳌和他的弟兄浴血奋战,用自己的血和命硬生生的打跑了鬼子。小说中罗汉大爷、“我奶奶”都是有着血性的侠义之人,罗汉大爷知恩护主,怜家爱国,视死如归,在日本人的枪下被活剐而死。与红高粱一样挺拔、自由、奔放的是“我奶奶”的生命,作品把我奶奶置于高密东北乡民间文化色彩当中,没有“规范化”的社会活动方式,没有世俗的人伦道德,所注重的是人性本原的东西,是生命挣脱了一切羁绊之后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和大欢喜。“我奶奶”还是个巾帼英雄、侠女子,她为了留住任副官临危不惧,为了“义“不计生死,最后她死在了日本人的子弹下,死前还发出了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呐喊。针对“我爷爷”辈的英勇,莫言对“我”们这一辈的风云涣散,不再有父辈们的狂野英勇,进行了调侃和揶揄。中篇《父亲在民夫连里》写的是 1948年间,父亲(《红高粱》里的父亲)率领一队民夫为解放军赶运粮草、出生入死、完成任务的故事。再一次把“农民英雄”和江湖侠义结合,读来回肠荡气。
(三)、匪性、人性、侠性在欲望中的嬗变——贾平凹“侠盗小说”中的赞美与批判。
在贾平凹创作中,有一个系列中篇《美穴地》、《白朗》、《五魁》、《晚雨》、《烟》被很多评论家归于“土匪小说”。如果把这股源起于 1986年莫言“红高粱家族系列”引发的“匪性小说”创作热潮中的几位作家做个比较,就会发现,一是以莫言为代表的,强调人的个性生命强力的小说。二是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在人性两极的对立与转化中展示人的复杂性的小说。三是以尤凤伟为代表的在人性道路上探寻人的本质的小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霍布斯鲍姆在 1969年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土匪的著作《土匪》,在这本书的影响下,贝思飞在 1988年出版了专门研究中国民国时期土匪的专著《民国时期的土匪》,“霍布斯鲍姆和贝思飞以大量的史料为依据,科学地分析了土匪之为土匪的原因,土匪的来源、类型、性质和生存方式,给出了符合事实的结论。”“土匪的来源混杂,他们的目的和动机也各有差异,故而其性质有别。以其性质大致可归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社会土匪’即‘他们不是被公众舆论当做单纯的犯罪分子……而是作为英雄、战士、复仇者、保卫正义的斗士,也许甚至是解放运动的领袖,总之他们受人赞美,值得帮助和支持。’这类好的土匪就是‘社会土匪’,中国百姓常常称他们‘绿林好汉’。第二类土匪是恶匪,即歹毒成性、欺压良善、滥抢滥杀的邪恶之徒,即‘坏的土匪’。第三类土匪是纯粹为生计所迫,在小范围内进行一般性的抢劫,但不实施烧杀抢劫奸淫的‘季节性土匪’。当然,更多的土匪是混合型的,难以明确归类。”〔17〕依据霍布斯鲍姆和贝思飞的观点来分析莫言、贾平凹、尤凤伟三作家的“匪性小说”就可以发现,尤凤伟、莫言笔下的大多数土匪形象属于“社会土匪”即“好的土匪”一类,比如尤凤伟《石门夜话》中的“二爷”、莫言《红高粱家族》中“我爷爷”“我父亲”,作家极大地赞美了他们身上的英雄品质和侠性气质。
贾平凹笔下的土匪,“好的土匪”有之,作者也极大地赞美了他们人性的良善和侠义之道,“坏的土匪”也有之,作者借他们批判了“我们民族文化中沉积的野蛮、暴力、自相残杀与互为谋害的民族劣根性”〔20〕。作者把他们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空里,探讨了灵肉、人性兽性、道德人性,善恶、侠匪品质等在历史时空里的互为依存的关系和嬗变轨迹,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民族文化的驳杂和民间文化(侠文化)的二元对立。《白朗》中的白朗、《晚雨》中的天鉴、《五魁》中的五魁、唐景他们都是“好的土匪”,但是又各有特征,都在各自的生活轨迹中、在欲望的泥淖中丢掉了生命的雄强、本色,弃了侠匪的道义和血性,走向了生命的觉醒和退让。白朗是个美男子,是狼牙山的寨主,在土匪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是众望所归的山寨首领。当他意识到他的成功是以牺牲无数人的性命为代价的时候,瞬间“苍老得如一个朽翁”,消了“一代枭雄”的志气,人性的自省让他归隐了山林。五魁的生命轨道恰好和白朗相反,他由一个憨厚、老实、勤快,有一颗充满责任而良善的心的“驮夫”变成了一个匪性暴戾土匪。人性的善终于在极端中转化为恶,这恶昭示了善的隐痛,揭示了善恶互为相依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侠义的品性在极端环境中也可以摇身而变为匪性,“侠”的血性忠直和“匪”的放纵残忍距离其实很近。天鉴(《晚雨》)的“变”和白朗、五魁又是不一样的,他不是在极端事件的刺激下突变的,而是在由“匪”而“官”的过程中渐变的,他的“变”体现了人性和侠性在变化过程中的挣扎,体现了人的本质在欲望中被弱化和扼杀的事实真相。《晚雨》中有两个为了成全天鉴,为朋友之“情”兄弟之“义”、为报知遇之恩而死的人,一个是故事开头的“小匪”,一个是王娘举荐的督渠严疙瘩,这是作者真正赞美和讴歌的人物。小匪和严疙瘩的行为彰显了任侠的“损已而益所为”的精神实质。作品的侠义的内涵也从这两个人物形象凸现出来。
贾平凹的笔下也有恶的土匪,《美穴地》中的苟百都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一副奴相,阴险狡诈、巧取豪夺。当了土匪就强占四姨太,枪崩刚为自己帮忙的柳子言,最后为了尽快占那吉地,硬是将老娘“掀进沟里跌死,对外说是失了足”,人性的恶,匪性的凶残在苟百都身上有了最完整的体现。
〔1〕杨经建.侠文化与 20世纪中国小说〔J〕.文史哲, 2003(4):156.
〔2〕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七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40.
〔3〕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9.
〔4〕罗维.百年文学之“匪”色想象[D].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绪论:1.。
〔5〕〔7〕〔9〕〔11〕尤凤伟文集:第三卷〔M〕.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543.544.302.89.
〔6〕〔10〕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47.
〔8〕王达敏.土匪形象的又一种改变——杨少衡小说《昨日的枪声》的人道主义意蕴〔M〕.文艺争鸣, 2010(5):157-158.
〔12〕〔1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70-171.
〔14〕〔16〕莫言.红高粱〔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4.
〔15〕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M〕.北京:三联书店, 2006:217.
〔18〕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编〔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1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