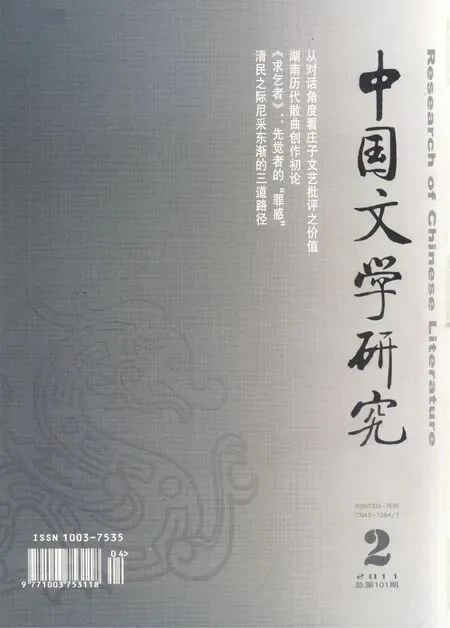底层叙事:阶层美学的凸显
滕翠钦 刘小新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福建 福州 350001)
一
底层是对社会某种类型人群的命名,它的“社会面相”由众多个人活生生的人生经历构筑而成,所以它们并不是毫无血肉的抽象体。底层拥有落魄的生活经历,人们用“底层”这一具有具体象征意味的空间词汇表达这个群体给人的习惯性印象。这个群体并不像“人民”、“无产阶级”那样,是一个有机群体,它只是人们对某些人的生存方式的归纳总结。很久以来,中国社会更钟情于持久的“组织和集体生活”的非凡形式,群体被认为是社会形式的惊人象征,这些有机的组织和形式更像一副充满生命的身体。有机性群体中必有一个权威机构对这个群体的社会行动做出规定,个人必须拥有某种实在的姿态以表明他是这个有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些划分的标准具有绝对的政治意味,它们被看成是对这个社会景观的一种本质表达。这个机体的繁荣和衰落成为历史进步或者倒退的关键标志,和其他那些无关紧要的标准相比,它们绝对高高在上。革命时代,“阶级”被视为“劳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实,这使得带有强烈暴力冲突的革命成为了历史的合法姿态,但这种合法性的确立在中国也是一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1925年以前的革命被认为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五卅运动之后的革命越来越呈现一种社会性的向度——阶级斗争——这最终摧毁了维系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关系的脆弱纽带。……人们对于社会矛盾的敏感性的日益增长,使过去并不需要的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更为具体更为复杂的分析,得以出现。”〔1〕所以,尽管“阶级”被看作是社会的客观事实,但它也确实是思想的建构,把阶级作为社会秩序的模式预示着深刻的心理事实。“底层”取代“阶级”同样也必然是这种事实的外在社会背景引发的适当变化。
“底层”这一“集合”并不是永久性的。人们没有有意地创造出诸多的仪式、符号来巩固底层的“集体意识”,每一个“底层人”脑袋里装的东西并不一样,他们不会都是“同病相怜”。“底层”的内部成员甚至没有认识到“底层”这个命名本身对于自己存在怎样的约束力。这个术语与其说直接反映了弱势群体的真实境况,不如说它是知识精英某个历史阶段思想结构的具体展示,是知识分子的文字游戏而已。“底层”实际的政治效力大大降低,它只是人们叙事的众多平等角度中的一个。“底层”没有过多深层的寓意,而只想实实在在地反映现代化潮流中某个群体的社会经历,讲述那些社会卑微者对财富的向往,他们在繁华街市和落后村庄里的哀伤,他们的愚昧和朴实。“底层”更多时候安守于缓慢的日常生活。“阶级”是对群体集体生存的想象的深刻变形,人们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同阶级的观念井水不犯河水,而且必然相互咬牙切齿。在一个适当的时间,他们之间就会发生激烈的流血冲突,然后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就诞生了,这种更替的形式变成历史的必然性特征。因此,如果说“阶级”经常沉浸在革命的狂喜中,那么“底层”则重新回到社会学领域,人们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审视群体间的关系。“底层”没有“阶级”式的极端悲观和极度乐观,这种情绪的大起大落将会丧失对现实社会细节的冷静审视。人们在追溯“阶级”概念缘起的历史心理背景时相当深刻,“在欧洲的社会理论中,阶级这一‘习惯’出现于19世纪人们对法理社会的稳定性和合理性所怀有的悲观主义。它以及同其相联系的社会主义政治学说,体现了一种对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共同体)以及对被个人主义秩序破坏了的传统形式的怀旧意识。”〔2〕这段话的意思是,“阶级”源自怀旧意识,对旧事物的肯定不是出自革新的目的。但后来,“阶级”背后的思想背景发生逆转,对现存社会的悲观和不信任是建立在未来美丽新世界的乐观向往之上的,这种线性的发展观和断裂观赋予了革命以无限的动力。因此也可以说,人们关注“底层”是为了反思社会弊端,但它却说明人们对不同群体和平共处的信心,这也印证了前面提到的“功能主义”的说法。
某些人断定,热衷于社会功能的“底层”概念缺乏未来的时间向度,这一概念对任何事物都缺少可贵的激情,力求问题“客观性”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深深的悲观,但这些结论都显得过于单薄。“消灭贫困、消灭贫困所引起的‘生存斗争’,将为这个转变提供物质基础……然而,社会风气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所要求的心理上的革命,不仅仅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也不仅仅意味着物质财富和福利的纯粹的‘爆炸’。它们意味着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的革命,这场革命将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协作和团结成为经济活动发展的动力。”〔3〕“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分裂在传统阶级理论中是基础,消费者总是被假想成十恶不赦的剥削阶级,他们是毫无生产力的社会寄生虫。但在现在这个“物质发展”的年代,这两种社会身份是弥漫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同时拥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这样生动的社会景象并非“冲突”两个字所能容纳。“底层人物”甚至不可避免地对“富人”的生活产生强烈的憧憬,李师江的《廊桥遗梦之民工版》中讲到的主人公对“传宗接代”的“愚公”式的个人理解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钱仁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猛然醒悟到传宗接代的真正含义:自己不能实现的任务,由儿子来完成,儿子完不成,孙子再来,子子孙孙,总有当上包工头的时候。甚至,别说包工头,就是皇帝最终也能当上。”〔4〕可见,“成为富人”会成为某些“底层人”几代奋斗的目标。
二
“底层”首先避开不同“社会群体”绝对冲突理念。“阶层”一词取代“阶级”意味着以经济差异为根本的人群区分标准的取消。因此,大型的“社会冲突”逐渐式微,并逐渐被社会中“非暴力的权力制衡”所取代,人们更多时候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自身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就目前看来,战争意象无法恢复昔日的力量,战争更多时候被看成是“人道主义”的沦丧,至于它是否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人们大都无心过问。社会差异带来的“怨恨”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行动对抗,都无法变成社会的普遍现象。另外,这些对抗群体很多时候夹杂了私人的情绪,这种冲突也不会上升到对另外一种全新社会形态的普遍诉求。时下,人们甚至将适当的冲突看成是对“底层”不满情绪的及时疏导。那么,当“底层”进入人们的视野,并被界定成现代社会全面发生的事实时,人们在文学叙述中如何呈现“底层”的集体状态呢?在《那儿》当中,为“底层”利益请命的“小舅”并没有号召出底层的同一行动,人们更多时候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做出选择,这里并不存在整体的阶级利益。所以,文中的“小舅”不但被权力部门的规则消遣,而且也被那些“困苦”的底层所背弃。文本里写得很清楚,“阶级”带有的伟大昭示在这个时代里并不吃香,它无法上升到令人晕眩的理论高度。小舅心中的疑惑显得相当悲凉,“工人阶级怎么能这么冷漠?这么自私?这么怕死?这还是从前那些老少爷们的兄弟姐妹吗?”〔5〕可以说,革命时代“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在小舅的心中根深蒂固,这也决定了小舅如何选择自己的生命方式。小说中“记忆中的姥爷”和“狗”成为小舅命运的镜像,但是这两个参照物都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一个是“亡者”,一个是人们眼中的“小畜生”,作者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表达现实生活当中“人和人之间要达成共识”的艰难。“姥爷”的英勇事迹在小舅内心形成了某种卓越的记忆,这种记忆塑造了他的性格,但小舅的失败开始透露出这种昔日的“革命英雄”的光荣行为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可行,它无法在人们心中变成一种心理模范。小舅心中那个“卓越的记忆”没有加入现代心理的塑造过程,只能被安静地陈列在博物馆里,变成人们的参观对象。在另一方面,小舅的失败说明“底层”本身并不同一,“革命阶级”的步调一致而今已经变得相当奢侈。“事情并不像小舅想象的那样,他振臂一呼,然后应者云集,然后大家同仇敌忾就把厂子保住了。小舅的错误在于,他根本忘记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6〕尽管小舅内心怀有继承革命传统的强烈愿望,但是成为“姥爷”那样的英雄是过去的传奇,在现代社会,成为这样的英雄也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奇,“小舅”的最大错误是“生不逢时”。流浪狗“罗蒂”却拥有和“小舅”一样壮烈的死亡方式,这种参照说明了“人和物”的差别要比“人和人”的差别小得多,现代社会想要“革命主体”那样同一的群体观念很难。但关键的问题是人们是悲观地看待这种差异,还是理智地审视这种“差异”?有人质疑《那儿》的主人公不是“底层”,而是“知识分子”〔7〕,小说反复重申的还是个人“英雄主义”,小说中关于“罗蒂”的情节简直就是一则“动物寓言”,其中不乏对英雄“独行”姿态的称颂。即使这个定论不可动摇,问题是文本透过某个“知识分子”的命运折射出来的“底层”群体面貌也极其到位,但“苦难”毕竟不是“底层文学”的唯一内容,底层的“阶层性”也是文学书写不可回避的方面。
作为社会学概念,“阶层”预示着阶级关系逐渐从对抗走向了对话,人们仍然承认“阶级”关系最终潜在的作用力。今天,“阶级”权威的确开始被挑战,对此,“阶层”背后的“商业逻辑”首先挑起了大梁。80年代后期,当商品经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方向时,“阶级”开始被戏仿,因为它褪下了那些偶像般的意义,变成了社会现象中的普通一员。“只要五元钱,阶级关系就可以调整。戴足金项链的漂亮小姐,可以很乐意地为一个脸色黝黑的民工演唱。二十元钱就可以买哭,漂亮小姐开腔就哭。她们哀怨地望着你,唇红齿白地唱道‘人家的夫妻团圆聚啊,孟姜女,她的丈夫却修长城哪’,漂亮小姐一边唱一边双泪长流,倒真的是可以在那么一阵子,把你的自我感觉提高到富有阶级那一层面。”〔8〕在金钱的蛊惑下,原先“神圣的阶级关系”被商品化,变成街头小贩肆意的表演。人们对有钱人生活的向往在这些表演中得到了满足,这也说明在现实生活中,底层和富人在某些层面上实际上是融合的。革命时期“水火不容”的两种事物以商品交换的形式平等存在,“阶级”的政治严肃性消失殆尽。金钱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人多力量大”的理念在金钱面前显得十分脆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是社会形式的原点,绝对不可被“戏仿”,一旦如此,就是对现有统治秩序的亵渎。但悖谬的是,以经济基础划分的阶级一旦开始变成了真正的商品形式,立即就被取消指称的合法性。阶级和阶层从最终的意义上而言,都是从物质的角度进行划分的,前者虽然是对物质的崇拜,但是这种物质绝非是商品,后者开始完全浸润到商品的汪洋大海中。“底层”包含的是关于群体生存的随意事件,但人们却迅速捕捉到这些随意背后固有的社会原因。一些人认为“底层”取消了“人民”背后“理想主义”的色彩,进而将“公民”视为未来发展的理想主体,这是对“未来平等”的想象。
随着“底层”的出现,对立的阶级关系也逐渐被更多元的主体间关系所取代,这样就避免了对不平等原因的本质主义追溯。有人甚至开玩笑,“很长时间以来,肌肉发达的人们一直在欺负不发达的人们”。〔9〕这句话将人类长久的物质和精神压迫的根源追溯到人的生理状态,这就取消了社会和文化的那些不平等的结构性存在,把社会变成了普遍野蛮的动物世界。当然这句话是有背景的,作者主要是反对将各种社会生活的实质单纯地归结到某种理论阐述,例如普遍的“父权主义”。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理论的描述,是以牺牲社会复杂性和丰富性为前提的。与其说父权主义是普遍的,不如说单纯直观的、生理性的、无太多文化因素的“肌肉发不发达之间的对立”更为普遍,所以这背后的讽刺意味是非常浓厚的。
三
生理、性别、年龄等原先被忽视的因素造成的社会等差是人们认识“底层”的重要维度。从“人民”到“底层”的转变,意味着“阶级”的语义在新的现实面前遭遇深刻的质疑。“阶级”具备许多关于革命的浪漫和激情,“革命的宿命论”让群体开始从社会现实经验的琐碎中挣脱出来。但是“底层”恰恰相反,人们关注底层,最重要的不是是否将社会发展的短处揭示出来,而是要避免政治话语的模糊性,力图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寻求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人们对底层的划分从“物质”角度出发,当然,“阶级”最终立足的也是经济角度,那二者之间又有怎样的区别呢?前者“物质”仅仅是划分的标准之一,很多时候,人们是从“文化资本”的角度观察社会群体的差距。人们发现“文化贫困”有可能使人们丧失摆脱物质贫困的机会,而如果仅仅只是“物质贫困”,那么人们根本无需畏惧这些暂时的困难,因为地位“世袭”被废除,人们改变境况的机会要多得多。这个观点实际上又承认了“贫困”源自个人素质。而阶级论则把经济作为最终的划分标准,似乎只有一个人口袋有了一定的钱,就会“荣登”剥削阶级的行列。当然,基于这些不可回避的缺点,也有人因此要取消以“人群”的“阶级和物质”为出发点的划分标准,人们认为这些“卑贱的物质”意义上的区分仅仅只是停留在人的表象,而“道德和精神能力”才是人和人之间“差别”的本质所在。但是,除非承认这种道德和精神的划分只是某种暂时的方法,否则一旦它们上升到“形而上”的层面,这种划分标准就同样取消了人的差异的复杂性,这和“阶级论”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将精神能力作为人区分人的最终标准,这种做法很快陷入保守主义的陷阱,将人的弱势看成是个人素质的问题。尽管有人已经指出底层人的高尚道德,但这种区分将导致人们对社会物质贫困的漠视,将贫富差距合法化,最终将取消底层现象背后深刻的社会根源。
阎连科在《受活》中塑造“社会底层”的标准恰恰是处于“经济”和“文化”之外的。在这里,人和人之间的区分来自最“形而下”的“肉体”差别,这样就使来自于经济的阶级划分标准重新陷入混沌。“男人说,啥王法,圆全人就是你们残疾人的王法”〔10〕是整部小说的文眼,身体的优势蕴含统治的欲望,但这却被解读成是有利于社会秩序的规范化“道义”。“王法”恰恰是民间的原始治理形式,这种形式和“公正与平等”无关,而是与野蛮和随意有关。所以,小说当中宏大的政治语汇——“人民”——所持的天然道德优势已经失落,在原来的社会语境中,“人民”的道德性是革命政治意识的必然前提。在阎连科的小说中,人民的缺陷是历史的必然,甚至成为这个整体不可逆转的命运,所以他只好想象出一个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世外桃源”。阎连科描述一个令人惋惜的事实,身体和道德之间并成正比,道德的沦落变成成为一个圆全人的必要前提,例如槐花的经历,她靠和圆全男人睡觉而成为了圆全人。在这部小说中,道德的完美全都回归到一些毫无美感的身体当中去,而让那些圆全人扮演自以为是的愚人。作者构想出一个超越所有现实政治制度的单纯的生存世界,“退社”成为主人公“茅枝婆”最终的人生目标。“茅枝婆”始终以“老革命家”的姿态出现,这就消解了“革命”和“人民公社”在原来的社会语境中牢不可破的关系。“革命历史的政治语汇”不过是外在的政治秩序强加给“受活人”的零余物,这种强加物剥夺了受活人原先宁静的山野生活。“划分地主、富农、贫下中农的事”原本是“革命历史中最为关键的一课”,在“受活人”那里却成了人们急欲挣脱的无用重负。
在这个并不脱离现实时空的地域之中,身体残缺的“受活人”的生存不再是一种天真的民间形式,他们拒绝某些极端的政治形式对生命自由的剥夺,热衷于对“丰饶和乐土”乌托邦的强烈想象。在与外在“现实世界”的总体组织形式丧失仅有的微弱联系之后,“受活人”终于拥有非凡而美好的生存形式,尽管这种形式带有原始主义气息。我们有理由怀疑阎连科心里掖着太多“原始主义”情结,在小说中他似乎力图把生存图景拉回到久远而古旧的社会。“受活”和“外在世界”的区隔带上了神秘的气息,自然气候的差别在两个世界之间划开了遥远的距离,“说到底,世界上还是冬天哩,耙耧外的世界里漫山遍野落了雪,结了冰,只是耙耧山脉里却越过了春天,到了夏天了。不仅树都发芽了,长成叶片了,连坡脸上的草地也都披挂着绿色,一坡脸的葱翠了”。〔11〕当然,《受活》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底层小说”,这是因为这部小说是对“底层”命运的寓言式书写,它对“底层”理想生活的想象和当下人们关注“底层问题”的社会目的相距甚远。尽管故事铺开的背景是人们熟悉的“现代性”,但是二者的最终目标却并不一样。人们并不想因为“底层”的存在就开始极力追求和现行社会形式相异的简单的、无“欲望”之扰人的组织模式。但阎连科在“商业”面前退避三舍,他要让深受“商业”伤害的“受活人”和那个热闹而堕落的“健全人”世界彻底了断。
以“身体”为人群划分的标准乍一看是不可原谅的短视,它忽视了广大社会场景中涌现出的无限错综复杂的现实性,但这个标准至少放弃了占优势地位的“阶级”众多牢不可破的规定。在这些规定中,“身体”根本上不了知识和理论的台面,它大多数时候存在于深闺的“枕边书”中或者意图蛊惑人心的淫荡言论中。可是现在,且不说“身体”标准的寓言性质,在社会“阶层”中,“身体”已经富有强盛的意义生产力。这个标准从另一个角度反衬了“阶层”概念描述人群时的独特有效性,人们开始发现“躯体”竟是社会秩序的缩影,躯体修辞对人的文化身份至关重要。但是躯体只是阶层划分的标准之一,社会群体的“划分”是极其复杂的,人必须有“集体性”,但这种“集体性”的属性是流动不居的。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社会场合,人们的社会角色完全可能相互冲突。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对人群所做出的哲学层次上的“机械划分”的“阶级”忽略了日常生活的多变和差异,这种划分方式在于混淆了“结构”和“行为”。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阶级意识形态阐释的效力就大大降低,对人群做出本质主义的区分显示理论实用效果的滞后,许多社会事实靠简单的二元对立是说不清楚的。反过来说,人们认为“底层”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传统“阶级”观念的旁落,“阶层”概念更适应新的社会现实。但前面提到的农民阶级的内部区分暗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被“阶层”取而代之的“阶级”概念是特定“革命”语境下的。事实上,人们早就开始用“阶级”分析社会群体的复杂情况,尽管它的出发点还是经济,而且划分人群的角度不像阶层那么“多样化”,但它已经像“阶层”那样,注意到群体内部的多样性。
〔1〕〔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M〕.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49-50.
〔2〕〔英〕戴维·李、布赖·恩特纳主编.关于阶级的冲突——晚期工业主义不平等之辩论〔M〕.姜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29.
〔3〕〔南斯拉夫〕米洛斯·尼科利奇.处在 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M〕.赵培杰、冯瑞梅、孙春晨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01.
〔4〕李师江.廊桥遗梦之民工版〔J〕.上海文学,2004(1):52.
〔5〕〔6〕曹征路.那儿〔A〕.那儿〔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72,71.
〔7〕张硕果.还是知识分子,还是困境——评《那儿》〔J〕.当代作家评论,2005(6):101-103.
〔8〕池莉.生活秀〔A〕.雷达选编.近 30年中国中篇小说精粹〔C〕.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327.
〔9〕〔法〕理查德·罗蒂.女性主义、意识形态和解构主义:一个实用主义的观点〔A〕∥〔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等.图绘意识形态〔C〕.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1.
〔10〕〔11〕阎连科.受活〔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4:164,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