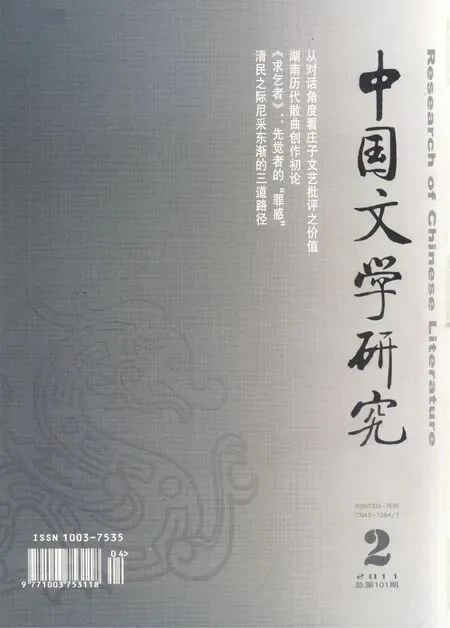商业文化的误读
——鹿子霖形象的象征意义
赵 智
(湖南商学院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白鹿原》是陈忠实第一部长篇小说,但却毫不夸张地说是中国近几十年最为优秀的作品。亦如海外评论家梁亮先生所云:“《白鹿原》是大陆当代最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并不逊色”。[1]作品从一个家族斗争的视角客观地描写了 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渭河平原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作者在小说卷首引用巴尔扎克的话:“小说都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很显然,作者写作目的就是要真实地反映中国民族的现代史。以历史学家眼光来看,上个世纪不只是中国,而乃至世界都是最不平凡的时代。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合作,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直至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波澜壮阔、变化莫测的历史,都在《白鹿原》中得到具体显现,小说写白鹿原两家(实为一族)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权明争暗斗,动魄惊心。而白嘉轩、鹿子霖这两个家族的代表,作为全书主人公贯穿始终,要读懂《白鹿原》,就必须读懂白嘉轩与鹿子霖,而这二个人物又都是读不透的,大有“说不尽的王熙凤”的艺术魅力。
在《白鹿原》中,鹿子霖始终是与白嘉轩作为对立面而存在的,对于这一艺术典型,人们已有太多的论述与解读。总其大端,对鹿子霖无不是取贬斥的态度,认为他是商业文化的代表,认为“以白嘉轩为代表的白家和以鹿子霖为代表的鹿家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中国由此已久的两种文化——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斗争的体现。”[2]因而鹿子霖人格上的卑微与人性上的丑恶,就是“商业文化对其的挑战在鹿子霖依然呈现卑微丑恶的形态,是恶的个人主义的需要”。[3]鹿家的发迹,与白家自给自足的农业文化完全不同,是“以劳动作为商品以烹饪作为技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价值交换,这种商业交换要求确证个人价值,强调个人奋斗,恩仇有报,恩怨分明”。[4]甚至有人认为,小说对鹿子霖的描写与贬抑,“无不反映出潜在的意识中作者陈忠实重义轻利轻商的一种文化心理”。[5]总之,鹿子霖是商业文化的典型代表,其立身行事乃至诸多恶迹无不是受这种非农业文化的支配。事实果真如此吗?回答是否定的。对鹿子霖做出这种判断乃是对商业文化的误解。通过对鹿子霖形象的分析与对商业文化的解读,不难发现,鹿子霖是具有一个象征意义的艺术典型。
—、传统文化的背叛
作为鹿家的第二代,鹿子霖开始便是与白素轩对立的。他五代前的先祖鹿马勺是一名乞丐。为了生存,他从生养他的农村流入城市;历尽艰险与苦难,成为一个名尉。也许是生活给了鹿马勺太多的屈辱,所以留下遗嘱,鹿家子孙后代一定要好好读书,读书做官就能改变命运,光宗耀祖。鹿氏遗嘱,所反映的完全是中国传统“耕读传家”的文化思想。但是,到鹿子霖的身上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几乎彻底背叛了这种传统的民族文化,流于卑琐与无耻。他逐利,手段卑劣,无所不用其极;他求官,则根本不想走科举一途。作为封建宗法文化负面价值的鹿子霖,集虚伪、自私、残忍、阴冷于一身。
他唯利是图、自私残忍、阴损冷漠、虚伪无耻。为了一己利可以抛却道义、甚至亲情。他的所作所为无不与传统道德背道而驰,但又时刻不忘给自己披上一件“仁义”的外衣。他时刻牢记着先祖鹿马勺的教诲:“无论你将来成龙还是成虫,无论你是居官还是为民,无论你是做庄稼还是经商以至学艺,只要居于人下就不可避免要受制于人,就要受欺。你必须忍受,哪怕是辱践也要忍受;但是你如果知识忍受而不思报复永远忍受下去,那你注定是个没出息的软蛋狗熊窝囊废;你在心中忍着,又必须在心中记得,有朝一日要踩到他头上,让他也尝尝辱践的味道。”为了做人上人,他一辈子与白嘉轩争斗。白为长房,族权鹿子霖无法问津,他便把目光投向了政权。辛亥革命的到来,他对此根本是一无所知,但他却认定这是一次机会,便顺应形势摇身一变成为“乡约”。后来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土地改革等时局动荡,他犹如一株墙上草能随风而动,企图从中捞取资本,达到做官最终发财的目的。尽管他被诬陷度过两年的铁窗生活之痛,曾一度发出“瞎也罢,好也罢,我都不管它?种二亩地有一碗糁子喝酒对嘿”的叹息,但洞察世事,心如止水,实际上依然故我。正如冷先生所说:“我只说他从监狱里似乎回来,该当蹲下来了。没料到在屋里蜷了没几天,又在原上蹦开了。这人啦,官瘾比烟瘾还难戒!”鹿子霖如此热衷于当官,其目的就是一个,可以依仗权势、欺压他人、强取豪夺、谋取私利。他一当上“乡约”,便与田富贵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倚势恃强、鱼肉百姓。同政治上的蝇营狗苟相投的是他在道德上的肮脏败坏,卑鄙无耻。他淫乱成性在白鹿原上,凡有点姿色的妇女都被他奸污过,以至于长的像他“深眼窝长睫毛”的“干娃”可以坐三四席。他甚至乘人之危奸污田小娥,又唆使田小娥勾引白孝文以打击白嘉轩,田小娥最终为其公公鹿三残忍杀死,但鹿子霖完全是凶手之一。就是他儿媳因“淫疯病”被冷先生亲手毒死,也无不与鹿子霖阴损毒辣有着直接的关系。
鹿子霖是邪恶的,但他又极力保护自己的人格面具,见人一副笑脸,令人感到和蔼可亲。他恶施美人计陷白孝文于不仁,又策动“跪谏”为孝文求情。白嘉轩“捉奸”气昏在田小娥屋子里,他会适时出现将白嘉轩背回家,既做了好人,又损了对方的面子。可谓一箭双雕,阴毒而虚伪至极。小说中有一段写鹿子霖荡秋千,说他“一上秋千就引起满场喧哗,他不是以高度取胜,而是以花样见长,他一会儿坐在踩板上,一会儿又睡在上面;他敢于双足离开踩板只凭双手抓住皮绳,并将身体缩成一团;他可以腾出一只手捏住鼻子在空中擤鼻涕,故意努出一连串的响屁,惹得树下一片亲昵的叫骂。”这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描写,作者用暗喻的手法形象地展现鹿子霖喜欢张扬卖弄,有心存邪恶的性格。这样一个为了名利不择手段,急功近利,放纵张扬的人物,是完全没有传统商业文化精神的。
二、商业文化的解读
说起商业文化,人们往往容易与逐利、纵横、欺诈、阴毒等不良品质联系在一起。所谓“无商不奸”是也。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也正是这种对商业文化的误读,才导致人们把鹿子霖当做商业文化代表的错误判断。我国是个农耕古国。“农本商末”“重农抑商”为历代的基本治国策略然而“抑商”并非是抑制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周易.系辞》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制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即充分说明商业性质及其功能的重要性。基于此,所以要求商人在市利的基础上,反对贪利而忘义,见利而丧德。这种商业道德的构建,完全是按照儒家传统文化而设置的。
首先,为商者必须以仁义诚信为本。“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作为人修身处事的总体道德规范。古之商人,同样把“仁”奉为做人与经商之圭臬,不易之法则。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商人对社会有一种责任感。对他人有一份博爱,能以平等心去对待任何人。于是,经商准则之中就有“童叟无欺”,“不以利小而不为”等行为规范。讲诚信、不欺诈、货真价实、不短锱铢。而小说中的鹿子霖却完全是作为“仁义”的对立而出现的。
其次,轻财重义,义不取材是传统商人正确的义利观。经商之由,本在争利,故为商者,尽管也确有为利而不择手段者,但这不是古之商者所倡导的职业规范。古之经商,绝不会如鹿子霖般为逐利而不择手段,甚至丧失良知,他们秉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只取正当之利,不贪分外之财,尤其是在大义面前,能顾大义而舍小利。《左传》中“弦高犒师”事件就是很典型的范例。
在对待金钱上,传统商业文化也是遵循儒家天道观而有着较为进步的金钱观。古人认为天道至公至廉,了无贪欲,为人处世,必须合乎此道。故为商者,不可唯利是图,应以善为本,不义之财,有如浮云,富不可骄,贫不可欺,安贫乐道,天必佑之;为富不仁,天必诛之。在《白鹿原》中,鹿子霖何曾有一点传统商道的风范。当上乡约,便迫不及待到先人鹿马勺坟上放铳、放炮,大肆渲染。小人得志之势,不可一世之态,跃然其间。他从无同情弱小、乐善好施之举,有的是欺凌弱小,多行不义之为。白狗蛋这样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可怜者,只因在田小娥窑炕上学几声狼叫,鹿子霖就依仗政权,派两个团丁打断他的腿,使其在非常痛苦中悲惨地死去,顺利时得意忘形,倒霉时垂头丧气,等等这一些,没有一丝传统商人的内在精神。古之儒商,家有余财,一则行事要谨慎,不要骄横,用心处事,不昧天良。一则乐善好施,广积阴德。较之这些,鹿子霖又何曾能代表商业文化呢?
更重要的是,传统的商业文化在为人处事上,特别讲究“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是妇孺皆知的古训,体现在接人待物上,就是“执中”为道。商人经商,对象是人,要让顾客如坐春风,要使自己诸事能忍。鹿子霖为人,多是阴狠卑劣,丑恶龌龊。当然,他也有微笑,但那不是他内心真情,而是化装的伪饰。越是微笑,越是凸现出这个人物的虚伪与可憎。
综上所述,鹿子霖的性格中,几乎找不到传统商业文化的内在精神。诚然,他有着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一面,更有着不守旧制、趋向新潮的精神,但那并非商业文化精神之所致,而是他趋利悦货的性格的另一种表现。也一如他并不了解诸多的“革命”,却对每一种“革命”都向往之,其终极目的就是寻找机会,大发一次,投机取巧,如是而已。
三、负面文化的象征
有人认为:“以白嘉轩为代表的白家和以鹿子霖为代表的鹿家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中国由来已久的两种文化——农业文化和商业文化斗争的体现。”[6]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椎的。尤其是列宁之所论,在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是两种民族文化,并非指任何民族具有二种文化的意思。事实上,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复杂的,多元的,决非只有二种。以中国为例有儒家的文化,道家的文化,墨家的文化,形形色色,难以数计。列宁所论,乃是指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有着正负两个层面的内涵。譬如中国的道家文化,其正面内涵是清静无为,顺应自然,淡泊名利,乐观开朗;负面的内涵则是消极无为,因循守旧,悲观厌世,不求上进。这才是列宁所论的要旨。《白鹿原》所反映的民族文化,究其根底,乃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作者自己曾经说过:“当代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起初的那种思绪,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性境界,甚至连‘反右’、‘文革’都不觉得是某一个人心偶然的判断失误或是失误的举措。所有的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7]很显然,作者探求的必然是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而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则是儒家的文化,毫无疑问,作者要宣扬的就是传统儒家文化。所以,“《白鹿原》是一曲儒家文化的颂歌,主人公白嘉轩作为儒家道德的现实承担着,受到了作者格外的推崇”。[8]由此可见,白嘉轩所代表的是儒家文化的正面价值,毫无疑问,作为白的对立面的鹿子霖,代表的自然是儒家文化的负值。儒家文化同样有着正反二个层面的内涵,挚其大要,即“君子”与“小人”之别而已。君子小人的区分原则又主要在“义”与“利”。谁都承认这样的事实,在《白鹿原》中,“仁义”二字贯穿其始终,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它不只是一条个人修养准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基因和激素,正是这种基因和激素在不断以不同方式激活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方呈现出种种不同的风貌,而文化之脉也得以世代延续”。[9]可见“仁义”在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在传统儒家文化中,与“仁义”相对立的即是“利”。“义利之辩”是儒家文化价值观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志。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与利。”君子者,见利思义,为人舍利;小人者,见利忘义,为利丧义。泾渭分明,对比分明。在《白鹿原》中,白嘉轩是君子,鹿子霖是小人,儒家文化中正负值的二种文化代表,白鹿二人是非常典型而真实的。白嘉轩主张的是耕读持家,他倡仁义,守礼法,沉着冷静,坚毅顽强,具有一种强大的震慑人心的人格魅力。而鹿子霖呢,信奉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哲学,追名逐利,不择手段,抛弃仁义,唯利是图,体现的是一种遭人唾弃的小人德行。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鹿子霖使用各种卑劣手段,即使有过暂时的胜利,但最终都斗不过白嘉轩,他自己无法理解为什么总是白嘉轩获得胜利。当其发出“天爷爷,鹿家还是弄不过白家”的悲叹,其实道理很简单,得人心自得天下,广施仁义,宽厚待人,自然能具有强大的精神感染力,最终一定能获得事业的成功与道德的胜利。而小人反其道而行之,多行不义必自毙。当然,这个道理鹿子霖是无法弄懂的。尽管到了后来,他也感悟到“你说啥最珍贵?钱吗地吗家产吗还是势吗?都不是。顶珍贵的是——人”。但这只是生活受到重挫之后的短暂感悟,紧接着,他在一个旧时“相好”的启发下,在原上各村庄搜寻自己的私生子,认作“干娃”,最终还是回到他那小人的道德范畴之中。
总之,鹿子霖的形象所代表的不是商业文化精神,而是儒家文化的负面价值,其形象有着象征性意义。在作者看来,负面的文化必须产生道德的怪胎,对于任何一种文化,应坚守的是正面的价值,只有这样,民族才有希望,社会才能进步。
这既是鹿子霖这一典型形象的美学意义,也是作品透露给我们的文化信息。
[1]梁亮.从《白鹿原》到《废都》看大陆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5.
[2][6]李文军、吴潇芳.历史是一杆秤,文化是掂量好砣〔J〕.苏州职工学院学报,2006(1).
[3]王健、李文军.试论《白鹿原》中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J〕.苏州大学学报,2000(1).
[4]余蕾.《白鹿原》中人物结构解读〔J〕.湖南社会科学,2004(3).
[5]纪芳芳.论陈出寮在《白鹿原》中对传统文化的态度〔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2).
[7]陈忠实.走出白鹿原〔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270.
[8]高旭东.比较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85.
[9]唐云.觅我所失:论《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禅释和留连〔J〕.小说评论,1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