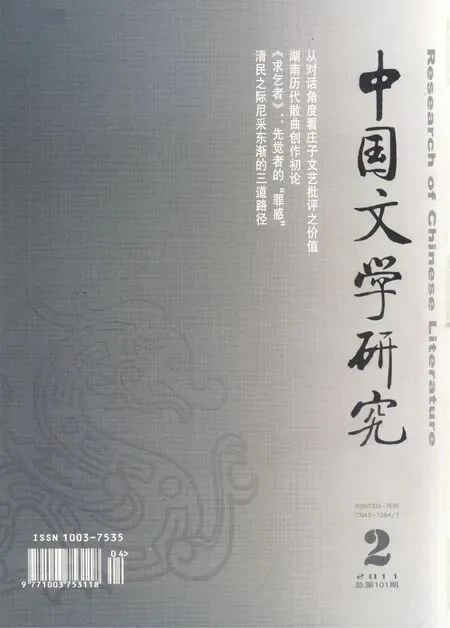中国儿童幻想小说的生态意象
何卫青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中国儿童幻想小说在经历了 20世纪 90年代初的理论自觉之后,从 90年代至今,其创作一直处于方兴未艾的态势。阅读这些作品,一个最直接的感受是:小说对童年在野外的生活异常关注。而且,这些小说所塑造的“形象“在美学上与发展着的社会格格不入:天性好奇单纯、感知敏锐聪慧的儿童、精灵;荒原上无拘无束的唱和跳、大海边宁静的遥望,月亮河畔孤独的沉思、魔塔里、森林中惊心动魄的冒险;荒原、海岸、花园、沙滩、溪流、森林……它们属于于童年也属于自然,“格格不入”因为它超越了成年人文化的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一方面,小说在对大自然非再现的泛灵泛神的狂野想象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迥异于现代思想的另类解释;另一方面,又把童年作为与大地、与各种动物、植物形成联系的重要纽带。这种童年时代的纽带“具有神奇的效果,可以使人在生态方面富于想象力”。〔1〕这些形象,伴随着小说的主人公—儿童或儿童似的动物、精灵的奇异经历,展现出一个个富于生态意义的过程。它们在记忆中唤起并维护的东西隐藏着我们无法清晰表达的内心需求;它们与我们无意中的某些沉淀产生了共鸣,它们令我们对人造物和人为事件的敬畏感重又转向大自然,并带上了超现实的、精神的特征。这样的“幻想”因而成为一种“表达人们心中不断涌现的田园冲动的方式”。〔2〕
由于这些形象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内涵,所以,采用生态批评的视角,它们便成为中国儿童幻想小说表现自然意识、传达生态预警、生态责任以及生态理想的生态意象。根据其所属的不同的美学层次,笔者认为中国儿童幻想小说的生态意象有三种:自然、地方、身体。
一、自然
现代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不少都是逃离乡村,试图在城市中重建梦想,但城市(意味着与土地、自然的分离)使生命变得炽热、肮脏而又饥渴。与之相反,儿童幻想小说的主人公们却往往是从城市出发,从现实之境到幻想之境的穿越、从此地到彼处的探寻其实是一次次向自然的回归:阁楼精灵们向着被人类遗忘的精灵谷(汤素兰《阁楼精灵》)、沈雪和孩子们向着西南大森林(班马《绿人》)、神奇的邮路在赣南原始森林(张品成《神奇邮路》);穿越神奇的闪光胡同之后,男孩小瓦目睹的是一片美仑美奂的落日海滩(薛涛《精卫鸟与女娃》);而鼹鼠米加从月亮河(王一梅《鼹鼠的月亮河》)、小野兔阿洛兹从苦艾甸出发的异乡(也包括城市)之旅(常星儿《吹口琴的小野兔阿洛兹》),似乎也是为了给已经与自然、大地相距很远的人们带去一缕清新的绿色气息……一句话,儿童幻想小说的自然书写是在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界线的前提下的书写。“想象”重建了自然的神秘、威严与包容,也重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小说中,“自然”不再被看成人类之外的一个领域,其中的每一种生命,人、动物、植物等等,所有的物种都是休戚相关的。“情智”这个在现代思想中仅为人类所独有的属性在中国儿童幻想小说中弥散、延展到了自然界所有的生命体。这些生命体,无论看起来多么卑小和微不足道,都以与人类相似的情感智慧,体验着来自自身、来自宇宙万物的痛苦与快乐,同时也成为宇宙中其它生命痛苦与快乐的源泉。忠诚的大狗、报恩的秋蝉、复仇的大熊、诡异的白猫、善良的雪琪鸟、甚至邪恶的绿刺猬,都与人的喜怒哀乐、爱欲情仇联系了起来。
以班马的《绿人》和汤素兰的《阁楼精灵》为例:这两部小说以更为清晰自觉的叙事揭示了人的情感、情智与自然界的这种联系。在《绿人》中,自然景观的渲染是小说叙事的一个侧重点,从别墅阁楼上沈雪的神秘小屋、探寻绿人的考察队的阮江之行、姨父回忆中的屁股沟玉米地,亚热带江峡上的南苍山房,大西南森林里的“树屋”到考察队体验的林莽幻境,“绿色”都是一个极其醒目的色彩意象。它不仅指向沈雪的长发,小屋中的绿色植物,指向宁静的江水,苍茫的远山以及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指向“绿色智能生命体”绿人的血液,同时,“绿色”也是一个合诣平衡的自然的精神元气。被科学家们称为“绿色智能生命体”的绿人虽然是小说家虚构和想象的产物,但它同时也是自然界所有非人的动物的象征和代表,绿人颜色由深变浅,由浅变深的变化指示的是这些动物与人的关系的亲疏远近。虽然在小说中,以烟囱、电视、可乐意象为标识的现代文明、特别是城市文明成为绿人家庭生死存亡的最直接的“罪魁祸首”,但是,沈雪长期居住在大西森林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对自然界的热爱;阁楼小屋中的各种植物在疯一般的生长中不约而同为沈雪的小床搭建一片透明的空间所蕴藏的情意;六个小绿人藏在沈雪的背包中来到城市所透露出的犹犹豫豫的信任;三个孩子在科学报告会上以想象而不是“具体可靠的”生物学知识对绿人的生存状况的描述;都说明,维系人类与绿人(其实是自然界的所有其它生命体)距离的,是情感的有无与深浅。濒临危机的绿人家庭始终不愿向人类发出求救的信号,尽管可以看成是对人类文明科技所带来的负值效应(破坏性行为)的忧虑、质疑和抗衡;但是,绿人家庭向考察队的成员们的演示却是绝望之中的最后一缕牵挂,这种表演不仅以曼妙的梦幻般歌声、携裙踏舞的阵列、灵活优美的动作,以及与人类类似的举丧仪式和服饰向人类展示了绿人家族的智慧,更以“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沉默、高贵的神态和高贵的举止瓦解了人类在自然界中自以为是的高等“动物”身份,也颠覆了“人类”中心的宇宙观。
与“绿人”表现出来的这种对人类情感的犹疑相对,古老阁楼精灵们就是靠自己对人类的关怀和爱,获得永生的。“没有对人类的关怀和爱,没有人类对他们的依恋,他们就不能永生。他们的永生并不在生命本身,而在灵魂、在世世代代相传的音乐、舞蹈、绘画和其他一切艺术里。”小说《阁楼精灵》传达了一种内涵更为宽广深邃的宇宙观:不仅人类与自然万物应该和谐相处,而且大自然之外的精灵、巫师、幽灵和魔法师都是宇宙中的一分子。其中的精灵,其实是人文精神——献身的勇气、梦想的实现、英雄主义般的冒险——生命化隐喻体,他们既要从大自然的馈赠——清晨的露水——中滋养现世的生命,又要从与人类的爱的情感沟通中完成永生的梦想。当人类将森林里的大树砍倒,用它建造城市;当人类将溪谷中的溪流堵住,让水变成电、照亮夜晚;当森林消失、草原消失,人类与大自然的冲突对立日益加剧时,精灵们失去了赖以维持此时生命的露水,只能选择迁移到被人类遗忘的遥远的地方去,此时的生命得到了保障,永生的梦想却被搁浅了。“大自然”在长于科技理性的人类和象征着人文精神的精灵们之间充当了中介,而精灵们远迁精灵谷,小说表达的或许是对人类文明异化、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分裂的忧虑。小说写到:“人类在自然的照料和精灵的关怀中,逐渐强大起来了。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改造着这个古老的世界。他们让世界按照自己所描绘的样子而改变,而不是让世界按照自然本身的样子发展。”大自然被破坏、精灵们已经离去,人类的“强大”变得虚无而脆弱。
意识到自然环境改变的适度性规则,懂得大自然中的所有生命都有自己相应的生态身份,自然界并没有尊卑等级的差别,大地孕育了自然万物,也孕育了人类,所以人类不能也不该成为大地的主宰。“回归大地”这是儿童幻想小说代自然母亲发出的邀请。
二、地方
人是嵌入在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的存在。人与“地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地方是与限制联系在一起的:小区纽带、大家庭、传统以及局部的自然需求。”〔3〕这曾经是人们指认自己来处和特征的根本,尽管人们生活在一个地球共同体中,但“地方”是人们辨认自己出生地文化的场所,然而,随着信息技术、多媒体、电影电视的发展,全球化步伐的加速,文化的“异质性”正逐渐变得模糊不清。
作为“艺术异化”〔4〕的方式之一,中国儿童幻想中却出现了不少于“地方”相连的意象:小人精丁宝的“孤独孩子之家”(秦文君《小人精丁宝》)、夜晚宁静的月亮河畔(王一梅《鼹鼠的月亮河》)、被落日染红的海滩(薛涛《精卫鸟与女娃》)、野玫瑰怒放的花园(韦伶《幽秘花园》)、荒废的白楼(殷健灵《纸人》)、远离人群、鲜花盛开的秘密领地(张洁《秘密领地》)……等等。这些与天然相连的地方与孩子们情投意合,但是成年人却很少或根本不能涉足其间。这些“地方”常常是秘密的,也常常迥异于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环境,要到达这个“地方”,有时候也不是容易的事,需要一个时刻、一种契机、一条神秘的“通道”或入口,而那个地方,那个它们曾以一个孩子的全部心灵去体验的地方带给他们的感觉,会印入他们的脑海。这样的“地方”唤起了孩子们内心深处的想象力,给他们提供了庇护、支持、稳定、优雅的感觉,不仅帮助他们自己的成长,甚至也改变了他们身边的成年人的生活状态:在白楼里,女孩苏了了越过了身体成长带来的心理困惑;阁楼上的“孤独孩子之家”是一个奇异、谐趣、快乐和充满温情的世界,这个世界所给予孩子们的是他们在成人文化环境中很少或不能拥有的忠诚、平等、自由和仁爱;幽秘花园怒放的野玫瑰让女孩韦三妹的一生都散发着经久不息的香气;夕阳西下的神话海滩牵引墨守成规的男孩小瓦经历了比“现实”更真实的体验;孤独的小鼹鼠米加沐浴在月亮河畔如水的月光下,不被别人理解的苦恼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这些“地方”都与自然亲近、与“差异性”相连、孩子们在其中体验着面对宇宙的畏惧,惊讶于生命的美丽和神秘,身体和心灵追求着生命律动的和谐,在这些“地方”,蕴藏在孩子们身上的全部人类感觉都调动了起来,而这些感觉的缺失正是在宇宙自然中只看到了资源和限制的现代人不能深刻参与生活的原因所在,缺乏对生活的深刻参与,导致了弥漫在现代人心头的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和厌倦感。其实,大陆儿童幻想小说以成人文化、城市文化为背景构建它的“现实之境”,又常常以与自然有着天然联系的“地方”构建它的“幻想之境”,而且,又常常把两者设置为对立的,中心人物从现实之境出发,对幻想之境的穿越常常以对现实的单调、枯萎、不满为前提。
小说中,孩子们对“地方”的亲近,对现实之境的超越,并不是脱离关系、走向孤独的个人自主状态的过程,而是进入到对直接环境和知觉的宇宙探索的过程。月亮河的米加虽然是鼹鼠家族的孩子,但却处于现代生活环境中的大多数人类孩子一样的境地。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世界的看法不被与他们有社会关系的其它人,特别是那些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人所接受。米加黝黑的全身之与家族成员的棕色、他白天嗜睡晚上清醒的作息习惯之与家族成员正常的作息时间、他对挖掘的毫无兴趣之与鼹鼠家族世世代代的传统,所有这些对立带来的苦恼,都在月亮河畔宁静如水的月光的映照中得到了缓解,也就在这里,在那样无言的静坐中,鼹鼠米加的身体、心智都在感知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并且进行着某种协调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米加不再把自己熟悉的唯一环境当作世界的全部,因而从这里出发,踏上了确认自我的道路;幸福的“孤独孩子之家”既是小桃子、丁宝和男孩胡三郎、虫虫逃避以阿仙为代表的成人世界的冷漠、不理解和各种各样约束的秘密领地,也是这些孩子营造自我文化的成果,在这里,孩子们与蜘蛛交流沟通,攀登蜘蛛丝织的梯子,女孩子可以穿着旧被单围成的帐篷裙旋转着跳自己想跳的舞,裙边拖在地上,她们看见的不是磨损,而是因此变得像镜子一样光滑的地板,他们在地板上涂涂画画,各种身边的材料装扮着这里,并且用爸爸妈妈姐姐弟弟的角色让这个孤独孩子的家更像一个家,每个孩子对这个“家”都拥有一份责任,这个“家”不以成人世界的逻辑运行,而以联系和创造为核心,在其中,孩子们滋生的是富有同情心的智慧。
三、身体
生态批评的视角使得我们看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许多结合点。生态批评家格洛特费尔蒂指出:“在研究文学作品的描述时,生态批评不应将自然界本身作为惟一关注的中心。不少相关主题都值得探讨,包括边疆、动物、城市、特定的地域、河流、山川、荒漠、印第安人、技术、垃圾以及人体。”〔5〕中国儿童幻想小说涉及了人、动植物等非人生命体、特定区域(地方)等,同时也特别关注了“人”本身,这是由“身体”这一意象来表现的。
陈丹燕的《我的妈妈是精灵》中的精灵妈妈就是这种具有灵动调节能力的“身体”意象。小说的第一章命名为“我家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可以看成是对“身体”的一种从惯常、习俗的理解到变幻莫测的重新认识,“惊天动地”喻示着现代“身心分离”的身体观的第一次决裂所带来的震颤。
在平淡的日常生活里过着平静得不能再平静的日子的女孩陈淼淼因为晚餐桌上一个小小的恶作剧,第一次目睹了被常识遮蔽了的“身体”的“异常”:妈妈的身体在爸爸的胳膊里轻轻挂下来,像一块最轻的绸子……在走廊里拐弯的时候,妈妈垂下来的双腿像绸子衣服被风吹过的时候那样,飘了起来,“那飘飘摇摇的两只脚一点点变成了蓝色。在遥远的灯下,“妈妈的脸也成蓝色的了,像一张蓝色的手帕,那么轻,那么薄,那么飘飘摇摇的。接着,看不清了,被蓝布遮了起来似的,妈妈的脸不见了。”“妈妈成了一团蓝色的影子”,在陈淼淼惊恐的目睹中,身体坚定不移的实在性被虚无和飘渺取代,往事逐一得到了解释:为什么妈妈从来不吃酒,甚至也不吃醉虾,为什么陈淼淼拍的照片上,妈妈的身影总是模糊不清。有趣的是,小说让作为“解释者”的爸爸拥有一个“医生”的头衔而且是“外科医生”。相对于以“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人作为背景、主张辩证施治的中医来说,外科医学是在“身体与思维是分离”的现代思想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作为外科医生的父亲在面对自己妻子“异常”的身体时产生了困惑与矛盾,多年来积聚储备的现代科学知识发生了断裂。拥有这些知识,曾经使陈淼淼的爸爸获得了智力上的优越感,对于这个外科医生,“身体”是躺在手术台上、镁光灯下充满物性的存在。自己手中的一把柳叶刀,几柄手术钳可以为之造型、打扮,补救缺陷,剔除瑕疵,但是面对陈淼淼妈妈轻飘飘的透明的蓝色的模糊身体,他手中的“柳叶刀”无所适从。婚姻的危机并非来自情感的变浅变淡,而是陈淼淼爸爸在这种“无所适从”中深深体验的人类智力优越感的丧失,正如他自己对女儿的解释:“我是外科医生,我们否认世界上有精灵这种说法,因为它是不科学的。在知道你妈妈真的是精灵的那天,我的世界观都要崩溃了。我不像你,你能这么快就觉得精灵没什么不好而我却要昏过去。”
最后,在现代科学思想中浸染已久的陈爸爸唯有以自己的妻子与自己不是一个空间的人聊以自慰,他对陈淼淼说:“我们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蜜蜂的窝一样,有好多洞洞,住着不同的人。妈是另外一个洞洞里住的人。”这个解释勉强使得陈父接受了“不是真的人的人”的妻子的真实存在,但却就此搁浅淡化了夫妻之间的情感,当然,这种变化是单方面的,精灵妻子本来就是为爱而来,也清楚地知道自己与丈夫的“不同类”,但显然,她不曾意识到“真正的人”的世界的现代人无法想象与“另类”共同生活,尽管事实上,人类从未摆脱过与地球乃至宇宙的其它生命体的共生共存的命运。而陈父的变化可以说是“人是世界、宇宙的中心”的现代思想的逻辑结果,按照这种思想,人是“高等动物”,宇宙是有一个等级秩序的金字塔的,塔顶端的位置被现代人牢固的占据着。尽管人类可能对其他生命体也表现出某种关爱和尊重,就像陈父那样不得不承认人生存的其它空间的存在,也明白这个空间的“人”,“它们不害人”,但是现代人根深蒂固的种属优越情怀使得陈父对待精灵妻子的尊重和礼貌只不过是一种从高往低的俯视姿态的悲悯罢了,中间并没有平等观念的渗透。
另一方面,《我的妈妈是精灵》的想象力在“精灵妈妈”这个形象上的指向,从某种意义上,是把她当成了一种迥异于以现代思想作为哲学根基的现代西医学视野中的“身体”的象征的。精灵是一种“蓝色会飘”的人,和“仙女、人鱼”住在一起,精灵的身体是没有重量的,但是这并不是它的固定属性,只要与某个真正的人有了情感,它们就可以获得人的有重量的身体。精灵妈妈就是在教堂旁的精灵大树上看见了正抬头仰望天空的陈父,爱上了他,并且也在精灵的魔法——一朵吹到人眼睛里的蓝花的帮助下,让陈父也爱上了自己。精灵的身体在“爱”的粘合下变得沉重,变得有形了,而一旦对方的“爱”不再,精灵就只能返回自己的世界,并再也不可能回来。尽管有“蓝花”魔法,但魔法总是有限的,在与自己的迥异于真正的“人”的身体没有认同、默契的人那里,多少朵蓝花也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蓝花而已;尽管精灵妈妈需要青蛙的血来保持人性,尽管一点点酒精就会使得妈妈的身体变蓝,但更关键的在于“情感”的匮乏。因为“身上和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太少,精灵本身的东西就越来越多”。“情感”,而且是与“他者”的情感,作为心灵的本质属性,在这里,与“身体”的变化密切相关,精灵妈妈身体的有形与无形、轻飘与沉重反映着一个以“身心统一”作为生存之道的“另类”与仅仅把身体作为人的物质个体的现代人的世界的冲突。
与精灵妈妈随情感的深浅、有无而变化的身体一样,《绿人》中的身体也是具有“认知”能力的,他们身体绿色深浅,是随着生存环境的污染程度与周边绿色植被的多少而变化的,在人口聚集的城市,身体愈来愈淡,而距离西南大森林越近,身体的绿色也就越来越浓。其实,精灵妈妈也好、绿人也好,当小说家们把“具有认知的身体”的生态“意识”赋予非人类的“他者”时,隐含了对以分离为特征的世界观指导下的现代人的某种批判。令人深思的是,小说在儿童身上看到了这种生态意识的复苏。陈淼淼的爸爸在知道自己的妻子是“非人类”后,心灵发生了巨变,生活也随之改变,每天都会喝点酒,看报纸时,中缝的寻人启示也不放过,工作之后的晚上时间,消磨在影视光盘中,一种世界观被真实的遭遇质疑后的颓唐、落寞与无聊。而孩子陈淼淼则不同,在经历了短暂的恐惧惊愕之后,她对精灵妈妈的执爱不仅保留了从前女儿对母亲的亲情,甚至还超越了这种情感,将“爱”延伸到了自己永远也无法到达的精灵世界,比之于成年人,儿童更具有与“他者”和谐相处的平等意识。在《我的妈妈是精灵》中,尽管精灵妈妈一再强调“感情是世界上最黏的胶水”,但似乎,她的具有认知能力的身体只是对局限于男女之间的爱情的有无、深浅做出反应,孩子,不管是女儿陈淼淼,女儿的同学李雨辰以及那个趴在窗户边的外国小男孩的爱,似乎都无力阻止精灵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轻。小说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来自更纯真的儿童世界“感情”与来自成年人的“感情”在精灵身体上的不平衡折射,为浪漫主义立场下塑造出的更健康、更人性的童年生态投下了一束意味深长的阴影。
这样,在小说家把“身体”的变幻莫测作为使小说达到“奇幻”的效果的同时,却意外地在这种书写中隐喻了一种生态学的“身体观”。不管是精灵身体轻重的变化,绿人身体颜色的浓淡(班马《绿人》),还是爷爷和孙子的身体“换位”(单瑛琪《小哥俩和一只猫精》),又或者是雅特萨利人与鹰、熊、鹿等鸟兽之间身体的变形(左泓《不能飞翔的天空》),少年边域借助于蝉、少女雪琪和哥哥伦子借助于鸟儿的重生(张之路《谁为蝉鸣》、薛涛《废墟居民》),甚至包括有着人的意识,但却不想将怪物形体再变回人形的舅舅的身体“奇遇”(彭懿《魔塔》),以及现实主义色彩较浓的女孩身体的成长(殷健灵《纸人》),等等,在这些关于“身体”的叙事中,都表现出了对“身体”更丰富、更复杂的理解。这些变幻莫测的“身体”对自己对周围的力量都异常敏感,并自行进行着选择组织。每一个“身体”都在为生存斗争。
这样,小说中,“童年”所昭示的人的自然生命和“自然”所昭示的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协调、统一的,这种健康的、互构的“童年生态”和“自然生态”的书写,反映了中国儿童幻想小说追求一种人与自然亲密和谐的关系模式的写作立场,这种写作立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念的回归,也是对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日渐隔膜、物理环境被严重破坏、人的精神麻木虚无这一生存图景的危机性的幻想式应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儿童幻想小说与写实主义之间发生了一种比一般的现实主义小说更为深刻的联系。
〔1〕转引自M arina.Sehauffier,Tu rning to Earth:Sto ries of EcologicalConversion.CharlottesaillUniversity of V irginia p ress,2003,p56.
〔2〕Annette Ko lodny,The Lay OF the Land,Chpel H ill:The University ofNo rth Caro lina p ress,1975,p150.
〔3〕[美]查伦·斯普瑞特奈科.真实之复兴〔M〕.张妮妮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7,30页.
〔4〕[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55.
〔5〕Cheryll Glo tfelty,“In troduction,”in Cheryll Glo tfelty and Haro ld Fromm eds.,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 arks in L iterary Eco logy,A thens:University of Geo rgia Press,1996,p.xx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