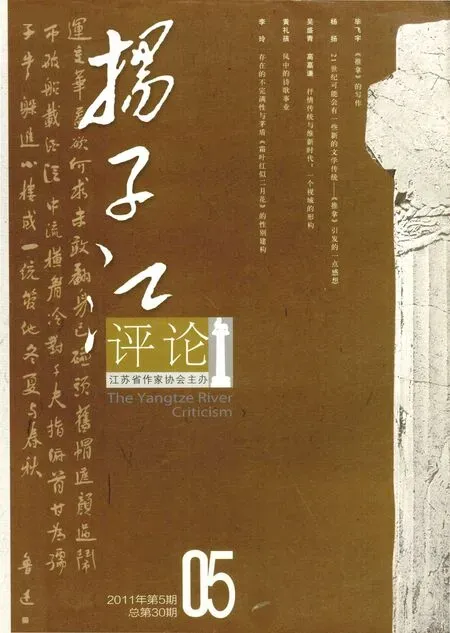抒情传统与维新时代:一个视域的形构
吴盛青 高嘉谦
古典诗词与现代文学史视域
1923年,同光体诗歌的代言人陈衍,在《近代诗钞》刊行之际,作五言古诗六首,抒发心情。其中第二首如此写道:
汉魏至唐宋,大家诗已多。李杜韩白苏,不废皆江河。而必钞近人,将毋好所阿。陵谷且变迁,万态若层波。情志生景物,今昔纷殊料。染采出闲色,浅深千绮罗。接木而移花,种样变刹那。爱古必薄今,吾意之所诃。亲切于事情,按之无差讹。①
诗中表达了爱古人也不薄今人的态度,诗歌的历史就像陵谷变迁,绮罗染采,今人通过移花接木的转化努力,可抵达种样刹变、脱胎换骨之境界。陈衍编辑《近代诗钞》所展现的与时俱进、不因循守旧的姿态,意味着他对近人诗歌有披沙拣金的评判眼界,也在诗教的承传上彰显个人见识。尽管这部收有五千余首,从咸丰到民初369位诗人,共24册的《近代诗钞》顺利问世,但诗的写作和发展的环境已分崩离析,诗的核心精神遭逢文学革命摧枯拉朽的力量的抗逆,一种惘惘的威胁笼罩在诗的生产和传播空间,让近代以来的古典诗词②和诗人都逐渐走向了历史的边缘和暗角。在标榜时代精神的现代文学史叙述中,他们自然地被束置高阁,甚至被刻意遗忘。
长时期以来,以“五四”为源头的新旧嬗递成为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唯一的范式。带上“历史的眼光”,意味着学者握有一把刻度清晰、单线进化的计算尺来勘探文学演进的过程。③这个过程甚至成为了政治历史的另一翻版,1919年、1949年也由此成为文学史上大写的日子。④在此类刻舟求剑式的文学史的表述中,旧文学要么在“五四”的高歌猛进中溃不成军,要么将它在现代的持续存在视作是旧文学的负隅顽抗。旧形式在新时代,透过现代性的镜片,被先验地被涂抹上保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些都昭示了我们批评视域里长期因意识形态的作祟而形成认知的封闭系统。同时,这类表述也经由将文学史长期用作教材的方式,影响了几代人的文学教育。陈思和在九十年代初曾生动地描绘过文学史的写作状况:“像变戏法似的随着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编造文学史的神话。”⑤
当文学革命风起云涌,白话文运动替“五四”新文学建立典范之际,胡适却坦言诗的堡垒是他号召的文学革命中最难攻下的一役。他挑明古典诗学的语言问题是必须被征服的对象,文学必须选择一套可以表述“当前的时代”经验结构的思维,等同换一口腔调来重新表达自己、认同自我。新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由此更为紧密。“五四”一代人对古典文学的重新评价,改变着文学史的价值观,也重写了文学典律。⑥在此语境下,以白话文为主导性的现代文学史几乎遮蔽了20世纪的传统诗词的写作。⑦随着文学革命的发展态势,古典诗词作为文类被推向边缘化,但那些被视为旧派或传统文人群体的持续写作,依然在民初以后的文学场里占据难以忽视的位置。古典文学,从广义的“文”的概念中分化出来,独立成为文学学科,更在现代学院体制的创设中登堂入室,诗与词建立各自传承的学术谱系。⑧随着诗社的普遍成立,以及逊清遗民避居租界而形成圈内人的聚集和交流,文人雅集赓续不断。相对新文学运动的各种社团与流派主张,这些写作古典诗词的文人,却在传统的诗社活动与读者圈里找到延续文学生命的渠道。对日抗战开始,诗社团体也纷纷成立,雅集活动并不中止。无论抒情言志,表现民族气节,或刻画乱离苦难,古典诗词在形式意义上,契合了忧患意识与文化民族情感。民初以降古典诗词写作的生生不息,显然抛出更为严肃的议题。诗人以诗为志,甚至安身立命于其中,暗示了古典诗词的文学储备影响了好几个世代的文人养成,形塑了其自我圆融饱满的美感经验的表征模式,当然这类模式在离乱的时代里亦遭遇表达的危机。换言之,古典诗词在现代情境内隐然展示着其不可轻易替代的文类意识与功能,其丰厚积累的文化资本,不可能是一场文学革命就能消耗殆尽的。这提醒了我们在现代文学史视域下重新审视古典诗词的写作与生产,成了重要议题。
针对现代历史语境与诗歌文本之间的互动,在方法学上我们有如下的考虑:首先,牵念于一个历史时间点、事件或是单独的文本作细部的描绘。近年来陈平原提倡“回到历史现场”的治学方法,投身历史的情景去把握在特定的语境下文学与文化事件的意义,以期对宏大学术话语进行纠偏。⑨坚持从文本、事件、细节而不是从固有的观念出发,注重的是将文本作历史化的处理。其次,历史的具体细节与文学史描述体系该如何做一个衔接?我们的每一次细部的述说都只是在接近本体论上“真实”的历史现场迈进的一小步,我们穿不过历史时间的隧道。“时间距离”是意义产生的场域。⑩史海钩沉,让这些被人遗忘了的记忆浮出地表,并不是为现存文学史拾遗补缺,填补空白。而是通过重建历史现场的多音复义,去思考旧文学的负隅顽抗是否可以撼动现存的文学史诠释框架。甚至可以考虑说,是否一定要拼出一块新旧更替,有终极目的的文学历史图景。历史演进的渊源与线索往往多元并置,回旋往复,一部线索清晰的“进步”的文学历史,往往消弭了异质的声音,遮蔽大块斑驳的色泽、时代的错误(anachronism),还有匪夷所思的基因突变。
历史是一种叙述,这类说法如今颇为流行。这个说法提醒我们对史的叙事性的特征保持清醒的认识。历史作为叙事,并不是在漠视钩沉索隐的材料功夫,而是强调历史文本的真实性,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联系框架,以及文本与历史学家譬喻性的语言描述之间的关系。⑪宣判文言死刑,仿佛一夜之间就催生出新的事物,诞生与死亡互为因果。在此类我们熟悉的文学史叙述中,新与旧一刀两断,毅然决然,但是这个故事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在讲述,缺少血脉精髓、五脏生气,更有叙述者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想。讲一个生动的历史故事,我们需要在材料的局部的真实性与阐释视角的丰富性之间找到有机的平衡,描画它的千头万绪,它的起伏跌宕,尤其关注其间被压抑的声音与反抗的实践。一个世纪之后,当我们在对伴随现代性而至的历史暴力了然于心的前提之下,这些当下情境中的历史的哀音,模棱两可的思想,文学形式的靡丽艰深化,是否同样可以进入我们文学历史写作的范畴?在新/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性几乎划上等号的同时,我们该如何去描述没有现代性的、反现代性的或是在现代性的大框架里左支右绌的抒情实践?
作为文学历史的研究者,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有阐释的权力,撰写的是属于个人的文学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旧体诗词能否被写入现代文学史的命题是一个伪命题。如果纯粹将现代文学史视为现代性文学经典生成的历史,以此拒斥和忽视文言写作的位置,那么这个定义的理论预设——白话文学等同于现代性,大有可商榷之处。同时,本书的一个目标即是勾勒传统抒情文类或隐或显地与现代性进行辩证的线索。此外,我们亦无意提倡刻意去书写“另类”(alternative)的文学史,在新文学史之外再形塑一种文学历史的描述体系。“另类”作为概念的局限性在于它已隐含了对正宗的确认。本书的作者达成的共识,旨在超越“五四”论述框架之后,描画文学变化的多重轨迹,共同关注在现代性发生的环节中,新与旧的交织角力,乃至共生同谋的关系。面对浩瀚如烟、亟待整理的近现代诗文,“从历史出发一部分一部分地对待一个事物”,⑫细究各部分交互扣联,是我们切入文学史秉持的基本方法。
诗与维新时代
本书的框架建立在1870年延续到共和国初年,集中辛亥鼎革前后的文学写作,尤其以古典诗词为大宗,广义的抒情文类为主要的考察对象。这是我们界定的历史研究领域⑬,而这个预设显然有明确的意义指向。王德威在其影响深远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本书正是顺接这样的思路,跳出“五四”作为现代文学滥觞的论述框架。王德威将现代性的发生在时间表上向晚清的推进,并不是简单的对历史事实——现代性的源点的操作,而是希望通过对近代小说多声喧哗的状态重新描画,来勾勒文学现代性迂回曲折的道路。换言之,此说法的内涵不在于断然否定“五四”典范的“变”与“新”,而是提醒已典律化的“五四”文学、文化和精神,可能在一个“起源”或“起点”的意义上简化或窄化了民国初年种种的文学生产背后对知识、正义、欲望和价值的重新定义和追求。⑭而我们将视域拉回到晚清,不过是正视晚清文人如何调动传统资源以应对和解释他们所面对的新时代,并为创造意义而做的种种实验。
“维新”一词,典出《诗经·大雅》,经由近代日本,始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变革图强之意。本书的“维新时代”从广义上涵括晚清尤其戊戌变法以降,中国社会激进变革,中西思潮相击荡的时代。晚清以追求启蒙、新知为尚的主旋律,在后续的“五四”运动、革命文学中继续生发张扬,成为主导现代中国的精神结构。以诗歌为主体的抒情传统与追求现代化的精神气质相呼应,晚清与民国诗文是当下境遇、历史模范与个人内在心境互动激荡下的产物。维新时代带动改革的激情,从国族到个体被迫积极向现代转化,却同时有着历史的反讽与困顿。知识分子遭遇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变的不仅是国家局势,更是文化根本。他们经验时代的丧乱和暴力,个体意识一再遭逢日常性灾难和断裂,以致书写的形式和内容,成为我们所熟悉的“感时忧国”和“涕泪交零”的集体氛围。诗歌在捕捉到了时代风云变幻的同时,更有力见证了创伤性的文化经验,呈现了一个强行植入的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痛苦的症状。陈三立有云,“遭际极艰而情蹙”,正是极艰的历史情境给旧体诗创作带来了崭新的驳杂色泽、锐利的生命体验。无论是惊心动魄的文化裂变的感受,还是家国沦覆之痛、儿女切切之情,诗歌中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的纠结与复杂的现世心态与情绪。直面历史时刻时主体经验顿挫有力的回应,文人的沧桑心境,都成为建构复杂的现代主体性不可或缺的环节。
当我们观察诗面对浩劫创伤的处理,“诗史”的叙事传统难免诱惑诗人去象征性的表述灾难。他们或由此进入“诗史”的语言系统,又或透过抒情主体介入巨变所选择的视角,以带有悲剧性氛围的自伤、流亡、哀情来面对历史,呈现灾难背后主体与巨变的情境交织认同的审美姿态。我们由此改变了对诗的圆融和谐的象征精神的认知而随着诗人深入巨变灾难的内部,理解陈述主体的惶恐不安,以及处身历史当下碎片状的存在感。因此我们更能掌握“震惊”⑮如何成为诗的现代性特质,透过“震惊”深刻显示了诗如何走入革命历史、悲剧氛围,招魂或复古式的怀旧。诗作为一种手段和载体,更清晰纪录着诗人存世的矛盾和冲突,并精准勾勒在时局的转化和危机中,诗人如何表现抒情自我体验的幽暗情怀。我们思考的出发点并不是传统的“以诗证史”,而是坚定地要将诗歌中呈现的震惊、犹豫、悲剧、反讽、历史胁迫的力量等写入现代性的历史中。⑯
与此同时,旧体诗词作为维新时代的古典文学遗产,构成一种格式化的古典文化氛围。诗人在历史当下追忆“古典”时代,意图在日常生活的缺罅和断裂之间,藉由诗“填补围绕在残存碎片四周的空白”。⑰所有在帝国崩毁、新文化运动后被弃置及一再改变的经验及记忆,在抒情诗的安稳结构里找到了栖身之所。如此说来,传统诗教的言志抒情,可兴可观,提示了诗人处身在除魅与暴力相间的现代文明世界的根本意义。
在维新时代里讨论诗教,不能忽视黄节的独到见识:“诗之所教,入人最深,独于此时,学者求诗若饥渴。”⑱近代知识分子肩负诗的使命,或以诗救人心,展现诗教从最纯粹的诗歌鉴赏与表意实践,导向召唤民族的文化心灵作为写作的伦理和历史心志。由此就不难理解,坚守诗的堡垒,尤其成为逊清遗民追怀传统的媒介与对象。他们藉由诗将自己投射到文化长河,以解救现代意识内的精神危机。而在遗民之外的广大士绅群体,他们经由自身的传统教养所延续与建构的文化道统,仍以诗的生产与传播,清楚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意识。诗由此深入为生活的组成部份,在复杂的政治纠葛与文化想象之间,他们以身教和著述试图采集古典文化“光晕”(aura),重新辩证与重建传统文化的存在意识。我们或以本雅明笔下“历史的天使”视之,看他们站在时代暴力的面前,伸手触及堆积的历史残骸之际,却随时被现代性的风暴吹得七零八落,或卷向不知名的未来。
以上种种面向强调了诗与维新时代的复杂关系,相对现代新诗必须重建其表意格式和审美经验,旧体诗的文类意识却接近于一种诗与魂结合的形式,表征民族心灵与文化美学的集体想象。藉此我们可以再度审视抒情传统与维新时代的辩证意义。抒情传统作为一个现代学术情境下建构的一套话语,更由此提供给我们一个文学史视域的观照。
抒情传统与文学史
20世纪70年代以来,陈世骧教授以《中国的抒情传统》及系列文章,揭示和命名了“抒情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诠释概念与认知框架。接着高友工教授从西方语言哲学的概念语汇,在中国文化史的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了一个占据主导意识型态的“中国抒情精神”,并从文论、诗律、乐论、书论、画论等层面提出“抒情美典”的辨识与历史面貌。如此一来,“抒情传统”经由系统的知识化处理,奠定了宏大的理论架构与知识空间,更扩大为中国抒情美学体系的研究路向,成为东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相继投入与深耕的重要论题。学者们分别在不同的研究面向对“抒情传统”做出深刻的演绎和思辨,由此展开的对话、重构与衍伸,建立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版图内具有强大解释效力的一套抒情论述和学术传统。
70年代末以降的三十年间,抒情论述的大量研究成果,分别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文学史的角度衍生出各类议题,并从不同文类、源流辩证和论证“抒情传统”的存续和意义。在古典文学方面,包括台湾学者蔡英俊、龚鹏程、张淑香等人对重要古典诗学观念的清理和解读,厘清“抒情传统”概括的内涵和具体作用;同时又深入本体论、发生学角度思考美感经验、抒情本体,抒情自我的构成,对应“抒情传统”展现的一种现象学意义的自觉。另外,对“抒情传统”的回应,还包括站在现代文学立场,思考现代情境下对“抒情传统”的“召唤”与“发明”,如何成就中国文学现代性——现代主体的多重面貌,以及此一传统元素的角色与功能。包括陈平原、王德威、陈国球、黄锦树等学者都注意到了“抒情传统”的延续、转化及其构成的文化逻辑,显现了其在现代语境内的辩证潜力。因此,“抒情传统”作为中国文学有效的诠释框架,以及这套抒情论述和典范的产生,在文学史的观照下就有了理论梳理和反省的意义。
不论抒情是文类概念,还是一种情感结构、史观,甚至是一套思维方式和诗学规范,抒情“话语”的建构提示了我们在现代情境中对中国文学史观的洞见与盲点。因此,我们对“抒情传统”的思索,可以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为“抒情的文学史”的理论视域。这一概念本身,旨在展示并探究抒情“话语”如何与文学史对话,抒情是否被后设为一套表述文学史的机制?“抒情传统”生成的历史条件为何?同时重新检视抒情“话语”运用的情境脉络和有效范畴,在跨领域的多元视域内为“抒情传统”探索出可能汇通经学、史传、思想史等领域的发展路向,以及探讨现代文学系统内中国“抒情传统”如何展现其美学和政治的向度,为中国现代性提出繁复的辩证意义。尤其当我们将抒情传统的观照放在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那是小说地位已大幅跃升、文类结构重新洗牌的时代,透过抒情传统的切入和考察十九世纪末以降文学史各环节之间的关键性转折,可以有效展示抒情传统在现代流变的丰富差异。在本书关怀的晚清至民国时段,“抒情的文学史”因此是一次省思和架构抒情论述的新起点。
现代性观照下的抒情主体与形式
王德威是近年努力探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议题的重要学者。在一篇有着导论意义的重要论文《“有情”的历史》中,他明确提议在革命、启蒙两大话语之外,将抒情作为现代主体建构的另一重要面向。他提到:“抒情传统的关照对于我们持续思考中国现代文学,以及中国文学所呈现的现代性问题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轴。”⑲现代性一词,涵盖广阔甚至歧义纷出,詹姆逊近年提倡将之视为一种“叙述范畴”(a narrative category),局限于审美领域,可以用来叙述现代性的不同情境。⑳在西潮拍岸的晚清,本土的抒情传统在新旧秩序的更替中面临冲击和变动。其间的成功转化,其间的偃蹇困顿,藏而不露的现代性线索,具体而微地呈现了文学演进的螺旋往复、错综矛盾的状态。文人对现代性的掘发和辩证,既有选择地调动传统资源,亦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创造意义和解释。这种种的努力探索,恰恰构成我们与世界对话的重要面向,且丰富和提供了我们探索文学现代性的多种可能。本书中所有的文章都从不同的侧面直接或间接地叙述了个案中的现代性议题,勾勒出现代性视野观照下的“传统”抒情主体与形式的多重面貌。
当诗人直逼现代历史时间,而陷入内部自我的抒情时刻,抒情诗因此生发了其作为诗人存续与自我证成的逻辑。抒情自我的主体性如何在现代情境中被表征和呈现,文人写作如何利用传统资源,安顿自身的处境,进而创造个人在此时代际遇中的意义,显然都值得深究探析。这指出了文人的古典诗词写作响应、延续和转化了他们创作意识内的抒情诗美典,重新铸造他们在此现代情境下文学意义内的美感经验。尤其旧体诗词赖以存续的语言表达模式(无论格律、修辞和语言的合法性)被文学革命炮轰,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检视古典文学的现代生产,意味着此抒情文类也正检视着其生产的意义如何发生效用,抑或辩证和自我证成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言下之意,在传统文化落幕的维新时代,以旧体诗词为骨干的抒情传统所持续坚守的写作态度和立场,且以顽强的生命力在新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展现了旧形式的诱惑。这是一个“启蒙”视域下颇有时空错位的文学景观,却也是诗与维新时代的辩证。这是抒情诗/抒情传统观照下的提示:文人的主体性如何在广义的抒情文类,自古延续以降的古典传统中展示此一抒情自我/主体性在现代情境下书写的脉络和意义。我们以抒情作为切入这些古典文学生产的观察视角,提出了两个值得省思的面向:首先,旧体诗词在现代情境的持续书写,带出文人浸淫和共享的抒情传统的实践方案和现象,其在背后反思和反刍的传统资源,显示了创造出其依存和寄托的民族精神和中国文化逻辑的企图以及歧义纷出的实践。这种现象不但暗示了文学革命划分的新诗时代,遭遇到功能与形式的瓶颈,而且同时提醒我们旧体诗词总能自寻出路,在不同环节展现其蠢蠢欲动的文类意识。旧体诗词背后藏有的另一层文化编码,昭告了一个审美意涵上文化共同体的想象。再者,抒情的主体如何去辩证和转化出自身的文学力量以及美学经验?写作旧体诗词的文人的审美趣味,他们对当下情境的处理和创造,以及他们试图确立的审美现代性,如何在一个宣扬启蒙与革命的维新时代找到生活实践和论述对话的方式?细究抒情的实践与形式在面向世变时所作大小不一的调适或不适,诚如胡晓明表达过的,古典的诗学因而“才具有了古代不具有的思想意义和价值紧张”㉑。
在考察晚清与民国诗人面对时代变局时,尤要关注文本内部及其语言形式的特质,以及形式与表述心境、生存体检之间形成的张力。㉒一方面我们反对将诗歌研究作非历史化或时间性的处理,而另一方面当我们以现代性的一套理论话语来观照抒情传统,必须考虑抒情文类的因为形式而带来的一些特殊性。延续了两千年的古典诗词传统,绝对承载庞大的美学经验,熟烂格式与定型化的文字表述形式,如“感时书愤、陈古刺今、述怀明志、怀旧思人、送春感秋、抒悲遣愁、说禅慕逸”等构成“情感内容的相似性与连贯性”㉓。千篇一律的抒情言志、使事用典,或许已经符码化,但是在异代异时,在迥异的文化语境里,可以被移花而接木,化陈腐为新奇。也就是说,一样的吟风弄月,一样的偎红刻翠,我们必须思考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催生的新意,以及对读者产生的不同意味。即便形式与情感的内容改变甚微,但社会与文化语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动。文言在晚清到民初的兴盛是时空错置的大展演,彰显的恰恰是旧形式在新时代的再生产意义。而这类“相似性与连贯性”在一个转型的时代,对那些拥有儒学教养与抒情资源的人来说,恰恰意义深刻。诗人往书写传统回归,将自身镶入古典抒情序列,用典故与熟练套路来应对、模拟眼前困境,为自我作为历史主人公的当下,延续或独创一个属于自己的古典诗格局。抒情诗人正是藉由古典诗词走入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成就自我在当下的意义。
再则,抒情诗歌,有别于叙事文类,呈现更多地对历史主义(historicism)的抵抗。当我们坚持不懈要在旧体诗歌中寻找时代新内容时,不可否认它常与现代社会发展步调不一致甚至毫无瓜葛。超越、永恒、崇高等字眼,在当代“后”字当头的研究理路中几乎成为了敏感词而被轻易屏蔽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也早已深入人心。维新时代的诗歌中固然留下了许多易于辨识的时代标记与风格,但是不可漠视的是,古典诗歌作为一种高度形式化与风格化的写作,有其稳定规范的特征,常常与历史当下的物质现实不直接建立起指涉关系,或是说这种关涉必然要经过长久积淀下来的文本传统的过滤。迪皮什·查克拉巴蒂对泰戈尔的研究或许有参考意义。他指出,如果用发展阶段论来审视泰戈尔的诗歌,就会发现其作品缺乏政治性,无甚新意。浸染民族主义思想的泰戈尔在文学创造性的活动中有劳力分工,典型的孟加拉村庄,在其小说与诗歌创作中呈现出两种矛盾的形象。他在诗中坚持描绘丰饶和平的农村景象,显示现实主义的缺席与政治的疏离。查克拉巴蒂郑重指出,“诗歌的功用在于在历史时间中创造停顿,将我们带入超越历史的空间。此另一空间就是泰戈尔所谓的永恒。”㉔这个说法听上去或许并不新鲜,但是放在舶来品的现代性与殖民地文化相冲击的论述框架中则意义显明。泰戈尔的例子提醒我们,守成与新变在一位作家身上亦可以有多重暧昧呈现。而在新文学作家中,无论是“怒向刀丛觅小诗”的鲁迅,还是以“骸骨迷恋者”自称的郁达夫,都在旧体诗中寄托别样的生命隐喻,更是众所周知的例子。抒情诗歌对历史化有显豁的抗拒,但是这类抗拒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条件下的文学行为,我们亦可以从中搭出另一种历史暗潮汹涌的脉搏。
有关文学形式与内容的话题,中外前辈学者有大量的理论表述,实非一两句话可清楚厘析,在此不再展开,仅想提倡关注文学形式的中介意义,表与里的凑泊。一个维新的大时代里,文学的风格与类型,师法的对象与文学的美典,新语汇的尝试或排斥等等,呈繁复多样的形貌,其中既可以有对形式的精心守护甚至变本加厉的运用,也可以有对形式与经典的小心翼翼的修正乃至激进反叛。晚清的诗歌在实践上(如新媒体的利用)与诗学理想的表述上(如诗界革命的观点),都有大张旗鼓的新变。但诗艺本身所带来的变化往往是极其微妙的,引用寇志铭的说法,所谓的“微妙的革命”㉕。在形式与语言的缝隙中,渗透进了一些需要细心辨识的现代性的质地。这些细微的差别,或许喻示了诗歌传承转化的某些轨迹与契机,值得今天的学者重视与玩味。
柯庆明曾指出,在文学历史的论述中,学者往往偏好发掘其中的新颖与变化的美感知觉,将之视为那个时代的成就与代表,而忽略了那些臻于圆融完美的重复“仿古”之作,其实亦大有可观之处。㉖新异与故常是流动而相对的概念,古人喜从形式的角度来谈诗歌“生”与“熟”的矛盾统一,诗家显示的是“熟后求生,密后求疏,巧后求拙”的追新心理。㉗现代文学研究者高举现代性的大纛,自觉地求新求变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此类嗜新之癖几乎在所难免,但是至少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偏见保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援引了詹姆逊的说法,现代性是情境中的“叙述范畴”。摒弃“新”眼光,甚至可以说,晚清与民国年代的古典诗词,作为一种在被迅速边缘化(或是说将被重新定义)的文类,在退幕前带着镣铐舞出了美仑美奂的卓约风姿。同时代的俄国白银时代的杰出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曾以其天才的敏锐,嘲笑过诗歌中的“进步”的概念,认为“诗歌的进程是一种不间断、不可逆转的失去。失去的秘密多得像创新。”套用他的话,或许有些偏激,这座错彩镂金的诗歌的七宝楼台,或是句度的参差、平仄的配置,“使所有关于艺术中的进步的扯谈变得毫无意义。”㉘
本书收录的专文,主要落实在几个不同面向的观察。作者群横跨欧美汉学界,两岸三地以及新加坡的华语研究学界,都属近现代文学领域耕耘的学者,呈现中西观点之间的交集与差异。书中设定的五个单元,纷呈不同的议题和论点,希望开启不同论述视域间的多元对话与越界潜能。以下将针对书中的五个单元的议题稍作说明。
(一)媒体、社团与文化生产
在欧美文学研究界曾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学文本研究,而近年来书籍史、文学社会学的流行显示的是对这类封闭的文本研究的反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著名的“文学场”的概念,指一个由多种能动者与各类机构组成的鏖战之地,以及体现他们各自文学意向与审美趣味的紧张空间。他深刻阐释活跃的文学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及其消长过程,年轻文化人在文学场域中要策略性地找到自己的定位,通过社团建立人脉关系,通过期刊提供的平台,积累自己的社会与文化资本。文学生产/再生产是一个由出版商、编辑、作者、读者、评论家等组成的生产链,其中两个主要生产场域,即文学社团与杂志,是生产链的关键。㉙这个理论为我们研究现代文学社团与媒体提供了意义深刻的方法论参照。贺麦晓首开其端,将之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研究,并在中国语境中对此作过很多修改。贺麦晓在研究思路上的特点,即是对体制(institution)的重视,尤为重视文学出版物在一个群体的文化产出上的重要性。他在《文学社团的职业化:以南社为例子》一文中,认为十九世纪后期的新式文学社团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特征是比政治化更为重要的趋势,而职业化最为显著地反映在文学社团对出版行业的介入与利用。该文指出从19世纪晚期开始,文人亲身参与并承担书籍的定期出版,许多成员本身亦是编辑或出版人,同时文学活动和出版物也呈现了更为自治与专业化的特点。学界对于处于新旧蜕变转型期的南社的研究,成果丰硕,相关讨论大多侧重突出这个社团的爱国热情、革命情怀。㉚贺麦晓的研究关注体制内的章程确立、定期出版物的刊行、诗文雅集,以及围绕柳亚子而形成的文化人圈子。这些见解为我们提供了理解1910年代文坛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全国性文学群体的锁钥之一。
从广义上说,布尔迪厄的理论对于文学研究有两个基本的方法论上的提示,即文本研究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和对历史情境的深度描绘(thick description)。㉛其“文学场”的概念是建立在对文学自主性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而这个理论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它不能涵盖现代作家感时忧国的文化关怀,文学与政治的纠缠互动。吴盛青的《风雅难追攀》采用别的取径,关注易代之际的“有情的共同体”的形成,友朋间的相濡以沫以及个体的文化理想的诉求。该文考掘了民国时期文人三月三的修禊情况,简要勾勒了两个在沪的遗民诗社——超社与晨风庐唱和集团的雅集情况。民国修禊展示了民初士人对兰亭禊集与文学美典魔咒般的迷恋,而在抚今追昔中体尝的是时间与文化断裂的愤悱之情。该文对诗歌文本的讨论侧重在时空的轴向上展开,面对现代时间的不可逆转性,都市生存场景的大转换,民国遗民在诗歌中构建起一个封闭的帝国魅影,铭刻惘惘而不甘的文化招魂的姿态。这些身心错置的忧伤书写,是对历史加速度的自卫性的心理回应,其间亦有抒情主体介入历史的自我证成,以及延续斯文的文化担当。
张晖与魏泉的文章关注传统诗词在公共领域与现代传媒的互动,体现的亦是将文学研究带回到生产现场的努力。他们在关注作品发表的语境的同时,关注杂志的发刊词、插图、栏目、作品间的关系以及广告、发行渠道等,强调一个文本与同期刊登的所谓的“副文本”之间的空间关系。㉜张晖以前期的《小说月报》的《文苑》栏目与不定期增设的栏目《最录》为研讨对象,这是1910年代最大规模发表旧体文学的阵地。魏泉一文选择了三十年代旧文人群体的在沪的同人刊物《青鹤》。两篇文章的共同之处在于:首先,两文都考察了主编王蕴章与陈灨一的核心作用,以及编辑活动背后所寄寓的文化理想。张文指出《小说月报》能够吸引并刊登大量诗词体现了文化人对“风流末歇”的一种文化焦虑,而陈灨一更是表达了“学术盛衰之变迁,诚国家存亡之关键”的认识,显示出两位文化人在旧学垂绝之际以道自重,以挽颓澜。其次,两位主编都利用其广阔的人脉,汇集了清末民初一批重要的文人墨客,利用学养背景、世谊或姻亲等,建立起私谊甚笃的文化人圈子。如果说1910年代的文言写作是浓墨华彩的夕阳灿晖,储备丰富,那么到了三十年代陈灨一是呕心沥血,艰难持续,因而也更有了薪火相递的文化意味。这两份杂志在相距了近二十年之后,稿件来源竟有颇多重合之处,表明旧文化生产链的顽强延续。鬻文卖字的旧文人,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依然拥有象征资本与文化资本。此外,受陈衍、朱祖谋等老辈提携且成就大业者如龙榆生,同时期在沪刊行《词学季刊》,表明耆宿相继凋零之后,学养上新旧相参的年轻文人已经接上地气,强韧地维护并志在开拓旧文学的生态环境。龙榆生如此看待他这一辈倚声者应尽的责任:“不在继往而在开来,不在守缺抱残,而在发扬光大。”㉝
(二)离散与跨太平洋的诗学想象
十九世纪末以降,士大夫与平民百姓的跨境出国已成常态,尤其以谋生为主的群体迁徙,似乎说明晚清以来的中国正进入大离散的时代氛围。在此脉络下重新讨论诗的写作,除了凸显诗的境外书写已成为迁徙者在流动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文学实践,同时亦清晰勾勒出中国精粹的文学形式,必然遭遇的海外异质世界与文明体验,以及衍生面对文类形式守成与改造等等的修辞手段与内容表征议题。如此一个迁徙流动的情境,一个主动与被迫的现代境遇,无形中预告了传统文人最熟悉的古典诗词写作,势必进入到一个现代情境世界的书写。透过文人的汉诗写作,及汉诗表征的境外视域:殖民地、城市空间、文化冲击、离散际遇、双乡体验、民族和语言的裂变及融合,汉诗面对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现代巨变,深化了我们理解这个古典文类遭遇的现代元素刺激可能的改变与不变。换言之,诗遭遇了现代性,以及离散境遇改变了诗的世界与眼界。
我们重新看待古典诗词的现代书写,似乎不能轻易略过一个更直接处理现代体验的时空现场。因此,从中国离境后,直下南海,或跨太平洋的迁徙路线,都见证了不同的汉诗书写脉络,可以整合为一个离散诗学的视域。
距离当代最近的1949年,一个划时代的两岸政治分水岭,国民政府的渡台,开启了我们重新反思离散书写的核心内涵。什么样的时空动荡与文人心事,成功在诗的世界造成转化。王德威的《国家不幸书家幸》处理了台静农的渡台。台静农是随国民党政府迁台的学者和书法家。丧乱作为那一代人的命运,台静农从文学到书法,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书写”政治学与美学。他难以压抑的诗情和政治胸怀,寄存于书法的字墨行间,展示了绝境逢生的抒情特质和生命形式,书法成了中国现代性最特殊的抒情见证。
而境外写作与离散叙事的密切关联,呈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境外”与“离境”框架。在此议题下,黄锦树的《境外中文、另类租借、现代性》敷衍一个流动的文学与文化史论述。黄锦树以南洋的星马为据点,讨论晚清南来使节左秉隆、黄遵宪,以及流亡诗人康有为如何以各自的文化资本,擘画南洋的境外诗学。甚至二战时期南来的郁达夫,以特殊的肉身经验和死亡,透过诗的写作形成一个巨大的象征遗产。从以上个案的简要讨论,他试图透过“境外中文”的框架,将这些流寓者或南来者的文学实践,或建立的文学象征,放入一个流动的文学史论述。在此基础上,作为中原境外的南洋,可以视其为“华人的另类租借”。境外的离散与流动,成为马华文学更早的际遇,它的起点不在新文学,而是晚清。
同样是对南来诗人的观照,高嘉谦针对两位晚清岭南的著名诗家丘逢甲和康有为,探讨他们南来的短暂岁月里,他们的行踪与汉诗创作如何改变了南来文学的传统格局,替南洋诗学形塑了迥异的风貌。丘逢甲的汉诗写作与当地孔教复兴作了一种民族主义式的结合,他的保种保教和民间立场激扬的汉诗精神引起阵阵回响。相对于此,康有为亡命之际彰显的诗学底蕴,就是孤臣的身心悲怆,以及内嵌的帝国视景。在引人注目的政治光谱之外,流亡者的诗学是康有为替南洋形塑的一道汉诗风景。在传统文化塌陷,遗民大流亡的前夕,康有为落难南洋赋诵楚骚──忧患的汉诗欲望,颇具象征意义的内化为南洋华人移民史的一个部分。
在南洋之外,香港是观察流寓诗人另一个重要的据点。从晚清的动荡局势到辛亥鼎革,避居和南迁港澳的广东文人不在少数,由此开启了香港文学的发展格局。黄坤尧和程中山的论文分别处理了陈步墀和潘飞声这两个文人个案。陈步墀独力编印《绣诗楼丛书》,虽以个人及家族的诗文著作为主,但也辑录了大量师友朋侪间的诗文墨宝,保存了珍贵的晚清史料及乡邦文献。显然香港的斯文存续,在避难南来的文人身上获得见证。潘飞声在晚清时期移居香港,昌诗论文,成为当时香港的诗学大家。他撰述的《在山泉诗话》更是香港第一本诗学批评著作,而居港时期撰述完成的诗集──《香海集》,则是程文探析的焦点,揭示了潘飞声的香港写作在近代诗坛上别树一帜的风格。在离散诗学的谱系里,香港另有值得关注的传承视野。
十九世纪以降由移民和淘金客开启的跨太平洋移动路线,掀开了一个重整汉诗谱系的新世界局面。黄运特的《诗意的错误》探讨了无名诗人留在美国旧金山天使岛上的诗篇。这批经后世学者以《埃仑诗集》成册的早期离散诗学文本,呈现的不是诗的精粹饱满,而是以充斥生命刻痕的具体形式赋形了迁徙流动生涯中错置的真实人生。黄运特的研究则试图提醒我们天使岛的“题壁诗”该作为历史纪录,还是文学文本来理解?其可能的诠释视域何在?尤其在经典化过程中,天使岛诗歌内容的简朴和错译,却反讽地揭露出离散文本的书写有其历史因素呈显的独特形式。黄运特在其英文近著中提出“跨太平洋的想象”这一概念,将“太平洋”理解为多元、矛盾的地理与隐喻性的空间。他指出边缘化、反诗学的文化实践,可以用来抵御普世经验、国族国家的疆界,从而为星球想象创造可能。㉞以上种种议题都可视为离散诗学范畴内的探讨,从南海到太平洋彼岸,离散汉诗描述了一个我们探究汉诗的新界面,也为晚近兴起的研究领域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探讨提供了新话题。
(三)抒情与性别的政治
性别作为一个分析的概念,已成为一全球性的学术趋势,广泛运用于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包括单个的女性形象塑造的探讨、写作与阅读主体的性别建构、文学中的换装与拟仿、男作家的女性意识等等。在老一代学者如胡文楷、谭正璧等人开疆拓土的基础上,明清文学与女性主义的研究在近二十年中蔚成声势。1993年在耶鲁大学召开的明清妇女与文学的会议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九十年代后期晚清女性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有追赶之势头。关于女性文化的两种定性论述,在近一时期的研究得到广泛质疑与修正:首先,生活在传统父系制下的女性,在“五四”时期被建构成作为被压迫、被凌辱的空洞的能指;近年来通过学者共同的努力,颠覆这一女性沉默失语的印象,展示帝国后期女性的主体性在书写中的自我呈现,在网罗桎梏的缝隙中的自我抗争。其次,十九世纪中后期以降,女性的写作与女性自身的解放往往被置于国族主义的大话语之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顺势提升女性社会地位的同时,贤妻良母成为了建构性别化的国族想象的重要资源。而近年学界关注女性如何与现代女权、民族主义运动互为利用的复杂关系,强调女性在国族与妇女解放运动中借势成就个性价值,凸显性别的主体性。
魏爱莲、方秀洁、胡晓真的三篇论文均以新材料,梳理晚清新语境里的闺秀诗词写作与新兴媒体之间的关系。从历史时间段来看,她们处理的女性作家,承接明清闺襜诗书之泽,并成为新文学女作家的前身。魏爱莲多年致力于明清妇女文学的研究,尤为关注女性文学社群的形成与互动,十九世纪的女性与媒体的关系。《1870年代以降“精通媒体”的闺秀》一文认为,晚清闺秀的从私人间诗歌酬唱、书信传播到积极利用新的印刷媒体的转变在1870年代即已现端倪。通过对四种文学期刊上女性发表诗作的情况的调查,展示了旧式闺秀文化在新媒体的催生下在向新的方向发展。该文集中讨论了两位鲜为人知的女性作家王庆棣与张庆松的投稿情况,细绎其间的变化,以及男性友人与读者在其间可能扮演的推手角色。方秀洁在其英文近著中集中探讨了17世纪早期到19世纪中叶,江南地区的女性写作情况,细致爬梳了实际与想象的女性写作社群的构成,尤其强调女性是如何将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类型转化为女性主体的自我呈现与自我铭刻的媒介。㉟本书收入的《激进化的诗学观》,以《女子世界》(1904-1907)为中心,考察女性诗歌在清末的嬗变轨迹,涉及作者的性别、旧形式在新时代的意义、女性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等议题。魏爱莲与方秀洁的文章均提出了晚清时期男作家伪装成女性在女性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文化现象,包括周作人在内的文学扮装。方秀洁指出,男性作者的托名游戏,一与文人借香草美人而言志的书写传统有关,二是缘于男性作家策略性的运用笔名,以期在竞争激烈的出版市场胜出。方文进一步指出女性诗歌中豪放风格的模仿与娴熟运用以及新语汇和新概念的使用,颠覆了传统的文学女性惯常的吟风弄月、摛藻扬芬。
胡晓真对于17世纪以降女性的弹词文化研究成绩斐然。㊱收入本书的论文在时间上顺接方秀洁一文,到达晚清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混沌地带,以王蕴章主编的《妇女杂志》为讨论重点。《女子世界》与《妇女杂志》,均设有“文苑”一栏,而《妇女杂志》为“文苑”专列一栏,以“文苑”来重新定义女性文学。胡晓真认为,此举“预设女性文学成为经典的可能”。同时“文苑”栏目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诗词歌赋,出现了新的文类如散文甚至白话小说的尝试。她以施淑仪刊登照片、在文中现身说法等形式来例示当时代闺秀在世变中的自我调适与表现,向往革命思潮的新姿态。这三篇论文勾勒了“五四”前女性文学的景观,描画了浸润诗书之泽的晚清才媛如何开始偏离明清才媛文化的轨道,从不自觉的新媒体的投稿者到积极的参与者甚至弄潮儿的变化历程,体现了创造的能动性(creative agency)。而这三篇论文涉及的共同课题,也在晚清女性文学研究中颇具代表性,即女性与新媒体提供的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性别(闺秀)与文类(诗词)的关系,以及男性名士的奖挹的角色或踌躇的立场。这几篇论文彼此呼应,共同呈现女性活跃于晚清文化舞台的风姿,展示了性别理论关照下的文学社会学与历史叙述的多重关照。
吕文翠的文章代表了近时期蔚成风潮的近代“上海学”与海派都市文学的研究。其近著《海上倾城》以开拓的视野,细致描画了19世纪后期上海洋场才子文化圈子的形成,长篇小说情感主体的建塑与当时迅速商业化的多元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㊲收入本书的《情色乌托邦的回归与消解》一文正是显示了传统的言情书写模式在近代衍生的变异,认为《海上花列传》正式终结了《红楼梦》续貂之作中重复呈现的哀感顽艳的传统审美情绪。该文对备受“五四”评论家批评的该小说后半段里的官家花园——一笠园的描绘作了重新诠释,认为韩邦庆将传统名士、仕女花园的写作嫁接到新旧糅杂的商业社会中,对文学典律既有“趋进”,更有“消解”,“勾绘出城市商业文明中成熟成形的女性文化与现代性之隐喻结构”。韩邦庆小说中的酒令诗词与《红楼梦》里的诗词预言人物命运的写法不同,无甚深意,吕文翠由此提出一个新颖的见解,即他在无深度的堆砌辞藻与操作表演中达到对才子佳人言情模式的违逆与反讽。该文为我们的抒情讨论带来的新议题,即传统诗词中的风花雪月或忠贞不渝的情感套路,在新的物质文明与情感关系世俗化的过程中,遭逢峻切的挑战,成为了讽喻或戏仿的对象。
近时期的性别研究超越了早期本质主义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关注再现(representation)、话语(discourse),尤其是语言媒介在性别关系与性别形象塑造中幽微曲折的意义。此外,曾在文学史上失踪的女诗人,风华绝代的吕碧城、薛绍徽,在晚近引起学界以及文学大众的注目。打捞这些文学史上的遗珍散珠,或可免去其蒙尘之憾,但是我们更期待在女性诗歌文本分析上有进一步的拓展,从而重新建构仍以男作家为发言主体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
(四)遗民诗词与历史记忆
综观民国以后投入古典诗词写作的文人群体,逊清遗民是其中的坚实班底。这一批从亡清过渡到民国的人物,在自我认同与身份标签上,缔造了政治与文化交错的人格类型。他们或许有政治理想,或许依恋旧朝,但新生活的经验裂变却曝显出他们无所适从及文化怀旧的生存症状。这理应从一种超越政治、王朝的文化眼光,着眼于他们安身立命的价值:一种对传统生活、稳定秩序的企盼。作为追忆古典时光的文化采珠者,他们赖以存身的终极价值是对上层精致文化的眷恋,相应也成了他们产生旧朝情结的部分根源。㊳旧朝情结与文化怀旧因而有着交融互涉的模糊地带。相对“五四”以降新兴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与进步信仰,遗民遁入历史潮流的暗角,呈现出悲观、荒凉、忧患、颓靡、破碎的生命情调与时代景观。
相对“五四”新文学作为时代的主旋律,遗民文人的古典诗词生产显得边缘和守旧。然而,我们却无法忽略这些旧体诗词在民初的文学场域占有重要的位置和文化资本。文人聚集组社,特定的期刊报纸依然保留古典诗词发表园地。这方面的议题已在前述单元介绍处理。但值得我们探究的是,遗民的诗词写作如何响应和解释他们的历史记忆?诗人如何对诗的审美意义重新认知,旧体诗词又如何构成文化遗民的根柢?诗的抒情技艺如何成为遗民的生存及自我想象文化母体及生存伦理证成的手段?
以上种种问题在林立和胡晓明的论文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处理。林立的《泡露事、水云身》着眼的是词的文类,凸显其作为清遗民群体中负载历史记忆的关键媒介,讨论遗民词人之间的唱和活动,如何藉词作来唤发、维系和巩固他们的忠清意识,以达到彼此认同的目的,进而在词人面对历史记忆的共同表述中,建构遗民词人群体的特征。林立还在另一篇近作中,通过对天津的须社与诗集《烟沽渔唱》的分析,进一步阐发集体唱酬在维系、强化清遗民群体的记忆与身份过程中的作用。同调同题所形成的微妙的互文关系,更是从艺术形式上强化彼此间的声气相通, 巩固遗民文化身份的认同。㊴
胡晓明的《陈三立陈寅恪海棠诗笺证》则以一对父子,又是两个世代的重要诗人和学者,他们在不同时间创作的海棠诗展开探究。父子二人个别遭遇了各自的时代风暴,海棠诗的写作反而见证了各属的父亲认同,且突出了诗作为精神对话和心灵相守的载体。这可以看做诗学传统的重新发明,也赋予二十世纪古典诗现代内涵。
在中原境内的遗民群体之外,1895年的乙未割台令台湾率先进入殖民地境遇。面对地域的割裂,岛民成为天朝弃民,清朝正统未亡,他们却开始有了遗民感觉;新文化运动还未揭幕,他们却有了文化焦虑。从乙未割台开始,自殖民地台湾出走或留下的文人,他们以遗民自称的吊诡身份,让遗民情结跳脱出传统朝代更迭范畴,成了一种症状。他们流连中原,在帝国疆域内寻求机会;或流放海外,寻找其他谋生可能。当然还有苟活、避居台湾岛内,周旋在殖民者的诱惑与压力之间,导致认同的游移。在弃民的集体流亡意识中,他们写作大量古典诗词,试图描述自我处境,传达与古人共感的飘零情怀,或以诗词记载流离域外的地理空间意识的改变。
施淑和黄美娥都是长期耕耘台湾文学和台湾古典诗学领域的著名学者。施淑的《台湾诗人洪弃生的文化意识及身份认同》以避居岛内的诗人洪弃生为例,从其数量庞大的古典诗词作品中,探究在艰困的殖民地境遇里,洪弃生以诗作为文化象征和抵抗,坚守遗民志向,不忘中华原乡。他的诗作记录台湾沦亡大事、批判殖民体制,强化他在殖民统治下的社会性死亡,更加深他的自我异化。这些诗作见证了诗人启动传统资源以建立自我完整的遗民形象,却也在台湾汉诗版图奠定了其光彩夺目且屹立不摇的位置。
日本殖民台湾五十年间,诗社发展蓬勃,汉诗写作从未断续。黄美娥的《日、台间的汉文关系》勾勒了殖民地时期台湾古典诗歌的知识论形构。该论文着眼日本、台湾汉文接触后引起的诸多问题,聚焦于日本、台湾间的汉诗跨界流动,及其所带来的文学知识生产,提示日本汉诗在殖民台湾的关键时期,如何被引用、挪用或拉扯、抗拒,尤其这些来自异域的知识如何转化成自我的范畴,而安置在台人的古典诗歌知识系统。以上种种问题呈现了一个迥异于中原地域的古典诗词发展谱系,同时凸显了20世纪另一个复杂的古典诗词生产场域。
(五)汉诗形式与文体变迁
这一组文章从更为开阔的视野下看世变中的文类、文学形式本身的守成与变迁,稳定的形式与巨变的内容之间的龃龉、磨合或突变。在文化研究依然大行其道的学界风气里,文学文本常沦于意识形态的注脚。在此我们强调的是在理论关照下的文本研究,第一手材料的梳理,和对文学形式与美感的辩证。如果说以上单元关怀的主题都是诗词文本与抒情传统实践,跟晚清民国的历史现实的相激荡,从而衍生出的种种新变;那么这一部分的讨论除了以十九世纪末以降汉语诗歌形式的变异和转化为焦点,还扩展至其他抒情形式,关注审美与技艺的丰富性。
胡志德在八十年代后期发表过两篇重要论文,对十九世纪的文学潮流与思想作过系统梳理与深入辨析,影响深远。在《从书写到文学》一文中,他通过对十九世纪桐城派与文选派的研究,细绎写作的角色在知识体系中的嬗变轨迹,认为“古文”与“文”的复兴显示了道德关怀渗透进了写作领域,社会文化的危机意识在文学层面上的展演,并指出“文”地位在此一时期的升迁为1895年后“文学”概念的重新整合做了有效铺垫。㊵收入本书的《新的书写方式》一文,在时间上承接前文,深入剖析“转型时代”的散文理论,写什么与如何书写成为晚清知识分子萦怀于心的关键议题。该文指出,原本内涵丰富、意义宽泛的“文学”概念与狭义纯粹的文学概念相互纠缠,使得文学成为二十世纪文化领域中“充满张力的竞技场所”。胡志德将吴汝纶对雅洁风格的守卫看做是对西方观念的摇摆不定的抵抗,并认为文选派中,刘师培通过对阮元的“文”概念的张扬,为“文”划定疆域,反对杂糅的文风,从而将“文”提升成为一种有效的、抽象的“国粹”。胡志德在《将世界带回家》一书中继续发挥这个议题,进而指出,在外来文化观念与本土文化的锋刃相交中,“新小说”最终脱颖而出,承担起维新救亡的重任。这一系列文章揭露出晚清士人面对西潮欲拒还迎的复杂心态,伴随而至的深重的文化危机以及彼此激扬生发的轨迹。在把中国带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自觉努力过程中,晚清知识分子试图抛却历史包袱的同时,又认定文学将在其间扮演确证国族、文化身份特征的关键角色。“对其本身的多元性,采取矛盾的立场”,成为了那一个时代的征兆。㊶
在桐城派与文选派的研究中,注重对其文学理论与思想的逻辑脉络的梳理,戴沙迪的《辛亥之际文论的承前启后》另辟蹊径,借镜布尔迪厄的“位置制造”(position making)理论,关注社会制度的变化与理论、方法之间的互动,显豁文化行动者(agent)如林纾与刘师培等人的具体文化实践。该文采用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两个视角,来探讨林纾与刘师培各自的古文教学、阅读的实践,诠释这些实践背后的动机以及他们在文化场域中的种种斡旋,进而论证其成为新文学效仿对象的缘由。颇具吊诡的是,所谓的“桐城谬种,文选妖孽”以及20世纪初的传统文学话语,成为了催生新文学必不可少的历史条件,进一步论证了“二十世纪初传统文学话语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元的辩证空间”。胡志德与戴沙迪两文之间的交集,为读者进一步追索晚清文论提供了不同的思索维度。
面对时危国难,古典诗词负载了巨大的文化期待。晚清“诗界革命”,呼吁在诗歌中反映新内容、新思想,成为诗歌变革的契机,同时也遭遇挫折,而面对形式的变异和转型,诗人们在亲近新世界时有所自觉地进行实验并努力尝试不同的写作方案。诗人在熟悉的古典诗歌传统中调动典故成词、创造新语汇,甚至放弃格律,既为诗寻找出路,也在定位和改造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黄遵宪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郑毓瑜近年的研究着眼于古典文学传统中的“感知模式”和“语言系统”在面对经验、记忆和知识,所产生的语言调度和替换,扩大和具体陈述了抒情的文学传统的意义认定模式。㊷她的《旧诗语的地理尺度》进而将时空拉近到十九世纪末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检视了遭遇异地文明的诗人必然从烂熟的旧典传统中,调动古典辞藻和意象去传译他所描述的明治维新世界。郑毓瑜指出“诗、注并存;旧诗语、新事物并置”的相互撞击和磨合现象,其离合和参照的意义脉络,正是我们观察晚清以降古典诗词展示的自我认同的外部视域和世界。换言之,我们看到了晚清以后古典诗词的变异举步维艰,却又毅然自信地走进的新世界观。此观点试探性地陈述了汉诗的旧与新不是文学价值范畴的定义,而是在意义阐释过程中体现其曲折反复的“现代”见证和效应。迈入二十世纪的旧体诗,接棒走上同样的路。
寇致铭的《论陈衍、陈三立、郑孝胥和“同光体”诗》讨论了近代诗学范畴内不能回避的同光体诗人群。他从诗人的境遇验证了诗风的变异,彰显了经验世界的土崩瓦解,以及自我的怀疑和生存危机。这些见证时局的旧体诗词,以支离破碎和残败的意象重新组装了诗的感觉结构,并准确把握了局势动荡与文化衰颓的精神状态。这是诗人特殊的时代感,同时也是诗的现代性体验。寇致铭在专著《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里对此议题有更深入的开展,并指出旧体诗词对时代微妙而复杂的反应,显示出诗人们在历史体验和个人感受之间所建立的美学距离,进而形塑和构成了我们讨论古典文学形式的现代性特征的重要路径。
而最直接表现诗的抒情美学与现代性结合的个案,当属杨昊昇《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的政治抒情》处理的郭沫若和毛泽东三十余年的旧体诗词唱和。从诗人的浪漫主义转向张扬政治抒情,进而投入红色革命的抒情浪潮,郭毛二人的旧体诗唱和,见证了中国的政治进程,却同时暗示了旧体诗词在文学革命后最具爆发力的展示,反而是政治的抒情主义。杨文对郭毛诗词唱和的分析论证,指出了在政治浪漫想象的视域里,必然突出彰显的抒情主体,构成了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写作最具体的现代性特征。在抒情跟政治密不可分的时代语境内,旧体诗词生生不息的活力,却狡黠地体现在郭毛的时代唱和。这恐怕是当年胡适企图推倒旧体诗堡垒时未曾料到的发展,但也说明了古典诗词内蕴的抒情传统力道与政治文化一拍即合,后劲不容小觑。
于是,我们可以重新检视诗界革命以来,对汉诗形式变革的呼吁,所衍生的对文体/文类疆界的种种纠葛和反思。张宏生《诗界革命:词体的“缺席”与“在场”》从词体的独特性出发,客观地评述了由于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审美定势与词体“要眇宜修”的文类特征,形成词在时代新变中的局促应对、扞格难容的境地。该文再次提醒我们,思境与艺术形式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熔铸新思想又要兼顾词体之美是那一代词人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四”战。在艰难融合新理想、新词语与旧风格之途上,“五四”新文化运动者高扬革命旌帜,以一种激进的姿态颠覆窠臼,另起炉灶。奚密的《诗的新向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一文,深入分析了古典诗歌与白话新诗在形式、意象、感性等方面的根本性的分野以及现代汉语诗歌裂变背后的“不可控制的力量”。首先,该文指出古典诗歌是建立在有共同教养的“同质”的读者群体之中,而在新诗的诗人与读者间则不具备这样的同质的教育背景,共享稳定的诗歌语汇,以及预设的整体文化价值体系。同时,该文以朱光潜等为例,简扼地讨论了现代汉诗所呈现的革命性转变的哲学与文学的意义。“什么是诗?”“诗人对谁说话?”“为什么写诗?”等这些命题划出新/旧诗歌的文类疆域,成为建构新诗的本体观与现代性的关捩。
这本《抒情传统与维新时代》论文集孜孜矻矻思考的命题之一,即抒情传统在现代语境中的发明或演化。但是需要澄清的是,我们并非在理论上预设从传统到现代的绝对的延续性,或是说一个活跃了千年的形式就必然要在现代得以承继。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许多个案中发现新诗的虽新犹旧,与旧诗的藕断丝连,但是总体而言,新诗作为全新的反形式的诗歌形式,是在“断裂”的大前提下,在审美空白的空间中,开掘独特的表现力与想象力的自由维度。㊸在1910年代,如果说同光体与常州词派是盘根错节的千年古木,那么新诗是些移植来的细细嫩枝,但是这些嫩枝在二十世纪将遭逢催生茁长的机缘。奚密还在另外一篇重要论文《中国式的后现代?——现代汉诗的文化政治》中,以高度的自觉,驳斥了对新诗的质疑,反思新诗在世界视野中的自我定位与文化认同的焦虑。该文对于我们的醒示意义在于,当代对抒情传统的重新发掘研讨,并不是要抑此扬彼,退守古典主义或本土主义的立场,执红牙檀板,怅惘若失于走远了的晓风残月之景;也不是要从抒情传统中去寻绎、去建构一种一成不变的、本质化的“中华性”(Chineseness),以期获得一本国际旅行的通行护照。陈世骧、高友工等前辈学者张扬抒情传统,虽有其特定的西方汉学语境,但抒情传统作为一套“传统之发明和转化”的话语系统㊹,可以有效展示中文抒情文类在现代世变语境中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或以王德威所提醒的另一个关注面向:我们如何透过中国传统文论的检视和反思提出不同于西方的问题,或对相同问题的不同解答路径和方法,建立和设定自己的议题范围。㊺我们无意强调全球视域下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文化的特异性,旨在展示传统在流变中无可争议、不容简化的丰富形貌。本书关注古典诗词及广义的抒情文类、话语如何在传统的裂变和融摄中生长与衍异,期望为晚清民国诗学与文化研究推波助澜,引发更多的相关探讨与论辩。本书安排的各单元均涉及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我们毋宁希望借此提出一些粗略的观察,起抛砖引玉之效。
【注释】
①陈衍:《近代诗钞刊成杂题六首》,见氏著,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3页。
②本书对十九世纪以降的抒情文类探讨,交替使用了几个常见的词汇,包括古典诗词、旧体诗词、汉诗、抒情诗等。相关词汇的概念并没有太大歧异,仍指向传统诗词形式的写作。交替使用主要是针对不同语境脉络方便凸显其参照和辩证意义。旧体诗词乃对立新诗而言,凸显新文学革命性的态势。汉诗是过去学界已渐进使用的词汇,可概括为汉语诗歌。当然,其过去习惯使用的范畴乃指在域外与汉字文化圈生产的汉语诗歌。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学界开始提倡表征现代经验的“现代汉诗”概念,奚密专著也以“现代汉诗”为题,标榜1917年以后的新诗书写。现代汉诗既表征现代意识与时代精神,反衬出晚清以降的古典诗,似应正名为“古典汉诗”。本书使用汉诗,既响应一个相对“中性”的汉语诗歌概称,也同时关注域外离散诗学。至于抒情诗,则泛指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以抒情文类是尚的诗学体式和范畴,而诗词仍属其核心文类。尤其当古典诗词作为晚清以来文人之间交际和抒情媒介,其追求的价值精神与文化秩序,表征了古典抒情诗的审美想象,与文化共同体的追求。
③见王汎森对线性的历史观对近代史研究的检讨。详氏著《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9-108页。
④宇文所安:《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他山石头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⑤陈思和:《一本文学史的构想》,收入陈国球编《中国文学史的省思》,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1页。同时参见该书中陈国球的导言,详氏著《导言:文学史的探索》,第1-14页。
⑥宇文所安:《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第306-335页。
⑦其中当然有例外,如钱基博的成于1930年代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对近代诗词及文章变革均有精彩的论述。关于白话文对文学史写作的主导,详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⑧关于学科体制下的中国文学的现代研究和文学史建构,研究成果不少。可参考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⑨陈平原:《导言》,《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1-7页。
⑩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中“时间距离的阐释学意义”一节。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385页。
⑪Hayden White,Tropics of Discou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 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chap.3,esp.pp.94-95.深受语言学研究影响,历史学家怀特认为历史的真实是通过历史学家所运用的譬喻性的语言与文本之间建立的关系而获得的。
⑫见德里达在中国的演讲记录,阐述其寻求差异性的解构学思路(第68页)。转引自陈晓明《现代性与当代文学史叙述》,《文艺争鸣》2007年11月,第63-72页。陈文对文学史的写作与现代性等议题有深入讨论。
⑬需要指出的是,此时间断限乃是我们编辑权宜下择取的历史研究的时间范畴,此处无意涉入界定莫衷一是的关于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分期的讨论。
⑭王德威近期对中国现代性的考察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参考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72-73页。
⑮这是本雅明诠释机械时代的现代性体验的关键主题。这种震惊体验成为诗人潜意识的一环,赋予诗的精神结构。详本雅明著,张旭东、魏文生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⑯参见Dipesh Charkrarbarty,Provincializ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2000),p.43.迪皮什·查克拉巴指一种历史写作,要特别彰显在“现代”的普世原则下的“压抑的策略与实践”。
⑰宇文所安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追忆的机制,为诗歌提供养料。详氏著,郑学勤译:《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3页。
⑱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氏著《曹子建诗注(外三种)阮步兵咏怀诗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07页。
⑲王德威:《“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首刊于《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33期(2008年9月),第77-137页;后收录入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65页。
⑳Fredric Jam eson,A Singular M odernity: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New York:Verso,2002),p.40,p.57.书中讨论了现代性的四种准则(pp.15-96).
㉑胡晓明:《二十世纪中国诗学史小言》,《社会科学家》2003年5月,第126页。
㉒关于晚清文言、白话和方言以及文学形式的深入讨论,参见袁进《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章“语言与形式”,第59-132页。
㉓刘纳:《最后一位古典诗人》,刘纳编《陈三立》(传记、作品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㉔Dipesh Charkrarbarty,Provincializng Europe: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pp.149-179;引文见p.171.
㉕Jon Eugene von Kow allis,The Subtle Revolution:Poets of the“Old Schools”during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CA: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06).
㉖柯庆明:《中国文学的美感》,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 200-201页。
㉗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收入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47页。关于这一点的深入讨论,见马亚中:《中国近代诗歌史》,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版,第46-48页。
㉘[俄]曼德尔施坦姆:《论当代诗歌》,收入黄灿然等译:《曼德尔施塔姆随笔选》,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㉙主要参见布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㉚对两岸三地的南社研究成果的综述,见林香伶《南社文学综论》,台北里仁书局2009年版,第17-36页。
㉛Michel Hockx,“Theory as Practice:M 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Bourdieu,”p.236.
㉜“副文本”(paratext)定义见,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著,史忠义译:《热奈特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㉝龙榆生:《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
㉞Yunte Huang,Transpacific Imaginations:History,Literature,Counterpoetics(Cam 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10.
㉟Grace S.Fong,Herself an Author:Gender,Agency,and Writ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nolulu,HI:University of Haw ai’iPress,2008).
㊱胡晓真:《才女彻夜未眠──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㊲吕文翠:《海上倾城:上海文学与文化的转异1849-1908》,台北麦田出版社2009年版。
㊳葛兆光对沈曾植的个案讨论,引导出文化遗民的价值观念与情感特质。详葛兆光:《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读书》1995年第9期,第68-69页。
㊴林立:《群体身份与记忆的建构:清遗民词社须社的唱酬》,《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1年1月第52期,第205-245页。
㊵Theodore Huters,“From W riting to Literature:The Developm ent of Late Qing Theories of Pros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7,no.1(June,1987):51-96.
㊶Theodore Huters,Bringing the W orld Hom e:Appropriating the W 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Honolulu,HI:University of Haw ai’i Press,2005),pp.100-122;pp.19-20.
㊷郑毓瑜就此议题所发表的论文,详郑毓瑜:《类与物:古典诗文的“物”背景》,《清华学报》新41卷第1期(2011年3月),第3-37页。郑毓瑜:《替代与类推:“感知模式”与上古文学传统》,《汉学研究》2010年3月第28卷第1期,第35-67页。
㊸见臧棣对新诗现代性的讨论。详氏著:《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文艺争鸣》1998年第3期,第48-52页。
㊹黄锦树:《抒情传统与现代性:传统之发明,或创造性的转化》,《中外文学》2005年7月第34卷第2期,第157-185页。
㊺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第 74-7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