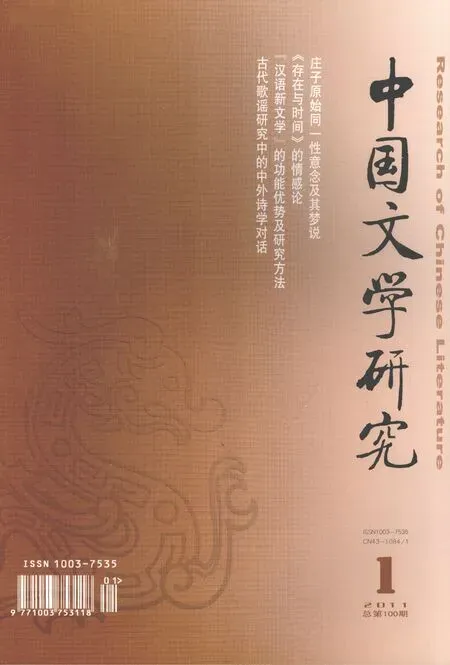隐喻·主题·记忆
——论张爱玲小说的政治叙事
张文东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在现实的意义上,任何写作都是“体制”下的写作,都必须依从于某种现实政治结构及其话语机制,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也不例外,虽然她始终都在申辩自己的写作是完全脱离政治的〔1〕,但事实并非如此。与所有人一样,张爱玲的小说也是一种政治叙事,其政治话语虽有“隐喻”、“主题”与“记忆”等叙事样式的不同,但却始终贯穿在她各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当中。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从1943年5月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到1976年写完却出版于2009年初的《小团圆》,虽几经搁浅,亦断断续续几十年〔2〕。一直以来,受夏志清的影响,人们常以《秧歌》和《赤地之恋》为分界线来思考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历程,将其分为三个时期,即“上海时期(《传奇》)”、“香港时期(《秧歌》和《赤地之恋》)”、“美国时期(《怨女》和《半生缘》等)”〔3〕,甚至更愿意将“上海→香港→上海→香港”看作是“张爱玲写作的循环之旅”,以证明“香港时期”的里程碑意义〔4〕。但实际上这种具有鲜明“政治意味”的“地域性”划分,恰因对“香港时期”的“偏重”而成为一个“伪题”。在我看来,“上海时期”如果是以“沦陷时期”来标示的话应可确定,因为《传奇》几乎是唯一的〔5〕;“美国时期”也可以,因为期间间或几部“记忆性”文本的书写,以及在“惘然的回忆”中不断改写的文本,都具有相同或相通的品格;但是唯独“香港时期”不能单独划分出来,因为就在此前不久的1950年3月至1952年1月间的“上海时期”里,张爱玲还有《十八春》与《小艾》两部小说——尽管和她到香港之后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在“政治情绪”上完全相左,但在“迎合”某种现实政治的“政治叙事”意义上却完全取向相同。所以纵观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整体历程,我主张还是用一种虽通俗但却更整一的划分:前期(1943—1949)——《传奇》;中期(1950—1955)——从《十八春》到《赤地之恋》;后期(1956—1995)——从《五四遗事》到《同学少年都不贱》或《小团圆》。而我所谓“整一”,实际就是着眼于其政治叙事的整体取向。
一、前期创作的“政治隐喻”(1943—1949):《传奇》
我曾在指认张爱玲《传奇》的政治叙事时明确谈到,写作是张爱玲甚至唯一的生存方式,而她的“自私”与“智慧”则是其生存和写作的“本质特征”——“自私”是说她“人生的底子”是“自私”的,并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智慧”则是说她有自己的“活法”,即以一种特殊的写作来活出“自己的享受”——《传奇》首先如此〔6〕。
《传奇》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起点也是巅峰,其中内含了她几乎全部的现实“生存智慧”即“政治智慧”。“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掰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7〕,所以在当年沦陷中的上海滩,喊着“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首先要“自私”地“活着”,然后为了“活得称心”,便不得不以一种特殊的“智慧”写作作为她“活着”的方式来“进入”这个特殊的时代,即以一种委曲的政治叙事来仅仅做“自己的文章”。但这篇文章真的是“自己的”吗?恐怕不是,也不可能是,因为沦陷的上海只是一个相比其它地域和时代都更加严酷的“如此这般窒息与庞乱的氛围”〔8〕。不过,“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的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9〕。于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10〕,为了在乱世里“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乃至活出“自己的享受”来〔11〕,张爱玲便不得不在其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心态的驱使下,自觉地走向了与“国家、政治”并不直接相连但却与沦陷区政治密切相关的“饮食男女”,为现实政治文本以及文本的政治书写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
“小说,无论如何,都处身于政治的变迁当中,有意识也好,无意识也好,总是以叙事的方式阐释着政治,参与着政治,成为政治美学形式的表达。”〔12〕从这个角度看,《传奇》的政治叙事可说是“有意识”的。张爱玲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而在所谓“飞扬”与“安稳”、“斗争”与“和谐”、“力”与“美”、“英雄”与“凡人”、“时代”与“记忆”乃至“神性”与“妇人性”等等对立当中,前者是一般“弄文学的人”所注重的,后者才是她自己所追求的〔13〕。不过有意味的是,如果所谓“神性”是一种“永恒的超越”的话,那其所谓“妇人性”则差不多就是一种“委屈以求全、妥协以求生、苟且以求安的生存态度”〔14〕,由此,张爱玲自觉而明确地展示出了一种与“主流”完全不同的“自私”和“逃避”的人生观与文学观。所以,张爱玲并不是从来都“没有写历史的志愿”〔15〕,而是从来都没有对于历史和时代的“责任心”,只是试图以一种“自私”的现实“智慧”来书写历史,因而她在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里面偏不写战争和革命,而只写那些“沉重的”、“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16〕,如《传奇》;然后却在一个不再充满革命和战争的时代里切切书写着自己从那个时代走过来以后的“革命记忆”和“战争体验”,如《色戒》与《小团圆》——这就是张爱玲的“智慧”以及“政治”。
由这种“自私”与“智慧”结合而生的叙事策略所导引,《传奇》的叙事时间和空间几乎都成了一个隐喻。一方面,《传奇》里的故事差不多都是关于时间的寓言,而寓言的核心即是一种对历史以及时代的对立、颠覆和重构:时代叙事及历史叙事被个人叙事或私人叙事所取代,“时间”在私人的、“过去的”甚至“退化的”的意义上与现实的整体、“进化”以及“进步的”时代、历史完全背离,所有的故事和人,都被笼罩在一种游移于“回忆”与“现实”之间“陈旧而模糊”的时间情境中,在“现在”的意义被昨天的“回忆”消解了的同时,没有了“明天”,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在这个“影子似的沉没下去”的时代里,书写这个时代的她“没有”、“也不能有”对于“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的“象征”和“建构”。所以,张爱玲在她极端个人主义的“政治智慧”导引下,发现和书写一个时代的阴暗混沌的“背影”、一个社会的没有前途的“过去”以及冰山在水面以下的“没有光的所在”,既是一种现实的无奈,也是一种写作的技巧,当然也就是她力图塑造的“政治个性”。于是,她截断了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完整的“时间流”,以私人时间颠覆了原本具有“集体记忆”性质的历史时间概念,在其他作家力图把握时代脚步和社会变化的时候,只是从“现代”的意义上发现了“过去”,对立性地解构并重构着社会化的历史,使其话语形式中的“时间”在现实的意义上成为一种个人政治意识的“隐喻”。另一方面,《传奇》的“空间”也完全是一种从“公共空间”中被“封闭”出来的“个人空间”〔17〕。可以说,对现代以来所谓“主流”的大多数作家而言,“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生活、介入与他人共同生活世界的方式”〔18〕,所以他们对都市生活以及现实时代的把握,也都体现在一种积极的“参与”和“承担”之中。不过,在沦陷时期的极端政治之下,中国人的“政治权利”和“公共性品格”已被彻底取消,与之相应,极端政治语境下的“文学空间”的“公共性”也被迫成为一种“私人空间”里的“私语性”,所谓的“莫谈国事”及“饮食男女”,实际都是这种政治语境下的无奈体现。因此在《传奇》里,社会和时代的“公共性”背景总是彻底模糊的,取而代之的都是“封锁”着的“个人空间”,无论是具有封闭性的没落的旧家庭,还是中西杂糅的“怪胎”式的生存环境,都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文化氛围即“空间政治”。即如她自己那个曾飘荡着“鸦片的云雾”的“家”一样〔19〕,一个个没落的旧家庭与时代相背离地坚守着一种自成体系的封闭与沉沦,挣扎在躲不掉的回忆的“梦魇”中,由几代人共同演绎着一幕幕的“现代鬼故事”,用这些“现代的鬼话”隐喻着与“五四”以来“人的话语”及其“公共性”的疏离和对立。依阿伦特的观点,文学和艺术作为“积极生活”中的“行动”(Actor),是最有可能在公共生活中显示“我是谁”的,但前提是必须有一个“自由言说”的环境〔20〕。不过在张爱玲这里,显然文学作为一种“行动”(Actor)是危险的,因此其对于“公共空间”的任何一种“参与”,都只能以某种“暧昧”的方式来实现,所以她“智慧”地选择并设计了一个完全游离在现实“公共空间”之外的“个人空间”,以一种“退避”甚至“退隐”的姿态,在“自己的世界”里窃窃“私语”,将“五四”以来具有社会和时代意义的“我是谁”的问题置于社会和时代的“背影”里,既彰显了一个消费意义上的“私语者”的“我”,又有效地规避了一个“行动”意义上的“我”的危险,形成了一种深刻的、隐喻的政治叙事〔21〕。
二、中期创作的“主题政治”(1950—1955):从《十八春》到《赤地之恋》
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政治叙事,并没有所谓“起点”或“终点”的意义,只要社会与时代的政治本质不能消解,这种政治叙事便同样不能消解,甚至还会在更加明晰的政治形态之下愈演愈烈,其中期创作便是一种鲜明的呈现。此时张爱玲小说政治叙事最重要的特点是:一改《传奇》时“委曲的”、“非政治主题”的写作姿态,也不再只是“个人主义”的“忆往”题材和写法,而是把目光集中于“现实”的人事,迎合着现实的政治要求,以一种显在的摇摆于“左”、“右”之间的“政治主题”的叙事,有意识地试图重新申说“我是谁”。
抗战胜利后,因与胡兰成的婚姻,以及沦陷时期态度暧昧的写作等,张爱玲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文化汉奸”一类的指责甚至谩骂〔22〕,虽然忍不住可以站出来辩白几句,但其小说创作却一时沉寂下来。“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23〕,直到1950年3月25日,她才以笔名“梁京”开始在上海《亦报》上连载长篇小说《十八春》,带着一种异样的光彩登上了新时代的文坛。小说从1949年倒溯18年开始写起:平民女子顾曼桢与世家子弟沈世钧于上海相恋,中间曲折横生,致使人事相隔,18年后两人于新时代里偶然相遇,虽然唏嘘不已却憾难复合,结尾时,“几位青年男女经过重重感情波折,最后都投身到‘革命的熔炉’去寻找个人的理想”去了〔24〕。可以想见,这个故事依旧延续了《传奇》所刻意营造的“情欲”故事模式,并同样是“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的叙事策略,不过在叙事话语上却尝试了与《传奇》不同的写实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将一部自己前所未有的长篇小说作为在新时代里“重新”写作的开端,并以她并不熟悉的连载形式在新时代到来不久便匆匆面世,这里面是极有政治意味的。而同样有意味的是,与《传奇》那种几乎完全“忆写”“陈旧而模糊”的沪、港不同,《十八春》写的是一个“现代上海”的故事,作者站在一个新时代里,不仅诅咒着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25〕,且有意识地写到了这个新时代所带来的变化,虽然从18年前写起,但最后落笔却在当下,并留下了一个“光明的结尾”。这就更让人们看到,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张爱玲的政治“敏感”与“智慧”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登场,并以对政治风尚的自觉追随,开辟了一条由日渐鲜明的“政治主题叙事”所铺就的创作道路。
1951年底至1952年初,张爱玲在《亦报》连载发表《小艾》,这部在新政治形势下创作的中篇小说,也是她在大陆时期的最后作品。张爱玲曾说她“非常不喜欢《小艾》”,一是因“缺少故事性”,不够“传奇”;二则从她后来的体会看,觉得写出的故事与最初的构想变异太大了,尤其是在结尾上,不但没有像原本设想的旁敲侧击一下共产党,反倒给了小艾一个“美丽的远景”〔26〕。联想到张爱玲说这句话时已是在1986、1987年的美国,而《小艾》又在由台湾《联合副刊》重新发表,其中的政治寓意便不言自明了。不过这倒也反证了当年《小艾》的写作中应该是有着一种对现实政治的刻意迎合的——故事写的是大户家里女佣小艾的一生,这可谓是张爱玲一向熟悉并擅长的题材,不过写来与《传奇》不同,小艾最后走进了新时代,虽没有像曼桢那样远赴东北参加建设,但在上海同样也是为未来“幸福的世界”而工作着。而且,如果说在《十八春》里张爱玲还有意无意地尽量不在字面上显现出直白的政治话语的话,而在《小艾》当中,则已经毫无顾忌地出现了一些诸如“蒋匪帮”等富有明确政治性的用语,进而更加凿实了一种现实的政治主题叙事。由此可见,不管张爱玲在刚刚走进新时代之时还有着哪些忐忑或是犹疑,但“在思维方式、价值评判、社会观念上已贴近主流话语”了〔27〕。
1952年夏,张爱玲到了香港,期间复学、赴日等均不如意,在为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新闻处翻译美国文学作品的同时,开始以英文写作《秧歌》〔28〕。1954年4月,《秧歌》中文版先在美新处发行的杂志《今日世界》上连载,7月由香港天风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不久后的10月,《赤地之恋》也由天风出版社刊行。对张爱玲来说,这两部作品原本并没什么大不了,不过仍然是她以“活着”为欲念的“私人的政治”叙事而已。但没想到的是,“不过如此”的两部作品,却引发了一场围绕其政治话语的跨越世纪之后仍没完没了的纷争。在我看来,如果除去评论者站在不同政治立场上的“有色”评判以及由此生成的“定性”与“定位”,围绕着两部小说的话题并不十分丰富,其中有意味的话题也许只是一个,即张爱玲“为什么写”或“为什么这样写”?
如我所强调的,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始终是其生存的甚至唯一的方式,对她来说,“写作”不过是手段,“活着”才是目的。因此作为“活着”的前提,任何一种现实政治的“影像”,都会委曲甚至直接地投射在她的“智慧”写作当中,进而形成一种委曲或直接的政治叙事,《十八春》与《小艾》如此,《秧歌》与《赤地之恋》也不过如此,这种已成“定势”的“政治智慧”与“政治叙事”是完全可以确认并一目了然的。当然,政治的主题并不是一定由政治性的话语写出来才好,这个道理张爱玲是完全明白的,所以她在《秧歌》和《赤地之恋》的写作当中都使用了一个富有深意的“导读”,即《秧歌》的“跋”和《赤地之恋》的“自序”,刻意地强调自己“为什么写”或“为什么这样写”的材料背景与写作策略。她曾说《秧歌》“里面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据的”,并言之凿凿地说材料来自于“三反”运动”中《人民文学》上刊载过的“一个写作者的自我检讨”〔29〕;而《赤地之恋》虽是“把许多小故事叠印在一起”,但“所写的是真人实事”〔30〕。但可笑的是,我依张爱玲的说法认真查阅自1950年10月创刊至1952年底的《人民文学》,却根本未发现她说的这份材料〔31〕!又有传说张爱玲曾参加土改工作队在江苏农村走过几天,我看恐怕也未必是真〔32〕,即便是真,也未必有了“真实的生活”。正如她自己强调过的,如果对“背景”不熟悉,即便有了材料,“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她也“暂时不能写”,甚至“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去住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那个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所以她只能“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33〕。可是《赤地之恋》中则不仅有土改,在上海之外还有抗美援朝,都是她所不了解、不熟悉的,那她信誓旦旦的“真实”从哪里来呢?所谓“写所能够写”的信条又在哪里呢?后来她才承认,《赤地之恋》的故事是在“授权(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写成的”,连故事大纲都“已经固定了”〔34〕,所谓“真实”不过是“为了生计”的“遵命文学”的“真实”而已!
三、后期创作的“政治记忆”(1955—1995):从《色戒》到《小团圆》
1955年秋,张爱玲到了美国。如果说香港还因当年“求学”而有“家园”之意的话,美国对张爱玲来说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他乡”,所以这时才是她人生以及文学之路的真正转折。于是,经历了英文写作的彻底失败之后〔35〕,张爱玲不无遗憾地开始了她漫长的“回忆”之旅。不过,如果说当年她是在《传奇》里试图发掘“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的话,那么现在却剩下“自己的世界”里的一种“个人记忆”了。现实的情况是,张爱玲虽身在美国,远离大陆、香港以及台湾,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远离依然“对峙”的现实政治文化,尤其在自己忽然成为一种“阅读”的“政治标本”之后〔36〕,她的政治意识便在自己和别人的共同记忆中被又一次激发出来,进而使“政治记忆”叙事成为其后期小说创作的“底子”。
“政治记忆”在张爱玲后期小说中的存在样态主要有两种:一是以不断泛起的“政治记忆”作为一种“检讨”来不断改写自己的旧作;二是让在当年不敢或不能言说的“个人记忆”浮出水面并重新成为历史与个人政治的“地标”。
张爱玲大概可算是一个改写自己旧作数量以及次数最多的作家之一,这一方面与她的文学史地位的纷争与重评有关,同时也是她在“他乡”的政治文化里不断检讨自己“政治记忆”的结果。事实上,早在大陆时期《十八春》连载次年出单行本时,张爱玲便已有过对作品的大幅修订,其动因和效果便都是为了确立并修正她与主流话语之间的某种联系,以及自己政治身份和话语空间的确认,并初步体现了她在“经济、文化的危机中得以引发和深化”的“自我反省的能力”〔37〕。这种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自我反省的能力”在她1966年再次将《十八春》改写为《半生缘》时同样得到了承袭,其中许多情节的改变尤其是结尾只到沈、顾二人重逢即戛然而止等等,都是按照作品重新出版的政治要求来完成的,甚至使两部作品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倾向。《金锁记》改写为《怨女》也一样,如果说当年傅雷看重《金锁记》是因为曹七巧所具有的“深刻的悲剧性格”的话〔38〕,而到了《怨女》当中,银娣却被改造为一个“小奸小坏”的平常女性,仿佛又是一次她对当年那段官司的遥远回应。其它如《秧歌》、《小艾》等也都经过重新发表和多次修润,即便是新作发表如《五四遗事》、《色·戒》、《浮花浪蕊》等,也都是“屡经彻底改写”,甚至在收入《惘然记》中时还在修改〔39〕。从这些作品在1950年代即已成篇却在1970年代屡经改写后发表的过程来看,记忆里的“政治”应该始终是她难以回避的一种“规范”吧。
实际上,《色·戒》、《五四遗事》、《浮花浪蕊》等创作也可视为后期创作中的另一种“政治记忆”。比如《五四遗事》中仍旧不能释怀的对“五四”以及“五四”以来新文化的“反讽式”的记忆描绘,或如《浮花浪蕊》中借和挑夫一起出罗湖口岸时的害怕狂奔所表现出的对大陆的某种讥刺,尤其是《色·戒》,简直就是当年“政治斗争”的某种再现。关于《色·戒》,张爱玲曾有两次自己做出解释〔40〕:一次是因有人指责她有同情汉奸的嫌疑而回应说:“这故事的来历说来话长,有些材料不在手边,以后再谈”,暗指《色·戒》原有“本事”〔41〕;再一次是因有人指证《色·戒》确有所本时回应说即便真有此事,但“当年敌伪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又试图否定“本事”〔42〕。其中虽自相矛盾,破绽不少,但分析起来还是前者更为真实。现在看来,当年的“邓苹如刺丁默邨”一案,实应为《色·戒》故事之本:一则从胡兰成角度讲,此事他既不会不知,热恋中亦应不会不对张爱玲讲;二则从张爱玲角度说,沦陷时期她身边并不乏走动于汪伪政权中人,更何况这种“本事”原就十分具有“传奇”色彩。事既如此,而张爱玲为什么迟迟未能落笔,落笔后又何以必经反复修改方使其面世?我看恐怕还是其“自私”与“智慧”结晶的政治意识使然。试想,小说后来发表时早已事过境迁多年,但还是引发了许多纷争,即令当时,则以张爱玲之“妇人性”又何以堪!所以余斌说:张爱玲有独特的个人视野,“她‘张看’到的一切总是与他人所获不同,无论何种题材,她总是能在其上留下鲜明的个人印记”〔43〕,其实这种“印记”又如何不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记忆呢!
《小团圆》可谓是张爱玲最“可信”的“情感传记”〔44〕,当然,用一部小说来为自己的一生做脚注,也许并不是《小团圆》创作的初衷,但在现实上却有了这种客观效果,所以,如果对照着去读《小团圆》,张爱玲的人生可能会有更加清晰的影像。不过,与一般小说的虚构和想象不同,自传体的叙事往往都是一种追忆,故追忆中的“往事”便成为一种特殊的“现实”,被作者所寄寓的心理力量内化为一种寓意丰富的象征结构,甚至比现实的“事实”来得更加深刻。在《小团圆》里,张爱玲大概只写了自己“三十年”的人生历程,但却唱出了两种“成长”的变奏:一个旧的大家庭的没落、衰变,在追忆中成为一首挽歌;而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恋,在追忆中却“梦境般”地等待着复活。虽然它不是一部“成长小说”,但是其中种种在“退化的”、“失落的”过程中“成长”的生命经验,却是张爱玲自己不得不时时捡拾起来的“自我”的碎片,她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外在的”任何“进步”,还是未能带她逃离那个过于狭小的“自己的世界”,自始至终,时代和个人依旧是完全对立的,《传奇》里面“自私”的“自我”不但回来了,而且以更加暧昧的姿态退出了一个原本激扬的历史时空——唯一不同的是,这时的张爱玲已经可以不再借助任何的政治智慧,而直接将自己的“记忆”敷衍成一种极端私人的“政治”和叙事。如结尾的那个梦:“青山、蓝天、阳光”的背景下,“之雍出现了,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来快乐了很久很久”〔46〕。用林幸谦的观点看,这里似乎暗示了张爱玲倾向于“小团圆”的怀念和延续〔47〕,设若果真如此,那么,张爱玲一生乃至最后的“等待”和“快乐”除了一份“自恋”的“乱世情缘”之外还有什么呢?在其私人的“政治”里,一个如此激扬的时代,有时甚至连一场“春梦”的背景都不是。
“个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任何个体的生存及其主体的生成其实都逃不脱政治的透渗、介入和刻画,所以,再私人的记忆也都会有着政治的印记,再私人的政治也都包含着种种“现实”的政治话语,《小团圆》也如此:比如在万众一心的抗日战争中九莉却想着“这又不是我们的战争”,虽是遁词,“但是没命还讲什么?总要活着才这样那样”的心理是真实的〔48〕;而当战争即将结束时九莉却“希望它永远打下去”,虽有一种矫情在里面,但她“不觉得良心上过不去”的态度却难免说不过去〔49〕;尤其是在最后结尾时,张爱玲还忘不了对现实时空中的“大陆”做一点揶揄甚至讽刺:“现在大陆上他们也没戏可演了。她在海外在电视上看见大陆上出来的杂技团,能在自行车上倒竖蜻蜓,两只脚并着顶球,花样百出,不像海狮只会用嘴顶球,不禁伤感,想到:‘到底我们中国人聪明,比海狮强。’”〔50〕看到张爱玲如此不再遮遮掩掩地将自己的“政治底色”如此“揭发出来”,前面有关其政治叙事的指认应该可以更加凿实了吧!
实际上,一直以来在张爱玲的定位与评价当中,始终都存在着一些来自不同政治立场的阅读和评判,尤其在《十八春》、《小艾》、《秧歌》和《赤地之恋》等一些具有鲜明“政治情绪”的作品上。因此,稍微系统一点地发掘并梳理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政治叙事”,应该是可以寻绎到一个重新审视张爱玲的视角,并对其文学世界做出符合实际的解读的。
〔1〕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1944)中说:“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在《有几句话同读者说》(1947)中也说:“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74,258.
〔2〕按出版时间,《小团圆》是张爱玲最后面世的小说,但《同学少年都不贱》的写作时间可能在《小团圆》之后。据陈子善考论,《同学少年都不贱》的创作时间当在1973至1978年间,而据宋以朗随《小团圆》出版时公开的通信来看,《小团圆》应该在1976年3月便已完成并寄出。同学少年都不贱·序〔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小团圆·前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54.
〔4〕苏伟贞.孤岛张爱玲〔M〕.台湾:三民书局,2002:29.
〔5〕《传奇》于1944年8月15日由上海杂志社初版,《传奇》增订本于1946年由上海山河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略可以“唯一”概称。
〔6〕〔21〕张文东.“自己的文章”的背后——张爱玲《传奇》的政治叙事〔J〕.文艺争鸣,2010(7).
〔7〕〔11〕〔13〕〔15〕〔16〕〔19〕〔33〕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228,238,172,53,174,105,133-134.
〔8〕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M〕.北京:三联书店,1998:15.
〔9〕〔23〕柯灵.遥寄张爱玲〔J〕.//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425.
〔10〕这是借用阿尔蒙德、鲍威尔的“政治文化”观点,指“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本文中的所谓“政治”通常是在这个意义上的用法。见〔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12〕骆冬青.叙事智慧与政治意识〔J〕.小说评论,2008(4).
〔14〕解志熙.走向妥协的人与文〔J〕.文学评论,2009(2).
〔17〕这里所谓的“公共空间”及“个人空间”或“私人空间”,是我个人的一种理解和用法,主要是指在“公众”和“个人”的对立意义上所生成的“生存活动空间”,其“政治性”隐含在某种“活动方式”与“活动场域”的关系中,当然也隐含着某种权力结构。
〔18〕〔20〕徐贲.文学公共性与作家的社会行动〔J〕.文艺理论研究,2009(1).
〔22〕陈子善.1945—1949年间的张爱玲〔J〕.南通大学学报,2007(3).
〔24〕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132.
〔25〕叔红.与梁京谈《十八春》〔J〕.见金宏达.昨夜月色〔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215.
〔26〕〔39〕〔41〕〔42〕张爱玲.重访边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30,121,111,155.
〔27〕〔37〕杜英.离沪前的张爱玲与她的新上海文化界〔J〕.见李欧梵.重读张爱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354,366.
〔28〕1952年7月,张爱玲持香港大学同意复学证明出境抵港,先寄住女青年会,11月因“奖学金波折”,乘船赴日本寻昔日好友炎樱谋求工作未果,三个月后返港,开始为美新处工作,参见陈子善作《张爱玲年表》,收入《同学少年都不贱》。又,此间经历后在其小说《浮花浪蕊》及《小团圆》中均有体现,既可见张爱玲初出大陆后生计之艰难,更可见出《秧歌》、《赤地之恋》两部作品实为其“生存政治”下之产品。
〔29〕张爱玲.秧歌〔M〕.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193.
〔30〕张爱玲.赤地之恋〔M〕.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3.
〔31〕艾晓明不仅查阅了1950年至1954年间的《人民文学》,而且遍查了1950-1954年间当时登载这类检讨最多的《文艺报》,也没有任何发现。见艾晓明.从文本到彼岸〔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30.
〔32〕据袁良骏说,张爱玲曾随上海作家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江苏农村走过几天,这一材料来自于上海文坛前辈唐弢与袁的谈话。不过据张子静说,他曾就“有人传说张爱玲曾去苏北参加土改”一事专门问过上海文艺界前辈龚之方,而龚之方则答曰:“我不清楚这回事,我也没听张爱玲提起过。”分析来看,龚之方自1946年7月与张爱玲相识,至张离开大陆之前一直来往密切,张的《太太万岁》等影片就是由龚与桑弧共约创作的,《传奇》增订本也是两人合作结果,龚还是当年《亦报》社长,张创作《十八春》,也是龚与当时《亦报》总编唐大郎两人共约并连载于《亦报》。由此可见,以龚与张的熟悉程度与密切联络,如果张在农村呆上一段时间参加土改,既使张不说,龚也应大概知道。故可见此事大致为虚。
〔34〕水晶.替张爱玲补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20.
〔35〕张爱玲最初写《秧歌》时,便有用英文写作——因不合中国读者以及东南亚读者口味——来试图进入“英语”文学世界的努力,不过最后未能如愿。虽然1955年英文版《秧歌》由美国纽约 Charles Scribner’s Sons公司出版后得到些许好评,但从1957年《赤地之恋》(The Naked Edrth)英文稿不为美国纽约Dell公司接受之后,其先后创作或改写的《粉泪》(Prnk Tears)、《北地胭脂》(The Rouge of the North)也始终命运不济,虽然最后《北地胭脂》终由英国伦敦Cassell&Company出版社出版,但反应寥寥,“张爱玲从此对英文创作小说不抱任何希望”。
〔36〕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于1961年3月在美国出版之后,张爱玲便成为与大陆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另一极”阅读中的经典之作。
〔38〕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J〕.万象,1944,5(3).
〔40〕张爱玲另有一次也谈到《色·戒》的材料,不过不是什么回应,而是说“故事都曾经使我感动”,“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过程”。张爱玲.惘然记·序〔J〕.//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339.
〔43〕余斌.张爱玲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91.
〔44〕〔45〕〔46〕〔48〕〔49〕〔50〕张爱玲.小团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前言,15,283,56,209,283.
〔47〕林幸谦.张爱玲“新作”《小团圆》的解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