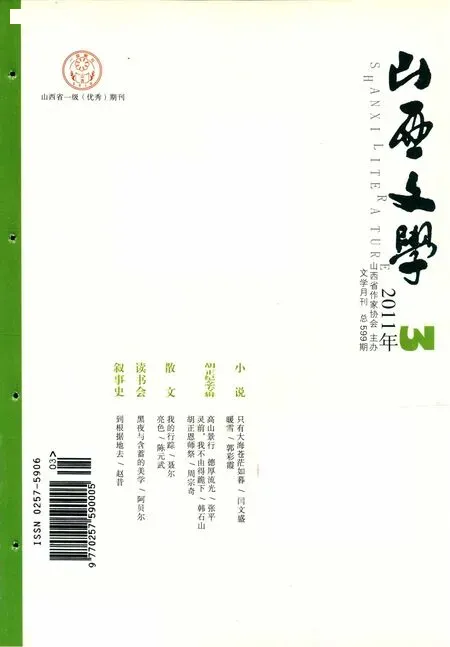被想象的生活够不够宽阔
陈克海
被想象的生活够不够宽阔
陈克海
认识文盛好几年了,头一回见他,他坐在那里,自始至终,一声不吭,不免心下骇然,好家伙,世上还有比我更闷的人。当然,这肯定是偏见,那个时候,我二十郎当岁,看人待物,没什么主见,几年过去,现在也没什么主见,成见倒是与日俱增。碰面的次数多了,才明白,他已经把沉默寡言发扬成一种生活习惯啦。来办公室转悠时,也不说多话,翻翻杂志,弄完了他要办的事,抬腿就走。这和想象中的那种人际交往太不一样了。不是应该弄点热情出来么,不是得敷衍一番么,总要寒暄两句吧。寒暄不会,总得做出点倾听的姿态吧。可,他连这些都省去了。他懒得虚情假意。
怎么能这样呢?
为什么不能这样?
直到后来,陆续读了他的些散文。他在文章中反思。他津津乐道日常琐事。原来他把热情都用在这上头了。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小宇宙。别看平日里不吭不哈,其实是在观察,在审视。看似写的是内心微妙情绪,却有对庸常生活的反抗。
按照我的理解,在一个口语化的时代,投机取巧者都在做流水账,贩卖流言和八卦,而文盛,居然用的是半文言的笔法,看看他的散文里都有些什么句式吧:设若,目下,譬如……我为吗一叶障目,老抓住这些不放?拔高点讲,作为一个没念过多少古书的文盲,我想,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你看,从鲁迅、胡适、周作人那拨人以来,这个传统就有了,他们古文的底子好,又有现代的观念,表达看起来半文不白,却是地道民族的。抛开立场不谈,单说形式。什么是文化?文化不就是流布在这些文字当中嘛。
我怎么表达不清了呢?在一个清汤寡水文字速朽的时代,文盛如此执拗,故意把文章摆弄得古旧,节奏慢了一拍,感觉,似乎也就来了。
印象中,他好像说过特别喜欢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而他的絮叨风格,即便不是受了老普的影响,至少影响过他看待人间诸事的角度。文盛的强悍处在于,看似温吞的一个人,铺排起文字来,表达的欲望却特别强烈,一句跟一句,不带用句号,还喜欢用分号,一排列就是好几行。
但,能看出来,夸夸其谈,或者说,哗众取宠,并不是他的追求,他想的还是要探究生活的本来面目。他在尽力琢磨:为什么世界偏偏变成了这个样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糟糕了?
他是摆明了要来说教的。他把生活的表象一层层拨开,企图将格物致知的本事应用到写作中来。他处理文字时多么讲究,至少他是奔着讲究的方向去的。这可能和他细腻的性格相关。细腻可不是绵软。他倔强。要不是有足够信念的支撑,他靠什么来维系那浓酽的情感?从他的文字当中,可以看出他对传统的迷恋。他在以自己的标准打量人世,衡量他眼中的事物。最新由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的《失踪者的旅行》,就是他的追求他的成果的集中展示。说集中展示可真不是什么虚头巴脑的词儿,看看那些标题……我的意思是说,在没有足够时间阅读内文的情况下,看看标题应该也能明白他想表达什么了。换成是我,哪敢用那样一些词儿。我喜欢朴素实在点的东西,而文盛,摆明了是奔着传唱千古的艺术范儿去的。他确实是在用心爱着他笔下的一切,他维护自己的文字,时刻都透着几分唯美的劲儿。生活再怎么不尽如人意,可在他的笔下,似乎也有了那么点迷离的意思了。对,就是迷离,乏味的生活一经他分析,设若,就显得意味深长了。
照已有定论的说法:“文盛的散文作品,大多写于他远离故土之后在各地漂泊的时间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他采用了内心诉说的方式,把阅读者想象成了一个具体的人,坐在他的面前,听他叙述往事、思考、渴望和焦虑。同时又有相当多一部分作品,则是把社会、乡村、土地等作为考察对象,进行私人化的描述、观照与思考,这使得他的散文出现了向外和向内两个方向的延伸,从而构成了他的散文世界。”
我以为也就是这样了。
谁知道他竟然写开了小说。
而且用的还是散文的笔法。
一般这样来解释散文笔法:“散文笔法有许多,主要有写意、延伸、指点、兴波四种。”看起来,文盛也真是这么做的。几年来,文盛的小说也在各大刊物发了不少,这里不说别的,就谈谈在本刊发的两篇吧。
先说《分居》。《分居》讲了个什么故事?粗粗读来,也没说出什么故事。似乎作者的心思并不在故事上头,他一直在反思。他铺排的速度多快。几十年的婚姻,那么漫长,将错就错的夫妻,两代人的隔阂与包容,他信笔写来,浓缩在了短短的九千来字中。真要提取故事,也只能约略说个大概,因为作者用的也是绍介性的笔法,好像根本不管不顾读者要的是以情动人,他上来抱着的就是讲道理的姿态。是啊,你看,父母的冷战给儿子造成了多么沉重的心理阴影。好像又不全是这样。咳,他是个多么爱絮叨的人,鸡零狗碎的事情,看不出有多奇特,可他如此有耐心,似乎这辛酸的人生当中,藏着别样的秘密。
真的是这样。通过再现无聊的生活,折射出如魔似幻的当下。在他的笔下,现在的人不知怎么了,似乎总是面带菜色,一腔抱怨和不满。他们的小奸小恶,甚而是算计的得意,仿佛都带有悲愤的色泽。
写家长里短,人生穷酸,美国有个卡佛,干得特别漂亮。他不交代,只是不声不响地折腾出细节来,然后,就像俗话说的那样,随着阅读的深入,被感动了。啊,卡佛。我为什么要提卡佛?人人都在说简约,可我从他的小说中读到的是人生的无奈?为吗?因为每个人都会在用心观看的事物上发现自己的影子。
照我鄙陋的理解,小说么,就是飞短流长,就是疯长的野史,就是对正史含沙射影的一点修正,就是渲染在现实之外的一点幻梦,现实问题又不能靠小说解决,至少小说的主要功能不是奔着去解决问题的。往远了说,现在的人,抱负太大,杂念太多,没搞明白怎么在小说里过日子,怎么在小说里做人,结果误把平庸的唠叨当成了诚实的叙述。于是,写恶恨不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幽默感少得可怜,更糟心的是,大家要么装疯卖傻,要么拿苍白无知当噱头,要么直奔恐怖和不幸,纠结欲望和残酷。人的面目,暧昧不清,事的进程,似是而非,本来彩色的世界,好像完全被缺乏理性盲目苟且的人盘踞。结果私欲放任,故事本身魂飞魄散,磕巴无聊。帕斯卡尔说,没有平淡无奇的人,只有平淡无奇的观点。而那些声称为了谁为了谁写作的人,他们热情的生活劲儿都跑到哪里去了?多么邪恶。搞到后来,好像脱离了有趣的故事,小说才能得以正名,灵魂唯有在乏味的苦难中打滚,才能获得更纯粹的依托。我们的生活,被灌输的奇谈怪论已经够多的了,现在轮到小说也成了超度自我的工具。
无疑,文盛的小说也有类似用力过猛的趋向。这只是最初的印象,读到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写出了平庸生活,却无喧闹,有的却是苦口婆心的安静。
生命中的恶意一点点消散,渐渐开始澄明懂事起来。
非要找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我一时难以适应的是,文盛在《分居》用了那么多的分号。就像我初读李娟的散文时,就是那个阿勒泰的李娟,写散文的李娟,看到一页页到处都是省略号时,也是半天适应不了,后来发现,好家伙,原来省略号可以用得这么别致,意想不到的转折,有真欢喜,也有小惊奇,读起来真是别有味道啊。文字的褶皱里满是按捺不住的可乐情绪。这里不加转折了,我是说,好像现在写小说很少有人像文盛这么干了,干吗老用分号呢,大家都是直接分段了。又清爽,又自然,看起来效果也差不到哪里去。一堆堆着,老是平行,排比,这个,果真能增强文章的气场吗?
再说《只有大海苍茫如暮》。
在这里,文盛把那种夫妻间将就凑合的状态撕开了,根本不给人一点希望。一对夫妻,搞不清楚他们怎么生活到了一起,到了一起,怎么又没有好好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模棱两可的,言不由衷的。读这样的故事,让人恍惚处于其中,特别容易对号入座,容易把它看成是未来生活的前景。一地鸡毛的生活,刘震云写过,烦恼人生,池莉写过,刘恒也写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同样是写夫妻生活,为什么读文盛写的,总让我抓狂呢?他对人的善意呢?
啊,没有批斗文盛的意思,我只是痛恨他把人的温情去掉了,这些分明就是生活原初的样子,他却还要黑字白纸地再来强调一遍。往狠里说,这都不是什么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了,而是立场问题。不是说要弘扬真善美么,怎么能揪住人性的私处人性的恶不放呢?
真是让人绝望。作为一个宿命论者,我更偏好以嬉皮笑脸的方式应对悲观。人人都想糊个大花脸,喧哗一下,闹热一下,乐呵乐呵,阿Q一下,来掩饰自己还死皮赖脸活在当下的尴尬,而他,文盛,却不留情面,他是如此热衷审视人生,以至于逮住个物事,就想倒吊起来,严刑逼供一番,拷打出暗藏的秩序。他摽着劲,往人间真相的地方奔,往人事抵牾的路子上走,好像人世间,唯余勾心斗角,男女战争,焦虑啊……叫人情何以堪。
责任编辑/吴 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