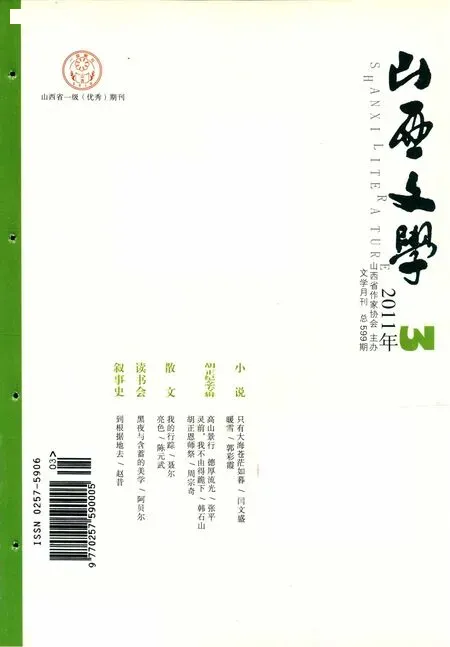亮 色
陈元武
亮 色
陈元武
1
我曾经试图打开那个金属盒子,可是徒劳无功。它被锈严严地封死,或许,已经死亡的历史是不可以重新开启的,它封住了一段历史。我看过父亲将它随身带着,形影不离,或许,父亲并不想让我们知道盒子里的秘密。它被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个先辈摩挲过,除了那把锁之外,呈现出一种铁的亮色,使银亮的底子蒙上了些许汗的化学成分,乌哑的氧化铁遮盖住了铁的本色。虽然,它依然闪着亮光,在一次次被肉体温暖和冷却之后,金属的亮色失去了原始的意味。
父亲喜欢将铁盒子揣在身上,虽然,这样让他感觉不舒服,沉重的铁盒将他的衣服坠斜向一边,看上去,他有点溜肩。我问过父亲,那里边有什么东西?父亲看了看我,不知道,你爷爷就这么揣着它,我从小就看你爷爷这么揣着,寸步不离。那他知道里头有什么吗?父亲摇了摇头。这成了我睡不着觉的一件巨大的诱惑,这个秘密太诱人,可是,我没有胆量去尝试父亲的宽容程度,父亲绝不允许我们哪怕碰那个铁盒子一个手指头。我想,谁家都会有这样的秘密,一个不可以打开的暗盒可能包含了这个家庭最为重要的历史谜案,它会是打开那个谜案的唯一钥匙。父亲迟早会将铁盒子传给我的,就像他的父亲最终将铁盒子传给他一样。我只有耐心地等待,才会将这个谜底揭开,不让它继续成为一个谜。
早晨的太阳高高升起,父亲出去了,他像往常一样,下地干活。铁盒子留在了家里,放在了那口樟木箱里。老屋里里外外透着盛夏潮湿而新鲜的空气,树叶让风和阳光蒸得半蔫。蝉在树荫里扯开喉咙,释放出持续的噪音。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南方的盛夏,屋外是火,屋里是水。一棵树拦住了半屋顶的阳光,一口井将地底下积蓄的凉气呼呼地往外喷。树荫底下的生活是惬意的,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太阳照在邻家的屋顶上,一片片瓦反射着不太清晰的光,除了那几扇玻璃窗外。红红的砖墙或者瓦片,让盛夏具有真实的意义。稻田里飘着青草的气息,以及稻草和稻穗略带微腥的香味。这是一种视觉的盛宴,浓重的油彩,那种被烤化的柠檬黄四处流淌。青草让这四处流淌的柠檬黄里透出另一种明亮而晃眼的颜色,它仿佛刀的锋刃部分。青草也让大地保持着一种清醒状态,黄色是与死亡接近的名词。大地需要持续不断的生气。稻田让苍老过早地降临大地,南方一年中需要经过两次以上的收获。绿色、黄色,再绿色、再黄色,季节就走到了头。
盛夏的天空无法用字眼来形容,说实话,我很喜欢这种蓝得几乎纯粹的颜色,它是一种冷色调,就像钢铁,像一泓巨大而无比深邃的海。南方的太阳名符其实,它将一片片荔枝树叶烤出一种类似于陶釉的亮色。我躺在竹床上,胡思乱想着与那个铁盒子有关的各种答案。竹床类似于古代的一种家具——美人躺,它有着优美的弧形,细腻的竹皮让肉体和汗渍磨蚀得光滑而明亮,它呈一种深紫色,微微具有玉石的透明质地。我被浓烈的颜色包围着,任何的思路可能出现转机,思索需要冷静和灵感,铁的亮色让我费尽脑汁,无所收获。我只能漫无目的地看天空,搜索每一片飘过的云团。在幽深和暗蓝色之间揣测太阳的高度和阳光的方向。这是一种视觉上的累,像长时间对着一朵白色的花一样,最终,我会失去视觉,陷入一种暗绿色的黑暗中。
我手里握着一只碗,瓷碗让我的思索有了具体的物象。屋檐下摆着几只酸菜坛子,每年这个时候,需要对坛子进行曝晒。坛子表面亮光闪闪,琉璃光色,院子里还有一架瓜棚,交织着丝瓜和瓠瓜、苦瓜等藤蔓和花朵,果实累累,层出不穷。金黄色的花朵和纯白色的花朵同样具有视觉上的优势。视觉在强烈的光线下疲劳,我感觉头微微地胀疼。手中瓷碗里的开水一点点凉下去,甚至低于我掌心的温度。这种沁凉的感觉能够使我重新回到清晰的思索中。我反反复复地想着那些可能的结果,那铁盒子里有我们家的屋契、婚约、田契、某位做过大官的祖先的遗训、某件珍宝、血书、或者是某种家族唯一的凭证?我母亲是童养媳,她娘家在离这十几里外的坂头村,三岁的母亲被送给了我的大舅伯家,然后嫁到我家,这中间出现某些变故?母亲是否有卖身契?或者是大舅伯家欠我家什么?有什么字据为证?这都可能是铁盒里的物什。可是,它传自我的祖父,是不是我祖父最先拥有这只铁盒子?丝瓜花浓烈的颜色和香气引来了许多昆虫,它们发出轰炸机般的动静,这让我心烦意乱。我一无所获,在接近一个早晨的时光里,我被困惑所磨蚀着,像一只找不到巢穴的蜜蜂,懵头乱转。我感觉有些疲惫,盛夏的热无以复加。我被谜一样的壳重重裹着,动弹不得。
2
我不知道早稻的收割何时开始。父亲给了我新的任务,我得为他准备好锋快的镰刀。家里共有十三把镰刀,父亲刚从打铁铺那里订制了几把。那些镰刀经过若干个季节的休憩,已经蒙上一层灰尘,锋刃喑哑,暗褐色铁锈像菌一样繁殖蔓延。南方的镰刀更像月牙,不像北方,像把大锯子。镰刀的锋刃是锯齿状,它会被锈钝化,失去刃齿,会被稻草啃去锋刃,最终,会被稻草磨成一块废铁,回到它的出生地——打铁铺。磨镰刀有个说法,不能磨光,就是带着磨石的削痕,这样才是把好镰。父亲交给我十几把新旧的镰刀。我只得去找张屠夫借磨石。
磨好的镰刀让我有一种快感,我将它们背回家的时候,微微感觉到它们的锋刃刺痛我的后背。风从我背后刮过去,或是风已经被镰刀割成无数绺碎片,风已经不是完整的风了,它像一块巨大而透明的绸布,在我的面前破碎。我想象着稻草在它们的刃齿下纷纷倒下的情形。这是一种铁制的牙齿,比蝗虫更加可怕而威力无比。田野里的柠檬黄颜色在消退,夏天像一片片树叶一样飞快地飞走。在一小片收割过的稻田里,小小的水洼反射出一片刺眼的亮光。这是如释重负后的大地积聚的一点点小情调,像一块刚刚剃光的头皮,泛着青光,颇为惬意和轻松。大地在努力恢复着本色,在泥泞、水、阳光的重复作用下,它渐渐地苏醒,但是不久,又会被牛蹄和犁铧的锋刃践踏蹂躏一番,然后重新被水淹没,插上新的稻秧,继续着下一个轮回。我好像很喜欢收割后的田野那种难得的娴静,赶着鸡鸭下田,看着它们与野麻雀争食的场面。太阳向着山后落去,在下午宁静和燠热的风中,我骑在一棵荔枝树上,继续着那无谓的猜测。吹过树林的风变成杂乱无章,像无数枚暗器,击中我的身体。我悬于河流之上,荔枝树倾向河中央。这是很微妙的体验,人在河水与天空之间,被一棵浓密的树所搁置,像一只无名的鸟儿。树叶响动,像水泼出去的声音,河水或明或暗。水草在河水的暗处簇集并蔓延,我像一只鸟一样关注着河水和鱼的动静。那一片片闪忽的亮光让我炫迷,阳光透过无数的树叶,打击着树底的荫凉。我被困惑所搅扰不安,父亲究竟会不会将他的铁盒子交付给我?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或许,就像这河流一样,时光流走了,鱼游走了,可是,那些水草不会流走,还有树的倒影不会流走。亮色总是被暗色所遮盖着,重重叠叠的亮色和暗色错综复杂,像一团麻一样,不知道何始何终。我想,随着时光流逝,父亲会将所有的秘密负责任地告诉给他的儿子。家族的历史就像田野的季节一样,节节相扣,毫厘不悖。
父亲总有干不完的活,所以,我们之间缺少交流,父亲沉默得像一块石头。他过早地负起家庭的重担,母亲只能是一个配角。父亲的沉默让我无语,我常常和他说不上话,偶尔说什么话,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父亲惜话如金,或者,他天生就不善交谈。父亲的沉默让我和他产生了距离感,我不敢太放肆,也不敢不按他的话做事情。因此,父亲的铁盒我无缘接触。我仿佛穿过一条小巷,这条巷深不知底,幽暗或者微微明亮,如错杂的山墙。父亲可能很想向我洞开一扇门,可是我太小了,或者,他认为我还不到能够理解他的想法的年龄。我从铁器的角度揣度父亲的内心世界,他坚强,像一块铁,但他很钝,不是一把好刀,他的钝让我失去了了解他的机会。一些树渐渐地长出墙头,我没有树的生成速度。院子限制了我的想象自由,我在磨刀石和铁器之间徘徊,我像是磨刀时泼上去的水,我无法定形,瞬间就流走了。我希望自己会透过喑哑的铁盒,看清楚里边的物什。我朝墙看,希望能够看透墙体,看到墙后躲着的一只鸡或者一条狗。可是我什么也没能看见,我只好闭上眼睛,想象总是无拘无束的。
家里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动,母亲被生产队委派去养那几头耕牛。母亲的腿关节有毛病,走不得远路,而放牛需要去后山,那里有草坡,有和我一样高的苇草。养牛能够给家里带来一些好处,比如,生产队按一头牛一年三百个工分给母亲记账,年底分红。母亲分担了一些家庭的任务。我却要为母亲分担放牛的任务。我上学的学校离后山不远,我能够做到将牛赶到那里,将牛绳的一端用铁桩钉在地上,然后去上学,放学后再将牛赶回家。有时候,是母亲自己将牛赶上后山,然后,我再将牛赶回去。星期天和母亲上山割草,让牛驮回家,备雨天用。母亲没有牛高,牛自然不将她的吆喝当成一回事。牛怕我,我会使狠劲抽牛,我有我的办法。
3
打铁铺里终日火光冲天,锤声交加。一块烧得通红的铁在锤的重击下柔软得像面团。一把刀的制作过程也就是小半天的锤锻,淬火,再回炉,再锤锻,再淬火。刀刃打出浅浅的窝窝,交给主家自己回去磨削。牛的鼻子需要定期更换鼻拴铁,控制牛全靠它,绳子拴住一扯,牛钻心地疼,不得不听人摆布。牛铁需要钢质好的,含碳低的钢质好,不脆,那铁用上一阵子,就让牛鼻涕泡烂了,不小心就扯断,将牛鼻子扎出血来。牛鼻子受伤,就不吃草,疼啊。
我看着他们打铁,心里生出快感。铁的硬度毕竟没有火和锤子厉害。我想到那把锁、铁盒子,这种念头一闪即消。牛铁打好了,牛换鼻拴是件难活,这不是我干得了的。在后山,红土堆成的后山绝异于稻田,红土的后山是先人们安息的地方,埋着许多先人的地方,是习惯中人们止步的地方,我不知道在这种地方放牛是不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牛喜欢那里茂密的草,我喜欢后山的高度,让我有了俯瞰村庄和田野的机会。在初秋的时候,满山长出旗帜一般的芒苇,狼藉遍地。秋的意味从风中一点点明晰了起来,我像一枚果实一样,由青转黄。后山通往西边无穷的群山,后山只是一个引子,一首曲子的引子。
我一步步走向后山,跟在牛的身后,牛胯下滴沥着不明的液体。随风扑面而来,臊气难闻。我发现我的身体开始变化,鼻子底下长出毛茸茸的须苗,我的声音开始变粗,我有时候感觉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让我哑然失声,然后突然蹦出一种让我吃惊的陌生的声音,我的喉结开始突出,我的胸部隐隐胀疼,我开始遗精和失眠。父亲发现了我的变化,脸上露出一种期待的微笑。我的内心开始有一团火,燃烧的时候像被阳光突然灼伤一样,浑身火辣辣地难受。身体的荷尔蒙开始苏醒,我向父亲的未来一步步靠近。牛开始感受到我的变化,我火暴的脾气,我突然猛增的力气,它低驯着走路,夹紧了胯小跑着,唯恐挨我的鞭子。山上太多的芒苇,让我看不清祖父们的坟地在哪儿。芒苇坚韧地打在我的身上,像我抽牛一样抽着我,虽然它的花序柔软无比,但它的身体部位坚而硬实,如竹子一般。这清醒的刺痛让我冷静,我反思我的一切。大地开始被秋色所笼罩,我抚摸着日渐枯萎的芒苇,失声痛哭。我向铁盒的秘密越来越近了,突然我又害怕知道那个秘密。它几乎是我生活乐趣的全部,我怕忽然间明白了一切,而它却与我想象的任何一种答案都不同。我害怕我失去想象的对象。我害怕铁的亮光,我战战兢兢地怀揣着任何一件铁器。我想,我失去了某些自由和选择。我会被铁盒所禁锢,甚至会被无形的铁所包围,成为它的某个秘密的延续。
在某一夜,月光遍地。我忐忑不安。父亲突然想和我长聊。我们聊什么?牛、刀具还是后山?父亲不会和我聊铁盒的事情,他不急于让我知道那些秘密。我不知道他会和我聊什么。月光从院墙上泻进来,像泼进来的水,满地的亮色,像银子,像铁器磨过的部分。父亲的额头上也泼了一片月光,闪亮,像一件铁器一样幽暗而莫测。父亲点着一根烟,说:你是不是想知道铁盒子里都有啥?我无措地点头,然后摇头。父亲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将铁盒交给我。父亲已经将铁盒用砂纸磨了一遍,亮晃晃的,闪着月的冷光。锁已经开了。父亲说:秋收的时候,我就知道该给你看铁盒子了。因为我在你这么大的光景,你爷爷也给了我这个铁盒。我不知所措。父亲亲手将铁盒子打开。
里边空无一物。但十分晶亮,仿佛从来没有生过一丝锈迹。
父亲说:这是你爷爷偷的一只洋烟盒,从他的东家那里偷来的,他深感耻辱,就决定将它世代相传。为的是让后人不再犯错,不再贪非分之物。清清白白做人,像这铁盒的内里一样,外头虽然锈着,里头可不能锈了。
责任编辑/白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