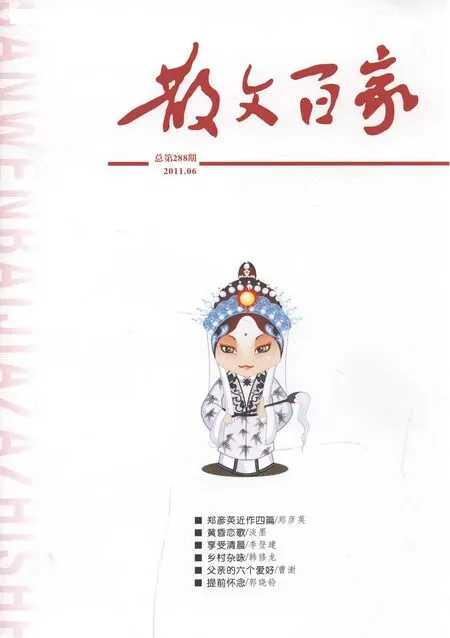郑彦英近作四篇
●郑彦英
郑彦英近作四篇
●郑彦英
母亲的安然
母亲今年79岁了,我们做儿子的,按照过九不过十的乡俗,给她过了80大寿。
母亲的头发朝着白色上发展,大部分是灰色,一部分是黑色,还有能数过来的一些白丝。母亲腰不酸,腿不疼,上下楼比我还快。小区的几位老太太,羡慕地向我询问母亲如此硬朗的原因。我说,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手从来没有停止过劳动,还有,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母亲每天晚上都在炕上纺线,纺线时盘着腿,腰直着,右手一圈一圈地摇纺车,左手从下到上来来回回地拽线,当时是为了一家九口人的衣裳,现在看来,这些劳动很像现在的瑜伽。
其实父亲的身体比母亲还好,大前年,父亲骑着自行车,驮着母亲,从他们居住的姚寨小区出发,到航海路去逛,距离大概有十公里,来回就是二十公里左右,我听说后向父亲表示担忧,父亲说:“这能有拉架子车累?一点都没事!”
父亲每到清明前都要带着母亲回老家,说是急着回去上坟,我知道还有一条原因,父亲酷爱下象棋,他陕西口音重,在城里没找到能和他下棋的人。前年初冬,他和乡亲下棋,坐在马扎上,棋盘铺在地上,头低着,四个多小时后,他身子一歪,离开了我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当时我在景德镇电视剧拍摄现场,接到噩耗后立即乘飞机飞回老家,在北京转机的时候,我的泪水不住地流,弄得候机室的许多人都看我。其实我的悔恨比泪水还要稠密。因为我已经托围棋八段王冠军先生为父亲找到了一个下象棋的人,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把这个消息早一些告诉他,否则,他就会早一些来郑州,在郑州下棋,坐在桌子前,头朝上,怎么会一去不回呢?
将父亲安葬后,我排除多方主张,坚决把母亲接到郑州,陕西老家那张土炕,承载了她和父亲许多年的生活,住在这里,每一个物件都会把她带往昔日时光,她就会朝朝暮暮地被悲伤笼罩着。而郑州不同,她这些年和父亲就是在这里享受暖气,几乎是暖气来时他们来,暖气停后他们走。但是,这次只剩母亲一个人了,对母亲来说,失去丈夫,绝不仅仅是失去了一面天,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原来的生活秩序和习惯,这些秩序和习惯所构成的岁月链条,会缠绕甚至撕扯母亲的心理堤坝。怎样让母亲远离这个链条呢?我和在郑州铁路局上班的弟弟商量,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母亲被连绵不断的亲情围绕着,被亲情牵出来的劳作忙活着,让她很少有空回忆,这样,母亲就会很快进入新的生活状态。
我弟弟有一对双胞胎女儿,正在上初中,我便让弟弟一家住在母亲这里,两个孩子正是发奋学习的时候,早出晚归,三餐饭都吃得匆匆忙忙。母亲一到,就为两个孙女的学业操心劳神,孩子快放学的时候,她站在阳台上眼巴巴地看着归家的路;晚上,孩子做作业的时候,她惟恐孩子睡得太晚;早晨天没亮,就唤孩子起床上学。上午和下午,空闲时间长些,我让母亲到楼下去,楼下有个停车场,院里的老太太们爱聚在那里聊天,我让母亲去和她们说话。母亲开始担心自己一个农村老人,会被人看轻,就拿着针线活,这是母亲一辈子的习惯,在村里,和乡亲说话是不会影响做活的。没想到的是,母亲拿着针线活,一下子就融入了小区老太太们的群体,因为她们大都不做针线,母亲的针线也许唤起了她们年轻时或者更遥远的记忆,她们就向母亲请教做针线的一道道工序,有的甚至要购买母亲做的鞋子,母亲说:“鞋给你,钱是贵贱不能要的。”有人要,说明他们稀罕,说明他们认同。自然,母亲由此得到了许多自豪,我一去就给我说,谁向她要鞋样子了,谁家得了小孙子,让她帮着做月子里娃娃的衣服裹肚。我一听很高兴,知道母亲已经走进新的生活,有了新的生命光景。而且,母亲过去生活在父亲的大树下,父亲的喜怒哀乐就是她的喜怒哀乐,现在,母亲自己立起来了,有了自己的牵挂,有了自己的圈子,有了自己的荣誉和自豪。
但是,母亲最为重视的,还是我的生活和身体。得知我长期对着电脑写作,近期眼睛常常发干泛酸后,一见我就说:“不能再写了,都五十多的人了,得啥都没用,只有身子是自个的。”
我喜欢母亲做的菜面,母亲就到菜市场去,亲自挑选菠菜或者红薯叶,回家后洗净,用开水一过,就直接将过水菜放在面里合,这种面特别好吃。但是我的行政事务多,并不能每天去母亲那里,而且,行政事务千变万化,自己并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时间,我常常去母亲那里时,已经到了吃饭时候,母亲就有些措手不及。于是,母亲干脆把菜面做好,速冻在冰箱里,冰箱里放了三层。因为有时候我还带着孩子朋友去吃,这让母亲很高兴,我们一到,她就烧开水下面,每每看到我们吃得很香的样子,母亲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填满了喜悦。
十一月下旬,省里开中原作家论坛,请了铁凝主席和全国大家来为河南作家把脉,加上会前会后的忙碌,一个星期没有去老娘那里,老娘就问弟弟:“会上的饭好?”弟弟说:“当然差不了,大部分是自助餐,想吃鱼有鱼,想吃肉有肉。”母亲听后点点头,没有吭气。弟弟一想不对,就给我打电话:“妈知道你忙,问会上的饭菜呢。”
放下电话,我在陪全国重要作家吃饭时,尽量少动筷子,饭后立即赶到母亲那里,海海地吃了一碗菜面,心满意足地抹嘴的时候,母亲说:“没有会上的饭好吧?”我说:“再好的饭菜,也比不上妈这一碗面。”母亲笑了,笑得很浅,却很满足,然后说:“快去陪客人吧,别把远路人晾着了。”
今年初冬,是父亲去世两周年祭日,我在八行笺上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在父亲坟前烧了。信上有这样一段话:请父亲大人放心,母亲在郑州日子过得满满当当,心里头安安然然。
陕西关中方言中的安然,含有幸福的意思。在发音上,然字读作Ren。
毛胡子太阳
“豫东的麻雀都能喝四两酒!”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到河南工作时,这句民谚常常穿行在我工作的空间。冬天我到豫东组稿,我的几场大醉证实了这句民谚的准确。我很奇怪:这里远没有我家乡关中平原富庶,怎么遍地都是能喝酒的人?晚上散步于大街小巷,酒的味道弥散在空气里,划拳行令的声音将西北风切割成细碎的丝片。这里的房子大都很破旧,县城、乡镇、村落的区别在面积的大小上,不在建筑的高低上,每一家几乎都没有院墙,家里有人没人,房子门都开着,走进不管哪一家,能带走的东西只有锅碗瓢勺和破被子。这样的家境,在我老家关中,是绝对不能买酒喝的,关中人先要筑墙,然后置产,将所有有关生命安全的问题解决之后,才会置酒,喝酒也是小酌,而且是遇到婚丧嫁娶之类的大事才喝,这里的人怎么把我认为重要的都排在后面,而把喝酒排在前面?!
豫东人很快给了我答案,而且是三种。
第一种说法追溯到殷周之交,周朝军队将称为殷顽的殷商大员集中迁移到洛阳看管,而将其余殷商人员,从安阳、内黄等适合居住的地方赶出来,赶到了沼泽遍地的豫东,商人思念故乡,不能带走财产,就将故乡的名字商丘带了过来。殷商人在这片沼泽上艰苦创业,生活很快好起来,却担心周朝的眼细发现了他们的富庶,于是就将财物变成美酒美食,酒肉穿肠过,贫穷在表面。久而久之,这种好酒轻物之风渐渐变成习惯,一直遗留到现在。现在的商丘市版图是行政区划,实际上,殷商人遍布于目前的商丘、周口、亳州、曹州等地。
第二种说法将时间后移到元代。豫东地区是黄淮海平原的腹地,更是中原的心脏地区,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金元的铁蹄踏到中原,豫东必然在铁蹄之下,而豫东的人,背井离乡,远离中原,成了现在的客家人。北方游牧民族的人在中原依然保留着一匹马能驮走所有家产的习惯,豪饮本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人乐居豫东,哪有置产的兴致,每日半醺,是他们的最高境界。后来明取代元,但北方游牧人已经在中原几百年,历经数代,已经成了中原人的一部分。人是中原人,习惯却还是游牧习惯,这种种性随着血脉的流传一直至今。
第三种说法是有历史记载的,某年某月某日,黄河决口于某某地方,黄水泛滥至豫东某某地区,淹没良田多少顷,房屋多少间,致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出逃。而且,黄河发水大多在伏汛期,天热,水灾之后,相对干旱的豫东地区变得潮湿,利于蝗虫生长,蝗虫每来,遮天蔽日,地上所有绿色浩劫一空。千百年的记载一平均,就有了黄河三年两决口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令人恐怖的,三年两决口,水灾之后是蝗灾,人们还能安居么?所以,今日有酒今日醉,是黄河催生出来的豫东人的性格。
不久我到武汉大学上学,与豫东人朱秀海同学,他的家乡在鹿邑王皮六乡,他说很久以来,每到冬季,他们的乡亲就去全国各地要饭,腊月底回到家乡,从年三十到正月十五,王皮六的人都在喝酒,在所有背风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呼啸着呼噜的醉汉,还有吃了人的呕吐物醉倒的狗。他说在正月十五这一天,王皮六的月亮不可能是圆的,一双双惺忪的醉眼,能把月亮看成椭圆形就不错。我和朱秀海讨论形成豫东人性格的原因,我们倾向于后一种说法,殷商人和金元人历经数代,已经完全是中原人。生活在三年两决口的黄泛区,纵然是欧美白种黑种人,也会形成好酒轻物的习性。
今年春节前,我去了两趟豫东,我们摄影家协会组织摄影家,去给豫东一个乡村的每个家庭拍全家福。我惊奇地发现,这里的人几乎完全改了样子,住平房的有了院墙,盖楼房的门户严密,而且,每家都有像样的财物,大量的现代化设置。我和村民聊起了这种变化的原因,他们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年景好了,日子不往好处过往哪里过?
午饭跟乡亲们一起吃,我知道豫东人的酒量,先声明我的量不行。老乡说:不叫你多喝,光喝个一高一低一稳定。我问咋讲,老乡拿来三个烟盒,一个竖着立起在桌子上,一个横着立起,一个平放着,然后拿来三个平底茶杯,与三个烟盒对应放着,往三个杯中倒酒,每个杯中的酒和烟盒一样高,这就叫一高一低一稳定。我一看,单这三杯下去,我就醉了,便说:“我还是喝一稳定吧。”
稳定这个说法很好,油然让我想起三门峡大坝和小浪底大坝,就是这两个大坝,保证了豫东人民岁岁平安,安居乐业。
乡亲们不答应,在湿软稠密的劝酒中,我还是喝了一高一低一稳定,酒是本地产的酒,性烈,下肚后,我怎么也“稳定”不下来,只觉得太阳在我眼前摇晃,太阳咋像个老汉,长了一脸毛胡子?!我问同行的朋友,朋友回答说:“太阳被酒泡了。”
豫 赋
辛酉初秋,德国汉学家威先生访豫,我受友人之托到机场迎接。威先生金发碧眼,身高肩宽,却穿中式服装,与我一见而如故。
是时新雨初霁,清日出云,风习习而爽面,气湿湿而宜人。威先生上车之前即驻足近望,上车之后更凭窗远眺。见草木葱茏,庄稼茁壮,平原辽阔至眼光尽头,耕者踏歌在天地之间,叹道:“选择如此广袤原野生长繁衍,大象真乃灵物!”我愕然:“君言豫为大象?”威先生点头,“近年常见解豫之言,有人与大象亲密相处之说,有人与大象博而驯化之谈。”我摇头:“此乃望文而生义,均与史实不符。”威先生震动:“有此论者,依河南出土有大象化石为据。”我说:“除南北两极,各地皆有大象化石出土,此据不能服人。”威先生对:“汉字为象形字,豫字似有此像,再说典籍,许慎亦将豫解为大象。”我摆手:“此大象非彼大象,难道你不知豫州?未读易经?”
威先生求知心切,到郑州即阅经查典。夜半时分突然致电邀我共饮。此时明月高悬,白露低伏,列车疾行之声隐约远去,鹭鸟夜欢之音清晰飞来。我俩对坐于窗前,无老酒而有新茶。威先生微笑道:“今日读古,收获颇丰。知豫州为东汉州名,辖郡、国六,县九十七。豫为豫州之延续。豫字本意为欢喜快乐、安闲舒适,典中即有豫游、逸豫之词,上海之豫园,即为愉悦老亲而建。《说文解字》释豫为象之大者。此象非生物学之大象,而为大气象也!《周易》之豫卦为雷出地奋之象,生机盎然之势,故言豫之时义大矣哉!”
我不禁击掌应和,“河南称豫,名副其实。北有巍峨太行、王屋,南有峻秀大别、伏牛,西有苍茫崤山、秦岭,三方相合相抱,聚万象于其间;中岳嵩山于万象中挺拔而立,散灵气于四方;加之黄淮二河,蜿蜒奔流,滋润豫北、豫中、豫东之大平原,粮食产量为中华诸省之冠。金银铜铁等矿,从上古开采至今而不竭;钼铝铅钛等金属,为全球瞩目之蕴藏地。如此物华天宝,养万民安其居、美其服、甘其食、乐其俗。杰出人才,自然层出不穷。思想家有老庄二程;文学家有杜甫、韩愈、白居易;科学家有张衡、朱载堉、郭守敬;政治家有商鞅、李斯、贾谊等。河南向称中原,居中华腹地,中国之中,两大铁路动脉干线京广、陇海即交汇于郑州。一年四季、二十四节之分,亦由周公从登封告成测日影而定。因此,夏商王朝即建都于郑州,殷朝定都于安阳,宋金等六朝建都于开封,汉晋等九朝建都于洛阳,中华上下五千年之改朝换代,常在河南完成,故有问鼎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
威先生端坐静听,至此执杯而立,感慨道:“若以一动物喻河南,当改庄子《逍遥游》,中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话音刚落,突听窗外有飒飒之声,急开窗而视,见满天月光濛濛,遍地朝气腾腾,中原大地,似有起飞之势。
是夜,鲲鹏入梦,我乘鹏而翔,化为鹏之一羽。鹏之轻鸣,则声贯九州。梦醒,见晨曦入室,彩霞满天,心中澎湃而不能自已,遂焚香沐浴,笔记于上。
为今人写赋(代跋)
写《豫赋》,是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既然是任务,再艰难,也得完成。艰难的原因是我对赋体文章只知皮毛,虽然曾星星点点地读过一些古体赋,但是我从来没有写过。于是花了半个月时间,阅读研究了赋体文。
《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指赋的内容;铺采摛文,指赋的形态。
赋体文在内容上既然要通过“体物”来“写志”,就必然在艺术表现上注重于铺陈,词藻注重华美,色彩注重绚丽。赋体文特别讲究声韵美,将散文的章法、句式与诗歌的韵律、节奏相结合,用长短错落的句子、灵活多变的韵脚和排比、对偶的调式,形成自由而又严谨的文体,既有散文式的铺陈事理,又饱含诗意。所以深得古人喜爱。
赋体文大致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等阶段。可以看出,这几种赋的代表作,在当时都是上好的文章,可以说是流传千古的佳作,诵读每篇,都让我心动。但是要用这种文体写《豫赋》,生活在快节奏中的现代人不可能喜欢看,因为大量的排比、对偶句式和严谨得近乎于死板的文体,对今人的阅读形成很大负担,一些词句,甚至要查字典词典,这是繁忙的今人、特别是年轻人所难以接受的。
唐宋时期的文赋,是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由骈俪返回散体的赋体文,不刻求对偶、音律、藻采、典故,章法开放流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自由,若当今散文,好看好读。如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这是我反复诵读的几篇赋,比较下来,我更喜欢欧阳修的《秋声赋》和苏轼的《前赤壁赋》。这里面有人物故事,有对答呼应,文章因此而起伏多彩。于是我决定,以这种赋体,来写《豫赋》。
但真正开始写作,又遇到新的问题,这两篇赋中,一些词语在古文中司空见惯,于今人却略显生僻,如《前赤壁赋》中,光曰字,就用了4处,如果我也这样用,很多今人会读成日,而且会问,日字怎么弄扁了?更不知所云。为此我思索良久,如果将曰改成说,一些学者肯定笑我。但是反过来一想,文章是写给大众看的,不是写给几个学者看的,目的是为了让广大读者有阅读快感,而不是为了让几个学者认可。
就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我回避了古文中的生僻字,用文赋的写法,写出《豫赋》,前后历经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一千多字的文章。
写完之后我长出一口气,回头再看,就觉得不单是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更是给养育我的河南人民交了一份作业。感谢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宋华平先生将拙作书写成八幅六尺条幅到天津展出,由于书法的美丽使文章增色。
虎门思危
1980年夏天一个闷热的上午,我利用出差的机会,专程拜谒虎门要塞靖远炮台,那时候我还在广州军区空军服役,在距离炮台不远处的一棵木棉树旁,我不禁联想到林则徐在虎门销烟的壮举。走进灰色石头砌就的炮台廊道,看着百年风雨在石头墙上留下的沉重色斑,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1841年2月,英国侵略者在炸断拦江铁链,攻占横档等几座炮台之后,全力轰击关天培所在的靖远炮台。关天培率领将士,从中午顽强坚守到深夜,眼看炮台即将失守,他将提督大印和自己脱落的两颗牙齿让随从带走,与守卫炮台的四百多名将士,全部壮烈殉国在这座炮台上。
炮台石缝中的一丛阔叶草,把我的思绪从百年前拉回到现在的虎门,在阳光的照耀下,阔叶草呈现出水嫩的绿色,我想,它和它同类们的根须,百余年来,无忧无虑地成长在关天培等勇士用鲜血浇灌的沃土上,遇到和平年代,显得根深叶茂,郁郁葱葱。走出廊道,站在临江的炮台上,作为一个军人,我觉得关天培等将士的英灵就在我的身边,于是我想:如果再爆发战争,面对敌强我弱,我会不会像这些英灵一样,为身后的国家和民族血战到底!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我随即反问自己,为什么不会想到,在敌人还没有进入要塞之前,就将敌人击沉在海上呢?但我当时就摇头了。因为我身在空军,深知我军实力,虽然我军将士依然有关天培一样的血气,但是我们的装备,比起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比起后来入侵我国的八国联军,依然相差很远。所以真的打起来,在核武器不介入的情况下,我们还会面临1841年的局面。
想到这里,虽值盛夏,我心里却生出挥之不去的寒气。
今年冬天,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又一次造访东莞,而且专程到了虎门,这一次有解说员,有海战博物馆,我也看得很仔细,一些技术性问题也可以做一些深入的研究,自然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感悟最深的是弱国无尊严。想当年,清政府虽然以天朝自居,骨子里已经弱不经风,而长期掠夺国外资源和财富的英国政府,特别是东印度公司,非常清楚我们的家底,所以在根本不讲道德和情理的情况下,向中国走私鸦片,鸦片的输入量由道光即位之初的四千余箱,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十多年间,已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致使许多民众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行尸走肉,而东印度公司等外国列强却以蛇吞象一般的贪欲夺走了中国大量的白银,以致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林则徐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不禁,几十年后会国贫民弱,“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于是毅然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二万余箱,相当于二百多万斤鸦片。按说这完全是正义之举,但长期明目张胆地在全球范围内强取豪夺的英政府却派兵打上门来。1840年6月,由四十八艘舰船和四千余名官兵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发现在林则徐的部署下,虎门要塞坚固难攻,将士严阵以待,于是调头北上,攻陷了浙江定海,继而又猖獗进犯天津海口,将英国外交大臣的照会送交直隶总督琦善,胆颤心惊的琦善答应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圆给英国。这种卖国行为立即引起朝野震怒,清政府只好对英宣战,但这时,朝廷内的主和派已经削弱了虎门要塞的兵力,英军立即南下强攻虎门炮台,在一天之内攻占了虎门,然后沿珠江长驱直入进犯我国内地。同年夏秋,英军继续扩大战火,先后攻陷福建厦门,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并一度侵占上海,宝山,又闯入长江,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直抵江南重镇南京。在实力悬殊、根本无法对垒的情况下,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于英国,还要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元作为他们不辞辛苦进犯我国的补偿。尝到甜头的英政府步步紧逼,随后又胁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补充文件,《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唾手得到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和开设租界等特权。虚弱的中国,在英国坚船利炮的威胁下,只能忍气吞气。
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引起海外列强的巨大贪欲。葡萄牙竟然敢在澳门驱逐中国官吏,停付租金,傲慢地强占了澳门;紧接着,美国总统泰勒派全权大使率军舰到广州,已成惊弓之鸟的清政府急忙与他签订了《望厦条约》;法国也不示弱,匆匆将军舰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并未动手,道光皇帝就连忙着人跟他签了《黄埔条约》;正像柏杨所说:“一些中国曾经听说过,或从没有听说过的弹丸小国,在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排队而来。”清政府根本不敢应战,只有割地赔款、签订条约,《南京条约》中英国人的特权,被列强一概享有。中华大地,一片呜咽,顿时陷入半殖民地状态。
就在我写这一篇文章前的2009年12月29日,英国毒贩什肯·阿克毛于在新疆乌鲁木齐市被注射执行死刑。同一天,中国驻英大使傅莹被英国外交部传召。英国媒体形容,她与英国外交国务大臣伊万·刘易斯进行了一场长达40分钟的“非常费劲的对话”,刘易斯想知道为什么之前英国关于阿克毛事件向中国发出的27次部长级抗议,中国都不予理睬。会后,刘易斯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中国在处理阿克毛事件上“毫无怜悯之心”。我们当然不能有怜悯之心,我们对毒贩有切肤之痛。但是今天的英国,也仅仅能够表示抗议,他还敢明目张胆地侵犯中国吗,不敢了。原因其实很简单,今日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我们的强大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就说虎门,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影响下,美国等西方经济强国四面楚歌,风声鹤唳,而虎门仅在2009年上半年,GDP就达到114.47亿元,可支配财政收入达到6.29亿元,这仅仅是一个乡镇,而全国有41636个乡镇,他们在华夏大地异彩纷呈地崛起,成为中国经济的基础。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GDP排名及分析,中国的综合实力在2008年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时隔一年,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我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贸出口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虏纵有万般贪婪之心,也只好对中国垂涎三尺,望而生畏,在毒贩被处死时,也只能高号几声,摆一下自己日不落帝国的虚荣心罢了。
还有一个重要感悟就是,两军对垒,在冷兵器时代,靠智靠勇靠谋,但在脱离了冷兵器之后,打仗的重要因素就是科技了。
在1841年中英虎门之战中,武器的科技含量是完全不对等的。
先说两军大炮射程,根据关天培给朝廷的奏折,战争前夕,中国安装在虎门炮台的重型炮,最大射程在4华里之内,有效射程约为二三华里左右。而英军火炮的射程远远高于我们,1842年8月,钦差大臣伊里布的家人张喜等四次登上英国军舰,惊叹英军装备:“其船之头尾,安设两大炮,俱系自来机关,封口炮子式如雷槌,底有小口,口用绵封贴,内包小子,类百颗,名为飞弹。据云:‘可打九里,并可攻城。’”在海战博物馆,讲解员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打出的炮弹是实心,目的是想把敌舰打出个大窟窿,进水沉没,而敌方用的炮弹则是开花弹,落地爆炸,伤人成片。进一步比较,清军火炮装填程序复杂,费时多,射速慢,还要冷却,每小时平均只能发射8发,如果每一发不中,则第二发已因敌舰远去而鞭长莫及。战争之后,林则徐被朝廷谪戍伊犁,路过兰州时,还深深地陷入在海战的回忆里:“彼之大炮,远及10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以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若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这个技,不是技术,而是武器性能的各个方面。而决定这些性能的,是科技。
所以,我们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在科技上有长足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才能保证我们光彩照人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否则,我们又会重新落入“技不熟者”之列,挨打、壮烈、割地、赔款。
而如今,单说东莞虎门,科技发展之风已经浩荡而来。这里地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高科技发展的前沿阵地,仅在东莞市,高新技术企业就有上万家,今我们吃惊的是,仅在东莞松山湖一处,就有台湾高科技园、中小科技企业创业园、IT产品研发园、创意设计园、东莞创业园、松山湖虚拟大学园、松山湖国际企业创新园,甚至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就在我们访问东莞的时候,又有电子信息、生物技术、金融服务三大产业33个项目携100亿资金进入松山湖,香港商报如此评价:松山湖,中国力量浓缩的标本!
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飘飘然,因为我知道,在东莞,在珠江三角洲,大部分的企业是制造业,而且大量依赖出口,仅仅一个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就使很多企业面临破产,原因很简单,这些企业利用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到美元和人民币小小的浮动都承受不了!能承受得起的合资企业,核心技术大都被他人掌握,大的利润被他们拿走,我们只是安排了就业,增加了税收。当然,这些企业都是引进的,而且我们在逐步实现国产化,但是,令我们沮丧的是,国产化的大部分配件,连国人都信不过,在使用中,大不如原装进口。我们确实是有载人飞船,但是,我们自己制造不出大飞机,而大飞机是现代战争机动性的重要工具。我们的潜艇虽然落后于美国,但是毕竟有,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有数艘航空母舰,而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造。要不是我们在60年代就爆炸了原子弹,在上世纪发生的多少次政治危机中,列强都会像八国联军一样卷土重来。我所举的这些,都是拒列强于国门之外所必须克服的,但是,靠什么克服,只能靠人才。东莞市提出,要从东莞制造,跨越到东莞创造,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忧虑的是,创造不是靠口号,而是靠人才,而我们培养人才的大学在搞产业化,我们的许多教授在搞一些从国家拿资金的科研项目,这些教授被他的研究生们称为老板。但是这些项目,一半左右是纸上谈兵,在武汉某高校,我院一位作家的儿子在那里读工科,基本没有教授给他们讲课,一些他们弄不懂的问题,讲师也弄不懂,他们只好请教高年级学长。对国家教育失去信心而又怀有远大理想的同学们,在国内难以安排就业,继续深造又需要家里投入大笔学费,只好选择出国,他选择去美国读研究生,美国六所大学都以全额奖学金吸引他去,他义无反顾地去了。他们班的同学,几乎都去了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更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现了我们中国的软肋,纷纷放宽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我们的有希望的下一代大都在外国,不说半个世纪,就是十几年后,我们靠谁来发展?我们不但不会缩小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反而会因为人才匮乏而拉大和西方的距离。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事实。可能有人会说,现在的西方发达文明,秩序井然,讲究人权,不会无缘无故对我们动武。这就更不对了,伊拉克惹美英了吗?但是美英把伊拉克变成了人间地狱,几乎每周,都能听到那里的爆炸声和死亡的嚎叫。还有,在美国,真正的主人是印地安人,但是,印地安人被赶到山野去了,头上插着鸡毛乱哄哄地叫,谁为他们主持正义了?在西方,正义的含义永远是强者来注释的。当然,十几年后,我们不会沦落到印地安人的程度,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必然会与西方拉开距离。到那时候,如果再来拜谒虎门,我的心情会更沉重,我心里说不定还会生出寒气。当然,有人会说,我们有核武器,别人不敢动我们,差矣,我们驻南大使馆,不是被炸了吗?我们驻任何国家的大使馆,都是我国主权地,炸大使馆就是炸我国,我们能怎样呢?我们敢动核武器吗?不敢,因为核武器一旦动用,就是全人类的毁灭。
好在有虎门,好在有圆明园遗址,不断地给我们敲响警钟,让我们不再去粉饰太平,让我们常存警惕,枕戈待旦。
虎门,谢谢你!
郑彦英,男,现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出版长篇小说《拂尘》、《从呼吸到呻吟》等6部,作品集《太阳》、《在河之南》等12部。被搬上银幕的电影剧本《秦川情》等3部,被搬上荧屏的电视连续剧剧本《石瀑布》、《彭雪枫将军》等6部。散文集《风行水上》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30余部著作获全国社科人文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以上文学奖。系一级作家、河南省省管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