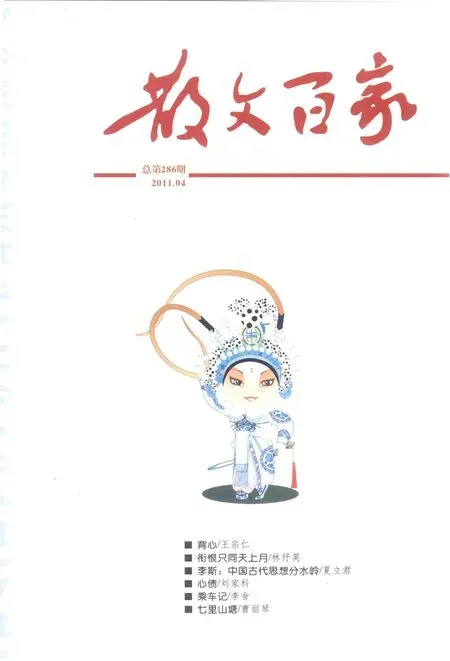文学艺术中的或然论
●余辔扶桑
文学艺术中的或然论
●余辔扶桑
一般读众只知道《红楼梦》的另一书名叫“石头记”,其实并不知道“红楼梦”还另有几个备用的名字,而且就红楼文本自己说——这部书的作者似乎也还有好几位哩。
红楼开篇不到十个字就出现“作者自云”的字样。不久,书中这样写到: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指那石头对其的述说),思忖半晌,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大旨不过谈情,亦只实录其事,绝无伤时淫秽之病,非假拟妄称,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闻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说来,难怪仅红楼作者是谁,人们就推敲了近一个世纪,至今余波未消。
原来,这红楼文本一开头就搞出这么多的“作者”来。仅这一小段文字就出现3位或抄录或题名或增删纂目之人以及4个书名来。而这些还不包括这书的原作——那块曾经(成精)历事的“石头”,和后来沿用下去的书名——“红楼梦”。然而我们再认真想一想,什么“空空道人……将这《石头记》再检阅一遍”;什么“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什么“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什么“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该书的真正作者曹雪芹先生真的就希望后世读众这样来理解这部书的这一段文字吗?我想,绝不是的。作家的良苦用心是潜隐在红楼文本情节之中的。而他这种手法的真正价值,远在文本文字之外。
作者编造故事、自圆其说,乃至谐音暗喻、模糊逻辑、偷换概念等手段,都是来干扰读众思维,使读众一翻开这书不知不觉就陷入一种思索的“陷阱”里——先追索起这书的作者到底是谁?这书的名字该用哪个?等等。这是什么?小说艺术——即“阅读陷阱”或叫“悬念”“谜团”之类。更重要的是,曹翁是要用这种具“或然论”的认识方法向观读者的智商发起挑战。因为他老人家深知被几千年皇道统文化禁锢而智障甚深的华族人的认识论的单一与顽固。不用“或然分析”的方法刺激,人们思想难脱旧套路。而这种有意启迪读者搞“或然判断”的意绪,将随小说的展开,作者再不断抛出其他“谜团”进一步启迪读者;以便由一种思维最终构成红楼艺术的——“或然论”这一概念。看,接下有“宝玉之谜”“可卿之谜”“香菱之谜”“金锁之谜”“麒麟之谜”“叔嫂疯魔之谜”“薛宝琴十首怀古诗之谜”等等。细数红楼文本当有数百个这样的“谜团”,且都是多解的,甚至是悖论的;都须读众作“或然分析”“或然判断”方能逐渐辨识了然。
而这“或然论”概念非但把红楼整部小说思想内涵加深,同时又能使读过这部小说的人的思维得以升华。
那文中几次提到的“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绝妙对联,就是启示“或然判断”的标识语。这是作者的创作方法论和暗示给读众的阅读方法论的最完美结合。
由此,我们也完全可称“红楼梦”是一部开启新认识思维的著作。
这有点像荷兰版画大师埃舍尔的那幅著名的版画《画画的双手》。那画面上——有两只手,一只左手一只右手,感觉是一个人的两只手;而这两只手各执一支画笔在画对方——那只右手正细心地描绘左手的衣袖,并且很快就可以画完了。可是在这同时,那只左手也正在执笔细心地描绘右手的衣袖,并也正好处在快要结束的部位,画面戛然而止。
这样,这幅画也就把一种“迷惑”抛给了我们:究竟是左手在画右手?还是右手在画左手?我们不管怎么看都无法辨别清楚?而且我们又该想到,这两只手无论哪一只都是画家埃舍尔画出来的。而这幅画,又跟埃舍尔的其他许多版画一样——既真实又荒谬、既有可能性又无此可能性;你说不清谁是起点?谁是终点?哪里是传统?哪里是继承?画家对于这些造成错觉又令人迷惑的空间,似乎又情有独钟,总是在二维空间里把三维的物体表现得既分割又对称,又循环连续,而冷静思考之又是那么的矛盾与悖理的。
——那么,诡谲的埃舍尔大师到底想要在这画中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我觉得,他跟伟大的曹雪芹一样,是要启迪人们作“或然思索、或然判断”的;从而提高我们的智性。因为这个世界极复杂,不确定性和未知性极大,悖论之理潜于社会各个角落,人们生活中逐渐丧失了统一判断价值,“偶然法则”被奉若至宝,甚至人都被碎片化——这就不允许我们再用单一思维、以表面条件来断定其好与坏、正确与不正确、光明与不光明的……尤其许多事物,从另一角度一看就截然相反。当然,这不说明一切都是无定论、一切都是虚无的。但我们思维方法必须多角度、多层面、具分析意义的。
——这,就是逻辑学中的或然判断。
这让我想起评论“当代爱因斯坦——霍金”的一句名言:让思想在宇宙最深处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