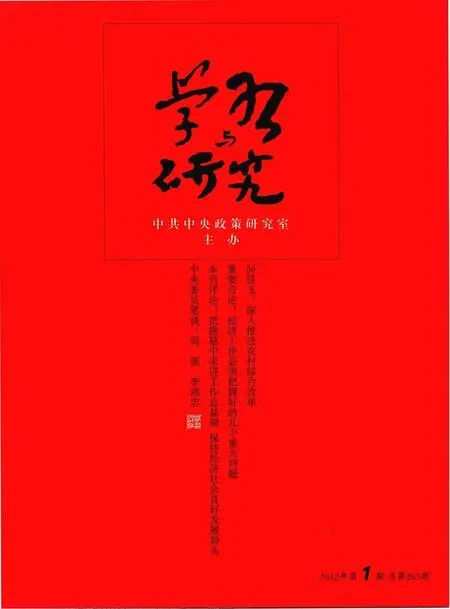吴锦堂与辛亥革命
徐文永
(丽水学院 华侨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吴锦堂(1855-1926),原名作镆,字锦堂,以字行,浙江慈溪人。早年居于乡里,以务农为生。1885年,吴锦堂经由上海东渡日本长崎,初以日本国内及中日间贸易为业。1887年,他与人合伙在大阪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商行“义生荣”,1889年,他在神户设立了“怡生号”商行,并以神户为定居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吴锦堂抓住机遇,业务范围也逐渐拓展至贸易、航运、实业、金融投资等各业。此时的吴锦堂已由一个初到日本的小商贾,逐渐成为阪神地区赫赫有名的殷商大户,成为日本关西财阀之一。作为被日本学者认为是旅日华商中唯一一位成功转型为日本财阀者,吴锦堂自然也成为日本关西地区华侨的翘楚人物。他积极参与侨社各项公益事业,在日本华侨各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1898年中国戊戌维新之后,日本成为革命派与维新派活动的重要据点。而此时已成为日本关西地区侨社领袖的吴锦堂,在日本和中国官民各界都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也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至于吴锦堂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支持与贡献,早为学界所公认。但对于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吴锦堂对待民主革命和革命党人的态度和行为,以往的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其主要原因笔者以为在于吴锦堂的身份、经历的复杂性以及相关史料的匮乏。吴锦堂在辛亥革命之前,主要生活地在日本,以坐拥文献之利、治学严谨的日本学者都承认研究的难度。笔者不揣浅陋,意就所接触到的有限资料,对此一问题作一简要梳理,以求教于大家。
一
吴锦堂侨居日本之后,亲眼所见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蒸蒸日上,日本上至国家,下至民间,“虽贩夫走卒,无不勤学读书”的情景,给吴锦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惨败更使他大受刺激。他“眷念祖国明智未开,非上下热心共谋公益,不足以振兴国势,开通风气。”认为创办学校“尤为强国富民之根本”,把教育看成是国家争生存、争富强的手段。吴锦堂一生贡献教育之力尤著,被后人称为与陈嘉庚齐名的“办学三贤”之一。戊戌维新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出走日本。1899年9月,经当时流亡神户的梁启超倡议,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开始筹建,吴锦堂“助之尤力”,是主要的参与者之一,并先后慷慨捐赠学校14000多元,“更且每年捐助常年经费”。1905年,吴锦堂又开始担任同文学校副理事长,亲自参与学校的管理,进而得以实践他的办学理念。同文学校自成立之日起,就受到各方的关注。首任校长是日本前文部大臣犬养毅,1906年学校入录清政府学部,光绪帝曾授“设教劝学”匾额以资褒奖。由此可见,神户华侨同文学校的创立,既有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的倡议,又有日本政界的背景,也有当时中国政府的扶持。但在百年之前风云激荡的岁月里,同文学校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大潮的冲击。学校早期的学生“大抵皆粤人子弟”,背景各异,其中应当不乏当时旅居日本的革命党人的子弟就读。从其百年校史那长长的毕业生名录中,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大公子梁思成和民主革命杰出领导人廖仲恺之子廖承志竟然同为校友,也可窥见该校包容并蓄的办学宗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神户华侨各界群情激奋,爱国青年踊跃报名回国参加革命。同年12月8日,由38名青年组成的神户义勇军在侨界欢送中毅然诀别亲友,登船返回祖国。与义勇军一同回国参加革命的同行者就有同文学校的教习伍雨生。作为当时神户主要华校的同文学校,其莘莘学子定然不会旁视而落于人后。
吴锦堂除在侨居国积极支持华侨教育事业外,还在家乡积极捐资办学,曾捐款给宁波教育会及宁波旅沪同乡会3000元用于办学,还直接资助以中国同盟会会员为主发起创办“合一郡之力,集一郡之才”的效实中学。而最负盛名者,莫过于在家乡慈溪创办“浙省私立各学堂之冠”的锦堂学校。锦堂学校于1905年开始筹建,1909年5月成立。锦堂学校创办初衷本为培养农业人才为主。但慈溪所处的浙东本就是革命团体光复会活动的重要地区。辛亥革命烈士马宗汉早年即在家乡慈溪任教,传播革命思想。因此,辛亥事起后,锦堂学校学生纷纷要求参军,学校因此而不得不暂时停办,由此可见锦堂学校事实上对当地开通风气,启迪民智之作用。
1893年1月,广东、福建、三江三个同乡帮联合组成了中华会馆(俗称“神阪中华会馆”)。会馆的创设可作为神户华侨社会成熟的一个标识,在神户华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创立之初的捐助者芳名录中,吴锦堂并不算引人注目。(据现存神户关帝庙的《谨将神户各捐金芳名开列》石碑记载,吴锦堂捐资300日元,在捐助名单中仅排在十几名开外。)这想必同他当时的经济实力有关。不过在时隔十年之后的1904年,在会馆申请注册为财团法人时,实力已今非昔比的吴锦堂作为三江帮的代表,与福建帮王敬祥、广东帮麦少彭分别认捐2万元作为基金,并获选为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并担任该职至1907年。(1914-1919年吴锦堂再度当选阪神中华会馆理事长,前后二届合计长达7年)神户华侨社会的许多重大活动,有许多是中华会馆组织或在中华会馆进行的,而吴锦堂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自然举足轻重。1911年11月,为了响应刚刚发生的武昌起义,中华民国侨商统一联合会在中华会馆成立,并在其后的4个月中,开展了大规模的声援辛亥革命的活动,包括组织义勇队回国,捐募款项支持革命等等。以吴锦堂在中华会馆的地位,即使吴锦堂未在侨商统一联合会中担任要职,但吴锦堂对待革命的的态度绝不会是消极的。
二
以上是吴锦堂通过创办新式学堂,主持中华会馆期间,以其地位和影响力对民主革命作出的间接贡献。吴锦堂“身虽在外,而对于祖国实未尝一刻相忘”的爱国爱乡情怀,被后人赞为“成大业而非为身家,振远图而藉扶祖国”。种种造福桑梓之感人事迹不胜繁举,无庸赘述。
对于吴锦堂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否有直接赞助革命党人的举动,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大部分学者认为吴锦堂在辛亥革命之前已经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工作,不但为同盟会募集经费,甚至还让出自己的私宅为同盟会作办公之用。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此一阶段吴锦堂的政治倾向缺乏记载,以他同保皇党人和清政府的密切关系,断无“积极参加同盟会活动,把他在神户私邸中的一部分借给同盟会办公,并带头捐资赞助”之事。
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一些华侨上层人物和大资本家等为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财产、人身安全,便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走着看等着瞧、走一步看一步、随机应变是他们共同的心境和普遍的心态。吴锦堂以殷商大户之家,是否也应归于此例,笔者认为还有待商榷,仅举一二例如下。
1905年10月,吴锦堂在离别故国多年以后,回乡省亲途经上海,受到了同乡,上海“宁波帮”的代表人物虞洽卿的热情接待。两人惺惺相惜,一见如故。吴锦堂对虞洽卿十分看重,在建造锦堂学校过程中,所有款项汇到中国后,都委托虞洽卿代为拨付。后来虞洽卿的堂妹采莲与吴锦堂之子启藩结秦晋之好,可见两家关系非同一般。1906年春,虞洽卿有机会与端方、载泽、戴鸿慈、李盛铎、尚其方等五大臣赴日本考察,在神户也受到了吴锦堂的热情接待。其后,吴虞二人在生意上也多次合作无间。而虞洽卿本人却是同情和支持革命党人的反清活动,与同盟会上海支部负责人陈其美过从甚密,多次出资相助陈其美的革命事业。辛亥革命后,又带头捐款解决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等。以吴锦堂同虞洽卿及“宁波帮”的关系,虞洽卿的政治倾向相信会影响到吴锦堂对待民主革命的态度。
吴锦堂与立宪派和清政府上层关系较为密切,多次受过朝廷典封及赐匾,确为如此。作为他当时的地位和保护其身家的考虑,本未可厚非,但他得到回报却远非其所望。作为一名商人,他在中国国内的投资却历经坎坷。1908年后,吴锦堂“近值朝廷恩准招抚华侨兴办祖国实业,凡有血气,孰不奋兴”,在致力家乡公益事业的同时,开始回国投资。吴锦堂在国内的投资不可谓不谨慎,合作对象也是相熟悉的有名望有背景的实业家,如盛宣怀、张謇、虞洽卿等,投资的企业多为当时的大公司大企业,且多为分散股权投资以规避风险。但即便如此,在晚清那动荡险恶的环境中,仍处处碰壁,“弟为祖国各公司股单所受损失甚巨,种种受人鱼肉,实可寒心”。对清廷和时局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此时,孙中山倡导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至富强的民生主义思想是否会让迷茫之中的吴锦堂产生一种新的憧憬和向往。其实,同时代的许多华侨巨商大贾的选择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由以上我们可否推断,吴锦堂在辛亥革命之前,已然有同情革命之思想并暗中出手相助革命党人的活动,是完全可能发生并实际存在的。
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吴锦堂此时的政治倾向已经明朗,他对新生的政权充满期待,“先后捐助上海军政府银一万六千两、银元贰千伍百元,捐助宁波军政分府银一万零六百两、银元二千五百元,捐给红十字会银元一千元,共计银元四万多元”。同时,他又出任浙江省军政府财政工商顾问,省谘议局参议员。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极度困难。临时政府不得已向日本求助借款,吴锦堂在其中发挥了牵线搭桥的作用,“与三井洋行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向日借款及汉冶萍相关事,多次与盛宣怀函商”。此事虽最终未成,但足以说明吴锦堂与临时政府的关系以及对辛亥革命的态度。
1913年1月,吴锦堂成为国民党神户支部长,此后一直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以致其晚年修身养老之地的移情阁今日成为神户孙中山纪念馆,足以证明其对孙中山及其民主革命的贡献。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