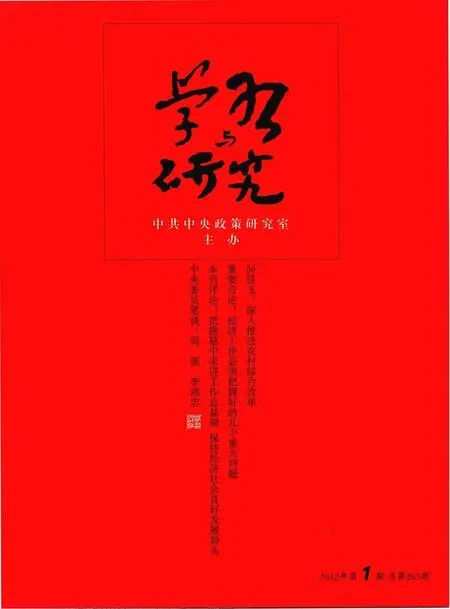辛亥前后的浙东士绅与兴学活动
蔡 彦
(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浙江 绍兴 312000)
浙东的宁绍地区一直就是文风鼎盛,人文荟萃之地,世代取得功名者多、为官者多,士绅阶层的势力较大。步入近代,浙东处在经济转型的前沿阵地,士绅阶层感觉更为灵敏,思想转变更为迅速。甲午战争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认识到,国家强盛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基础在教育,弃旧学求新学已在士绅阶层中蔚成风气。加上两地士绅长期受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忧国忧民的思想强烈,向来有捐资兴学的传统,所以在国家有难的关头,政府一经提倡,便开风气之先,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兴学热潮。
1.士绅阶层早期的兴学活动
鸦片战争后,在维新思想以及清末新政的推动下,浙东一批开明士绅和受西学影响的留洋知识分子相结合,率先以私产捐资办学,以新学为特征的近代教育诞生了。当时所办的学堂,根据不同的创办者分为三类:由官府出资兴办的称官立学堂;由私人创办的称私立学堂;由某村、某族集体创办,经费从庙产、公田、公祠等公共收入中支出的称公立学堂。公立和私立两类,统称为民立。这一时期在浙东境内出现的各类学堂,小学堂如辫志学堂﹑当阳初等小学堂,普通中学堂如绍郡中西学堂﹑东湖通艺学堂﹑越郡公学,专门学堂如大通师范学堂﹑明道女子师范学堂﹑绍兴法政学堂﹑汝湖初等农业学堂等多非官立,而系民立。据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浙江巡抚廖寿丰为遵旨开办求是书院兼课中西实学事奏折》:“(浙江)各府属经臣分札饬办(学堂),如宁波、绍兴、金华、湖州、台州、严州﹑温州、海宁等属或就书院加课,或设学堂专课,各视经费多寡议章开办,亦均未请动公帑”。这里所说的宁波学堂就是由宁籍旅沪绅商严信厚和地方士绅汤云崟、陈汉章等发起创办的“中西储才学堂”。“储才”二字寓有为国家储备人才之意。校址系借用月湖西面的崇教寺(今偃月街小学),经费依赖捐助。储才学堂开设的科目有译学、算学、经学、史学、词章、舆地。光绪三十年(1904),储才学堂改办为“宁波府中学堂”。
《廖寿丰折》中的绍兴学堂指的是绍兴士绅徐树兰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捐款倡设(的)绍郡中西学堂,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遵旨改设中学堂,因即归并办理。”《浙江绍郡中西学堂章程》载明了学堂宗旨:“吾越人文自昔称盛……我朝定鼎后姚熙之功在台湾,傅重庵泽流苗峝。盖时局变则学问不得不变。道咸以来习于故,……不求实用。而中外通商,蕃节书撤,时局又一变。今钦奉谕推广学校各省渐次举行,而吾越风气未开,土多守旧。今并为中西学堂遴选乡人子弟之颖异者而程课之以翼其成,亦独十年教训之意尔”。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回忆说:“光绪二十四年(1898)绍兴已经有一所中西学堂,是徐君诒孙的伯父仲凡先生所主持的,徐先生向知府筹得公款,办此学堂,自任督办(即今所谓校董),而别聘一人任总理(即今所谓校长),我回里后,被聘为该学堂总理”。据光绪二十五年(1899)蔡元培日记:“二月一日学堂开学,学生到者二十三人,附课生三人,算学师范生一人。”是年,学校更名为绍兴府学堂。据《光绪二十六年绍兴府学堂重订详细章程》:“学堂初立,于国文普通学外兼教英吉利,法兰西二语学,名曰中西学堂。今添课日本语学遂更名绍兴府学堂。学堂教授国文普通学外,其别五:曰经学﹑曰物理学﹑曰史学﹑曰词学﹑曰算学。学生兼学外国语言文字,其别三:曰日本﹑曰英吉利﹑曰法兰西。”
2.辛亥前后的浙东士绅与兴学活动
辛亥前后是浙东士绅兴学活动的高峰。据宣统三年《浙江教育官报》:“浙省教育经费不充,由官款拨给者尤居少数,其各属设立大小各校得以有增加者,每由绅民热心捐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宣年间浙江兴办新式学堂史料》汇编了当时宁绍地方官员对士绅兴办学堂的奏报:
(1)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七日《浙江巡抚任道镕为请奖捐资省城安定学堂、绍兴府通艺学堂官员事奏片》:……再,浙江省城改设学堂……。其外府县应设中小学堂,据报已经开办者计有三十余处,其余均饬次第设立。惟事当创始,筹款维艰,尚赖地方绅富集资捐办,以辅官力之不足。……又,三品衔花翎候选道陶濬宣,于绍兴府城设立通艺学堂,计修建学舍、置备器具及开办经费,捐洋一万八千元。……朱批:户部核给奖叙。
(2)《浙江巡抚聂缉槊为余姚县绅士捐资办诚意学堂请奖匾额事片》:……再,据藩司具详,据余姚县绅士江苏补用知府何恭寿等禀称,前在县治硬北乡建设义塾。继改诚意学堂,三年以来,规模渐备。现已筹得经费七千三百两,存本取息岁可得银五百余两。又,劝募上海同乡绅富认捐,常年经费岁约二千余元,统计出入可以相抵。……
臣查余姚县绅士江苏补用知府何恭寿等倡设诚意学堂,试办已著成效,虽非一人捐资,而集款数逾巨万,规模较大。……,俯赐准予立案,……
(3)《浙江巡抚聂缉椝为上虞县经正书院改设小学堂请奖捐资绅士事奏片》:……再,据办理浙江全省学务处藩、臬、运三司具详,据署上虞县知县何金魁详称,该县现拟将城东经正书院改设高等小学堂,惟是开办经费为目前紧要之款,估计约需洋二千元方可办理。商诸绅士,二品衔候选道陈渭(陈春澜)慷慨独认,如数捐助经费洋二千元,洵属急公好义。查例载地方士民捐银至千两以上,准予专案请奖。……
(4)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增韫为镇海县绅樊棻捐建便蒙小学堂请奖事奏折》:……邑绅花翎三品衔江苏候补知府樊棻,早岁读书,深明大义。迨投身商界,旋居沪渎,宾礼文士,常如不及,一时名公巨卿、海内知名士道经沪上者,辄闻声造访,缟带联欢。该绅究心教育,时以起发童蒙、培植后进为已任。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于邑城创设便蒙初等小学堂,章程皆其手定。逮奉诏兴学,樊绅益欢欣鼓舞,逐加推广。爰改办两等小学堂,额定百名,教授管理诸法悉遵钦定章程,益臻完善。自筑校舍,由族人而推及阖邑,悉与收录。计开办六年,捐助用款四千八百二十六元;购置校地建筑校舍五千元;置办器具、图籍二千四百二十八元;常年经费基本金二万二千元,总计用洋三万四千二百五十四元,均系独立担任。……该绅产仅中人,乃能挥斥巨资,注意教育,似此热诚办学,理应表章。
继徐树兰创办绍郡中西学堂之后,三品衔花翎候选道绍兴士绅陶濬宣于绍兴府城内设立通艺学堂,计修建学舍、置备器具及开办经费,捐洋一万八千元。陶濬宣(1846-1912),原名祖望,字文冲,号心云,别号东湖居士,又号稷山居士,会稽陶堰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后任广东广雅书院山长,在福建漳州开过煤矿,在会稽白米堰创办丝厂。学堂取名“通艺”是因为在他看来“国子是教,六艺是职,艺可从政,渊源圣门”,故名之。
显然,士绅们的兴学举动得到清政府充分肯定。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七日谕令:能独立创设学堂者于特赏。五月二十二日谕令:着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之学校。六月十一日又谕令:各省中小学堂应一律设立,以为培养人才之本。唯事属创始,首贵得人,着就各省在籍绅士中选择品学兼优能孚众望之人,派令管理各该学堂一切事物。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当年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措施有:七月十六日谕令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八月初二日再次颁布兴学诏书,提出兴学育才为当务之急。谕令将“各省书院一律改设学堂”。又规定“一切教规及学生卒业出途皆与官学一式”,确保新式学堂毕业生与科举士子一视同仁。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停止岁科考试,专办学堂”。据《绍兴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概览·校事纪略》: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邑人钱绳武、徐伟(字仲荪)等创议办学,修改蕺山书院旧宇为校舍,名曰山阴县学堂,由县署照会钱绳武为堂长,徐锡麟任总理。这是绍兴府城开办的第一家官立学堂,经费以书院原有款产之收息充之。堂长钱绳武,字荫乔,清末举人。民国后编有《龙山诗巢志略》﹑《陆放翁生日诗辑》。
实际上就清政府而言,对建立新式学堂一直很积极,但鉴于困拙的实力,其能做到的恐怕还只是提倡,给创设学堂者于特赏。尽管这样,学堂数量还是不足。清末新政期间颁行的有关兴学的法规都反复强调只有官绅合力,方能风气渐开。光绪三十年(1904)上虞经正书院改设高等小学堂,绅士陈渭(陈春澜)慷慨捐助经费洋二千元,经浙江巡抚聂缉椝奏报,以“旌表建坊,给予急公好义字”加以褒奖。此时已有明确的兴学请奖“定例”。受到褒奖的陈渭又捐资5万元,“在县北四十里横山之阳建造校舍一所,计上下楼房平屋共五十余间,用银一万三千元有奇,除置办图书器具外,约余银三万六千元,置产生息作为常年经费,定名春辉学堂,先办初小,以次递升(浙江学务公署编《浙江教育官报》宣统元年第12期,3页)”。稍后,为鼓励士绅捐款兴学,对捐助数额较大者除依例褒奖外,还可给予“给奖实官”的重奖。据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浙江巡抚增韫为镇海县绅樊棻捐建便蒙小学堂请奖事奏折》,由于镇海县邑绅樊棻捐建便蒙小学堂的“捐银数已及(定例)二十余倍”,学生“由族人而推及阖邑”,实非“寻常捐输可比”,故由浙江巡抚增韫奏请“免补本班,尽先补用”。
在清末兴学过程中,绍兴各地举办的学堂大多由地方绅士捐资创办。据光绪三十三年《浙江教育官报》的统计:旧绍兴府属五县共有小学堂145所,民立逾9成。至民国初年,绍兴民间捐资办学仍较为普遍。民国元年(1912)统计五县共有小学校446所,民国二年(1913)为685所,居全省第二位。光绪三十四年《浙江教育官报》显示宁波府有小学堂280所,中学堂5所,专门学堂6所。
3.部分士绅开始向“学绅”转变,成为“职业教育家”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迫使一大批士绅转向新式教育。据当时官方的报告,“各省初办学堂,学生率皆取诸原业科举之士”(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上册,197页)。在辛亥革命前后,不少有功名的士绅通过留学海外或国内的新式教育机构接受“再教育”,同时也有许多绅士成为新式学堂与学务机构的教职员。这些由“绅而为学者”,成为清末以新式教育或新的文化事业为职业的“学绅”。
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他二十六岁就中了进士,被授与翰林院编修。为了探索教育救国的道路,毅然放弃令无数科举学子钦羡不已的官职,南下故乡,担任绍郡中西学堂监督,甘当致力推动新式教育的“学绅”。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到上海,先后创办了中国教育会,爱国女校与爱国学社,成为上海最早的教育团体。蔡元培的日记中曾经回忆过多位辛亥前后“学绅”形象,其中包括自己的僚婿薛炳。他说:“薛炳,字闻仙,山阴县人。少时与我同受业于王子庄先生,那时君年十六岁,我十四岁。我元配王昭夫人,即君之姨妹,所以君与我为僚婿。君好书好客,我于书肆中见有好的书,无力购买,一告君,君就往购,与我共读,我很受君的益。君治经,守家法,治《毛诗传》,治《礼义疏》,详读数次,用红笔点勘,一句一字不放过”。薛炳先后任绍郡中西学堂,上虞春晖学堂教习,但骨子里对新式学堂的态度仍然摇摆不定。据蔡元培日记“(中西学堂中)反对我及马君的,实自君始。民国七年,我以北大校长兼任国史馆长,曾聘君任国史馆编纂,然不久君即辞去。”这样一位守旧老师,却博得了学生好感。30年后,胡愈之在《我的老师》一文中动情回忆起这位春晖学堂老师说:“薛老师教我读书,从没有半点老师架子。每次薛老师在面前,我觉得他是一个大孩儿。他时常要我学习把古代文译成平易通俗的今代文。”
当时,在蔡元培去职后任中西学堂总校的马传煦,东湖通艺学堂学监陶濬宣,储才学堂首任监督杨敏曾,慈湖中学堂堂长关维震都是堪深经术,好古力学的“学绅”。
4.“宁波帮”在兴学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宁波是近代首批对外开放的港口,商业发达。近代“宁波帮”在捐资兴学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以创办叶氏中兴学堂的叶澄衷和创办锦堂学校的吴作镆成绩最为突出。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五金大王”叶澄衷斥资三万两白银,在庄市叶家筹建忠孝堂义庄,附设叶氏义塾,供族姓子弟启蒙教育。他去世后,叶氏义塾由其族叔叶志铭遵嘱继续督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落成招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改名为叶氏中兴学堂,开始允许异姓子弟入学,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赵安中等许多享誉海外的宁波帮实业家都毕业于该校,因此被誉为“甬商摇篮”。光绪三十一年(1905)旅日华侨吴作镆在慈溪东条山购地50亩,创办锦堂学校。吴作镆,字锦堂,以字行,慈溪人。他31岁(光绪三十一年,1885)赴日本经商,成为日本举足轻重的大企业家。吴氏深谙日本发展与教育的关系,认为“近世列强竞争,教养二事,实为至要。国民失养,则无以为生,国民失教,则难以争存”。据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申报》中《请奖独立办学堂》:“(吴氏)先设两等小学堂……俟将来两等卒业再酌改为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而以小学堂附之”。宣统元年(1909)小学堂落成,宣统三年(1911)小学堂改办为农业中学堂。至民国九年(1920)锦堂学校由浙江省政府接收,改名为浙江省立慈溪锦堂师范学校,前后共历时25年。
对比宁绍两地士绅兴学活动,由于宁波很早就被列为通商口岸,部分士绅因商致富,他们往往更有财力来投入举办学堂的活动。据宣统三年(1911)《慈溪锦堂农业中学堂遵造册报呈请》中所记:“学校经费所出:海地租息、浙江铁路股息、汉冶萍煤铁厂股息;经常费数目:地租岁约银三千元、铁路股息银一千四百元、厂矿股息银四千元。临时费数目:随时应用由校主捐助无定数。”通计常年经费达八千四百元。而同时期绍兴府学堂的常年经费是三千七百元,不及其1∕2,为弥补经费来源,还不得不向钱庄借款,月息6厘,学堂一度出现了“办而中缀”景象(蔡元培《浙江筹办学堂节略》)。宁波绅商投入兴学的资金不仅数额大而且来源稳定,保证了学堂的正常运转,已经初步具备了现代教育某些特点。
5.最早的留学生群体
甲午海战后,大批青年学生不惜背井离乡,出国留学,特别是留日学习成为一种风尚。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国留日学生608人,浙江占84名,位居全国第三。而在这84名学生中,山阴、会稽两县就有14名,大致占全省六分之一。这其中,地方士绅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十六日《浙江巡抚聂缉椝为浙省考选一百名官费生赴日学习师范事奏折》中说:“浙省考选官费生一百名送往日本学习完全师范。札由学务处转饬各属保送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之精力强壮,不染一切嗜好、恶习,中学已有根柢各生,由各该府考取册报。兹经学务处司道调省,分场扃试,秉公取定,杭属十一名,嘉属九名,湖属九名,宁属九名,绍属十名,台属八名,金属十名,衢属六名,严属七名,温属八名,处属十二名,驻防二名,共计合格生一百名。”这些“派往日本各生”需由“地方官与士绅通饬遍举”,意“在将来各属皆有本地教习,各学教法均归一律起见,实为改革全省学务之根本。事属创办,关系甚大,所望各该生专心致志,兼程并进,庶可策效将来”。宁波﹑绍兴两地数量在全省排名第四。留日学生除学习日文外,还“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其中就有光复会的主将秋瑾,徐锡麟、陈伯平、孙德卿、王金发、范爱农等。以后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这些留日学生发挥了很大作用。
6.近代传媒业在浙东的发展
教育改革的推进,带来了近代传媒业的发展,并与社会改革相呼应。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十五,《绍兴白话报》创办,其宗旨为“唤起民众爱国,开通地方风气”,“致力于为宣传革命而推广白话文”。该报每期仅四五千字,但内容丰富,文字通俗,辟有论说、大事记、五千年人物谈、小说、绍兴近事等专栏(王文科《浙江新闻史》,47)。办报人为陈公侠﹑王子余﹑蔡同卿。光绪二十九年(1903)12月19日《中国白话报》一篇报道称它是“老牌子”。据《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文统计1876-1903年间全国有白话报15份,《绍兴白话报》就是其中之一。辛亥前后,绍兴府城有《绍兴白话报》、《绍兴公报》﹑《越铎日报》﹑《越州公报》等报纸,这些报纸的创办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打下了了舆论基础。从举办者来看,它们都是由商界名人资助的,文人执笔。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绍兴的商人当属于觉悟较早的新经济成分。商人办报反映了他们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寻求社会变革的愿望在上升。
比《绍兴白话报》创办稍后,光绪二十九年(1903)宁波人钟显鬯、虞士勋、陈屺怀(字训正)等在上海福州路惠福里发起创办《宁波白话报》,以“开通宁波之民智,联合同乡之感情”(庄禹梅《关于宁波旅沪同乡会》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第三十四辑)。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创刊。《宁波白话报》的内容“虽然近乎改良主张,可是文字运用明白浅显的白话对于旧礼教,旧习惯,且肯用力抨击,仔细想来,不仅在宁波文化中,是报界先进,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难能可贵的一页”。(《宁波人周刊创刊号》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十日,18页)
辛亥前后,士绅阶层的兴学活动深刻反映了近代社会的变迁,体现了一部分士大夫顺应时势,向近代知识阶层的转变。这股兴学热潮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达到高潮。士绅阶层在新式教育的背景下“兴民权﹑开民智”培养人才,推动了民众觉醒和辛亥革命爆发。
[1]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绍兴县志资料[M].民国二十八年.
[2]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宁波市志[M].中华书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