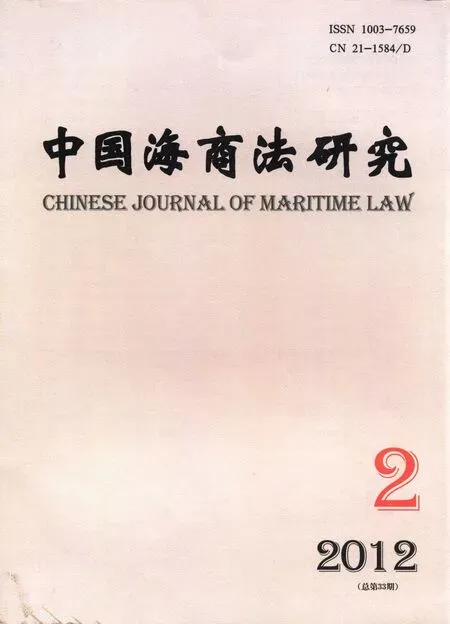船舶油污损害公约在中国的适用问题研究*
叶洋恋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上海 200042)
一、问题的提出
日益脆弱的海洋环境促使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对海洋所担负的义务,从20世纪50年代起,许多以保护海洋环境为宗旨的国际公约陆续被制定出来。致使海洋遭受污染的原因很多,海底矿产资源的开采、石油及天然气的开发、海洋生物的过度捕捞以及核污染等等。在这些因素中,最早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是油污问题。1954年,彼时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的前身)尚未成立,第一次国际防止海洋油污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通过了《防止海洋油污国际公约》(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for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of the Sea by Oil,1954)。从这个公约开始,关于油污损害方面的公约被不断地讨论和通过。至今,这些公约已经形成了一个防止船舶油污损害的国际法律体系。[1]388-412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贸的发展和航运业的腾飞,中国也加入了一系列涉及油污损害的国际公约。公约要产生效力,就必然涉及其在内国的适用。在中国,这些公约的适用一方面促进了国内油污损害的立法进程,另一方面也给实践中应当如何适用公约提出了一些问题。
截至2012年3月,中国已经加入的涉及船舶油污损害方面的公约有:《1969年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及其1973年议定书(自1990年5月24日起对中国生效,1997年7月1日对香港特区生效)、《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及其议定书(1996年3月3日生效,中国是缔约国)、《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响应和合作公约》(1998年6月30日对中国生效)、《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简称1969 CLC,1980年4月29日起对中国生效)、《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92年议定书(简称1992 CLC,2000年1月5日对中国生效)、《1971年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国际公约》1992年议定书(仅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生效)、《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2009年3月9日起对中国生效)。
从性质上看,这些公约可以明显地归为两类。一类以加强船舶管理和防止油污事故发生为目的,另一类则以污染事故发生后的弥补和赔偿为目的。
对于第一类公约中规定的事项,中国国内有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第71条规定了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对船舶污染事故的干预权,这种干预包括公海上发生的海难事故。这是对《1969年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的呼应。同样,《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章“防治船舶及有关作业活动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损害”中的相关规定则是对《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及其议定书精神的贯彻。国务院颁布的《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一方面对《海洋环境保护法》及《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及其议定书进行了细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响应和合作公约》中的应急事故及时处理原则。可是,在公约和国内法的适用规则问题上,究竟应当如何界定并不明确。
对于第二类公约中规定的事项,中国虽然加入了1992 CLC和《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但国内还没有关于船舶污染损害赔偿的专门立法,涉及这方面的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之中,并且多为抽象的原则性规定和程序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1]416
类似情形使得在中国适用有关船舶油污损害方面的公约可能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是在公约和国内法均有规定的情况下,适用的规则和顺序应当如何界定;其二是在仅有公约规定而无国内法规定的情况下,公约是否能够在国内直接适用,如果能,其效力范围又如何。这既涉及到公约在中国的法律地位问题,又反映了公约在中国的接受方式和实施情况。目前国内法对上述两个问题并无明确规定,有鉴于船舶油污损害的危害性以及产业和环境平衡的重要性,笔者将从国际法理论出发,考察船舶油污损害公约在中国的适用。
二、国际法理论上的一般原理
关于国际条约在中国国内的法律地位问题,宪法并没有原则上的规定。条约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需要从学理上对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分析。
(一)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
国际法理论中,关于条约在国内法的地位,存在许多观点。总的说来,从理论上探讨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关系的学者主要来自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和法国,而英美等普通法国家一般说来不重视理论问题,而偏重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的实际解决方法以及各国在这方面的实践。[2]
中国国际法学者李浩培先生认为,各国的现行制度可以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国内法优于条约;二是国内法与条约的地位平等;三是条约优于国内法;四是条约优于宪法。[3]323-331这种分类方式更多地体现为对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问题的延伸思考。而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问题,又涉及到二元论和一元论的理论划分。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一般将一元论分类为国内法优先说和国际法优先说,[4]而二元论似乎是现代国际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劳特派特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就是这种观点的忠实拥护者。虽然二元论还有不完善之处,但总的说来,它关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重大区别的观点是比较接近客观现实的。正因如此,许多从事司法实践的法官,特别是国际法院法官基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在法律渊源和适用范围方面的区别,也支持二元论的观点。[5]
周鲠生先生的划分方式有所不同,他将各国的实践归纳为了三种形式:一种是把条约认作法律在国内当然执行,美国是采用这种形式的代表,在美国条约的效力要受到后来的与条约相抵触的法律的影响。另一种则是英国模式,在英国条约如果没有预先由国会通过法案,或至少从国会获得必然通过的保证,国王是不能够批准的。第三种为介乎于英、美两种方式之间的德、法等国采用的方式,可以总称为欧洲大陆的方式。[6]
所以,越来越多的法学家希望避免一元论和二元论的对立,认为两个论点都与国际和国内机关和法院运行的方式相冲突。或许正因如此,周鲠生先生并未将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简单地归于一元学说或是二元学说,而是提出“自然调整说”。[7]周先生认为,从法律和政策的一致性的观点来说,只要国家自己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总是可以自然调整的。
(二)条约的国内法效力
调和国际法和国内法相互间的关系确是国际法在内国得以有效施行的重要原因。因此,作为国际法体系的组成部分,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也需要调和其与中国法律规定之间的关系——承认条约的国内法效力。
日本学者曾经说过:所谓国内法中关于承认条约的国内效力的规定,具有创设的效果。也就是说,有了这种规定,条约才具有国内效力。换句话说,这种规定具有把条约全面地“纳入”国内法中,使之“国内法化”的效果。正因为没有使条约因其本身所固有的效力而理所当然地具有国内效力,才使承认条约的国内效力与否,和在什么程度上承认条约的国内效力,成了各国的自由。[8]
李浩培先生认为,一个在国际上已经生效的条约,其规定在各国国内得到执行是以得到各国国内法的接受为前提条件的。接受条约规定的各国国内法,可以是宪法、议会制定法或者判例法。接受本身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将条约规定转变为国内法;二是无需转变而将条约纳入国内法。前者以英、意为代表。后者以美国为代表。[3]314-318
条约是否是国内法,各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而是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宪法。有的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条约是国内法律,《美国宪法》第2条第2节即规定,“在美国的权力下缔结的一切条约,与美国宪法和根据该宪法制定的法律一样,都是美国最高的法律。”但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却并没有明确规定条约是国内的法律,而只是规定条约可以经过一定的程序或在一定的条件下获得国内法的效力或具有国内法的权威。《法国宪法》第55条规定,“经过合法批准或核准的条约或协定,在公布后,具有法律的权威”。《德国基本法》第59条也规定,所有规定联邦共和国政治关系或涉及联邦立法事项的条约,必须要经过联邦法律加以规定才能取得在德国法律上的效力。此外,意大利宪法、韩国宪法等也都采取这种模式。宪法规定条约具有国内法律的效力或权威,并不等于条约就是国内的法律,二者必须区分开来。如果宪法规定条约就是国内的法律,那么条约从生效之日起,本身就具有了国内法的效力;如果条约必须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或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国内法的效力,问题则要复杂的多,因为其涉及到条约获得法律效力的方式,即是通过采纳的方式获得法律效力,还是通过转化的方式获得法律效力。[9]
中国宪法并没有就此作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简称《立法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简称《缔结条约程序法》)中也没有明确规定条约的缔结是否具有立法性质问题。根据中国法律精神,早期学者间持“纳入”观点的分析较多,近年来混合论的观点成为了一种趋势,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对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问题,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有学者就认为,依照中国现有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国适用条约的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在国内法中直接适用国际条约;二是将有关条约的内容制定成国内法予以实施;三是只允许间接适用国际条约。虽然中国适用条约的方式有三种,但居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直接适用。[10]
按照传统观点,对于船舶油污损害公约来说,如果是前述第一类性质的公约,即船舶油污损害公约中以加强船舶管理和防止油污事故发生为目的的公约,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但大体上仍然是纳入模式;如果是前述第二类性质的公约,即以污染事故发生后的弥补和赔偿为目的的公约,则显然应当直接适用。也就是说,目前在中国,“纳入”(又称“并入”)仍然是船舶油污损害条约获得法律效力的基本方式。
三、船舶油污损害公约在中国的法律效力问题
(一)依上位法高于下位法方式决定船舶油污损害公约效力
由于中国目前并没有关于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关系的一般规定,唯一具体针对条约的法律规范就是《缔结条约程序法》。《缔结条约程序法》中的相关规定将中国加入的条约分为了三类: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条约或重要协定;国务院核准的协定或具有条约性质的文件;无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批准或核准的协定。
按照此种分类,中国截至目前加入的有关船舶油污损害的公约,性质上都属于国务院核准的协定或条约性质的文件——根据国函[1990]6号“国务院关于加入《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及《1973年干预公海非油类物质污染议定书》的批复”,《1969年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由国务院决定加入,在1990年3月12日至16日召开的 IMO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M EPC)第29届会议上,中国代表通知委员会中国正式加入该公约;根据原交通部2006年42号文件“关于我国加入经修正的《经1978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I V的公告”,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于2006年11月2日向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交存了加入经修正的《经1978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I V的文件,除此以外,《经1978年议定书修订的〈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本身以及其他几个附件也均由中国政府批准;根据原交通部1998年327号文件“关于我国加入《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映和合作公约》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于1998年3月30日向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交存了关于加入《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的文件;根据原交通部1999年425号文件“关于《〈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92的议定书》对我国生效的通知”,该公约的批准机关也是国务院;根据原交通部2009年第1号文件“关于国际海事组织《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生效的公告”,经国务院批准后,中国向国际海事组织递交了有关加入该公约的加入书。
《缔结条约程序法》并未就三类条约的效力进行明确规定。但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其他组织立法职权上的高低等级。国务院核准的协定或条约性质的文件效力似乎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条约或重要协定,高于无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批准或核准的协定。也就是说,当全国人大批准的条约与这些公约就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条约优先适用;当政府部门或其他组织协议缔结的条约与这些公约就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的,这些条约优先适用。就前一种情况而言,由于船舶油污损害公约性质特殊,针对的也是特定事项,所以实践中出现冲突的情形可能不多。就后一种情况而言,冲突出现时,前文所列举的船舶油污损害公约应当优先适用。归纳起来,船舶油污损害公约之间效力等级一致,并且与上下等级效力公约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但如果依照这种标准,条约与中国国内法之间的效力问题会很复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宪法》)、《缔结条约程序法》以及《立法法》的精神,前述条约的划分方式同《立法法》对中国法律法规的分类方式是相同的。那么对比适用,其效力或许依次相当于中国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于是,有观点认为当国际条约与国内法规定相冲突的时候,要明确其效力等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具有同等效力,适用上出现意见分歧时,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法律与条约和重要协定的优先适用问题。
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其效力高于国务院核准的条约与协定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并高于政府部门对外缔结的协定及其所制定的规章。
第三,当国内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够明确时,可以直接适用条约和重要协定的内容。
第四,国务院核准的条约与协定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具有同等效力,并高于政府部门对外缔结的协定及其所制定的规章;
第五,法律明确规定某条约优先适用的,该条约得以优先适用。但是条约的效力始终低于《宪法》。[11]
(二)国内法相互之间的不同规定导致船舶油污损害公约效力悖论现象
依上文所述,似乎立法能够给船舶油污损害公约与中国的法律法规之间的效力等级确定一个顺位标准。但在中国的一些现行法律中,却作出了与上述标准不同的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第14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该国际条约。并且,这些法律的通过机构是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民法通则》和《海商法》这两部法律为例,前者的颁布机构为全国人大,后者的颁布机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那么,如果依据前述标准,船舶油污损害公约与这两部法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一种悖论。
就《民法通则》而言,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条约之间应当是什么关系并不明确。如果推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条约和重要协定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话,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条约之间效力的比较就如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之间的效力比较。事实上,《立法法》并未明确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之间是何种关系。
有观点认为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两个不同的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非基本法在效力上是不同的。如果依照这种观点,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条约效力就应当低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民法通则》中的规定就应当优先适用,即国际条约的效力是高于国内法律的。这便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条约效力低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这一前提相矛盾。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一个常设机构,只是在全国人大闭会时行使全国人大的职权,所以事实上二者是一个机构。同一等级的法律应当适用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但就船舶油污损害公约与《民法通则》而言,船舶油污损害公约规范的是特定领域内的事项,与《民法通则》就同一事项进行规范的可能性很小。条约等级比照法律的话,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的,后批准的条约效力高于先通过的基本法,后修订的基本法效力高于先批准的条约。这样一来,又与《民法通则》中条约优先适用的规定相矛盾。
(三)船舶油污损害公约在中国的实际地位
综合前文所述,单纯地按照制定机关的等级来确立条约在中国的地位,或者单纯地认定条约在中国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都无法较为准确地概括现阶段船舶油污损害公约在中国的实际地位。这一方面与中国现阶段的国情有一定的关系,高速发展的经济使得法律难以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也与世界范围内条约在各国国内适用的发展趋势有关,随着国际组织的发展,国际条约的数量和种类呈现飞速发展的态势,各国在实践过程中也通常都采用复合方式来调整条约和国内法的关系,很少单一地采优先说。因此,虽然目前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并没有对条约在中国的地位给出一个明确的原则,但在解释和适用条约时,还是应当朝着融合条约和国内法的方向去走。
鉴于目前已有许多法律明确了条约的优先适用效力,从解释一致的原则上讲,在一般情况下还是应当确认条约的优先效力。而就不同机构批准的条约之间以及条约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还是认为同一等级条约与法律中条约应当优先适用,条约与条约之间平行,有冲突的由该等级机构进行解释。不同等级之间的条约与法律按等级区分效力。
基于这样的考量,就船舶油污损害公约与国内相关法律规定间的关系而言,目前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民法通则》规定了条约的优先适用效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海商法》也规定了条约的优先适用效力。而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缔结条约程序法》在位阶上低于《民法通则》,制定时间上又早于《海商法》,并且《海商法》是特殊法,在海商海事领域应当优于普通法适用。那么,《民法通则》和《海商法》所确立的条约优先原则应当适用于船舶油污损害公约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此种优先受到法律位阶等级的限制,即船舶油污损害公约优先于国务院条例及下位法适用,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批准的条约则优于船舶油污损害公约。由于船舶油污损害公约属于海商海事领域内的专门公约,一般而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批准的条约多为涉及国家与国际间的基本法律事项,国内针对船舶油污损害的法律规定除《海商法》的一般规定外均为条例和部门规章,因此与中国国内法相比较,船舶油污损害公约在涉及船舶油污损害的案件中具有优先适用效力。
四、船舶油污损害公约在中国的适用效力边界
倘若接受船舶油污损害公约在中国应当具有优先适用效力这一结论,那么接下来要解答的问题是:船舶油污损害公约在中国有无适用边界?如果有,如何界定?
(一)关于无涉外因素船舶油污损害案件能否适用公约的争论
在中国的实践中,对于船舶油污损害公约的适用范围曾经出现过争论。这种争论主要集中于沿海运输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是否应当适用1969 CLC及1992 CLC。1999年“珠海市环境保护局和广东省海洋与水产厅诉台州东海海运有限公司和中国船舶燃料供应福建有限公司”一案发生后,对于进行沿海运输的中国籍船舶应不应当适用1969 CLC及1992 CLC,存在不同的观点。
该案中,沿海运输船舶的船东在发生油污损害事故以后,根据1969 CLC申请责任限制。因中国目前并没有关于油污损害赔偿的专门立法,法院认为应当适用中国批准的上述公约。但沿海运输船舶的案件当事方往往均是中国籍,案发地点也位于中国领海内,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应当被认定为是无涉外因素的船舶油污案件。无涉外因素的案件是否能够适用国际条约?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有人主张因《海商法》没有油污损害赔偿的规定,应根据《民法通则》确定赔偿数额,且没有责任限制;有人主张适用《海洋环境保护法》;有人主张油污损害也是一种海事赔偿,因此对于被告的责任限制应该适用《海商法》第十一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也有人主张中国是1969 CLC的参加国,该公约于1982年4月29日起对中国生效,在国内立法没有对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作专门规定的情况下,应该允许适用1969 CLC的规定。两原告对申请人责任限制的申请提出异议,认为“闽燃供2”号轮(钢质油船,总吨位497,净吨位325)不属于公约调整的船舶。本次油污事故没有涉外因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简称《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该案只能适用中国的有关法律。[12]71产生如此争议的原因可概况为以下几点。
首先,适用1969 CLC存在阻碍:其一,《民法通则》以及《海商法》关于公约优先适用的规定书写于“涉外法律关系适用”篇章中;[12]73其二,对于中国加入的1969 CLC,原交通部1980年3月1日下发的《关于中国已接受〈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通知》中没有提及对沿海运输船舶适用,《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第13条也仅仅规定,“航行国际航线,载运2 000吨以上的散装货油的船舶,除执行本条例规定外,并适用于我国参加的1969 CLC”。所以,有学者认为,未作特殊规定的载运2 000吨以下散装货油并航行于国际航线的船舶,以及从事沿海运输的油船不适用1969 CLC,仍然适用国内法。然而,1992 CLC对中国生效后,《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第13条的规定是否仍然有效,具体地说,载运2 000吨以下散装货油并航行于国际航线的国内船舶是否适用1992 CLC,是不明确的。[13]
其次,如果不适用公约,国内法并没有相对应的规定,出现2 000吨以下沿海运输油船油污损害的情况时,会产生无法可依的法律真空。而对于2 000吨以上的沿海运输油船,适用民法体系的赔偿原则会与整个海商法体系中的责任限制原则产生冲突,显然也不适宜。
最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于规定不明确的这类国内船舶而言,随着1992 CLC对中国生效,1969 CLC便随之失效。如果这类船舶适用1992 CLC,其巨大的限额对于中国沿海运输船舶而言是过高的。因此,学者建议应当明确无涉外因素的国内案件如何适用对中国已生效的国际公约,并且考虑中国国情,无涉外因素的国内关系一时难以或部分难以接轨的,应在批准参加公约前作好准备,在批准参加公约的同时,作出该公约对国内适用程度的规定。[14]
事实上,由于中国在公约的适用问题上缺乏明确规定,造成了法律与条约间适用的不确定。实践中,对于海事公约,一般采用“打补丁”的方式来解决:交通运输部发文或国务院发文规定条约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方式。即便如此,在一些无需区分国内与涉外适用的情形下,上述发文与条约及国内法适用范围的具体表述无关。因此,在出现条约与国内法冲突(无论是积极冲突或消极冲突)的情况时,实践中需要对相关的具有法律属性的文件进行解释。
(二)法律状况变化后争论的再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实践部门和学界的解释观点是基于当时的法律展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法律状况出现了变化。2009年9月2日国务院第79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该条例于2010年3月1日起施行。伴随着《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施行,1983年发布的《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已废止。相较于旧条例而言,新条例确定了三项制度:船舶污染事故赔偿责任限制、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以及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52条规定,“船舶载运的散装持久性油类物质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污染的,赔偿限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执行。”有关国际条约事实上即是1992 CLC。条例的此项规定,从立法上明确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限额适用1992 CLC的标准,解决了长期以来就限额标准而产生的争议。
除此以外,《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53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内航行的船舶,其所有人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投保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相应的财务担保。但是,1 000总吨以下载运非油类物质的船舶除外。船舶所有人投保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或者取得的财务担保的额度应当不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油污赔偿限额。”与1992 CLC相比较,新条例将强制保险的投保范围拓展至所有油轮。
条例还进一步确定了海事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落实《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交通运输部制定的《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对相关问题进行细化规定,该办法目前尚未施行,但施行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已经进入日程。
从整体上讲,《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对油污损害赔偿限额作出了适用条约的规定,并且明确适用1992 CLC。但在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强制保险或者取得其他财务担保的船舶范围方面,相比较1992 CLC规定的要求载运2 000吨以上作为货物的散装持久性油类的船舶进行强制保险或取得其他财务保证,条例将强制保险的投保船舶范围大大增加了。根据条例,所有油轮,不论其载运持久性油类或者非持久性油类,均应当进行强制保险或者取得其他财务保证。[15]不过,在投保额度方面,载运持久性油类适用的仍是1992 CLC,载运除此以外的油类物质和1 000吨以上非油类物质的船舶则比照国内法规定适用。
如此说来,《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及其配套办法在油污损害赔偿的额度、投保金额和基金方面明确了条约在其管辖范围内适用于在中国管辖海域内的船舶油污损害,而在条约规范之外的领域则适用中国国内法。但1992 CLC的规定并不只限于上述事项,还包括了适用范围、责任主体、民事赔偿责任和免责事项、时效、管辖及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这些事项有的与国内法规定不尽相同,有的国内法律尚无专门规定。所以《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鉴于其本身规制范围的限制,只是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对于相关油污损害民事赔偿条约与国内法的其他冲突问题,争议依然存在。《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贡献在于其给出了一个中国适用油污损害民事赔偿条约甚至是适用所有船舶油污损害公约的解释路径,即条约管辖范围内国内法与条约有冲突时应当适用条约。
(三)船舶油污损害公约在中国的适用范围
就近年来所产生的争论和相关部门的新近立法来看,在船舶油污损害公约的适用边界问题上,中国目前尚缺乏明文法律规范。如果要给船舶油污损害公约划定一个标准和范围的话,上位法确立了一个大的原则:条约优先。在这个原则之下,船舶油污损害公约管辖范围内的事项则应当适用公约规定。但《民法通则》和《海商法》均将条约优先适用规定于“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一章,那么船舶油污损害公约的规范范围就被界定为涉外法律关系。如此一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无涉外因素的船舶油污损害发生时,应当适用条约还是国内法?
面临的问题是,“打补丁”解决船舶油污损害公约与国内法的冲突是目前行之有效并且能够实际解决问题的方式。当“补丁”明确规定依照条约解决相关问题时,条约当然适用于该无涉外因素的船舶油污损害。因此,事实上对于无涉外因素的船舶油污损害,依据仍然是国内法。即使最终适用条约规定,也还是要经过国内法的转换。但“补丁”的弊端在于其有限性,目前中国针对船舶油污损害的国内法规范尚不完善,公约有规定而国内法无规定时能否参照适用公约的问题还是没能得到根本解决。这个问题集中体现在规定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机制,即前文所述的第二类公约之中。中国国内立法在船舶油污损害领域有一个偏向,公法性质法规较为完善而私法性质法规规定不足。现阶段仍然缺少有关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的专门规定。《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及其配套办法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仍然不完整。司法案例(前述争议案件)中法院倾向于在无涉外因素的国内法无规定时适用条约。而立法倾向则表明如果国内法有高于条约要求的规定时适用国内法,国内法无规定时根据一般原则条约法适用。
因此,中国目前在无涉外因素船舶油污损害的条约适用方面所存在的困境在于,中国加入公约之时并未作任何保留,而对于非涉外因素的包含在公约管辖范围之内的船舶油污损害国内法规定又未得以覆盖。面对无涉外因素船舶油污损害的法律真空,可能的解决办法有两种:一是逐步完善的船舶油污损害国内立法,特别是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立法;二是明确国内法律无规定时适用公约。相较之下,第一种办法在现阶段更为现实可行,对于产业发展而言也更为有利。
五、结语
国际法理论表明,条约在内国法上具有效力。条约在内国法上的效力及其等级是由一国国内法进行规定的。
船舶油污损害公约在中国面临着适用位阶和边界不明确的问题。《缔结条约程序法》《民法通则》和《海商法》对条约的效力作出不同划分,单一采用任何一个划分方式都无法解释条约在中国的实际地位。因此,基于条约优先、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规定,船舶油污损害公约与船舶油污法律法规相比,应当优先适用。
但这种讨论的前提是涉外情形下的条约适用,在非涉外情形下,立法倾向表明国内法应当予以适用。当国内法未就相同事项进行规定时,不可径自参照条约适用,而有待国内法的确认。
[1]胡正良,韩立新.海事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HU Zheng-liang,HAN L i-xin.A dm iralty law[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9.(in Chinese)
[2]王铁崖.国际法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77.
WANG Tie-ya.International law introduction[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98:177.(in Chinese)
[3]李浩培.条约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LI Hao-pei.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treaties[M].Beijing:L aw Press,2003.(in Chinese)
[4]劳特派特.奥本海国际法(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4-32.
LAUTERPACHT.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Vol.I)[M].Beijing:Commercial Press,1981:24-32.(in Chinese)
[5]余先予.国际法律大辞典[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9.
YU Xian-yu.International law dictionary[M].Changsha:Hunan Press,1992:9.(in Chinese)
[6]周鲠生.国际法(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654.
ZHOU Geng-sheng.International law(Vol.II)[M].Beijing:Commercial Press,1976:654.(in Chinese)
[7]周鲠生.国际法(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0.
ZHOU Geng-sheng.International law(Vol.I)[M].Beijing:Commercial Press,1976:20.(in Chinese)
[8]日本国际法学会.国际法辞典[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393.
Jap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 aw.International law dictionary[M].Beijing:World Know ledge Press,1985:393.(in Chinese)
[9]刘永伟.国际条约在中国适用新论[J].法学家,2007(2):143.
LIU Yong-wei.New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pplicable in China[J].Jurist,2007(2):143.(in Chinese)
[10]王丽玉.国际条约在中国国内法中的适用[M]//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法年刊(1993).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282-285.
WANG Li-yu.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in domestic law of China[M]//Chinese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Chines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1993).Beijing: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94:282-285.(in Chinese)
[11]宋洋.国际条约在中国内地与港澳适用的比较[J].检察理论前沿,2008(8):39.
SON G Yang.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pplicable to Hong Kong,Macao and mainland of China[J].Prosecution Theory Forefront,2008(8):39.(in Chinese)
[12]韩立新.从一起海事案例谈国际海事公约的适用[J].当代法学,2001(12).
HAN Li-xin.With a case to talk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nvention[J].Contemporary Law,2001(12).(in Chinese)
[13]司玉琢.沿海运输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法律适用问题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2-3.
SI Yu-zhuo.Application of the law on coastal transport vessels for oil pollution damage compensation[J].Journal of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02(1):2-3.(in Chinese)
[14]司玉琢,朱曾杰.有关海事国际公约与国内法关系的立法建议[J].中国海商法年刊,1999(1):5-6.
SI Yu-zhuo,ZHU Zeng-jie.Legislative proposals related maritim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domestic law relationship[J].Annual of China Maritime L aw,1999(1):5-6.(in Chinese)
[15]国务院法制办,交通运输部.《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释义[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10:122.
Legislative Affairs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P.R.China,Ministry of Transport of P.R.China.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 on Regulations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Vessel-induced Pollution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M].Beijing:China Communication Press,2010:122.(in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