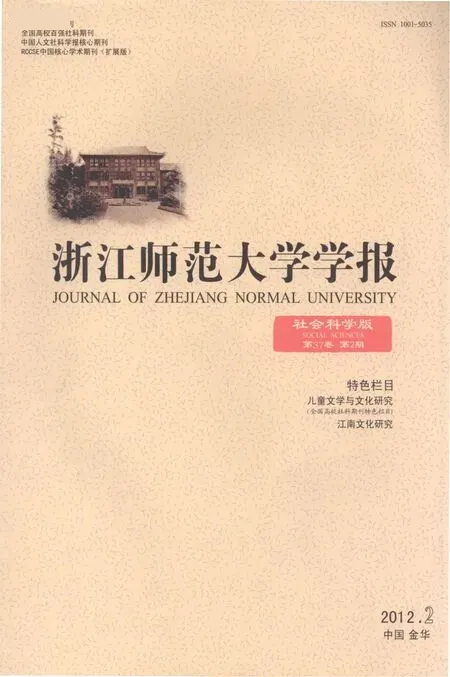“秩序审美”的伦理向度
——以群体性事件生成机制为解读路径
曾粤兴, 于 涛
(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4)*
两则一度引起网络热浪的新闻令人值得深思。一是2011年5月9日,沈阳小贩夏俊峰刺死城管案终审宣判,夏俊峰被判处死刑;[1]一是2011年4月27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在官网发文,规定5月1日至9月30日,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2]
我们冷静地分析这两则看似不相关事件背后的玄机。在两个事件中,民意为何出现一边倒的反对和质疑?刑法的适用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如此刑法适用背后有着怎样的伦理选择?冲突的暴力化、群体化折射出怎样的价值取向?我们需要构建什么样的伦理生态?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结合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以伦理向度为方法论,尝试解读和反思新闻背后的社会机理。
一、隐藏在城管暴力符号背后的“秩序审美”
网络里关于城管的新闻,基本上和暴力执法相伴,可以说城管被贴上了暴力的标签,成为城市里最不和谐的符号。打开各大网站,都有城管街头武戏的视频,因为城管暴力执法引起的群体性事件也早已不鲜见——2011年4月28日,长沙城管打人酿成群体性事件;2010年3月26日晚,昆明五华区城管在北市区北仓村农贸市场门口与小摊贩发生纠纷,随后引发群体性冲突;2009年3月31日下午,因不满城管暴力执法,四川南充市数千市民集结城市中心进行抗议,致使最为繁华的五星花园各交通要道交通中断;2009年7月1日,上海普陀区城管打伤小贩引发群体性事件。[3]当人们对城管打人“审美疲劳”时,对暴力抗法、伤害城管的不法或者犯罪行为却有了潜意识的期盼和鼓动。这种心态不仅源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对正义的向往,更源自对城管执法正当性基础的质疑和对执法方式简单粗暴的深恶痛绝。
不断遭遇暴力反抗和舆论声讨的城管部门,为什么能理直气壮地公开“城管实战操作手册”并明目张胆地在街头上演武戏?笔者认为,除却宏观上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引发社会变迁,农业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徙让城市管理者面临巨大压力以及微观上城市管理亟需高效、强力等客观需要外,城市管理者主观上在潜意识里形成的对“秩序审美”的顶礼膜拜,客观上在化解矛盾和防范纠纷的方法中形成惯性维稳的“路径依赖”,才是城管暴力化的罪魁祸首。
对美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类自古不懈的源动力。对国家或者社会而言,美更是被赋予了特殊的期许和定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给出如下定义:“美的最高形式是秩序、对称和确定性。”[4]建立并捍卫秩序是国家的内在功能,与之相应的是,国家统治者和城市管理者对“秩序审美”的坚定追随。被誉为“当今用英语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的齐格蒙特·鲍曼以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为研究路径,对自由与安全、陌生人与秩序、大屠杀的深层次诱因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剖析。按照鲍曼的理论,现代性的目标是追寻美丽、保持整洁、建立和维护秩序。建立和捍卫秩序是现代性的不懈追求,这种“秩序审美”的价值取向,驱动着国家统治者不断地做着扫除脏、乱、丑的努力;不断地与现代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模糊性、异质性、多元性和多样性相抗争。鲍曼甚至做了极端的比喻,将现代性比作从“荒野文化”(wild culture)向“园艺文化”(garden culture)转变的过程。荒野文化中的人无需有意识的计划、管理、监督,过着代际复制的生活;而在园艺文化中,“园中的野草”增强了社会秩序的脆弱性,它们让园丁们想到需要对田园进行不间断的管理和监视。[5]因为除草是“园丁”的职业本能,对外来的犹太人而言,不仅本身属于“陌生人”的范畴,而且带来就业竞争、挤占社会上升渠道、海量吸收财富,在大萧条的时代背景之下,被视作野草惨遭大屠杀就有了“合理性”依据。
“秩序审美”的泛滥最终演变为上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大屠杀的助推器,这绝非鲍曼耸人听闻的自我演绎。我国恰好处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期,正如我国学者郑杭生所言:“社会转型……,意即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也即从农业的、农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的转型。……它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6]他还指出:“陌生人世界形成、价值观开放多元时代到来,表明我们社会异质性的加强,同质性的减弱,多样性的提升,统一性的弱化,预示着多样性的统一,要由旧的形式转变为适应新情况的新形式。这正是我国社会转型,即从传统型社会到现代型社会转型的突出表现之一”。[7]并且,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两百年完成的现代化转型之路,我国在短短三十余年里就快速走过,现代化所伴生的流动性、多元性、异质性、不确定性等元素在我国城市中更显突兀和尖锐。每个城市管理者都希望自己治下的城市是美轮美奂,有序、顺畅、整洁和安全的。并且,城市管理者们上任伊始即投入极大的热情按照“秩序审美”的目光去清理、整顿城市里不和谐的因素,就像每一位称职的园丁一样,每天巡视着自己的美丽花园,努力扫除一切污垢、仔细剪除每根杂草。住在城市里的人们,也当然喜欢自己的城市如花园般美丽、整洁和安全。但是,现代化带来了大量的外乡人,他们突如其来地闯入自己的花园,穿着是那么不入时、或许还脏还破;在原本干净、顺畅的大街大声叫卖着、拥挤着,甚至留下一地的瓜皮菜叶和汤汁,妨害市容市貌,和“秩序审美”格格不入。交通、卫生、工商、税务等七八顶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的尴尬,在这样的治理矛盾中,城管自然应声而出了。随着我国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城市人口不断扩张、城市日渐庞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堆积,而市民对城市的期望值在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难度也不可同日而语,城市管理者的“秩序审美”也渐入误区。在大势拆迁、大规模改造旧城的努力中,合肥放言要建“无摊城市”,不遗余力驱逐流商摊贩;昆明十余年屡战屡败要“创卫”,甚至向临街防盗笼发起攻势;更有甚者,不少城市划下红线,让面积不足的小吃铺通通关门。
如此“秩序审美”下的城市管治思路,“城管”队员们的压力可想而知,艰巨的政治任务、宏大的治理目标不断下压,面对“你来我走,你走我来”、“屡教不改”的“陌生人”,焦虑的“城管”又怎能不收车砸称、拳脚相向呢?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城市里下层“待业”的体制外人士、坚守“孤楼”的“钉子户”,在追求完美秩序的现代化城市里,就意味着不安全和失序,无论城市管理者,抑或城市“精英”,都隐有视其为野草杂物的审美冲动。
二、“秩序审美”催生的“刑法剪刀差”
城市管理者建设“美丽”城市的良好愿望,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似乎总是事与愿违——拆迁钉子户、乱搭乱建者、乱停乱放者、占道经营者等等影响市容市貌的人在不断地制造着无序和混乱,破坏着城市管理者的审美标准。现代化又偏偏是流动性的,我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和城市的扩张都决定了城市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现实的城乡二元剪刀差,也必然迫使、诱导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寻梦。面对大量涌入的“陌生人”,城市管理者既爱又怕——爱,因为他们是可以创造财富的劳动力;怕,因为随着他们的迁入,还带来了举家迁入、举村流入的剩余劳动力,“秩序审美”的无序预设和“除草”冲动让城市管理者对“城管”爱不释手,甚至不惜扬起最后的盾牌——刑法,来塑造理想的城市之美。
还是拿新闻说事,打死城管者被判了死刑,对暴力执法致人死亡的城管又当如何呢?滕彪在《夏俊峰案二审辩护词》中列举了本世纪每个年份城管致人死亡的典型代表——2000年9月6日,四川眉山县城管监察大队管理中队郑光永、吴顺乾、驾驶员张卫东等人上街整治乱摆摊设点将杜某乱拳击伤,唐德明被甩下货车身亡。2001年5月29日,宁夏灵武市城建局城市监察大队执法人员强行没收锅灶时,将杨文志打死,并打伤杨建荣夫妇等人。2001年11月12日,因与市容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安徽宿州市个体工商户张福才在多名执法人员的推搡与踢打中身亡。2002年1月18日,重庆市沙区城管人员在检查市容卫生过程中与沙区双碑村陈家连生产队的个体户余波发生争执,他们开执法车从余波腹部碾过致其死亡。2003年2月,西安市雁塔区城管在小寨兴善寺东街清理占道经营时,一工作人员竟将摆摊的孕妇金昌艳推倒在地,并在金的肚子上踩了两脚。后经医院检查,金昌艳腹中的胎儿不幸死亡。2004年7月20日,广州天河区员村街道办城管人员在野蛮执法过程中将商贩李月明打死。2005年7月20日,经营蔬菜的56岁江苏农妇林红英被城管人员打死。2006年10月9日,广西来宾市象州县的一名流浪汉被喝醉酒的城管队队长覃宗权殴打致死。2007年1月8日下午15时40分左右,山东济阳县经一路宏伟酒业经营部老板李光春被11名城管打死。2008年7月30日,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综合执法大队的周某等4名执法人员在大田湾体育场附近将正经营的摊贩刘建平殴打致死。2009年10月27日,昆明市福发社区城管分队在野蛮执法时与一三轮车夫潘怀发生冲突,并将其打死。2010年11月16日湖北武汉黄陂区龚泽林驾车撞伤11名城管执法队员后被群殴致死。2011年5月3日,辽宁省辽阳市城管执法局宏伟区分局数名执法队员,与龙源小区居民周晓明发生冲突,后者在冲突后一个多小时即被医院宣告“猝死”。[8]
笔者没能找到太多的后续报道,仅仅从中国法院网查到重庆渝中区08年周某案的审判结果,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如下:被告人周鹏因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代剑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被告人肖在元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9]
如果说上述死者本身尚有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如龚泽林)在先,那么魏文华则纯属死得冤屈。2008年1月7日,湖北省天门市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曾被评为“湖北省优秀企业家”、“天门市优秀共产党员”、“学雷锋标兵”的魏文华路过该市竟陵镇湾坝村时,发现城管执法人员与村民发生激烈冲突,他掏出手机录像时,被城管人员当场打死。湖北潜江市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原天门市城管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孙代榜有期徒刑6年,原天门市环卫局局长熊巍5年,原天门市城管局城南执法大队长鄢志明5年,原天门市城管局城北执法大队长胡落红3年。[10]
“城管”和民众的生命价格与刑罚对价在刑法面前出现了“剪刀差”。无独有偶,深圳市《关于切实做好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结算支付工作共同维护大运会期间社会和谐稳定的通知》(深建管(2011)15号文件),为了维稳,悍然动用作为后盾法的刑法来对付讨薪的农民工。深圳市已经多次出现在舆论漩涡里了,公安局反恐演练以农民工讨薪为假想场景,住建局用追究刑责来威慑农民工集体讨薪。当农民工自身的合法权利受到不法侵犯时、当农民工辛苦几年拿不到报酬交不了孩子的学费、老人的住院费,不能回家连生存都出现危机时,城市管理者们没有想着怎么为其寻找有效快捷的维权渠道,没有想着如何将恶意欠薪者绳之于法,而是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怎么防范、威慑要求自身合法权利的农民工。这和“城管”致人死亡不被判极刑而对致“城管”死亡者施之极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过度的“秩序审美”思想在作祟。小贩和农民工一样,都是城市里的“陌生人”,都被预设为无序、混乱甚至犯罪的制造者;而“城管”是城市管理者用着顺手的利器。剪刀差刑法渐有市场。现代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寻找农村无法提供的职位和机遇,打破了城市原本的宁静和熟人社会的管治模式。在“秩序审美”的“野草”预设中和追求美丽城市的理想化冲动下,城市管理者们和刑法权执掌者们,渐渐淡忘了刑法的保障功能,为了维稳不断扩张刑法的保护功能,放纵着刑法的极端功利性。
城乡二元化分治管理模式,从体制上造就了经济和社会领域诸多剪刀差的存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交通等等优势资源汇集到城市中,农村日益边缘化;户籍管控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限制了农民的身份转变——农民工,他们城进了,工人的活也干了,但还是农民的身份;农民在社保、医保、养老保险等基本保险制度中,天然地有别于城市人口。众多剪刀差的现实存在,虽不合理,但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经济、社会领域的剪刀差可期待制度创新带来改革。但是,“刑法剪刀差”的出现,却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外地人与本地人、乡下人和城里人、小贩与“城管”、农民工与企业主、“草根”与“精英”等等的身份撕裂,一旦折射到刑法上,突破公正的伦理底线,个案不公正宣导出的刑法伦理,将加剧区割不同群体的交流和融合,无形中助长了社会敌意的酝酿。
刑法本身就是社会某一时段公共伦理的体现。普通民众对刑事立法的理解是滞后的、后觉的,对刑事司法个案的感触却是切身的、敏感的。国家刑法权执掌者透过对个案的判决,明确表达了国家对特定事件、特定行为人所持的否定的态度和评价。这种否定和评价带有十分强烈的道义谴责性,国家借助这种蕴含伦理价值的惩罚来教育国民。同时,在个案中,刑法除了实现惩罚、威慑、矫正的功能外,还必须实现补偿功能、鼓励功能、安全阀功能(安抚和泄愤功能)。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又宣扬、倡导国家推行、社会认可的公共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流商游摊们已经无奈于同城异权的时代剪刀差,如果在捍卫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刑法的面前,再遭遇“不同命”的剪刀差,包括刑法在内的国家法治体系努力宣导的公正、人道等等伦理价值,可能因为变质而与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公共伦理产生错位和冲突,民众的守法意识和伦理取向都将大受其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专门将欠薪行为规定为犯罪,对用工者进行威慑,就是在宣扬一种诚信、公正的价值观,对被欠薪的农民工则体现了补偿和安全阀的功能。如果城市管理者和刑法权执掌者不善用刑法,而是用惯性维稳来满足“秩序审美”,打压无处伸张权利而走上街头的农民工,正义的天平发生倾斜,国家构建和谐伦理的努力将毁于一旦。
笔者多次强调,刑法以公平正义、自由、秩序、人道、谦抑、宽严相济等价值为自身的伦理价值标准,这些价值还只是手段性的,只有和谐才是人类社会的目标性价值,刑法体现伦理性的最大价值就是促进社会和谐。[11]对犯罪的小贩和“城管”判决的剪刀差、对农民工和欠薪企业主的刑法剪刀差,惯性“维稳”造就的刚性秩序带来的有限的正价值远远小于伤害公共伦理、制造不和谐的无法预知的负价值。
三、“秩序审美”的伦理向度探析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从社会学的角度为我们描述了正是道德盲区的普遍存在使得大屠杀得以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发生在秩序的统治和秩序审美的精心设计之下,而不是发生在缺乏秩序管制的前现代文明社会。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缺位,使得秩序统治在对秩序的非理性追求过程中隐藏着巨大的弊端和危险。罗尔斯明确指出:“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12]4即使城市管理者的“秩序审美”出于好心,也能让大多数人享受到最大限度的城市美好,但如果以牺牲一部分人的权益为代价,就是非正义的。“某种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12]3不可否认,对秩序的追求是现代性的特征,塑造秩序之美也是每个城市管理者的理想。关键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秩序?秩序的构建需要怎样的伦理生态?
(一)理性的审视
理性作为衡量一切事物是否合乎自然性、合乎人性的判断标准,能帮助我们正确把握秩序和自由的博弈,以及权力的边界。我们理性的目光,至少应当审视下列问题:
第一,“秩序审美”背后,是否有部分官员因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造成的官员只对上负责、与民众脱节的客观现实,在追求秩序之美的过程中,对自身政治利益高度热忱而漠视了底层民众的基本利益?笔者认为,此种情形当不在少数。
第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秩序?高压管控下产生的秩序是不可持续的,笔者为这种秩序命名为“无氧秩序”——高压管控无法让“社会安全阀”正常运转。城市管理者如果不能提供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矛盾各方往往选择非法的手段来表达意见。这就是为何“城管”习惯暴力执法,又往往引起众多无直接利益相关人参与的泄愤型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就在笔者写作本文时,贵州安顺7月26日因小贩疑被城管打死引发千人围观,并最终酿成群体性冲突事件,[13]不幸成为本文的注脚。
城市管理者基于政治前途抑或其他利益驱动产生“秩序审美”的冲动时,往往忽略了管理城市的成本考量。好的城市管理者应当制定理性的、公开的、稳定的、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来维护“有氧秩序”。这种机制需要构建完善的制度体系来界定政府、社会和个体三者间的权益边界,各自守住自己的边界又共享边界利益。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在于守住政府权力运作的边界,即保证权力运作不缺位,又保证不错位不越位。对于诸如游摊流贩、城市美观之类的管理,完全可以交给社会自我管理,无须政府付出巨大成本去直接面对矛盾,出力不讨好。城市管理者需要做的是指导和协调,为各利益参与方提供公平的博弈平台。好的秩序,一定是高回报高效益的,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城市管理成本是“有氧秩序”的内在要求。
第三,当秩序与生存权发生冲突时,秩序优先还是生存权优先?夏俊峰们都是因为赖以谋生的工具被“城管”没收后,或者被暴力执法伤害后,才磨刀霍霍向“城管”的。古人将此称为“布衣之怒”,今人则称为“弱者的武器”,①城市管理者的“秩序审美”不断挤压底层民众的生存空间,一旦越过生存权的最低边界,在生存难以保证时,个体的“怒”和“武器”就不会再以“非暴力不合作”的形式出现了,“生存理性”②会引爆个体的暴力,或者自焚抗议、或者武力抗法。这些极端行为,又特别能换来围观者的同情,并激发出群体对正义的诉求。如果这种对弱者的同情与正义的被剥夺感得不到及时的合理释放,最终只会以群体性的泄愤方式表达出来。在城市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是社会优先还是个体优先?在我国这样有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传统的文化语境中,城市管理者更应该找到社会权益和个体权益、公正和效益、自由和秩序、权利和权力间的最佳平衡点,体现中道和均衡的伦理价值。
第四,幸福城市是谁的城市?当执政党和城市管理者纷纷提出打造“幸福城市”的新概念时,我们不仅要问:什么是幸福?幸福是谁的幸福?笔者认为,幸福城市当然是美丽的,她应当包括但不限于秩序之美,还应包括生态之美、和谐之美。幸福不是针对哪一部分人的,应广荫于原住民与外来人口、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草根与精英。城市管理者应当用包容性增长的思维来管理城市,为各阶层人士提供充分发展的平台和理性博弈的渠道。“陌生人”们背井离乡,在城市游走,更加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更应该得到关注、关心和关爱。幸福不是政治的定义,没有“指数”的量化,但幸福一定是个体真实的切身体验,是城市管理者和所有市民共同营造的城市灵魂。秩序之美是幸福城市的必要条件,生态之美与和谐之美才是幸福城市的充分条件。
(二)善的路径
理性是种美德,问题的提出更有利于我们构建幸福城市的伦理生态。笔者完全赞同鲍曼的两个论点,一是现代化的过程是伴随着无序而展开的;二是对秩序的追求只能是理想的愿景。秩序只可能是相对的,这是客观规律。在秩序和自由、权力和权利的矛盾对立范畴中,对秩序审美的道德约束,必须有伦理的向度,必须以公正、人道作为评判标准——秩序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筹码、不能侵犯任何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维护秩序,则更应当捍卫分配正义,倡导以人为本的政治准则;对权力边界的划定,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刑法应当力行谦抑特性,不能过度介入,和谐才是善的终级价值追求。
太多的城市管理者热衷于GDP崇拜,醉心于靓丽的摩天大楼和齐整宽阔的马路,而忘记了对城市底层的民生关注。执政党提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就在于要求城市管理者和城市“精英”们多一些底层关注,学会理解人、同情人和关心人。外来务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偏低,他们受制于自身条件,大多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工种,高强度的职业特征和城市所能提供的有限职位,必然将一部分人排除在职场之外。本来流商摊贩们依靠自己的小本经营和努力,既解决了自身的生存问题,没给领导添麻烦;又迎合了市场的需求,使社区生活更加便利。但“秩序审美”隐含的功利思想,却将“陌生人”预设成麻烦的制造者,打着为了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旗号,冠冕堂皇又霸道地断绝了他们享受城市美好的权利,将之生硬地阻挡在幸福之门外,“秩序审美”的语境下,城市管理者的人道再次缺位。部分城市管理者为了城市的光鲜外表和自身的顺畅仕途,忘记了以人为本的政治伦理,忘记了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民本思想,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
就在大陆各大城市的街头“城管”武戏粉墨登场、群体性事件风起云涌之际,台北荣获了“多元美食文化城”的美誉。笔者在台北没看到雄伟的地标性建筑和太多的高楼大厦,却在宁夏夜市、士林夜市和那些静静的巷陌,见到了全国各地的美食和轻声慢语的热情款待,品尝到了许多美食。漫步台北街头,很少见到警察和城管,秩序依然井井有条;夜市散后,摊贩自觉组织保洁工作,街面始终保持清洁;除了美食还可享受台北的温馨惬意。幸福城市是一个城市的魅力所在,幸福应该是城市里所有人的共同感受,包括原住民、打工者、流浪者和观光客。在幸福的城市里,人们尽管有贫富之别,但没有贵贱之分,平等是各人群交往遵循的准则。和谐的社会氛围,是靠大家去营造的。城市管理者天然具有政治上的主导性和道德上的引导性优势,理应把握好这种优势,这就需要掌握着伦理话语主导权的城市管理者,在管理城市的过程中,不懈地追求和彰显公平和正义,不懈的提供人性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公平地为个体提供生存的尊严和自由发展的机会;公正地提供各阶层对话和博弈的平台以及有效的矛盾解决机制;在维护秩序的同时,实现分配正义。城市管理者只有通过与民共治城市的互动,不遗余力地推行社会伦理,才能真正构建幸福城市。
笔者认为,不坚持科学发展观,无法实现包容性增长;大拆大建的运动式跨越发展,底层的生存境况被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所掩盖,城市越来越光鲜,却越来越没人情味。普遍存在的“剪刀差”现象,制度性地撕裂了人群,制造了阶层对立和社会敌意。药家鑫丧心病狂的背后,就掩藏着城乡保障体系剪刀差的祸根。富二代、穷二代、民工二代等“二代传递”现象,折射出了社会上升渠道的闭塞已经制造出了科层板结型社会。城市管理者不能引导阶层和解、不能构建“有机团结”③的社群关系,不能开放流畅的社会上升渠道,不能保证市民体面地工作、尊严地生活,幸福城市从何谈起!
善治,在于好的制度安排,其价值在于为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以及人际交往提供激励—约束机制,形成合乎理性的、有氧的秩序。城市管理者在这样一种秩序框架内,提供出的“公共产品”应当为所有市民的交往创建平等交换、有机博弈、正当竞争的平台,而不是搭建阶层对立、族际隔阂、街头武戏的斗争舞台。善治,在于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正贯彻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政治伦理的体现。善治,更在于与民共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才是和谐之美的演绎。善治,绝非随意动用刑法威慑、打压。刑法作为后盾法,不可能解决社会的一切矛盾、包揽一切问题,并且,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更不应有意无意地淡化其对公民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功能。滥用刑法,甚至出现“刑法剪刀差”,无异于滥用抗生素,一旦社会肌体起了抗药性,刑法这道最后的防护网也就失去了作用。
四、结 语
古代中国的“秩序审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整个社会秩序都被严格笼罩在“礼”、“乐”的规制之中,甚至建筑的格局、方位朝向、色彩装饰、屋顶式样、建造用材等等都有极其严格的尊卑区分和等级限制。如此秩序的追求,必然以压制社会发展和侵犯民众个体权利为代价,国家统治者殚精竭虑营造出的秩序,也就必然与和谐的终极价值背道而驰。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良性运行、社会有序发展、人们安居乐业和谐相处的社会。”[14]秩序之美,更在于对多元性的包容、对自由权利的尊重。2011年7月23日,一个应该铭刻在史书中的悲情时刻。在动车相撞后的第一时间,双岙村的村民们自发地冲向现场实施救援。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们、小商贩们,是地地道道的“陌生人”,正是这些住在城市边上的“陌生人”,为动车上素不相识的伤者打开了一条条生命通道,为我们演绎了大爱无疆。希望城市管理者们在看了视频或者图片之后,能对城里城外的“陌生人”们,多一点宽容、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关怀、多一份爱。
注释:
①“弱者的武器”最先由美国学者斯科特提出,其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通过对马来西亚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
②笔者认为“生存理性”源自求生本能的驱使,会让挣扎在生存底线边缘的人做出任何事情,去偷、抢、骗、杀人、贩毒等等犯罪都有可能,这种“理性”是反伦理的。
③涂尔干在其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中提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机械团结意指建立在社会同质性和个人相似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方式;而有机团结则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联系方式。前者是传统社会的联系方式,而后者则是现代社会的联系方式。
[1]李婧.沈阳小贩夏俊峰扎死城管终审判死刑[EB/OL].[2011-07-21].http://legal.people.com.cn/GB/14588313.html.
[2]古成.深圳发文:农民工群体性上访讨薪可被追究刑责[EB/OL].[2011-07-21].http://news.sz.js.cn/china/topnews/1892592.shtml.
[3]百度视频.城管暴力执法[EB/OL].[2011-07-22].http://video.baidu.com/v?ct=301989888&rn=20&pn=0&db=0&s=8&word=%B3%C7%B9%DC%B1%A9%C1%A6%D6%B4%B7%A8&fr=ala0
[4]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296.
[5]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M].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7.
[6]郑杭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M]//于建嵘.抗争性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0.
[7]郑杭生.陌生人社会的裂痕黏合难题[J].人民论坛,2009(9):36-37.
[8]滕彪.夏俊峰案二审辩护词[EB/OL].[2011-07-21].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6365.
[9]刘璐璐.重庆三城管队员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一审公开宣判[EB/OL].[2011-07-21].www.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811/05.
[10]褚朝新.湖北天门城管打死人案一审4名官员获刑.[EB/OL].[2011-07-21].http://news.sina.com.cn/c/2008-11-11/034716626815.shtml.
[11]曾粤兴.刑法伦理性研究[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4):75.
[12]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3]欧阳艳琴.小贩疑被城管打死引千人围观(组图)[EB/OL].[2011-07-26].http://roll.sohu.com/20110728/n314744985.shtmlhttp://roll.sohu.
[14]叶晖.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收入分配公平问题研究[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6):98-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