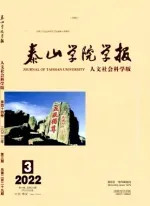试析中共与苏共执政的民众基础之差异①——基于几个维度的考量
黄波粼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上海 200241)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共产党的帮助下而诞生。两党虽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及组织架构等方面有较多相似之处,但两党执政的生命力却是迥异。执政74年的苏共②在瞬间丧失政权,原因固然很多,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执政的民众基础相对比较浅薄与脆弱。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虽然面临着各种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但事实证明,中共执政的生命力强大,这得益于其执政的民众基础还是比较深厚与稳固。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但两党执政的民众基础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本文拟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进行考量:
一、夺取政权难易程度之差异
(一)革命道路之不同
苏共与中共虽然走的都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但具体路径却不一样。苏共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革命由大城市首先发动,然后推向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各地城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些城市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原先比较强大,如鲁干斯克等是用和平方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另一些城市则经过革命与反革命的反复较量,如基辅等地是通过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
中共早期曾以城市为中心进行暴动,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的国情与实际开创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通过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政权革命赢得并掌握了民众,故而能有效领导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参加革命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赢得底层民众支持的同时,中共也赢得了广大中间势力的同情和支持。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岁月中,中共先期奠定了深厚的民众基础。比如,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中共辗转华东、华中、西南、西北等十几个省份,在广大的民众中宣传了党的纲领、理论、方针和政策,向广大民众播撒了革命的火种,赢得了民众的普遍好感和支持。
作为落后国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俄国和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均散布在农村而非城市。不难想见,苏共先期的民众基础远不如中共。
(二)革命周期之不同
苏共夺取政权所耗费的时间比中共短得多。如果以1912年布尔什维克成为独立政党③算起至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苏共夺取政权的周期是5年。如果以二月革命算起至十月革命胜利,苏共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便夺取了政权且伤亡微小。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进行了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故而,中共夺取政权较苏共要艰难得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说中共取得革命胜利付出了极大的艰辛与代价,但中国共产党得到了经过血火考验的民众基础。
从革命道路和革命周期来看,苏共夺取政权的难度远不如中共,“得易失易、得难失难”,这或许是苏共一夜之间就“轻易”丧失政权的一个原因吧。后人虽不能简单地以夺取政权的难易来考量丧失政权的难易,但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经过长期艰难磨砺的中共,其生命力要比苏共强大。亨廷顿指出:“通过持久的民族运动所产生的一党制又比那些由斗争历史较短,胜利较为容易的运动所产生的一党制更为稳定。一般来说,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为独立而战的时间越长,它能享受与独立一起到来的政权的时间也就越长。”亨廷顿的论断为我们从夺取政权的时间和难易这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个政党执政生命力的强弱提供了一个反思的视角。
二、意识形态开放性之差异
意识形态对于执政者而言,具有特有的政治整合和政治凝聚功能。意识形态如果僵化、封闭化和凝固化,将削弱民众对执政者的忠诚和信服,从而消蚀其民众基础。
苏共与中共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建党。两党在各自的革命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分别形成了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虽都是两党执政的意识形态,但两党对这一意识形态的态度却大不相同。苏共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其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僵化、凝固和封闭的。苏共将马列主义神圣化、教条化、简单化,且将“意识形态全面贯穿于政治生活,连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渗透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对真正的社会症结问题,或竭力掩盖,或言不及意,导致民众的政治冷漠。值得注意的是,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导致其免疫力低下,当它“一旦进入开放的环境,理论便再难以驾驭实践”。以致于在苏共二十八大上,75%的代表对戈尔巴乔夫投了赞成票。这说明苏共自夸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其说服力甚至比不上“新思维”,反映出大多数党员在思想、理论上的迷失,也说明了长期以来苏共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重大缺陷和失误。
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虽也发生过不少失误甚至是错误,但在不断地进行自省并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使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并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又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中共既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动摇,又不将意识形态僵化和封闭化,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适时提出与之相契合的思想理论成果,从而使其意识形态系统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进而增强其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中共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乃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惟其如此,才能不断夯实执政的思想基础,从而不断夯实执政的民众基础。
三、对待领袖人物态度之差异
对于苏联和中国而言,斯大林和毛泽东已不仅仅是开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袖人物,还成为苏共、中共执政资格的化身。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在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成为合法性的象征和根源。一旦领导人的个人权威受到挑战,便不可避免地导致合法性危机,导致政治秩序的失序。
可惜的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行“非斯大林化”,甚至把斯大林的错误简单地归结为其“粗暴、任性、不容人”的个性和“病态的疑神疑鬼”、“迫害狂”心理以及“自大狂”、“不容异己”、“贪权”、“残暴”等不良品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造成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巨大的思想混乱。此举无疑削弱了苏共执政的思想基础,也削弱了其执政的合法性,从而也消蚀其执政的民众基础,进而削弱其执政的生命力。
中国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后,邓小平沉痛地总结经验教训,审慎地对毛泽东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认为毛泽东功大于过,从而维护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邓小平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百周年诞辰时,江泽民专程赴韶山为毛泽东铜像揭幕;十六大结束后不久,胡锦涛亲赴西柏坡考察,重温毛泽东的“两个务必”。无疑,中共在对待领袖人物的态度上远较苏共辨证,从而使中国广大民众对领袖人物的感情依旧,进而对党的忠诚依旧。民众固然对党有这样有那样的不满,但公允地说,中共的民众基础还是相当深厚与稳固,这不能不说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依然不减。
四、改善民生的力度之差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众基础的稳固度还取决于执政者改善民生的程度,它包括经济增长及民众的生存状态等方面。日本学者山口定指出:“能长期成功地满足人们对‘效用’的期待,其‘效用’不久就可能转化为‘正统性’(即合法性,以下同——笔者)的‘政治体制’。反之,如果长期在满足‘效用’方面连续遭到失败,那么也很可能会使其原来具有的‘正统性’受到损害乃至全部丧失。”
苏共执政期间,一直比较忽视民生的改善:
(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经济发展陷入停滞。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严重下降,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到1984年国民收入只增长3.2%。1987年苏联国民收入只增长2-3%。正如李普斯特所言:经济增长一再丧失,或长期丧失,就会危及一个政权的合法性。
(二)重积累轻消费。从1980、1985年消费与积累的比例表中可窥一斑: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84年,1985年
(三)偏重发展重工业、轻视与民生紧密相关的轻工业。比如苏联轻工业品生产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快的特点,产品品种不全,质量又差,不适销对路,广大消费者抱怨到商店里买不到需要的东西,而商店却积压了大量色泽单调、式样陈旧的商品;以 1985年为例,针织品的产量是1732000000件,人均消费量却只有6.8件;皮鞋的产量是764000000双,而人均消费量只有3.2双。又如1981—1985年轻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计划是3.4-3.7%,但实际却只有1.5%。因此苏联工人问:“为了啥去卖力提高生产,去挣更多的工资?工资再多,国内经济也做不出足够的像样的东西,吸引他们购买。”
很明显,苏共的经济发展战略严重制约了改善民生,民众的日常生活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民众的切身利益长期得不到改善,必然会出现执政的合法性危机。
中共执掌政权后,以苏为鉴,试图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必须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等方面的关系。尤其是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如1978—1999年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从343.4元增至5854元、133.6元增至2210元;全国城乡居民银行储蓄存款余额从210亿元增至59621.8亿元。1978年至2008年的二十年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从184元增至8183元,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57.5%降至37.9%。
尽管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过热、物价上涨、贫富差距加大等情况,但平心而论,中国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到了较大满足,民众的衣食住行均得到了较大改善。虽然中国民众的民生还有待进一步改善,但中共改善民生的意识一直是比较自觉的。
五、廉政建设的成效之差异
苏共执掌政权后,虽也试图尽力进行反腐和廉政建设,但苏共内部还是逐渐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呈现稳定化和扩大化的趋势,甚至在共和国、州、区也形成了自己的小特权阶层。据俄国学者保守估计,“特权阶层”在这一时期约有50—7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亲属,共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人口的1.5%。西方学者估计特权阶层人数大约为25万人,约占苏联人口的千分之一。特权阶层享有名目繁多的津贴;免费疗养和特别医疗服务;宽敞的住宅和豪华的别墅;特殊的配给和供应等。他们除享有许多特权之外,还贪污受贿,非法攫取国家资财。特权和腐败导致了民众强烈不满的政治情绪,而这种情绪使民众极度不信任党和政府,工作热情普遍消退,显示出政治冷漠。可见,苏联民众对苏共已丧失希望,苏共与民众的离心力越来越大。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民意调查,结果是: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考察苏共丧失政权的诸多原因,不能不说严重的腐败和恶劣的民生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其彻底丧失民众基础,最终被民众所抛弃。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前夜,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居安思危并提出“两个务必”。执政后,毛泽东对腐败的高官处以死刑,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保持党和政府的清廉。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由于各种因素,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虽也是层出不穷,但中国共产党反腐的决心是非常大的,甚至把反腐提到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不管其官位有多高,势力有多大,一定严力查处而绝不姑息,绝不允许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同时,党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的防腐、反腐的制度和机制,进行有效的廉政建设。中国民众虽对腐败表示不满,但对中共反腐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还是有所上升。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介绍,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至2010年,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从51.9%提高到70.6%;公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3.8%。这表明,中共近几年来的反腐和廉政建设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中共反腐、廉政的意识是主动并较自觉的,且将其做为一个长期的治理过程。正如胡锦涛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大会上所言:“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由此而言,反腐关系到中共执政的民众基础是否稳固。故而,民众对廉政建设的满意度是执政党生命力的风向标。
结语
苏共与中共均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两者均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革命并夺取了政权。由于两国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民众心理等方面不同,也由于两党的革命经历及自身建设的迥异,故将导致两党生命力的不同。通过对影响两党执政之民众基础的几个维度进行考量,可以发现中共在执政前和执政后之民众基础均要较苏共深厚与稳固,这既是历史形成的,也是现实调适的结果。
较苏共而言,中共更具有开创性和世界眼光,更善于不断总结执政的经验教训、又善于不断汲取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较自觉地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能居安思危、与时俱进,不断适时调整相关政策,兼顾各阶层的利益;正确认识并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进而主动并自觉地去夯实其民众基础。
中共唯有不断有效化解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不利因素,从严治党,才能使其执政的民众基础得到夯实而不致于流失。
[注 释]
①本文入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优秀论文。
②苏共的名称有个变化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将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成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本文为叙述方便起见,对此一律概称为“苏共”。
③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召开,通过新的党章与党纲,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提出一套独立的纲领、路线和策略,标志着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1912年的布格拉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最终分裂,各自成为独立政党。
[1]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美]塞谬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
[3]周尚文,等.苏共执政模式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5]周尚文,郝宇青,等.合法性视野下的苏联政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意见[A].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7][日]山口定.政治体制[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8]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85年[A].世界经济年鉴[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9]世界经济年鉴[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0][美]S.M.李普斯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1][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2]中国经济年鉴(2000年)[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14]赫·史密斯.苏联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M].香港:香港朝阳出版社,1976.
[15]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6]金鑫.中国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