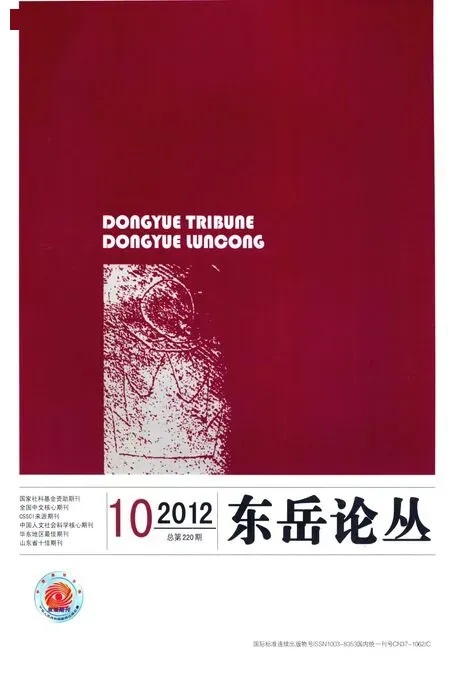刘勰“《书》标七观”说考源
刘 曈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曲阜 273165)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有“《书》标七观”1本文因引用传统古籍文献较多,只在行文中直接说明出处,不再对引用常见古籍作注,只对近现代的参考文献做尾注。的说法,今人多引《尚书大传·略说》篇载记的孔子与子夏、颜回论《书》时的相关表述来对其标注,其实《孔丛子·论书》篇里亦有《书》之七观相关内容的载记。《论书》篇相关内容仅为孔子与子夏论《书》时的相关表述,并没有提到颜回,而且所涉及的具体《书》篇及其所观之序次,与《略说》篇亦有差异。从考证学角度而言,根据《尚书大传·略说》篇单一的记载来断定孔子曾有《书》之七观说,不免显得有些武断,故《孔丛子·论书》篇相关内容的记载就显得非常重要,至少为考证孔子七观说提供了重要的旁证。伏生引述孔子《书》教之心传来教授汉初的门徒弟子,是符合史实的,至于两者有关孔子《书》之七观说的文字差异,甚至一些具体内容亦有着明显的不同,主要原因理应是由传述者的不同造成的,这种现象在先秦、两汉时属于常见现象。
七观说属于论《书》类的内容,两处文献均载记为孔子提出,笔者认为此说是符合史实的。论《书》的现象并不是孔子先为之,在孔子之前有关《书》之说解的现象早已有之,孔子只不过是对此传统的承传和进一步拓展而已。故本文认为孔子论《书》提出七观说,与孔子论《诗》可“兴、观、群、怨”一样,完全是有可能的。从较为可信的传世文献《论语》有关孔子论《书》的内容来看,虽然不多,但孔子在以《书》为教时确实曾提出过一些有关《书》的说解。《尚书大传·略说》、《孔丛子·论书》两篇都将“七观”说载记为孔子所言,而且稍有差异,恰恰说明此说绝不是空穴来风,当为两汉甚或晚至魏晋时儒家不同《尚书》学派收集整理载记下来的来源于先秦时期的有关孔子释《书》的“传”文或传说,并不能说明此说确为汉魏时人所伪造。因七观说较早言简意赅地概述了《尚书》中的核心要义,故对后人诠释《尚书》的向度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尚书大传》及其七观说考源
《尚书大传》一书,旧题秦博士伏生撰。伏生单名胜,字子贱,山东济南人,为汉代今文《尚书》学派的开山始祖。《后汉书·郑玄传》载郑康成最早为《尚书大传》作注,据宋王应麟《玉海》三十七卷转引陈骙《中兴书目》所抄录的郑玄为其《尚书大传注》所写的《序》里,关于《大传》的作者却又有另一种说法:“(《尚书大传》)盖自伏生也。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授之,音声犹有讹误,先后犹有差舛,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曰《传》。刘向校书,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据此又多认为《尚书大传》同《论语》的成书过程极为类似,是伏生弟子张生、欧阳容等根据伏生所教《书》之大义而撰成。台湾郑裕基先生就此分析认为“说伏生是这本书的作者,似乎不太精确。不过书中记录的是伏生讲课的内容,将著作权归诸伏生,好像也不算离谱的事。”①
《尚书大传》的成书年代当为伏生去世不久,而且在郑玄之前一直以四十一篇的版本在传播。从文献载记来看,《尚书大传》成书后在汉代流布很快,流传非常普遍。生活于汉武帝时的夏侯胜就曾诠释过《尚书大传》中的“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痾”,郑玄的《尚书大传注》就曾转引过夏侯胜是如何说解该句中的“伐”宜为“代”的;刘向所著的《洪范论》更是其“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的结果;在《白虎通义》一书中《尚书大传》之专名更是多见,该书的《礼乐》、《诛伐》、《灾变》、《王者不臣》、《文质》、《三正》诸篇都可以找到不少“《尚书大传》曰”的相关表述。查《汉书·艺文志》并未发现直接著录有《尚书大传》之名,只著录有“《传》四十一篇”,紧随在“《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之后,但未标明作者,学界多认为此“《传》四十一篇”即为《尚书大传》。至于班固为何不直接著录为“《尚书大传》”而是著录为“《传》四十一篇”,个中原因也许是受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体例的影响,毕竟《尚书大传》即为刘向“校书,得而上之”的“凡四十一篇”之《传》。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最早载《尚书大传》三卷,伏生作。《隋书·经籍志》亦著录为《尚书大传》三卷,郑玄注,并说“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唐书·艺文志》亦照例将此书著录为三卷,伏生作。刘勰在《文心雕龙·练字》篇曾说:“《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帝王世纪》云‘列风淫雨’。‘别’、‘列’,‘淮’、‘淫’,字似潜移。”但刘勰所看到的《尚书大传》具体情况已无法查考,理应为由汉代郑玄所注的八十三篇本向隋唐时期的三卷本转变期间的本子。
《尚书大传》三卷本之流传,在唐、宋之间又有变化,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今本四卷,首尾不伦”,叶梦得亦云:“今世所见,惟伏生《大传》,首尾不伦,言不雅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更有“印版刓阙,合更求完善本”的说法。足见至宋《尚书大传》的流传本还出现过四卷本,而且已经出现前后不伦、版面残缺的现象。元、明两代公私书目都不曾著录《尚书大传》,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仅为后人的辑本,以清人的辑本为多。如孙之录所辑的《尚书大传》三卷,《补遗》一卷;董丰垣的《尚书大传考纂》三卷,《备考》一卷,《附录》一卷,《补遗》一卷;惠栋的《尚书大传注》四卷,《补》一卷;卢见曾刊行的《尚书大传》四卷,《补遗》一卷,卢文弨为卢刊本作的《考异》一卷,《续补遗》一卷;袁钧的《尚书大传注》三卷,《尚书略说》一卷,《尚书五行传注》一卷;王仁俊《尚书大传佚文》一卷,《补遗》一卷;另外还有王谟的《尚书大传》二卷,任兆麟的《尚书大传》一卷,孔广林的《尚书大传注》四卷,黄奭的《尚书大传注》一卷。而陈寿祺的《尚书大传定本》五卷②、《洪范五行传》三卷,皮锡瑞的《尚书大传疏证》七卷本较其它者最为精审,王闿运的《尚书大传补注》七卷本亦有可观之处,但较陈、皮二氏所辑所证显然较为疏略。
《尚书大传》为最早的解说《书》的专著,虽为依附《书》的解经之作,但其解经的具体内容相当广博,与《韩诗外传》颇为相似,故而在探讨先秦《尚书》学说的具体模式方面价值巨大。《四库提要》认为该书“古训旧典往往而在”、“于经文之外撮拾遗文”,今人台湾学者程元敏先生也认为该书“杂采古事异辞,审证经义,实非尽释经”③。《尚书大传》分为《唐书》、《虞书》、《虞夏书》、《夏书》、《商书》、《周书》、《略说》七卷,七观说之相关内容见于《略说》卷。《略说》卷为伏生通论全五代《书》义和孔子及弟子《书》学问答之内容,多属于“杂采古事异辞,审证经义”、“古训旧典”、“于经文之外撮拾遗文”之类。
《尚书大传》虽已失传,但其七观说的具体内容尚赖一些传世文献的称引而得以保存。清陈寿祺《尚书大传辑校》据《路史·外纪》卷九所辑有以下表述:
子夏读《书》毕。孔子问曰:“吾子何为于《书》?”子夏曰:“《书》之论事,昭昭若日月焉。所受于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穷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壤室蓬户,弹琴瑟以歌先王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上见尧舜之道,下见三王之义,可以忘死生矣。”孔子愀然变容曰:“嘻!子殆可与言《书》矣。虽然,见其表未见其里,窥其门未入其中。”颜回曰:“何谓也?”孔子曰:“丘常悉心尽志,以入其中,则前有高岸,后有大谷,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通斯七者,《书》之大义举也。”
《路史·外纪》未明说此段文本征引于何种文献,但《太平御览》四百十九人事部六十、《困学纪闻》卷二、《小学绀珠》卷四并引此段文本中“六誓”以下的相关文本,而且均明言引自《尚书大传》,故此段文本为《尚书大传》文本无疑。陈寿祺对此另加按语曰:
薛季宣《书古文训序》亦有此文,未有“通斯七者,书之大义举也”二句,亦不称所出。而末叙“七观”云:“是故《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其序次与《孔丛子》同,与《御览》、《困学纪闻》所引《大传》“七观”异,则非《书大传》之文明矣。《孔丛》言《大禹谟》、《益稷》者,盖伪作者羼入,而不知真古文与今文皆无《大禹谟》,其《益稷》一篇则统于《皋陶谟》中也。
陈氏此说受到了清人辨伪之学的影响,故认为《孔丛子》之说为伪作,此种说法尚有不少商榷之处,下文另将别论。
二、《孔丛子》及其七观之说考源
《孔丛子·论书》篇所记孔子《书》之七观说的相关内容为:
子夏问《书》大义。子曰:“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大禹》、《皋陶谟》、《益稷》见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勋焉,于《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泰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
《论书》篇为传世本《孔丛子》的第2篇。《孔丛子》共23篇,由《孔丛子》21篇、《连丛子》2篇、《小尔雅》为《孔丛子》的第11篇三部分组成,是一部记述自孔子至东汉中期十几位孔氏家族著名人物的言语行事的杂记。由于分卷不同,现存有两个版本,一是见于《四库全书》的三卷本,一是见于《四部丛刊》的七卷本,二者大同小异,应来源于同一个祖本。《论书》篇共计16章,主要记载了孔子从不同角度与门弟子或列国诸侯或宏观或微观诠释论辩《书》的言行片段,具体而言,包括孔子回答子张关于“受终于文祖”、“有鳏在下,曰虞舜”、“奠高山”、“尧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则?以教诚而爱深也。龙子以为教一而被以五刑,敢问何谓”4章,回答子夏问《书》大义、辨析子夏“何为于《书》”2章,回答宰我“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禋于六宗”2章,回答季桓子“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1章,回答孟懿子“钦四邻”1章,回答公西赤“其在祖甲,不义惟王”1章,回答鲁定公“维高宗报上甲微”、“庸庸祗祗,威威显民”2章,回答齐景公“明德慎罚”1章,回答鲁哀公“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1章,以及孔子直接论“《书》之于事”1章。“七观”说见于《孔丛子·论书》篇孔子回答“子夏问《书》大义”章。
《孔丛子》旧题孔鲋撰,但班固《汉书·艺文志》未记载此书名,书名最早见于三国魏时王肃所作的《圣证论》中。因孔鲋至王肃四百多年间无人提及此书名,而且书中的一些内容属于孔鲋之后的事,显然非孔鲋所能撰,故自宋、明以来多视其为伪书。第一个为《孔丛子》作注的宋咸认为前6卷21篇为孔鲋撰,后1卷为孔臧所附益,而朱熹怀疑此书应是宋咸本人伪作。亦有学者认为王肃首先伪造了《孔子家语》,后又伪造了《孔丛子》,以便两书互证为真。今人李学勤、黄怀信等学者认为此书之成书时间应当提早,且可能是“孔子家学”,可能是孔子二十世孙孔季彦或其后某位孔子后裔搜集先人言行材料编辑而成,非王肃等人伪造,故近年来,《孔丛子》一书的价值才重新为学界所重视。王均林先生则继李、黄二人之后进一步指出:
从考证作者入手来论证《孔丛子》的真伪,在方法论上存在错误。从《孔丛子》全书来看,《孔丛子》部分与《连丛子》部分不是一位作者所撰……就《孔丛子》部分而论,除开《小尔雅》,剩下的20篇,在题材上与《说苑》、《韩诗外传》相类似,都是一些孔子子孙的言行片段,篇幅短小。这些言行片段,必非记述于一时一人之手;而且推测其数量不少,零星散处。到了汉代,孔子子孙中有人出来加以搜集、整理,编订成书,于是有了《孔丛子》。因此,《孔丛子》没有作者,只有编者。这位编者很可能是孔鲋,但孔鲋没有最后完成全书的编订工作,他的后人(儿子或孙子)继承其未竟的事业,连带将孔鲋的言行一并编入书中。④
台湾学者许华峰通过比对《孔丛子》称引《尚书》的相关材料后则指出:
《孔丛子》所引《尚书》来源不一。而且亦无意将所引的《尚书》版本统一。其中,引《尚书》相关材料与《伪孔经传》不相违背的部分,并无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一定引自《伪孔经传》,而不是出自其它来源。就整体的引用情况而言,《孔丛子》比较重视与《今文尚书》相关的篇章。少数可能与“《伪孔本》多出《今文尚书》诸篇”相关内容,往往不明言出自《尚书》,且文字多与《伪孔本》不同。⑤
王钧林先生认为包括《论书》篇在内的《孔丛子》部分没有固定的作者,只有搜集整理者,是有一定道理的。许华峰认为“《孔丛子》所引《尚书》来源不一,而且亦无意将所引的《尚书》版本统一,引《尚书》相关材料与《伪孔经传》不相违背的部分,并无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一定引自《伪孔经传》,而不是出自其它来源”,亦较为合理。而今人阎琴南据杨慎《古隽》卷二所引作“孔鲋曰”,“帝典”作“尧典”,且无“大禹谟”、“益稷”,与《大传》同,认为《孔丛子》与《尚书》有关的内容本袭用《尚书大传》,但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发生了文字讹误,怀疑《帝典》系“今本《孔丛子》袭《大传》改”,“益稷”二字系“今本妄增”,导致今本《孔丛子》《论书》篇的内容异于《尚书大传》。笔者以为此说欠妥。不过阎琴南关于“秦誓”与“六誓”之别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
诸本“秦”或作“泰”,疑双误。当据《书大传》改作“六”,盖《孔丛》此章乃袭《书大传》成文,后世讹“六”为“大”,复缘“大”与“泰”近(形似音亦通),而书作“泰”,今本作“秦”者,盖《书》有《秦誓》,且“秦”与“泰”形近所致。薛季宣《书古文训序》引正作“六”,“六誓”与下文“五诰”亦相对,此可为旁证。⑥
若按程元敏“六誓”当为《甘誓》、《汤誓》、《泰誓》、《牧誓》、《大誓》、《费誓》六者来讲,“六誓可以观义”是完全能够讲得通的,每一誓都可以观到出师于义的内容。但若说“《秦誓》可以观义”则就讲不通了,因为从《秦誓》里根本观不到义,而是悔过之辞盈余满篇。故阎琴南认为“讹‘六’为‘大’,复缘‘大’与‘泰’近(形似音亦通),而书作‘泰’,……‘秦’与‘泰’形近所致”,若从内容对应上来看,也是能够成立的。
从所观之结果来看,“七观”在《尚书大传》里包括观义、观仁、观诫、观度、观事、观治、观美,在《孔丛子·论书》篇里包括观美、观事、观政、观度、观议、观仁、观诫,都是七者,只有“政”与“治”、“义”与“议”之间的差异,二者只是字异,实则义同。从叙述之序次来看,“七观”在《尚书大传》里是义、仁、诫、度、事、治、美,在《孔丛子》里是美、事、政、度、议、仁、诫。序次之别,可能为言说习惯不同造成的。从所涉具体篇目来看,七观说在《尚书大传》里包括“六誓”6篇、“五诰”5篇、《甫刑》、《洪范》、《禹贡》、《皋陶谟》、《尧典》,总计16篇;在《孔丛子·论书》篇里包括《帝典》、《大禹谟》、《禹贡》、《皋陶谟》、《益稷》、《洪范》、《秦誓》、《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甫刑》,其中《帝典》是单指《尧典》还是《尧典》、《舜典》的合称已很难考证,故计13篇或14篇。二者虽有篇目之差异,但从传世文本来看,《益稷》一篇统于《皋陶谟》之中,《舜典》一篇统于《尧典》之中,事实上仅有《大禹谟》与《大禹谟》、《禹贡》,“六誓”与《秦誓》之别。传统观点认为《大禹谟》既不在今文篇目之内,亦不在真古文篇目之内,是伪古文所参入,但出土文献郭店战国楚墓竹简中的《成之闻之》篇中有《大禹》篇名,李学勤先生认为《大禹》即《大禹谟》。
由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竹简、上博简及最新发现的清华简的部分相关内容可知,孔子早在战国初期已经被尊为圣人,其言语已被广泛称引,而孔门弟子又先后曾在广大的区域内传播过孔子之术,战国时期流传的孔子论《书》、释《书》史料大部分文本的主旨理应出自孔子,《大传》、《孔丛子》两则文献正体现了孔子《书》学的一些基本主张。至于二者在一些细节上的差异或出入,不但不能证明“七观”说是汉魏时期学者伪造,更不是今古文学者在伪造时引起的冲突或露出的破绽,反而更真实地证明了孔子七观说确实有着遥远的文献来源,在官方、民间都在以某种样式流传,因当时的书写、方言或门派之别等多种原因,其局部内容稍有出入,是很正常的事。
三、孔子论《书》与七观说之要义考源
从文献载记来看,不仅古《书》早于孔子已有之,对古《书》的解说行为,亦早于孔子而有之。皮锡瑞曾就此现象指出:“孔子以前,未有经名,而已有经说,具见于左氏内外传,内传所载……夏后之‘九功九歌’,文武之‘九德七德’,《虞书》数舜功之‘四凶十六相’,……非但比汉儒故训为古,且出孔子删定以前。”⑦程元敏先生则进一步指出“《左传》所称夏后功歌、文武德、舜功,盖《尚书古传》,孔子尝编次之。”⑧程氏言孔子曾编次过《尚书古传》,不仅在情理之中,因为孔子以《书》为教,虽有一些属于言前人所未言的自我见解,亦必参考古人的诠释,不可能不对前人的零散《书》传进行系统整理编次,而且亦有文献明确载记,《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司马迁在这里所说的《传》即为《书》之《传》,为孔子所编次。这些《传》文或说解多是在孔子与其弟子问答《书》时生发出来的,并曾被孔门后学记载下来或在一定区域内得以传播,后来又被战国时期的一些儒学流派所接受。孔子的《书》学思想对后世儒家学说影响很大,尤其对汉代《书》学及治政思想影响甚巨。孔子的《书》教思想包括宏观、微观不同层面,隐含于孔子本人对于《书》的认知以及具体的用《书》实践中,一方面表现为孔子对《书》中的思想进行充分地汲取、吸收,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这些思想进行选择性地弘扬传播。孔子的《书》教思想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孔子教化思想与《书》所蕴含的政治思想的有机结合。义、仁、诫、度、事、治、美七者,实为孔子实施王道政治的基本主张,是孔子整体思想体系中的核心部分。“七观”说中的仁、义、美是孔子对《书》中所倡导的“德”、“治”、“事”、“政”等命题的扩展与深化,儒家早期所主张的中庸思想也是在孔子对《洪范》中“度”命题准确把握之后由其弟子们进行提升的结果,孔子明德慎罚思想更是渊源于《甫刑》之可观诫。
孔子为何认为可以从《书》之“六誓”中能看到“义”呢?“义”字繁体为“義”,为会意字,从我,从羊。“我”是兵器,又表仪仗,“羊”表祭牲,故其本义为一种天命道德范畴,指按照天命的要求而应当做的,包括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即天命之正义。《周礼·秋官》曰:“誓,用于军旅。”《墨子·非命上》曰:“所以整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可见,“誓”主要是指君王诸侯在征伐交战前率队誓师之辞,交战征伐之前统治者对师旅的誓辞必定要陈述征伐的正义性,故孔子提出了“六誓”可以观义的思想。《甘誓》、《汤誓》、《泰誓》、《牧誓》、《大誓》、《费誓》六篇均为战前的誓辞,《甘誓》是夏启讨伐有扈氏的誓师辞,其申诉征伐有扈氏原因的誓辞为:“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汤誓》是商汤讨伐夏桀的誓师辞,其申诉征伐夏桀的誓辞为:“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此,今朕必往。”《泰誓》可分为三篇,上篇是武王伐商大会诸侯时的誓师辞,其申诉征伐商纣王封原因的誓辞为:“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厎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従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中篇是武王率领军队渡过孟津驻扎在黄河北岸后的誓师辞,其申诉征伐商纣王封原因的誓辞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总申商纣王封力行无度:“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无辜吁天,秽德彰闻。”二是从天命、人事两方面力陈商纣王封的罪行:“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下篇是讨伐大军出发前的誓师辞,其申诉征伐商纣王封原因的誓辞为:“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痡四海。崇信奸回,放黜师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上帝弗顺,祝降时丧。”《牧誓》亦是武王在牧野与商纣王决战前的誓师辞,其申诉讨伐商纣王封原因的辞为:“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费誓》是鲁公伯禽率师讨伐淮夷、徐戎时在鲁国费地发布的誓师辞,其申诉讨伐淮夷、徐戎原因的誓辞为:“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大誓》之辞已亡佚。《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均是有德之君讨伐昏君,通过这五誓,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分清正义与非正义,可以使我们对于战争的合理性以及圣王的统治有更深层次的理解。《秦誓》是秦穆公兵败于崤以后的自誓辞,并未申诉进行战争的正义性,而满篇充斥着待士过失的悔辞以及对好贤容善的体认,很难观到义。
孔子为何认为可以从《书》之“五诰”中能看到仁呢?《礼记·经解》曰:“上下相亲谓之仁”。《说文》曰:“诰,告也”,《说文通训定声》曰:“上告下之义,古用诰”。《五诰》指《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大诰》是周公以成王的口吻在东征前对多邦诸侯及其官员的诰辞,《康诰》是周公对康叔封卫的诰辞,《酒诰》亦是周公对康叔封卫的诰辞,《召诰》是周公、召公关于如何巩固政权的论辞,《洛诰》是周公归政成王的诰辞。《五诰》均为西周初年所作,其诰辞充分体现了以文、武、周公、成王为核心的周初统治者营周安殷的辛劳和心系臣民的关切之情,我们可以从周初统治者的言行中领悟到上下相亲之“仁”,以及做一个“仁”者所应具备的基本才能和品质,亦可以观到周初统治者推行仁政于殷之遗人。
孔子为何认为可以从《甫刑》中能观到诫呢?《说文》曰:“诫,敕也”。周穆王初年,滥用刑罚,政乱民怨,吕侯为相后劝导穆王明德慎罚,采用中刑,结果国家得到了很好地治理。《吕刑》是周穆王对四方司政典狱及诸侯大臣的一篇诰辞,但其内容体现了吕侯的刑罚主张,故篇名为《吕刑》。吕侯后为甫侯,故也叫《甫刑》。该篇内容涉及刑罚的目的、五刑的内容、实施刑罚的原则等法律方面的内容,使人们认识到量刑公平、适度、慎罚的重要性,孔子认为通过看《甫刑》就可以认识到刑罚适度的道理,对刑罚采取慎重的态度,认为理解这一点对于成功治理国家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郭店楚简《缁衣》篇中,孔子引用三条《尚书》文本来宣扬他的“慎罚”主张,其中2条出自《吕刑》篇,即《吕刑》云:“非用侄,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日法”,孔子是用苗民滥用刑罚而导致“乃绝厥世”的反面例子来说明慎罚的重要性;《吕刑》云:“播刑之迪”,孔子引用这句话是为了说明量刑要公平。可见,出土文献是与孔子所说的“《甫刑》可以观诫”主张一致的。
孔子为何认为可以从《洪范》中能观到度呢?度为形声字,从又,庶省声,“又”即手,古代多用手、臂等来测量长度。本义为计量长短的标准。度体现出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从某个角度讲,阴阳的对立统一就是度。在《洪范》中,箕子向武王陈述了“洪范九畴”,即“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每一畴体现的都是一种动态的秩序、标准或程度。孔子认为,把握度的原则,在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有适度,才能算是“中”,二者具有同等的含义。《洪范》中“建用皇极”的“极”字就代表“中”,故孔子说:“发乎中而见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范》乎”。在“洪范九畴”的每一畴的具体陈述中,“适度”的思想更是随处可见。另外,《论语·尧曰》所记帝尧的话“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也是孔子对“中”思想的宜扬,是与其“《洪范》可以观度”思想相一致的。
孔子为何又认为《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呢?事为形声字。从史,之省声。史,掌管文书记录。甲骨文中事与吏同字,本义为官职,《说文》曰:“事,职也。”《大禹谟》中有“六府三事允治”之说,“事”字在这里就是指一种官职。《大禹谟》记录了舜帝与大臣禹、益、皋陶讨论政务的情况,《禹贡》记录了大禹区划九州、制定贡赋、治理山川、规定五服的业绩。孔子说“《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即指通过学习《大禹谟》、《禹贡》,就可以掌握治理国家大政的本领。
孔子为何又认为《皋陶谟》可以观治或观政呢?政字为会意兼形声字,从攴从正,正亦声。攴,敲击,统治者靠皮鞭来推行其政治,“正”是光明正大。故政的本义为匡正。《皋陶谟》记述了皋陶向禹陈述如何为君的言论。皋陶认为做君的要“知人”、“安民”,并提出了著名的“九德”之说,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孔子认为《皋陶谟》可以观治或观政,事实上是在高度评价舜、禹、皋陶的治政言行,认为虞廷君臣雍穆共治的言行可为后世效法,后人可以从中学习到治国经验。
为什么孔子会认为可以从《尧典》或《帝典》中看到美呢?因为从《尧典》或《帝典》篇中能看到尧舜揖让、九官相与推贤之美政。甲骨文中“美”是人戴着羊头跳舞,似乎与原始的巫术礼仪祭祀活动相关。美又与善同意,如《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今《尧典》称帝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记述了尧任命羲、和掌管天文历法,并让位于舜的事迹。孔子说《尧典》可以观美,既是对尧“圣人”人格的赞美,也表达了孔子对唐虞禅让理想政治的称许和向往。
七观说是孔子对《书》之大义的说解,代表着孔子《书》学思想的核心观点,可以说是孔子对于《书》之教化作用最为本质的认识。子夏受之于夫子且志之弗敢忘的“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在孔子看来,只不过是《书》之表,孔子经过“悉心尽志以入其中”,又发现了《书》有“七观”之义,这才是《书》之里。《荀子》曰:“《书》者,政事之纪也。”仁、义、政、美、事、度、诫七者实为孔子推崇的德治施政大纲,体现了孔子心系天下的高度责任感。正是在孔子这一以“七观”为核心内容思想体系构建过程之中,逐渐形成了早期儒学的一些重要理论范畴,其核心部分即为义、仁、诫、度、事、治、美七者。
四、结 语
“七观”之说最早见于《尚书大传》、《孔丛子》二书,二者所记虽均明示为孔子在与弟子论《书》时提出,但所涉具体《书》篇及其序次又稍有差异。二者局部差异之原因应是多方面的,并不能就此认为“七观”说属于秦汉时期儒者的臆造,实为从战国流传下来的一些有关孔子论《书》的文献或传说。“七观”之说不仅代表着孔子对《书》教化作用最为本质的认识,而且在两汉时期曾发挥过重要影响,一度是非常流行的《书》学观念,是汉代《书》学理论中最为核心的思想。
孔子的《书》教“七观”说,在我国先秦文学理论批评中亦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对我国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传统、文艺批评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对汉魏六朝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影响甚巨。从孔安国受《古文尚书》的司马迁对孔子的《书》教观领悟得最为深刻,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创作观可以说是对孔子《书》教思想的最好注脚,《书》的有关文本不仅成为后世史家编撰中国上古历史的重要文献史料,而且《书》的行文体例所蕴含的就事析理、一事一议、不枝不蔓、事简而理明的写作艺术,也成为史传文学创作的范例,为“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导夫先路,同时也首开《书》之文体学研究的先河,对汉赋劝百讽一风格的形成亦有一定的影响。
[注释]
①郑裕基:《谈谈〈尚书大传〉和它对语文教学的助益》,《国文天地》第22卷第5期。
②原名《尚书大传笺》,后改名为《尚书大传定本》,附《叙录》一卷、《辨讹》一卷。
③⑧程元敏:《尚书学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467页,第358页。
④《孔丛子》,旧题孔鲋撰,王钧林,周海生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7页。
⑤许华峰:《〈孔丛子〉引〈尚书〉相关材料的分析》,《先秦两汉学术》第2期。
⑥阎琴南:《孔丛子斠证》,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学研究1975年硕士论文,第48页。
⑦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