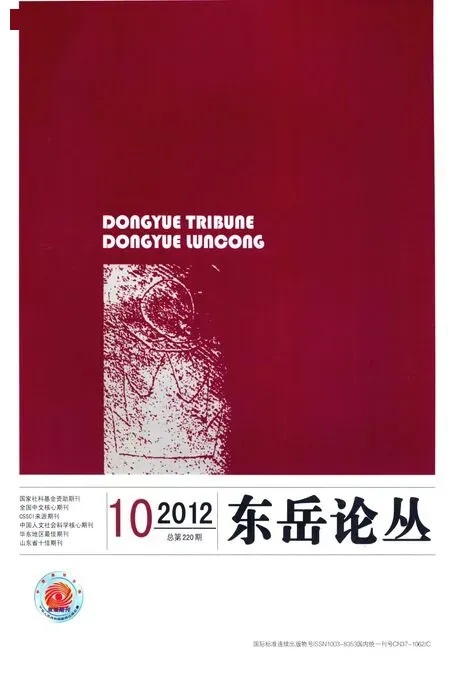《北洋画报》与北伐后的“天津”想象
陈 艳
(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100029)
《北洋画报》(以下简称《北画》)在中国现代画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26年7月7日至1937年7月29日,《北画》共出版1587期,是民国时期北方出版时间最长和出版期数最多的综合性独立画报,堪称北派摄影画报的代表。它以“时事”、“艺术”、“常识”为口号,兼及“报”的新闻性和“画”的形象性,为研究1926至1937年间天津及北方的社会文化氛围提供了图文并茂的珍贵史料。
1928年6月,北伐基本完成之后,整个国家的发展重心迅速转移到南方,平津地位一落千丈。“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已经从字面上隐喻天津昔日重要地位的失落,“自迁都而后,天津已失其过去重要之地位,外省侨居此地者,纷纷他去,人口已形减少,观于各处招租房屋招贴之多,可以想见”①记者:《天津电影业之危机》,《北洋画报》,1929年5月16日,第7卷第319期。,而且经济、教育、政务随之迅速滑落,而南方的宁沪却在新政府人力财力的大力支持下快速发展,“直有幽明异地死活殊途之感”②《南北气象不同》,天津《大公报》1928年12月11日。。这些都造成了平津地区普遍的落寞,与此相应的是,市民中的“怀旧”情绪高涨。但同时,这也是天津摆脱对北京的“隶属”地位,寻求独立发展的最好时机。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天津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劝业场、交通旅馆等大型标志性建筑纷纷开业,新闻报界和文化界进入活跃时期,新的政治局面刚开始也给天津带来了稳定和发展的希望。正是在这种失望与希望交织的复杂心态中,天津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城市新身份及其现状、前途的探索。而天津人刘云若入主《北洋画报》恰逢其时,《北画》对“天津”的关注大大超过以往,表现出本土文化转型的趋势。《北画》“时事传播”的重心也转向天津本埠新闻,出现了图像天津和想象天津的高潮。
一、“天津现况写真”
在对天津的想象与表达中,摄影图片充当了最为重要的角色。1928年12月1日,《北画》举办“本报第十次征求象征天津照片”,“专征求足以切实象征整个天津市的照片。不论其为人物名胜均可,但必须具有天津特殊色彩,以一片而能代表整个的天津市者为合格。应征者并须附寄理由书”。这是《北画》读者征集活动传统的延续,刘云若办过三次,比起1926年7月至1928年7月间的八次征集,数量并不算多。但是,其中两次都与天津有关,这在《北画》历史上绝无仅有。虽然这次征求并没有像以前一样列出中选名单,但自此,象征天津的影像源源不断,又可以说是《北画》持续时间最长的征集活动。
12月8日,征求刚刚启动,《北画》就顺势推出由本报记者摄影的“天津现况写真”,颇有示范作用:“我们要使市民认识我们的特别市,所以要把天津现况写真贡献于读者之前。”这是一次对天津的重新认识,其目的是清晰而自觉的——它是一个具有“特殊色彩”的“特别市”,而不再是“上海化”或“北京门户”的天津。“写真”包括三张照片,分别是“天津金刚桥头之反日标语”、“天津市民开会之所——河北公园”和“天津河北大经路旁冰中辟道摆渡而过”,旁边附有文字说明:“反日风潮剧烈,所以有金钢桥头的标语。当日直鲁军牧马的公园,还给了市民,所以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对联。天气寒了,河冻了,然而薄冰不可履,仍须摆渡而涉,所以舟人凿冰以利舟行。”这段文字并不具有逻辑性和整体感,只是把三张图片的说明“组装”在一起,但它实际上涵盖了“天津现况”的三个主要面向,编者看似随意的选择显示了关注天津的重点和线索。三张图片都是人景结合,但人物位置的不同,却给读者带来不同的注意焦点和观看效果。第一张图片中的人物只占据右下侧的一角,金刚桥处于图片的中心。它于1924年修成,上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和“三民主义”的巨大牌楼使得这座北洋政府时代的著名钢桥旧貌换新颜,并且后者更为突出、醒目,这显然是北伐胜利的直接产物。而河北公园看起来人流量更大,记者以对公园门口及前方人流走动的抓拍,营造出一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的动态观感,这与图片的主题“天津市民开会之所”相得益彰。昔日军阀牧马的地方,现在成了市民集会的公共场所,这既是时局变动给天津带来的积极改变,也是城市新身份引发的连锁反应,市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天寒河冻下的摆渡照片更多是一种气氛的营造,渡船上的人物因为中规中矩的中远景的缘故而成为画面意境的一部分,并不具备独立的意义。这是一幅颇具地方特色的照片,照片的背景也不再是现代化建筑,而是低矮古旧的天津民居。渡船和金刚桥恰好相映成趣,作为密切相关却又截然不同的日常生活方式,表明传统与现代的奇妙混合,而且金刚桥沟通大经路和海河对岸,两者在同一河段。“天津现况写真”反映了当时天津复杂的城市面貌,历史和现况、城市与市民、传统和现代彼此纠结,而“写真”表明记者和编者用摄影图片记录天津的自觉,这也是对读者有意识的引导,表明记录的“直观性”和“真实性”,这正是后者认知的基础。同时,它又像一个引子,城市建设、市民活动、地方风情成为《北画》接下来的天津影像的主要类别。
关于城市建设的照片为数最多,它们大多表明了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天津市民中一种普遍的乐观情绪——这正是“天津现况写真”前两幅照片所流露出来的,并以此来重新审视天津。比如“天津法界各马路口新设之指挥灯”、“天津市警察之新装束”,其关键词为“新”,尽管只是些城市细节,但以小见大,体现了城市的新兴事物及发展的深入。当然,这同时也是在表明立场,像大多数北方舆论一样,《北画》对南方北伐经历了从贬斥到欢迎的急剧转变,而且它与张学良的关系人所共知,时局转变后更需审时度势,以求得生存和发展。“天津鸟瞰”图——“日本租界及最高建筑:中原公司”①《北洋画报》,1929年6月20日,第7卷第334期。和“英中街花园戈登堂工部局”②《北洋画报》,1929年6月29日,第7卷第338期。,则透露出天津社会更为复杂的矛盾情结。它们是空中摄影,以航拍的方式呈现了天津日租界与英租界中街花园的全貌,并重点突出中原公司和戈登堂,其选择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分别是天津商业繁荣和历史地位的缩影。二十年代中后期,天津租界发展迅速,日租界旭街和法租界梨栈一带先后形成了新的商业中心。中原公司即位于旭街,1928年元旦开业,很快成为天津最受市民欢迎的娱乐和消费场所,号称“天津第一高楼”。图片中的中原公司一枝独秀,矗立在照片中央。而戈登堂又是另一番景象,图片看起来优美静谧,它具有英租界市政厅和上流社会公共娱乐场所的双重身份,而且与李鸿章、德璀琳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象征着天津从晚清以来的重要政治外交地位。表面上看来,两张图片都以天津的标志性建筑,强化市民读者对城市的整体印象,使得“标准化”和“美化”③[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艾红华,毛建雄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的城市形象的生产和传播成为可能。但不难看出,它们实际上代表着北伐前天津的繁盛与尊荣,正如当时一位英国侨民所说:“戈登堂曾经是英租界的荣耀,而今看上去就像是一座正在凋零的纪念碑。”④[ 英]布莱恩·鲍尔:《租界生活1918-1936——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刘国强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在不得不接受南方胜利的现实、并作出有利于切身利益的反应的同时,这种间接或直接的“怀旧”也在天津市民社会中普遍存在。
市民活动是天津影像的另一重要内容。天津市民在这一时期的活跃既是事实——现代市民意识在种种外力刺激下进一步觉醒,又与《北洋画报》的着力表现密不可分。《北画》作为天津流行的大众媒体,积极参与对市民活动的报道和市民形象的塑造,并且它兼有摄影画报的特殊优势,能以大量直观的摄影图片带给读者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而照片的“真实性”假定也使它比文字看起来要客观中立,往往更容易推广其意识形态标准。考察这一时期《北画》对市民活动的报道,多为群体活动,展示的是一种市民群像。1928年12月底,天津进行全市清洁运动,刘云若及时加以称颂:“人民经此提倡,亦引起公共卫生之观念,……长此以往,此藏垢纳污之天津,将尽变为街明巷净,庶不愧于头上之青天白日乎。”⑤云若:《好漂亮的天津》,《北洋画报》,1928年12月22日,第6卷第260期。可能觉得光凭文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一周后又刊发市政府参事王敬侯赠送的相关照片“天津市清洁运动之大观”,以强调“新市民”的“新气象”。当然,其中不无配合官方宣传的意思。市民群像的塑造还体现在各种群众仪式上,天津被和平接收之后,双十节、“五三”惨案等作为新的纪念日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而电车罢工、撤销领事裁判权运动等充满现代抗争意味的群众活动更能显示天津市民的成熟和作为一个群体的不容忽视,摄影记者的表现对象走向“十字街头”,扩大了市民群体的内涵,有利于现代市民意识由上而下的广泛传播和接受。
地方风情图片在天津影像中独具魅力。“冰天雪地中之渔家生活”⑥《北洋画报》,1930年1月7日,第9卷第420期。,和海河里的摆渡船一样,也是天津传统生活方式的展示。北洋摄影会会员谭林北拍摄的这幅照片,主人公为“万国桥下之用鱼鹰捕鱼者”,冻住的河面,小渔船,排成一列的鱼鹰,画面简单而不单调,非常有意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河岸上的西式建筑,很可能是码头一带的外国商贸公司和货舱,——这正是现代天津复杂面貌的某种隐喻。用鱼鹰捕鱼是天津渔民的传统劳作方式,晚清天津竹枝词里就有“鸬鹚(俗名‘鱼鹰’,笔者注)艓子小于萍,贩得鲜回尽入城”①杨映昶:《竹枝词》,张焘:《津门杂记》(卷下),清刻本1884年版,第6页。,但它在现代都市生活的挤压下已经越来越失去其生存空间及价值。谭林北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使照片带有一种矛盾的美感。这张图片就像画龙点睛之笔,给这一时期“象征天津”的“写真”照片征集画下一个句号。
二、“专页刊”:本埠深度报道
除了画报内容的有意倾斜,刘云若主编时期的《北洋画报》在形式上也做了重要改革,开始大量以专页、专面或专刊、专号即“专页刊”的形式对重要内容作集中全面的报道。这也是这一时期《北画》最为突出的形式革新,刘云若离开后,立刻锐减。在此之前,冯武越对《北画》各版面的内容设计有明确规定,除封面外,二版被设定成“动”的一面,即时事图文,三版为“静”的艺术版面,四版则是连载小说和广告。而且“种类之支配,必以均匀为主,以期能满足各种阅者之希望”,连各类图片刊登的数量都有一定的标准,力求综合、平均②《编辑者言》,《北洋画报》,1926年9月18日,第1卷第22期。。“专页刊”的出现打破了《北画》版式的固定模式和内容编排的均匀原则,它也不像《戏剧专刊》的单一,能够及时对社会方方面面的热点作出反应,灵活自如,又能尽量降低综合性报刊因过于均衡而重点、特色不突出的风险。不到三年间,除去《戏剧专刊》,刘云若出版专页刊达四十余次,充分说明了这一革新的自觉:
在第五卷里,像杨村石幢专页,杨耐梅专号,菊花专页,昆曲专页,还不过是一种尝试。我们预备在第六卷开始种种新工作,最先要采用渐进的手续,用这一张画报,把一切社会全表现出来,除此之外,凡我们所能见到想到的,全要发挥新的精神,作新的努力。③记者:《卷首语》,《北洋画报》,1928年12月1日,第6卷第251期。
事实上,“专页刊”也是这一时期表现天津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考虑到大众传播的就近原则和读者接受的接近心理,以及刘云若的天津意识和当时对天津命运的关注,“专页刊”的策划主要以天津本地人物和事件为主。何况“专页刊”的专题一般需要系列照片和深入采访,外地策划将降低效率、增加成本,因此即便是上海电影明星或北平戏剧演员的专题,也是在他们旅津期间进行采访和演出报道。“专页刊”图文结合,文字有时候甚至会超过图片,占据更大篇幅,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以文字为主,恰恰相反,文字多用来勾连图片,或作补充说明,“由于报道摄影(photojournalism)的出现,文字随着图片而走,而非图随文走”④[英]约翰·伯格:《看》,刘惠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58页。,独家、独到的摄影图片才是其精华所在,也是《北画》在激烈竞争和北方萧条时局下发展壮大的根基。“专页刊”与“天津写真”的零散记录不同,它把相关内容集中在一页或几页甚至整期画报的做法,直接确立了读者的关注焦点,能够迅速引起读者的重视;并且它能就选中的主题作深度报道,甚至是连续追踪报道,从而给读者带来全面、立体的观看印象。就表现对象而言,“天津写真”与“专页刊”对天津的描摹也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前者多为具有象征意味的单幅照片,题材内容往往“以小见大”,侧重于小型的时事新闻摄影和风土人情类的艺术摄影,而后者的专题性质让它把目光投向本埠“大”新闻,包括社会特殊群体、大型文艺活动和现代商业消费的方方面面,充分体现出北伐后天津的城市面貌。
女性形象的消费一向是《北洋画报》的重要卖点。但之前《北画》上的女性群体主要由上海女明星和名媛闺秀组成,北伐后由于地方意识的极大增强,平津女性得到更多关注,并从封面上率先得到体现,平津地区的名媛闺秀、戏剧明星取代了上海电影明星和交际明星的绝对优越地位。这些都是城市中上层女性,制造的是摩登、优美的都市女性范本。与封面女郎不同,女性专页把目光投向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天津女性。这与刘云若的阅历背景有关,他接触过各种城市下层女性,对她们的生存状态相当了解并怀有深切的同情。但刘云若在北画上并不止于为她们的命运鸣不平,而是切实探讨她们在现代城市中的合理出路。“天津妇女救济院专页”就是聚焦这一社会问题,详细报道妇女救济院的运行现状和社会意义。妇女救济院1929年由新成立的天津妇协创办,用以救助社会上走投无路的女性,包括下等妓女、女伶、女难民以及遭遇婚姻家庭不幸的女子。专页的八幅图片中有四幅均为院中女子的特写,她们穿着简单朴素的旗袍,却是时兴的宽大中袖的样式,神态也都落落大方,表现出健康良好的精神状态,联想到她们的身世,不难看出妇女救济院巨大的积极影响。《妇女救济院参观记》是刘云若惟一署以真名而非“记者”的专页刊采访,可见其重视程度,除了感动于妇女救济院的井然秩序和院中女性的精神面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为这些女性提供了切实解决社会生存问题的出路。专页以两幅图片表现了院中刺绣教室上课的情景,这是在小学程度的文化课之外,救济院开设的实用课程之一。“院中教育,趋重职业方面,现分刺绣缝纫理发三班,务使出院之生,皆有经济独立能力,不再为寄生虫”,刘云若为此盛赞“妇女救济院为青天白日旗下津门社会事业之最著成效者”⑤云若:《妇女救济院参观记》,《北洋画报》,1929年9月26日,第8卷第376期。。从简陋的济良所⑥参见《慈善机关》,《居游必携天津快览》,上海:世界书局,1926年版,第40页。到组织完备的妇济院,此类妇女慈善机关的改良成为刘云若对新政府有所期待的重要原因。
天津大型文艺活动的报道占据“专业刊”总数的一半左右,比重最大,包括摄影展、画展等艺术展览,同咏社、城西画会等天津文化社团的活动,以及电影和话剧在津的演出,充分展示了当时天津的文化动态、文化时尚以及文化环境。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摄影、电影、话剧等充满活力的新兴城市艺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民目光。其次,传统艺术门类如戏曲、绘画等仍是天津的主流艺术形态,这从天津主要文艺社团的主题,以及熊佛西率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毕业班来津赔钱演出与各类戏剧明星在天津大赚包银的对比可以看出。不过,这些传统艺术已然成为城市独特的商业景观,在天津现代商业经济迅速膨胀和报刊媒体“煽风点火”的背景下,艺术的商业化在所难免。《北画》在“电影明星”、“交际明星”的名号之外,别创“戏剧明星”,本来就表明一种商业化、时尚化的噱头,而画展专页也不是纯粹的艺术展览,倒更像个人的卖画广告。当时天津画展盛行,但实际上是一种流行的商业文化,绘画作品往往成为文化商品,“艺术”的含量可能相当低,像青年画家萧松人就直接以自己为卖点,在专页上刊登穿戴奇异长袍帽子、宛若女子的私人照片,制造噱头,以吸引观众和买家,这分明借鉴了现代商业促销的惯用手段。刘云若小说《换巢鸾凤》中的任笑予就是以萧松人为原型,不但批评了这位所谓“革命画家”的不学无术和虚伪做作,而且揭露了当时的普遍现象:“那时一般画家,正盛行着明开展览会,暗作售品所的风气。”①刘云若:《换巢鸾凤》,《北洋画报》,1936年5月26日,第29卷第1404期。
在文化消费之外,《北画》的“专页刊”也热衷于介绍报道天津现代商业消费活动的其他方面,体现出天津市民日常消费的新趋向。这类专页刊比较特殊,介于新闻报道与广告宣传之间,算是一种软文广告。天津市民耳熟能详的娱乐消费场所几乎都在这类专页中露过面,既有西湖别墅、大华饭店、中原公司等老牌名店,也有劝业场、交通旅馆等北伐后新建成的娱乐消费场所,它们均为《北画》的重要广告客户,在广告栏里出现频率极高。另一部分属于市民的健康消费——这在现代都市中日益得到重视,是更为科学和理性的现代消费习惯。它们主要是天津新式的西医诊所,包括“牙齿五官之卫生及模范医室之一斑”和“天津一模范医室之内观”。从标题的“模范”二字可以看出,这类专页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价值判断,在为两家医室大做宣传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提倡一种健康、理想的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专页中的图片给读者展示的也是西医诊所的科学、卫生和规范,而且它们还通过日用常识的普及“曲线救国”,以加强读者的良好印象和对被赋予一系列现代特质的西医的向往,比如在介绍黄林两医室时,先从牙齿五官的卫生谈起,进而呼吁现代市民讲卫生讲科学。“仙宫理发店”这类生活消费也出现在“广告专页”中,它的独到之处在于展示新的理发知识和技术之余,聘请著名漫画家曹涵美绘制了一系列新颖时髦的发型图在《北画》发表,满足城市女性读者追逐时尚的需要的同时,给读者留下“仙宫”等同于“时尚”、“摩登”的深刻印象,洞穿了日常消费的流行本质。把这类专页刊称为“软广告”,是要表明它们的“遮遮掩掩”和“伪装”,但它们体现出现代商业与流行文化结合的趋势,而且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现了读者和商业上的双赢。画报主要靠广告维持运营和盈利,《北画》的种种扩刊计划之所以难以实现,往往与顾虑广告收入的缩减有关,但是广告版面过分增加又会引发读者的不满和抵制。把广告融入画报,成为主要版面的一部分,同时提供知识和娱乐,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初的天津,还是一种新颖有效的形式。
三、“市花”选举:天津前途的缩影
在全面关注天津现状的同时,《北洋画报》也就天津的前途进行了探讨,集中体现在“关于天津的市花”的读者征求活动上。北伐后不久,1928年11月20日,针对南京、北平已选出市花,《北画》宣布征求天津市花:“南京北平既皆已有市花之规定,而我天津尚付缺如,二四四期本报,有王小隐先生曾以个人意见,请定芍药为天津市花,因而引起多人研究之兴趣,本报因即以此问题,征求答案。”市花是城市的文化标志和象征,《北画》此时有意识推出这个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对天津变为新特别市的敏感和关切,而且《北画》对市花的选定早有打算,涉及对天津的定位和未来发展的期许。11月15日,王小隐进行了先期造势:“比者南京以兰花为市花矣,北平以菊花为市花矣,而天津一市为东方重镇,华北巨埠,若不速定市花,以资象征,非徒相形见绌,抑且不免简陋。”他认为市花应是“与其地之人民性质类似之花”、“富有意义之花”,并详细论述了选择“芍药”的理由,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第四条与第五条:
芍药之开,多在春残,桃李既谢,夏木初荣,芍药乃通春夏之邮,此与津门沿海之区,常得风气之先,又富保守之性,若合符节;况复婀娜之中,饶有刚健之意,艳冶之外,别具朴素之风,四也。北平既为历史上之都城,而平津密迩,势若陪邑,牡丹既称国花,芍药乃为市艳,两花有相似之点,尤宜以类相从。牡丹既为药品,芍药亦可疗疾,津门工商之区,市花亦稗实用;津门为近海之区,芍药有迎风之韵,芍药为赠别之花,津门绾交通之枢,五也。②《天津“市花”问题》,《北洋画报》,1928年11月15日,第5卷第244期。
芍药乃天津常见之花,在民间深受喜爱。每年春末夏初,天津人都要到城西大觉庵看芍药,也因此留下大量相关诗歌,如“犹忆嫣红映晚霞,东风憔悴曼殊家。此花怪底名婪尾,不过春时不见花。柴门西对水西庄,墙内花枝明夕阳。花本无心风解意,向人吹得十分香。”③陈珍:《大觉庵看芍药》,张焘:《津门杂记》(卷下),清刻本1884年版,第3页。“大觉庵前野径斜,千畦锦绣灿朝霞。游人漫说丰台好,百亩先开芍药花。”④崔旭:《大觉庵看芍药》,张焘:《津门杂记》(卷下),清刻本1884年版,第6页。在王小隐看来,芍药与天津的人情地理十分吻合,均兼具开放与保守、婀娜与刚健、艳丽与朴素。在这里,王小隐对天津的把握相当准确,也符合《北画》同人及一般市民的看法。而且第五条理由实际上关涉天津的定位和前途,王小隐顺应时局,抛开政治等其他因素,着重强调天津在工商业方面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近海之区”,又是内地的交通枢纽,看好天津作为华北商业中心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发展,并以此作为新特别市的立足点。这在当时,是符合现实情势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军事优越地位及其带来的特殊利益已然丧失,只有凭借新的相对稳定的历史条件,以及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工商业积累,取得进一步的城市化发展。出于共同进退的亲密关系,《北画》对新北平的前景也相当关注,何况北平的“复兴”于天津大有好处。但与对天津的考量不同,这些文章大多赞成因地制宜,把北平建成旅游文化城市。“河北主席商震氏,人颇精明,尤能虚怀请教于人。南中某君因公来平,商氏颇表示北平衰落之可惜。某君献议,谓宜整理古迹,广事宣传,吸引外邦人士,来游此地,则地面上以及附带之工商业,必因之渐归兴旺,并举瑞士国之惟赖游人立国为例”①妙观:《商震口中之中国式大饭店》,《北洋画报》,1929年6月18日,第7卷第333期。,“妙观”是冯武越的笔名,他是广东人,文中的“南中某君”,很可能就是他自己。
1929年1月8日,市花答案揭晓,王小隐的文章显然打动了很多市民读者,“蒙阅者纷纷投函,年前已接有百数十件,惟以选举芍药者为最多。芍药前有王小隐君倡之在先,复经众意公选于后,故本报即假定‘芍药为天津市市花’”,并由曹涵美拟出市花图案。紧接着,1月24日,“天津市当局暂定竹为市花”②《如是我闻》,《北洋画报》,1929年1月24日,第6卷第273期。。虽与征求答案相左,但时间间隔如此之近,很可能与《北画》有计划有步骤的大力鼓吹有关,而且竹的选择,也符合王小隐列出的五个条件。
不过,王小隐称:“北平既为历史上之都城,而平津密迩,势若陪邑,牡丹既称国花,芍药乃为市艳,两花有相似之点,尤宜以类相从。”这段话看似有点牵强,北京既已改为北平,不再是国都,天津以芍药与牡丹“以类相从”再无必要,但以“故都”、“陪邑”的历史来作为挑选市花的理由,其实是当时普遍的怀旧情绪的体现。正如颜惠庆所说,在天津,由于迁都造成的地位失落,“不少人向往过去,不满现实,怀疑将来”③颜惠庆:《颜惠庆自传》,姚松龄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161页。。天津的历史与故都北京纠缠在一起,它被称为“北京的门户”,也是北方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和最大的商埠,历经晚清李鸿章、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前台”时期,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后台”时期,其重要的政治、军事、外交地位由显而隐,却从未改变。1928年北伐后首都的南迁,给天津带来了巨大影响,更直接引发了《北画》的本土文化转向。同时《北画》对北平的关注也大大超过上海,“平津”构成了最重要的一对城市参照。封面女郎的“变脸”是最为直接的信号。仅以第八卷的五十期(1928年7月29日至11月21日)为例,来自京津的戏剧女明星、女学生和闺秀名媛占据了其中三十期的封面,达百分之六十之多,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画报首先要以封面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以达到“把杂志卖给读者和把读者卖给广告主”的双重目的,因此“封面宣告了杂志的个性特征、对读者的允诺,同时也宣告了它的目标读者”④[美]卡罗琳·凯奇:《杂志封面女郎》,曾妮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1页。。封面的大变动预示着《北画》注意力的转向和办刊方向的调整,“平津”无可争议地成为关注的焦点。
关于天津的想象和表达已在上文详细论述,值得注意的还有对“北平”的表述。《北画》上出现了很多有关“故都”的图文,代表作品有冯武越分上中下连载的《故都之行》和《日暮途穷之故都》,以及李尧生的“北平平民生活”系列摄影图片。其实“故都”、“旧都”已经暗示其中的微妙心态,时局造成的城市地位的巨大落差造成了市民中普遍的“怀旧”情绪,而且随着南京政府的执政日久,平津市民的失望愈深,早期对新的统一政府的期望很快被南北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现实所打破。《日暮途穷之故都》对北平冷清萧条现状的不满与追慕昔日的繁盛互为表里,而“北平平民生活”与迁都前著名画家陈师曾的北京风俗画内容相似,情感内涵却大不相同。它分别选取“卖酸梅汤者”、“缝补破鞋者”、“看西湖景者”、“卖大粽子者”、“卖山炭者”、“换洋取灯者”等北平街头平民为拍摄对象,街头风景依旧,但风土人情的浓郁趣味不再是表现的重点。这些照片的背景都被尽量忽略,人物得到极大的突出,他们皱褶的脸、破旧的衣裳,以及被重担压弯的身体,都带给读者沉重、疲累的观感,与北京风俗画的鲜明对比很容易触动“怀旧”的心事。
鉴于京津在历史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关系,不难发觉“故都”其实是天津的另类指涉,它就像一面镜子,最终还得返归自身。1930年在关于天津的影像中,有两张特殊的老照片,均由清末天津摄影师梁时泰所摄取,是中国早期时事摄影的代表作。其一为“庚子前十五年之天津海光寺中之后楼”,“右图为光绪丙戌年醇亲王检阅海军,抵津时驻节之海光寺后楼原景。楼上有乾隆帝宝座及其御笔封联。该楼于庚子年拳乱时毁于兵燹,今海光寺已成日人驻军之所,抚今思昔,能无感慨乎?此片摄于四十四年前,为摄影术最初流入中国时之创作,名贵非凡,不可等闲视之”⑤曲:《四十四年前之天津海光寺遗影》,《北洋画报》,1930年1月18日,第9卷第425期。。另一张是“中国前清之海军旧影”,“左图为四十四年前光绪丙戌岁,醇亲王抵津,检阅海军时舰队之摄影,悬帅字旗之船,即如今日之旗舰。船首醇亲王中立,原照甚大,尚隐约可辨,缩制铜版,则小不可识矣”⑥《中国前清之海军旧影》,梁时泰摄,《北洋画报》,1930年2月6日,第9卷第430期。。它们属于天津的“前台”时期,当时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天津在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上占据着重要而显赫的地位,北洋海军煊赫一时,慈禧太后于1885年特派醇亲王奕譞到天津巡视海军,由梁时泰负责摄影,这些照片因此进入宫廷,照片中的庄严气象正是对今日天津没落景象的无声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