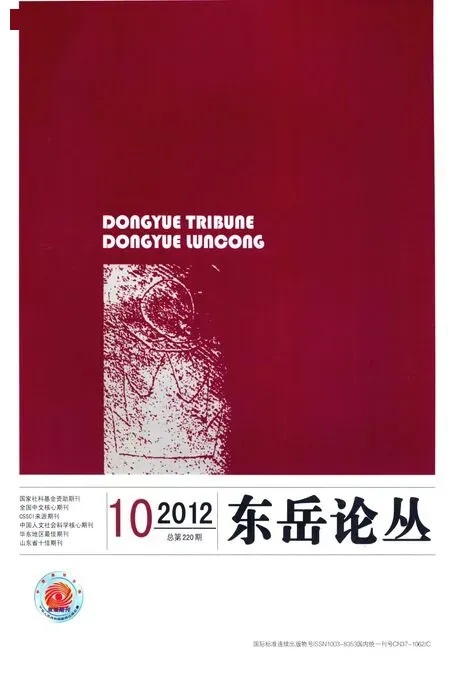实指定义与“私人语言”
孟令朋
(南京理工大学马研部,江苏南京 210094)
自维特根斯坦提出“私人语言”这一论题之后,就引发了无尽的论争,它已造就了一门“哲学工业”①程炼:《思想与论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今日繁难之局面,究其原因,是对近代西方哲学传统没有很好的反思。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曾言“哲学家处理问题就有如治病一般”②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节,第309节。,其关于“私人语言”的探讨就是一种“哲学治疗”,既然是“治疗”,那么就会有“治疗对象”。“私人语言”这一论题的“治疗对象”就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传统,笛卡尔、洛克、休谟的哲学均是其治疗对象。或许维特根斯坦对西方哲学史并不谙熟,但他“敏锐的批评抽空了传统西方哲学的基底”③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56页。,维特根斯坦通过这一论题揭示出西方哲学自近代以来在一个大关节上出了问题。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另一处,又言及:“(他的哲学目的是)给苍蝇指明飞出捕蝇瓶的出路”④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节,第309节。。如果以石里克的实指定义(ostensive definition)为纽带来探究,我们会发现休谟、罗素、石里克、艾耶尔的相关论证都是基于实指定义。倘若追随休谟、罗素、石里克、艾耶尔的相关思路,必定会困在“捕蝇瓶”中,直接导致“私人语言”这样一种想法的产生,其实也代表了一种许多人对语言的误解:语言要么指涉外部世界(external world),要么指涉内在经验(inner experience),外部世界与内在经验这样的提法相当粗糙,经不起推敲,并且恰恰在这里埋下了“私人语言”思路的种子:当语言用来指涉所谓的内在经验时,就会导致“私人语言”这样的想法。如果把所谓的“外部世界”与“内在经验”合称为实在(reality),当然这也是一种很不审慎的提法,那么这一误解的另一表达就是:语言指涉、描述实在。语言与实在的地位绝对不是平等的,实在并不信赖语言,语言反而要以实在为基础。维特根斯坦通过“私人语言”的讨论,提出与此截然相反的一种思路:不是语言依照实在,而是实在要依照语言,在语言与实在的关系中,语言才是重心,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探讨与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具有一致性,可以称之为维特根斯坦的“哥白尼式革命”。
一、石里克的实指定义
有人抱怨:维特根斯坦并没有足够清楚地说明“私人语言”概念包含着什么东西,“私人语言”意味着什么?⑤库克:《维特根斯坦论私人性》,马蒂尼奇(Maritnich,A.P.)编,《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87页。实际上,这完全没有跟上维特根斯坦的思路,私人语言是否存在以及如何界定私人语言是次要的,关键是维特根斯坦揭示了为什么会产生“私人语言”这种想法。从根本上来说,之所以产生“私人语言”这种想法,是因为对语言本身持错误看法,认为语言是建立在实指定义基础之上的,或者说语言的主要作用是用名称来指称某物。石里克认为实指定义是“用一个指明某些词的实际用法的行动来解释这些词。最简单的一种实指定义就是一个与某词的发音相联系的指点手势,例如我们教小孩‘蓝’这个声音的意义时,就指着一个蓝的东西让他看”。石里克也承认,一些语汇显然不能以这种简单的实指定义来定义,“我们无法指着一样东西,说它相当于‘因为’、‘直接’、‘机会’、‘再’之类的词。在这些场合,我们面前要求有某些复杂的情况(situations),用我们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使用这些词的方式,来给这些词下定义”。石里克的这种论证方式虽然符合常识,但极为粗糙,并遗漏了问题的关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开头就批驳这一观点,在这一问题的源头之处,石里克就搞错了方向。石里克认为实指定义是意义证实中最核心的原则:“没有一种理解意义的办法不需要最终涉及实指定义”①石里克:《意义和证实》,洪谦编著《逻辑经验主义》(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9-40页。。把实指定义叫做“指物定义”②“指物定义”是陈嘉映先生的译法。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6节。更贴切,我们作进一步区分,就会发现这种实指定义有两种形式,即所谓的“物”(或者说“实在”)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对象,另一种是内在经验(inner experience),“私人语言”的最根本的思想源头就在于以这种实指定义的方式来理解语言。艾耶尔与罗素的相关论证中应用的是实指定义的前一种,休谟使用的则是后一种。
二、语言指称外在对象——实指定义在艾耶尔、罗素有关论证中的运用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一开头就批评了以实指定义的方式来理解语言,这里的“物”是外在的对象。
奥古斯丁,《忏悔录》卷一第八节:当成年人称谓某个对象,同时转向这个对象的时候,我会对此有所觉察,并明了当他们要指向这个对象的时候,他们就发出声音,通过这声音来指称它。……。③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节。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多次明确提到实指定义,比如第 6、28、29、30、33、34、38、380 节,更多的地方并未点明实指定义,但实际上也是针对实指定义的。
艾耶尔与罗素并没有明确提到实指定义,但他们的相关论证都是基于实指定义展开。
1.在“私人语言”的讨论中,艾耶尔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况:想像一个鲁滨逊·克鲁索式的人,当他还是一个婴儿并且还没有学会说话时,就被孤身留在他的岛上。并假设他成长,他一定能够辨认岛上的许多事物,也命名这些东西。同样也可以设想某个未受到使用任何现存语言教育的人为自己编造一种语言④艾 耶尔:《可能有一种私人语言吗?》,马蒂尼奇(Maritnich,A.P.)编,《语言哲学》,牟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79页。。我们看到艾耶尔设想的,只有这个克鲁索式人物自己使用的“私人语言”完全是基于实指定义,这里的“物”是外在的对象。艾耶尔这个设想的前提是这种“私人语言”是建立在事物与名称的一一对应之上的,语言中的一个词指称相应的物。这个前提又假设了“一般的语言”也是基于这种指称关系,词与物的指称关系建立之后,无需别的条件,语言就形成了。
2.罗素认为世界包含事实,罗素认为这是一个“自明之理”,“显而易见”。罗素接着说,信念指涉事实,通过对事实的指涉,信念不是真就是假。“苏格拉底死了”这个信念之所以为真是由于很久以前在雅典发生的某一生理事件使然⑤罗素:《逻辑原子主义哲学》,《逻辑与知识》,苑莉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19页。。这一表述的潜在前提是指称论:“苏格拉底”与历史上的“那个人”建立起了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也可以算是实物定义的一种,虽然这个“人物”并不出现在面前。“世界包含事实”这个提法,看似“自明”、“显而易见”,但问题绝非这么简单明了。虽然,维特根斯坦前期也有类似的观点:《逻辑哲学论》中的“1.1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1.1,陈启伟译,《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但是,两人更多的是不同:“命题是实在的一种图象,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命题是实在的一种模型。”⑦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4.01。,命题是实在的图像与命题指涉事实的说法相去甚运⑧张祥龙:《当代西方哲学笔记》(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173页。。石里克与罗素的论证思路完全一致,石里克认为经验证实的可能性就是基于实指定义①石里克:《意义和证实》,第40页。,即名称与对象建立起指称关系,判断才能成为事实的标记,石里克举例说“雪是冷的”这一命题标记一个事实,其根基在于,雪的概念与白的、片状的、从天空飘落下来的物之间建立起了指称关系。
在艾耶尔与罗素的论证中,实指定义都起奠基作用,舍此,这两种诠释根本无法进行下去。维特根斯坦的评价是:
奥古斯丁没有讲到词类的区别。我以为,这样来描述语言的学习,首先想到的是“桌子”、“椅子”、“面包”以及人名之类的名词,其次才会想到某些活动和属性的名称以及其他词类,仿佛其他词类自会各就各位。②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节,第96节,第28-29节,第262节。
维特根斯坦的批评很到位:语言如果是简单建立在实指定义之上,那么各种词类如何能各就各位?如果各种词类能各就其位,那么必定有一前提:语言与外在对象或者说实在或者说所谓的世界是一一对应的,语言不过是世界的对应物:
思想、语言似乎是世界的独特对应物,世界的图画。句子、语言、思想、世界,这些概念前后排成一列,每一个都和另一个相等。③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节,第96节,第28-29节,第262节。
这实际上是石里克、罗素隐秘的理论预设。
在问题的根本处,石里克、罗素、艾耶尔的论证都有致命的漏洞,实指定义绝非石里克所言的那样“简单”,维特根斯坦认为,实指定义导致一种不可解的“死循环”:
我指着两个核桃给二这个数字下定义说:“这叫‘二’”——这个定义充分准确。——然而怎么可以这样来定义二呢?听到这个定义的人并不知道你要把什么称为“二”;他会以为你要把这对核桃称作“二”呢!
人们也许会说:只能这样来用指物方式定义二:“这个数字叫‘二’”。因为“数字”一词在这里标明了我们把“二”这个词放在语言的、语法的什么位置上。但这就是说要理解这个指物定义就要先定义“数字”一词。……。——于是我们又是通过别的语词来定义!那么到了这个链条上的最终定义又该怎么样呢?④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节,第96节,第28-29节,第262节。
三、休谟的感知论与内在的实指定义——“私人语言”的直接思想源头
实指定义的另一种形式中的“物”内在经验(inner experience),或者说心灵中的对象、心理体验、心理感觉,“私人语言”主要是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表面上,这与艾耶尔设想的克鲁索式人物使用的“私人语言”不一样,但究其根本,具有一致性。这个思路可以追溯至休谟:
人类心灵中的一切知觉(perceptions)可以分为显然不同的两种,这两种我将称之为印象和观念。两者的差别在于:当它们刺激心灵,进入我们的思想或意识中时,它们的强烈程度和生动程度各不相同。进入心灵时最强最猛的那些知觉,我们可以称之为印象(impressions);在印象这个名词中间,我包括了所有初次出现于灵魂中的我们的一切感觉、情感和情绪。至于观念(idea)这个名词,我用来指我们的感觉、情感和情绪在思维和推理中的微弱的意象。⑤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页,第19页。
一个印象最先刺激感官,使我们知觉种种冷、热,饥、渴,苦、乐。这个印象被心中留下一个复本,印象停止以后,复本仍然存在;我们把这个复本称为观念。⑥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页,第19页。
休谟在这里是含混过去了,他的论证过程必然依赖实指定义,而且这样的思路必然要求这种实指定义是在个体的心灵之中发生的,一种“内在的实指定义”(private ostensive definition)⑦维特根斯坦对此曾言:“你一再把舵打向一种内在的实指定义”,《哲学研究》第380节。,不是指向外物,而是指向某种私人的内心经验,“谁为语词给出了一个私有的定义,他现在就必定内在地(inwardly)决定要如此这般使用这个词。”⑧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节,第96节,第28-29节,第262节。比如某个人胃疼,那么这个人好象可以“指着”自己(在内心里)疼痛暗暗地告诉自己“这就是胃疼”,“我的确能够[内在地(inwardly)]下决心将要把这个称为‘疼痛’。”①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263节,第258节,第293节,第243节。按照休谟印象与观念的区分,这是印象,而“胃痛”的观念或者说“胃痛”一词的意义则是后起的,源自之前发生的印象。
维特根斯坦指出了这其中的背谬,其一:
我们来想象下面的情况。我将为某种反复出现的特定感觉做一份日记。为此,我把它同符号E联系起来,凡是有这种感觉的日子,我都在一本日记上写下这个符号。——我首先要说明,这个符号的定义是说不出来的。——但我总可以用指物定义的方式为自己给出个定义来啊!②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263节,第258节,第293节,第243节。
这种内在的实指定义的问题在于:把这种内在于心灵之中的感觉与这一符号E联系起来的标准是什么?“维特根斯坦反对所谓‘私人语言’,反对休谟提出的词的意义归根结蒂来自私人的印象或感觉材料的观点。如果每个人所使用的词的意义取决于这个人自己的印象或感觉材料,那么,不仅不同的人所使用的同一个词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甚至同一个人先后使用的同一个词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因为记忆往往是不可靠的。如果休谟的主张是正确的,就会出现每个人都在使用各自的‘私人语言’那样的荒唐局面。”③涂纪亮:《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页。
其二:
维特根斯坦《蓝皮书》中的一段:“人们可能说,思维是我们的‘私人经验’的一部分,它不是物质的,而是私人意识的事件。”④维特根斯坦:《蓝皮书》,涂纪亮译,《维特根斯坦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维特根斯坦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第一,思维与物理实在是不一样的,这一层区分比较浅显,可是这已经向错误方向迈了一步。第二,思维(或意识)是在心灵之中的,思维就与“私人经验”联系起来了。在这一层面上出现的问题就更隐秘了,心灵如同一个盒子,思维(意识)类似于装在心灵这个“盒子”里的甲虫。现在“盒子里的甲虫”是语词的意义,维特根斯坦以反证法的方式,揭示出其中的悖谬。
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盒子,盒子里装着我们称之为“甲虫”的东西。谁都不能看别人的盒子,所以每个人都说,他只是通过看自己的盒子时的东西才知道什么是甲虫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每个人的盒子里装着不一样的东西。甚至可以设想这样一个东西在不断变化。盒子里的东西根本不是语言游戏的一部分;因为盒子里的东西也可能是空的。我们可以用命盒子是这个东西去“约简”;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它都会消掉。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根据“对象和名称”的模型来构造感觉表达式语法,那么对象就因为不相干而不在考虑之列。⑤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263节,第258节,第293节,第243节。
按照“对象和名称”的模型来构造感觉表达式,或者说用实指定义的方式,把“疼痛”的意义与某种私人经验对象对应起来,仿佛我们是通过“疼痛”的感觉来定义“疼痛”这个词的意义,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如果我们是从每个人的内在经验来定义“疼痛”这个词,那么这种内在经验在语言游戏之中,就可以像“甲虫”一样消掉,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从这里我们会看到“私人语言”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如果把意义看作是心灵这样一个“容器”之中的东西,语言的意义是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的,加上另一条件:人与人的心灵不是透明的,那么我自己心灵之中的“意义”是不是只有我能理解?如果这样的话,这是不是一种“私人经验”(“私人语言”)?是否存在只有自己能理解而别人无法理解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所表达的含义只有讲话人能够知道,是指涉他直接、私有的感觉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263节,第258节,第293节,第243节。。即把语言的意义当成一种内心经验、心理上的感觉。
维特根斯坦的这两种论证采用的都是归谬法,不止如此,他还从正面作了回答,他以“疼痛”这种最为典型的“心理体验”为例作了分析。“如果你说我知道他疼痛,因为我看到了他的行为,但我知道我疼痛,是因为我感觉到它,这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我是从我的个人私人感觉中派生出像‘我的疼痛’这种说法”,这是不正确的⑦维特根斯坦:《感觉材料的语言与私人经验》,江怡译,《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我的疼痛”源于我的个人私人感觉,这种观点与休谟观念论如出一辙。
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是:
疼痛这样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有这些联系。(即是说:只有这样地存在于生活中,有这些联系的东西,我们才称为“疼痛”。)①维特根斯坦:《纸条集》,吴晓红译,《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33条、第240页,第534条、第240页。
只有在某种正常的生活表现中才有关于疼痛的说法。只有在更广泛的、特定的生活表现中,才有关于悲伤、喜悦的说法,如此等等。②维特根斯坦:《纸条集》,吴晓红译,《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33条、第240页,第534条、第240页。
你随着语言一起学到了“疼痛”这个概念。③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384节,第261节。
这种学习过程不是一种指称活动,不是去学习用“疼痛”来指称一种感觉,而是一种理解,是对一系列生活形式的理解。
四、维特根斯坦的“哥白尼式革命”
这两种形式的实指定义都是以“物”(或者说“实在”)为重心的,“物”分为外在对象与内在心灵之中的对象(私人经验),相比而言,语言的位置是次要的,语言的作用是用来指称某“物”,这完全是对语言的错误理解。
维特根斯坦批评了这两种形式的实指定义,我们对他的立场就清楚了:绝不能以所谓的“实在”为重心来理解语言,而要以语言为重心来理解所谓的“实在”,即要从语言的立场来看实指定义如何能发挥作用,换言之,实指定义看似能成立,它是建立语言的使用之上。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在讨论所谓的“私人语言”时,使用的都是“公共语言”中的术语、语词④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384节,第261节。,我们在使用“感觉”一词的时候,它已经是公共语言的一部分了。“私人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悖论,即使有“私人语言”,我们也只能用“公共语言”讨论“私人语言”,无法用“私人语言”来讨论“私人语言”,因为“私人语言”是无法交流的。因此要以语言为标准,而不是以感觉为标准。
从外在对象、私人感觉经验出发,恰恰是石里克、罗素、艾耶尔、休谟的思路,维特根斯坦关于“私人语言”的相关讨论就是对这种思路的“治疗”,因此,说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探讨蕴含了类似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不无道理。Dilman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哥白尼式革命”可以表述为:“我们的语言不是建立在我们通过感知与之发生关联的经验实在(empirical reality)之上的,恰恰相反,语言是我们生活组成的部分,我们又是过着一种使用语言的生活,语言决定了我们以何种方式与这种生活所涉及并由我们构想(conception)出来的实在发生关联。”⑤Dilman,Ilham:Wittgenstein’s Copernican Revolution,NY:Palgrave,2002,p10.施怀泽(Schwyzer,H)也认为,“无论是在康德,还是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关于思想和实在(thought and reality)的形而上学问题都居于其思想的核心”,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这种形而上学取向(metaphysical orietation)表现为对“思想和实在及其关系”的探究,“这也正是康德所言‘哥白尼式革命’观点的一部分,即实在的本性与思想的本性相符合,而不是相反”。“维特根斯坦对奥古斯丁语言指称论的反驳只不过是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一个示例(intantiation)”,概括说来,这就是语词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语词所指称事物本身的性质,恰恰相反,事物的本性取决于(相关的)语言的使用⑥施怀泽:《思想和实在: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形而上学》,宋志润译,《多维视野中的维特根斯坦》,张志林,程志敏选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第13页。。维特根斯坦关于私人感觉的讨论也表明了这一点,即所谓的私人的感觉“取决于我们可理解的说出的东西,取决于我们的语言游戏。这就是维特根斯坦对哥白尼式革命的肯定。”⑦施怀泽:《思想和实在: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形而上学》,宋志润译,《多维视野中的维特根斯坦》,张志林,程志敏选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第13页。
我们可以用“哥白尼式革命”来看待维特根斯坦的“私人语言”论证:不是语言依照实在,而是实在要依照语言。不是先有“疼痛”这一实在对象,然后用“疼痛”这一语词去描述它,而是相反,我们随语言一起学会了对“疼痛”的表达。
如果勉强使用“实在—语言”这一模式来分析,那么就“疼痛”这一典型的“私人经验”来说,我们或许可以区分出来“疼痛”的实在对象与“疼痛”的语言表达。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我们只能说脱离了疼痛的语言表达(或者说“意义”),我们无法理解疼痛的“滋味”(实在对象)。“疼痛”的“意义”(语言表达)是在先的,有了“疼痛”的“意义”(语言表达),我们才能把某种心理状态叫做“疼痛”。就好比一群人手中持有不同面额的钞票,这些钞票的“价值”或“意义”并不仅仅是由每个人持有的一张张纸决定的,而是由一个“价值”或“意义”体系决定的。也就是说,并不能从每个人的手中的钞票来定义何为钞票,而是要从我们现代社会生活方式、金融系统来理解钞票是什么。每个人的“疼痛”也许各不相同,但其中所分享的“疼痛”的意义是公共的,并且“疼痛”的意义是在先的,假钞为什么要做的和真币一样?它为的是能进入流通,取得像真币一样的“价值”,假钞并不仅仅是因为做得逼真而有“价值”,最重要的是假钞仿造得如同真币一样而披上与真币一样的“价值”。人们为什么能假装“疼痛”,没有“疼痛”这个实在对象,人反而能假装出来,这表明,作为实在对象的“疼痛”并不是重点所在。
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用“意义即用法”①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43节,第30节,第31节,第654-655节,第199节。来代替“实在—语言”这一模式更恰当,换言之,并不需要“意义”这一环节,并没有所谓的“疼痛”的“意义”。我们可以追问一下,小孩子是怎么知道“疼痛”的呢?比如当孩子第一次打针,当针头刺进去的时候,父母就说:“宝宝不怕痛,勇敢!”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会让他哭。当他伤到了手指,父母会说:“宝宝啊,痛不痛啊。”他学走路的时候大人告诉他,慢点走,会跌痛的。我们可以说类似的经历多了,他自然就“理解”了“疼痛”,这里并没有一个“疼痛”的本质,没有关于“疼痛”的定义,“疼痛”体现在一系列的情景之中,我们可以把这一系列的情景都称为“疼痛”,但其中的任何一种情形也不是“疼痛”的定义,我们是通过理解把这一系列的情形串起来的,把它们当成“疼痛”。
维特根斯坦又用“样本”来说明,“有人问我:‘疼痛是什么?’我就捏他一下。我是给出疼痛的样本。”②维特根斯坦:《感觉材料的语言与私人经验》,第229页。“样本”不同于指物定义,样本是让他来理解“疼痛”,而不是来定义“疼痛”。
五、实指定义之重新定位
实指定义是石里克、罗素、艾耶尔、休谟的立论基石,这是从外在对象、内在经验出发的必然要求,在他们看来,实指定义无须其它前提,是“自明”的。从表面上来看,实指定义也符合常识,我们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教儿童识物的,以致于艾耶尔、罗素的相关论证,根本无视这一环节。
把实指定义当作语言之基础,是本末倒置。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实指定义还须另一些东西支撑:“为了能够询问一件东西的名称,必须已经知道(或能够作到)某些事情。”③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43节,第30节,第31节,第654-655节,第199节。“只有已经知道名称是干什么的人,才能有意义地问到一个名称。”④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43节,第30节,第31节,第654-655节,第199节。
这种“哥白尼式革命”把重心转到了“语言的使用”、“语言游戏”之上。
我们的错误是,在我们应当把这些事实看作“原始现象(Urphänomene,proto-phenomenon)”的地方寻求一种解释。即:在这地方我们应当说的是:我们在做这一语言游戏。
问题不在于通过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一种语言游戏,而在于确认(Feststellung,noting)一种语言游戏。⑤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43节,第30节,第31节,第654-655节,第199节。
语言游戏是最为根本的东西,它无法再还原。我们确认一种语言游戏也是“一股脑、整个、全盘”接受下来的:“理解一个句子就是说:理解一种语言。理解一种语言就是说:掌握一种技术。”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43节,第30节,第31节,第654-655节,第199节。当我们指着某物以实指定义的方式教幼儿学说话时,他(她)已经对这种语言游戏有所“领会”,他(她)已经模糊知道这个物的名称是用来作什么的,也就是说,对语言的“前理解”是实指定义的基础,而不是相反。
实指定义展示出来这样一幅图像:人用名称(语词)指称对象,它把名称、对象与人的关系表达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就是在最要紧处,它已经遗漏了问题的关键,它把语言与人的关系简单化了。语言与人的关系远非这样“透明”,可以说人与语言的关系是“共氤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