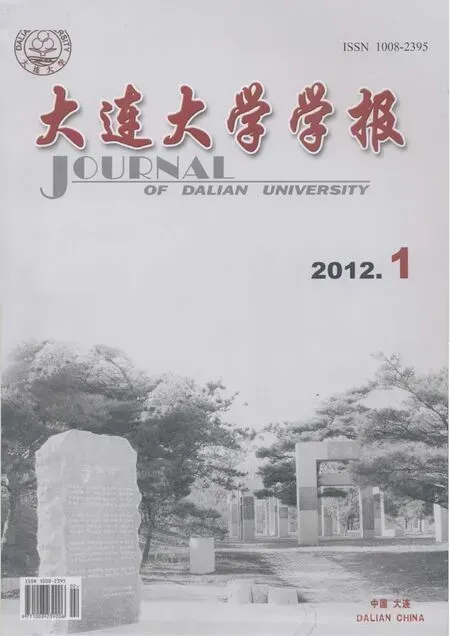清代中前期的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赵玉敏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部队管理系,河北 廊坊 065000)
清代中前期的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赵玉敏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 部队管理系,河北 廊坊 065000)
明清更替对传统的中缅宗藩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缅甸东吁王朝拒绝向清王朝臣服。直到乾隆时期,因内忧外患的加剧,才重新向清王朝入贡,其媒介就是边境地区矿丁吴尚贤的劝说。然而,1752年东吁王朝的猝死令新建立的中缅宗藩关系流产。中缅关系的发展演变,揭示了清代中前期双方国力对比和内外环境的变化,从根本上影响着双方的对外政策和宗藩关系。
政策;入贡;流产
学界将清代中前期的中缅两国政治关系作为叙述主体,并从宗藩关系的角度研究者并非很多。而且目前研究多集中在乾隆时期和1885年缅甸灭亡前后,对清代中前期的研究则相对不足。
以乾隆朝中缅战争及其有关问题为例,目前研究性专著有黄祖文《中缅边境之役(1766-1769)》。
另,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一书中对中缅战争曾单独加以论述。论文方面,国内主要有宁超《桂家、敏家及其与乾隆年间的中缅之战》、黄祖文《清代乾隆年间的中缅之役》、朱亚非《从中缅之战看清政府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杨煜达《清朝前期(1662-1765)的对缅政策与西南边疆》与《花马礼:16-19世纪中缅边界的主权之争》、庄吉发《清高宗时代的中缅关系》、山东大学任燕翔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乾隆时期清朝对缅政策述论》等。
国外主要有日本学者铃木中正《清缅关系(1766—1790)》与《桂家宫里雁和中缅战争》、美国学者Richard L.K.Jung:The Sion-Burmese War,1766-1770:War and Peace under the Tributary System、英国学者Ying Cong Dai:A Disguised Defeat:The Myanmar Campaign of the Qing Dynasty.
一些国外学者的通史性论著,对清代中前期的中缅政治关系问题亦多有涉及,如(缅)波巴信《缅甸史》、(缅)貌丁昂《缅甸史》、(英)G.E.哈维《缅甸史》。这些论著因所据史料多来自于缅甸,对中国古籍中的相关史料运用不足,故对有关问题的论述颇失于浮泛、谬误等。
一、清朝以前的中缅关系
中缅关系源远流长。公元前128年,就有了一条通过缅甸北部的陆路,中国的货物就是沿着这条道路经过印度运往西方的。公元97年和公元120年,罗马帝国的使者两次沿着这条道路来到中国。
随后,中缅经济、文化交流一直不断,至唐代,中缅双方在经济、文化方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休戚相关的紧密关系。缅甸学者貌丁昂即言:“骠人的最后衰落、南诏的侵袭、中国唐朝的崩溃都发生在九世纪下半叶,这些事件打乱了东南亚的贸易,破坏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力量的平衡。上缅甸的动荡不定使得缅甸、中国和印度之间的陆上贸易陷于停顿,也影响了穿越阿拉干山区的陆路贸易和沿着伊洛瓦底江的水路贸易。”[1]23
宋元之际,元朝在实施其全面包围南宋基本战略的过程中,因对中缅边境地区一些部落与人口控制权的争夺,曾与缅甸蒲甘王朝产生矛盾,自至元十四年(1277年)三月始,双方一度发生军事冲突。
1468年缅甸东吁王朝建立以后,在以军事统一缅甸的同时,对周边部落尤其是北方诸部也施行了军事征服政策。而明王朝云南地方政府因为对中缅关系的认识不足,在有关问题上决策接连失误,更加纵容了缅甸方面的军事行动。自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以后,因为缅甸方面接连出兵云南顺宁、盏达等地,中缅双方遂开始进入长期的军事冲突状态。明军在刘綎、邓子龙等将领指挥之下不断击败缅军,与此同时,明云南巡抚陈用宾为加强防务,乘机在腾越州西北至西南边界筑建八关,包括神护关(今腾冲县西北孟卡山上)、万仞关(盈江县西北布哈山上)、巨石关(盈江县西北息马山上)等。稍后,缅甸因为进攻暹罗的失败,与在北方对明王朝军事行动上的失败,陷入内外交困的处境中。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前后,中缅战事基本停止[2]6389。
清军入关,南明桂王政权抵抗无效而流落入缅。缅甸方面对之先恭而后倨,并大肆杀戮随行诸臣,永历君臣形同罪囚。对此,明清遗民多有记载,如客溪樵隐《求野录》、自非逸史《也是录》、戴笠《行在阳秋》等。随后,李定国、白文选等多次入缅解救永历皇帝未果,吴三桂又乘机率军入缅以武力逼迫缅甸俘献永历父子,南明桂王政权灭亡,而缅甸东吁王朝因为接连受到军事冲击,加之其国内统治方面的一些问题,亦随之而走向衰落,清王朝中前期的中缅双方遂长期未发生正式的官方接触。
二、清朝初期以来的中缅关系与对缅政策
明清易代,清王朝在承袭明朝正统的同时,也力图继承其原有的朝贡体系。
顺治四年二月,清军刚刚平定浙东福建一带,顺治帝即宣布“东南海外琉球、安南、暹逻、日本诸国,附近浙闽,有慕义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3]251同年六月、七月,又接连两次颁布诏令,招徕琉球、安南等国。
同年六月,清军平定福建,顺治帝再次颁布诏令:“谕琉球国王敕曰:朕抚定中原,视天下为一家。念尔琉球自古以来世世臣事中国,遣使朝贡,业有往例。今故遣人敕谕,尔国若能顺天循理,可将故明所给封诰、印敕,遣使赍送来京,朕亦照旧封锡。谕安南、吕宋二国文同。”[3]267
七月,清军平定广东,顺治帝又谕:“南海诸国,暹罗、安南附近广地,明初皆遣使朝贡。各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朝廷一矢不加,与朝鲜一体优待。贡使往来,悉从正道,直达京师,以示怀柔。”[3]272
在清王朝的上述诏令中,不难发现,惟独少了一个国家――缅甸。对缅甸与明王朝的藩属关系,清王朝并非一无所知,但因种种缘故,清王朝还是在有意无意中对缅甸――这个远在西南一隅的国家予以了忽视。
缅甸第一次正式走入清王朝的眼中,是在14年后。因为清军的强大攻势,南明永历政权残余势力最终败退入缅。清军将领吴三桂为了消除后患,率领大军入缅追杀。对此,《清史稿》记:“顺治十八年,李定国挟明桂王硃由榔入缅,诏公爱星阿偕吴三桂以兵万八千人临之。李定国走孟艮,不食死。缅酋莽应时缚由榔以献,遂班师。”[4]14661
清王朝与缅甸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却是以一种兵戎相见的方式。在擒获永历皇帝后,清王朝并未责成缅甸像安南、朝鲜一样加入其朝贡体系。时隔多年,中缅战争中的乾隆皇帝曾有诗云:
缅甸南赢裔,于古朱波是。赵宋宁宗时,一通中国始。元明数征讨,叛服亦云屡。宣慰仍土酋,羁縻而已矣。其时谁最悍?哒嘛莽瑞体。考其所侵轶,陇川界迄通。厥后明桂王,逃缅延喘哆。世庙宣索之,献出遵挥指。缅则置度外,遐荒非所取[5]534。
清王朝未曾乘机迫使缅甸称臣纳贡,部分原因或许是鉴于缅甸与历代中原王朝的复杂关系。而顺康之际,清王朝正忙于平定东南沿海一带的抗清势力,也根本无暇顾及与缅甸的关系。
但清王朝对中缅关系的忽视,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中缅未能就边界划分、沿边土司及其辖地的归属等问题进行商讨,并迅速予以妥善解决,从而为后世所出现的双方边界冲突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埋下了伏笔。其后参加了中缅战争的赵翼即不无遗憾地记到:“是时三桂未及为善后计,边外木邦、孟密、大山诸土司听其仍为缅属,不复能如明初之众建而分其势,由是缅甸竟国于西南。”[6]732
另一方面,“缅自是不通中国者六七十年。”[4]14661在长时间内,中缅双方相互认识不足,彼此缺乏了解。清人师范即言:“迨至顺治十八年,(缅甸)莽猛自立,戕永明王君臣,自是不通中国者六七十年。雍正七年,与整卖构兵,求进贡而不果,盖百十年来,中国几不知有缅甸矣。”[7]728
因为吴三桂的入缅行动,清王朝一度注意到了缅甸,并产生将缅甸拉入其朝贡体系的念头。康熙元年“十月,议赏缅酋,三桂奏罢之。”[8]但议准缅甸贡道由云南。
其后,清王朝忙于巩固统治,且与西北准噶尔长期处于军事对峙状态,其国家政策的重心并没有放到东南边境。缅甸则因南明军队的进攻而渐趋衰弱,亦无暇顾及中缅关系。故至雍正朝中后期,中缅基本上再无官方往来。
乾隆帝即位初期,继承了清初以来的此种对缅政策,即尽量保持中缅之间相安无事,避免发生任何可能的直接冲突。乾隆十四年,当缅属木邦土司请求称臣纳贡时,清王朝即以木邦自明末以来已经归属缅甸为借口,予以拒绝[9]604。
又,乾隆二十二年云南巡抚刘藻奏:“至开化、普洱、永昌等府皆与交趾、南掌、缅甸为邻。年来外夷内讧,多有自相攻击之事。然距内地甚远,不足致问。惟在严饬文武员弁,于沿边要隘,加谨防范,则边民安堵,中外肃清。”对此,乾隆帝朱批:“此见果认得真,行得力,何愁不治。”[10]1084可以说,正是在此种对缅思想的指导下,中缅之间才会在长时间内保持了一种虽缺乏接触,却又相安无事的状态。
三、东吁王朝中后期的缅甸及其对清政策
东吁王朝中后期的缅甸,已经危机四伏。恰在此种情形下,发生了南明桂王入缅事件。据《明史·朱由榔传》记:“明年(顺治十六年)正月三日,大兵入云南,由榔走腾越。定国败于潞江,又走南甸,二十六日,抵囊木河,是为缅境,……五月四日,缅复以舟来迎。明日,发井亘,行三日,至阿瓦。”[2]3653
其后,李定国、白文选等相继入缅试图迎回永历帝,但缅甸方面对永历帝“阳款之而阴拘之。李定国率兵入,欲护王以出奔。莽应时弗与。”[8]由此,明军与缅军发生冲突[11]991。其后,明军一路向阿瓦进发,但因种种客观因素而未能成功。在其后两年中,明军一直出入缅甸不断。
明军接连不断的进攻,以及东吁王朝在处理相关问题上的失误,对缅甸国内政局产生极大影响,“以致其国陷于极端混乱之状态中。”[12]240“国王平达力在绝望中向马都八强征兵员,但是不仅遭到反对,而且激起了叛乱。”[1]131
顺治十七、八年之际,因明军到来,阿瓦城内再次发生恐慌。“粮价高昂,100元钱才能买到3缅升米,士卒们得不到粮食,上奏缅王说奴等已两三天没吃上饭了。然而得到的是已无粮可发的回答。缅王让宫女们在皇宫西门内称卖粮食,而部下们无钱买粮,都在挨饿。”[11]995在此情形下,缅军将领遂联合王弟卑明在1661年发动政变。
为尽快摆脱明军的进攻,卑明政府很快转变了在处理永历帝问题上的态度。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当吴三桂与爱星阿率领清军前来追击永历帝时,缅甸方面立即派遣“缅相锡真持贝叶文降于三桂,愿送驾出城,乞王师退驻锡箔,而别遣兵百人进兰鸠江捍卫。戊申(初三日),缅酋执明桂王以献于王师。”[13]770
其后,卑明政府即集中精力平定南部白古人的叛乱。当清军入缅追讨桂王政权时,白古人就已经图谋叛变,“擒马都八太守,遣使将其解至阿瑜陀耶京,求(暹罗)那莱皇予以保护,并助之以抗缅君。”[12]245
其后,白古叛乱虽被平定,但缅甸未能恢复往昔的繁荣与安定。“缅甸王国已经精疲力竭,贸易也受到损害。”“国王和人民都隐约预感到他们王国的末日快要来临了,但最后的灾难到底来自何方,他们却不清楚。”[1]131
在此种情形下,缅甸对外政策遂发生变化,逐渐呈现出一种闭关自守的色彩:一方面,其结束了自莽应龙以来与暹罗的长期战争,“缅暹息争,共历九十余年之久。”[12]245并且,暹缅双方在长期内基本断绝了官方往来,直到1744年。
另一方面,其对中国的政策亦发生重大转变,试图与中国保持一种不相往来却相安无事的状态。对此,《清史稿》记:“顺治十八年,李定国挟明桂王硃由榔入缅,诏公爱星阿偕吴三桂以兵万八千人临之……缅酋莽应时缚由榔以献,遂班师。缅自是不通中国者六七十年。”[4]14661
18世纪初期,缅甸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缅甸西北部的曼尼坡人“侵袭缅甸领土,直达阿瓦对面的实阶城。”为了抵御曼尼坡人的侵袭,缅甸不得不将大量军队布防在伊洛瓦底江西岸。鉴于此,“居住在首都附近的桂掸人趁机宣布他们的首领为缅甸国王,与附近的孟人联合起来,制造骚乱。”[1]132
1733年,缅王达宁格内死于曼尼坡人的侵袭,其子摩诃陀摩耶娑底波蒂继位,并于次年迁都阿瓦。其后,各地叛乱此起彼伏,东吁王朝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在此种情形下,东吁王朝遂逐渐转变其原本所奉行的与邻境诸国不相往来的政策,开始主动地寻求建立友好的周边关系。
对其宿敌暹罗,在1744年,缅皇遣使至阿瑜陀耶京――百年来是为首次――向暹罗国君波隆摩葛皇表示谢意,因为他在白古人发动叛乱时,对逃入暹罗的缅甸平民和官员都给予了妥善的安置。暹罗方面对缅甸使节给予隆重接待。在1746年,当暹罗使者抵达阿瓦进行友好回访时,亦获得缅方同等热烈的欢迎[12]300。
与此同时,缅甸对中国的态度也开始转为积极,几次遣使请求入贡,表现出一种建立友好政治关系的渴望。雍正八、九年间,缅甸与景迈土司发生争斗,缅甸曾一度宣称要在次年向清王朝入贡[4]14661。
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将此上奏,雍正帝朱批:“极好之事,此皆卿代朕宣猷之所致,但总宜听其自然,不必有意设法诱致。”[14]但不知何故,缅甸使者却最终没有派出。此举令雍正帝君臣极为不快。雍正十三年,镇康土司刀闷鼎禀报缅酋愿通职贡,云南地方政府予以拒绝[15]113。
缅甸方面似乎仍未死心,“乾隆十三年,缅甸差喇札达等订贡前来,……明年,缅甸复差来边。”[9]604对此,出于种种考虑,清王朝方面最终仍未同意。但中缅接触已是历史的必然,故在时隔3年后,便发生了东吁王朝的入贡与吴尚贤事件。
四、吴尚贤与缅甸东吁王朝的入贡始末
据载:“吴尚贤者,石屏州民也,家贫走厂,抵徼外之葫芦国。其酋长大山王蜂筑信任之,与开茂隆厂,厂大赢。”[7]728大发横财之后的吴尚贤在中缅边境地区极为活跃,力图对中缅双方产生一定的影响。乾隆十年,吴尚贤劝说葫芦国王将茂隆银厂献给清王朝。[4]14662但此次献厂似乎未能达到吴尚贤的个人目的。事隔几年,终于又发生了吴尚贤劝说缅甸入贡事件。
据缅甸官修史书《琉璃宫史》记载:“是年(公元1751年,乾隆十六年)中国皇帝派遣埃都耶、冬达耶等偕随从5000余人带着九尊阿巴达亚梵天佛像,为了结盟通好而来。缅王安排他们驻于玛瑙仰曼花园接见。中国人也表示愿对桂家、孟人的野蛮行径进行镇压。缅王表示不打算劳请友邦出师,只愿友好。埃都耶、冬达耶等表示虽然不需让我们去攻打,但贵邦国主之敌,即我主之敌也。让我等5000人去攻桂家、孟军。结果未能取胜,缅王派出使节随埃都耶、冬达耶等返回中国。”[11]1107
缅甸方面所记的此次中缅双方遣使互访事件,虽未见中国官方记载,但据昭梿记:“(乾隆)十五年正月朔日乙巳,……吴尚贤带练兵一千二百余人前赴缅甸。”“丁未,自干猛起程。庚戌,至木邦,木邦令头目猛占等八十余人从之。丁巳,至锡箔,庚子,至宋赛。”“贵家头目宫里雁,素与缅甸有隙,因率兵阻之。吴尚贤至麻里脚洪,又遣人致书讲和,贵家羁其来使,吴尚贤遂会缅兵三千余人至德岭城与贵家数挑战。三月庚戌,贵家出迎敌,诈败,吴尚贤前赴之,为贵家所败,缅甸复遣人和解之,……尚贤意欲邀功,因谋说缅酋莽达拉遣使入贡。”[15]114
如果推测无误,缅方所记埃都耶、冬达耶两人之一,当即为昭梿所记茂隆银厂吴尚贤,而缅甸方面将吴尚贤的前往误记为清王朝的正式使节。但是,无论如何,由于吴尚贤的媒介作用,缅甸东吁王朝终于向清王朝第一次派出了正式使节。乾隆十五年七月,吴尚贤禀称:“缅甸国王莽达拉情愿称臣纳贡,永作外藩。”[15]114
在接到吴尚贤的禀报后,云南政府曾召集有关官员进行了一番讨论,最终大多数官员认为:吴尚贤“今率缅甸来归,实有邀功之意,且外国归诚,亦断无借一厂民为媒进。将来缅甸设有寇警,必另求援兵,不应则失统御之体,应之则苦师旅之烦,恐鞭长莫及,反难善处。况前明频通赋贡,受侵扰者数十年,我朝久置包荒,获宁谧者百余载,边境之敉宁,原不关乎远人之宾服。”[15]115
但云南巡抚图尔炳阿却单独将此事上奏。乾隆十五年七月,乾隆帝下旨同意缅甸入贡[10]1078。
十二月初十日,缅甸使节由边入关,抵达蒙化府;十二月二十九日,抵达云南省城;乾隆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启程赴京;六月十一日,乾隆帝谕:“向来苏禄、南掌等国入贡,筵宴赏赉俱照各国王贡使之礼。所有缅甸贡使到京,一应接待事宜,亦应照各国王贡使之例,以示绥远怀。”[16]552
六月二十五日,缅甸使节抵达京师,并觐见乾隆帝,进贡物品为:毡缎四、缅布十有二,驯象八。皇后前驯象二[17]827。鉴于缅甸第一次入贡,乾隆帝对缅甸国王和使节进行了超乎寻常地厚赐:赐国王蟒缎、锦缎各六匹、闪缎八匹,青蓝彩缎、蓝缎、素缎、绸、纱、罗各十匹……加赐国王御书“瑞辑西琛”四字,青白玉玩器六、玻璃器十有五种共二十有九件,瓷器九种共五十有四件,松花石砚二方,法琅炉瓶一副,内库缎二十匹;贡使内库缎八匹,银八两[17]865。
七月二十一日,缅甸使节离京南返。其正使希里觉填于十月初六日在贵州安顺毛口驿途中病逝,其余人员在十月十九日抵达云南省城,二十六日离滇回国,云贵总督遣人护送至耿马土司地方,又令耿马土司转送至缅属木邦土司。缅甸东吁王朝的第一次入贡活动结束。
就东吁王朝而言,因其已处于统治中后期,故一方面希望与清王朝“各守各界”,“不愿内地弁目涉伊境界。”[10]534另一方面也渴望能够将双方关系进一步推向睦邻友好状态,以巩固其国内统治。而此次遣使入贡的成功,无疑标志着其长期以来力求打破中缅隔阂,并正式建立两国友好关系目标的实现。
对清王朝而言,缅甸方面的此次入贡,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缅宗藩关系的建立,标志着其天朝上国的地位获得承认和受到尊重,更预示着其西南边疆政策和对缅政策的巨大成功,乾隆帝和整个清王朝似乎都在一种踌躇满志的喜悦中看到了中缅关系的光明前景。
但随后历史的戏剧性变化令清王朝失望了。乾隆十六年冬,就在缅甸使节还至云南顺宁府地方时,传来了缅甸方面发生叛乱、东吁王朝最后一位君主麻哈祖兵败被囚的噩耗。东吁王朝与清王朝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友好的政治性接触,因东吁王朝的猝死而中途流产。清王朝曾经的希望在一瞬间又全部化为泡影。因种种缘故,缅甸新兴的贡榜王朝,也无暇顾及中缅之间的关系。加之中缅之间缺乏了解,故直到中缅战争爆发前,清王朝与缅甸新兴的贡榜王朝之间始终未曾发生任何官方的正式接触。
小 结
在乾隆朝中缅战争之前,尽管中缅之间的民间经济、文化交流也始终没有中止,但是,在政治和外交上却基本维持了一种交往不多却又相安无事的关系。甚至是在乾隆初期吴尚贤引荐缅甸东吁王朝主动入贡的过程时,清王朝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也是一种热烈欢迎中的理性谨慎态度。这种情形的出现,可以说,既是清王朝长期以来对缅政策与西南边疆政策的具体内容之一,也是其对缅政策和西南边疆政策的具体影响之一。这种防御性的友善的政策对西南地区的安定和发展,对促进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着积极作用。
[1][缅]貌丁昂.缅甸史[M]贺圣达,译.昆明:云南东南亚研究所,1983.
[2]张廷玉.明史(刘綎·邓子龙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清世祖章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赵尔巽.清史稿(属国三·缅甸)[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李根源.永昌府文徴(一)[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6]赵翼.平定缅甸述略[M].魏源全集(第十七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
[7]师范.缅事述略[M]//魏源全集:第十七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
[8]刘健.庭闻录:附录·平定缅甸[M].上海:上海书店,1985.
[9]明清史料.庚编·第七本[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0]庆桂.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琉璃宫史(下)[M]李谋,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7.
[12][英]W·A·R·Wood.陈礼颂译.暹罗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13]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57.
[14]朱批谕旨:第56册[M].雍正八年十二月十七日,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奏,光绪内务府刊本.
[15]昭梿.啸亭杂录(缅甸归诚始末)[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乾隆朝上谕档:第二册[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
[17]清会典事例(礼部·朝贡·贡物一)[M].北京:中华书局,1991.
[][]
On the Relationship of“Suzerainty and Vassal”Between China and Burma in the Early&Middle Qing Dynasty
ZHAO Yu-min
(Department of Force Management,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 AcademyLangfang,Hebei 065000)
The subrogation of the Qing and Ming Dynasties had a deep impact on the suzerainty and vas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Burma.The Toungoo Dynasty refused to pay tribute to the Qing Dynasty until the Qianlong period when it su ff ered from domestic troubles and foreign invasions.The Toungoo Dynasty started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Qing Dynasty then through Wu-Shangxian,a miner working at a border region.However,the sudden perish of the Toungoo Dynasty in 1752 put an end to the new suzerainty and vas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Burma.The evolution of China-Burma relationship revealed that the di ff erence of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had an important e ff ect on their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uzerainty and vassal relationship.
policy;Pay tribute;abortion
D829.12
A
1008-2395(2012)01-0025-05
2011-10-09
赵玉敏(1982-),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部队管理系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清代政治史、边疆史等研究。
基金课题: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SZ2011606)“晚清中缅宗藩关系对西南边防建设研究的启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