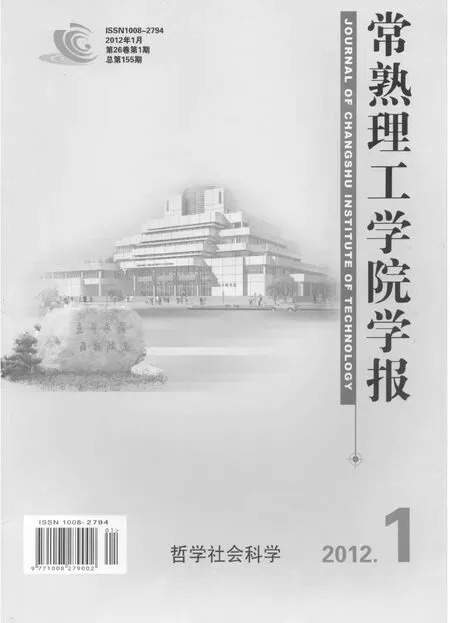汉代经学意识形态化路径探析
黄海涛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昆明 650091)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化路径探析
黄海涛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昆明 650091)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是通过经学思想政治化和经学信仰大众化两方面实现的。经学政治化是从思想到制度再到结果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即统治思想经学化、通经入仕制度化、官僚队伍儒生化。经学大众化主要通过儒生信仰和创造推动统治者的信仰、政治威权和禄利诱惑推动官吏的信仰、经学教育和政府奖进推动知识分子的信仰、教化和风俗推动庶民的信仰而实现。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路径
一、引言
儒家学派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挫折和秦王朝“焚书坑儒”的打击后,艰难地存留下来。儒家学派尽管得不到新生汉王朝的重视,但汉儒们并没有放弃复兴孔教儒学的努力,他们通过对经义的再诠释和具体应用使之适应了现实的需要,从而获得了统治者的支持。“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1]1——经学,在汉武帝时正式确立,并从此成为儒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讲,两汉时为政权名义上所独尊的学说并不是儒学的全部,而仅仅是阐释经典的经学。甚至连经学也没有立即被政权全部认同,从公羊到榖梁,从今文经到古文经,历经两汉,经学才基本为政权接受。汉武帝以后,经学渐趋与政权各个部分结合,最终成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思想,被称为两汉的意识形态。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化,主要集中在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和儒生的推动两方面。作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经学必然同时被政权支持和大众信仰,因此把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仅仅归结为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有失偏颇。陈劲松指出,两汉时期,儒学意识形态化并非一蹴而就,它主要包括“以吏为师”意识形态的终结,“独尊儒术”政策的提出,以及儒学的法律化运动等相关进程。[2]黄清吉认为,儒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是逻辑与历史共同推演的结果,儒学自身逻辑一致的理论品性,与中国传统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及专制王权的内在契合,是其国家意识形态化的根本成因。[3]经学意识形态化的原因不仅在于它符合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需要,也在于它顺应民风满足民众的情感需求,得到社会群体的认同和服从,并使所有人适应这种主流文化支配下的社会生活。
经学意识形态化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是经学思想在官方的认可下成为一种合法的结构性力量,即经学思想政治化;二是经学教义深入人心,从而为社会各个阶层所认同,即经学信仰大众化。
二、经学思想政治化
政治化使得经学可以合法地参与政治现实的建构,但经学的政治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时,经学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被完全地政治化。汉代经学的政治化历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
(一)统治思想经学化
经学成为汉王朝的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高祖刘邦本不喜儒生,史载“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4]2105-2106但经过“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4]81,他对儒学的态度有所改观,这从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一月“过鲁,以大牢祠孔子”[4]76可以看出。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挟书之律”废除,诸子百家开始了一个复兴的阶段。但由于秦汉之际的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汉初统治者以黄老思想为统治思想,实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加之当时的公卿将相大多是草莽英雄,不喜儒术,所以儒家思想一直得不到重视。
汉武帝即位时,经济开始繁荣,同时国内外的矛盾日益尖锐,于是汉王朝开始推行积极有为的统治政策。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室立五经博士,诸子百家皆被罢黜,经学获得了官方独尊的地位。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一统天下,汉代统治者并没有因为儒学独尊就完全奉行儒家思想,如汉宣帝明确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4]277
经学真正成为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观念体系,则是在汉元帝时期。早在为太子时,元帝就向其父宣帝提出改变统治思想,摒弃霸术,改用儒术。“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4]277但元帝遭宣帝斥责,太子之位也险些被“明察好法”的淮阳王取代。元帝即位后,开始实施他“任德教”、“用儒生”的主张,大规模培养和任用经学之士,经学到此才完全成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正如皮锡瑞所说:“汉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5]67
(二)通经入仕制度化
汉初制度草创,选官制度也呈现多样化特性,多种选官途径并行,如察举制、征辟制、任子制、资选制等。但这些制度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譬如察举制,自高祖以后到武帝即位的五十五年中,仅诏举贤良二次,选举孝廉二次。实际上官吏的选拔已被封建诸侯、军功贵族垄断,汉初朝廷公卿和地方二千石长吏几乎全是直接从封建诸侯、军功贵族中举任。这种贵族垄断世袭制不利于举贤任能,军功贵族对文化的缺乏和轻视也不利于建设知识型的政府。
汉武帝时,汉室在采用察举制、征辟制、任子制、资选制同时,又增加太学养士制和公车上书自荐制。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兴建太学,置“五经”博士,“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6]3119。汉初察举有贤良、孝廉两科,武帝增设四科,其它各种制度在整个选官制度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察举制和太学养士制成为两大基本选官制度,而太学养士制和察举制中的明经科皆直接以经学作为选官依据。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郎吏制度,察举制和太学养士制这两大基本选官制度有机结合成完备的整体,成为两汉定制。
太学在武帝时还很狭小,仅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宣之时,规模逐渐增大,昭帝时增至百人,宣帝时二百人;元帝时,博士弟子更是激增到千人规模。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就授以相应的官职。同时,察举制和征辟制等选官途径也与经学紧密联系起来,征辟和察举的对象多为经学之士。就像当时学者夏侯胜所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4]3159可见读经做官已成为当时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通明经学也成为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依据。
(三)官僚队伍儒生化
汉初以黄老道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上自皇帝、公卿,下至曹掾小吏,多修黄老道家之学。除汉高祖外,汉初诸帝均学过黄老之术,这对官吏群体的构成影响极大。同时,汉初也存在着大量出身法家的官僚。由于秦代“焚书坑儒”的打击和汉初诸帝对儒学和儒生的排斥,同一时期跻身政坛的儒者极少。但是,王朝的建立又离不开礼制制度的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一些儒者因此被聘为博士、礼官或帝王师、傅,叔孙通与其弟子便因制定朝仪进入朝廷。这些儒者为官僚队伍的儒生化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独尊儒术,兴办太学,儒学成为官吏选拔的主要依据,官僚队伍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6]3119-3120。据统计,这一时期文化状况可考的公卿中,儒家学者占其总数的45.1%,居各家之首。但由于历史原因,武帝时黄老道家仍有很大实力,并且由于国家政治事务的实际需要,法家的官吏也占有很大比例。因此,无论从构成还是从统治思想来看,武帝时官僚队伍都有“霸王道杂之”的特点。
汉武帝之后,历代君王均以儒者为师,文化取向、政治行为和个性人格都受到极大影响,如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4]298-299。《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列出元帝时期中央官员50人,出身事迹可考的31人中,经学之士17人,占54%以上。汉元帝时期,地方长吏中的经学之士也占绝对优势,成为地方官吏的主体。元帝时中央和地方官吏儒生化的完成,既是经学对行政的影响,又为进一步扩大经学影响提供了保证。[7]330
三、经学信仰大众化
儒家学者对“经”具有万世法典的神圣意义一直深信不疑,并且对其功用和意义做出了诸多演绎,以便于向世人推销,最终获得官方认可。而汉武帝对经艺的表彰使得“经”的神圣性合法化,其功能和意义也随之大大拓展。虽然汉武帝对经学的推崇并没有多少信仰包含在内,但其后的汉代帝王们对经学的信仰却是逐渐加深,这些表彰和信仰使得经学具有了诱人的政治利益,推动了官吏和士民的经学“信仰”。
(一)汉代皇族经学教育与经学传播
在汉初的上层社会里,儒学的地位不如黄老之学,虽然刘邦开皇帝祭祀孔子之始,但统治阶级思想的主流依然是黄老思想。这种现象到景帝时出现了转机,宗室子弟开始由儒士教育。武帝自小接受经学教育,也是其崇儒的重要诱因。武帝以后,对皇子的经学教育几成制度。昭帝幼年即位,有儒臣蔡义、韦贤等进授《诗》;宣帝曾“受《诗》于东海澓中翁,高材好学”[4]237,“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4]238,并亲自召开石渠阁会议;元帝“柔仁好儒”,并认为宣帝持刑太深,建议用儒生。成帝、哀帝也都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东汉自光武帝开始,皇帝及皇族不但大多受过经学教育,并且亲自参与讲经和撰写经学著作。“皇帝与皇族及上层社会阶级的儒学教育,促进了政府对儒学的提倡,并影响了当时的文化政策”[8]52,同时也极大影响了政治活动。
皇帝接受经学教育的结果是,从汉武帝之后,经学逐渐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依据。由于禄利的诱惑,传授、研习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史称“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6]3118。汉初制度,无功者不得封侯,如今读经不仅可以进入仕途,而且可以封侯拜相,于是经学大为昌盛,全国上下一片学经之风。班固评论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馀年,传业者寖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馀万言,大师众至千馀人,盖禄利之路然也。”[4]3620
(二)儒士群体与儒生化官僚对经学的传播
儒士群体在推动经学的大众信仰尤其是博得统治者的认同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其中最主要的是通过修改、完善自身学说来适应统治者的需求。在汉武帝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士充分吸收墨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子学说,改造传统儒学,成就了以公羊学为代表的经学独尊的地位。到西汉末年,经学又跟谶纬结合,经学成立之初的神秘化趋向变成了现实,这虽然是思想发展的一个歧途,但这种神秘化的经学却迎合了帝王统治和人民迷信两方面的需求,成为东汉经学获得更大范围传播和更大程度信仰的重要因素。此外,两汉儒士群体的私学教育与游学之风,也促进了经学的散布。
自西汉中期以后,官僚队伍儒生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这些具有官员身份的儒士(即循吏)在推广经学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汉代循吏接近基层社会,更容易推行儒家教化、普及经学知识,他们自身以经入官也是宣扬经学价值最好的例证。同时,循吏们希望建立礼治或德治的秩序,在日常的司法过程中,也多援引经义以为依据,这便是流行于两汉的“春秋决狱”。此外,代表政权对践行经义行为的奖进也是循吏推广经学的一个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地方建立了完善的官学组织,而“地方官学在推进礼乐文明,风化乡里,其作用不可低估”[8]81。
(三)渐完备的经学教育体系与经学传播
太学兴办于武帝时,得力于董仲舒与公孙弘。董仲舒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4]2512,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由丞相公孙弘拟定具体方案,正式建立太学。后来太学规模逐步扩大,成帝时博士弟子增至三千人,后汉更是多达三万人。郡国学始于景帝末蜀郡守文翁“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4]3626,武帝时令天下郡国效仿兴办,到平帝时下令县、乡、聚也设立学校。东汉时,学校教育更加发展壮大,中央除太学外,还有为皇亲国戚开办的宫邸学,地方上除郡国学外,县有校,乡有庠,聚有序。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教育体系,连遥远的边地也普遍开办了学校,以至“四海之内,学校林立,庠序盈门”[9]1386。
由于武帝时才确立官学制度,汉初的教育几乎全由私学维持,从事私学教育的主要是治经的儒者,如叔孙通、伏生、申公等。汉武帝以后,官学体系逐步建立,但渴求读经的人日益增多,这些官学难以满足庞大的需求,大部分的教育工作仍然由私学承担。到了东汉,官学教育的弊端日益显露,普及经学教育的任务更加繁重,因此私学继续发展。此外,家庭教育也对经学传播产生很大影响,两汉出现很多“累世经学”的大家族,他们各专一经,进行家族内部的经学传授,影响很大。
(四)风俗与基层社会的经学传布
经学与基层社会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民间风俗上。中国自古为礼仪之邦,礼仪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代基层社会的礼仪和风俗正是从上古三代春秋战国一直流传下来的。汉代民间的婚姻礼仪基本是《礼记》中“六礼”的损益,家庭伦理中也有浓厚的经学色彩。两汉时期盛行招魂、沐浴、饭含等葬俗,其中不少是源于儒家经典的。如招魂的仪式,就是基本按照《仪礼·士丧礼》、《礼记·礼运》、《丧大记》所说进行的。当时所使用的敛具、敛衣、铭旌等丧具,所进行的出殡、治丧等活动,所制作的随葬器物等,也大体与三《礼》所记相合。[10]329此外,两汉之时尤其东汉,复仇之风盛行,而这又与儒家经义《春秋》、《礼记》、《周礼》中的复仇之义密切相关。民间风俗与儒家经义内在的契合性,使得经学在基层社会的传布成为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四、结语
两汉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一些做法和精神,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譬如建构能发挥积极建设性的社会历史功能并且富有感召力的意识形态;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使其更加契合广大人民的情感;深化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更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当然,时代不同,标准不同,我们要坚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和道德建设更好地发展。
[1]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中国经学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2]陈劲松.两汉时期儒学观念的意识形态化及其路径[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2).
[3]黄清吉.儒学国家意识形态化的成因探析[J].湖北社会科学,2004(1).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秦汉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夏增民.儒学传播与汉晋南朝文化变迁[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9]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张涛.经学与汉代社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Exploring Approaches to the Ideology of Confucian Classic Studies in Han Dynasty
HUANG Hai-tao
(School of Humaniti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91,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deology of Confucian classic studies in the Han Dynasty is achieved through both the politicalization of thoughts on Confucian classics studies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its faith.Its politicaliza⁃tion is a continuous process from thought to system and finally to the result,that is,ruling ideology becomes Con⁃fucian classic studies,approaches to political career institutionalized while bureaucratic officials Confucian schol⁃ars.Its popularization is mainly through scholars’faith and creation in promoting rulers’faith,political authority and the temptation from fame and fortune to promote the officials’belief as well as the educ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 studies and government’s rewards to promote the intellectuals’belief.Its political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are inseparable and they mutually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deology of Confucian classic studies in the Han Dynasty.
Han Dynasty;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ideology;approaches
K234
A
1008-2794(2012)01-0089-04
(责任编辑:顾劲松)
2011-07-03
黄海涛(1986—),男,河南信阳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汉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