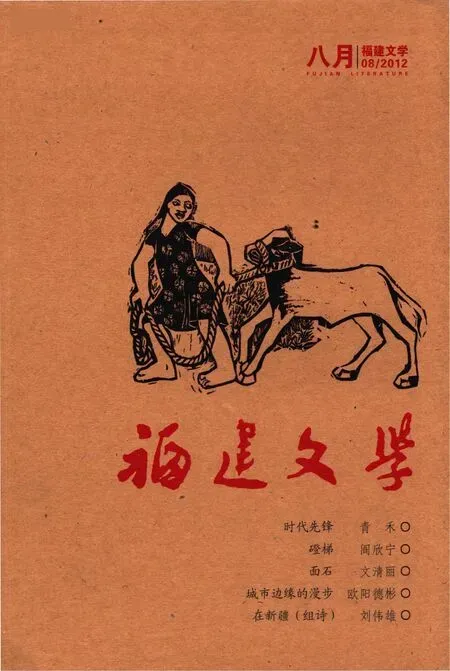多义性文本和寓言化写作——解读陈毅达小说《赃犬》
叶砺华
任何小说文本皆具有多义性,故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过这种情形是对阅读群体的集合描述,若就单个读者的阅读状况而言,可供进行多层面、多向度阅读的文本,应当说为数并不多。陈毅达的中篇小说《赃犬》(载《福建文学》2012年第4期,《中篇小说选刊》2012年第4期转载)之所以可归于多义性文本之列,是由于它选取了独特的叙事对象和叙述视角,以及作家采用寓言化写作方式所构成的诸多隐喻,使小说文本具有了多重释读的可能。
从最直观的层面,《赃犬》可以解读为官场小说:它叙述一只特种犬的奇特经历和一个官员的命运沉浮,借此讽喻公权力的某种私化现象,从中不难读出小说的反腐意义。这样的常规解读不能说毫无深刻性,只是过于轻松和简化,把作家赋予文本的丰富意蕴给轻易忽略掉了。
笔者以为更应当把《赃犬》解读为世情小说。小说中的黄副市长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其地位和尊荣令常人艳羡,但他处在官场层级分明的夹层中间,并非可以为所欲为,他有很多忌惮,如他想藏富不露,弄了一只警犬来看守乡下老屋,不料正是此举导致其最终落马。如果我们把人物身份的外延扩展,将黄副市长置换成某位乡村暴发户或都市豪亨,那么故事的逻辑展开和结局可以不必有太多出入和变化,这样小说文本意义的涵盖面就远远逸出官场之外,“黄副市长”也在更大范围内成为一种类型的象征,《赃犬》便可解读成一种世风的隐喻。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小说对黄副市长并非采取直接描写,而是通过叙述一只特种犬的经历来对其进行间接描写,这只名叫“行者”的特种犬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小说也因此有了独特的叙事对象与文本结构。饲养宠物是当代生活具有浓缩意义的样本,从中可透视出当代人物质层面的奢华和精神层面的空虚。当这种风气发展到极致,便有了警犬基地的李副队长在即将退役之时,为了今后到地方上能混出个人模狗样,冒险将刚出生的“行者”违规带出基地,送给黄副市长作为铺路之礼,这便是整个故事的起因。故事的最初导演是人,人为动物提供了表演舞台,但“行者”不是听话的演员,它只依照名犬后代的优良基因行事,于是故事越往后发展,它越摆脱人的掌控,以一系列自发的忠勇行为,无意间使黄副市长、李副队长等陷于难以自保的境地,并暴露出冷漠自私的面目,从而勾画了一幅人欲横流、道德滑坡的现代世情风俗画。
以动物的行为反观人的行为,这是《赃犬》独特叙事产生的强烈隐喻效果。我们从文本中看到,人与动物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价值错位。狗本能地做好事,它发现一老人发病困于屋内,便去找小区保安设法救助;它目睹女子钱包遭飞车抢夺,便勇猛追击擒获歹徒。然而每当狗做好事,它的主人就很不高兴,就莫名恐慌,因为担心偷狗一事败露影响其前程。被毛教授估值三百万的“行者”,当被媒体捧为“英雄”和“明星”之后,还是免不掉遭主人嫉恨抛弃的命运。小说中描绘了种种世相,无不具有荒诞色彩:李副队长为巴结黄副市长演出了献狗一幕,不料最后却马屁拍到马腿上,遭到黄副市长唾弃;“李大师”借给黄副市长算命之机骗钱,他的算法本属荒唐结果却不幸言中;陈白露想找丈夫回来处置“行者”,却要仰赖“行者”的寻人本事才找到丈夫,不料又意外揭开丈夫金屋藏娇之谜。小说巧妙地借毛教授之口评价“行者”:“它不随意地认主,这说明它品正;它不曲意地逢迎,这说明它品高;它不与普通的犬类合群,这说明它品贵。”“行者”的行为印证了这一评价是中肯的,然而教授说这番话目的不是赞狗而是要与黄副市长套近乎,教授的媚术也是一种奴性的流露。这些皆使小说具有很强的荒诞感,其中又隐含了作家的伦理、道德及社会价值判断。这是《赃犬》的深刻独到之处。
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推演,还可把《赃犬》解读为生态小说:它是对人类生态和地球生态的复杂隐喻。动物与人相比,无疑更接近原生态,它身上的大自然本性体现得更充分,而人却经过了自身创造的文明的后天改造,一旦这文明发生畸变,人也就被改造成了“非人”。我们不妨这样思考:当尼采喊出“上帝死了”,结束了人对大自然崇拜的时代,伴随人的个性解放与独立,物质主义和享乐之风逐渐盛行,人性中自私贪婪的一面得以不断发酵膨胀,这加速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加速了人的异化。以工业革命为发端,催生了以欧、美为首的富人世界,对这个星球肆意挥霍索取,它们是奢侈之风的源头。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又被后发展国家广泛复制,演变为更加激烈的资源、财富争夺,掀起造富炫富的狂潮,国家、地区、人群的贫富分化愈演愈烈,自然生态遭受空前劫掠,人们有理由担心这个蓝色星球已经岌岌可危。动物不如人,人是动物效仿学习的对象,这是人类的习惯思维。但在《赃犬》中则相反,人不如动物,要向动物学习。这种大胆的比照,是对万物之灵的揶揄,是对人类文明生态与自然生态危机的忧患,是呼唤人的价值和自然本性的回归,是一种道德与灵魂的自我救赎,其中透射出可贵的思想之光与批判锋芒。
以上多重解读虽然带有阅读主体的主观成分,但又都能从文本中找到依据。概而言之,主要是源于《赃犬》以动物为叙事对象和运用动物视角的寓言化写作方式。小说的寓言化写作和寓言本身不同,前者往往具有很强的现实色彩,不像寓言那样完全采用荒诞或拟人化手法。《赃犬》中运用了多种叙述视角,有作者的全能视角,对小说中的人与动物进行一种全景式观照。有以小说中的人物为视角,如黄副市长、陈白露、李副队长、黄尼龙,从他们的眼光看人与动物,表现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评判。这些视角无疑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仅运用动物视角,小说中大量的现实性描写就无法进行,小说的现实感就会大为削弱。不过小说中最有意味的还是运用了动物视角,即从“行者”的视觉、嗅觉及心理感受角度来观察、评判人的行为,借此提供了另一种观照世界的视角和态度,这是非寓言化写作所无法达到的。为了完成这一角色使命,作家将他笔下的动物“行者”塑造成一只特立独行的狗,它不谄媚,极少奴性,没有被人驯化和奴化,具有真正的狗性也即自然本性,它在狗中显得孤独,但也因此它具有独立的眼光和判断力。小说中“行者”凭借嗅觉可以判断人的身份和秉性,如它嗅出黄副市长的手味,“有一点油墨味,一点茶水味,还有点尿臊味”;嗅出黄尼龙身上的汗味,“是总爱吃动物肉类和油腻食品,又开始进入青春期了,但汗腺发育有缺陷的男孩,才会散发出的。”在人们看来习以为常甚至趋之若鹜的事情,如对金钱、地位、名誉的攫取,对富足奢侈生活的追求,换了“行者”的眼光去看却显得很可笑。在“行者”眼中,它所置身的现代都市社区,缺失的是“空旷的原野,或是常年积雪的高山,以及荒无人烟的森林”。自然界的本色失落了,人类的自然本性也就失去了。写实主义加寓言色彩,使《赃犬》既可读出很强的现实意义,又可探寻出诸多隐含的深刻寓意,它构成文本的多义性,并以文学陌生化手段,建构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有必要加以辨析的是,小说运用的并非纯粹的动物视角,寓言化写作不过是人对动物、植物等的想象和模拟,是人的视角的巧妙物化,究其实质还是运用人的思维,使用的也是人的语言文字。这样的例子在《赃犬》中俯拾即是,如“行者”超强的是非判断能力,未经训练而与生俱来的现场施救能力等,显然加入了作家的主观意愿与想象色彩。再如刚出生的“行者”第一次见到黄副市长时,就看出他“戴着一副德国原装进口的镀金眼镜,一套浅灰色的法国古琦西装”;第一次走进黄家时就看出客厅里“摆放着用印尼花梨木制成的仿古家具”,“后阳台是通透的钢化玻璃落地窗”等,也是把人类的知识和语言安放到了动物身上。再迟钝的读者都能看出这是作家有意而为之。这在寓言类作品中不会构成问题,因为寓言的假定性远远超过小说,寓言中的一只虫子一棵草都可以说人话做人事,但小说中如果也这样那就近乎古代神异小说或现代魔幻小说了。《赃犬》显然既非神异小说也非魔幻小说,那么作家对“行者”的高度拟人化处理,是可能使小说的真实性受到影响呢,还是更强化了寓言化的讽喻功能呢?小说的寓言化写作在运用动物视角进行叙事时,是应当更接近动物性呢,还是允许更多地拟人化呢?就笔者所知,目前为止的小说创作理论尚未就这一问题进行过专门探讨,更未给出结论。《赃犬》作者也许无意中触及了小说创作的一块新的领地,这本身或许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赃犬》的意义在于:它在写实的同时融入了更多表现主义成分,独特的叙事对象和叙事方式,多种叙述视角的综合运用,寓言化写作对隐喻、象征、荒诞等现代小说手法的巧妙汲取,使文本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意蕴和内在张力,这些皆表明作家的文体意识已更加自觉,这种重要的创作蜕变或许可视为作家在创作上步入成熟的一种标志。
- 福建文学的其它文章
- 那些光鲜和隐痛——说说赖妙宽小说《城里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