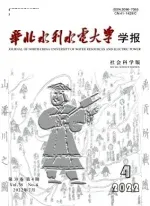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时代的黄淮水运①
王 琳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52)
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如果以20世纪20年代末安阳殷墟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为起点,那么时至今日已断续进行了近一百年的时间。这一个世纪来的学术成果越来越有力地证明了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中国早期古代文明的起源、发展都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产生并发展的。但随着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海岱、辽西及其周边地区,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华南、西南等地区的古代文明面貌又被不断揭示。系统研究这些区域内的文明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区差异,而且更能帮助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全貌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因此对于文明起源的地区差异及其相互关系的系统梳理,无疑会推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这一富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向纵深推进。在近一个世纪的学术实践中,我们的研究视野虽已聚焦于祖国境内的灿若群星的文明差异,但唯对于淮河流域古代文明起源的认识缺乏更深层次的探讨,这一方面的研究或可谓空白。那么在文明起源时代淮河流域与黄河流域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如何评价淮河流域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文明起源时代的黄河和淮河流域不仅没有被隔绝,而且是可以通过水运相联通的。《禹贡·导水》说:“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顾颉刚先生认为:“古淮水自桐柏山东流,经今河南桐柏、信阳、罗山、正阳、息县、光山、潢川、固始,至三河尖入安徽境,又东经颍上、寿县、凤台,又东北经淮南市、怀远、凤阳、五河、泗县入江苏境,又东经盱眙,为洪泽湖所汇地,又东北经洪泽、清江市、泗阳、涟水、阜宁等县市间,又东北入于海,就是《禹贡·导淮》‘东会于泗、沂又入于海’的故道。”在这里顾先生特别提及了泗水、沂水在沟通淮河流域交通方面的价值,《禹贡》中所说的淮水故道中泗水、沂水是淮河两条大的支流。而泗水、沂水两水,在《禹贡·九州·徐州》中又有详尽的阐述。按《禹贡》所说,沂水在泗水之东,下游在古下邳汇入泗水,而泗水又向东南最后注入淮水,因此沂、泗两水又可并视为一条入淮的大水,所以《汉书·地理志》说“(沂水)南至下邳入泗”。可今天的沂水并不入泗,可见古今河道差别很大。
《禹贡》在言及徐州通中原的贡道中是讲,自淮河的中下游向黄河流域去,贡物必须通过泗水。按《水经注》所说,古泗水出今山东泗水县北山,西南过今山东曲阜、滋阳、邹县、济宁市,荷水自西来注之,又东南过江苏沛县、铜山、邳县南入于淮。这是《水经注》中记载的河道,今天看来泗水的流向大体作南北向,泗水自铜山以上至济宁市一段虽是古河道,但已无遗迹可循,铜山以下即淤黄河故道。泗水尽管出自今山东泗水县一带,但泗水在南流时却有一条东西流向的荷水注入其中。《水经注·泗水注》上又说荷水自菏泽分流,东南经今山东金乡、济宁市入于泗水,而荷水是自济水分出的支流,所以《禹贡·导水》上说“东至于荷”。这样通过荷水,泗水便相联通了济水。既然荷水是自济水分出,而济水分黄河的地方是在荥泽,所以《禹贡》说济水“入于河,溢为荥”。因此,我们由《禹贡》徐州的贡道可知在文明起源时代,从自然地理角度来看,黄河与淮河的关系是淮通泗、泗通荷、荷通济,而济水出于黄河。也就是说,地理意义上的黄河与淮河是相通的,但后来,随地理环境的变化,黄河与淮河之间这一套相互沟通的水系已荡然无存。
二
除了《禹贡》上所讲以外,《水经注》中也记载了一套古水系,证明历史上的黄河与淮河也是相通的。《水经注》中记有鸿沟水系,鸿沟水系也是自黄河向东南分出的一条古水系,这套水系中有两条河间接入淮,有三条河直接流入淮河。鸿沟水系中的汳水也叫获水,即后来的汴水。其在彭城注入古泗水,而泗水是入淮的,这是间接入淮的一条。鸿沟水系中还有睢水,睢水在沂泗水的下游注入其间,从鸿沟水系中来看,获水、睢水是两条间接注入淮河的河流。鸿沟水系中还有三条水直接注入淮水,即涣水、阴沟水(即涡水)、狼荡渠。涣水虽已不复旧闻,但阴沟水即今天的涡水在安徽怀远注入淮河,其入淮之处被称为涡口,其地今日犹在。除涣、涡两水外,从鸿沟分出的狼荡渠其价值犹大。狼荡渠是自汴河分出以后先入颍水,而后从颍入淮河。颍水入淮河之处至今仍称颍口,在今阜阳颍上县,也就是《水经注》中所说颍水入于淮的“颍水之会淮也”。由此看来,古代黄淮之间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黄淮平原东部的沂泗水系和西部的鸿沟水系,沟通了黄淮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的传播。
三
由黄淮间的水系构成来看,文明起源时代的黄淮交通主要是通过东部的沂泗——淮河水系和西部的颍汝——淮河水系来完成的,因此这两大水系成为黄河、淮河两大流域间古代文明传播的地理基础。就这两条通道而言,山东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以及后来的岳石文化的传播很可能借助了沂泗通道。以大汶口文化为例,皖北、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与汶泗河流域的大汶口、大墩子类型关系密切,尉迟寺遗址出土的陶尊(臼)上刻画的图像文字与沂沭河流域的陵阳河等遗址出土的极其相似,可能昭示着它们之间具有某种特殊关系。这方面学者已多有论述。但皖北、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也给予了汶泗河流域类似制陶技术等方面的强烈影响,建新、西康留、西公桥、六里井、泗洪赵庄等遗址出土的篮纹、绳纹的鼎和罐等器物或可说明这个问题。至于这个时期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因素也是经皖北、豫东大汶口文化传播或以此为主体直接交流过去的。安徽中南部和江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联系也是以皖北大汶口文化为中介的。这说明中原、山东地区的古代文明的南传,很可能借助了沂泗通道。而西部的颍汝通道对于黄淮间文化的交流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视。就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时间而言,目前从考古学上能够将中国文明社会形成说清楚的只有二里头文化。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一直是中国早期国家起源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对二里头的研究不仅关系到夏人和夏王朝,而且更关系到中国古代国家和文明的形成。二里头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从二里头文化来看文明起源时代的黄淮关系,则似乎更能说明淮河流域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历史地位。就鸿沟水系中最西的狼荡渠而言,狼荡渠是注入颍河的,颍河又向东南注入淮水。在颍河的上游的嵩山脚下,有禹都阳城,而且在登封发现了登封王城岗遗址。遗址时间是龙山晚期,已到了夏代纪年之内。登封王城岗也就是禹都阳城,这一淮河流域距今4 000年以前城址的首次发现,实际上拉开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大幕。更有价值的是在颍河入淮向东不远,蚌埠西部涂山南麓就有“禹会村”。禹会村的由来按《左传》所记是“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也说“夏之兴也以涂山”。据说禹会村遗址是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在淮河流域唯一的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禹会村遗址是研究中华文明早期在淮河流域的起源与发展及其环境关系的重要资料。禹会村还发掘了大型人工堆筑的“T”形夯土台,该遗址的功能是大型祭祀和重要仪式的举办的场地,这也可能是和“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等相关。这样以淮河及其支流便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文化链。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安徽江淮地区的寿县斗鸡台、青莲寺,霍邱小堌堆、洪墩寺、楼城子,含山大城墩,肥西大墩子,肥东吴大墩等斗鸡台文化中,其中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物有陶鼎、深腹罐、盆、瓦足盘、爵、觚、豆、瓮及铜铃等,分别见于二至四期。不仅如此,包括在苏南、上海和浙江的江浙地区,二里头文明有江苏江宁点将台,丹徒团山,上海闵行马桥,青浦金山坟,金山查山、亭林,浙江象山县塔山,江山肩头弄等。宁镇地区的点将台、团山遗址所出二里头因素遗物有带按窝的侧装扁足鼎、三足盘、豆、觚等,分别属于点将台文化(或称“点将台下层文化”)和湖熟文化早期,年代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前期。太湖流域的马桥、金山坟、亭林及宁绍平原的塔山和浙西南的肩头弄遗址等地二里头因素遗物均属于马桥文化或其地方类型,器类有盉、觚、觯、三足盘、豆、盆等。发掘者将马桥文化分四段,其一、二段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至四期,三、四段相当于商代前期,而二里头文化因素是马桥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这说明二里头文化很可能是顺颍河而下,再沿淮水向东,然后再越过淮水,进入安徽的江淮地区,再经安徽江淮间越过长江进入宁镇地区和太湖流域,再南传至浙江等地区。以前我们对淮河流域在中国国家产生中的历史地位认识不够,现在看来,淮河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不仅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而且中国古代早期南北文明的起源及其空间上的扩散和传播都借助了淮河及其支流,如果此推论不误,那么淮河流域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应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