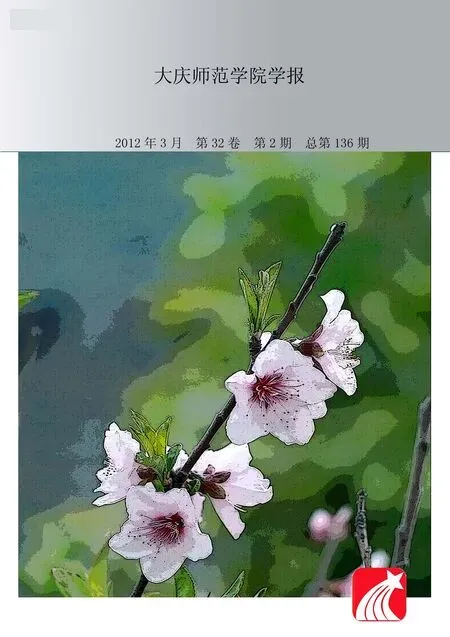晚清上海城市社会控制的近代化
黄杰明
(嘉应学院 梅州师范分院,广东 梅州 514721)
社会控制是将某一区域的社会(人们和人们的组织)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和机器的某种控制机制一样有其控制系统,在这个系统下,有机体的各个部分相互之间进行信息的交换和反馈,从而使有机体或其某些部分改变自己的运动状态和进入各种状态,使各个部分之间保持平衡,使有机整体向前发展。
上海城市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有机的社会整体。晚清上海城市社会控制系统开始从传统模式向近代模式变迁,这个变迁是上海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社会控制系统的近代化是指社会控制的制度化、组织化和规范化的过程。在上海,这个过程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头十年,已经显示了近代化的明显趋势,但离近代化的真正实现还相差很远,不过也已经为民国时期的进一步近代化奠定了基础。这个变迁的原动力是上海自身发展的需要。上海自开埠以后,近代工商业开始兴起,人口和建筑不断增加,近代的城市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如治安、户籍、卫生、街道、房管、税收、消防,等等,因此需要对城市进行系统管理。近代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的传入,促使了上海官民意识的革新与开放,对于城市管理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要求。在一些开明绅士和官僚的推动下,借鉴租界的现有控制模式,上海城市的社会控制开始了迈向近代化的步伐。
一、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上海华界的传统控制模式和租界近代控制模式的并存
1.华界的传统控制模式
上海开埠以前是一个小县城,人口不多,经济的繁荣也不能与开埠后同日而语。在县署衙门的上级,还有道署衙门。道署的长官是道台,是驻治上海的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的一种普通的称谓。但官书史著对其称呼不一,约有十种:沪道、巡道、兵备道、苏松道、苏松常道、苏松太道、江海关道、关道、上海道[1]。
上海道台是上海各方面的首脑,职责繁多,如治安、关税、外交、洋务、学校、开埠造路等均由其兼管或任总办。
治安是上海道台的职掌之一,没有专门的治安机关。本来分巡苏松道就是为巡查盗案而设的。1725年,巡抚张楷的上奏中说:“该道系为巡查盗案而设,驻劄苏州。臣细思上海远在海隅,更为宵小出没之地,盗案最多。若委该道经理关务,移驻上海,不但关税得有专责,并可办查奸匪,似于地方更有裨益。”[1]该道移驻上海是在1730年巡抚尹继善的奏请经清廷报批以后。尹奏中说:“分巡道有巡缉之责,兵民皆得治之,靖加兵备衔,移驻上海,弹压通洋口岸为便。”[1]另外,上海县尉、巡检也掌理盗贼、奸宄事宜。可见,上海传统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重叠交叉,职能不明确。
而且,传统的管理体制对市政方面的建设是无所作为的,关于清道、路灯、筑造桥路、修建祠庙、举办团防等事项,均归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经办。消防也一直是地方人士自办,组织救火会,每月开支经费均由地方救火会向地方商店、厂栈、居民分配征收,称为救火月捐。[2]整个晚清时期,上海消防事业都处于各自为政、缺乏统一指挥、自生自灭的民间自办状态。这是由于传统的“回避制度以及地方官的频繁调动等制度方面的限制削弱了地方行政的管理效能,地方官府除注重于税收与治安外,很少能对其所辖城市的发展有所作为,而将部分行政管理职能留给地方社会,但却缺少制度化的、吸纳本地居民参与地方政治的途径”[3]。
太平天国以后,上海出现了专门的治安机构巡防保甲局,它是在清廷于战乱后对地方行政大加整顿,推行传统的保甲制度,颁布保甲章程的情形下设立的。总巡由上海道委任。总局设在城中,初在沉香阁,后迁入县署旁常平仓内。下设九个分局,城内东、西、南、北各设一局,城外北新泾、引翔港、虹口、浦东等处,先后设五局。局中员弁,由驻防军营拔充。[4]巡防保甲局并不是近代的警察行政机关,仍属于传统的保甲制度,军警不分。
各行各业均有商人自己的组织进行管理。这些组织可分为两类:一为会馆,一为公所。前者属于同乡的集合,后者属于同业的集合。同业的未必同乡,但同乡的多半同业。晚清时期,这些组织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还保持着封建社会部落经济的形式;另一方面,职业类别的划分已经相当严密。[5]会馆和公所的董事均为有名望和地位的绅商,他们是推动上海社会控制走向近代化的最重要的力量。他们积极推进上海的地方自治,组织自治机关和自治的研究团体,使地方自治得以实现。绅商除有会馆和公所的组织外,还有自己的武装保卫力量——商团。
另外,一些苦力行业、小商业如码头、人力车、倒粪、渔市等,和一些非法行业如烟毒、赌场、扒窃、人贩、走私等,是帮会和流氓控制的范围。[6]
民间控制力量的强大是传统控制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而绅商则是民间控制力量的主要部分。
在华界仍处于传统控制模式的时候,租界已开始形成了近代的控制模式。
2.租界近代模式的形成
租界的意思,并不是中国政府将一个地方的界内土地整个租给外国政府,再由外国政府将这界内土地分租给外国侨民,只不过容许外人在一定范围内以私人资格租地居住。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软弱、外国政府的霸道、条约中规定的领事裁判权以及最初的华洋分居制度,使得租界事实上成为外人控制的地盘,中国政府无权或极少有权进行管辖。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外人能在租界按照自已的习惯或制度组织社会控制系统。而这种系统的形成,对相邻的华界传统控制模式向近代模式的转变起着不可估量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英、美、法三国租界分别创设于1845年、1848年和1849年。租界的人口、面积是逐渐增加的。公共租界方面,据工部局(公共租界的行政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1870年,华人为七万五千余人,洋人为一千六百多人;1880年,华人为十万七千余人,洋人为二千二百人不到;1895年,华人为二十四万余人,洋人为四千六百多人。[7]英租界的面积,1846年为138英亩,两年后即达470英亩。美租界,1893年面积已达1309英亩。1899年,公共租界面积达5583英亩(等于中国33000余亩)。[8]随着人口、面积的增加,经济的繁荣,房屋、道路建设的增多,治安、消防、税收问题也随之产生,于是,近代城市社会控制模式开始在租界形成。
1854年,小刀会进占上海县城,英、法、美三国领事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一起组织了“工部局”,共同管理三个租界。接着由工部局组织巡捕,聘请曾任香港巡捕房职员的克列夫登为总巡。“巡捕”只是中国人的翻译,外人称为警察(policeman)。警察制度是近代产生的,这一制度有自己的组织体系,有明确的职责范围,有自己的活动经费和专职的警察。工部局第一年度的预算,巡捕方面占总数的五分之三,约为一万五千元。[9]1855年4月,英、法、美和工部局都签字允准巡捕为常备。
后来法租界脱离工部局,于1862年创立公董局。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工部局便成为公共租界的行政机构。
公董局经历了由领事委任董事→领事直接主持公董局→选举董事的发展过程。公董局设立之初由领事委任董事8人,后来董事与领事不和,遭到领事的解散。1865年10月后,有八九个月由领事主持公董局,这是一个过渡时期。1866年7月,领事正式颁布《公董局组织法》,采用选举法选任董事。由委任制到选任制,是一个向民主发展的过程。
董事会下有八个委员会:工务、财政、卫生、交通、医院管理、地产、教育和园艺。公董局下属的各处有市政管理处、医务处、警务处、救火会、公共卫生救济处等。[10]这些处的设立并非同时,公董局各职能部门的完善也是逐步进行的。
法租界脱离工部局后,拟组织自己的巡捕房,在1856年召开的地主大会上,法国领事提出了这个要求。第二年正式成立了巡捕房,有巡捕12名。公董局成立后,巡捕房归该局管辖,由董事会委任驻沪法国退伍军人龙德为总巡,捕头增至4名,巡捕20名。[9]至此,法租界的警察制度基本确立。
公共租界的纳税外人会是工部局的监督机关。会员资格为符合下列任一条件者:(1)所执地产价值在五百两以上;(2)每年付房地捐项在十两以上;(3)每年付房租在五百两以上而付捐者。纳税外人会的会议分两种:年会和特别会。年会每年举行一次,讨论通过预算和决算、通过捐税以及选举地产委员1人。特别会则临时以特别事故召集,讨论批准工部局所定的附律、商议与租界内大众相关之事。[11]可见,纳税外人会是外国有产阶级对租界进行控制和管理的一种民主政治形式,是公共租界的最高权力机关。
工部局的行政对纳税外人会负责。董事会是工部局的权力机关,最初只有5名董事,后来陆续增加。外国董事由纳税外人会直接选举,董事的当选有一定资格:每年付房地捐款在五十两以上者或每年付房租一千二百两以上而付捐者。华董当选资格与外董相同外,尚须居住公共租界五年以上。华董的选举,先由纳税华人会、同乡团体和商业团体三者平均选出代表81人,再由代表大会选出董事。可见,董事会是由中外有产阶级的中上层人物进行控制的,而且董事是名誉职,不支薪给,更是非有钱人不能充任。董事会决定工部局的重要问题与行政方针,每两周或三周举行一次会议。董事会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咨询顾问性质的委员会,委员也是名誉职,不支薪给。在工部局里,实际行政执行者是有薪职员,最高为总裁,下设总办处,公布对外文告,管理下属各处,有万国商团、火政处、警务处、财务处等,各处主持人多为西人。万国商团是租界的武装力量。美国人密勒曾经指出:“租界实于万国商团,后备巡捕、水上巡捕之中,拥有其自身的海陆军,此项军队直接受工部局总董之指挥。”[12]工部局是领事和纳税外人会监督下的公共租界有产阶级中上层人物的“全能”的自治形式。
租界除拥有自己的行政、财政、军队、警察等大权外,还拥有自己的司法权。租界法院有三种: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堂。领事法庭依据的是领事裁判权;领事公堂由几个外国领事组成,于1882年依据1869年的《地皮章程》成立。法租界于1859年的时候就设立了一个违警罪裁判所;1869年,继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即会审公堂)之后设立法公廨,华人的民事、刑事案件均由领事与上海道台派一人会审。[8]
防火是城市控制的主要项目之一,因为城市人口集中,建筑林立,人为的火灾最容易造成严重的损害。公共租界自华洋杂居以来,人口和房屋激增,工部局就在各主要街道开井储水,作消防之备。到1863年,除商家私有的灭火机外,工部局还从美国购来灭火机一架。1866年1月7日,工部局火政处成立。消防经费由各保险公司和其他中外商家捐助。消防人员均是义务性质,成立有上海机队、虹口机队、金利源机队以及钩梯队。1899年租界扩充后,火警增加,义务制改为雇用制。这是一个规范化的过程。法租界方面,1863年时仅有手抽水龙机一架,有火警任务的时候,临时召集工人帮助。1869年,法租界用募得的三千元购办新式灭火机,以自愿的救火员29人成立消防队,加入公共租界的火政处,公董局必须按年给工部局津贴。此项津贴逐年增加,公董局于是组织自己的救火会,成立于1908年5月,其仍是义勇志愿制度。[13]
3.会丈局——清政府与租界的联系纽带
清政府对租界的管理主要局限于租地丈量,办理手续。起初并无一定的办理机关,遇有洋商租地,上海道台就临时派员会同领事前往勘丈。土地勘丈无误,各项手续清楚,即由上海道台发给印契了事。由于洋商租地之事越来越多,于是上海会丈局于1899年8月成立。局方人员均由上海道委任,委员以下有丈绘生等。会丈事务由局方人员与领事署派员双方会同办理。1900年,工部局成立清丈局,规定由田单转换道契时,在租界或邻近越界筑路地段内,必须由工部局或公董局加入会同丈量,核对为数,更正界石,出立照会。自此会丈手续,便由双方变为三方,中国方面的权力无形削弱了。[14]
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华界和租界控制模式见图1。

图1 华界传统控制模式与租界近代控制模式
二、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华界社会控制模式的近代化
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开埠已半个世纪,新式工商业日趋繁荣,城市问题已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只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工业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而首先是要学习西方的民主自治制度。上海是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官民意识都比较开化,而且旁边就有租界的近代控制模式可供借鉴。于是上海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便开始了由传统控制模式向近代化转变的过程。
1.市政与警政的产生
上海最早的市政机关是创设于1895年的南市马路工程局,主要任务是填筑沿浦马路。此局以职任和组织来说,只能算是现代型市政机关中工程处的一小部分。[15]两年后工程竣工,改为马路工程善后局,其职责范围有了扩大,涉及工程以外的一些市政问题。该局总办由江督刘刊一派委,襄办则由沪道札委,除继续清丈浦滩、开筑里马路以及办理附近居民领用马路两旁隙地印发执照管业事宜外,还于1898年设立南市的电灯以及创办中国巡捕房,由该局分派巡捕到各马路巡逻。巡捕房除由江苏抚标沪军营调派勇丁选充巡捕外,还对外招募巡捕,定有招捕章程,对巡捕有严格的要求。该巡捕房计经招选、派定巡捕60名,后来上海道又雇用印捕六名。[4]专职巡捕的出现,招捕章程的制定,比巡防保甲局军警不分有了进步。但中国巡捕房还有军丁充任的巡捕,而且它的设置,是隶属于马路工程善后局的需要与管辖,离近代的警察行政还有一段距离。
吴淞方面,1898年,有督办吴淞开埠工程总局的设立。督办为沪道蔡钧,由江督委任。局中所有经常和临时费用完全由公家拨给,年仅数万元,又没有具体计划,结果仅筑路数条而已。浦东方面,1906年,设有浦东塘工善后局,是由高行、陆行两乡绅董朱有恒、谢源深等呈请上海知县而创设的。
闸北方面,1900年,设立闸北工程总局,最初由地方绅商陈绍昌、祝承桂、沈镛、钱康荣等主办。由于闸北一带毗连租界,且与宝山县境犬牙相错,建桥筑路耗费甚大,民力难以担负,于是由当地士绅呈请官办。1904年,江督周馥派道员徐乃斌为总办。1905年5月,改称为闸北工巡总局,另委道员汪瑞闿接办。那时的行政设施注重警务,道路、桥梁因收入有限适当修造。次年正式改为上海北市马路工巡总局。[15]
南市和闸北市政机关的设置,都伴随有巡捕和警务的产生。紧接着,相对独立的警察行政机关也就应运而生。1904年,清政府举办新政,那时上海租界扩张,外人借口我方枭匪横行,治安不好,市政设施又不完备,于是越界擅行收捐筑路,侵犯中国主权。上海道即详准江督苏抚,举办警察,委上海知县为总办,驻营军官一人为会办,并聘绅董五人佐理。先办警察学堂,训练警士人才。1905年,将巡防保甲局撤销,改称警察总巡局,但因经费所限,规模小,章程亦简略。1907年,江督要上海道推广巡警,并委候补道一人为总办,将北市马路工巡总局改组为上海巡警总局。次年,又设巡警道一人于上海,四路十二区开始实行设警。后巡警道改驻苏州,上海巡警总局改设局长。[4]上海治安随之进入警政时期。
2.地方自治的实现
地方自治的实现是地方士绅行使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参与地方政治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它不同于传统的地方士绅对社会的民间控制,它有比较完备的章程和组织,也有比较明确的职责范围;它不再是地方官府放任自流、自生自灭的纯粹民间组织,它得到地方官府的承认和监督,合法地行使自己的某些权力。
地方自治是作为一项先进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而被当时的人们进行介绍和推行的。20世纪初,康有为写有《公民自治篇》,梁启超《新民说九》第十节便是《论自治》,留日学生同乡会的各种刊物更是大力宣传和介绍地方自治。在这股思潮的鼓动下,地方有识之士李钟珏、祝承桂、郭怀珠、叶佳棠、姚文枬、莫锡纶等人积极推动上海地方自治的实现。他们“惕于外权日张,主权浸落”,“道路不治,沟渠渍汙”,市政衰败,于1905年向沪道袁树勋建议创设总工程局,以整顿地方,立自治之基。[16]袁树勋欣然应允,答应将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撤除,“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均归地方绅商公举董事承办”[17]。同年,采用“先就向来办事诸绅商中公同选举”的办法,选出76名议董候选人呈报沪道,由其决定设领袖总董1人,由李钟珏担任;办事总董4人,由莫锡纶、郁怀智、曾铸、朱佩珍担任;另设议事经董33人,由姚文枬、郭怀珠等担任。然后接管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正式成立。这是上海第一个颇具规模、组织完备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市政机关。总工程局简明章程是经官绅双方拟定公布的,条文虽然简单,规模却也具备,是上海第一部市宪,和以后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以及辛亥革命后的《江苏暂行市乡制》大致相仿。
总工程局下设三科一所,即户政科(下设户籍处、地产登记处、收捐处)、警政科(下设巡警处、消防处、卫生处)、工政科(下设测绘处、路工处、路灯处)和裁判所。可见,总工程局拥有市政建设权、民政管理权、公用事业管理权、社会治安权和地方税收权。总工程局还设有议事会和参事会。议事会由议事经董33人组成,内举1人为议长。议长任期二年,议董任期四年,但每两年改选一半。议事会章程规定:“议董由本地绅士及城厢内外各业商董秉公选举。”选举人必须“年纳地方捐税十元以上满三年”,被选举人必须“年纳地方捐税二十元以上满三年”。参事会由领袖总董、办事总董、各区区长及各科科长共13人组成(后又增加名誉董事7名)。总章规定:议事会为代议机关,参事会为执行机关。议事会有立法权,即有权“创立并改正本局各项章程及规则”;还有组织与监督行政权,即“参事会成员以议事会之同意分掌本局行政事务之一部”[18]。
可以这样认为,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是类似于工部局或公董局的自治机关,但前者的职能范围、权力大小都远远比不上后者,而且它们之间的内部组织结构也不尽相同。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均为有产阶级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组织社会控制机关,行使社会控制权力的官方监督下的自治机关。
总工程局是士绅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自治机关。1909年1月,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各地城、镇、乡必须设立自治公所。1910年四五月间,总工程局正式改称城自治公所。上海地方自治进入奉命兴办时期。这个时期,城自治公所的权力范围有所扩大,但官方对它的控制也大为加强。这是上海市政进一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标志过程。
城自治公所设议事会和董事会。《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议事会议长、议员,董事会总董、董事及名誉董事任期都是两年,但议员和名誉董事每年抽签改选一半。章程还规定,“年纳正税(指解部库司支销之各项租税)或本地方公益捐二元以上者”[18],可作为选民,条件比以前放宽。但是,城自治公所的董事会和议事会成员大都是前总工程局参事会和议事会的成员,两者有极大的承续性。城自治公所除拥有以前总工程局的各项权力外,还拥有部分工商管理权和文教、卫生管理权,实际行政范围也推广到了闸北等地区。但是官方也加强了对它的控制,地方官可随时检查其办理情形,并可经督抚同意解散议事会和董事会,撤销董事、议员的职务;同时加强对董事会的控制和增加董事会的权力,削弱议事会的权力,即总董的担任须由督抚择批,而议事会的选举由董事会负责办理。
地方自治机关的出现,是绅商吸取前官办或绅办的初级形式的社会控制机构的经验和教训,学习西方的民主自治制度,使城市社会控制走向组织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即近代化)的一种努力,而官方对其控制的加强又加重了这层近代化的色彩。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与继后的城自治公所都是一种较完整的社会控制系统,包括市政、警政(治安、消防等)、司法等各个方面,并且各个方面都有职责明确的部门设置。系统化和正规化(作为正式的官方行政机构)是近代城市社会控制模式的重要特征。清朝末年,上海出现的城自治公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两个重要特征,表明了传统控制模式向近代化发展的明显趋势。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华界城市社会控制模式向近代化变迁的过程见图2。

图2 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华界控制模式的近代变迁
上海华界城市社会控制模式向近代化变迁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民间控制与官方控制互相交替、渗透和补充,官绅之间既斗争又合作,推动近代化的进程,市政、警政等社会控制机关从不完备逐步走向完备。
[参考文献]
[1] 蒋慎吾.上海道台考略[M]//上海研究资料续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
[2] 上海市政概要·上海租税华人会重要文件[M]//上海研究资料.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3] 贺跃夫.清末民初广州城市的政治近代化提纲[M].
[4] 蒋慎吾.警政讲话·上海市公安局沿革[M]//上海研究资料.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
[5] 蒋慎吾.清季上海地方自治与基尔特[M]//上海研究资料续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
[6] 薛耕莘.近代上海的流氓[M]//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7] 木也.公共租界户口史话[M]//上海研究资料.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
[8] 徐蔚南.公共租界沿革[M]//上海研究资料.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
[9] 蒋慎吾.警政讲话·上海英法两巡捕房小史[M]//上海研究资料.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
[10] 席涤尘.法租界沿革[M]//上海研究资料.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
[11] 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行政组织[M]//上海研究资料续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
[12] 蒯世勋.上海万国商团史略[M]//上海研究资料续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
[13] 蒋慎吾.警政讲话·消防行政之史的发展[M]//上海研究资料.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
[14] 席涤尘.会丈局小史[M]//上海研究资料.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
[15] 蒋慎吾.市政讲话·上海市政机关变迁史略[M]//上海研究资料.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
[16] 杨逸.上海市自治志·大事记[M].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1915.
[17] 杨逸.苏松太道袁照会邑绅议办总工程局试行地方自治文[M]//上海市自治志·公牍甲编,1915.
[18] 吴桂龙.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M]//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