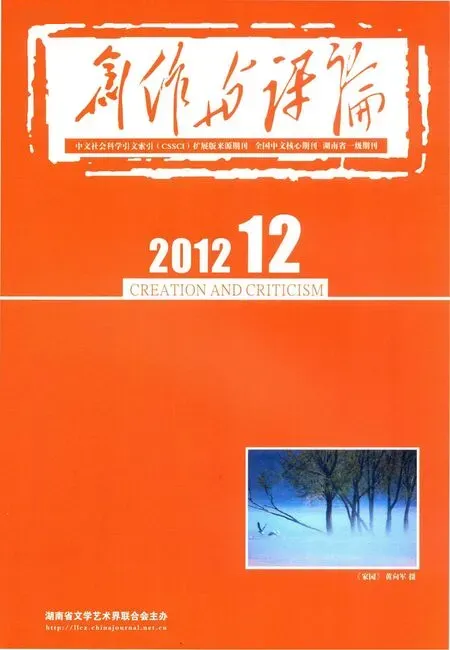以退为进 以念为生——论林培源小说创作兼谈“80后”写作伦理
■ 单昕
一、逃离或皈依:两种“80后”自我身份建构
“月光死了!”二十世纪初,年轻的未来主义者们提出这样的口号,激进主义姿态使他们宣称要毁灭一切旧日的“肮脏”与“腐朽”,追求速度、力量和技术,将所有与之相悖的艺术都贬斥为“过去主义”。这种源自先锋派内在诉求的现代性焦虑,是艺术对体制及其自身的自我批评,在推动当代艺术走向多元的同时,也使规范和标准变得支离破碎。在百余年来的中国文学中,这股解构的力量从未消遁,2000年前后,一批年轻的写作者以迥异的审美体验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景观,也为自身获得了“80后文学”的命名。此后的十余年中,“80后”作家逐渐发力,并在文学生产方式变革的推动下占领了市场。想当初,这一略显粗暴草率的代际划分曾经引起很多年轻作家的不满,认为其自身和作品的独特性被抹平;也曾因为“80后”内部的分野而引发“谁能代表80后”的讨论。而今,当这群写作者从“写手”纷纷成长为“青年作家”时,身份认同的困境逐渐消弭,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建构起自身的合法性。
“80后”作家们全面否定了上一代作家的影响:“我们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肯定是受过先锋派的影响,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不一样,但后来却发现他们没有把他们的世界观表达出来”,“那些曾经作为我们少年偶像存在的作家们,如今已经淡出了我们大部分人的视线,我们其实都已经羞于提起自己曾经喜欢过这一批作家”,“上一辈作家已经没有资格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①这些被媒体称为“集体反水”的自我身份建构宣言,加之韩寒等人早已表达过的对当代文学传统的摒弃,很容易使人回想起“80后”的来路,加之多数作品一味描写城市浮华和青春感伤,因而“80后”的写作“理念”便与“实绩”相吻合,被笃定地套上以下标签:另类、叛逆、孤独、残酷青春、反传统、都市、物质化、欲望化……这正是80后写作所呈现出的悖论之一:他们一方面想要以标新立异的姿态从传统中突围,获得话语权;一方面又受制于知识结构、道德立场、精神状态、文学资源的缺失或短视,而无法在力度、广度、深度上与传统文学抗衡,成为尴尬的“飘一代”。其实,反传统依旧有传统可循,这种断尾求生式的突围策略在当代文坛并不鲜见,正如形式实验之于先锋派,断裂姿态之于晚生代,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反传统策略捧红了“80后”文学,但同时也深刻地制约着它的发展,这不能不说是“80后”文学基因中的一处硬伤,也是其对自我身份建构的一次错误操作。
当然,也存在着另一种“80后”,他们以退为进,回望传统并借以寻找突破的可能性,林培源是其中之一。虽然与时下走红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周嘉宁等人一样由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但他从一开始就锁定了“跨越青春文学的藩篱,直抵严肃文学的内核”的创作目标。他曾在访谈中表示:“我更希望自己能走进传统文学的队伍,写一些有关乡村题材的小说,而不是只关注青春期的人和事。”②这种向传统靠拢的姿态,也决定了日后林培源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气象。之所以在80后青春文学当道之时做出这样一种文学选择,以传统作为骨架来建构自身的“文学体格”,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作家的阅读史。与上述80后作家迥异的是,林培源毫不掩饰自身与传统的关联:“读高中时我几乎把他(余华)所有的作品都看完了,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叙事语言上的力度,其他对我影响很深的作家,一个是马尔克斯,一个是福克纳,前者的《百年孤独》把我引向了文学,后者的《喧哗与骚动》以及《八月之光》、《野棕榈》等作品则令我意识到了叙事结构的重要性。此外,苏童让我学会了渲染故事的氛围,严歌苓让我看到了叙事的血性和灵动如何精巧地集于一身。”③
传统的荫泽与作家承续文学传统的姿态于作品中得到彰显。小说《打马而过的旧时光》首句“许多年后,当我面对那一方衰草凄迷的坟墓时,我会想起祖母带我去看社戏的那个下午。”直接师承至被认为影响了中国一代先锋作家的《百年孤独》的开篇。此外,《章台柳》是一篇在结构上具有实验性质的作品,从叙述视角与声音的复合、交叉和转换中可以看出作家向马尔克斯、福克纳甚至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敬的意味;在具体操作上则颇似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追溯母系家族史与个人成长的双线交叉叙述。小说的第 1、3、5、8、10 节交代“我”的家庭与女子颖的故事,而在第 2、4、6、7、11 节中,作家以第一人称出现在小说里呈现情节建构的过程,剖白内心抽丝剥茧的痕迹,甚至苛刻地评论自己的小说。这种元叙事的方式在先锋小说中屡见不鲜,马原在《虚构》等作品中的操作脍炙人口。在近作《南方旅店》里,作家尝试使用嵌套结构来推进情节的发展,大故事中套小故事,涉及三条线索,并贯穿了两重时空。作家在这里向叙事难度的挑战,既可以看成是向福克纳、冯内古特、纳博科夫等使用嵌套结构的经典作品的致敬,也可以看做是作家身上所秉承的先锋精神的再一次演练,因为先锋正是朝向自由的、不断创新的、永远在路上的。
除却叙事结构的师法,小说《我的石头祖父》、《平凉旧爱》、《秦歌》、《最后一次“普渡》、《秋凉》中所营构出的氤氲气息、作家对表现偶然与命运的偏好、对神秘感与宿命感的迷恋等等也都似曾相识,这些正是先锋小说的拿手好戏。林培源并不避讳谈及先锋文学的影响,“我出生的时候,正是苏童、余华等作家盛行的时候。不过,我直到上高中时才开始接触到他们的作品,读后非常喜欢。我觉得他们在精神层面上走在了同时代作家的前列,虽然当时他们的作品也是处在探索阶段,但是这种探索精神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更值得如今像我这样的年轻写作者学习和继承。”④所以,如果仅以“逃离传统”为精神指向来解读“80后”文学,无疑是对这一类写作的粗暴简化,因为在这批作家当中,也存在着如林培源般的“异类”,他们关注生存现实,有价值伦理表达与建构之诉求,写法上更接近“经典”、“传统”的一脉,力图靠近当代文学资源与精神传统。
二、精神还乡:乡村叙事的有效捷径
中国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所以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⑤并且,中国作家大多来自乡村,有直接的乡村生活经验,这在日后成为他们文化心理中最深刻的记忆。五十年代以后,乡土文学叙事参与进现代民族国家合法性建设之中,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推动下获得张扬。此外,八十年代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也使中国作家再度聚焦于乡村,并直接产生了“寻根文学”等流派。是以“乡村”成为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的重要言说对象,乡土或曰农村题材文学叙事绵延百年,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传统的重要一脉。自鲁迅、沈从文,到柳青、周立波,再到莫言、张炜,乡村在一代代作家的书写下,承载着中国人的欢欣和苦难,以及建构于其上的中国式心灵、精神和情感。这一当代文学靠心灵甚至体温所积蓄下来的传统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渐渐开始产生变化,现代性焦虑裹挟着都市迫不及待地加入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于是文字里的村庄渐渐消隐,取而代之的是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的关于城市的欲望书写。“80后”在如此前提下登场,其写作中也自然对以乡村为代表的“过去主义”的一切保持警惕,进而追求更具现代感的“未来”。在这样一个文学的“小时代”中,难得尚有一些年轻的作者在反复书写他们的乡村记忆。
林培源以其具有浓厚原乡精神的乡村叙事在当下“80后”写作中凸显出来。他的精神根据地在潮汕乡村,那里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也是他取之不尽的写作资源,这为其小说创作建构了一个原点。而他的乡村叙事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并非以自然主义式的对乡村自然风物的描绘为诉求,而是以精神还乡,在乡村叙事中保存童年经验、反思传统道德和价值伦理、拷问人类信仰与欲望的纠葛。有评论家曾说,在每一个作家身上,都兼具“出生地”和“异乡人”这两个心灵标记,“写作既是精神的远游,也是灵魂的回家。你在故土的根须扎得越深,你的心就越能伸展到远方。你走得越远,回家的渴望就会越强烈。”⑥已在地理学意义上成为“异乡人”的作家,却经常进行灵魂回家的旅行。他在很多小说中都有意识地置入了浓郁的潮汕元素,并在地域文化书写上建构对人性的挖掘。《最后一次“普渡”》中由花岗岩石板铺成的清平街是一条典型的潮汕老街,老厝区屋顶盖的青瓦爬满了青苔,诉说着老街的历史。小说借张裁缝一家在清平街上的生活历程透视了清平街人的生存哲学,展现出一卷乡村生活史。农历七月半的“普渡”是潮汕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美学的集中呈现。
清平街的“普渡”是祭品的大比拼,香火燃起,烛泪低垂,旺盛的人气与这节日原本的阴森气氛相互调和,使节日所承载的祈福和施舍之意浸润至每个人的心里。小说中关于“普渡”风俗的描写,以及以“普渡”为核心的家庭悲剧,不仅表现了潮汕民俗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庇荫下人的生存状态,同时也深刻体现了蕴藏其中的关于存在、灵魂、现世与永恒的哲学思考。
小说《章台柳》中有关于红头船的讲述。红头船是潮汕地区重要的文化符号。它是清代潮州从事远洋贸易的商船,大多数潮汕华侨乘坐红头船到海外谋生;红头船亦曾经是中国同世界各地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纽带,承载着潮汕文化中开拓进取的精神。《薄暮》中为祛病的请“娘娘”仪式、逢年过节的祭拜祖先仪式等等,表现了乡村生活伦理中关于生与死的信仰,这是潮汕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人所应秉承的生活道德。
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时的复杂心境,体现了作家价值伦理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同时也为作品营构出一片模糊地带,谱写出一曲乡村挽歌。中篇小说《平凉旧爱》中,平凉镇地处韩江平原,是再典型不过的潮汕小镇。镇上的老人院原是祠堂,是传说中韩愈被贬至此地倡议所建。祠堂庄重肃穆,积存着平凉镇的历史、伦理与道德传统。而正是这厚重所系的祠堂(老人院)中,却又生发出诸多与传统相悖的不和谐。孙婆婆是杏林世家的唯一后代,因而打破了家族医术传男不传女的传统,成了小镇唯一的医生;老人院的周青海院长饱读四书五经,却终生未娶,犯了无后为大的大忌;火葬规定实行后,平凉镇老人都惶恐起来,因为这意味着“一辈子的时间在几小时之内被统统压碎。”小镇作为传统文化的守成者,提供了一个看似稳定的空间结构,然而在外界和内部的双重压力下,内中酝酿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坚守与摧毁的冲突,文明与变革的冲突,这些冲突所改变的,不仅是平凉镇人千百年来所秉承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伦理,也体现了作家深重的忧虑与悲悯。
乡村文学叙事绵延百年,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传统的重要一脉。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地方经验为作家提供了精神根据地,使他们经由窄径而通达开阔的人心世界,所以无论是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沈从文的湘西,还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都是作家为自己的写作建立的独一无二的王国。林培源的作品保有自己的精神根据地,这为文学提供了扎实的来头和去处,也使他的小说具有明显的精神向度。
三、追问意义:精神向度的纵深及其可能
在谈及小说《薄暮》的创作意图时,林培源曾做过如下阐释:“我想表达的是一个人怎样承受和度过人生里的苦痛,又是怎样用爱去化解生命中的仇怨。”⑦的确,对生命中欢欣与苦痛的深刻理解,朝向人灵魂幽暗处的探寻,以及对人存在意义的追问是林培源小说的一贯主题。
小说《秦歌》中的“我”姐姐秦歌是一个十五岁就怀孕的堕落少女,“贱货”是身边人包括父母、“我”还有周遭人对她的定义,年幼的“我”也因此备受歧视和屈辱。父亲因走私被判刑,母亲因操劳过度而病倒,秦歌也负气离家,完美家庭瓦解,此后我便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但心中却怀有无限阴郁和忧伤。直至秦歌因难产死去,“我”才放声大哭,真正理解和原谅了她,并渐渐在漫长的成长里领悟到生之可贵,也读懂了自己的名字“念生”——“心怀善念,以念为生”。秦歌是生命的歌者,虽然“她的歌唱是躲在黑暗角落里”,但她仍以顽强的生命力绽放出生命本该有的刹那光华。而人心中秉持的善念则是人类于生生不息中所应坚守的最深刻的道德。在作家的早期作品《打马而过的旧时光》中其实就已然蕴涵了“以念为生”的主题,小说诉说对祖母与我的童年经历的追溯与怀恋,其中包括了对信仰的思考。
祖母在岁月的流年中尝尽了生活的苦难,在磨砺中活出了自己的尊严,她给予了幼小的“我”关于亲情最原初的概念,同时作为连结几代人的温柔而绵长力量传承着家族的生生不息,同时也延续着文化传统和忠孝敬恕的伦理观念。是以在祖母的坟墓前,在“生活与生活密不透风的罅隙间”,“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为深切的体察。在《我的石头祖父》中,作家也表现了这样一种生命伦理。堂哥意外落水而死,“我”作为迟来的孙子,被祖父命名为“迟年”,从出生起,就被赋予延续家族生息的使命。祖父对于其石匠事业的固执坚守是因为“他坚信人生来便是一块石头,唯有历经风吹日晒才能显示出坚硬的质地。”这是祖父最朴素的关于生命的信仰,也是作家对生存意义进行追问的立足点。
在后来的长篇小说《薄暮》中,作家开篇即道出“一切和母亲有关”,这一部以“我”母亲秀米一生的经历为主线的成长叙事,关注了女性的生存和命运,及其在成长中所遭遇的种种欢喜、挫折、困顿和疑难,并对人灵魂深处信仰与欲望的冲突进行了深刻表达。十五岁时“出花园”是潮汕地区特有的一种风俗,也是秀米的成人礼,这是她一生的转折点之一。母亲在“出花园”时的企盼“人这一辈子啊,就图个平安”传达着世代相传的对安稳生活的向往,然而生命本身却无法如此圆满。小说中的人生满是补丁,苦难成为常态。在家庭意识极为浓厚的潮汕地区,“不孕”是笼罩在人心上的阴影,无论对作为女性的陈姨、莲姨,还是大姐秀旗的丈夫春生,这都是命运悲剧的主要诱因。小说记录了女性生存之艰辛:莲姨被兄强奸而失去生育能力,后又经历了两次丧夫;秀旗与丈夫春生因矛盾重重而离婚;秀米不情愿地嫁人、不情愿地被过继给陈姨夫妇,又因生女儿遭到轻视。作家对乡村女性充满了理解和仁慈,满怀怜悯地写出她们生命中的希翼与苦痛,诉说女性置身于中国乡村传统道德与伦理中的悲剧宿命,于细腻中呈现大悲悯。此外,人生苦难和命运无常还表现在若干男性人物的非正常死亡中,秀旗丈夫春生从树上跌落,莲姨丈夫被毒蛇咬死,来生做爱时心肌梗塞,许伯从脚手架跌落,“我”的年幼堂哥也失足跌落池塘而死……事故的偶然性与命运的永恒悲怆合谋,为人生笼罩上了一层层暗色。然而,当苦难“如车辙一般延伸至无边的旷野”时,人们只能用爱去化解它。所以无论是莲姨对许伯的原谅,还是母亲秀米对祖父母、陈姨和伯父一家的谅解,都源自这种充满命运智慧的大悲悯。这不仅是小说所要最终抵达的精神向度,也是命运将要去往的彼岸。
《欢喜城》也是女性成长和生命的寓言。主人公叶贞青自幼起便背负着一种“原罪”,只因为她是女儿,而父母继生过一个死去的男婴后再无法生育。于是,她从小在极之淡漠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而“传宗接代”也成为这个家庭无法触碰的陈年伤口。叶贞青很早就明白,“她身上,是寄寓了另一个早已逝去的生命的。”这成为一个诅咒,使她内心溢满苦楚,从能自立起便迫不及待地离开家乡,因为即便是在这里,她亦如“一座幽暗的离岛”,看似和辽阔的大陆相连,实则异常孤立。宿命使她成为一名助产护士,在血缘轮回中领悟生命的高贵,而见证那些鲜活生命的降生,是治愈她幼年创痛的一种方式。真正触及并最后解救这种“罪感”的,是叶贞青抱养的一个弃婴。
作家在这里赋予人物以非常的勇气和力度,让她在面对弃婴时一寸寸地揭开灵魂深处最幽暗的创疤,并不断拷问自己和家庭的“原罪”。然而,也正是这一极之矛盾和痛苦的过程,使她最终做出收养弃婴的决定,关于生命的“原罪”在另一条生命的延续中得到了救赎,这不仅是叶贞青一生刻骨铭心的痛切记忆得到舒缓的结果,也是生命轮回本身的逻辑。对叶贞青受难和自我救赎的不断推进与追问,体现了作家书写灵魂重量的精神向度。
新世纪之初,曾有媒体推出专辑,将迈入成年的“80后”称为“飘一代”,以此来概括这代人身上的“无根性”。时至今日,仍有很多“80后”作家深陷世俗社会,在精神层面放弃对价值世界的建构,现实中也与各种公共生活割裂,导致作品虽然布满浮华世界的喧嚣,却仍然呈现出单薄、虚弱的面貌。相比之下,林培源是一个有着主体性建构意识的作家,他有意与现实世界和主流传统发生关联,采取的方式通常是为意义的寻找搭建一副历史框架,作家试图介入历史,找到一条在历史与自身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途径。吊诡的是,支配作家将故事置入历史加以言说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作家面对的历史与主体的焦虑。小说《薄暮》即是一例。作家在小说中设置了若干时间点,并多以历史事件作为标记,以此来作为人物命运转折的节点,如莲姨丈夫下葬那天恰逢重阳节,六年后的那天毛泽东逝世;许老姨到达为秀旗说亲,正是全国恢复高考、大批学子涌向溪桥镇报名点之时;以及林可树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等等,欲为故事的讲述建立更为坚固的合法性。然而历史感的缺失与主体的青涩使得此处的历史更似一副空置的躯壳,历史语境的设置与人物命运走向是割裂的,二者互相平行,自说自话。《平凉旧爱》中也有同样的问题,抗美援朝和文革的时间点设置,也仅在结构上对情节有所推进,未能进一步参与营构小说的意义空间,扩展小说的精神含量。历史不应该仅仅是漂浮在纸上的文字记录,更应该承载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为人的种种精微深刻的情感、悲哀无告的心灵和被扭曲的命运立言。如果说先锋作家通过摒弃对官方历史叙述的无条件信任,融入大量的虚构与想象,以异端的视角表达了自由个体的叙事伦理,去重写既有观念逻辑和价值体系的话,那么“80后”小说所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对存在的理解。这是制约“80后”写作的精神向度与意义探寻推向纵深的因素,当然,也会成为其继续出发的起点。
注 释
①张悦然主编:《鲤·因爱之名》,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4页。
②金星:《“断裂”之后还有决绝》,《工人日报》2009年12月18日。
③钟华生、彭勃:《林培源:我写的不是青春文学》,《深圳商报》2009年8月21日。
④杨媚:《这条路不吃香但我义无反顾》,《深圳特区报》2011年8月1日。
⑤钟华生、彭勃:《林培源:我写的不是青春文学》,《深圳商报》2009年8月21日。
⑥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⑦谢有顺:《乡愁、现实和精神成人》,《从密室到旷野——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转型》,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
⑧钟华生、彭勃:《林培源:我写的不是青春文学》,《深圳商报》2009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