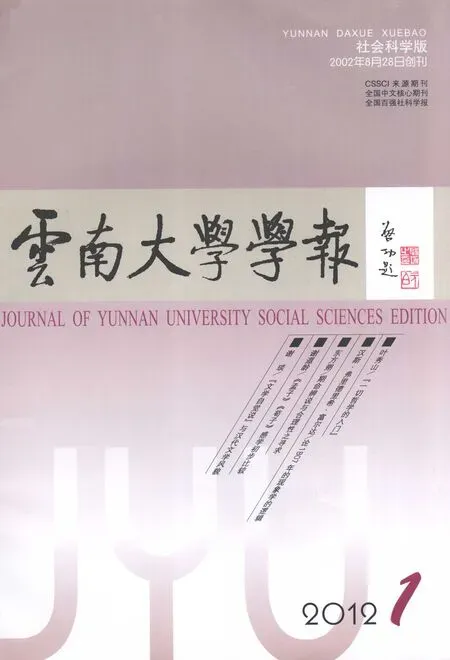《孟子》《荀子》感学初步比较
——儒学之美学的可能性探讨
谢遐龄[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孟子》《荀子》感学初步比较
——儒学之美学的可能性探讨
谢遐龄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儒学;善;感学(美学);感性判断力;智的直觉
本文鉴于汉语“美”字与西文beauty、Schöne不相当,遂着眼于把美学按古希腊文原义与此词首铸者鲍姆伽登的意思理解为感学。论及儒学之感学,就要分为美学、善学两个方面。《孟子》:“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荀子》的相当学说为:“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同样主张美、善同根:感性判断力;荀说更细致、完整。分析《荀子·性恶篇》对孟子性本善的批判,其失误在于“性”这一概念所指相异,孟子指四端,荀子指好利、疾恶、耳目之欲、声色之好。牟宗三智的直觉说对儒学之感学是一重要挑战。智的直觉之意义是良知返照。如果牟说成立,则儒学之美学依据感性直觉,儒学之善学依据智性直觉,那么,儒学之感学须歧出为二。儒学之美学论美,还须论境界、气、神、骨等,与智的直觉说不相容。
Aesthetics有两个意义:一曰关于美的学问,二曰关于感的学问。理解儒学,要点在感学。儒学之感学,一是关于美的学问,一是关于善的学问。换句话说,论及儒学的Aesthetics,不可避免地关涉到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美的学问,一是关于善的学问。故此,本文把Aesthetics译成感学,并释感学意义为统括美学、善学两个方面的学问。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说文解字·四篇上》释“美”字曰:“甘也……美与善同意。”《三篇上》释“善”字曰:“吉也……与义、美同意。”这就是说,美与善在字义上有重合处,也有区别处;重合处程度会有差别。本文不打算对这两个字的字义作详细辨析。查《孟子》使用美字时赋予的意义,并不特别有后世的论美之学中的“美”之意义,如“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美与圣之间还安排了一个“大”的概念。如果诠释“充实”为“秀美”,“大”为“崇高、壮美”,“圣”为“至善”,似显得牵强。所以本文采用的方法是寻绎《孟子》、《荀子》书中涉及论美的思想和学说。
一、《孟子》、《荀子》中美和善建基于同样的哲学基础上
(一)从《孟子》看判断美、善的两个关键环节
康德区分心之能力时,用情感能力(即愉快、不快)与感性判断力(通常译作审美判断力,本文把“审美的”还原为“感性的”)两个词指称一种能力。这种做法容易引起误解,似乎下判断是根据情感。实际上,康德本人并不认为愉快感与判断是一件事。*康德《判断力批判》第9节标题是“硏究这个问题:在鉴赏判断中愉快感先于对象之评判还是后者先于前者”,开首第一句是“解决这个课题是理解鉴赏批判的钥匙”。
怎样认知美,或曰怎样找到美?先读孟子的一段话: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嗜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第七章)
这段话是孟子论美、善的经典言论,讨论得比较细致。他先讲人类的口味有共同性,而后用了个嗜字。这个字,从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不是很准确。因为他下面所讲的内容实际上是论“美味”。“嗜”可以理解为个人独特的偏好。而“美味”却是天下人共同认可的味之美者。“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放在这里更属不伦不类。如果讲谁做的鞋最美,还算是美学问题。至于“屦之相似”,与美学关系就不是很大了。
孟子讲易牙烧菜,可以看作美学问题。每个人吃菜时会有个人偏好,这不属于美学问题。然而,让他担任美食评委时,他就必须考虑他的评价要让天下人都接受。*康德一再讲,鉴赏判断要求每一个他人都同意自己的判断。他还讲须从每一个他人的角度反思自己所作的判断。见《判断力批判》第40节。康德称之为“扩展的思维方式”,将其明确地列为判断力的准则。可见,在要求他人同意自己的判断的同时,就在力图从他人的角度反思自己的判断,这就揭示了求协调一致出自本性。他要尽量让他所发表的意见有“客观性(即普遍同意)”。因此,当孟子讲到“天下期于易牙”时,涉及的就是美学问题了。“天下之口相似”是基础。从“相似”到“同嗜”,是个飞跃。相似是有差异的意思,同嗜则是普遍性。天下之口相似,其实意指每一个人都有辨味能力、判断力。然而,每一个人的判断都可能夹杂着个人的偏好。所以,人们必须交流各人的判断以求协调一致,形成共同判断。因此,“同嗜”当指对于食物之美的共同判断。为什么要讲“天下期于易牙”?这是因为以往的经验让易牙在辨味方面获得了权威性。“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承认易牙的权威性,与今天我们对音乐比赛、选美比赛的评委有充分信任类似(评委投票属于协调,是协调的一个环节。有的评判还让在场观众投票,意思是在更大范围中协调)。这样,本来繁复的协调过程就可以简单而快捷地完成——由一个权威下判断来完成本来要人们互相交流切磋多时才能完成的协调一致。而“期于易牙”说明这个协调环节是不可缺少的。
怎样找到美?孟子上述言论告诉我们,有两个环节是关键的:一是各人自己下判断;二是人们彼此协调求得一致。许多学者对第二个环节不够重视,其实第二个环节极重要。孟子讲天下众心之所同然,道理即在于此。康德之所以在共通感概念上大着笔墨,道理也在于此。
(二)美、善同根:直觉,感性的还是智性的?
显然,孟子把美与善看作在研究方法上、甚至在哲学基础上是一致的。
他讲过口味,就立即讲到听音乐、选美。对这两种活动的研究在今天公认属于美学,不必赘述。
孟子的重点是讲心之同然。找到道德上的理、义,与上述找到美的道理是一样的。圣人与我是同类者,同样要自己下判断,而后与人们相互协调求得一致。与口味期于易牙相仿,理义期于圣人。口味,“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理义,“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孟子的结论是: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这里遇到解释孟子思想的关键句子。本文的立论是:美、善同根;而此根是感性判断力。
而目前流行的对儒学思想的解释是:可以承认美、善同源于直觉(判断力),但直觉须分为感性的和智性的两种。用牟宗三先生的用语表述,就是要有“智的直觉”。
“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关键词是“悦”字。那个“犹”字较易处理。“犹”解释为“好比”。“刍豢之悦我口”是感性判断。“理义之悦我心”可以不必是感性判断。不一定“犹”一下就非感性不可。这样曲说之,别人也无可奈何。牟先生机智地抓住“悦”字做文章,他讲,不必一讲到悦就是感性的。
于是,他把“理义之悦我心”解释为智性的悦。如此,“理义悦心”就解释为智性的活动。
牟先生此说对会通宋明理学是一大贡献。宋明理学从程子开始设定理为心中所固有,是人与生俱来就备有的,是人之本性。然而,朱子沿袭程子学说,仍然把格物致知解释为感性判断。这样就留下了一个毛病,给陆九渊攻击他提供了口实。阳明重释格物致知,一反朱子从事事物物中寻绎道理的工夫,把格物解释为用心中固有的天理来校验事事物物而断其是非,这样就克服了程朱学说留下的弊病。于是,虽然坚持了中国思想一贯的重直觉的思路,却不再取感性直觉说。牟先生把这种工夫解释为良知返照自身,因而称作智的直觉,显示了阳明思想的逻辑内涵,贡献甚伟。
如此立说,连带着必须把论美也说成智的直觉。不幸的是,美学一词在西学中是感学Aesthetics,牟先生若要统一感学须有两种思路:或者造个新词,以“智学”为美学,且解释儒学之美学为智学方可;或者分裂感学,部分地修改美、善同根说,主张儒学论美为感学、论善为智学。牟先生在主张“理义之悦我心”为智性的悦的同时,认可“刍豢之悦我口”是感性的悦,取的是后一思路。
综上述之:康德认为美源于感性判断力,善源于实践理性。儒学统归美、善于直觉(判断力)。当代诸大儒对美源于感性直觉似无异议。而当代心学派主张善源于智性直觉(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牟先生依康德在实践理性领域论善,从而创智的直觉说)。当代理学派意见似不很明确(与程朱理学做工夫依感性直觉对比而言)。我们主张善源于感性直觉,或换个说法:感性判断力(有时把感性写作直感,称作直感判断力)。
(三)感性直觉:荀子论善
荀子有与上引孟子“同然”一致的言论: “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师旷,言治者予三王。”(《荀子·大略篇第二十七》,518)杨倞注:特意谓人人殊意;予读为与。因而“共予”即“共与”。王先谦疏引王念孙曰“唯即虽字”。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天下的人虽然各自都有独特的意向,然而又有共同的态度。可见“共予”即共通感。
有趣的是,在荀子留下的、比《孟子》丰富的资料中,有一段话很传神,点出了品味判断之来历:“今夫亡箴者,终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见之也。心之于虑亦然。”(荀子·大略篇第二十七》,501)旧注“眸”字似均未得其义。吾臆其义当为“神来之瞥”,故而心之于虑属“灵机一动”、“妙手偶得”。
此处“虑”字是个关键词。旧注均未得其义。试详解如下。
荀子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之“伪”字之义,与此“虑”字关系极大。现多引几行:“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荀子·正名第二十二篇》,412)
“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虑”义为思虑。思虑什么?按康德,心有三种能力:知性(理论理性)、理性(实践理性)、判断力(感性的及目的论的)。荀子此处的“虑”字意义很确定:对情作选择。那么,这个“虑”属于理论理性还是属于判断力?这个“虑”不能归到理论理性,不属于知识论(或认识论)问题,而应归入判断力领域且归为感性判断力问题。从众多“情”之个案中作选择,即康德所谓“反思判断力”;从众多个别案例中找到足以成为普遍性之代表的个案,此即“从个别求得普遍”。不是从一个个别提升为普遍,而是从众多个别中选择出一个个别,并经与人们协调获得一致同意升格它为普遍。而且依上引《大略篇》中的言论看,下这种判断相当不容易,多半属于“终日求之而不得”。不过,在这段引文中,荀子对“虑”所给予的地位似乎并不很高,仅仅是作为判断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下面一个环节是“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
在这句话中,“动”是关键词。杨倞旧注曰:“伪,矫也。心有选择,能动而行之,则为矫拂其本性也。”这里对“动”字的批注含糊其辞不明何义。如果“动”指行动,何必后面再加个行字曰“行之”?动之主体是什么?是“心”还是“能”?依“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一句,“虑”是心在虑;那么,“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一句,“动”应是能在动。这就是说,“动”之主体为“能”。于是,须解说这个“能”究竟指的是什么。
下文曰:“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案:此知当指人获得的知识或曰判断];知有所合谓之智[案:此智当指知识与对象吻合]。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案:此能当指获得知识的能力];能有所合谓之能[案:此句费解。或指与他人相合?与他人协调?既然前“能”指认识能力,这个“能”当指认识能力与认识能力相合,就应是指协调、亲和]。”对这个“能”字的解说是困难的。
这里要注意的是:论及知,不止于理论理性(知性),也可能涉及感性判断力。通常只谈“认识论”,一涉及知识就与康德第一批判挂钩,未虑及还可能涉及第三批判。
回过来再看这个“动”:“能为之动”解释为能使之动作、作为,即把“动”解释为行动,似不准确。“虑积焉能习焉”,杨注曰“心虽能动,亦在积久习学”。“心虽能动”怎么解释?“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择情;“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相当的句式应当是“能动心”。
把“动”解释为“心动”,似顺当。后文有句曰:“不动乎众人之非誉”(《荀子·大略篇第二十七》,425)——“不动心”、“不动摇”。动摇也是心态,可能会行动但未必有行动。
又:论及欲与治之关系时用到“动”之又一字义:“……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荀子·大略篇第二十七》,428)杨注:“动,谓作为也。”心之“止”、“使”皆落实到“动”上。心在此为意欲能力,释动谓作为,亦通。如此解,则此“动”之义与前“动”不同。“心之所可”之心,释为实践理性、感性判断力似均可,然而释为感性判断力似更准确。既然说“心之所可”中理或失理,足见心面对实事作判断,再衡量这个判断(所可)中理还是失理。所以说,“心之所可”说的是感性判断力之活动。
归结以上讨论,“能”当指感性判断力,“能为之动”当指与他人思虑协调而形成共通感。如是,“伪”就是共通感。
荀子曰:“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伪与性、知、能一样,各有两个命题述说各两义。“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杨注曰:“伪,矫也。心有选择,能动而行之,则为矫拂其本性也。”郝懿行驳曰:“《荀书》多以‘伪’为‘为’。杨注训伪为矫,不知古字通耳。下云‘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与此‘能为’之‘为’,俱可作‘伪’。”杨注与郝驳似均未得其义。
吾臆:要害在于解读此“伪”字为动词还是名词。杨、郝之说均以此“伪”字为动词。吾臆其为名词,且为意指概念的名词。荀子明确地讲“散名之在人者”,散名,诸概念也。无论字义为“矫”还是“为”,“伪”为概念,其义为判断。
“心虑而能为之动”:能,感性判断力;能动心,或曰心被能打动。于是,“动”字之义就凸显了:“心动”不就是愉悦么!故而,吾断此“动”之字义是“愉悦(感)”。
在两个对“伪”之字义的解说中,“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此“伪”字之义当为得到理义的判断能力,或解读为一个个人对理义的判断。“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此“伪”字之义当然也为理义。这句话讲到了三个环节:虑积、能习、而后成。“积”字很重要,怎么理解呢?荀子在此处的论述似乎不够完整——他没有提到人们之间的协调过程。然而另处提到“共予”,而且讲到“言治者予三王”,与孟子“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相当。也就是说,这个“伪”之字义是“共予”应无疑义。“积”显然是个过程。“虑积”或许是圣人根据积累的多次体验独自反复掂度。而“能习”必定不是圣人自己实践,应是让人们实践。所以是把从群众在实践中选择(今日语言称作“提炼”)的、能令人有愉悦感的“规矩”放回到群众中去实行。“能习”的意思就是在实践中通得过的。由此看来,“虑积”与“能习”不是两个截然划断的阶段,而是反复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交互开展的过程。而后才能找到确定的理义。*《周易·咸·彖》:“咸,感也。柔上而刚下……男下女……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张载易说谓“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风动之也”。程颐易传谓“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圣人感之也”。皆未尽其义,把双方互感解说成圣人单方向地感动人民群众。此卦之《象》辞明明讲“君子以虚受人”,《彖》辞称“柔上刚下”、“男下女”,义皆涵圣人首先须从群众中来,而后再到群众中去,如程子所说“相感相应而和合”。此卦涉及的心智能力为感性判断力无疑。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就包含了协调在内。“虑-习”是个比协调更复杂的过程。由于这个“习”字透露了实践环节之必要性,得到“伪”比参透“美”难度更高。
小结以上的讨论,可以确定,孟子、荀子关于美、善基础的论述,皆可视为感性判断力学说。*这里提一下,戴震对孟子的解释可能较为合适。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开首劈头就说:“问:古人之言天理,何谓也?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又“问: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是理又以心言,何也?‘曰: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非理也、非义也。凡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论者多从“知识论”或“认识论”角度评论戴震此说,不妥。戴震此处所依据的全属感性判断力。
二、荀子反对孟子性善论
上面讨论了荀孟相近处。有论者甚至说荀子的思想与孟子是相当接近的。荀孟之区别何在?究竟有多大?遂成一有趣的题目。
先看《荀子·性恶篇第二十三》中批判孟子的言论。
《性恶篇》的主要内容是批判孟子性善论。篇章结构是:
第一部分是正面阐述性恶论。
第二部分是驳孟子“人之学者,其性善”。在目前的杨倞注本中,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构成第一自然段。
第三部分答诘难者问“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此为杨倞注本第二自然段。可看作对第二部分从另外一个角度的阐发,看作是上文驳孟子之补充、发挥。
第四部分(第三自然段)驳孟子“人之性善”。
第五部分(第四自然段)答诘难者问“礼义积伪者,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是第四部分驳孟子之补充、发挥。
第六部分(第五自然段)解释曷谓“涂之人可以为禹”,也是回答质疑者,意思是与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划清界限。
第五自然段或者可以再划分出一个部分:自“有圣人知之者”[案:当作“有圣人之知者”]以下为另一个部分。不把这个段落另划为一个部分亦可。
如此划分段落,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此篇全篇都在驳孟子。
本文特别关注的是在荀子眼中孟子的性善说之究竟。在第五部分(即杨倞分的第四段)比较明显:
问者曰:“礼义积伪者,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应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斫木而生器,然则器木岂工人之性也哉?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则陶埏而生之也,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哉?
把这段看作上段之补充发挥,意思就是孟子之性善即把“礼义积伪者”看作人之本性。然而,把“礼义积伪者”说成人之性似不通,所以,杨倞说礼义是积伪所为,王先谦案语说“礼义积伪者积作为而起礼义也”,(《荀子·性恶篇第二十三》,441)把荀子这句话解释为“礼义是人之性”。可见他们认为,把“积伪”二字也解释为“人之性”说不通。
可是,此处是荀子在讲话。在荀子看来,不仅礼义不属人之本性,积伪也不属人之本性。他说得十分清楚:“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而[其]不过[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于众者,伪也。”(《荀子·性恶篇第二十三》,438)荀子认为积伪不属于性。“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荀子·性恶篇第二十三》,436)荀子的“性”之概念的内涵相当狭隘,未把学习能力、从事能力包括在内。在辨析“涂之人可以为禹”时论曰,圣人可积而致,然而人们皆不可积,在于“可以而不可使也”——有能力做到但无意愿去做。“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荀子·性恶篇第二十三》,443、444)由此看来,荀子认定圣愚皆有学习、从事之能力,只在意愿上有差异。同时,他的“性”概念又未把这些能力包含在内。看来,辩才雄健的荀子,在理论上还是时有疏漏处。
以上分析在于作下述断定:荀子认为,礼义积伪者为人之本性是孟子的性善论主张。这样讲,与宋明理学对孟子思想的论断是一致的。然而,孟子是否如此立论在我看来尚待论证。即如上述“礼义积伪者”,笔者认为“积伪”属于天生之能力,即使荀子也不否认人们具备此等能力,可以列入“性”概念。此与孟子之存养扩充说大同小异。二者之根本分歧在于“礼义”是否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中固有的成分。
我们必须看到,这不是辩论,而是单方面的批判。荀子后于孟子百年,孟子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所以,荀子对孟子的理解是否准确是可以怀疑的。或许,荀子所驳者为孟子后学的学说,未必是孟子本人的学说。从《性恶篇》的篇章结构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显驳孟子之后,列一个答诘难者问的段落,若是若非、若即若离,似乎诘难者问是引申孟子而来但未必即孟子学说。
荀子之失误,首先在于对生而俱来的本性看得过于褊狭。孟子论及善性,举的是恻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荀子没有把这些本初心理反应列入人性。其次就是没有就这些反应不能列入人性作论证(即未正面驳斥孟子)。他驳斥孟子“人之学者其性善”,完全不顾孟子的意思可能是对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存而养之扩而充之,作针锋相对的辩驳;而是对性另行规定,对学也另行规定,另立学说另树旗帜,这是一种战斗姿态而非学术讨论的态度。
以上对《性恶篇》的分析证明:荀子之所以立性恶之论,意在否认礼义乃与生俱来的人之本性。按《性恶篇》之语气,似乎那是孟子性善论之基本点,但荀子口口声声驳孟子却未把这论点直接强塞给孟子。笔者一贯认为孟子无此思想,荀子之驳论也未能为主张孟子性善为礼义即人的天性之说提供直接支持。
三、智的直觉与儒学美学的可能性
儒学美学在孟、荀有一致性。孟子论易牙之烹调、师旷之音乐、子都之美,荀子论易牙、师旷,如出一辙。孟曰“同然”,荀曰“共予”,皆归之于共通感,所论与康德《判断力批判》所述比较,丝毫不爽,故曰:此即儒学美学的经典言论,中国思想在先秦时代已经达到美学理论之极高境界。
按本文之中国哲学中美学、善学均属感学之论点,释Aesthetics在中国哲学中包含美学与善学两个维度,就必须讨论智的直觉说对儒学美学的阐释是否有损害。
上面已经述及,在荀子时代,孟子的性善论被看成认定礼义为天生的本性,在人之存在中与生俱来而备有。此论点为宋明理学之基础。为何如此说?理学即设定理为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之学派。既然这一点为基本点,那么,衡量朱熹、王阳明差异之主要尺度就在直觉观上。
孟子美学、善学关联之关键词,在“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一语中的“悦”字。刍豢悦口属美学,理义悦心属善学。如果设定理义为人的存在中与生俱来所备有,则理义须向内求,无须与众人协调,也无须与往圣协调。阳明工夫论所主张的就是良知返照:良知认知仁义礼智无须格外物,返观自身即可。朱子工夫论主张一事一物均须仔细掂度,以求妥帖,实则包含了与天下古今所有人的协调,可见朱子工夫论依据的是感性直觉。但朱子的工夫论与其关于理的设定有冲突。依靠格外物(事亦物也)领会理,置自身本性之理于何地?!故而陆九渊有充分理由讥笑他。王阳明提出良知返观(返观即返照,观即照也)说,完满地解决了朱子所面临的理论在逻辑上面对的难题。这就是说,如果有矛盾,就出在违背事实方面。在逻辑上,既然理为天命之性,则修养向内求无懈可击矣。
阳明此说,有牟宗三先生提出智的直觉说为其现代解释。牟先生此名词取自康德的实践理性学说,自然是出于误解或曲解,但其内涵指实践理性返观自身,颇得王阳明之意,理论大致能够成立,是一绝妙的创说。
困难在于怎样解释孟子“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中两用之“悦”字。牟先生不得不断言“刍豢悦口”为感性的悦、“理义悦心”为智性的悦以完成其立论之证明。如此,牟宗三分裂了儒学的感学。儒学美学还能成立吗?如果牟先生的立论要成立,就必须让美、善分家。这样做合乎中国思想之传统与真实吗?
我们不能设想,在同一句话中,两个“悦”字居然有根本不同的两种含义;也不能设想,孟子时代的“悦”字会有双重意义;更不敢设想,孟子会如此偷换概念。我们只能认为,两个“悦”字均指感性的情感。
孟子是孔子的继承者。感性判断实际上源于孔子思想。请看孔子的下述语录: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这两段话都有“择其善者而从之”。“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是多闻的意思,案例多了才可以择。从多中择出一个善,是一种比较的善;或者从多中推想出一个最恰当的行为为善,好比实际选美的第一名是相对之下的比较的美,而同时可以想象理想的美。(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7节“美的理想”)
孔子论“择善”,就是运用感性判断力从大量实例中发现善。这也是格物致知之义。格物即掂度,多闻而比较各案例;致知即下判断,运用感性判断力从大量案例中得出中和判断。为什么说善是感性的?因为诸事(众多案例)是感性的;“善”判断源于对这些案例运用反思判断力。
把握了善的那个时刻,心之愉悦不言而喻。《论语》中多处提到这样的欢悦。“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程子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乐在致知——得到关于善的感性判断。或曰:你凭什么说孔颜所乐为感性判断,难道不会是出自智的直觉的智性判断?答曰:孔子何曾有返观自心之说?其道为多闻择善。《周易·大畜》象辞:“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识”义兼多闻与判断;且为感性判断。孔子所论与之一脉相承。上引孔子语“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之“识”,字义与此略有不同。此“识”字义为“志”,记住甚或牢记。遇事时以模拟推理行之,故为知之次。
本文开首处曾引孔子论《韶》、《武》的话以说明孔子对美、善关系的观点。这与康德所说“美是善德之象征”(das Schöne ist das Symbol des Sittlich-Guten)可否作比?由于中国思想中缺少目的理念,故而很少含有目的论意味,所以,康德美学中的“合目的性”概念用于讨论儒学美学并不贴切。《韶》尽美尽善,《武》尽美未尽善,无论美还是善均称境界,区分而并行,不能说美是善之象征,只能说美与善是两境之连体。从这句话怎么可能得出论善属“良知返照”?
孔子曰“仁者乐山”。诚然,按康德哲学,山既有数学之大,又具力学之紧张,以康德解释孔子似可通。然而,康德美学论山属“崇高”(或译“壮美”),论水也如是。那么,何以“智者乐水”?在康德同属崇高的山、水,在儒者则对应不同的道德境界。合目的性概念无效矣。本文无篇幅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只是据此立论曰:智的直觉理论在此难以立说。(若立说,该怎么说胸有成山?)
归纳上述孔孟思想,结论是:儒学美学能够成立,不得脱离善学(道德哲学);智的直觉说与儒学美学不相容;孟子、荀子的美学思想一致;孟子、荀子的善学思想也相当接近,尽管荀子在驳论中似乎认定孟子主张礼义与生俱来,不足为孟子有此思想之证据;孔孟皆持美、善同根论,美、善皆源于感性判断力之活动。
四、附记
本论文的相关内容曾在某大会上报告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杨煦生教授针对我说“由于中国思想中缺少目的理念,故而很少含有目的论意味,所以康德美学中‘合目的性’概念用于讨论儒学美学不贴切”,要我对儒学美学做进一步说明。在会下他与我用了很多时间讨论合目的性与神学的关系。因而我对本论文作几点补充。
(一)Aesthetics作为硏究美的学科,无疑具有普遍价值;儒学中必定能够找到相应内容,无疑有话可说。然而,一旦说及儒学美学,或者把Aesthetics的意义阐释为感学,说成儒学之感学,就会出现困难。这是因为当我们说到儒学之感学时,不能不涉及美之境界、善之境界,而这就超出了西方论美之学的范围。换句话说,讲到儒学, 用美这个概念还是换用王国维首倡的境界概念(或者用远古时期的气、神、骨——刘勰论风骨),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我们说到儒学论美之学时,不仅硏究美,也硏究境界;而且境界更为重要。这就与西方论美之学有了根本区别。
(二)美学,Aesthetics,本来意义是涉及心智感性能力之学问,因而照字面意义,智的直觉属智性能力,不应归入Aesthetics。如果智的直觉与境界相关,甚至关系甚大,那么,儒学美学就成了有内在矛盾的概念(儒学须论境界,境界又关乎智性能力;而Aesthetics为感性能力之学)。
牟宗三智的直觉说是否是一个正确的理论?这是个有待考察的题目。我的初步判断是,这是个内涵存在诸多错误的理论。但这并不妨碍我承认这是个伟大的创说。单就“理义悦心”这一命题说“悦”为智性的,牟先生的错误在于,心悦理义实则是感性的悦。牟先生认定这是智性的,缘于他认为心即理,心悦理义即理义悦理义,是为良知返照,或曰理义自悦。吾破其说,要点在于破心即理说。释天理为内涵于文化之中,为意义世界之内核。天理于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浸润内化为人的文化存在。要言之,宋儒以为天理乃初生时即随气赋予人,我依气本论主张,人性只是气之性,天理等道德本体乃既生之后由社会教化而成。大儒们反观本心时发现,自身天理具足而无须外求,确非虚语。盖因他们内视时,自身已经化得天理,即已经具备天理,但不觉何时获得而已,遂以为随生而天赋。查理义悦心之悦,缘于遇事得一正确判断,于是心悦之。朱子说格物须逐事格以求理义,阳明说遇事时返照自心以心存理义衡量之。后者说为依智的直觉。判断两大儒之长短,要害在“遇事”。孟子曰“必有事焉”。遇事则集义、养气。事为感性的。朱说为事与事累积,于诸事得其中,此为感性判断力(或曰直感判断力),此无疑。王说事与心中天理(他又说为良知)相比较,以良知格之,实质上也是感性判断,只不过是以已得之理义与新遇之事比较,虽貌似规定的判断,实则仍是反思的判断——阳明自己就说酬酢万变、良知无方体,何来规定的判断?!直觉则直觉矣,智性的却未见,故而智的直觉说难以成立。
智的直觉是否有?确实有,此无疑者。问题仅仅在于它究竟是什么。理义返照不能成立,其他的却有可能成立。那么,是什么东西可以成立?心为主宰——主宰即良知返照所生。良知即心,心返照自身,即生主宰之念。此返照即智的直觉。然而,此主宰若与天理(理义)混为一谈,就陷入谬误之泥淖。此王阳明失足处(他此处说良知即天理,彼处又说良知即知觉,遂把感性的与智性的直觉混在了一起),亦牟宗三出错处。
(三)境界是否有客观性(暂视境界、气象为同等概念) ?境界无疑是主体的心态。美也是主体的心态。然而,美有客观性。那么,境界是否也有客观性? 境界概念虽然为王国维所倡说,但在我国思想史上仍属源远流长。孟子讲善养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又讲集义所生;后来曹丕“文以气为主”之说与其相关——均可视为境界说之渊源。其后刘勰论风骨、神思,也论及养气,或许可镕铸之汇入“气象”概念。境界、气象何为胜说,有待讨论。本文暂视为一体。曹丕论中又说“气之清浊有体”,内涵之设定为:文章之气他人可感知。这就是说,孟子说之主体心态,在曹丕的表述中已经说成文章中客观存在着的内涵。境界(气象)之客观性似乎是无可置疑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境界之客观性成立之前提,以及怎样生成一个客观的境界。
与美之客观性类似,主观心态要成为客观的,其前提是人们能够了解彼此的心态。因此,境界之客观性也须建立在其可传达性之上。知识判断之传达,须与一个客体相关。主体心态之传达,则经由话语、表情、行为(如《世说新语》中依言谈、行为品评人物)、风景、作品等引发听者的感性判断,与客体无关。听者的欣赏活动,从说者的话语、表情、行为、(指示的)风景、(提供的)作品等等中,不是致力于辨认说者关于某个客观事物的知识,而是意向于体会说者的心境。这就是说,听者运用的心智能力是感性判断力。境界则涉及对心境之评价,是比心境更高层面的概念。
作品内涵的境界,须经过传达、协调,形成共通感,完成其客观化,如是才成为客观的境界。在此意义上,境界就是共通感之一种,共通感是客观的。形成共通感必须有个协调的过程。西方学界近年所热议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关涉的就是这个协调过程;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交流就是协调的主要环节之一。在客观化中,这是极为要紧的环节。
■责任编辑/陆继萍
B222
A
1671-7511(2012)01-0086-08
2010-11-23
谢遐龄,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中国哲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