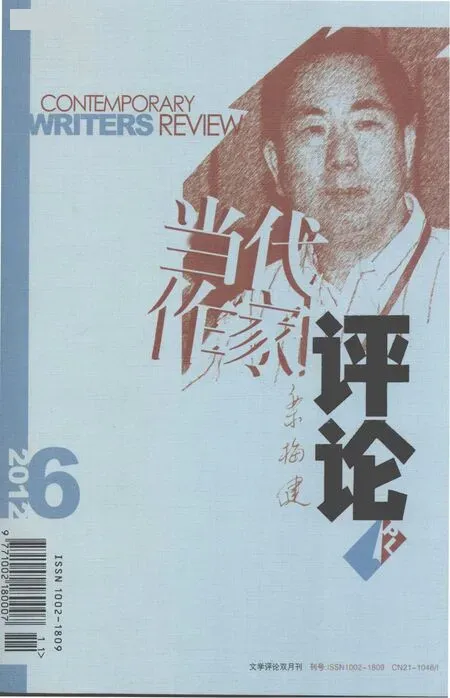“十七年文学”:红线黑线有异,实行专政则一——一九七六-一九七八年文艺界的“拨乱反正”
王彬彬
一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了《文艺情况汇报》第一一六号,其中,有《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介绍了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抓评弹的长编新书目建设和培养农村故事员的做法”。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介绍上海的这篇文章,决定将此件批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第二书记刘仁,并写了一段批语。批语很快以《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为题公开发表,全文如下: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是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是毛泽东“文革”前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的第一个。这个批示,对中共建政十几年来的文学艺术是基本否定的。在否定这十几年的文学艺术时,也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很清楚,在整个批示中,这只是一句用来缓冲语气的话。“收效甚微”、“死人统治”、“问题也不少”、“问题就更大了”、“还是大问题”、“咄咄怪事”等一个接一个的判断、反诘,十分明确地显示了对这十几年的文学艺术总体上的不满,那句用来缓冲语气的话,丝毫不能改变毛泽东对十几年来的文学艺术的整体否定。但是,这句实际上是可有可无的话,在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却被人反复提及。
这个批示当然是打向文艺界的一记闷棍。文艺界的领导自然惶恐不安。文化部党组立即对近年工作进行了反思。一九六四年三月下旬,中宣部决定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五月八日,中宣部写出了《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报告”还是草稿,尚未定稿,江青便将其送到毛泽东手上。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就是毛泽东“文革”前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的第二个。①关于“两个批示”的出笼,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1220-1222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最近几年”下面的重点号,为毛泽东本人亲加。较之半年前作出的第一个批示,第二个批示态度更严肃了,语气更严厉了,遣词造句更见斟酌挑拣,对十五年来的文学艺术的否定也更为明确。政治上的上纲上线,使得第二个批示寒气逼人。在“最近几年”下面加上重点号,是在强调文艺界“变修”的状况愈演愈烈。用两个括弧,为自己留一点余地,也是经过考虑的。刊物只有“少数几个好的”,但还是“据说”,有可能一个“好的”也没有。但“不是一切人”都坏,却是一个很肯定的判断:当然要保住一些人,要救出一些人,不然,下面的整风、下面的革命,由谁来发动、带领呢?
一九六六年二月上旬,江青受林彪委托,在上海锦江饭店召集军队文艺方面的领导进行所谓“座谈”。会后,炮制出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陈晋的《文人毛泽东》一书,对这《纪要》的形成过程有详细的叙述。江青在上海炮制《纪要》时,毛泽东正驻跸杭州。“毛泽东曾三次对‘纪要’作了重要修改。”二月二十八日,江青将《纪要》铅印稿送毛泽东审阅,数千字的《纪要》,毛泽东“修改有十一处”,特别重要的是,把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六字,就把林彪绑在了战车上。除了改,毛泽东还单独加写了这样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修改《纪要》。三月十四日,江青把第二稿寄给毛泽东,毛泽东作了第二次修改。这一次,又改动了“十几处”。第二稿退还江青后,江青又组织人弄出了第三稿,并再送毛泽东。毛泽东又作了第三次修改。这一次,“主要有四处改动”。三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把第三次修改过的稿子退江青。这第三稿才算是定稿。②陈晋:《文人毛泽东》,第595-59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这个《纪要》是极其重视的,对《纪要》表达的观点,是完全认同的。毛泽东是《纪要》的真正策划者。
二
这个《纪要》,最核心的内容,是对中共建政十七年来文学艺术的根本否定。《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即认为十七年来,在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具体表现为“黑八论”:“写真实”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反“火药味”论。
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现了许多颇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用语,“揭批”就是其中之一。所谓“揭批”,应该是揭露与批判的合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被捕,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也随之兴起。不过,由于“两个凡是”的制约,这一时期对“四人帮”的揭批,其实举步维艰。十多年里,江青等人的言行,与毛泽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话、认可过的事,便都揭不得、批不得。揭批的空间就很小了。在文艺界,对“四人帮”的揭批,从“《创业》事件”开其端。这一方面因为此次事件发生未久,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创业》事件”中,毛泽东没有站在“四人帮”一边。张天民编剧、于彦夫导演的电影《创业》,表现的是大庆油田会战中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世界观斗争,也歌颂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九七五年初,《创业》在部分城市上映,江青认为影片有严重问题,下达了封杀令,并宣称要追查背景。紧接着,江青策划的批判文章,给《创业》罗列了十条罪状。编剧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申诉。十来年了,文艺天地里,就几个“样板戏”唱个不停,连毛泽东也觉得太单调乏味了。这回,他决定支持张天民一下。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张天民的信上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江青说这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张春桥则说:“主席说无大错,那还有中错和小错嘛!”在九月间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大骂张天民“谎报军情”,威逼张再给毛泽东写信认错。①见潘旭澜主编《新中国文学辞典》,第469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四人帮”垮台时,此事刚刚过去,毛泽东又可说委婉地批评了江青们。从这件事上揭批“四人帮”,既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又在政治上十分安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了杜书瀛、杨志杰、朱兵三人共同署名的长文《围绕电影〈创业〉展开的一场严重斗争》。文章这样开头:“从去年起,围绕着彩色故事片《创业》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②杜书瀛、杨志杰、朱兵:《围绕电影〈创业〉展开的一场严重斗争》,《解放军报》1976年11月5日。文章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细致地揭露了“四人帮”对《创业》的企图扼杀,处处强调“四人帮”与“毛主席指示”的“对抗”。对抗“毛主席”、反对“毛主席”,被认为是“四人帮”一贯的行径、最大的罪孽。这篇文章长达万余字,而发表时距“四人帮”被抓捕不到一个月,应该是文艺界最早揭批“四人帮”的有分量的长文了。
文艺界从“十七年”走过来的一些人,尤其是在那时期曾或长或短地担任文艺界领导职务者,对“文艺黑线专政”论自然有着腹诽。但是,这个“文艺黑线专政”论与毛泽东的关系太密切,在“四人帮”垮台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仍无人敢对之表示质疑。是在教育界的示范下,文艺界才大起胆子,在对“十七年文艺”的评价上“拨乱反正”的。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会,开了三个半月。这样的马拉松会议,在那时期并不罕见。这次会议的“成果”,是炮制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对“文革”前十七年间的教育工作做了两个基本估计:一、十七年间,在教育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十七年间,大多数教师和培养的学生,“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圈阅了这个《纪要》,认可了这种估计。这“两个估计”,自然也成了压在教育界头上的两座大山。然而,由于《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经过毛泽东的御批,“教育战线”对“四人帮”的揭批,也迟迟不敢碰这两个“估计”。一九七七年,邓小平最后一次落而后起,对教育界的“拨乱反正”十分重视,积极策划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此次讲话后以“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邓小平的讲话,一开始就对“两个估计”提出质疑:“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邓小平进而肯定了“十七年”中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虽然有邓小平“身先士卒”,教育部还是不敢贸然“跟进”。究其原因,在于邓小平那时还似乎立足未稳,还有些前程未卜,教育部的头儿怕跟着邓小平“犯错误”。在邓小平的强力支持、催促下,教育部才敢于明确推翻“两个估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文章强调:十七年间,“教育战线”上占“主导”地位的是“红线”,而不是所谓的“黑线专政”;至于教育界的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而不是“革命对象”。①教育部大批判组:《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8日。
教育界对“两个估计”的否定,给了有关方面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勇气。两天后的十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人士座谈。座谈会的目的是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为“十七年文学”从政治上、艺术上平反,恢复名誉。茅盾、刘白羽、张光年、贺敬之、冰心、吕骥、蔡若虹、李季、冯牧等人参加了座谈。参加会议者,回去后都写了文章。此后一段时间,《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这些文章。茅盾、刘白羽的文章率先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茅盾文章为《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刘白羽文章为《从“文艺黑线专政”到阴谋文艺》。这是最早的两篇明确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十一月二十七日,蔡若虹的《揭穿“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谋》和冯牧的《炮制“黑线专政”论是为了实行法西斯专政》两文又在《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十一月三十日,李季的文章《毛主席的革命文艺队伍是一支好队伍——斥“四人帮”对文艺队伍的诽谤和诬蔑》在《人民日报》发表;十二月二日,贺敬之的长文《必须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十二月四日,冰心的文章《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流毒不可低估》在《人民日报》发表;十二月五日,吕骥的文章《“黑线专政”论是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张光年的长文《驳“文艺黑线专政”论——从所谓“文艺黑线”的“黑八论”谈起》和李春光的短文《斩草必须除根》。
三
在《人民日报》的带动下,其他报刊也行动起来了。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张光年和李春光文章的同时,《光明日报》发表了曹禺的文章《不容抹煞的十七年》,同一天,上海的《文汇报》也发表了秦怡的文章《彻底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陶钝的长文《揭批“四人帮”摧残曲艺的罪行——批“文艺黑线专政”论》。报纸之外,相关刊物这一时期也发表了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一九七七年第三期的《上海文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出版)发表了罗荪的文章《“文艺黑线专政”论必须批判》;一九七八年第一期的《解放军文艺》发表魏巍的文章《骗局·阴谋·镣铐》。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北京召开大型座谈会,在北京的文学界人士一百余人参加了座谈。编辑部负责人张光年主持了会议。座谈会的主题是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同时也研讨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为《人民文学》题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黄镇、全国文联副主席茅盾都到会讲话。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以书面的方式参加了座谈。会后,署名“文化部批判组”的万字长文《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在《红旗》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发表,这是一篇特别有分量的文章。而一九七八年二月六日的《人民日报》则发表了署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评论组”的万字长文《“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和破灭》。
为了“批倒批臭”这“文艺黑线专政”论,当时的文艺界是花了大力气的。茅盾的文章,这样开头:“人民日报编辑部这个座谈会非常及时,非常必要。教育界的同志们已经开过这样的座谈会,愤怒声讨‘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我们也迫切需要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恶阴谋,彻底批判‘四人帮’在文艺理论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本质,肃清其流毒。”①茅盾:《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5日。在否定、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前,先强调教育界已经推倒了“两个估计”,这种做法为后来的不少文章所效仿。这说明,没有教育界率先否定“两个估计”,文艺界是不敢去碰这钦定的“黑线专政”论的。既然教育界可以推翻“两个估计”,文艺界就也可以否定“黑线专政”论——这是可以公开、明确地表达的意见。援教育界之例,更有着不便公开、明确地表达的意思:“两个估计”也是经“毛主席”圈阅的,教育界能推翻它,那么,同样经过“毛主席”认可的“黑线专政”论,文艺界就也能否定它了。茅盾接着说:“‘四人帮’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大肆污蔑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艺战线,称之为‘黑线专政’,这是狂妄地否定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在十七年中的主导地位,狂妄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②茅盾:《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5日。把“毛主席”与“四人帮”严格区分开来;把“毛主席”从“四人帮”的躯体上切割下来并让其成为“四人帮”的对立面,把“文艺黑线专政”论说成是对“毛主席”的“狂妄反对”,是茅盾的话语策略,此后的揭批文章,都运用和光大了这种策略。强调在“十七年”间“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占“主导地位”,这一口径是对邓小平的套用,也为此后的揭批文章所袭用。所谓占“主导地位”,直白地说,就是在“十七年”里,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处于“专政”地位,是“红线专政”而不是“黑线专政”。一般的文章,在强调“十七年”里是“红线”在“主导”时,避免了用“专政”一词,但也有人干脆弃“主导”而用“专政”,贺敬之就是如此:“特别重要的是,十七年的文艺领导权始终是牢牢掌握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手里的。是无产阶级在专资产阶级的政。十七年文艺战线的所有斗争,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这是最根本的事实。‘四人帮’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把我们党对文艺的领导全盘否定,这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③贺敬之:《必须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人民日报》1977年12月2日。在“十七年”里,文艺界是无产阶级在“专”资产阶级的“政”,是一条“红线”在“专”一条“黑线”的“政”,这其实是当时各地揭批文章共同强调的。
让毛泽东与“文艺黑线专政”论脱钩,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但又是必须做到的事。没有这种脱钩,揭批在当时就无法展开,“黑线专政”论就无法否定,“十七年文艺”就无法摆脱污名。毛泽东深度介入了江青炮制的《纪要》,毛泽东完全赞成“文艺黑线专政”的说法,这是文艺界尽人皆知的。但是,所有的揭批文章,都必须绝对不提及此事,都必须认定毛泽东与《纪要》、与“黑线专政”论没有任何关系。署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评论组”的长文《“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和破灭》,一开始就这样定调:“江青勾结林彪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是这样一个假左真右的典型”。“江青勾结林彪”,所以产生了《纪要》。账,只能算在江青、林彪头上。这篇文章,对《纪要》的出笼经过,说得很详细,甚至叙述了一些细节,甚至有这样的深层揭露:“随后,江青把她的那个亲信(也就是一九七四年‘四人帮’搞‘三箭齐发’时,江青安插在部队搞‘放火烧荒’的那个‘纵火犯’)从北京再次叫到上海。江青一个,陈伯达一个,张春桥一个,加上那个亲信,就是这么几个志同道合的‘老伙计’,又聚在上海的阴暗角落,精心炮制出那个丑化无产阶级专政的‘文艺黑线专政’论。”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评论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和破灭》,《人民日报》1978年2月6日。(括号中话为原文所有——引者按)这说明,对《纪要》出笼的过程,文艺界当时就知道得非常清楚,毛泽东与《纪要》的关系,自然也为人知晓。绝不提毛泽东与“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不提毛泽东这尊神。相反,《“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出笼和破灭》,时时请出毛泽东与“四人帮”对照,处处借助毛泽东揭批江青。在揭批的过程中,坚定明确地把毛泽东作为“四人帮”的对立面,坚定明确地把“黑线专政”论定位为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是所有文章共同的基调。
四
那时候,在毛泽东与《纪要》之间进行切割,还不算很难的事。毛泽东与《纪要》的关系,毛泽东对《纪要》三次精心修改,当时并未向社会公布,并不曾见诸任何文字,在作切割时,装作不知即可。真正困难的,是如何面对毛泽东“文革”前针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人们心里都清楚,“两个批示”其实已经对“十七年文艺”基本否定了,“文艺黑线专政”的指控,在“两个批示”中已经表达了,江青们炮制的《纪要》,不过是把“两个批示”的观点细致化、系统化而已。“两个批示”影响巨大、无人不晓。要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却又避“两个批示”而不谈,是不可能的。要为“十七年文艺”恢复名誉却又不理顺“两个批示”与“十七年文艺”的关系,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当文艺界着手推翻“黑线专政”论时,“两个批示”是横亘在眼前的两大障碍物。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比起教育界推翻“两个估计”来,文艺界推翻“黑线专政”论要艰难得多。
政治往往就是修辞的游戏。署名“文化部批判组”的长文《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样强调了“四人帮”对“两个批示”的歪曲篡改:“‘四人帮’特别是集中歪曲、篡改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年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他们不仅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两个批示妄加解释,而且公然断章取义,为其制造‘文艺黑线专政’论寻找‘根据’。一九六六年七月,江青伙同陈伯达,借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机,在编者按中引用批示时,故意把‘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这句话全部砍掉;公然把批示中的‘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改成了‘文艺界’。在以后的许多文章、讲话中,他们多次照此篡改,并且作了许多歪曲解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①文化部批判组:《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红旗》1978年第1期。如果以抠字眼的方式,认定“四人帮”歪曲篡改“两个批示”,也能说得过去。但那句被“砍掉”的话,实在只是一句用来缓和语气的话,而把“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改成“文艺界”,也不算十分离谱。但这毕竟是一种“把柄”。许多揭批文章,都以此为证,说明“四人帮”对“两个批示”的歪曲。
仅仅以个别字句为证,说明“四人帮”对“两个批示”的歪曲,还不能对“两个批示”和“黑线专政”论进行有效的切割。于是,《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又作了这样的强调: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才能理解“两个批示”的精神实质。所谓当时的“历史条件”,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文艺界进行了严重干扰破坏,使得文艺界的确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毒草”。而毛泽东正是针对此种现象而作出了“两个批示”。在这特定时期,“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文艺界有过一场较量,结果,当然是“毛主席”战胜了“刘少奇”。许多揭批文章,都这样强调“两个批示”是在特定时期、特定语境中对文艺界的否定。把整个“十七年文艺”的历史,解释成“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更是许多揭批文章共同的套路。例如,冯牧的文章写道:“一个十分清楚确定、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潮确实对文艺战线有过破坏和侵袭,而且在六十年代的某些部门(如像毛主席批评过的戏剧部门)表现得也的确很严重,但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艺战线却始终没有占过主导地位,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专政’。”②冯牧:《炮制“黑线专政”论是为了实行法西斯专政》,《人民日报》1977年11月27日。为“十七年文艺”平反,不能把“十七年”说成是风平浪静,要强调这期间是贯穿着激烈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但是,是“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是“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实施了“专政”。罗荪的文章,列举了“十七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倾向”的批判;一九五五年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九五七年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罗荪强调:“在这历次的斗争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起着主导作用,从而取得斗争的胜利”。③罗荪:《“文艺黑线专政”论必须批判》,《上海文艺》1977年第3期。
江青们认为“十七年”文艺界是“黑线专政”。“黑线”的具体内容,则是“黑八论”。在推翻这“黑线专政”论的过程中,如何处置这“黑八论”,也是一个问题。正面肯定这八种观点,为它们去污名化,是一种方式。但在当时的情形下,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就只有在承认这“八论”的确很“黑”的前提下,强调这“黑八论”在“十七年”里是受到严厉批判的,是并没有成为气候的,是谈不上对文艺界进行“专政”的。张光年的文章,主要就是论述“黑八论”在“十七年”里怎样受到鄙弃。张光年逐一道来:“写真实”论,“这是胡风集团在文艺上的代表性论点”,而一九五五年,“打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当然也把“写真实”论批倒了批臭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这是一种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是‘写真实’论的翻版”,而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〇年,文艺界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深入批判”;“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这是在三年困难期间,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影响下,产生出来的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谬论”,而“毛主席及时觉察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逆流的危害性,指示中国作家协会查一查”,于是,中国作协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之“揭发和批判”,《文艺报》也发表了批判文章①张光年:《驳“文艺黑线专政”论——从所谓“文艺黑线”的“黑八论”谈起》,《人民日报》1977年12月7日。……张光年的文章,表明他们与江青们都认为“十七年”的文艺界存在着一条“黑线”,区别只在于,江青们认为这条“黑线”在文艺界实施了“专政”,而张光年们则认为这条“黑线”是被“专政”,至于对“黑线”实行“专政”者,当然是那条“红线”。
五
如今读这些意在“拨乱反正”的文章,时常忍俊不禁。例如,“文化部批判组”的文章写道:“‘四人帮’……甚至把毛主席亲笔加进一些文件和文章里的话也当作‘文艺黑线’的‘谬论’加以‘批判’,真是猖狂到了极点!”②文化部批判组:《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红旗》1978年第1期。在“十七年”里,许多关于文艺的文件、文章,都经过毛泽东批阅、修改。不少文件、文章里,都有些话实际出自毛泽东手笔。江青们要彻底否定“十七年”,就必须对这类文件、文章进行批判,而在批判的时候,自然不能把毛泽东加上的话分离出来,只能把毛泽东修改之事当成并不存在。当他们批判这些文件、文章时,实际上也批判了毛泽东加进去的那些话。“文化部批判组”的文章对这一点进行揭批,实在特别引人发笑。因为在这一点上,对“四人帮”的揭批者,与“四人帮”堪称异曲同工,甚至更“工”。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是“百步笑五十步”。“文革”前的有些文件、文章,虽然经过毛泽东修改,但是,没有哪一份关于文艺的文件、文章,像江青等人炮制的《纪要》那样令毛泽东上心。《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精心修改,重要改动累计数十处,还加上了大段的话。当茅盾、刘白羽、张光年等人以及“文化部批判组”批判《纪要》时,那些出自毛泽东之手的话,当然也一起受到了批判。当时,甚至现在,也都有人认为,这是“猖狂到了极点”的。
在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的过程中,冰心和曹禺的文章显得很特别。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目的是为“十七年文艺”平反,因此,肯定、歌颂“十七年文艺”,是题中应有之义。既然要论证“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是对“十七年文艺”的诬蔑,那“十七年文艺”的“辉煌成就”就是必须的论据。罗列“十七年文艺”的“辉煌成就”并歌颂之,许多揭批文章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冰心和曹禺的文章却十分另类。冰心参加《人民日报》召开的座谈会后,写了短文《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流毒不可低估》。文章只说对这“黑线专政”论的“流毒和影响,我们绝不能小看,绝不能低估”,并无片言只语明确地肯定、赞美“十七年文艺”。避开对“十七年文艺”的评价,却又要批判“四人帮”对“十七年文艺”的“诬蔑”,文章如何做呢?冰心别出心裁地说了一件“文革”期间江青对“儿歌园地”的摧残。一九七四年,江青插手“儿歌园地”,让儿歌变得非驴非马。冰心以自己一个外孙为例,说明江青一伙“连天真烂漫的孩子都不放过”。说完这件事后,冰心又说“四人帮”一伙“在文风上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然后以自己“最近看到的一首诗”为例,说明“四人帮”一伙“说假话、说空话、说绝话”的流毒有多么严重。①谢冰心:《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流毒不可低估》,《人民日报》,1977年12月4日文章的核心内容就是这两件事。严格说来,冰心的文章其实是文不对题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冰心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态。批判“四人帮”,冰心无疑是乐意的。推翻“文艺黑线专政”论,冰心自然也是赞成的。但是,肯定、赞美“十七年”,冰心是犹豫的,是不乐意的,是难以做到的。冰心参加了座谈会,同意写批判文章,表明她对“文革”、对江青一伙满怀痛恨,乐意加入揭批的行列。但是,“十七年文艺”在冰心的记忆中也绝不是美好的。江青一伙说“十七年”的文艺界被“黑线”所“专政”,固然可笑。但是,正如贺敬之等人所说的,“十七年”间,文艺界的确有一条政治路线在“主导”着,在“专政”着。“红线”也好,“黑线”也罢,有一条“线”在规范着、约束着所有人。而只要文艺界被某种力量所“专政”,就绝不能说是合理的,就绝不应该得到肯定、赞美。不愿意肯定、赞美“十七年”,却又愿意写文章批判“四人帮”对“十七年”的“诬蔑”,冰心便只能以“旁门左道”的方式成文。文章虽然短小,其实煞费苦心。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曹禺的文章。曹禺的文章题为《不容抹煞的十七年》。按理,应该正面列举“十七年”的“辉煌成就”,才算是合乎题义。但是,曹禺的文章,也可谓别出机杼。那“十七年”,留给曹禺的,有着太多不愉快的记忆。在那“十七年”,曹禺有着太多的苦闷、彷徨。一个如此优秀的剧作家,在“十七年”里正值盛年,创作成就却乏善可陈。曹禺自身的遭遇,曹禺自身的失败,就证明着那“十七年”是不值得肯定的。进入五十年代,曹禺以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开始新的艺术人生,以修改《雷雨》、《日出》、《北京人》这些旧作和杰作开始自己在新时代的戏剧生涯。在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后,一九五一年,曹禺开始写《明朗的天》。田本相在《曹禺传》说,曹禺后来对此有这样的回忆:“尽管当时我很吃力,但仍然是很想去适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硬着头皮去写的,但现在看来,是相当被动的,我那时也说不清是怎样一种味道。”②田本相:《曹禺传》,第379、472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那时,曹禺可谓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样一种荒谬的铁则所束缚、所“专政”。这样写出的东西,当然与那些旧作不可同日而语。画家黄永玉曾说“十七年”里的曹禺“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③田本相:《曹禺传》,第379、472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对于自己的萎缩、衰退,曹禺当然比任何人都清楚,也肯定比任何人都痛心。既如此,要他由衷地肯定、赞美“十七年”,那是不可能的。但曹禺毕竟与冰心不同。在“十七年”里,他曾有过“势位”,现在,“四人帮”打倒了,他还可能再有“势位”。他难以像冰心那样,连一句肯定、赞美“十七年”的套话都不说。在《不容抹煞的十七年》这篇批判文章中,开头和结尾部分有几句肯定“十七年”的套话,文章主体部分,则是对周恩来的回忆和怀念。曹禺述说着周恩来来看戏时怎样平易近人,平日里对自己怎样关心爱护。一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却主要是在怀念周恩来;一篇本该为“十七年文艺”评功摆好的文章,却主要是在叙述与周恩来接触时的细节,也打的是“擦边球”。
当时批判“黑线专政”论、为“十七年文艺”极力辩护者,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希望文艺重返“十七年”的轨道。他们觉得理应如此。他们认为必须如此。他们相信不能不如此。然而,历史的发展,有时还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在他们奋力推翻“黑线专政”论、一心想让文艺回到“十七年”的“正道”时,“伤痕文艺”在悄然兴起。“伤痕文艺”中的许多作品,虽然带着“十七年文艺”的遗风,有的甚至不无“文革文艺”的痕迹,但也明显地撑破了“十七年文艺”的规范,在总体上,不但是对“文革文艺”的否定,也与“十七年文艺”挥手告别。政治也好,经济也好,文化也好,重返“十七年”,只能是闹剧。这样的闹剧,还真不难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