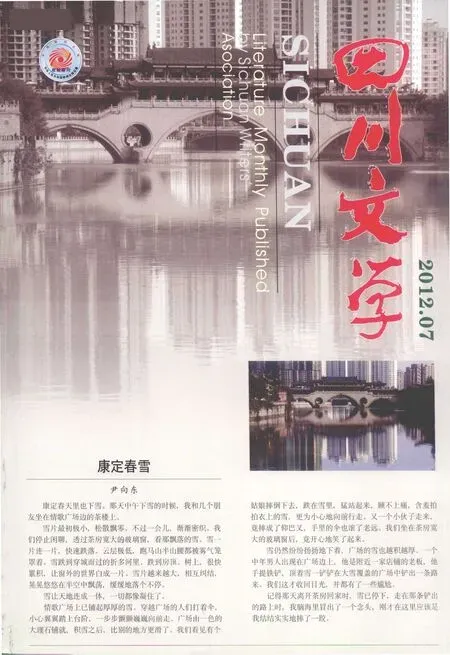川 断
□汪文勤
清晨7点20分,川断的手机响了,他的手机从来不会在这个点儿响。
刚刚过完59岁生日的川断,每晚的睡眠都是支离破碎的,好像切成好几截的腊肠。恰恰这个时间是他最重要的睡眠时间,一天的精力全靠这点觉撑着。
手机不停地响着,不像是打错的。川断勉强自己来接听这个电话。
“爸爸、爸爸,起床了!”
川断唔了一声,便怔住了。
电话里是一个小男孩的声音,这个声音冲破川断的耳膜,进入他半梦半醒的脑海里,好像一面响锣掉进了山谷,立刻溅起一串回声,不绝如缕。
川断的大脑一片空白,小男孩叫爸爸的声音竟不住地在空荡荡的脑壳里回旋起来。这个饱满而明亮的声音像一支小号,骤然吹响,川断凝神听着,整个人动弹不得。
按常理,川断应该说三个字,“打错了”,然后放下电话继续睡觉。但是,他发现自己举着手机紧贴着耳朵,一点儿不想放下来。于是,他的无语和犹豫,激励着小男孩用更大的声音叫起来,或许孩子以为爸爸睡得太香甜了吧。
“起来了,爸爸。别说我没叫你啊!在学校运动场比赛,我们是黄队。来不及了,我走了,再见,爸爸!”
小男孩挂断了电话。川断仍旧举着,里面的嘟嘟声,在川断听来,全部是“爸爸!爸爸!爸爸!”一声比一声紧密。
不知过了多久,川断放下电话,躺下来想再睡一会儿,但闯进脑海里的那一声爸爸却怎样都赶不出去了。
在一个59岁男人的世界里,四季的界限早已模糊不清,春天何时来,二月的风里飘荡着春的气息,兴许已经不是这个年龄的男人所能够感受到的。但是,小男孩不由分说,劈头盖脸叫爸爸的声音,好像用春天柔软的柳枝做成的柳笛,咂咂口,用力一吹就会响"啵——啵"——这哪里只是小男孩叫爸爸的声音。
柳笛吹响了,春天发声了,春天的声音就是小男孩叫爸爸的声音。
川断不睡了,柳笛在耳边那么一吹,心中竟有了一小片春色,痒痒的,绒绒的,这种感觉久已不在了,兴许是在他23岁,或者25岁时,很不经意的一些瞬间里,闪过那么一丝丝,好像柳絮飞进了脖颈,杨花沾在唇上,留不下来,捉不住,也掸不掉,转头也就忘记了,不在春田里,不再经历,便不再记忆。
“爸爸!爸爸,起床了!”小男孩儿误打进来的一个电话,真把习惯睡懒觉的川断叫起来了。他走进卫生间开始洗脸刷牙,许久以来,他都懒得多看自己一眼,胡子、眉毛、头发都像野草,自由发旺,自由生长。
现如今导演、唱歌的都喜欢留胡子和头发,对他们来讲,这个装扮是他们对世界的一个宣告,身份的宣告,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是人,但绝不是普通人,他们羞于和普通人为伍,似乎头发不长,胡子不长,就不能入行似的,长发和长须是进入演艺界的护照。有时候,电门还没摸着呢,先把胡子头发留起来,束在脑后了。川断从十七岁开始就触电了,只不过那时说的触电就是指电工,而不是指电影电视什么的。四十多年前,他是一个肩挎着灰白色帆布工具袋的英俊电工,在北京一家大型的兵工厂工作。后来,川断很自然地把自己摆渡到影视制作行业,他自认为这是一个必然。
这些年来,川断就一直混迹于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剧组里,游走在祖国大地上,剧组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生态环境,这里允许异类的存在。所以,不知不觉间,川断原本中规中矩的人生轨迹偏行一隅了,许多该停的站没有停靠,该看的风景没有看,头发一点点长长了,胡子也留起来了,他居无定所,每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一部片子,一个剧,从头至尾,再精彩的故事,拆开了再一点点拼装起来,又熬人,又枯燥乏味儿,如同孩子们面对乐高玩具,拆开了看一块一块儿的,完全看不出名堂,一旦拼装成形,才有了意趣。川断在剧组里干杂活儿,什么都干过,每天看见的都是乐高的零配件。事实上,川断并没有玩过乐高,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在孔雀的背后,看见的永远是孔雀的屁股,开屏是从正面才能看到的风光。川断是站在孔雀后面的人。孔雀屁股有什么好看,臭烘烘的。但是,有时候,臭也是一种香,好像榴莲,好像臭豆腐。川断习惯了,他已经离不开剧组这个特殊的环境了。好像有人吸毒成瘾,无法戒除,不是不知道那趣味儿是恶趣,会害死自己,但人生太清醒不易过,半梦半醒就容易打发。
后来这三十年真是混过来的,好像数得出来,吃过几顿饭,睡过几次懒觉,有时工作到后半夜,其实常常是后半夜,喝得醺醺然,倒头睡下,第二天上午起来时头疼欲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头发胡子都灰白起来,好像小时候看见的街角粮店里打面的工人,除了眼珠儿以外,别处都白着。后来,慢慢地,川断再也不愿意在镜子里看见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没有谁在意他,也没有谁能让他在意。罢罢罢!他想放自己一马。
就这样59岁的川断,从里到外透露出来的气质就是对自己的放手。所谓放浪形骸大致就是他这种样子吧。身体和脸都好像鸡蛋煎饼,随意地摊开去,谁还收得拢呢?
一直在刷牙的川断,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在看一个不认识的人,这是我吗?他问自己。他用牙刷柄扎一下自己的腮,痛还是痛的,是自己没错,是一个叫川断的人,但为什么会这样陌生?像一个来历不明,去向不明的人,有谁认得和记得这样一个人呢?百年以后将没有一个人会纪念他吧?
“我这他妈的,混成什么样了?什么都不是。”
川断的心往下沉,有点灰。
正当此时,又听见小男孩在叫:“爸爸,爸爸!起床了!”
川断使劲摆摆头,想搞清楚状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仅仅是一个打错的电话吗?为什么这个声音又出现了?
如果一个人的早晨是在小公鸡的“喔-喔喔”的叫声中,在小男孩清脆的声音“爸爸,起床了!”中开始的,那是何等真切的日子。阳光从墙肩上轻轻跳下来,一点点挪着,好像早年那些小脚的奶奶,从一面墙挪到对面那堵墙,正好是一天的光阴,日子被慢慢的暖暖的阳光烘焙着,厚厚的尘土都出了香味儿,可以咀嚼、品尝。有人叫爸爸的早晨,是多么真切的早晨,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那可能会是他川断的人生吗?他早已经不做这样的梦了。像他的名字预示的一样,川断,川断。生命一条河,他的生命之河断流了。
川断不无厌弃地看着镜中的自己,这鸡蛋煎饼已经不是新鲜的刚摊出来的煎饼了,而是一张残剩的,没有形状的,也许从不曾规整过的,现在更是起了毛边,缺了边角的,快要被扔进垃圾箱的废弃物……现在丢掉还有点不舍得,但吃下去一定会坏肚子。川断第一次感到有一点伤心,觉得自己有点可怜。难道在这世上活着的川断就不应该有另外一种生涯吗?比如:在合适的时间,遇见了合适的女人,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每天早晨,儿子会用柳笛的声音叫醒他,在他去学校之前。如果今天早晨的电话没打错,自己真的是被自己的儿子叫醒……川断问了自己一个无解的问题:这样一种再平常不过的、也本应该是自己的这种日子,自己什么时候丢掉了呢?应该叫自己爸爸的那个孩子在哪里呢?他本应有的儿子还会对他说些什么呢?
川断仔细回忆小男孩在电话中所讲的每一个细节,学校、比赛、黄队……川断在心里拼凑着这些碎片。这是谁正拥有的幸福生活呢?此刻,他无比痛恨自己是个没有家,没有孩子的老光棍。如今的时代比较宽厚,容得下各色人等,老光棍似乎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但是,在川断经历过的、现在还记忆犹新的上个世纪,老光棍是一种很狼狈的人生,如果是在一个村庄里,他除了要背负“绝户头儿”的悲情名声以外,差不多和身体有残障的人在一个级别上。人家家里有喜事请客,这样的人怕是不能上桌的。如今,时代变了,单身成了一种选择,而不是无奈,在小男孩叫爸爸的声音出现以前,川断也许并没有质疑过自己的生活方式。但现在不同了,小男孩柳笛一样的声音叫川断的心底里冻结的一种东西松动了。
川断开始修剪满脸的胡须,力求使自己的脸看上去有点形状,起初只是想把野草似的胡须稍剪一下,川断不是一个果敢的人,这满脸的胡须到底也是一寸寸长出来的,他可以承受这个缓慢生长的过程,即使此刻想有点什么变化,也不会让坡太陡,下得失去了方寸。可是,让他自己没想到的是,一寸又一寸,他居然把胡须弄干净了,他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觉得很久很久没有见过自己了。他用十根手指拢着头发,心想,头发也该收拾收拾了。
川断一刻都不能停下来,只要停下来一驻足,一凝神就听见那个声音在叫:“爸爸,起床了!”收拾停当的川断试图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去干点平常事,想点自己惯常想的事,或许,给什么人打个电话,约点什么事儿谈谈,在咖啡馆之类的地方,那个时间会过得很快,不觉就是一天,不觉又是一天。
手机上的联络人从头看到尾,没有哪个名字让他有兴趣去拨号。甚至排在最前面的白小姐的电话,以往,白小姐是一个他抗拒不了的诱惑,她在一家男士养生馆工作,她大而深邃的眼睛,柔软无骨的小手,尤其是她为他按摩头部时,她鼻孔里呼出的气息,小小的,温温的,带着青草的香气喷在他的脸上,那是他内心深处的美酒。他悄悄地,秘密地消受着,从来未向任何人说起过,他片刻地沉醉其中,有时候,他想自己是中了魔,对一种隐秘的刺激上瘾,他说不清楚,也从来没有细究过,每逢此刻,他会忍不住摁那个名字的号码,约一个近在眼前的时间,飞速地赶过去,躲在那一双小手下,陷在那一片气息里,陷下去,不愿自拔。
可是今天,川断的手指数次从那个名字上滑过,但他没有拨号。紧接着他看见早晨那个误打进来的电话号码。
“爸爸,起床了!”
这次听到的声音不是从话机里,而是在身旁某处的空气里,这个声音没有商量,更无歉疚,却好似有一点命令的成分在里面。
川断忽然想到,如果是这个声音在耳旁,别说是睡着了,即便是长眠了,也会被激励着翻身坐起的。这个声音让疲惫的人生有盼望,是兴奋剂,一听见就会起来去行动。
是的,川断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行动,但他已经开始行动了。他迷迷糊糊地剪掉了胡须,接下来,似乎还要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川断自己也不能确定。是的,他又不自主地走出门去,通常,他是不会这么早出门的。
走到大街上,看见有小孩子手里握着煎饼,一边吃,一边去上学,不是爷爷奶奶陪着,就是爸爸妈妈跟着。小一点的孩子被大人牵着手走。
“爸爸!”
身后又是柳笛一样的声音。
川断急回头,见一小男孩用双手从背后托着沉甸甸的书包,一路小跑追一个脚步匆匆的男人。小孩可能在用一个铁皮的铅笔盒,他一跑,铅笔在盒子里铛铛响着,川断清晰地忆起自己的童年,也是这样背着书包跑着,也有刷刷的响声,只是自己那时没有真正的铅笔盒,几根铅笔头装在卫生所废弃的装青霉素针剂的纸盒子里。有一个真正的会发出清脆响声的铅笔盒,是川断比天还大的梦想。
这样的回想,让川断激动起来。原来自己也小过,也做过梦。
那个爸爸站住,歪过头看自己的儿子。
“快点,要迟到了。”
儿子紧跑几步追上爸爸,然后两人用急行军的速度向前赶。
原来并不清楚自己要何去何从的川断,竟不知不觉地跟着小男孩往前去。来到一所小学校门口,小男孩儿和爸爸告别,挥挥小手跑进了校门,川断和送孩子们上学的大人们都站在门外,川断痴痴地站着看,尽管他没有一儿半女在中间。孩子们进教室了,大人们也散了,校园里空空荡荡的,只有川断还在门口站着,一间普通的小学校是他多少年都不曾多看一眼的陌生的地方,可这会儿突然变得亲切极了。
他看着一扇扇四四方方的窗口,听着孩子们清朗的读书的声音,竟有了一种莫名的感动。难道冥冥之中,真是自己的儿子在红尘之外的远方呼唤着自己吗?
“爸爸,起床了!”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保安观察了半晌,觉得川断形迹可疑。
“噢,没什么,孩子上学了,我随便看看!”川断神色惶恐地说。
“没事儿别在这儿转悠,接孩子下午3点半再来。”
保安说着,用手晃了晃已经关上的学校大门。
“能进去看看学生们比赛吗?黄队……”不等川断说完,保安说:
“有家长通知单吗?”
看川断一脸的张皇,保安又问:“孩子是几年级哪一班的?打班主任电话也行。”
川断仔细想着早上那个电话的细节,没有提供这些内容,是啊!爸爸哪里会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几年级几班?但是他只知道今天他穿黄色球衣。突然,川断担心起来如果小男孩不再打电话找爸爸,爸爸或许会错过看他比赛。小男孩一定会失望的。
川断第一次发现自己也是个心思缜密的人,居然会如此在意一个打错的电话,后来,他惊奇地发现,小男孩的声音并不在身体之外的什么地方,而是在自己的脑海深处,比想象的要深许多。同时,那个呼唤声一直持续着,川断注意时就听见了,稍一分心就忽略了,无论听或不听,小男孩一直在叫:爸爸!
川断痛苦地发现,这个声音早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叫了又叫,从来就没停下来过。只怪自己猪毛塞了耳朵眼,没听见。
叫声迫使川断没有了退路,他简直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回到今早电话来之前的光景。回到昨天,继续用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活下去。
在守门的保安眼中,川断一定是一个失常的人。因为保安已回到自己的小门房里,一边看手机,一边吃吃地笑,不再理会川断。
川断看见马路对面正好是本市最大的男科医院,他知道,要想把在自己生命中呼唤着的那个小男孩变成真的,他必须得再干点什么。他想堂而皇之地进入这所学校的大门,大大方方坐在球场边上,给穿黄球衣的自己的儿子大声喝彩,鼓掌加油。一大早可以被一个柳笛一样的小男孩的声音叫醒,那是所有的日子里的幸福加起来都不及的幸福。想得到这个幸福吗?川断发现自己的回答一点都不含糊,那之前的玩世不恭,不在意,没心没肺都是伪装。
川断准确地从医院专家一览表上找出了能解决自己问题的一位老专家,看照片,足有八十岁了吧,是退休后又被返聘回来的,他叫胡开雪,似乎每一个老中医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名字,他们的名字预备了他们悬壶济世的一生。
尽管这样,老人家在写下患者姓名时,还是被川断的名字给吸引了。
“川断,川——断。你的名字是一味儿中药啊!自己晓得吗?”
川断笑了,答非所问:“名字不好啊!给叫得断子绝孙了呢!”
说话间,脑海深处又响起小男孩的声音:“爸爸,起床了……”
“非也。”老中医一手搭在脉上,一手在纸上划字。“你知道吗?川断的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字,叫做续。川断续,断了,再续上。川断续专治骨折、骨裂。用川断续外敷,骨头在里面就接好了。”
川断听得浑身一阵酥软,呼吸竟也急促起来,脑海深处那个爸爸的叫声,一下子跳出来,在耳畔好像春天的第一声柳笛,把耳膜鼓得生疼。
老中医望也望了,闻也闻了,切也切了,只剩下问了,老中医开始问。
川断却因为一个“续”字狂喜着,除了听见不远处叫爸爸的童声,一时间,别的都听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