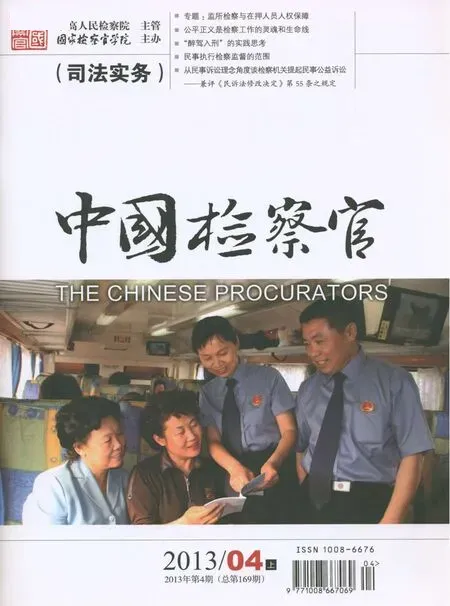构建中国式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
文◎陈卫东 孙 皓
构建中国式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
文◎陈卫东*孙 皓**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10008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事诉讼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00081]
2012年的刑诉法修改,在总则部分加入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以表明对所有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关注。而在这其中,最需要予以保障的无疑是被追诉者之人权,因为他们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身处弱势一方;而在前者之中,最需要加以呵护的则是羁押状态下被追诉者之人权。这是基于人身自由所受的剥夺,其权利所呈现的脆弱运行状态。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明确其应受保护的权利并且采取措施予以保障,固然十分重要。而一旦其不幸遭受酷刑、不人道待遇、有辱人格待遇等行为的侵犯,赋予其有效的救济渠道则是弥补权利损害的最后机遇。新刑诉法第115条确立了刑事诉讼中的侦查违法行为申诉控告处理机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投诉处理机制,是被追诉人获得救济的渠道。在我国的看守所中,监所检察制度是在押人员寻求投诉的基本路径,然而与域外那些成型的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相比,却还有诸多值得改造的内容。
一、投诉处理机制的基本特征
(一)主体中立性
在押人员实施投诉行为,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受理投诉的主体值得信赖。那么怎样的主体才能获得在押人员的信任呢?首先,这个主体必须拥有法律的授权,唯有如此,才能在制度层面拥有权威性。其次,这样一个主体必须独立于羁押场所,唯有如此,才能拥有超然于利益相关方的中立地位。试想,倘若有权处置投诉的主体是潜在的被投诉者,在押人员的投诉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才能付诸实施?即便在押人员有这样的胆识,最终获得公正处理的概率又有几成呢?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是程序公正的基本前提。作为现代羁押场所投诉机制的“先驱”,荷兰在国内就设有专门委员会,受理并处置在押人员的投诉事项。这个委员会由司法部任命,权力来自《荷兰监狱原则法案》的授予,独立于任何羁押场所。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包括法官、律师、教师、医生等等,他们代表普通民众解决在押人员与羁押场所之间的争议。此外,还有另一个类似的委员会,专司投诉机制的上诉程序。这两个委员会根据事实,做出无偏见、具有约束力的裁决,一般都会被信服,不仅是在押人员,也包括羁押场所。[1]
(二)调查有效性
投诉能否获得公正的结果,调查活动的质量至关重要。这就要求具有调查权的主体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触并保留相关的证据材料,一方面,调查主体应当享有法律认可的必要权限;另一方面,羁押场所应当无条件地向调查者公开卷宗档案、医疗记录、监控录像等官方资料,确保客观事实的还原。真正有效的调查活动应当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即迅速、独立、全面、透明。调查活动应当以书面化为必要特征,卷宗记录将成为各方在听证、上诉等程序中进行对质的依据,同时,有权主体的最终裁决也务必以调查活动的结果为基础。
(三)程序规范性
从性质上分析,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属于行政程序,然而在世界范围内,该机制已然呈现出“准司法化”甚至是“司法化”的特征。例如在荷兰,从投诉机制的启动到终结,无不体现程序正义的理念。首先,每一位在押人员在进入羁押场所伊始,都接受了充分的权利告知,确保了解并掌握投诉的方法和渠道。为了打消顾虑,保密性被作为原则加以贯彻。每个羁押场所都安置了投诉箱,并且只能由处理投诉的委员会开启,投诉材料会通过密封信笺,秘密投入箱中。其次,在投诉程序进行的过程中,在押人员可以聘请律师作为法律帮助人。律师可以帮助其收集证据、参与听证,尽可能地提供法律层面的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控辩平衡的理念,即便在押人员深陷囹圄,也不必对投诉结果持悲观态度。律师的介入拉近了在押人员与羁押场所之间的实力差距。再次,听证程序的存在使双方可以“当面锣对面鼓”地展开对质。听证程序是典型的司法机制,展现了公开性、参与性的程序理念。这样一个程序平台的存在,消弭了“暗箱操作”的生存土壤,增强了投诉处理机制的可信度;而在押人员对于程序的充分参与,也尊重了其主体地位,使其能充分发表自己的观点,享有程序利益;而听证程序中存在的举证、质证环节,也为事实的客观揭露最大程度地做好了铺垫。最后,上诉机制的存在使在押人员拥有了获得进一步救济的途径。这是程序的自我修正机会,避免因个别性偏差,而致在押人员于山穷水尽的境地。除了国内的救济程序,未获得满意结果的投诉人还可以向欧洲人权法院或欧洲预防酷刑委员会进一步寻求帮助。[2]在美国,在押人员可以通过监狱诉讼的形式获得法律层面的救济,在程序属性上,则带有绝对的司法化特征,使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被诉讼程序吸收。
二、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的新探索
2011年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与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检察院合作承担的“看守所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试点项目在当地正式拉开帷幕。当地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了《芜湖市人民检察院、芜湖市公安局看守所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实施办法(试行)》,为试点的开展提供了规范依据。[3]其中针对监所检察在此领域的不足,新的改革方案做出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探索。
(一)引入公民参与
借鉴荷兰等国家的经验,芜湖的试点专门设置了一个投诉处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来自普通的社会公民,主要职责是受理在押人员不服投诉处理结果的复核申请,带有救济审的特征。公民的参与可以成为监所检察的有效制衡力量,使法律监督者亦受到监督,从而缓解驻所检察官因身份尴尬而造成的困境。“司法活动的人民性要求在检察和审判过程中公民的合法有序的直接参与。”[4]笔者始终认为,民众的参与是解决当前司法改革诸多“疑难杂症”的良药,对于投诉处理机制而言也概莫能外。芜湖试点引入公民组成的投诉处理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投诉处理机制的公信力。当然,碍于法律授权和现实司法环境所囿,这个委员会并不享有做出具有法律效力裁决的权限,仅带有咨询性质;加之其选任方式完全受制于监所检察部门,因此还称不上是具有中立性地位的投诉处理主体,尚无法起到与荷兰投诉委员会相类似的作用。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芜湖的尝试起到了“先锋”效应。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公民参与的新模式也必将不断的发展,在权能上不断扩充、完善,形成成熟的经验,进而为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提供参考。
(二)强化程序公正
在芜湖的试点中,为了便于驻所检察官的实际应用,投诉处理机制呈现出了“精密化”的特征。首先,以在押人员投诉的保密性为前提,丰富在押人员的投诉渠道,如呼叫器、约谈机制、投诉信箱、律师、亲属代行投诉等,鼓励监室中形成投诉氛围。其次,明确投诉处理主体的调查方式,包括询问、查询、调取等非强制性手段。第三,在必要情况下可开展听证活动,赋予在押人员程序参与权利。第四,明确投诉处理期限,规定处理期间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体现及时性原则。第五,赋予投诉者上诉权利,当投诉者不满初步的处理结果时,可以向监所检察部门寻求进一步救济的机会,在听取投诉处理委员会的意见后,检察机关将做出最终的裁决。通过上述一系列细致的规定,投诉处理机制的程序公正特征得到进一步的凸显,在押人员获得了更多的程序利益。当然,目前的程序设计尚不足以令投诉机制彻底转化为“准司法”程序,例如律师还无法直接参与投诉进程、听证程序的内容尚不完善等。随着改革的日益推进,司法系统的结构与内涵势必会植入到投诉处理机制中去,在押人员的主体地位也势必会得到尊重。
总之,芜湖的经验为我国的在押人员投诉机制提供了难得的试验范本。笔者相信,中国式的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是值得期待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也一定会在投诉处理机制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和弘扬。
注释:
[1]Gerard de Jonge:《在押人员应保有自身权利》,孙皓译,载《法制日报》2010年8月18日,第12版。
[2]Miranda Boone,Martin Moerings,Dutch Prisons,BJu Legal Publishers,The Hague,2007.p209—223.
[3]张伯晋:《安徽芜湖:试水“在押人员投诉处理机制》,载《检察日报》2011年8月1日,第3版。
[4]郭道晖:《尊重公民的司法参与权》,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