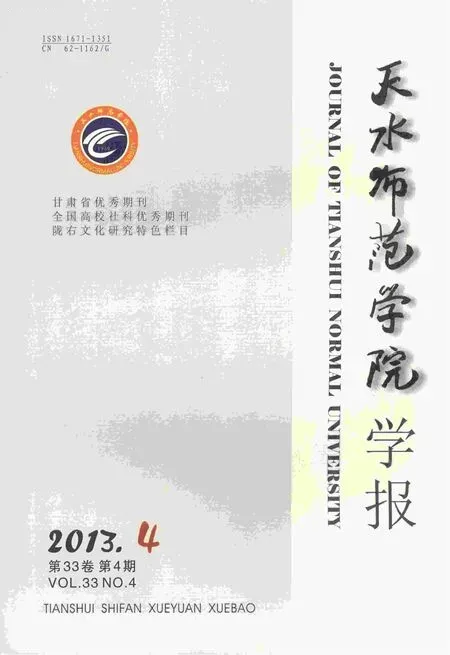论陇右的地域文学意蕴及其意义
王忠禄
(兰州城市学院 中文系,甘肃 兰州 730070)
陇右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中国古史上占有显赫地位。传说中的人祖伏羲和抟土造人的女娲,其活动领域就在今甘肃天水一带。位列五帝之首的黄帝亦在今陇东黄土高原上留下了许多遗踪。大禹治水,履迹遍及陇右大地。为华夏统一奠定历史基石的周、秦部族,其发祥地就在今甘肃东部。《史记》、《汉书》所书秦皇汉武出回中、登笄头、巡陇西、达祖厉,均在今甘肃东境。陇右也是汉唐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地处中原通西域的要道上,战略及交通地位十分突出。陇右多高原山地、沙漠戈壁、冰川雪山、石山裸地。丰富多彩的历史人文景观和奇特壮美的自然风光,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游览凭吊,与此相关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值得重视。就学界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从地域文学的角度对陇右的关注不够,本文结合陇右的文化特征以及历代文学作品对此加以研究。
一、陇右的地域文化特征
首先,陇右属于地理概念,原指陇山以西地区,约相当于今甘肃省黄河以东、陇山及其支脉六盘山以西之地。唐代置陇右道,辖境延达河西走廊及其周边今青海、新疆部分地区。北宋时的甘肃,除今兰州以西的河西地区为西夏据有外,大致包括现甘肃辖境。南宋时,甘肃仅保留武都一隅,其余地区为金人据有,河西地区仍为西夏占有。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取地处河西走廊的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首字,设甘肃行中书省,除辖今甘肃大部地区外,兼领今青、宁、新、内蒙部分地区。而黄河以东的中部、东部和南部,不属甘肃辖区。明代的甘肃没有行省建制,陕西辖今甘肃全境。后人习惯上多以陇右泛指今甘肃省地区,既包括古时河西走廊诸州郡,也涵盖今甘肃庆阳、平凉等陇东之地。
其次,陇右是周、秦文化的发源地,陇右文化具有粗犷悍厉、雄浑慷慨的特征。历史上,这里曾是多民族聚居区,先秦时期的西戎、氐、羌等民族,以游牧涉猎和强健勇猛见长。秦人入居陇右后,在与西戎长期争夺与交流中,练就了粗犷悍厉、果敢勇猛的民族气质。秦人那种轻死重义、奖励耕战的价值追求和不畏艰险、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构成了秦文化的一大特色。[1]我们从秦人早期作品《石鼓文》、《秦风》中歌颂车马田猎、赳赳勇夫的内容,可以看出陇右地域文化形成之初的原始面貌。自先秦以来“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的传统习俗和“天水、陇西山多林木”的环境条件的紧密结合,使陇右文化“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2]卷69《赵充国传》从汉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如意”[3]卷20《武帝征和四年》到隋唐时期的陇右,“其人性犹质木,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冠盗矣。”[4]卷29《地理志》
体现的都是陇人粗悍的气质和陇右文化苍劲慷慨的特色。
最后,陇人具有重视现世、重功趋利的历史传统。流传久远的伏羲、女娲、与日逐走的夸父以及商周之际,在庆阳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终成大业的公刘和牧马兴于天水一带的嬴秦先祖非子,都是勇于征服自然的陇人的杰出代表。《诗经》中有关周、秦的壮丽诗篇,更是陇人富于现实主义精神,勇敢面向现实的艺术体现。所有这一切,说明陇右文化在粗犷、慷慨的原始气息外,多了一层不畏艰难、积极进取的人文精神,在这种地域文化的熏陶下,所形成的陇右的地域文学,不仅颇具特征,而且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陇右地域文化特征进入文学的演变历程及意义
陇右独有的地域文化特征在历代文学作品中有着充分的体现。我们将这类作品称之为陇右文学(当然,这跟传统意义上的陇右文学有很大的不同。它是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以陇右雄奇壮观的自然风貌和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为视角来观照的地域文学)。下面试就历代陇右文学发展演变的历程及其意义加以探讨。
(一)周秦至隋——发展期
《诗经·秦风·终南》借外貌服饰的描写,表达了对秦襄公的敬仰和赞美之情,字里行间洋溢着秦人创业成功的喜悦和自豪之情。《诗经·秦风·驷驖》对狩猎游园的描写,正是陇右秦人尚武精神的形象展示。《诗经·秦风·小戎》中所写的妻子“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是对远征西戎的丈夫的深情怀念,是后代思妇诗的滥觞。《诗经·秦风·无衣》讴歌了秦军战士同仇敌忾的激昂情怀,于慷慨雄壮中体现了他们抗击西戎、保家卫国的献身精神。从《诗经·大雅·公刘》“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的描写,可以看到周人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诗经·大雅·皇矣》叙述文王在陇东开拓疆土,伐密伐崇之事。规模宏阔,笔力遒劲。有精语为之骨,有浓语为之色,为后世歌行所祖。这些诗或记叙陇人成功的喜悦,或表现他们战斗的勇敢,或赞美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或表达思妇对良人的深切思念,充满着昂扬奋进的激情和关注现实的热情,有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它们以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与《诗经》中的其他诗歌一道,共同形成了一种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的精神传统,直接影响着以后诗人的创作。
汉代是陇右文化进入陇右文学的一个重要时期。汉乐府杂歌谣辞、无名氏的《匈奴歌》和杜笃的《首阳山赋》是其重要标识。前者为西汉时期居住在河西地区的匈奴人所作,描写了他们因失去牧草丰美的焉支山、祁连山而产生的苦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民族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地的战争,以及这种战争给各族人民造成的灾难。后者是一篇咏物赋,作者以精炼的文笔,描绘了首阳山的风景。繁茂的林木,险峻的山峰,颇具地方特色。这两篇作品一写情,一写物。写情的渐渐演变成行旅、送别、征人、思妇诗,作品有班彪的《北征赋》、左延年《从军行》、乐府民歌《陇头歌辞》、沈约《有所思》、吴均《答柳恽诗》、张正见《从军行》、徐陵《陇头水》、王褒《关山篇》、周弘正《陇头送征客》、顾野王《陇头水》、江总《陇头水》和辛德源《成连》等。这些诗歌文赋借助于秋月层岭、流沙汉草等具有地域特点的景物,或书写怀古伤乱的感慨,或表达对友人的依依惜别之情,或描写边塞生活的艰辛,或表现征夫思妇的相思之情。风格或质朴或典雅,感情或凄婉或哀怨,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有的甚至有先声之功。写物的虽然仅仅一篇,但却是专门吟咏陇右景物的第一篇,对以后咏写陇右山川的诗文,颇具开拓意义。到魏晋以后,随着社会的动荡,许多陇右诗作通过从军生活及征夫思妇的离情别绪,表达了期望杀敌靖边、建功立业的意愿,同时又有非战的意义,如鲍照《建初诗》、吴迈远《棹歌行》、虞羲《咏霍将军北伐》、刘孝威《陇头水》、陈叔宝《陇头水》、辛德源《白马篇》、卢思道《从军行》等。尤以卢思道的《从军行》成就最高,此诗音响格调,咸自停匀,气体丰神,尤为焕发。排偶句式、隔句用韵以及篇中换韵,使七言诗臻于成熟,为唐代边塞诗的先驱。本期的写物类以温子升的两首《凉州乐歌》为代表。第一首以劲健的笔力,描绘了西北重镇武威车马交错、歌吹纵横的繁盛景象。第二首以玉关、龙城之远来烘托姑臧城的雄伟壮美,显现了武威当日的繁华兴盛。至此,陇右名都大邑第一次进入诗家视野,对此后人文陇右的展现不无积极意义。
自《诗经》“秦风”、“二雅”歌咏陇右的篇章之后,汉代是陇右文学拓展的重要时期,注重以景写情,以苍凉凄怆造境,劲健雄浑,继承了《诗经》触物兴词、赋比并用的手法和自然明朗、质朴刚健的风格,又聚拢到靖边建功、征人思家的情感指向,体现出魏晋南北朝文学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现实人生和个人的精神世界,从而使人成为文学的真正主题。到卢思道《从军行》“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接续了《诗经·秦风·小戎》“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和《诗经·秦风·无衣》“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其军旅的题材、苍劲的风格,开初唐边塞诗的先声。至此,历代对陇右的文学文化积淀都已准备充分,创作的高峰即将到来。
(二)唐五代——高峰期
唐五代有关陇右地域的诗人诗作更多。据不完全统计,8世纪中叶河陇沦陷前,初盛唐知名诗人如骆宾王、陈子昂、王昌龄、王之涣、王维、杜甫、白居易、岑参、高适、李益等数十人都亲涉陇右。他们创作的陇右诗有的达几十首(如岑参30首),杜甫则有117首之多。另外,保存在敦煌遗书中唐五代(包括宋初)诗歌达2000首左右,这些诗歌中,拟应入归敦煌地方诗歌创作之列的,粲然盈瞩,不唯数量几占大半,其中之名品佳作也蔚为可观。此外,唐代涉及陇右题材的还有著名小说(如李朝威《柳毅传》)和散文佳作(如王仁裕《麦积山》、敦煌遗书P·2488卷的《贰师泉赋》,S·5448卷的《敦煌录》等)。这表明,唐五代有关陇右地域的文学,不仅题材丰富,而且形式多样,是地域文学意蕴浓郁的时代,为历代陇右文学成就之最,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陇右形态与边塞生活得到进一步展示
唐代陇右诗歌在描写神奇壮美的边塞风光和千姿百态的陇右山川景物方面,为此前所少有。这里有“陇山飞落叶,陇雁度寒天”(沈佺期《陇头水》)的苍凉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凉州词》)的壮阔;有“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李颀《古从军行》)的辽阔和“玉门山障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王昌龄《从军行》)的雄伟。这里的云“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杜甫《寓目》),这里的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这里的风“雾卷白云出,风吹黄叶翻”(员半千《陇头水》),这里的草“四月草不生,北风劲如切”(长孙佐辅《陇西行》)。这里有闻名世界的莫高窟:“雪岭干青汉,云梯架碧空。重开前佛刹,旁出四天宫。”(无名氏《敦煌廿咏·莫高窟咏》),也有神奇壮观的白龙堆:“传道神沙异,喧寒也自鸣。势疑天鼓动,殷似地雷惊。”(无名氏《敦煌廿咏·白龙堆咏》)。蜿蜒的城堞,连着迷蒙的云壑:“城堞连云壑,人家似隐居”(许棠《陇上书事》),高峻的麦积山上,常年路危人稀:“绝顶路危人少到,古岩松健鹤频栖。”(王仁裕《题麦积山天堂》)
此时的陇右文学,对边地生活、习俗的描写亦颇具特点。身着胡服的牧马少年,在夕阳下歌声阵阵:“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两三声。”(耿湋《凉州词》),惯于戎马的羌女胡儿,在大漠上出入自如:“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杜甫《寓目》)这里不仅有“腰悬锦带佩吴钩,走马曾防玉塞秋”(李益《边思》)的关西将家子,还有“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李益《胡腾儿》)的边地胡腾儿。壁挂弓刀的风俗,让人对陇人的尚武精神叫奇:“寺寺院中无竹树,家家壁上有弓刀。”(朱庆余《自萧关望临洮》)击鼓赛神的民俗,足见西部边民的强悍:“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王维《凉州赛神》)炙牛烹驼的生活场景,散发着浓郁的异域情调:“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张筵置酒的太守家,尽显边疆官宦的奢华富有:“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
2.靖边意愿与建功思想的完美体现
从秦汉起,中原的主要威胁就在西北,陇右处于汉民族与游牧民族争夺的主要地区,是无数中原将士保卫边境的征战地。“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故从太宗立国至盛唐玄宗之世,“均以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5]唐代国力强盛,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充满着渴望建功边塞,报效朝廷的思想,具有“喋血多壮胆,裹革无怯魂”(员半千《陇头水》)的献身精神。“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的英雄气概,反应的不仅仅是个人建功立业的豪情,更是全体将士乃至盛唐时期整个民族从心底发出的呐喊。“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塞下曲》)的坚强决心,“谁断单于臂?今年太白高”(高适《送白少府送兵之陇右》)的胜利信心,“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高适《送李侍御赴安西》)的勃勃向上和“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昂扬慷慨,都充溢着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而王之涣《凉州曲》上极天际,下传人间,以白云的空明舒展,衬出黄河、孤城的雄壮高大,抒发了盛唐知识分子高昂明朗、达观热烈的情感。壮大浓郁的诗情与气势阔大的诗境融成一体,既写出了边关戎旅生活的艰苦,又突出了激昂的气度,传奇的色彩,不愧是唐代绝句的压卷之作。
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及河陇的沦陷,陇右文学所表达的爱国则与此前不能同日而语了。“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的伤国忧边与“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入汉家”(张籍《陇头行》)的收复失地、重振家国的愿望,构成了诗人们创作的主旋律。“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没尽空遗丘”(元稹《西凉伎》)的遗憾和“凉原乡井不得见,胡地妻儿虚弃捐”(白居易《缚戎人》)的悲痛,“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白居易《西凉伎》)的痛心与“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杜牧《河湟》)的赤诚,一直延续到唐代的终结。
3.将士厌战与征人思家的艺术结合
唐代的陇右,战事一直未断,多少征人离家别室,从军边塞。连年的战争,使他们“关河别去水,沙塞断归肠”(卢照邻《陇头水》)。从此以后,“死生随玉剑,辛苦向金微”(郭震《塞上》)。“征客重回首,肝肠空自怜”(沈佺期《陇头水》)表达的是征人的乡关之思和征戍之怨,“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李颀《古从军行》)谴责的是边塞战争的连绵不断和给边地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李白《子夜吴歌·秋歌》)既是思妇的心愿,也是对穷兵黩武、休兵罢战的期待。“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李白《关山月》)放眼古今,从更久远的边塞征战史上,寄托不尽的厌战思归之情,思绪如潮,感慨良多。此外,李益《从军北征》、《夜上西城听凉州曲》、《塞下曲》、《夜上受降城闻笛》,胡曾《陇西》,王贞白《古悔从军行》,孙光宪《酒泉子》等,表达了征人行役之思和久戍不归的悲怨之情,以及他们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同时,也抨击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希望过上和平安定生活的愿望。这些诗作,大都感情悲戚沉痛,境界阔大,写情婉转动人,读来感人至深。
唐代边塞诗是中国古代边塞文学中最为动人的乐章,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枝奇葩,它的繁荣及高度的艺术成就,是唐代国家强盛、边功卓著的结果,也是唐代文士尚武毅、重事功、追求千秋伟业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时代精神的体现。由于它空前绝后的成功,被文学史家视为唐诗繁荣的重要标志。而唐代边塞诗,又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它的卓越成就,与其所依托的地域不可分割。在唐代,边战频繁的地区主要在三边:西北、朔方、东北,其中尤以西北为甚。一部《全唐诗》,边塞诗约2000首,而其中1500首与大西北有关。更引人注意的是,这些诗反复歌唱的,又多是这样一些地方:阳关、玉门、敦煌、酒泉、凉州、临洮、金城、秦州、祁连、河湟、皋兰、陇坂等等。[6]这些作品描写边塞风光,歌唱异域生活,歌颂民族友谊,谴责民族战争,表达忧国忧民情怀,抒写戍边感受,写得慷慨悲壮,沉郁苍劲。正如孟二冬所说“最能体现盛唐气象、最能表现盛唐诗歌阔大、外展境界的,则无过于盛唐的边塞诗”。[7]这些成就的取得,陇右及其独特的地域文化,无疑功莫大焉。
(三)唐五代陇右文学繁荣的原因探究
唐五代的陇右文学,总体呈现苍凉慷慨的特征,既保留了悲壮、雄浑的陇右文化色彩,又继承了唐以前陇右文学的成就,融进了时代的文化气息,因之达到了高峰。详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陇右地域文化特征与唐文化达到完美的契合。陇右是西北要塞,唐朝尤其盛唐是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强大的国力和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非陇右广袤的沙漠,高峻的陇坂,雄伟的祁连,壮观的雪山,不足以表现其胸怀的远大,气度的非凡。没有“路出金河道,山连玉塞门”(员半千《陇头水》)的雄奇壮美,就不能表达“将军献凯入,万里绝河源”(员半千《陇头水》)的豪迈之情。没有“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王昌龄《从军行》)的苍凉广阔,就难以抒写“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的英雄气概。陇右文化弥漫着一种苍茫刚劲的原始气息和雄浑有力的人文积淀,广漠、祁连、陇坂、雪山,对好奇又热衷功业的唐人来说,怎能不成为绝佳的感发诗才之地呢?(2)唐五代之前留下巨大的创作空间。《诗经》“秦风”、“二雅”有关陇右的篇章,成就高,影响远,但作品数量少,题材大都集中在开疆拓土、保家卫国等方面。汉魏以后,社会动荡,民生多艰,陇右的地域文学虽然也写忧国忧民之情,征战思家之感,也写景咏物,但气格嫌小,境界不大。陇右与生活、文学的融合刚刚开启,为唐五代文人留下很多待拓展的创作空间。(3)连年的边塞战争,客观上为唐代陇右地域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契机。唐代前期的开疆拓土和士人的建功立业思想,河陇沦陷之后的家国之感,期望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愿望以及时世的艰难、人生的无常汇聚一起,共同促成了唐代陇右文学的高峰。
(四)宋金元明清——衰落期
宋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陇右的地理位置变得无足轻重。北宋开国不久,随着“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苏舜钦《庆州败》)的出现,陇右文学仍然高唱着爱国的主调,也出现了以凌云的壮志、豪迈的激情,抒发希望报国杀敌、重整河山的决心的诗句:“破碎山河不足论,几时重到渭南村。”(曲端《无题》)但终因“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场”(陆游《陇头水》),陇右地域文学不得不转向登临怀古、游览抒情的方向上去,并最终使这一走向成了陇右文学意蕴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关于陇右的登临游览诗文,宋前就有杜笃《首阳山赋》,无名氏《敦煌廿咏》等作品,但是宋代以后,此类诗作渐渐增多,明清更为突出。陇山(谭嗣同《陇山道中》)、崆峒山(游师雄《崆峒山》、唐龙《登崆峒》,李攀龙《崆峒二首》)、五泉山(段坚《五泉山》)、祁连山(郭登《祁连山》、陈棐《祁连山》)、麦积山(李师中《麦积山》)等清绝壮美的陇右名山和冰灵寺(解缙《冰灵寺》)、白塔寺(李文《白塔寺》)、华林寺(朱真淤《华林寺》)、灵岩寺(王菏泽《游灵岩寺记》)等风采各异的宗教寺院以及平凉(茅大方《次平凉》)、肃州(牟伦《题肃州景》)、甘州(郭登《甘州即事》)、山丹(杨一清《山丹题壁》)、嘉峪关(戴弁《肃州八景·嘉峪晴烟》)、武威(许孙荃《武威绝句》)、安西(马尔泰《安西杂咏并序》)、凉州(李渔《凉州》、沈翔《凉州怀古》)等陇右名都大邑,成了诗人们反复咏写的对象。这些诗作所描绘的陇右山川风物的秀美、人文景观的奇特,历史的悠久和文化的灿烂以及所体现出来的审美与境界追求,对中国山水诗歌的丰富和繁荣,不无重要意义。
总的来看,宋代以后,陇右文学的演变趋势有二:一是在前人基础上趋于写实,向俗化淡定,理性平和方向发展。而积极进取、慷慨激昂的理想主义色彩,较之以前,大有减弱。二是登临纪游诗大量出现。雄奇苍浑、刚健壮阔的陇右文化意蕴,在这些登临纪游诗里体现得十分突出。陇右自然人文景观是极好的入诗题材,但入诗造境与其所体现的精神特质,与唐人有高下之别,只有唐代才具备促成陇右文学顶峰的条件,后世难以再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一般性描写的景物情感特征,为地域文学所共有,但融合一地特有的文化特色以后,地域文学便有了独特的文学面貌。其次,地理位置、自然及人文景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情感对地域文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因素,而鲜明独特的地域文化才是决定这一地区文学的根本所在。最后,陇右是中国北方一个富有特色的地区,其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文学具有苍凉慷慨与刚劲有力的独特气质,只有唐人才能把陇右慷慨苍劲的意蕴发挥到顶峰。陇右有许多闻名遐迩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自然人文地理在文学中积聚到唐代是顶峰,而借助这些自然人文景观抒写个人情怀,在宋代以后,开始愈积愈厚,并一直具有鲜活的生机。
[1]雍际春.陇右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地域特征[J].西北师大学报,2006,43(6):105-110.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8.
[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4] 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5]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33.
[6]杨晓霭,胡大浚.陇右地域文化与唐代边塞诗[M]∥胡大浚.陇右文化丛谈.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8:232.
[7]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