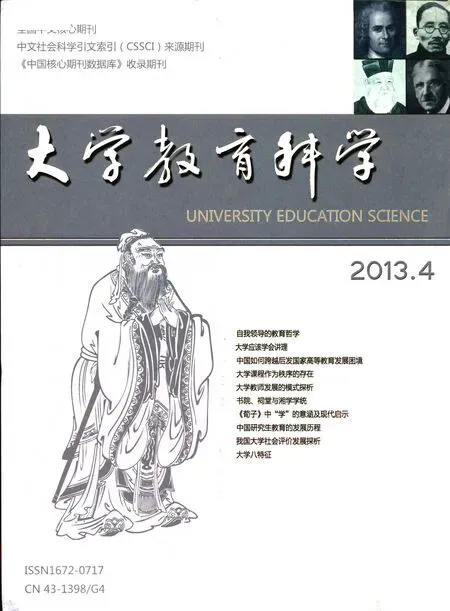关于教育史研究“国际化”问题的思考
□郭法奇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随着社会转型和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实践的推进,教育国际化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关于教育史研究“国际化”的成果却不多。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是教育国际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教育研究国际化影响及辐射教育史研究的必然结果。研究该问题并展开探讨,对于反思教育史研究,促进教育史学科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般来说,教育国际化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教育在国际意识和开放观念的指导下,通过开展国际性的多边交流、合作等活动,促进相互沟通理解、共享教育资源、联合培养人才,促进各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过程。
对不同国家来说,教育国际化有主动和被动、较早和较晚之分。被动的国际化受主动的影响大,较晚的国际化受较早的影响大。
当然,教育国际化过程可能存在负面影响的问题。如有人认为,教育国际化可能会出现被西方“同化”和完全“西化”,以及危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以本土化抵制国际化,替代国际化,排斥学习先进教育经验的问题。
这里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教育史研究“国际化”的途径是什么?坚持教育史研究“国际化”需要注意什么?
二、教育史研究“国际化”的理解
从目前来看,关于教育史研究“国际化”的解释主要有三种:一是指“历史上教育研究的国际化”;二是指“历史上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三是指“现实中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这三种解释相互联系,有时间上的先后;不过前两种解释容易混淆,主要是把教育研究的“国际化”当作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
从形成来看,最早出现的是“历史上教育研究的国际化”问题。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教育发展有限,往往是一国自己的教育发展,很少有与别国教育的交流和往来。但是随着经济、贸易、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人们抱着各取所需的目的,一些人员通过交流把他国优秀的文化、教育经验带回本国,这样就有了跨国交往学习、研究,以及结合本土情况消化和吸收外来教育的可能,也就有了最初的、所谓的教育研究“国际化”的问题。当然,这一时期教育研究的范围和规模是非常有限的。不过,它反映了以地域和文化相对开放为前提的、一定范围内进行交流的特征。一些地域、文化较为开放的国家,其教育也开放较早,注重学习和研究。在古代社会,教育研究“国际化”的目的主要是学习和借鉴别国的教育长处,改进本国的教育。我国教育史专家吴式颖先生曾指出,古希腊人通过交往和交流,形成了早期的教育研究。如柏拉图创立的所谓“四艺”可能与当时的毕达哥拉斯“盟会”有关,原因是毕达哥拉斯曾经在埃及、巴比伦生活过15年,吸收了当地的算术、几何、天文学等成果[1]。
总体来说,历史上西方国家教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起步早、范围广、程度较高,发展是多元的、有重点的。古代时期是学习和研究东方;文艺复兴时期是研究古希腊和罗马;近代主要是西欧各国相互借鉴,以英国和德国为主;现代则是欧美各国相互借鉴和研究。
关于“历史上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问题,主要是指某一时期研究者对别国教育历史问题的研究。客观地讲,这一问题与教育史研究联系密切,但出现较晚。
有学者指出,教育史研究最早起步于文艺复兴时期[2](p312)。也有学者认为,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教育史研究是19世纪早期的事情[3]。这些观点虽然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教育史研究早期主要是对本国教育史的研究①如15世纪的意大利史学家比昂多研究了维多利诺的曼图亚学校和盖里诺的斐拉拉学校。参见杜成宪,邓明言.教育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312.,还不具备教育史研究的国际视野。这一时期教育史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强调“线性”的历史观;注重以过去的成绩来论证现在教育的进步;反对教育的激进,强调研究教育史中的常规和常态现象;注重对原始资料收集和方法论的研究等。19世纪后期西方教育史研究视野开始发生新的变化。有研究者指出,德国教育家劳默尔与施密特合编的四卷本《教育通史》(1884~1902)被认为“极具国际文化视野。强调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和与之同在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联系和互动。”[2](p317)
教育史研究“国际化”问题的提出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20世纪60年代,受“新史学”的影响,西方教育史研究发生转型,出现了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教育史“研究形式”出现多样化的趋势。不仅有通史,还有断代史、国别史、专题史,以及问题史研究,突破了以往的“阶段划分、线性叙事”的研究格局。二是教育史“研究视野”发生变化,开始从全球视野出发关注超出本国、本地区的问题,不仅关注欧美,也开始关注亚洲和其他各洲的情况,突破了欧美“欧洲中心论”的研究格局。三是教育史“研究维度”也在变化,开始关注一般的教育事件、运动、法案等,突破了以往的关注教育理论、教育机构、大教育家为主的“三大块”的研究格局。四是教育史“研究内容”也发生变化,开始关注多方面内容的研究,如家庭教育、宗教教育、社区教育、环境教育等,突破了以往的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研究格局。
这一时期,对教育史研究“国际化”影响较大的是教育史研究机构和研究刊物的出现。1948年,美国全国教育学院教师协会在大西洋城成立了教育史协会,1949年《教育史杂志》(Histor y of Education Journal)创刊,1961年更名为《教育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美国教育史协会除了强调学术研究外,还鼓励国际教育史界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料互通共享。1967年,英国成立教育史协会,并于1972年创刊《教育史》(History of Education)杂志,编委会成员组成“国际化”,来自于英、美、德、法、意、比、加拿大、捷克等国。该刊物除了刊登英国的教育研究成果外,还有欧美等国的教育史研究成果。1973年,德国成立教育史协会。1978年,法国《教育史》(Histoire de L’éducation)杂志出版。
教育史研究“国际化”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1979年在比利时成立的国际教育史常设会议(International Standing Conference for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简称ISCHE)。1979年以后,国际教育史常设会议每年都举办年会,讨论有关专题,出版论文等。据统计,1979年至2008年的年会主题包括:1979年——师范教育史;1980年——历史上的教育革新;1981年——19世纪教育政策研究;1982年——学前教育史;1983年——历史上科学与技术对教育的影响;1984年——启蒙运动时期的教育研究;1985年——高等教育和社会史;1986年——义务教育史;1987年——国际教育关系史;1988年——教师职业的社会作用与发展;1989年——小学教学与课程史;1990年——宗教改革至启蒙运动教育革新研究;1991年——古代教育史研究;1992年——历史上的教育和体育运动研究;1993年——16至20世纪殖民地研究;1994年——教育与文化变迁关系(1500~1994);1995年——教育研究的历史;1996年——社会变革中的学校教育:历史与比较;1997年——信仰与教育:历史与比较;1998年——教育史研究视角的挑战;1999年——教育与民族性;2000年——书籍与教育;2001年——城市化与教育:城市是灯塔和明灯吗? 2002年——中等教育:制度、文化及社会的历史;2003年——教育与现代性;2004年——新教育:起源与变化;2005年——教育史上的国界与界限;20 06年——科技福音:教育史上的读写能力;2007年——处于危机中的儿童和青少年;2008年——教育与不平等:历史上学校教育和社会分层的途径等[4]。
国际性教育史研究机构的产生以及历年会议的主题表明,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是教育史研究发展、沟通和交流的产物。教育史研究不仅要关注自身问题,也要关注他人的研究;不仅关注本学科方法,也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不仅关注本国的教育问题,也关注人类社会共同的教育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教育史研究通过开展教育史跨学科的研究,强调教育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学、人口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结合,强调教育史研究范围、问题和方法的拓展等,超越了传统的教育史研究范式,实现了教育史研究范式的转型。这对于教育史研究“国际化”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现实中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问题,是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它主要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强调教育史研究的开放性,扩大研究视野,积极参与交流,在获取他人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改进本国的教育。
现实中发达国家教育史研究“国际化”的特点是,在坚持走“国际化”道路的同时,强调以“我”为主的“本土化”研究。在对待他人的教育经验上,肯定其合理性,对不适合的内容给予批判;在对待自己的教育问题上,不仅注重从现实中寻找原因,也强调教育史的视角,但基本特点是从自身内部寻找原因,不是单纯的借鉴和模仿别人。例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公立学校问题由于加强了现有的歧视和不平等而被诟病。修正派学者认为,学校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没有成为美国人社会流动的可靠资源,反而限制了大多数儿童,特别是那些贫穷和少数族裔儿童发展的机会。哈佛大学的贝林和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劳伦斯·克雷明等从美国历史的视角呼吁,教育史研究要有更广阔的领域,超越学校教育的界限,研究非正式的文化互渗和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广泛地检验诸如作为教育机构的家庭、教会,以及大众传媒等。
现实中发达国家教育史研究“从自身内部寻找原因”的特点可能有这样几个:一是西方学者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探索,占有创新知识的先机,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的解读,提出许多有影响的观点;二是西方学者也注重史学理论的研究,处于理论的前沿,也促进教育史学理论的发展;三是在史学研究方法上,他们进行大胆的探索,形成了多样化的教育史研究方法;四是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史学研究的管理体制。因此,也产生了许多引领史学,包括教育史研究前沿的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西方学者的教育史研究带有西方文化的特点,但从总体上看,它有利于我们开阔眼界,掌握一些属于前沿的理论和方法。目前,教育史研究在许多方面可以借鉴国外较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正是这种开放的结果。
三、教育史研究“国际化”的途径及困境
教育史研究“国际化”与教育史研究的“本土化”是密切联系的。有人认为,如果对教育史研究进行分析的话,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外国教育史研究是不同的。前者由于研究中国教育史的问题,可能较多的是本土化的问题;后者由于研究外国教育史的问题,可能较多的是“国际化”的问题。
也有人认为,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问题实际上是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问题,因为对外进行交流,中国教育史研究更具有优势。西方很少有人关注我们的外国教育史研究。这话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也有问题。这实际上等于削弱了外国教育史研究。外国教育史研究也需要交流,交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比较各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水平。
这里简要分析教育史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教育史研究的“本土化”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教育史研究借鉴的本土化,即把引进来的东西进行消化,以利于适应本国教育研究的需要。二是教育史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即以自己为对象研究问题,以产生对别人的影响。
教育史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密切联系的。它不仅需要把外来的东西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变成适合自己的,还通过研究好自己的东西,对他人产生影响。从历史和长远发展来看,强调教育研究的“本土化”可能更为根本。因为,没有本土化研究的丰富多彩,就很难有教育史研究“国际化”交流和沟通的必要。
不过,目前来看,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因为,无论是外国教育史研究,还是中国教育史研究,都面临一个“开放”和“走出去”的问题。教育史研究“国际化”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国际表达”,包括鼓励教师在SSCI上发表论文;支持教师参与国际会议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国外出版社出版英文著作等。第二是“国际合作”,包括合作发表论文、合作举办研讨会、合作出版著作等。这里,“国际表达”可能属于初级阶段,“国际合作”属于高级阶段。
有人可能会问,教育史研究有必要与外国人进行合作吗?这个问题其实就像关起门来办会一样,我们可以不邀请国外的学者来,自己内部进行交流即可。但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别人在研究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研究在国际同行中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如果审视一下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合作研究的有多少,与国外合作研究国外教育问题的有多少,与国外合作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有多少,与国外合作研究教育问题时,是别人来找你,还是你去找别人等等,我们就会有答案了。
目前来看,我们的教育史研究“国际化”还处于初级阶段。虽然有一些交流,觉得不错,但是交流后发现存在许多问题:一是研究的题目过大;二是方法和理论落后;三是规范化不够。不仅如此,还要面对西方知识霸权挑战的问题。
历史学者陈兼、余伟民认为,关于“西方知识霸权挑战”的问题,主要是我们与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关怀”和“有意义的问题”的双方认同问题。他们指出,西方学者的“知识关怀”主要指西方特定的学术与知识氛围下从事研究的文化和知识基础。“有意义的问题”是指在“知识关怀”基础上提出的,并由提出者特定的“知识关怀”所决定的研究问题。由于西方学者基于自己的“知识关怀”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因此,他们对于非西方学者所陈述的“有意义的问题”往往缺乏敏感与兴趣[5]。这样,“国际表达”可能存在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以自身的“知识关怀”为基础参与时,往往不为西方学者所重视;如果是以非自身的“知识关怀”为基础参与时,又失去了表达自身“知识关怀”的权利。
面对这一挑战,陈兼和余伟民的建议是,在界定“有意义的问题”时,要以诚实的、不急功好利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知识关怀”,并同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别人基于他们的“知识关怀”而产生的“有意义的问题”。
显然,这一建议是试图把双方由过去一个不平等的地位放在一个平等交流的地位。这一观点与中国传统强调的“和谐相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是一致的。
不过,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有一种选择,即在承认现有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坚持“国际视野”,既不是中国完全向西方学习,也不是西方完全向中国学习,而是相互尊重,遵循共同的规则,研究人类教育共同面临的问题。用林语堂先生的话说,“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6],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高教育史研究的解释力。
四、坚持教育史研究“国际视野”的思考
强调教育史研究的“国际视野”,就是把教育史研究看作是一个宏观考察人类命运及教育发展的过程,把西方和中国的教育史实当作个案,运用恰当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问题,不断接近教育历史真相,获得对问题的理解。
教育史研究是宏观考察人类命运及其教育发展的过程。人类自形成以来,为了生存,形成了运用智慧参与竞争和进行防御的策略。这一策略决定了人类的知识、技能和智慧的重要性,也决定了教育在形成人的知识、技能和智慧中的重要地位。但是,教育本身也会出现问题。因此,不断改革教育,进行教育创新就成为教育的常态。从教育的发展来看,任何一种教育,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是存在不足的,任何一种教育都需要经受历史的考察和检验。考察和检验的目的就是找到其中不足的部分并进行修正,使人类的教育得以更加完善,而不是对原有的教育全盘否定,推倒重来。教育史研究在宏观考察人类教育的得失方面,在探讨“什么是好的教育”方面可以而且也需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强调教育史研究的“国际视野”,需要把西方和中国的教育史实当作个案,运用恰当的研究方法,不断接近历史的真相。这里以社会学和国际史的研究为例。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研究“宗教宽容”问题时,不仅以法国为案例,也把中国作为案例。他认为中国的传统精神就是一种普遍的宽容精神。在他看来,中国人对于宗教的态度,就是最理想的宗教宽容的态度。显然,伏尔泰的目的不是要研究中国文化,而是要找到实例来论证他的观点——普遍的宽容精神[6]。20世纪60年代关于“冷战史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也值得注意。这一研究更涉及到多个国家,如美国、西欧、前苏联、东欧、中国等国档案资料的解禁和使用,超越了传统的只使用美国及西欧资料的阶段,开始重视对“冷战另外一方”的研究,使“冷战史研究”真正走向国际化。
坚持教育史研究的“国际视野”,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加强教育史研究的规范化,按照国际通行研究惯例和原则行事。国际通行的研究惯例和原则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在提出自己的观点前必须整理别人对这一问题的已有研究。其意义在于,你的研究是建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的;研究是具有连续性的。而更重要的是,一项研究只有了解别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以后,才能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二是引用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出处。这一观点的意义在于,教育史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你的研究所引用的观点是可以查得到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它既是对前人研究的一种尊重,也可以提供别人对你所引用资料的核实和考证。三是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任何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都必须以扎扎实实的第一手资料研究为基础。第一手资料通常由事件的实际观察者或直接参与者的报告及与事实直接有关的实物构成。因此,发现、甄别和评价第一手资料是一个教育史研究者的基本功。它包括逻辑推理、观察记录,以及生活的一般常识。例如,对教育史上儿童观的研究,我们过去主要是依据历史上教育家的著作或官方的文献,资料的使用和发掘缺乏想象力,而现在我们还可以通过许多关于某一时期儿童存在和生活的证据、图像、日记来研究和说明儿童观。四是教育史研究须严格遵守逻辑的要求。这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看研究问题的各部分逻辑是否具有一致性;其二是看各部分观点的逻辑推论是否与经验事实具有一致性。如一个研究结论在逻辑上挑不出毛病,其结论的推论也没有被经验事实所证伪,就可以暂时接受它;如果不一致,那这个理论可以受到修正或者摒弃。同时,对待国外的教育理论,不应该迷信,也不应该鄙视,而是将它看成研究中的一种假设,并在运用这个理论之前先来检验这个理论的推论与教育经验事实的一致性。五是研究的结论应当能够被证实或者被证伪。教育史研究是一种使用过去别人的直接观察和研究者的间接观察来研究问题的学问。它需要依据过去别人直接观察形成的数据或资料,也需要依靠对别人的推理进行逻辑分析来进行研究。当然,对过去别人观察形成的观点是不能随意改变的;而对自己观察所形成的解释是可以随着史实证实或者证伪,以及新资料的发掘而改变。因此,作为研究者,在进行研究的时候都应当自问:研究的每一个论点都有事实支持吗?所有这些事实都可以观察到吗?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研究的结论就值得怀疑,因为它很难被证实或者被证伪。
第二,要有对问题研究的新解释。强调有新解释的目的是,你的研究必须有新的观点,才能真正推动教育史研究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是较欠缺的。目前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教育史界已经出版了诸多著作,但不断修订的著作有多少本?哪些著作是出版以后就再也没有修订,一劳永逸的?有没有持续的研究?有没有不断推陈出新的观点?这是需要思考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假设是,我的研究水平是最高的,别人无法超越。果真是这样吗?美国教育史家乔尔·施普林的《美国学校:教育传统与变革》一书已经再版了七次①该书英文书名为“American School Varietie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参见中文版:乔尔·斯普林.美国学校:教育传统与变革[M].史静寰,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3.。每次再版作者总会增加新的章节,或者有新的观点补充。它表明:教育史研究的解释只是一定时期、根据一定材料进行的解释。当有了新资料以后,就需要有新的解释,甚至超越已有的解释。除非你没有新的资料,没有新的研究,或者研究的问题不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教育史研究也有需要理论解释的问题。理论是指解决某一问题时形成的概括性的思想或者观点。经济学家林毅夫曾经指出,社会科学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一般来说,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也越大[7]。当然,理论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历史中类似的条件出现时,理论的解释力就体现了。但是,当一个新的现象或者问题用以往的理论不能解释时,就需要提出新的理论。这种新的理论就是对原有理论的丰富和提升。运用理论对问题不断解释的过程,就是教育史知识不断增长的过程。
第三,教育史研究还要关注人类教育发展中属于常态的东西,用来说明和解释现实。教育中属于常态的东西是指在教育历史的发展中,经受长期实践检验、比较稳定、被人们认同和接受的东西。它包括一定的教育理论、观念,内容、方法,惯例、制度,以及器物或者实物等。当然,教育历史中也有非常态的东西。如教育中曾经有过长期存在的东西,或者被称为主流的东西,包括教育历史中的体罚现象,学校教育中的知识灌输、注重记忆的考试教育等,虽然它们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这些现象不是常态。因为从长远看,它对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是不利的。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建设学校体制、设置学科课程、教师主导教学、采取班级授课、坚持考试制度、强调管放结合等,是教育常态的重要内容。认识这些对于认识和继承教育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教育常态的东西也在变化。以考试教育为例,尽管各国教育强调坚持考试制度,但是考试制度本身及方式也在变化。这种变化的特点是向着更加人性化的、具有更多选择性的方向发展。而死记硬背的、以知识记忆和灌输为主的考试则成为非常态的教育,必定被淘汰。它意味着,实施考试制度总的趋势是不变的,但它可以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微调,以适应现代人和社会的需要。
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下认识和评价教育中属于常态的东西,这里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在评价一个事物时,应该关注事物本质的东西,即在这个事物中哪些品质是最值得尊重、最值得称赞、最值得认可的。比如说,在学校教育中,一个人的发展需要记忆知识,需要应对考试,需要培养兴趣,需要发展创造力,但在这些品质中哪个更重要呢?
从学校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与记忆知识和应付考试相比,培养学生的思考力、批判力和创造力可能更重要,这些品质是值得尊重、称赞和认可的。因为,它是一个现代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创造力的最重要的品质。如果不发展这些品质,压抑它、打击它,人的思维就僵化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思考力和批判力的重要原因。因此,学校教育的目的不在使学生记忆许多知识,也不再仅以应试为目的,而在养成学生思考问题,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能力、技能,以及发展创造力的品质。
总之,教育史研究“国际化”问题的探讨提供了重新反思和比较的契机。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史研究“国际化”在不同国家尽管有早晚、先后之分,但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教育史研究“国际化”需要注重与本土研究的结合,反映本土教育的实际;需要加强“国际表达”和“合作研究”,融入国际教育史研究,与其保持同步;也需要从“国际视野”出发,以中西方教育为个案,研究人类社会和教育共同的问题,宏观把握人类教育发展的特点。教育史研究的“国际化”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这条路没有捷径,只能踏踏实实,遵循规则,持续研究,积累经验,一步一步推动教育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1]吴式颖.教育:让历史启示未来[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34-35.
[2]杜成宪,邓明言.教育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3]William J.Reese and John L.Rury,eds.,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Chapter 1 Introduction:An Evolving and Expanding Field of Study,2008 by Palgrave Macmilan,New York.p.1-7.
[4]杨汉麟,李贤智.新史学视野下教育史研究的转向——基于国际教育史常设会议的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03):37.
[5]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J].历史研究,2003(03):20-21.
[6]乐黛云.中国文化面向世界文化的几点思考[E B/OL].http://www.chinainnovations.org/Item.aspx?id=36776.
[7]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J].经济研究,1995(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