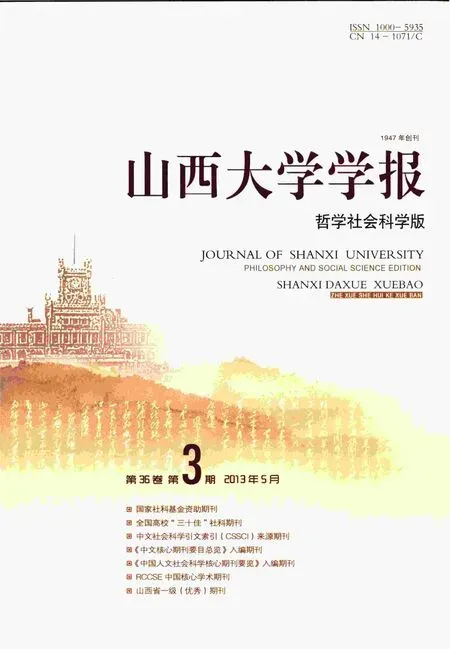多层治理背景下的欧盟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兼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机制比较
刘 华,邓 蓉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欧盟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因其特殊的组织结构和活动过程,以及先进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欧盟率先形成了地区性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将气候变化治理的理念和目标分解到具体的气候政策中并取得了实效。虽然欧盟气候变化治理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作为欧盟的新政策领域和全球的开创性气候政策,为研究欧盟机制和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对国际气候变化治理和地区气候变化治理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政策和机制样板。
一 欧盟的“多层治理”
欧盟治理因其独特的政治结构而具有独特的治理模式。学者们对欧盟治理的研究,虽然各有侧重,但一般都强调其多层次性,“多层治理”和“网络治理”是大部分学者所使用的概念。
“多层次性”被认为是欧盟治理的核心特征。“多层治理”的概念最早由马克斯(Gary Marks)提出。胡格(Liesbet Hooge)和马克斯在《多层治理的类型》一文中对“多层治理”的定义是:“相互嵌套的、政府之间在多个疆域层次上的持续协商的体系”[1]。查利·杰弗里(Charlie Jeffery)进一步指出,欧盟多层治理中,国家间和国家与欧洲层面机制的互动是重要的内容,然而次国家权威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而且,次国家权威的作用并不是被动的,而是自下至上的(bottom-up)的。[2]托马斯·里塞-凯本(Thomas Risse-Keppen)提出超越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之争,从概念上把欧盟界定为“一种多层治理结构,私人、政府、跨国家和超国家角色在密度、深度和广度都不断变化的复杂网络中相互交往。”凯本认为影响欧盟治理结构的因素,有国内结构和欧盟制度两个方面。从欧盟制度方面而言,就是指欧盟机构的设置。[3]西蒙·希克思(Simon Hix)也认为,欧盟已经发展成一个多层面治理的独特制度,这种超越国家的治理,“并不必然意味着是在国家之上的治理,仅仅是在更高的政治层面上以其组成因素重新组织国家。欧盟不是重新回到早期创造国家的进程和政策;相反,它是一个由共享的价值与目标、由共同的决策风格所集中在一起的成员国和超国家的制度网”[4]。在贝娅特·科勒 -科赫(Beate Kohler-Koch)和波特霍尔德·利特伯格(Bo Tehuoerde Liteboge)看来,欧盟治理作为一个需要相当大的扩展来囊括欧盟决策活动所有领域的概念,其核心特征是多层级性质。其他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点:“共同体方法”、“网络治理”和“超然的政治争论”。“网络治理”意味着在多层级的结构中,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对权力进行分配,国家和社会行为体行为聚集,国家权威色彩淡化,形成一种治理的网络体系。[5]
按照马克斯和胡格的分类,多层治理按等级强弱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权力的分散只在有限层面上,这些层面互不干涉,领土和地域的划分是明确的,等级性强,具有联邦主义性质;第二种是多中心的,各层次之间等级性弱,任务具体且有针对性,以功能任务而不是领土来划分,体制灵活多变。[6]气候变化治理更多地属于第二种治理,是一种功能性质的、具有治理目标导向特征的治理。
贝娅特·科勒-科赫以利奇法尔特(Lijphart)类型研究的标准和韦伯(Max Weber)的“宪法思想”类型标准为基础,将治理模式分为四类:国家主义、多元主义、团体主义和网络治理。而气候变化治理在特征上更符合网络治理的模式,它既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事实性网络治理制度,又是一种按照目的构建了和正在构建着的功能性网络治理模式。
二 欧盟气候变化治理机制
政治系统是“由单个要素组成的一个整体,它遵循特定的组织原则,这些组织原则确定了要素之间的相互配置(结构)、它们之间的互动模式(程序)和互动的效果(决策内容)”[7]。气候变化属于政策领域,属于政治系统范畴,因而应将欧盟看做是一个具有多层治理特性的系统,进而分析这个系统中气候变化治理如何决策和运作。就欧盟气候变化治理而言,从欧盟系统视角来看,其结构是基于欧盟机构设置基础上的,包括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的欧盟机构、成员国及包含多种主体的次国家单位行为者;其过程是欧盟气候变化治理的具体制定过程;其决策内容就是输出的气候变化治理。
(一)欧盟气候变化治理决策的系统结构
欧盟的系统结构是指欧盟的主要机构,是欧盟治理的制度基础,是欧盟政策的来源。
在欧盟机构中,与气候变化治理有关的机构包括:欧洲议会、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地区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环境署。欧洲议会和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共同分享欧洲环境政策的立法权,其中环境部长理事会的立法权强于议会。议会中的绿党在决策层面推动欧盟机构考虑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欧盟委员会负责起草欧盟环境法律并确保法律的执行。经济和社会委员会以及地区委员会在制定欧盟环境法律时向议会、理事会和委员会提供咨询性意见。欧洲法院负责解释欧盟的环境法律条款并受理有关环境问题的纠纷,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对欧盟决策机构是否将环境纳入其政策领域进行司法审查。欧洲环境署是欧盟环境保护统计咨询机构,其任务是“为欧盟、成员国和其他国家制定和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政策提供环境统计数据,并对各类环境保护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预测,提供有关的咨询”[8]。在气候变化治理的决策中,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和部长理事会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在欧盟气候变化治理决策过程中,地方政府、学术团体、NGO、相关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对决策施加影响。而且这种围绕在欧盟机构之外的行为主体通过持续性的合作和影响,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非制度性的参与体系。
(二)欧盟气候变化治理的决策过程
在欧盟气候变化治理决策过程中,在欧盟机构内主要以欧洲议会、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为框架依托,成员国和次国家行为体通过谈判、协商、提供信息、游说等方式施加影响,构成了多层主体参与决策的模式。
1.欧盟机构的决策过程
1.1.提案过程
在欧盟,决策的初始阶段是提案,也就是政策创议阶段,这一职能由欧盟委员会承担。据欧盟法律规定,欧盟委员会拥有正式的政策创议权。欧盟委员会负责起草包括气候变化治理在内的欧盟环境政策,提交给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
在气候变化治理的提案创建阶段,欧盟委员会有意识地为社会提供参与渠道,包括提案之前召开利益相关群体咨询大会、开通网络交流平台等多种方式,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利益表达等方式对提案施加影响。欧盟委员会的环境总司和ECCP(欧盟气候变化纲要)工作组运用广泛的信息资源、技术资源和社会资源,来保证委员会能够充分履行其作为欧盟主要立法创议者的职责,并使其政策具有多层治理的基础。法律草案的起草阶段首先由欧洲委员会环境总司提出提案,在欧盟委员会内相关机构协商后,经委员会大会通过,才能提交给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由于欧盟委员会的超国家性质,提案过程体现的是决策的超国家性。而提案的制定,受到多种行为体,尤其是次国家单位主体的影响。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欧盟委员会的提案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受部长理事会影响的。部长理事会可以要求委员会进行理事会认为是实现共同目标所需的任何研究,并向它提交任何适宜的提议。因此,欧盟委员会在起草提案时,会考虑到环境部长理事会的意见,在决策过程中,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间的合作日益密切,传统的提案者与决策者的分野也逐渐模糊。
另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欧洲理事会会起到较强的促进作用。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各成员国普遍重视的问题,尤其是因其治理需要跨国合作的特性,欧洲理事会的议题中已经较为明显地体现出对气候变化的重视,并敦促委员会创建具体的政策提案。
1.2.政策形成过程
欧盟的立法权属于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其中,部长理事会具有相对主导的决策权,是欧盟最主要的立法机构。欧洲议会的作用依据不同领域立法程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欧盟四大主要的立法程序是咨询程序、合作程序、共同决策程序和同意程序。在气候变化领域,欧盟的决策多是采用共同决策程序,即提案的最终决定权由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共同行使,议会拥有否决权。在咨询程序中,部长理事会在正式批准欧盟委员会送交的立法提案之前,需要先向欧洲议会征求意见,最终决定权属于部长理事会;在合作程序中,部长理事会为欧洲议会提供两次对立法提案提出修改意见的机会,欧洲议会没有立法的最后决定权,只能对部长理事会的立场做出有选择的回应,提案的最终决定权是由部长理事会掌握;在同意程序中,欧洲议会对立法提案没有修正权,但拥有最终决定权。
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除了本身就带有超国家性质和国家间性质之外,它们也受到来自次国家行为体的影响,比如:通过对议员的游说为议会提供气候变化信息,通过对国家政府的影响使得利益诉求通过部长在欧盟层面表达。
2.成员国对决策的影响
在欧盟决策的过程中,代表国家间层次的机构已经体现了成员国的影响。此外,成员国也通过参与政策的协商及表示对政策的态度等方式,影响政策的制定。
成员国在欧盟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角色差异主要源于态度和任务的差别。一是成员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性存在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讲,可以分为三类:一些国家对环保问题一贯比较关注,国内有强大的环境保护组织和绿色政党,经济上能够承担减排和执行标准带来的压力,诸如丹麦、荷兰、德国、芬兰、瑞典等;而一些相对“滞后”的成员国,国内对气候变化重视不够,其气候变化的国内立法主要是移植欧盟的法规,属于被动参与的角色,如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英国、法国等国家则处于上述两类国家的中间状态。不同的国内状况决定了成员国不同的态度,进而决定了成员国在气候变化治理中起推动还是牵制作用。二是成员国的减排任务差别较大。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状况和排放现状存在明显差异,欧盟需要以共同履约、区别对待的方式,对不同成员国规定不同的具体目标。一般而言是老成员国需要减排,而新成员国的排放可以增加,同时,各成员国对减排目标的承诺也存在差异,因而成员国对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制定的作用不同。
3.次国家行为体在决策中的作用
次国家行为体包括成员国的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研究机构、企业和个人等。在欧盟气候变化治理中,这些角色的影响不可小觑。成员国的地方政府在欧盟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影响逐渐增强,他们在布鲁塞尔设有某种形式的办事处,这些办事处的任务包括游说、收集信息、与有关决策者建立并保持联系以及作为欧盟与地方的中间桥梁,通过欧盟的地区委员会使欧盟的决策者能够了解并采纳地方代表的观点和主张等。利益集团在欧盟范围内有诸如欧洲企业家联盟、欧洲工会联合组织、跨国环境组织等超越国家范围而进行活动,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游说活动来保障其在欧盟层次上利益诉求的实现。欧盟的一些学术团体,也通过提供信息和研究成果,向欧盟的政策制定施加影响。如欧洲政策中心,其研究项目中包括能源与气候变化,研究计划是在和欧盟机构、成员国、其他研究机构,特别是工商业界人士、NGO、工会等磋商下进行。[9]欧洲还有大量的环保组织存在,作用较大的一般都在布鲁塞尔设立办事处,如欧洲环境局(EEB)、欧洲地球之友(FOEE)、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FF)、欧洲气候网络组织(CNE)、欧洲交通与环境联合会(T&E)等。他们通过参与政策的制定和监督,对欧盟气候变化治理发挥直接影响力。
三 欧盟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比较
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一般是指,建立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基础上,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规定了缔约方的责任义务和合作方式,以缔约方大会作为最高机构,并设置了常设秘书处和咨询机构等。欧盟是其缔约方,其内部的气候变化治理虽然与之相联系,却是相对独立的一个系统。
因此,我们将从系统分析框架出发,从系统结构、程序和政策措施三个维度,比较欧盟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机制。
(一)系统结构比较
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主要系统结构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公约常设秘书处、附属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附属履行机构等。《框架公约》签署之后,每年举行一次缔约方大会,这是公约的最高机构,《框架公约》规定其“定期审评公约和缔约方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相关法律文书的履行情况,并应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为促进本公约有效履行所必要的决定”。同时,缔约方会议也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会议,根据《议定书》规定,承担起评估、审查、协调等职能。按照规定,公约设立常设秘书处;附属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负责向缔约方会议及其他附属机构提供信息和咨询;附属履行机构由政府代表组成,开放供所有缔约方参加,协助缔约方会议审评公约的有效履行。
同欧盟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系统结构相比较,二者的共同点包括:都具备一定的组织机构框架,是气候变化治理或条约的基础,都承担着政策制定、咨询、执行和监督等相关职能;其组织机构均依照法律文件的规定设立,具有功能性特点。然而,通过比较,更能发现它们的不同之处:
一是在机构设置上,欧盟机构较之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机构更为成熟和系统化,其功能性的制度设计更为精巧和程序化。政策的制定和修改都要经历一个比较复杂的多机构共同参与过程,绝非单一会议或机构可以决定。这样的机构设置,能大大提高政策的质量,并能根据发展现状和实际问题及时修正政策。
二是在机构职能的界定和发挥上,欧盟机构比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机构的职能划分更为清晰,职能发挥也更为有效。提案、修正、咨询、审查等职能均由独立部门承担,分工明确且紧密结合,形成了一个决策系统。
三是在非制度范围内行为体的参与上,欧盟机构能够更好地将这些因素纳入其中。在欧盟机构周围,围绕着大量的次国家行为体,地方和民众力量可以获得介入欧盟决策的渠道,并因其长期性的活动,成为某些政策制定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非政府行为主体的参与,是欧盟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一大特色。
四是在超国家性上,欧盟机构的超国家性质不同于一般的国家组织和国家间合作的特性,这种超国家性对于跨国治理而言,无疑是一种有效的保障,有助于共同目标的达成和集体政策的制定。
(二)决策过程比较
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形成,由联合国主导,参与者主要是主权国家,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达成一致意见。以缔约方大会为基本的决策框架,缔约方在每年的大会上展开讨论,目标是制定出全球气候治理的下一步方向和政策。缔约方大会从1995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只有几次取得了明显进展,如1997年通过《京都议定书》的京都会议,其他年度的大会一般没有显著成效,甚至出现谈判僵局,如2000年因美国坚持大幅削减其减排指标而休会的海牙会议。
同欧盟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相比较,二者的决策过程具有相似之处:都借助于会议形式、都采用谈判协商的方式、目标制定都以尽可能满足各参与者要求又能达致共同意见为特征。而二者决策过程的不同在于:
一是决策机构的决策程序不同:欧盟的共同决策程序是一个较为完美的多机构决策模式,虽然复杂但却有效,对于各种不同的问题都有特定的程序安排。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机制通过缔约方之间的讨价还价来达成一致意见,缺少程序性保证,一旦出现较大差异的意见就难以调节,谈判效果难以预料,且多是不乐观的。
二是决策参与者的层次和作用方式不同:欧盟政治系统中超国家机构和政府间机构共同发挥作用,具体来说,超国家性质的欧盟委员会提出议案,超国家性质的欧洲议会和政府间性质的部长理事会共同决策。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政策是缔约方谈判协商的结果,不存在一个超越各方之上、具有实际权力的机构。在决策中超国家权力和作用的发挥有利于政策的整合,这是欧盟机构能产生更为有效政策的一大原因。而且,次国家行为体在欧盟层面能有效施加影响,不但有利于政策合法性的获得,也为政策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是政策创制来源不同:欧盟气候变化治理的提案权在欧盟委员会,表现出政策创制的主动性,以成员国和民众对气候问题的普遍共识为基础,以欧盟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对气候政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合作机制是政府间的,常设机构没有最终的决策权,具体政策措施的制定只有依赖于国家间的协商和谈判,才能最终形成整体性的政策框架,如此,政策的前进动力就会先天不足。
四是共识性程度不同:欧盟成员国入盟之时,就被要求接受欧盟的法律成果和共同目标,因而欧盟政策的约束力很强,加之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水平和价值差异相对较小,环保理念较为盛行,成员国的意见分歧总是趋向于在欧盟框架内得到协调和解决,气候治理共识也较易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中,缔约方的角色和态度差异很大,包括欧盟等积极参与的国家和地区、美国和日本等持反对或消极态度的“伞状集团国家”以及以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的发展中国家等。缔约方成分的多元化致使共识难以达成,所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政策的制定很难取得突破,其约束力的欠缺也决定了法规的落实难以保证。
在系统决策的结构和过程中,欧盟的机构和决策方式显著地优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机制,能够在制度上更有力地推动政策的出台和发展。其多层级的系统结构和共同决策模式确立的联系网络和谈判协商体系,对于气候变化治理的决策而言,是富有成效的。超国家性质的欧盟因拥有精细的机构设置和决策模式、较强的约束力和政策推动力、成员国和民众的共识、非政府行为体的参与渠道等因素,在气候治理中具有明显的优势。
(三)政策措施比较
欧盟气候变化治理遵循防备原则、预防原则、源头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原则等。在政策制定上,欧盟气候变化治理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政策网络,既有指导性的气候战略和规划,又有各相关方面的具体政策,还有为实现目标而制定的政策性工具和手段。欧盟气候变化治理的框架包括欧盟环境行动计划、ECCP和气候变化战略等;采取的具体政策手段主要包括排放交易机制与碳捕捉和储存;还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具体领域,如能源、交通、工业和农业等领域的减排措施。
在国际气候变化治理机制方面,联合国《框架公约》确立了指导缔约方履约的五项基本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行动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具体需要和特殊情况的原则;预防原则;促进可持续发展原则;开放经济体系原则等。《框架公约》号召各个国家自愿地减排温室气体,制定国家政策和采取相应的措施。《京都议定书》在《框架公约》的指导下制定了具体的减排目标和措施,规定了缔约方的阶段性减排任务,制定了三种市场导向的机制:排放贸易、联合履行和清洁发展机制。
二者的相同点包括:均有一系列指导原则,且其中的共同但有区别原则、预防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等都是一致的;均制定了总体的减排目标,并把目标分散到各成员国或者缔约方;都运用减排的灵活机制来作为政策的工具性措施;都是跨国层面的共识性和框架性指导政策,需要成员国或缔约方由国内立法或采取措施来贯彻执行;都对成员国或缔约方制定并执行其国内计划进行监督。二者的不同点主要在于:
一是政策体系化程度。欧盟气候变化政策措施已经形成初步的政策系统,拥有总体框架和具体政策,成为较为全面的政策体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措施还处于较为粗浅的框架构建阶段,仅对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进行了条约性规定,缺少具体化的政策分支,也没有形成一个政策体系。
二是目标制定。欧盟气候变化治理有一个总体的目标规划,并适时调整以确立较高目标定位,且其政策目标的改进具有持续性和长远性;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措施中,目标的达成较为困难,因而在《京都议定书》中只有一个短期目标,长期目标的制定是不切实的,成为一个难以弥补的缺陷。
三是排放交易机制。欧盟是最早开展多国间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地区,多种行为体已被纳入其中并逐步扩大,这是全球性排放交易在超国家层面的首次实践。全球性的排放交易则不能像欧盟那样有效地开展,原因在于缔约方的范围较大,层次较多,又缺乏一定的制度框架,排放配额、交易规则等存在难以解决的操作性问题。
四是政策的发展程度。除了总体框架广度的差异,二者在政策发展程度上也不同。欧盟气候变化治理呈现出与相关领域政策整合的特点,比如气候和能源、气候和交通等,能够从源头上对排放进行控制和管理。欧盟已经意识到适应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并在政策中得以体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在总体上还没有形成此类政策,因而其措施显得较为单薄。
在政策措施的比较中,欧盟的气候变化治理明显地表现出其发展程度已经远超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机制中的措施。在政策的整体框架结构中,其整体性的框架和战略、执行机制以及其具体领域的政策,都胜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政策的现状。
通过对欧盟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比较,我们可以从系统结构和形成过程以及政策措施的角度看到欧盟气候变化治理的特点和优势及其超越性成果。欧盟气候变化治理是区域性跨国气候治理的成功实践,其政策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其他区域乃至联合国国际气候变化治理短期内无法达到的。其相对完备的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为国际气候变化治理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模板。
四 通过欧盟气候变化治理认识欧盟治理
欧盟气候变化治理是欧盟治理中一个新的重要政策领域,为欧盟治理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素材,对欧盟治理理论的验证和欧盟体系的研究都有较大意义,对于欧盟多层治理的建构和实践,做了极好的案例说明,并可以该领域为例认识欧盟治理的有效性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欧盟气候变化治理取得成效的欧盟层面的原因
气候变化治理之所以能在欧盟得以较快发展,是因为气候变化治理本身与欧盟治理特征相契合,其气候变化治理理念也被欧盟所认同。
首先,气候变化问题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多层治理是其有效治理模式。气候变化问题是超越国界的国际性问题,一是排放问题各个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责任,二是其影响会波及各个国家。气候变化治理需要有效的国家间的合作,也需要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参与。
其次,欧盟系统具有多层治理特征,保证了成员国之间共同目标的达成和共同行动的开展。欧盟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性和制度性实体,其机构设置和气候变化政策决策模式表现出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特征,而且其超国家性能更好地促使成员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目标。
第三,气候变化治理作为欧盟治理的一个案例,既是功能性产物,又是一种观念的建构。欧盟气候变化治理不仅仅是作为对功能需要的反应而出现的实践,也是一种欧盟治理观念,这种观念在政策制定和内容中均有体现。“行为体必须面对物质世界发生的变化,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则取决于通行的‘信仰体系’,即取决于有因可循的结果和合法目标的共同设定。”[10]欧盟的环保理念较为先进,成员国和民众对于气候治理的认同能够在欧盟层面达成共识,这种治理共识是欧盟能制定出气候治理战略的观念基础。
第四,欧盟气候变化治理的发展得益于欧盟多层治理。欧盟体系是其气候变化治理能够取得进展的基础性原因,具体来讲,就是其超国家性质的体系将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单位通过一定的制度联系起来,在决策中以超国家力量为保障,以共识为基础,通过咨询协商等方式,共同对决策施加影响。
(二)欧盟气候变化治理反映出的欧盟治理的问题
在欧盟气候变化治理的决策中,反映出欧盟治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不同政策领域交叉时的部门协调、政策效力和欧盟治理的合法性问题。
首先,政策制定中可能出现部门冲突。欧盟的机构设置因功能细化而存在各领域的具体负责部门,这些部门各司其职,以本部门的利益为出发点制定相应的政策。这种分工能够保证部门政策的效率,但是也会给交叉领域的政策制定带来难题。由于欧盟不像国家那样存在一个强大的权力中心,部门之间的矛盾不易解决,解决方案也是部门之间通过欧洲法院或者谈判才能达成妥协,不能保证政策制定的质量,也不易达成以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部门合作。
其次,政策效力问题。欧盟不同的政策领域,政策的一体化程度和效果也不一样。气候变化治理政策只是近来发展起来的一个政策领域,虽然有欧盟的系统结构为支撑得以较快发展,成为国际范围内气候变化治理的先行者,然而该政策还只是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政策的制定多是框架性和指导性的,以指令和政策性文件的形式出现,其政策的效果依赖成员国的落实。由于成员国的多样性,政策效力能不能在不偏离政策初衷的前提下在成员国得以发挥,是一个难以驾驭的问题。而且,作为一种新兴政策,其有效制定和贯彻的途径还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处于探索的过程中。因而欧盟气候变化治理政策的实施会表现得力不从心。
第三,合法性问题。“民主赤字”一直是欧盟系统研究中谈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在欧盟系统中,欧洲议会代表的是民众基础,部长理事会代表的是成员国基础。这两部分是欧盟合法性的主要体现,而现有的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代表机制还不够。虽然在气候变化治理政策中,欧盟同样强调成员国政府和公众的参与,然而,由于政策的性质和超国家作用的路径依赖,超国家性质主体的参与越来越明显,对决策方向和决策内容的影响越来越大。尽管这样的趋势有利于气候变化治理等政策在欧盟层面的制定,然而,这只有建立在成员国和民众共识基础之上,其民主合法性才不会在很大程度上被质疑。
总之,欧盟恰能提供气候变化治理需要的治理模式,气候变化治理的理念也能被欧盟治理理念所包含,因而,欧盟的气候变化治理能够实现较快的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区域性气候变化治理政策。此外,欧盟积极发展气候变化治理机制还有另一层主观考虑:提高欧盟的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11]。欧盟通过积极的气候治理,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并被广泛认为是气候治理中的领导者,而欧盟也有意识地通过其气候变化治理及其对外合作担当这种角色。
[1]Liesbet Hooghe,Gary Marks.Unraveling the Central State,but How?Types of Multi- level Governance[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3,97(2):233.
[2]Char Lie Jeffery.Sub - N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Does it Make Any Difference?[J].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2000,38(1):23.
[3]Thomas Risse- Keppen.Exploring the Nature of the Beas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Meet the European Union [J].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1996,34(1):53 -80.
[4]Simon Hix.The Study of the European Union:the - New Governance:Agenda and Its Rival[J].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1998,5(1):38 -65.
[5][德]贝阿特·科勒-科赫,波特霍尔德·利特伯格.欧盟研究中的“治理转向”[J].吴志成,潘 超,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4):19-40.
[6]Gary Marks,Liesbet Hooghe.Contrasting Visions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M]//Ian Bache,Matthew Finderseds.Multi- level Govern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15-30.
[7][德]贝娅特·科勒-科赫,托马斯·康策尔曼,米歇勒·克诺特.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M].顾俊礼,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02.
[8]张茂明.欧洲联盟国际行为能力研究[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236.
[9]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思想库及其对华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418-420.
[10][德]贝娅特·科勒—科赫.转型视角下的欧洲联盟治理[J].吴志成,李向阳,译.南开学报:哲社版,2006(1):57-65.
[11]房乐宪,张 越.美日欧环境外交政策比较[J].现代国际关系,2001(4):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