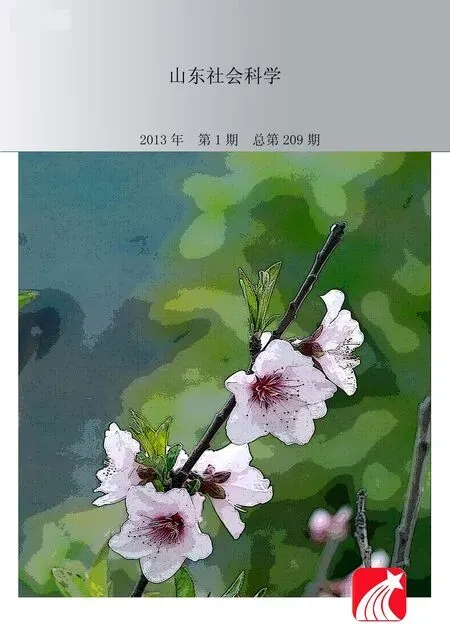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民歌保护模式研究
——以山西河曲“山曲儿”、左权“开花调”为例
段友文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山西被誉为“民歌的海洋”,晋西北的河曲、太行山区的左权都是著名的“民歌之乡”。河曲民歌、左权民歌的考察与研究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9 位专家学者专程到偏远的晋西北河曲采集民歌,出版了《河曲民歌采访专集》①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编:《河曲民歌采访专集》,音乐出版社1950年版。。进入新时期之后,山西歌舞剧院以山西民歌为题材创作的《黄河儿女情》与以山西民俗为题材创作的《黄河一方土》在全国上演,产生了轰动效应,被誉为“黄河歌舞派艺术”。八九十年代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音乐学院把左权确定为民歌采风基地,2004年8月,在左权举办了原生态民歌研讨会,同时举办了国家级大型文化赛事——“第二届中国民歌擂台赛”。2006年,河曲民歌、左权开花调双双被选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浪潮来得这样匆忙和急迫,人们尚未来得及对科学保护的方法进行深入、理性的思考,理论研究的滞后成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共性问题。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运用民俗文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河曲民歌、左权开花调的传承机制与保护模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河曲“山曲儿”与左权“开花调”的文化生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被不断地创造和传承下来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民间的活态文化。”②李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政府主导型抢救模式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事象,其创生与传承都与特定的环境休戚相关:因环境而生,因环境而传,因环境而变,因环境而衰。所谓环境,实际上是指民众生活的文化空间,它以特定民族、社区的民众为主体,集自然与人文、现实与历史、经济与文化、传统与现代于一体,形成自足互动的生态系统,构成非物质文化赖以立足的生命家园。如果把非物质文化比做鱼的话,那么特定的生态环境就是它的生命之水。水之不存,鱼将不再,二者不可分割。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濒危,是因为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构成其生存的传统生态要素或消失,或在现实生活中不再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要研究民歌的保护模式就必须把民歌置放于文化生态环境之中,从整体上把握民歌文化生态系统。民歌文化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总体性范畴,它是以民歌文化为中心,由与之相关联的文化、社会、自然三个生态圈以及文艺主体生态系统、文艺本体生态系统、文艺功能生态系统诸因素系统性组合的整体,是包罗了文艺活动及其相关因素的文艺生态场。①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民歌文化在特定地域文化生态系统中有其特殊的生态位,这个生态位并不是定层定点的静止状态,而是有生命的动态概念,在地域历史文化土壤上生长、发展并充盈着生命的生成精神和艺术活力。
民歌不同于一般文人作品的吟风弄月,也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儿女私情、卿卿我我。它以一种生存方式融入了民众生活中,紧密地伴随着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节日礼仪,成为传达民众情感和观念的重要方式。民歌创作活动作为人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对人性的生成和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具有重要的生态作用。
特定的文化生态系统孕育了特有的地域文化形态,特定的地域文化语境则孕育了山西民歌独特的表演传统。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晋西北生态环境脆弱、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困苦。而恰恰在这样的环境中,从明代即有“户有弦歌新治谱”、“儿童父老尽歌讴”②河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河曲县志》,1989年版,第471页。的记载,一代又一代的河曲人用歌声诉说着他们的苦难生活和情感经历。地处太行山岳的左权县虽为穷乡僻壤,商贾不通,舟车不至,代代相传的民歌却成为他们表露情感的唯一方式,明代万历年间的《辽州志》曾用“比户弦歌,文风颇盛”③参见《谈谈左权民歌·代序》,转载左权县人民文化馆编:《左权民间歌曲选》(内部资料),1980年版。这样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了当地民歌演唱的情景。这是因为在贫苦的生存环境中,在单调的生活节奏里,民歌成为人们弥补现实不足、抚平生命缺陷的一种生存方式,借助文学幻想摆脱生命的束缚、超越现实的困境,在理想的生命体验中激发对未来生活的希冀和追求,这正是民歌无法替代的审美功能。民歌的永恒魅力正体现在它对人性生成和生命体验的意义上,这种生命补偿功能正显示了民歌重要的生态平衡和优化作用。
然而,民歌的文化生态环境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在面临社会转型的今天,民歌如何在新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如何保持生命力而又不损害其魅力,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寻找新的适应时代要求、适合民歌延续的传承方式就显得极为重要。
二、河曲“山曲儿”与左权“开花调”的传承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承文化形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传承”是核心,是灵魂。它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实践问题。传承性是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是延续传统文化的内动力,传承即是传统音乐的生命。“无论是国家级还是地方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文化的精华;无论是国家级传承人还是地方级传承人,都是文化精英”④田兆元:《民俗本质的重估与民俗学家的责任——一种立足于文化精华立场的表述》,《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只有建立传承人保护机制,落实好发展保护措施,民间音乐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传承发展而日益繁荣。
民歌的传承方式主要有群体传承、家族传承、社会传承三种。群体传承指众多的社会成员通过共同的习俗风尚、岁时节令和大型民俗活动等,共同参与并展演本地特有的民俗文艺。如左权每年的元宵佳节,便是民歌艺人大展身手的时候,大多村子会在正月十五的晚上“观灯”、“转火盘”,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家家户户门前都燃起了象征吉祥兴旺的“小火”,大家在“社火头儿”的引导下,按预先定好的路线绕村一圈,敲锣打鼓,边唱边舞,在这一活动中演唱“开花调”是必不可少的项目,村民们既是观众也是演员,在狂欢热闹的自然状态下使民歌得到传承。家族传承是指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中间传授,如左权红都村的歌手们都是一家之内有两到三人会唱,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延。社会传承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承;二是没有拜师,常听多看艺人或把式的演唱、表演、操作,无师自通习得的。左权民歌手冀爱芳8 岁就开始唱民歌,11 岁进入左权县晋剧团,后被调入左权县文化馆直到现在,她未曾专门拜师学艺,而是在民歌的环境中耳濡目染、自学自通的社会型传承人。
无论何种形式的传承,传承人都起着关键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传承人的培养,如果传承后继无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就无从谈起。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是传承人。河曲“民歌王”辛礼生、韩运德、贾德义、张存亮,左权民歌手刘改鱼、冀爱芳、石占明等,都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间“活宝”,身上承载着祖祖辈辈创造的文化精华,丰富的民歌遗产就存活在这些杰出传承人的记忆和技艺里。这些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薪火相传的不可或缺的人才。对于这些传承人,我们要实行活态保护,既要对他们的生活精心照顾,在经济上予以援助;还要鼓励他们用充满活力的口耳相传的方式去传播民歌,担当起传承的重任;同时也要鼓励年轻的民间音乐爱好者虚心向他们学习,使这些身怀绝技的艺人们身上的宝贵财富得以继承发扬。
民歌传承机制的建立,除了要“活态”保护传承人外,也要注意一些民歌文本的“静态保护”。口头传承作为民歌最重要、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文本”,在20 世纪后半叶已经受到严重挑战。上个世纪开始,便有很多音乐人开始收集民歌,如《晋中歌谣集成》、《忻州地区歌谣集成》、《河曲歌谣集成》、《左权歌谣集成》等,这些歌谣集成、民歌集成为民歌的传承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许多表现民众真实生存状况、本真生活体验乃至最隐秘的内心情感的民歌仍在逐渐消失,因此,还需动员大批音乐学家、民歌爱好者,长期地投身到民歌采集和整理的工作中,即实现民歌从“口头文本”到“书面文本”的转换,并使之得以保存。
当然,民歌传承机制的建立除了关注传承方式、传承人、传承对象外,还要探讨和总结民歌的传播接受规律、传承渠道、传播层、传承心理、传承世系等等。因此,民歌传承机制的建立必须以详细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它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也是民歌能够继续存活的重要保证。
三、河曲“山曲儿”与左权“开花调”的保护模式
所谓保护模式,即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产生的地域环境、发展历史、传承特点等设计的稳定完善的、系统化的保护措施。保护模式是相对稳定的,又是灵活多样的,它是一种保护方式,也是一种科学策略。在具体制定中,应该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类别、体裁,同时根据特定的民俗艺术形式的特点分别制定。
山西拥有丰富的民歌资源,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民歌却面临着濒危的命运。首先,农村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致使一直生活、活动在村落中的老艺人们不再拥有单纯的生活环境,民歌的传承不得不直面外来文化的冲击。其次,许多农民在经济条件改善后向往现代化生活,迁入城市,使得民歌的流传范围受到压缩,传承空间也逐步缩小。再次,民歌传承人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出现了“断层”。在山西民歌传承人中年龄最长的已86 岁,50 岁以上的占到67%,而且许多老艺人体弱多病,生活条件差,无法承担传承的重任。此外,民歌的普及度也日益下降,在市场经济和多样性文化娱乐的冲击下,民歌无法吸引年轻人的眼球,也无法换取丰厚的经济利益,只能在现代社会中“失宠”,会唱民歌的人越来越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歌的“消逝毫无疑问将导致人类文化基因的断裂,会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持续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①李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政府主导型抢救模式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针对民歌面临的诸多困境,在对河曲“山曲儿”和左权“开花调”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我们针对河曲与左权独特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传承特征等,设计其保护模式如下:
1.河曲“山曲儿”的保护模式
河曲地处晋陕蒙交汇地,地埋位置偏远,境内沟壑相连,经济物质条件落后。“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地瘦风大年年旱,缺吃少穿过日子难。”歌谣中不仅吐露了民众生活的困苦,也反映了河曲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生态环境。但是,这种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正好成为实现原生态保护的优势。通过详细的调查,我们发现当地人都比较喜爱民歌,也乐意传唱,那么就应该创造积极的传承环境,河曲民歌传承的连续性,可以通过在当地建立整体的民歌生态区来实现,开展各种形式的民歌演唱活动,鼓励年轻人多学多唱,同时还可以将原生态的民歌保护和利用现代传媒相结合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保护。所谓整体就是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拥有的全部内容和形式,也包括传承人和生态环境,也就是说要从整体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关注并进行多方面的综合保护。这就需要从事民族、民间音乐工作的学者们,首先要从自身做起努力维护原生态环境,相关调查研究的开展要建立在不破坏民歌生态的基础上,其次还必须帮助世代生活在原生态环境下的民众认识当地文化的价值,了解如何以最小伤害的方式来自觉地发展其原生态民歌艺术。建立民族文化原生地的保护网,对这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原生态民歌文化区加以保护,像对自然生态保护中退耕还林的补偿政策那样,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予以相应的经济补偿和支持。在实地调查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河曲县已形成了县城河神庙广场每天早晚群众自发演唱、巡镇文化站组织周边村落民众定期或不定期的参与演出,以及县民歌二人台艺术团专业演唱,三个层级的传承构成互动互补的民歌传承系统。
利用现代传媒使河曲民歌代代延续,也是保护河曲民歌的重要方式。通过现代媒体不仅可以让人们认识原生态民歌歌手、传唱原生态民歌、体味民歌中蕴涵的精髓,同时也打破了原生态民歌仅以口头传播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可解决原生态民歌歌手的谋生问题、情感问题及经济问题。可见,根据时代需要,通过新的形式向原生态民歌注入新活力,才能让原生态民歌的生命生生不息或延缓其衰老。
2.左权“开花调”的保护模式
左权处于晋中农耕文化区,受现代文化冲击的速度较快,因此左权“开花调”的保护应该以确立具体的民歌村为基础,同时实行分层级的、有体系的保护。左权民歌传承主体既包括民歌村中的原生态民歌手,也包括国家批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包括有县政府和文化部门管理的“开花调”艺术团、麻田八路军总部艺术团,同时还有太行山盲人艺术宣传队,以及三圪蛋艺术团、四圪蛋艺术团等班社组织,构成了从民众个体到演出班社,再到县级演出团体的不同层级构成的传承体系,他们在不同的演出环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左权县政府和文化管理部门特别重视民歌传承人的培养与发掘,开展了民歌进校园活动,做到保护民歌从娃娃做起,重视民歌保护的“培根”工程,他们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接受能力和审美需求,编写出了对应性的音乐教材,以加强原生态民歌的传承教育。把本土的音乐资源转化为本地中小学的乡土音乐教材,扩大了民歌的流传范围,极大地增加了民歌受众,提高了民歌延续自发性传承的可能性。学生可以在音乐课的学习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民间文化的熏陶,对家乡文化产生自豪感,以会唱民歌为荣,珍惜先辈留下来的宝贵民族文化资源,并很好地传承发扬,促进民间音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红都村是著名的原生态民歌手石占明的家乡,在这里人人会唱民歌,而且能即景生情随性演唱,以石占明一家为例,不仅石占明唱得好,他的父亲、大哥、二哥、三叔、四叔、四姑都是村里的好歌手,每个人都懂一种或多种乐器,一家人就可以组成一个乡村自乐班,有良好的家族音乐传承环境。因此,左权县政府将其作为典型的民歌村进行保护,不仅保护这些会唱民歌的人,还保护其自然生态环境、村中的原始建筑,甚至村里村外的一草一木和人们唱民歌的那种气氛也在关注的范围之内,这是一种典型的整体性保护。但是,目前对民歌村保护的力度还很不够,除左权县政府外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此外,左权县至今仍有许多生态环境好、群众演唱风气浓厚的村落,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可被确立为原生态保护村或歌王村。对这些民歌原生态保护村要提出保护方案,保证其本原、本真、土色土香的乡土社会气息。在抢救、保护原生态民歌时,我们更应该培养、发掘新歌手,使原生态民歌能够后继有人。在歌王石占明唱响全国之后,张保萍、郝利宏、郝云籽、陈华、窦斌华、常新等又一批新星逐渐在全国、全省歌坛展露头角。
左权县实施原生态民歌进教材、进课堂,以学校教学的方式保障原生态民歌艺术的传承和提高,对民歌保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也有一定困难:一是语言关,原生态民歌以地方方言传唱,在中小学任教的音乐老师可能未必是当地人,未必会讲纯正的方言土语,这样就很难保证学生学到原汁原味的左权民歌。二是文字文本少,原生态民歌没有固定唱词,一般是歌者即兴之作,被采录之后,失去当时的表演语境,学生学会了曲谱、唱词,却难以理解歌词的精神韵味。三是时代断层,老一代的民歌手能够即兴即景演唱,民歌是他们生存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新一代的民歌手包括学校的音乐老师对原生态民歌了解不深,他们教唱的民歌大多是从民歌集中学到的,缺少民歌那种自发创作、自由自在的审美特质。学生们怎样才能学到原汁原味的民歌,民间音乐的教学怎样才能收到满意的教学效果,仍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针对上述这些困难,左权县政府做了很多工作:首先,在教材内容的选取上,不仅要挑选出左权民歌、小花戏中著名的篇章,而且必须是内容积极向上、唱腔简单易学的。其次,组织全县范围内较为著名的原生态歌手对学校教师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对原生态民歌的内涵、唱腔等充分了解。这样,学生才能学到经典的、原始的本土民歌。
民歌作为广大民众“心灵的声音”,既是人类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又是最脆弱、最易消逝的文化遗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许多珍贵的民歌没能保存下来。今天,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开展,民歌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对这些“人间国宝”、“人类活财富”如何保护成为共同关注的话题。因此,民歌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将是一项有着深远意义的工作,不仅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更需要广大音乐工作者、民歌爱好者认真研究和探讨。
——西藏河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