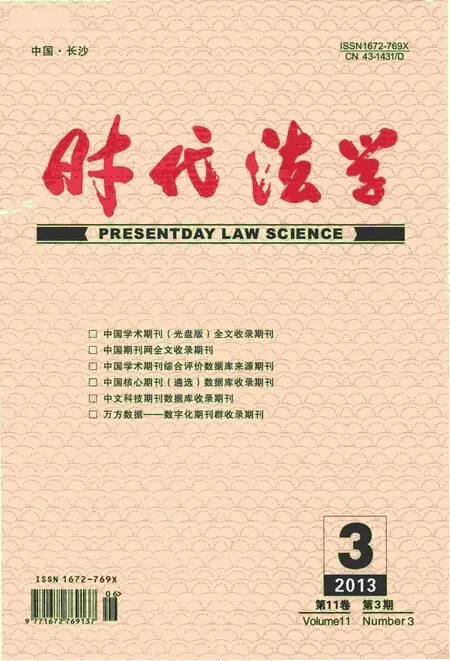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主权论*
杨 华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理论上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还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二是国际法优于国内法或是国内法优于国际法,还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互相独立而不发生一个优于另一个的两个法律体系〔1〕Lautercht's Collected Papers,Ⅰ,p.152.转引自王铁崖.国际法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80.?由于它牵涉到国际法的性质、国际法的渊源等诸多国际法根本性问题,始终是国际法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并引起热烈的讨论。围绕该问题形成了不同派别的主张,从早期的一元论、二元论,再到之后出现的自然调整论、协调论、法律规范协调说等等〔2〕关于一元论、二元论理论,可参见周鲠生.国际法(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6-19.王铁崖.国际法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80 -192.[奥]菲德罗斯.国际法(上册)[M].李浩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40 -153.关于自然调整论。见周鲠生.国际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9 -20.关于协调论,可参见 Ian·Browiie,Principl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6th ed,2003,p.33.关于法律规范协调说,详见参见李龙,汪习根.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法理学思考——兼论亚洲国家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J].现代法学,2001,(1):13 -19.。这些主张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性,即从规则主义出发,或者“主观地预设谁服从谁的逻辑框架”,〔3〕莫纪宏.论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新动向[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4):43.如一元论;或者人为地将两者截然割裂开来,如二元论;或者干脆回避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质,即“国家如何在国内执行国际法的问题,也就是国家履行依国际法承担的义务的问题”,〔4〕周鲠生.国际法(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0.如自然调整论;或者以“正义”、“秩序”等抽象的良法标准对国际法与国内法进行择优舍劣,单纯地以为法律规范可以统领国际法与国内法两大体系〔5〕贾少学.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论争的时代危机——对一元论和二元论进路的反思[J].法律与社会发展,2009,(2):63.,如法律规范协调说。虽各有其道理和根据,却有意或无意回避了影响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最深层次因素——主权,从而无法客观反映并回应日趋复杂的现实国际社会关系。
本文拟从主权的角度来考察和审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并试图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传统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理论背后的主权观;二是全球时代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发展的新动向及新主权观的确立。
二、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主权分析的可行性
从主权的角度探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考量:主权决定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又决定于共所处时代的情势。
(一)主权决定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主权一词源于拉丁文Super和Superanus,其中Superanus意指较高和最高,后逐渐演变为法文Souverainete、英文Sovereighty、德文Soueranitat。可见,最初的主权不是在近代含义上被使用的,而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概念是直到16世纪才真正出现。1576年,当被誉为“近代主权理论之父”的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其宏文《国家论六卷》(Six Livres De La Répubilque)率先明确提出“主权”概念并赋予其近代意义〔6〕博丹在《国家论六卷》一书中对“主权”所下的定义是“共和国的绝对和永久的权力”。在他看来,主权是绝对的、永久的、不可分的、不受限制的,君主是主权者,只受神法和自然法的支配。参见[日]筱田英朗.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M].戚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6.的时候,“主权”还只是一个被用于国内政治学上的词汇和术语〔7〕顾兴斌,章成.对主权概念在国际法上地位的再认识[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67.。将主权概念成功引入国际法领域,应当归功于“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年)。他的《战争与和平法》(the Law of War and Peace)将现代国际法发展成为一个较为系统的国际法体系〔8〕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98.。在该书中,格老秀斯以法律的语言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国家主权及其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仅弥补了博丹主权理论的先天不足,还从内涵上补充、发展和完善了近代主权的基本概念,奠定了国家主权内外统一性的法理基础”。〔9〕肖灵佳.国家主权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34.主权原则最终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中被正式确认为建立欧洲国家体系和稳定欧洲秩序的法律基础〔10〕邵津.国际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肯定了格老秀斯提出的国家主权、国家独立等原则是国际关系中应遵循的准则,开创了以主权国家基本行为体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该体系具有两个核心特征,“一个核心特征是用法律维持秩序的原则——即国家有尊重彼此主权的义务;另一个则是行为方式(尽管它也可以带有法律特征),即国家在国内和外交事务上享有高度自治权”。〔11〕[美]詹姆斯·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张胜军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66.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产生后的三百多年中,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但主权原则始终作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得以延续,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也全面继受了这一原则〔12〕《联合国宪章》第一章“宗旨及原则”第二条:“为求实现第一条所述各宗旨起见,本组织及会员国应遵行下列原则:一、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国际法思想虽然先后经历了数百年的理论嬗变,但主权概念始终是国际法中最古老、最基本的概念〔13〕程晓霞.国际法的理论问题[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15-31.。学者们在探讨国际法的定义、渊源、性质、作用等一系列问题时,都是围绕主权展开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问题。“正因为国家主权的存在和主权原则的确认,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才构成国际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学术史上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理论,也是基于对国家主权的不同认识。”〔14〕贾少学.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论争的时代危机——对一元论和二元论进路的反思[J].法律与社会发展,2009,(2):65.因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主权决定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理论折射出不同的主权观。
(二)主权决定于其所处时代的情势
主权从来就不是独立存在和与世隔绝的,它要受国际和国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军事、科技、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是对其所处时代的反映和回应。这归因于主权的工具性和开放性的基本属性。
诚如学者所言,“法学研究所创立的‘理论’具有服务功能”,理论都是为实践服务的。主权的工具性也毫无例外地体现在它的服务性上〔15〕“各国都视国家利益为主权的中轴,不是国家利益围绕主权旋转,而是主权围绕国家利益而展开。国家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动源,都深深扎根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中。正是变动中的国家利益决定了国家主权观的丰富多彩性。”参见肖佳灵.国家主权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497.。主权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是为国家推行国家政策,追求自身利益服务的。“依靠国家主权是居少数地位的国家面对居多数的敌对国家的一种自然的防卫性反应。”〔16〕[英]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M].汪暄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3.主权的工具性绝非笔者的主观臆想,让·博丹是如何创制出主权概念即是例证。近现代主权概念的创始人让·博丹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法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历史时期之一。当时的法国,政治和经济是封建制的,但思想文化罗马天主教会主导,法国君主的权力十分懦弱。法国各派政治势力围绕天主教派同新教胡格诺派之间的对抗而进行了长达36年的宗教战争〔17〕1562年3月,天主教派首领吉斯公爵率军突袭正在瓦西镇作祈祷的胡格诺派,残酷地杀害了许多无辜者,爆发了法国历史上的“瓦西镇大屠杀”,也成为这场宗教战争的导火索。直到1598年法国国王享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之后,战争才告一段落。战争持续达36年。这场战争虽然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从其性质和内容来看,可以称之为法国内战。参见江国华.近代主权概念的演进及其元价值——兼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的维护[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31.。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导致当时的法国四分五裂、生灵涂炭,法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以维护国家稳定,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博丹顺应时代需要提出了“国家主权”的概念,强调国家主权是绝对的和不受限制的,从而达到遏制国内封建割据势力和反对国外罗马教廷的干涉,加强君主的地位,谋求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安定的目的。这也是博丹的主权理论侧重于对内主权的原因所在〔18〕博丹在其《国家论六卷》一书中不仅提出了国家主权的原则,而且还具体地指出了国家主权的原则,还指出了国家主权的具体内容,即立法权、对外宣战及媾和权、官吏任免权、最高裁判权、造币权、度量衡选定权、征税权、带兵权、要求臣民忠节服从权等,主要涉及的是国家的对内主权。关于主权的工具性论述还可参见杨泽伟.主权论——国际法上的主权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71 -272.刘小川.全球化时代主权理论的困境与出路[J].学理论,2011,(18):50.。主权在之后的发展尤其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应用并没有改变其当初工具性的基本属性。
主权的工具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另一个属性——开放性。“主权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可以作出多种解释”〔19〕查尔斯·P·施莱克尔.国际关系导论[M].纽约:普伦蒂斯-霍尔,1954.173.转引自[日]篠田英朗.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M].戚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27.,就像任何一个国际法范畴一样,主权的范畴不可能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完全创新的概念,必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按照客观现实的需要而不断调整和充实自己。这也是主权这一古老而重要的范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主权法则可以从国际惯例、国际条约、国际法院的判决、学者专家的权威著作以及国际妥协和礼让等等方式中,取得自己的新的内涵和动因〔20〕[英]劳特派特.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M].王铁崖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7-24.。主权范畴的进化还来自于对现实的反省及理论的思考〔21〕王逸舟教授指出,最早在16世纪人们刚提出主权概念时,主要是针对神权而言的,因而把它界定为“国家的绝对和永久的权力”;到了17~18世纪,考虑到譬如说日耳曼帝国内部存在众多诸侯君主的事实,法学家们不得不争论并承认绝对的、完全的主权与相对的、非完全的主权的区别;19世纪在欧美继续着主权不可分与可分性的争论,它同样反映出现实中的复杂性和矛盾要求,如美利坚合众国与它的南部成员州之间的冲突;到20世纪,争执的焦点是,“从国内法的观点表现出来的主权,即作为最高的、原始的权力,并作为决定国家管辖范围的排他性职权,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是与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正常运作和发展相适合呢?”而21世纪,这一争论将继续下去。参见王逸舟.主权范畴再思考[J].太平洋学报,2000,(4):11.。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主权的历史演进中,就先后出现了绝对主权、议会主权、人民主权,以及部分的、可分的、附条件的主权等一系列主权理论。因此,我们“不能离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来理解主权”。〔22〕[澳]约瑟夫·凯米莱里,吉米·福尔克.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M].李东燕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4.
三、传统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理论的主权论
(一)“两派三论”之争
有关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传统理论,西方国际法学者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国内学者通常将其概括为“两派三论”,即一派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属于一个法律体系,即一元论;另一派则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即二元论。其中,在一元论中又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际法优于国内法,即国际法优先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内法优于国际法,即国内法优先说。从历史发展来看,在理论上最先出现的是二元论(传统二元论),并在一定时期占优势。后来又出现了一元论,并逐渐取代二元论成为占优势的理论。但一元论尚未一统天下,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理论中二元论至今仍有一定影响。
二元论在学界也被称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对立或平行说”,由德国学者特里派尔(Triepel)所创立〔23〕[奥]阿·菲德罗斯.国际法[M].李浩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40.,代表人物有安齐洛蒂、奥本海。他们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分属于两个独立的,平行存在的,不同类别的法律体系。因为国际法与国内法规则的主体不同,其所存在的社会基础不同,从而导致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在法律渊源、规定的关系、法律实质等方面的不同〔24〕贾少学.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论争的时代危机——对一元论和二元论进路的反思[J].法律与社会发展,2009,(2):67.。虽然二元论遭到一元论者(主要是国际法优越论者)的猛烈抨击〔25〕国际法优越论者认为,一切法律,包括国际法,无论形式上主体为何,其所规范的都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他们也不承认国际法和国内法出于不同的法源,认为法律的最后渊源是超乎人间意志的最高规范。,但至今在理论和实践中仍有一定的影响力。二元论“从实在法出发,较正确地分析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性质,论证两者是两种效力范围不同的的法律体系,这是国际法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发展”,〔26〕梁西.国际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18.但只是片面强调两者形式上的对立,割裂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内在联系,即“国家是制定国内法的,同时也是参与制定国际法的”,〔27〕周鲠生.国际法(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9-20.因此难以解释国际社会在国际法适用上的所有实践。
国内法优先的一元论以耶利内克(Jellinek)、佐恩(Zorn)、温策尔(Wenzel)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属于同一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国际法从属、根源于国内法,是国内法被用于国家对外关系的一个分支。它们的效力都源自于国家意志,而这种意志是绝对与无限的。总体而言,国内法优于国际法的观点本质上是对国际法的否定。随着时代的发展,该学说在现实中已没什么影响力,在国际法学界已几近销声匿迹。
通常所说的一元论专指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观点,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菲德罗斯、凯尔森、劳特派特、孔慈等。这一学说的主要观点是,世界上只有一个普遍性的法律秩序,各国法律体系是从属它而成为受委任的分支;国际法决定各国法律体系的属地和属地效力范围,从而使各国法律体系有共处的可能〔28〕Lauterpacht'x Collected Papers,Vol.Ⅰ,p.152.转引自王铁崖.国际法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86.。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将国际法视为世界法,完全超越了当今国际社会的实际。
(二)“两派三论”背后的主权观
“两派三论”的传统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理论,主要形成和流行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欧洲大陆。从主权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是民族主义的兴起。法国大革命后,“以王权之上为理论内核的主权在国王的头颅被法国革命者砍下之后已经不复存在”,国民主权的思想开始占有主导地位,这直接导致国家至高无上地成为主权的惟一拥有者,“隐含在‘主权’概念中的至高无上性在民族国家理论中被充分地表现出来”。〔29〕[日]篠田英朗.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M].戚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72-173.与此同时,为与让·博丹创立的相对国家主权理论相对抗,黑格尔开始鼓吹绝对国家主权理论〔30〕让·博丹把国家主权定义为不倚赖于国家法律的、对国家的公民和臣民的最高权力。但他也明白地承认,即使是主权的国家权力,也是受神法、自然法和国际法的拘束的。这样他从来没有主张过国家是最高的法律秩序。因而他提出的主权概念应当是相对的。参见[奥]阿·菲德罗斯.国际法[M].李浩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1-12.。他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国家意志理论。他认为国家是最高的秩序,没有任何法律秩序能够凌驾于国家之上〔31〕杨泽伟.国际法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18-119.。
尽管二元论与一元论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但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形式上,即从单纯法律规范的角度观察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异同的侧重点不同。前者注重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之间的相同点,而后者则侧重于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之间的不同点。二元论者充分认识到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主体、法律渊源、所规范的社会关系上的不同,从而得出国际法与国内法“不只是法律的不同部分或分支,而是不同的法律体系”的结论,认为二者“虽然有密切关系,但绝不是彼此隶属”。〔32〕王铁崖.国际法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81-184.与此相反,一元论者虽然也承认国际法在很多地方的确不同于国内法,但在性质上和功能上,国际法和国内法具有统一性。具体而言,在性质上,国际法与国内法一样都是法律,都具有法律的基本特征——强制性;在功能上,国际法律秩序是一种包括一切国内法律秩序在内的普遍性法律秩序,国际法律秩序决定各国内法律秩序的时间、空间和对人的效力。
如上所述,二元论和国内法优先的一元论之间的确存在分歧,但从主权的角度来看,两种理论又有一共性,即都带有黑格尔绝对国家主权理论的印迹。如最典型的二元论者奥本海就认为,“国际法无论作为整体或是其各部分,就都不能当然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只能是国内习惯或制定法使它这样,而在这种情形下,国际法的有关规则是经过采用而同时成为国内法的规则的。无论在什么地方或什么时候,如果不经过这样的全部或部分采用,国内法就不能被认为应受国际法的拘束,因为国际法本身对于国内法院是没有任何权力的。如果发现国内法规则和国际法规则之间毫无疑问地发生了抵触,国内法院必须适用国内法规则。”〔33〕王铁崖.国际法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81-184.奥本海所强调的当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根本冲突时必须适用国内法的思想,显然打下了绝对国家主权理论的烙印〔34〕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奥本海的主权观,当他期望根据“海牙和平会议”的经验起草一部国际共同体的“宪法”时,他坚持认为“这样的一部宪法绝不能侵犯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参见[日]篠田英朗.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M].戚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75 -76.。
黑格尔的主权思想在19世纪末被一些德国右翼理论家带向一个极端。在这个时代,主权被设想为只能在强大的国家中才显示出来的真正实体,而不能授予给每一个国家。检验主权的真正标准是权力,每一个主权国家都具有不可置疑的任意宣战的权力,也有随意推翻其签订的条约的权力〔35〕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主权的具体化”,是十九世纪末期主权概念的特征。参见[日]篠田英朗.重新审视主权:从古典理论到全球时代[M].戚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6 -58.。这种极端的绝对主权学说已经发展到几乎可以“完全毁灭国际法的程度”。〔36〕[英]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19.受此影响,一些德国国际法学者提出了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的一元论学说。佐恩和温策尔都认为,国际法的根源在于国内法,只是国内法的一个分支,适用于国家的对外关系。因此,佐恩提出“对外宪法”的概念;同样,温策尔也说到“对外的法律”;佐恩则声称:“国际法只有成为宪法才在法律上成为法律”。〔37〕Strupp,in Recueil des cours,Vol.47,1934,Ⅰ,pp.275 -276,176.转引自王铁崖.国际法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84-185.该学说的另一代表人物耶利内克在论证国内法优于国际法时采用了另一种说法——国家自我限制说。他认为,国家同意受习惯国际法和协定国际法的约束,是国家意志的最高体现;正是这种最高国家意志,限制了国家的主权;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国家本身通过“同意”这种机制,而对其主权意志所加的自我限制〔38〕杨泽伟.国际法史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20.。耶利内克的国家自我限制说是以承认国家享有绝对主权为前提的,与极端的绝对主权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正因为二元论和国内法优先的一元论在主权思想上的一致性,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二元论受到的批评主要来自国际法优先的一元论者,而非国内法优先的一元论者〔39〕王铁崖.国际法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84.。
这种极端的主权思想和国内法优先的一元论学说实际上是代表“德帝国主义传统的军国主义、权力政策的反动思想”,〔40〕周鲠生.国际法(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7.并最终将人类推向战争的深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向全世界敲响了绝对主权理论的丧钟〔41〕赵建文.关于国家主权的性质和地位的理论演进[J].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115.,否定或主张放弃主权的理论思潮开始兴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波利蒂斯(Politis)、塞尔(Scelle)、凯尔森(Kelsen)、菲德罗斯(Verdross)等人的有关理论。下面以凯尔森为例来说明国际法优先的一元论理论背后的主权观。
凯尔森无情地批判了主权信条:“国家只要被宣告为或者绝对化为主权的,它也就被假设成最高的法律本质了,它必须是唯一的法律本质,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主权排斥其他任何国家的主权,而且由此也排斥任何作为主权实体的其他国家”,因而认为国际法起因于多数主权国家同时存在的设想是不成立的〔42〕参见凯尔森,Allgemeine Staatslehre,1925,第106页。转引自[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M].王朴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97.。他断言,主权如果意味着一种无限制的权力,就肯定同国际法不相容;国际法既然对国家课以义务,就意味着限制了国家的权力;为了避免误解,最好是完全不使用“主权”这个模糊的概念来描述国家间的关系〔43〕周鲠生.国际法(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80.。凯尔森在其1919年发表的著作《主权问题和国际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国际法优先的一元论学说。凯尔森是规范法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法律秩序是一种规范体系,一个规范的效力来自另一更高的规范,最后追溯于一个最终规范——凯尔森称之为“基础规范”,并认为它是一个效力自明的最终规范〔44〕凯尔森将基础规范定义为“不能从一个更高规范中得来自己效力的规范”。基础规范并不是由造法机关用法律程序创造的。它并不是像实在法律规范那样由一个法律行为以一定方式创造的,所以才有效力。它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它是被预定为有效力的;而它之所以是被预定为有效力的,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一预定,个人的行为就无法被解释为一个法律行为,尤其是创造规范的行为。参见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26.132.。对凯尔森而言,国际法与国内法属于同一法律规范体系,这个法律规范体系是一种金字塔式的规范体系结构,是有高低等级层次之分的,而居于金字塔顶端的规范是一个“被预定为有效力的基础规范”,即“约定必须遵守”,它决定国际法的效力,也是整个法律规范体系 的效力根据。因此,国际法在整个法律规范体系中,居于效力等级最高的优越地位,它决定国内法的效力〔45〕凯尔森.国际法原理[M].王铁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33 -375.。国际法优先说完全把国内法的模式生搬硬套到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将国际法和国内法分别视为国家法和地方法,进而否定作为国家根本属性和国际法基础的国家主权,试图以世界法代替国际法,以世界政府代替主权国家,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故而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被认为是“所有现代学说中最有意识地和最完全地脱离社会实践的”。〔46〕沙尔·得·维舍尔.国际法的理论和现实(英译本)[M].66页.转引自凯尔森.国际法原理[M].王铁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译者前言第3页.
从主权的角度来看,凯尔森也承认一元论中的国内法优先说和国际法优先说之间的分歧关键在于对主权问题的看法,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学说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国家具有主权,本国法律秩序是最高法律秩序,在它之上并不存在任何秩序。相反地,主张国际法凌驾于国内法之上,当然会反对国家主权观念〔47〕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77.。
总之,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传统理论都是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不论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其背后的主权观或趋于绝对,或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否定国家主权的泥潭,都反映了特定时代国际社会的现实。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实践的发展,既有的主权理论也难免“落伍”,变革亦在所难免。
四、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发展的新动向及新主权观的确立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中的新动向
人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先进科技、民主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等因素的出现,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与“英美在20世纪40年代制定他们的理想计划时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时代背景相去甚远”。〔48〕[英]桑斯.无法无天的世界:当代国际法的产生与破灭[M].单文华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2-18.与此同时,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独立的国际组织,此外,在人权国际保护方面,随着国际人权法日益发展,国际人权保护的范围不断扩大,使主权国家承担了前所未有的保障人权的责任。
1.国际社会的组织化
“在人类演进的漫长岁月里,由原始集群发展到氏族,由氏族发展到部落,终于产生国家,这是一次飞跃;由国家交往而形成国际社会,在国际合作中又产生国际组织,这又是一次飞跃。”〔49〕梁西.国际组织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3.328.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组织蓬勃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国际组织的数量呈爆炸性增长,而且表现在国际组织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职能日益膨胀。各种类型的国际组织活跃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国际社会的大舞台无处不闪耀着国际组织的影子。“国际组织数量的增加与职能的扩大,使地球上彼此影响的各种国际组织,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组织网,出现了国际社会组织化的一种新趋势。”〔50〕梁西.国际组织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3.328.
国际社会的组织化对传统的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关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世贸组织建立的WTO规则以及为了保证WTO规则得以实施的“专家组”对WTO成员国之间贸易纠纷的仲裁权力,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国际法理论对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解释;同样,“超国家组织”欧洲联盟的出现,传统的一元论和二元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欧盟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以及目前存在于欧盟组织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2.人权保护的国际化
“人权最初与特定的阶级利益相联系,在新兴资产阶级反抗专制政治权力和僵化的社会体制的过程中,人权充当了意识形态上的和政治上的武器。”〔51〕[英]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的终结”六论[J].江兴景译.法学家,2009,(2):1.人权的概念,是17、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并被视为人一种天赋的、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例如,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就宣称:“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他们固有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有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在第1条就开宗明义写道:“人人生而享有自由平等之权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权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原则上仍然被视为主权国家的保留范围或国家管辖范围内的事项,尽管此时国际法已经存在各种保护个人的制度〔52〕Nigel S.Rodley,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2nd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这种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彻底改变。德、意、日法西斯大肆践踏基本人权的罪恶行径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在那些政府可以随意压制和毁灭自己国民的国家,和平是没有保障的;那些政府权力在本国行使时不受约束、不受限制的国家,在国外也不可能限制自己的行为;国际法不能停留在只关注一国在其国界以外的行为,国际法再也不能只是调整国家间法律,它也必须关注国家内部所发生的事情〔53〕Nigel S.Rodley,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2nd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3 -5.。人权问题由此从国内法领域开始进入到国际法的调整范围。到如今,人权已经成功席卷全球,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项核心原则。“人道主义干涉、对战争罪的审判、对国家首脑侵犯人权行为的检控等等,都是这一格局的表现。”〔54〕[英]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的终结”六论[J].江兴景译.法学家,2009,(2):1.
人权保护的国际化对国家主权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传统法理带来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在国际人权领域,主权国家与其国民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完全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而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从而使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国际法要求主权国家善待其本国国民,对国家及于其国民的主权权力作出某种要求或限制,已成为当代国际法的重大发展之一。”〔55〕杨泽伟.主权论——国际法上的主权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1.265.另一方面,国家主权受到人权国际保护的限制,主权国家不能违背国际条约中所体现的有关保护人权的一般性国际义务,也不得违反其缔结或加入的国际人权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总之,随着人权国际保护的发展与演进,各国对待其国民的主权权力,“已受到国际法和特别是人权的要求的限制”〔56〕[英]詹宁斯,瓦茨.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M].王铁崖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105.。
(二)新主权观的确立
面对日趋多元化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实践,传统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理论以及既有国家主权学说都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不得不面对这些新问题作适应性的调整。在欧美理论界。国家主权理论逐渐衰弱,而挑战、弱化和否认国家主权的思潮再次泛起,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主权过时论,该观点认为“国际法上主权概念之时代已经来过,但也已经过去”〔57〕Lillich,Sovereignty and Humanity:Can they Converge?in Grahl Madsen and Toman ed.,The Spirit of Uppsala,1984,p.407.。主权演变论,该观点认为主权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主权可分论,该观点认为主权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履行多种不同的功能,因而是可分的,大国和强国所享有的主权要素较多,小国和弱国所享有的主权要素则要少些。道德相互依存论,该观点宣称人类正在国家或公民社会向“人类社会”过渡,正在由“物质相互依存”向“道德相互依存”过渡。在这种情势下,主权国家的政府对人民的共同利益承担责任的状况不得不有所改变,它需要与国界内外的其他行为体分担这种责任。主权弱化论,该观点认为全球化和全球问题导致国家权能的“泛化和弱化”,主权概念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正逐步失去其传统基础。主权让渡论,认为主权是可以让渡的,且这种让渡是必然的、合理的,对国家有利,国家只有相互让渡主权,才符合国家发展的总体利益。人权高于主权论,强调保护人权是最高宗旨,人权问题不再是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国家主权正在被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的力量重新界定〔58〕卢凌宇.挑战国家主权的思潮[N].人民日报,1999-08-08.。
上述种种弱化和否认国家主权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其一,从论证逻辑上来看,上述观点大多有意或无意混淆了两个基本概念:主权和主权的行使(治权)〔59〕郭辉.主权概念的历史演变——起源和归属的角度[A].李双元.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第21辑)[C].北京:中国检察院出版社,2012.142 -143.。其二,虽然国际社会的组织化趋势不可逆转,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它都无法撼动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角地位,“即使国家的自治和作用由于超国家的趋势而减弱,也还没有出现一种足够的东西来代替它”〔60〕[美]保罗·肯尼迪.为21世纪做准备[M].何力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843.。只要民族国家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消亡,那作为其基本属性和构成要件的主权就不会消失。欧盟的产生绝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和主权的消亡,“把欧洲联盟视为一个超国家并在短期内能取代民族主权的各成员国,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61〕Magdalena M.Martin Martinez,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6,p.306.。其三,国家主权作为国际法的基本范畴,是整个国际法体系的支柱,没有主权概念,国际法体系必将坍塌,国际法的进步并未发展到完全否认主权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和地位〔62〕杨泽伟.主权论——国际法上的主权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1.265.。其四,应当辩证地看待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套用著名法哲学家、人权理论权威科斯塔斯教授的话来说,“两者貌似水火难容,实则紧密相联”,它们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应当警惕人权国际保护被政治性利用,因为人权一旦“成为被警察权呵护的‘天使’,正是(人权)理想消亡的原因所在”。〔63〕[英]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的终结”六论[J].江兴景译.法学家,2009,(2):1-11.
当然,我们在反对种种弱化、否认主权论调,坚持“不可能把主权从国际法领域内任意抹去”〔64〕阿南.国际法上的主权[A].阿南.对抗或合作?国际法和发展中国家[C].1987.72.转引自王铁崖.中国与国际法——历史与当代[A].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国国际法年刊(1991年)[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67.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当今主权国家和国家主权理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即如何根据主权的工具性、开放性特征,确立或发展出一种既符合国际法发展和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实践,又有利于实现各国政治独立和外交自主及经济社会发展等重大需求的新的主权观。在当代国际关系条件下,“主权这个古老的范畴顺应时势地衍生出一些新的内涵和趋势,适合各国及世界新的现实和要求。”〔65〕王逸舟.主权范畴再思考[J].太平洋学报,2000,(4):7.
笔者认为,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去解析国家主权,是一种可能的解决途径〔66〕关于这个途径,本文参考了郭晖的文章:《主权概念的历史演变——起源和归属的角度》,载李双元主编:《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第21辑),中国检察院出版社2012年版和盛文军、王庆国、田银华的文章《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载《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3期。。
要把握主权的概念,只能将与主权相关的因素剥离,即当我们不考虑主权的行使主体(主权者)、主权的行使方式、主权的行使对象之时,我们就可以将主权抽象为一种静态的、本质的东西——最高的权威。当博丹第一次把这种“最高的权威”定义为“主权”,并把它视为国家存在的基础之后〔67〕在《国家论六卷》一书,博丹形象地认证了主权与国家的关系,他把国家比喻成一条船,主权则是船的龙骨,如果把支撑着船体首尾和甲板的龙骨抽去,船就没了样子。同样,国家如果没有主权,国将不国。参见王沪宁.国家主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9.,主权与国家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从未分开过。主权作为国家的固有属性,是国家的灵魂,是国家必须拥有的资格。只要国际社会仍然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社会,主权的这种人格和身份属性就具有绝对性。主权的对内最高性和对外的独立自主和平等性从其产生之日起始终是主权的根本属性,只要这两种性质没有改变或者丧失,则此国家就享有主权〔68〕郭辉.主权概念的历史演变——起源和归属的角度[A].李双元.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第21辑)[C].北京:中国检察院出版社,2012.145.。在这个意义上,主权就是绝对的、最高的和不可分的、不可转让的。
由于主权是一种高度抽象、静态的东西,它本身的作用体现和实现方式不能通过它本身,而只能通过具体的主权的行使,即治权〔69〕关于治权的论述,可参见郭辉.主权概念的历史演变——起源和归属的角度[A].李双元.国际法与比较法论丛(第21辑)[C].北京:中国检察院出版社,2012.143 -147.。治权作为一种权力,是指政府治理国家的权力。它是由主权行使者(主权者)和行使者的行为以及行使的对象组成的。在这里,治权就是主权的另一个面。对于静态的主权而言,其动态的存在方式即治权具有相对性,是可变的、可分割的和可转让的。
综上,我们可以试着这样去理解主权:在主权理论的历史演变中,主权概念本身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治权。主权的两面性就体现在它的绝对性和相对性,主权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主权是国家存在的前提与基础,相对治权是主权的体现与保障。在实践中,主权与治权紧密相连,但两者并非总是相辅相成,有时也会发生分离〔70〕关于主权与治权的分离现象,也有学者称之为主权的“层化”。试举一例,在美国占领巴拿马运河期间,虽然主权仍然属于巴拿马,但谁都不认为美国人不曾拥有实在的好处和权力,如处置争端、处罚罪犯等等。在巴拿马运河区,在1999年巴拿马将它收回以前,巴拿马对它拥有主权但美国拥有治权。参见王逸舟.主权范畴再思考[J].太平洋学报,2000,(4):8.。丧失主权的国家,“国将不国”,治权更无从谈起。但若只是丧失治权,主权则仍有可能存在,“国仍可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