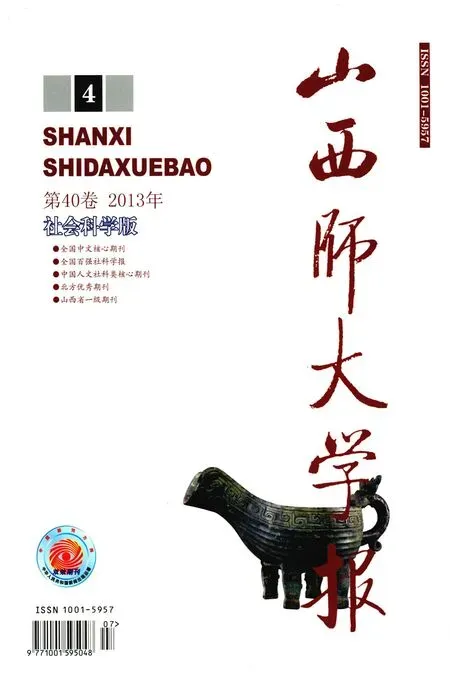牧歌式宁静与背叛式逃离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女性主体意识
乔婷婷
一、特蕾莎的牧歌——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
小说的主人公特蕾莎是一个生命之重的人物。对爱情的专注和责任、对丈夫的宽容和忍受、对事业的认真和执着、对善恶的爱憎和明断……,在重压之下艰难地活着,活得实在。以至在这个没有美和真爱的人间,最后只能在一条狗的身上找到人间的牧歌、找到真爱,在宁静的乡间完成了属于她的主体意识的建构。
法国著名女作家西蒙·德·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小说中的特蕾莎是一个在爱情中追求灵与肉统一的女人,她希望自己所爱之人能永远的不论在肉体还是灵魂上都忠于她,因为她要求自己也是如此。但她的爱人托马斯却是一个生活放荡、到处沾花惹草的人,在他们的爱情生活中,特蕾莎,这位女性毫无疑问的处于被动地位,她不自觉地处于被男性支配,处于“被看”的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托马斯与特蕾莎的爱情是建立在男权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该文化模式使女性沦为人类两性关系的他者,使其居于被支配的地位。从一开始托马斯就很自然地将特蕾莎置于“他者”的地位。托马斯一再强调特蕾莎“和他过去生活中的任何女人都不一样。既不是情人,也不是妻子。她就像是一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的孩子,顺水漂来,好让他在床榻之岸收留她。”当特蕾莎第二次与托马斯激情欢爱,共枕而眠后,“早上醒来,他发现特蕾莎还睡着,攥着他的手。他不敢把手抽出来,怕把她弄醒…他又一次对自己说,特蕾莎是一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顺水飘来的孩子。河水汹涌,怎么就能把这个放着孩子的篮子往水里放,任它漂呢!”特蕾莎在没有托马斯在的情况下很难入睡,“如果得一个人呆在单室套,她整夜都闭不了眼睛。而在他怀中,无论有多兴奋,她都能慢慢入睡。他为她编故事,轻声讲给她听,或者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他完全控制了她的睡眠,要她哪一刻入睡,她就在哪一刻入眠。”托马斯俨然成为特蕾莎的一切,掌控着她的喜怒哀乐,这是极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双方分别处在强者和弱者的两极,托马斯好像是她强大的庇护和依靠,对特蕾莎这个娇小、瘦弱而清纯的女子有种莫名的感情,让他“从中呼吸到了莫名的幸福的芬芳”,让他“想照看她,保护她”,所以两人的爱情是不平等的,并使两人都陷于痛苦之中。
就社会地位而言,托马斯和特蕾莎两人相差悬殊:托马斯是职位体面、待遇丰厚、受人敬仰的外科医生,外表潇洒英俊、风流倜傥,到哪里都能赢得女人的青睐,特蕾莎是一个骨子里是个传统伦理式,没见过什么世面,只想一心逃脱母亲的世界,投奔他而来的乡间女招待。托马斯就是特蕾莎的根基,在他们的性爱游戏中,托马斯总喜欢用一种职业性的口吻说“把衣服脱了”,就能令她激动不已,只想听命于他,让她加倍强烈地渴望服从。小说《卡列宁的微笑》一章中,描写了特蕾莎与托马斯在宁静的乡下生活,与朋友一起去酒吧跳舞时,特蕾莎与托马斯的对话,“我是造成你一生不幸的人……,是自己让他到了这么低的地步……我们俩不能比,对你来说,你的工作比世界上一切都重要,而我呢,随便干什么都可以,我不太在乎。”在特蕾莎意识中,女性就应该劣于男性,男性主导着一切的,自己只是依附于他,社会地位也就低于托马斯,这也造成了特蕾莎对自己女性主体意识薄弱的原因。
特蕾莎对托马斯的依赖程度,并不仅仅因为她爱他,也与自己成长经历有关。特蕾莎的母亲有过两次婚姻,她的第二个毫无男子气概的丈夫是其深爱的男人,但总爱沾花惹草,让特蕾莎母亲感到不安。在命运的折磨下,她由原来的端庄变成了粗俗。在特蕾莎与母亲的生活中,她深深受着母亲的影响,母亲对特蕾莎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展示给予严重的鄙视和嘲笑,“在这个世界里,青春和美貌毫无意义,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肉体集中营,一具具肉体彼此相像,而灵魂是根本看不见的。”在此表明,女性处于自我缺失状态,特蕾莎是母亲肆意践踏肉体、夸耀丑陋时竭力忽视的“他者”,对于特蕾莎来说,母亲是她自从童年就缺失的(她的母亲对她的恨超过了爱),她终生都被这种原始的缺失所困扰着。由于母爱的缺席,特蕾莎转向她深爱的托马斯企图填补她的缺失,对特蕾莎而言,与托马斯的偶然相遇唤醒了她的灵魂,从那以后,托马斯就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她觉得只有托马斯的爱才使她能够“逃离母亲的世界”——那个没有个体、没有隐私、没有灵魂的集中营式的世界。这也造成了她对托马斯的深深依恋。
关于特蕾莎梦的解析,也可反映出特蕾莎完全将自己置于忠贞、被动的地位,使自己处于以男性中心主义爱情的艰辛之中。在她和托马斯相爱的岁月里,托马斯却一直试图使她相信“他跟多个女人风流与他对特蕾莎的爱情毫不矛盾”。特蕾莎在理智上不得不接受了这一点,她对托马斯说:“我知道你爱我,我完全知道你那些不忠的行为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是特蕾莎的内心不能接受这一点,因为她爱托马斯只是因为托马斯能唤醒她的灵魂、自我,而托马斯愈演愈烈的偷情却把她推回了那个使她饱受羞辱、失去自我的世界,所以特蕾莎的生活中总是伴随着无休无止地关于死亡的噩梦。比如那个经常做的、关于猫的梦,“小猫总是跳上她的脸颊,爪子伸到她的皮肤里。”在捷克语中,“猫”为俗语,指漂亮姑娘。特蕾莎感到女人的威胁。所有女人都可能成为托马斯的情人,她为此而感到恐惧。还有另一类她总是送死的梦:在一个封闭的游泳馆,一个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们围着游泳池不停地走,托马斯坐在悬挂在馆顶的篮子里向大家发号施令,如若不遵守便被枪毙。这些梦完全将托马斯置于中心,甚至特蕾莎还想,“明明知道他的不忠,却又不要去惩罚他,办法倒是有一个,那就是他要把她带在身边!他到情妇家去时要带着她一起去!这样她的身体将成为托马斯的另一个自我,成为他的陪衬,他的帮手。”这是多么荒唐的想法,但软弱的特蕾莎面对托马斯毫无办法。这种无休无止地爱情的折磨说明,建立在男权中心主义之上的两性关系是无法和谐、幸福的,女性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证明自己的存在。
在小说最后《卡列宁的微笑》一章中,特蕾莎终于在宁静的乡下,和托马斯当起了农民,在牧歌式的生活图景中,才摆脱了嫉妒,摆脱了噩梦,摆脱了灵肉困惑。特蕾莎感到托马斯不再强大,她得到了完美的爱情,感到幸福。苏珊·格里芬指出:“我们(女人)知道自己是由大自然创造的——我们就是大自然。我是观察大自然的大自然。我们是具有自然观念的大自然。是哭泣的大自然,讲述大自然的大自然。”在她们看来,地球上的生命是一个有机整体,并无尊卑上下的等级差别。男性价值观的基调,如笛卡尔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观点所表现的那样:是对自然的蔑视和占有。而女性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更接近于感性和自然。特蕾莎找寻到的的乡间生活就是人在意识到现代社会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和人生存于其中的痛苦后所追寻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她摆脱了男性强大的困扰,她完成了自己女性主体的真正建构。
二、萨宾娜的背叛——女性主体意识的独特性
萨宾娜与特蕾莎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有着与她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她是一位独立的女性,她寻找自我的方式是背叛,这种自我意识的形成原因有着多方面的因素。
从孩提时代开始,萨宾娜就被教导背叛是世界上可以想得到的最可恨的事。但吸引萨宾娜的是背叛,在萨宾娜眼中,“背叛,就是脱离自己的位置。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萨宾娜觉得再没有比投身未知更美妙的了”。她为了反抗在十四岁时父亲对其初恋的压制而选择了背叛,在中学毕业后便去了布拉格,终于背叛了自己的家,心中感到一丝宽慰,之后她的一生都在不停地“背叛”:她背叛父母嫁给了一个平庸的演员,只因为他有离经叛道的坏名声;而后她背叛了自己的丈夫,再一次的投身于未知。她一反常规的作画,用以背叛丑恶的所谓的社会现实主义。她背叛横行的音乐噪音,背叛极权统治下整齐划一的群体运动,一切盛行的都是她背叛的对象。在她脚下展开的人生就如同一条漫长的背叛之路,每一次新的背叛,既像一桩罪恶又似一场胜利,时刻在诱惑着她。
出于艺术家的敏感,萨宾娜一直在追求一种真实、自由的生活。她洞察到当时的捷克、欧洲包括美国都力图建立某种“媚俗”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表面是清晰明了的谎言,背后却是晦涩难懂的真相。”对于萨宾娜来说,那顶旧的黑色圆顶礼帽,她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唯一遗产,是“她公然培植的个性的标志”,它成了萨宾娜独特个性和她的背叛本质的象征。萨宾娜认为,她终生的使命就是反对媚俗:她戴着礼帽凝视镜子的古怪行为是她厌恶媚俗的标记。那个古怪奇特的镜中映象显示了萨宾娜惊世骇俗、背叛传统的独特个性。它代表了她的“理想自我”——抛弃所有的媚俗,“叛己所叛”到极至,永远投身于未知之中。它“成了萨宾娜生命乐章中的动机”。萨宾娜对俄国的影片也很反感,“一想到苏联的媚俗世界会成为现实,而她又不得不生活其中,让她直起鸡皮疙瘩。她宁愿生活在现实制度下,哪怕有种种迫害…在现实的世界里,是可以生存的。”在由男性主导话语扩展为世界性话语的男权统治中,萨宾娜对抗的也是男权世界的统一,是整个带有男性特征的政治极权、文化专制等,这构成了萨宾娜的背叛所指。同时这种对抗媚俗的态度、观念、行为,也建构了她的女性话语和女性世界。
在萨比娜和弗兰茨的爱情世界中,弗兰茨对萨比娜迷恋的如痴如醉,但“他面对情妇时没有安全感,他是个英俊的男人,正处学术生涯的顶峰,总担心她会离他而去,在他们相遇不久后,采取主动的是她,而不是他”,所以萨宾娜是他们爱情和性爱生活的主导。弗兰茨对萨比娜无比的迷恋、尊重、忠诚,甚至在两人的性爱生活中,弗兰茨都是被动、软弱、服从的,虽然弗兰茨是很健壮,但他的力量仅仅是对外的。萨宾娜认为“他就像一只吃奶的巨大幼犬”,而当她深爱的弗兰茨选择离婚,想跟她结合的时候,她固然惋惜,却毫不犹豫地再次选择了背叛,去乡间作画,去追求自己轻盈的生活。
三、女性主体意识存在的意义
特蕾莎与萨宾娜这两个拥有不同生命体验的女人,虽然主体意识形成的过程与方式不同,但她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真实自我”的女性主体意识的探寻,特蕾莎在责任、忠贞等重压之下艰难地活着,活得实在,最终在牧歌式生活中赢得了“真实自我”。而萨宾娜的一次次背叛的逃离悲剧不是因为重,而是在于轻,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2]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3]苏珊·格里芬.女人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M].毛喻原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