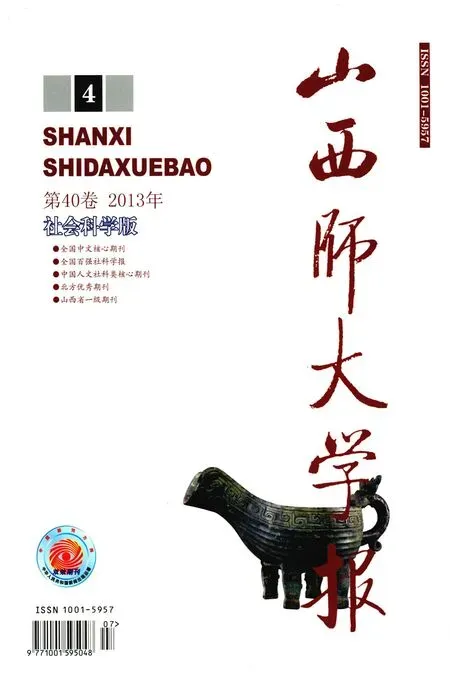电影字幕汉译中的“占便宜”现象浅析
——以美国电影《怦然心动》为例
杨 虹
翻译从来都是以一种受影响的方式在进行,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之争从来没有一个定论,因为它们都是受到影响后翻译活动的产物。从翻译伦理上来看,很难断言哪个好或哪个不好,因为翻译现实表明,两者在目标语言文化中“起着各自不能互相代替的作用,完成各自的使命,因此,两种翻译将永远并存,并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两者的差别在于,异化翻译者多受异族语言文化影响,并因此而在目标语中突显异域文本的异域性;归化翻译者则多受我族语言文化影响,并因此而在目标语中全力去除异域文本的异域性。
英文电影作为美国对中国文化入侵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人们的生活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英文电影字幕的汉译虽然不像文学翻译一样有着特定的译者,但其翻译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换言之,英文电影字幕的译者是“隐身”的。而按照韦努狄的主要观点:在翻译中要求译者隐身是错误的;译者在译文中不能隐身,而应当有形可见。这就是说,翻译应当采用“异化”的原则和策略,使译文保持异域风貌、异国情调,读起来像译文,而不是“归化”的原则和策略,使译文完全按照目标文化的意识形态和创作规范进行改造,读起来不像异族作品,而就是目标语原创。韦努狄对西方17世纪以来的翻译进行考察,发现西方翻译史上一直都是归化翻译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英国。究其原因,就是深藏在背后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规范在作怪。韦努狄对这种以我族文化为中心的归化翻译提出质疑和批评,认为把异族的东西归化为我族的东西,这是一种“文化侵略”。异化翻译则相反,它能抑制民族中心主义对源文本的篡改,特别是在当今处于强势地位的英美语言文化环境里,异化翻译“可以成为抵御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文化上的自我欣赏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以维护民主的地缘政治的关系”。
显然,在韦努狄看来,“归化”与“异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问题,而是必须把它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的范围里来考察。然而,在和平年代究竟应不应该把翻译活动放在这样的范围里来考察,或在何种程度上作出这样的考察,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在英文电影字幕的翻译过程中,这个问题同样值得探讨。
一、文化霸权与电影字幕汉译
把强势的英美语言与文化当作源语、源文化,而不是目标语、目标文化?如把英美作品译入某种发展中的非洲语言,而不是把非洲作品译入英语?如果在这个转换了方向的语境中,我们按“异化”原则移植了英美源文本的异族特征,所产生的结果会不会同样被看作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如果不是,那又是什么?假如因为强势的英语变成了源语、弱势的非洲语变成了目标语,而把原本提倡的“异化”主张修正为“归化”主张,以彰显对“阻抗”殖民文化入侵的考虑,那么,这会不会意味着韦努狄所说的“异化”只适用于把英语作为目标语的翻译?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韦努狄似乎没有给予必要的解释。虽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也因此而给了我们更多的研究空间,并引发更多、更深层次的思考。
总之,翻译应当从人出发,特别是从译者的感受出发。翻译的后殖民理论往往过分强调社会文化对于翻译的影响,忽略了人的自由、人的创造性以及人的冲破霸权的本能,因此都是离经叛道的理论。很明显,鲁宾逊的这个观点带有强烈的反文化学派的色彩。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能动作用,这又使他的思想接近文化学派的译者“操纵”观。其实,从根本上看,鲁宾逊强调人作为决定因素的译者中心论和强调文化环境因素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也就是鲁宾逊所说的后殖民理论之间并无本质的冲突。不错,翻译说到底是一项人的活动,翻译过程中的一切决定最终都是由译者这个人来作出的。然而,译者在进行抉择的整个过程中,始终都会受到各种因素,包括种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译者的最终抉择权无疑也只是一种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不受干预的权利。因此说到底,鲁宾逊的基本翻译思想仍属于文化学派的大的范畴。这一点,在他的主要论著中都得到了清楚的说明。
二、电影字幕汉译中的“占便宜”现象
电影字幕汉译中的“过度归化”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因为电影是集艺术、商业于一体,为了迎合目标受众,译者难免会以目标语为主,而忽视了源语,这就是电影字幕翻译中的“占便宜”现象。如果处理不好,会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障碍。下面将就美国电影《怦然心动》的字幕翻译翻译中过度归化现象的原因和表现形式进行探讨,试图找到解决的对策,以利于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1.滥用粗话。
例1 A retard?Well,that ought to tell you something.
译文:智障?操你也该看出来一些事吧
例1中对“well”的翻译有滥用粗话之嫌。不是人人都能分辨什么是迂腐之词,什么是诗的语言,也不是人人都能标新立异,因此在借用外来词时一定要慎重。可以采取四个步骤:(1)译者必须断定,所要引进的词在原语中是不是个好词;(2)仔细斟酌,看其是否符合英语特征;(3)征求有识之友,尤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友人的意见;(4)适可而止,不得滥用,因为外来词如果用得过多,就会显得引进外来词不是为帮助接受者,而是为了征服他们。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有略加增减的自由,但“增补的内容必须与原作思想有必不可少的联系,并实际上能加强原作的思想”。而删减的内容则应是那些“明显多余而又有损于原作思想的东西”,是“句子中的次要成分”。在译诗中,译者可以更加大胆地运用增减手法。同时,译者还必须“始终与原作者比智”,保持原作者的高度,并在可能的时候超越他、改进他。但这种超越和改进是有限度的。译者不能增加任何与原作者的特殊思想和表达方式不相符的东西,同时译者如果缺乏诗的鉴赏力和天才,也不宜滥用这种增减原作的自由。
2.滥用替代法。
例2 You know,the one where they cut down that big ugly tree.
译文:就是挨着以前那棵丑八怪大树的房子。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有过度、不及和适中三种状态,前两者是恶行的特征,只有第三种才是美德的特征、道德的标准,如勇敢位于怯懦和鲁莽之间,因此是美德。在翻译中,如果既不是借原作者之名以营私的胡译,又不是拼凑字典的死译,信息含量乃至轻重、色彩、分寸等都很妥贴,合乎具体翻译目的的要求,那么,这种状态不是“中道”是什么?翻译大家的过人之处究竟在什么地方?笔者认为不外乎以下两条:一是语言功底好,二是翻译原则掌握得好。第一条是“笔随人意”或称“言随意遣”(陈望道语)的基本保障,而这第二条,就是一个掌握“分寸”的功夫。王佐良先生译的培根散文,杨必先生译的《名利场》,都是把翻译中的各种因素协调得恰到好处的上乘之作。不止是翻译,文学作品中“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也是一种为文者孜孜以求的境界,而和谐、得体、适度自古以来就是修辞学的核心概念。不管是“过”与“不及”,还是“太白”、“太赤”,都是用否定式作出的陈述,而“第三种状态”是值得用肯定式为其正名的。摆脱两极纠缠以后,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似应更多地注意与协调、平衡有关的内容,
3.滥用反语。
例3 Mom,are you trying to make the Bakers feel totally worthless?
译文:妈,你这是要让贝克一家觉得自己倍有面子吗?
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就是过分突出国别翻译学的地位,强化民族偏见等。奥古斯丁把意思和语言明显区别开来,认为意思是“常数”,语言则是一系列的符号,在概念和听众之间起桥梁作用。翻译中,由于概念在各种语言中是共同的东西,因此,译文的符号结构必须反映原文的符号结构。而对于这种符号结构,特别是对于“所指”与“能指”在同义或多义问题上的联系,译者必须通过自己的语言能力加以分析判断,才能提供好的译文。它们之间所以存在差异,乃是因为圣灵具有神的权力,可以通过译者说出不同于先知(即原作者)所说的话。译者和作者都同样受着上帝的感召。因此,“如果有些话在希伯来文本中有而在希腊文本中没有,那么,这就是因为圣灵有意只让先知们(即原作者)而不让译者说这些话。反之,当希腊文本中出现希伯来文本中所不曾有的东西时,则是因为上帝选择那72名译者,而不选择原作者说的那些东西,以此表示他们同样是先知。”
毫无疑问,奥古斯丁极力提倡《圣经》的译者受到“上帝的感召”之说,是为其政治和宗教目的服务的。首先,通过肯定亚历山大的72名译员在彼此隔离的情况下,确实“发出了同一个声音”,“得出了同样译词、同样词序的译文”,使人们相信上帝的存在和力量。其次,用“上帝的感召”渲染上帝的神秘和《圣经》的玄义。奥古斯丁比斐洛更强调这种观点,即只有那些受了“上帝的感召”的人才能翻译《圣经》。这样,他便把《圣经》的讲解权置于少数几个神甫的手中,使包括一般基督徒的普通人都成为教会操纵的对象。至于译者得到的“上帝的感召”到底是什么,奥古斯丁从未也不可能说明白。无论从古代哲罗姆的翻译观点或从现代科学和现代翻译理论来看,所谓“上帝的感召”都是不存在的。翻译的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译者的语言水平和对所译题材的知识的掌握。由于人们的语言水平和所掌握的知识程度必然有差异,所谓“出自72人之手的36篇译文连词序都相同”的传说,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本族语可通过译借外来词加以丰富。贺拉斯认为,在安排词句时,要考究,要小心;如果安排得巧妙,家喻户晓的词便可取得新义,表述就能尽善尽美。而如果要表达的东西很深奥,必须用新词才能表达,那么,可以有节制地创造新词,特别是通过翻译借用希腊词,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写作、翻译时的需要,而且还可以丰富祖国的语言。
词语不应一概按它们原来具有的一般意思,而应当按它们在使用中被实际采纳的意思来翻译。我们也同意,由于使用习惯而具备了基督教意义的词不应再还原成不含宗教意义的词。”
把《圣经》译成英语,富尔克不主张过多地借用外来词,而主张挖掘英语本身的表达潜力,注重采用合乎英语习惯的表达法。他举例说,表示“偶像”、“崇拜偶像”之类的意思时,用an image、a worshipper of images、worshipping of images 比用 idol、idolater、idolatry更恰当,因为尽管image和idol两词都是外来词,但前者源于拉丁语,在英语中扎根较早,已符合英语习惯;后者源于希腊语,在英语中出现较晚,英语味道不浓,不易为普通英国人所理解。他还指出,如果译者“不用 elders而用 ancients,不用 wise men而用sages,那就好比你在说法语,而不是像我们一样在说英语,正如翻译confide这个词,你按法语习惯译成have a good heart,按英语习惯则会译成be of good comfort”(Amos,1920/1973:73)。而“倘若你使用evangelized这个词,那你就不是在翻译,而是在杜撰不为一般英国读者所理解的新词”(Amos,1920/1973:74)。富尔克承认,与更古的语言相比,英语的词汇量不大,低他认为这一点不能通过生造词语来弥补,而只能依靠英语的旧字新用。
过于灵活,而跳出了翻译的圈子。不能把他们作品中各自的风格特色、地方特色和历史特色一笔勾销,而应准确地传达过来。文学翻译不可过分自由,专业性翻译不可过分拘谨。译者的责任是做到与原作有几分相似。此外,就是使译作具有独创的艺术价值,译文本身即可成为独立的艺术品。
[1]詹妮弗·柯茨.女士交谈:构建女性友谊的话语[M].吴松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周海英.专制皇权下的爱情是一袭爬满虱子的旗袍——电视剧《甄嬛传》之剧评[J].文学界,2012,(5).
[3]秦晓帆.网络时代的诗性历史建构—流潋紫与 后宫·甄嬛传[J].名作欣赏,2012,(6).
[4]《怦然心动》剧本台词百度文库[EB/OL].http://wenku.baidu.com/view/96bb0bee4afe04a1b071deff?fr=hittag&album=doc&tag_typ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