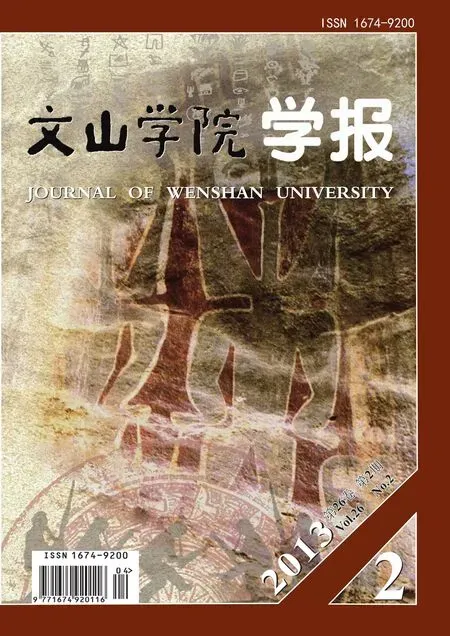网络传媒对公共权力的制约监督
梁耀东
(长沙学院 法学与公共管理系,湖南 长沙 410003)
2011年我国网民的搜索引擎使用率为79.4%,微博用户环比增幅296%,用户交互式信息配置方式已经取代了传统信息配置方式[1]。随着传统的线性传播方式转变为“裂变式传播”,网络传媒悄然成为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的强大舆论力量,如同悬在公权力掌握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网络集群行为和群体极化现象发展的同时,网络舆论和网络舆论情绪都对现实社会和政府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
一、网络传媒缘何对公共权力形成强大影响力
(一)科层制政府监管网络传媒的成本较高
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它背后的经济因素。媒体注重的是爆炸性新闻的效益,所以网络媒体总试图绕过监管发布轰动的消息而获取更多的点击率。网络曝光后传统新闻媒体的跟风也有类似的动因:既然当初不是自己爆料,就无需负担发布者的责任,它们便争先恐后地报道以争取收视率。各种媒介竞相互动的“第二媒介时代”网络传媒在传播意义上超越了国家的控制[4](P10)。
传统媒体擅长议程设置,它们告诉人们应该对哪些公共事务进行思考,从而组织和安排人们脑中的“拟态环境”[5](P16)。不同于电视和纸面媒体,在网络中进行议程设置的效果更难预计,网络传媒中不仅新闻发布较少受控,而且信息受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性接触”与他们态度相一致的信息[6](P209-234)。管理部门要跟踪调查网络议程设置所取得的效果则更难,工作量也十分巨大,就更难说全面掌控网络传媒的议程了。
(二)传统媒体未担负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
威尔逊曾言:“公共舆论对于精英的冒险行为可以起到一个刹车的作用,使政策制定者由于害怕失去大众支持而不去走极端。”[7](P184)公共舆论包含着对民生的关注、公众对社会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公共权力的道德评价。传统媒体的舆论对于公共权力的制约监督作用已毋庸置疑,西方亦称之为第四种权力。比如,在第一修正案的庇护下,美国记者对权力、暴力和腐败的监督:佛罗斯特之于尼克松、穆罗之于麦卡锡、西摩赫什之于越战和伊战、斯蒂芬斯之于美国城市腐败等都是经典的例子。从反战到反迫害,从善款去向到国宴菜谱,从食品安全到公务员工资[8],传统媒体几乎无孔不入,相应的监督也接踵而来。且不说C-span对国会唇枪舌战的全面直播和报刊杂志上对政府“吹毛求疵”的漫画和时评,就连晚饭后的黄金时段都充斥着各类政治脱口秀。
有学者认为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轰轰烈烈的“揭黑运动”源于新闻界的理念、制度和传统[9],也有学者认为媒体揭丑的动力是基于“法—政治”逻辑的政治理念、信仰与法律文化[10]。而这两种动力机制对中国传统媒体的推动都较为有限,所以当西方传统媒体像一个不惧艰险的巨人完全承担起了沉重社会责任时,我国的传统媒体却把“烫手的山芋”都扔给了网络,导致新闻不能由传统媒体及时报道出去。“等到网上炒到沸沸扬扬且偏离事实真相时,才容许传统媒体介入报道试图后发制人,而此时局面已显得十分被动了。”[11]
其实,我国舆论监督很早就有发展,20世纪50年代就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当时的纸面媒体就担负起了舆论监督的职责。尽管后来在反“右”和文革期间传统媒体的监督先后经历了收紧和畸变[11],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其发展一直在缓慢且谨慎地恢复当中。在社交网络崛起的时代,这种缓慢的恢复已被新媒体的发展所超越。传统媒体对某些潜在“敏感”事件的集体失声,令社会的压力无处释放。由于缺乏正规、可控的减压渠道,网民们不断地用网络语言对公共权力进行戏仿和暗讽。
许多由社会本身固有的问题都被诉诸网络传媒,如贫富差距的拉大、食品卫生监管、劳资矛盾、拆迁矛盾等。这些问题到了网上就都被认为是网络传媒带来的问题,其实社会问题才是其背后的原因。然而传统媒体却不能宣泄这种压力,当社会矛盾造成的压力无处宣泄时,民众便不约而同地选择网络传媒作为唯一的减压阀,因而中国的网络传媒独自承担了过重的社会责任。
(三)公众表达意识的增强
在传统的传播模式中,社会公众被置于金字塔结构的底层,对于公众而言公共权力遥不可及,故公众的心理权力距离较大。与其说公众缺乏制约监督公共权力的能力,不如说公众更缺乏制约监督公共权力的信心。
对于一些大型的住宅楼的建设更是由于暖通空调设备等所需要的材料的复杂性,就更需要管理人员注意这个问题了。暖通材料的质量是直接影响暖通设备的。购买的暖通材料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标准,在安装之前必须要仔细的检查和严格的规范。其中各种阀门和镀锌钢板等辅料的质量情况更是需要注意的。因为这几种在暖通管道的工程建设中直接影响着其质量。此外,还要加强对保温材料进场的检查,对施工前技术交底和施工中的检查要严格监控,总而保证暖通空调设备材料质量。
“网络传媒可以让公众更多地了解世界,同时它也使得公众能够发表自己的观点,聆听、讨论和及时获取决策信息,所以它也是自古希腊雅典的市民辩论会场以来最为卓越的一项发明。”[12](P46-47)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被扁平的、网络式的网络传媒所取代,原先被置于传播金字塔底层的公众能够与金字塔顶端的公共权力拥有者共同获取新闻信息,也可以自由发表评论。
网络打破了社会的僵局,打破了身份、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藩篱,社会大众能够跨越不同的阶层,直接以一个普通人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衡量公共人物及其行为(当然前提是没有诽谤或诬陷)。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科层制的形式仍然存在,但是虚拟的网络环境大幅缩短了民众心理上的社会权力距离。现实中公共权力的不均衡配置在网络中不被接受,民众开始通过网络传媒来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
二、网络传媒制约监督公共权力的模式
从制约与监督的维度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网络传媒制约监督公共权力的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包含了制约和监督的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制衡模式,另一种则是对公共权力进行网络舆论监督的模式。我们观察到网络传媒的制约监督能够引起政府公信力的变化,其过程是在现实行政领域和网络公共领域这两个场域中完成的。见图1。
(一)良性互动制衡模式
现实中行政权力的配置并不均衡,行政权力由行政部门及其官员享有。虽然在政治上有代表制度,但是民众对于行政过程中的决策和执行缺乏制衡的手段。虚拟的网络社会是现实公共生活在网络中的映射,网络公共领域为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提供了新的场域。由于现实中有些政策不够科学,以及有时在行政执行过程中忽视了民众的利益,此时民众便会通过网络向社会和政府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倘使民众的这种表达得到了政府的回应和意见征询,那么就能够进入一个政府和社会良性互动的模式。
这种互动的起点是民众知情权在网络中的部分实现,即民众通过网络知悉了政策的内容,并通过网络共享了对政策可能导致结果的分析。当其切身利益被权力所忽视时,民众更愿意通过网络传媒来发声。当地方政府或行政部门愿意倾听这种网络民意,并就公共利益进行探讨时,我们就可以说进入了参与式传播过程。这种把公共利益要求转变成重大政策选择的功能,称作利益综合,是各类公共利益得到社会资源的政策选择过程[13](P233)。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充分互动,这是一种典型的网络媒体对公共权力的制约。经过参与和协商,地方政府知道了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对提案进行修改,进而又改变了自身的行为方式。由于考虑和平衡了各方面的因素,政策制定更加科学和行政执行更有效率。这样,即使政策和执行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民众也能因曾经参与权力运作,而理解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难处。网民对公共权力运行做出正面积极的评价,最终政府公信力也能在这种互动中逐步增长。
(二)网络舆论监督模式
在伦理事件和贪腐案件(与事件相比,案件已从伦理范畴进入了法律范畴)成为公共话题的时候,政府对网络传媒的回应性就变得十分关键,甚至不同的回应速度都会使事态朝不同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政府通过网络知晓了案件基本情况以后,及时回应并妥善处理,处理结果令网民基本满意,那么政府公信力也基本不会有损失。另一种可能,政府没有及时回应网络舆论所关注的问题,紧接着事件背后深层的社会阶层冲突让该事件或案件在传播过程中被符号化,从而引起更大规模的舆论情绪爆发。这个时候政府才回应,或者回应不得体,甚至继续坐视不理,都将导致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公信力对于地方政府或行政部门维持其公共形象至关重要,良好的公共形象能增加群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感,也能在行政执行过程中有效地减少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然而当政府公信力已经走低时,无论政府说什么、做什么都将不被公众理解。如果地方政府或行政部门不在网络传媒中接受制衡,那么政府公信力就会一次次被蚕食,这恐怕会让整个政府落入“塔西佗陷阱”。
三、规范与促进网络传媒制约监督公权力的途径
公共行政学家、传播学家拉斯韦尔指出大众传播的主要功能是传输、联系和监督[14](P37)。如拉氏所言,由于大众传播往往引发对公共话题的讨论,从而引发对公共权力的质疑,所以网络舆论的矛头频频指向公共权力。虽然作为低成本的舆情监测手段和权力监督工具,它的潜力巨大。但是倘若网络缺乏规范,则必然会有负面效应产生,制约和监督都无从谈起。如何扬长避短,更加规范地利用网络传媒监督和制约权利,都有待于从多方面推进。
(一)构筑网络传媒监督的法制秩序
法律是规范人类行为的工具,人们在网络传媒中的行为也需要规范,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这股强大的力量就会被人利用。“人肉搜索”和“网络游街示众”无疑严重侵犯了个人权利,而有些网络事件中,在网民们“蒙面狂欢”的背后甚至有“网络推手”影响网络舆情的发展[15]。如果没有法律来规范网络力量,它所侵犯的可能不仅仅是公民个人的私权利,甚至有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图1 网络传媒制约监督公共权力的模式示意图
要规范网络传媒,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法律。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俄罗斯)均有《传媒法》或《新闻法》。而我国至今没有《新闻法》,也没有《网络法》和《诽谤法》。虽然我国有人大监督法,但并没有针对网络监督的有关内容。这不仅导致了传统媒体无法可依,而且网络传媒亦不能依法来制约和监督。现今的网络相关法规仅有对域名注册的规定、网上银行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知识产权法中关于侵犯著作权的若干条款及其司法解释。前二者只是一些行政管理的技术,而知识产权法的司法解释并不是针对网络传媒的特性制定的法律,这些零散的条款或规定无法满足现下的法治需求,规定网络传媒有关各方权利与义务的法律亟待建立。
在法理层面,要明确舆论与司法的界限。舆论以普遍社会道德为标准,“舆论法则判别的是美德和恶行;而美德又完全是根据公众的评价来衡量的”[16](P109)。虽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但一曰道德,一曰法律,二者泾渭分明,绝对不能将道德作为审判的依据。网络传媒和司法部门由于视角的不同,网络传媒的视角是民生,以道德为原则,以舆论为武器;司法系统的视角是法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当然另一方面,行政权力也不能介入司法审判。如果舆论监督走的还是“舆论关注——领导批示——司法执行”的老路,那么影响司法公正的是这种错位的权力分配。只有使网络传媒与法律和司法体系有效衔接才能真正规范网络中的行为,使网络传媒制约监督的力量用在正途。
(二)防止舆论情绪影响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权威的重要来源,良好的政府公信力能增强政府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降低政策执行成本[17]。网络时代的政府公信力既可以通过网络传媒获得增长,也可能因为对网络监督的不妥应对而降低。在网络舆论监督模式中,经过行政伦理事件或者贪污腐败案件的符号化,让网络舆论转化为更难处理的舆论情绪,进而使政府挽回公信力的努力失去效果。
社会阶层冲突意识在网络传媒中的符号化是产生舆论情绪的核心步骤。比如2009年分别由当时的三个事件而引出的“富二代”“官二代”“农二代”这三个词汇在网络上迅速窜红,次年两会期间,这些符号就“转正”为两会代表们的用语。符号化的背后是社会阶层冲突,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是一种深藏在社会结构内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只不过是它的不同表现形式”[18](P25)。不论中国的社会阶层被分为十层(陆学艺,2002),还是“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社会断裂(孙立平,2006),总之今天财富与权力在阶层之间的流动似乎难以寻觅,所以仇富和仇官心态在网络公共场域中的表达日益强烈。
网络中所折射的社会现象经过一次次的交互传播与要素提炼,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就逐渐地被符号化了。鲍德里亚阐明了从物到符号之间的发展分别经历了符号对物的反应、歪曲、掩盖和摆脱现实的过程。这些符号化了的“拟像”充斥着媒介,符号不再是指代,而是创造了我们所处的现实[19](P170)。“符号可以脱离于现实的根基而存在于对自身的演绎中,这使得社会的熵①在不断增加,拟像在电子媒介中的仿真成为现实”[20](P78),以至于我们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直接对这些符号产生了条件反射——这样的符号化是危险的,仇官和仇富心理可能会引起网民们对事件真相细节的选择性忽略。更不容忽视的是,仇视的思维方式并不会引领人们冷静地总结事件背后的教训,以及审慎、长久地进行反思。
我国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回应可以被分为“无回应”“被动回应”和“主动回应”三种类型[21]。在网上民众对政府和官员违背行政伦理的事件予以谴责,如果得到政府的及时回应和妥善处理,政府的公信力得以维持,但却难以实现增长。这是因为舆论是以高于常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官员,当他们的行为越过常人的伦理标准时就很难被民众所原谅。虽然民众在网络传媒中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在腐败案件的查处、甚至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方面都取得了许多标志性的成功,但是这一切如果没有政府的回应与配合,单靠民众是无能为力的。
在网络舆论监督模式中,当政府及时回应并妥善处理网络舆论关注的行政问题,可以勉强维持其公信力。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探索另一种模式。在良性互动模式中,政府的回应性被参与式传播所取代。参与式传播能促成地方政府、行政部门与社会的互动,在舆论情绪形成之前,甚至舆论事件发生之前发现和解决问题。
(三)通过参与式传播完善公共利益表达机制
从学术概念而言,参与式传播是在政府回应性的提法上更进了一步。俞可平教授认为,“公民参与又称公共参与、公众参与,就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民生活的一切活动”[22](P1)。公众参与是要实现民众参与、表达和影响公共政策的权利,而网络传媒的兴起就是民众实现这些权利的一个契机。新闻宣传工作应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3](P5)。可喜的是,在民众参与式传播的初步实践中,一部分政府官员在微博中放下官架,以贴近生活的语言与网民交流,听取意见与倾诉。其中最早一批建微博的官员现在已成网络红人,为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做出了贡献。
参与式传播的基础是公共理性与合理的治理结构。在网络传媒中,引起多媒体共鸣原因被解读为网络传播中中性的意见或者互相抵消的网络舆论占大多数,而有消极影响或起负面作用的网络舆论比例则较小[24]。故而网络传媒有可能成为理性的载体,且已有一些政治哲学与公共行政学同仁开始着手研究如何培育网络中的理性决策。参与式传播“在公共治理结构上,重要的是将所有利害关系的公民都包括在内,形成公共问题共同治理的共同体”[25]。在治理结构上,形成党委、政府、利益相关的民众、监督机构良性互动的结构。“正如参与不是分散政府权力而是分担政府责任一样,网络参与提升了政府治理的质量,而非分割政府的权力。”[26]因为“由政府管理者和公民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共同思考社会和民族的未来蓝图,远远比某一单方面的努力要重要得多”[26]。
参与式传播的前提条件是民众通过网络传媒行使知情权。如果公共权力自始至终都在黑箱中运作,那么坊间便会流传各种猜测,这样难免让民众对政府产生陌生感和不信任感。鉴于此,政府最科学的做法就是公开民众知情权的客体。在知悉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的决策信息之后,民众能有效地参与其中。参与式传播不应只是救济式的纠纷解决机制,还可以是积极参与政府决策的民主形式。“网络传播则创造了一种社会各个群体为了争取自身的利益相互斗争的传播文化,并且出现了不受地点限制的新型公众。这种变化凸显了源自古希腊参与式民主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参与式民主是文明礼仪和权力共享等(古希腊的)传统价值观相伴相生的。”[27](P337)其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只要政府主动吸纳网络传媒中的民意,再弱小的声音(只要是科学、理性、符合公共利益的)也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
然而网络的公民参与也应该有其界限。对于马歇尔·麦克卢汉来说,媒介是人类思维的延伸,其形式会逐渐驱逐其内容[28](P19)。让·鲍德里亚深受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论断的影响,认为传媒形式掏空了内容,媒介形式统治了社会。[20](P78)而与麦克卢汉不同的是鲍德里亚对媒介的日渐强大产生了戒心。尽管曼纽尔·卡斯特是网络社会的推崇者,但实际上卡斯特的多部著作中都透露出,他对网络在民主政治领域中的发展保持着警惕。他主张治理新媒体的原则包括“对政治保持必要的疏远”[29](P371),并且指出网络直接民主有明显的局限性,网络中大量低质量、极端的讨论难以与现实中高效的精英决策相兼容[30](P403)。所以网络中的参与式传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非组织性的利益表达机制,民众在网络传媒中的利益表达要成为有效的政策输入则有赖于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的关注和吸纳,进而形成“利益表达——利益整合——行为结果”的良性互动。
网络传媒不仅能督促公权力掌握者审慎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更可以是一座政府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如果公共权力在决策之初和运行过程中都接受民众通过网络传媒的制约监督(制衡),主动吸纳民众的利益诉求,那么参与式传播将不断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良性互动)。在网络公共领域中实现开放式决策和对执行的监督,民众就能更多地理解并配合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从而有效减少行政过程中的摩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平衡性,以及决策执行的效率。
注释:
① 鲍德里亚借用了克劳修斯的物理学概念,“熵”用以形容社会与自然界一样随着时间而增长的无序状态。
[1] CNNIC.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1年度报告[EB/OL]. http://www.cnnic.net.cn/gywm/ndbg/201204/P020120507358937384891.pdf.
[2] 潘祥辉.去科层化: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的功能再考察[J].浙江社会科学,2011(1):36-43.
[3] Pool, I. de sola (1983) Technologies of Freedom[M].Harvard, MA: Belknap Press.
[4] Holmes. Communication theory: media, technology and societ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2005.
[5] 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M]. New York:Macmillan, 1922.
[6] Sears, David O., and Jonathan I. Freedman, “Selective Exposure to Information: A Critical Review.” In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edited by William Schramm and D. F. Robert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1.
[7] Herbert G. Nicholas, “Building on the Wilsonian Heritage”,in Arthur Link, ed. ,Woodrow Wilson (New York: Hill&Wang, 1968).
[8] 历年“普利策奖”获奖名单[DB/OL].http://www.pulitzer.org/.
[9] 吴廷俊.理念·制度·传统——论美国“揭黑运动”的历史经验[J].新闻大学,2010(4):42-47.
[10] 陈堂发.亦析美国新闻界“揭黑运动”[J].新闻大学,2011(7):33-36.
[11] 范似锦,杨凡.舆论监督与社会政治生态环境[J].现代传播,2010(12):30-35.
[12] Jones, A.H.M. 1960.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3]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14] Harold Laswell.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1965.
[15] 王子文,马静.网络舆情中的“网络推手”问题研究[J].政治学研究,2011(2):52-56.
[16]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P109. 引自洛克. 人类理解论的“后来版本”,原注为: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II, §11;参阅Koselleck, 同上 , S.41ff
[17] 高卫星.试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流失与重塑[J].中国行政管理,2005(7):62-65.
[18] 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变化[A].李培林,李强,孙立平.中国社会分层[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9] Jean Baudrilla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M]. Selected Writing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 张天勇.社会符号化——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鲍德里亚后期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1] 刘力锐.我国网络民意的成长政治意蕴及政府回应[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9(5):22-26.
[22] 贾西津.中国公民参与——案例与模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3] 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08年6月20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4] 钟瑛,余秀才.1998—2009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4):45-52.
[25] 黄显中,何音. 公共治理的基本结构[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2):41-50.
[26] 顾丽梅.网络参与与政府治理创新之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10(7):11-14.
[27] 斯蒂芬·李特约翰,凯伦·福斯著. 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28] McLuhan & Fiore.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M].New-York: Bantham, 1967.
[29] (美)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0]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M].周凯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