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宿
□王保忠


潘洗,本名姜鸿琦,满族,工程硕士,1969年生于辽宁岫岩。曾在国企从事过共青团、会计、宣传等工作,现供职于辽宁鞍山供电公司。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发表小说多篇,著有小说集《香味橡皮》。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小说北2830”召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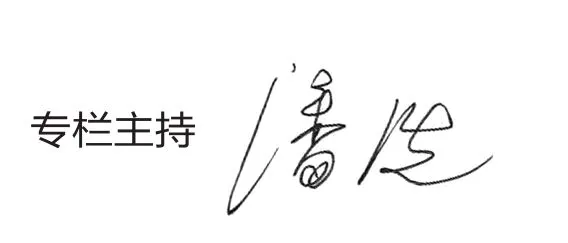
居然来了个女人,且说晚上要借宿。
是邻居家的亲戚,从镇子东边很远的一个村庄来的,二十五六岁的小媳妇。邻居是个热心人,在镇上人缘极好,好得简直没得说。他们刚来这里时,院子里要搭个小房子,放些柴呀炭呀的,邻居就过来帮忙,把家里能用的木料都扛来了。还帮着找木匠,帮着找泥瓦匠,帮着和泥,帮着搭顶子,就好像是给自己家干活。这样的人,镇上能找出几个?所以,他家的亲戚来借宿,他根本就没法拒绝,也没想过去拒绝。不就是来住一宿吗?就是住上一年半载的,又有什么呢?
他来这里也有些年头了,口音磨练得跟镇上人几乎不差多少了,不细听,简直以为他就是这小镇长大的。来了有多少年了?他有些记不起来了。来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镇里的人都说他长得英气,浓眉大眼,膀阔腰圆,像是当过兵扛过枪杆的。他也没去跟他们理论,有些事不能太认真,太计较,越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说,越会把事情搞个一塌糊涂。没错,他是长得帅气,个子又高,挺拔得像镇子周围的白杨树呢。要不是他带来一个女人,在镇上找个对象应该是没问题的。这镇子水土好,姑娘们长得水灵着呢,牙齿是雪白的,皮肤是白里透红的,腰肢是充满弹性的,怎么都看不够。邻居曾经开他的玩笑,说老艾,你怎么不在我们这里讨个老婆?你看你的女人,又粗又壮的,真像个男的呢。他听了脸色倏地暗了,老半天没泛上话来。邻居也看出了什么,解释说,我不是有意的啊老艾,是跟你开玩笑啊,你的女人好着呢,一点都不比我们镇上的婆娘差。女人嘛,会烧饭能料理家务就行,就是长得跟画儿似的又有什么用?又贴不到墙上。他笑了笑,说没什么,这真的没什么。
他知道自己的女人身段模样很不争气,可再怎样,他也不想从别人嘴里听到这样的话。镇上的人背着他也嘀咕,说他的女人粗声大嗓的,没胸脯没奶子没屁股。说得也太下流了,怎么只看到这一点呢?她的能干他们怎么看不到?他在镇上的一个厂子做工,她几乎把家里的活儿都包下了。还喂了头猪,他不在时,她就趴在猪圈墙上看,看着那头猪吃食,看着它睡觉。就连邻居也不得不承认她的能干,说你的女人真的很行啊,里里外外一把手。我的女人就不行了,病恹恹的,什么都干不了。他不知该说什么,他心里其实很喜欢邻居的女人,当然他不能说。他知道有些事只能深深地藏在心里,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就不好了,只有那些疯子才口无遮拦呢。像镇上的刘三婆,一个疯疯癫癫的寡妇,想男人都想疯了,逢人便说俺男人夜里亲俺了,叭一下,又叭一下,亲得俺湿湿的。这叫什么呢?这就叫疯子!邻居的女人没出嫁时,模样在镇上那可是数一数二的,还有个关于她的传奇。说小偷进了她家,本来想偷一些东西,结果呢,没翻出什么值钱东西,倒是在柜子里找出了她的几张照片,就把照片带走了,反而落下了东西。邻居的女人生了孩子还是很好看,他常常偷偷地看她,有次竟然看得磁在那里了,没注意到对方的目光迎上来。女人噗哧一声笑了,他知道她笑什么,脸一下涨红了。
晚上要来他家借宿的便是邻居的小姨子。
邻居的住房确实很紧张。两间正房,一间放杂物,一间住人,小姨子来了当然不能和他两口子住。这不,邻居就找上门来了,说话很客气,慢言细语的,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却还是很客气。邻居是这么说的,老艾,有个事,想和你商量一下。他是姓艾,叫艾国家,这名字镇上的人都知道。镇上的人说,这名字好记,叫起来也上口。艾国家,艾国家,多好的名字。他问,什么事啊,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邻居说,是这么个事,我小姨子来了,你也知道我那屋子憋屈,住不下的。他就明白过来了,说,那就来我这里吧,不就住一个晚上吗?好说好说,这还用商量?你让她来吧,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邻居对他的爽快显然很满意,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才离开了。
邻居走后,他笑着对五枝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人,拐弯抹角说了半天,不就借个宿吗?客套什么呢。
五枝点了点头。
五枝是他的女人,大名叫赵五枝。
他说,让邻居的小姨子和你睡,我到西屋去。
五枝点了点头,说那好,跟她睡就跟她睡。这时候,他们还谁都没意识到什么,都以为她只是来借宿,这有什么呢?五枝开始忙乎了,她打开那个大柜子,因为好久没翻腾了,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五枝皱了皱眉头,探下身,取出一床棉被,这还是他们刚来镇上定居时买下的,也是准备有客人来用的。她把被子抱出来,晾到了天井里挂着的一节铁丝绳上。是那种印花被子,上面绣着几只孔雀,翅膀张得很开,虽是多年没晾出来,色泽还是那么艳丽,新鲜,似乎是刚刚染过的。
这时候是下午,五枝站在天井里,半边脸笼在阴影里,半边脸朝着太阳,嘴角挂着的笑很明亮。她盯着那张被子,伸手摸了摸,知道那潮湿的棉絮会慢慢慢慢吸进阳光,然后鼓胀起来,充实起来。到夜里,它将暖暖地盖在那个陌生女人身上,感受到她和艾国家的热情。她不知道那个女人什么样子,如果像邻居的女人一样,就该是个好看的女人了。这么想着,她觉得心忽然跳了一下,脸也不自觉地红了。艾国家好像也很兴奋,话是特别的多,有点像刚刚下了蛋的母鸡。她忽然记起了什么,跑到了鸡窝那边,却没有看到窝蛋的鸡。她在院子里转了半天,将一只鸡逼进墙角,一把抱起,伸出一只手指在屁股门上摸,觉得没有下蛋的可能,又把它放开了。做这一切,她显得很熟练,这么多年了,她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可是她不知道为什么要找鸡蛋,那个女人又不来吃饭,只是来借宿,你这是急什么?想是这么想,心里却还是很急,不知做什么才好。
这他都看出来了,毕竟这么多年,家里没留过人。他们还没有孩子,家里要有个孩子多好啊,活蹦乱跳的,哭也好,笑也好,这家就多了几分生气。可是啊,他们没有孩子,这镇子,这街巷里的石头都知道他们没有孩子。他当然想有啊,看到邻居家的孩子,他和五枝都抢着抱,想给孩子买点东西,想领着玩一玩,还想把那孩子接过来住一宿。可邻居的女人没让,说这孩子太淘气了,你家多干净呀,还是别去了。他和五枝都有点失望,摇摇头,再摇摇头。
天还没黑,他们就早早吃了饭,收拾完了,立在院子里等着邻居的小姨子进门。
怎么还不来呢。他说。
可能还没吃饭吧。五枝笑了笑。
一顿饭能吃多久?
小姨子来了,他们能不好好做一顿饭,能不改善一下伙食?
天色在他们的等待中渐渐黑了下来。
五枝终于出了声,要不我去看看?
你急什么急?过会儿人家自然会来的。他摇了摇头。
说是这么说,他早坐不住了,好像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好像那个女人不来,他们就会很没面子,在这镇子就待不下去了。但好像又与面子无关,是身体,是内心里的事,心里有几分渴盼,几分激动,身体也惦着。手不知做什么,眼不知看什么,脸也不知该是个怎样的表情。只是天黑了,院子里也没灯,他们看不到对方的表情,要不然会很尴尬的。
他们等啊等,一直听不到门响。
五枝有些等不及了。
五枝说,我还是过去看看吧。他摇摇头,看什么看,这不等于说我们太小气了吗?五枝说,去看看也显得热情啊。他又摇了摇头,忽然说,要不这样,你给我搭个梯子,我爬墙头上听听?五枝说,你那么重,我怎么驾得起。他笑了笑,心说我是你男人,你不听我的听谁的?但他也没去认真,结婚这么多年了,他也真的宠着她了。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想做什么完全可以不做。这么多年来,他真的很宠着她啊。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做活,镇上的人都觉得他们很恩爱。他是该好好对待她的,谁让他是丈夫呢。镇长还把他们树为“好夫妻”,让镇上的家庭镇上的夫妇都学习学习。还热热闹闹开了个会,给他们戴了大红花,散了会他盯着五枝看了半天,忽然笑起来,五枝也笑,两个人都笑出了泪。他说,我们是模范,是模范啊。五枝说,镇长说我们是模范,就是模范。
后来他从西墙角的鸡窝顶爬上了墙头,他看到邻居家的灯亮着,邻居一家在里面说着话,也许是谁说了一句笑话,几个人都在笑。邻居笑了,邻居的女人笑了,有一个女人不认识,准是邻居的小姨子吧,也用手掩着嘴笑了。望着灯光下的几个人,他脸上也泛起了笑,眼里甚至有了泪水。他扭过头去看五枝,发现五枝不知什么时候也上来了,就立在他身边,眼睛也湿湿的。他忽然伸出手来,抓了一下五枝的手,五枝怔了一怔,也抓了一下他的手。他忽然想抱一抱五枝,然而没有,只是在心里抱了一下。他们就那样看着邻居一家人乐呵呵的样子,像是看着一幅画。
后来,他们看到邻居一家人出来了。他们匆匆地从鸡窝顶上下来了。他们都回了屋子,没事人似的忙乎着,然而却不知做什么,找不到可做的。这时候邻居进来了,然后是邻居的女人,再然后是邻居的小姨子。
他没去看那个陌生的女人,显得很平淡地对邻居说,吃过了?
邻居笑笑,吃过了吃过了。
邻居的女人说,你们也吃过了吧?
他说,吃过了。
五枝也说,吃过了。
邻居的女人笑笑,拉过那个女人,说,这就是我妹子。
他这才去看那个女人,只看了一眼,目光就移去了。这个女人跟她的姐姐长得简直一模一样,却更年轻更有活力,似乎是身上的每一处都长了钩子,一不小心就会把你的魂儿勾去。他由不得想起了跟他一条街的树叶,树叶和他青梅竹马,一块玩大的。树叶生得好看,好像比邻居的小姨子还好看,树叶好看在哪里呢?他说不出,好看的女人哪里都好看,眉是眉,眼是眼,胳膊是胳膊腿是腿,没有一处看着不让人舒服的。如果不是后来遇上了五枝,他和树叶早结婚了,早有了孩子。来到这个小镇,他想过好多次,他和树叶要是有了孩子,那孩子会是什么模样呢?可是,他想了好久也想不清楚。
这时候五枝说话了,哎哟,大妹子生得好看啊。
邻居的小姨子脸红了一下,这就让她显得更好看,更妩媚。他忍不住又偷偷看了她一眼,却像做了贼似的又倏地把目光移去了。
他们说了一会儿话,邻居两口子就走了。
他知道自己该回避了,该让五枝安顿她睡觉了。可他却觉得自己一双腿有点发软,挪不开的样子。他忽然有点嫉恨五枝了,凭什么你要和邻居的小姨子睡一起?然而这想法他是万万不敢暴露出来的。还是让五枝安顿这个女人吧,她是他的女人,一切原本该由她安顿的。然而,虽是这么想,他心里却怅怅的,好像失去了什么。然而他不能不离开了。他对邻居的小姨子笑了笑,又对五枝说了句什么,这就出了门。等他出了门,五枝就把门关上了,砰地一声,很响很响的。他知道五枝把门关得这么响是做给邻居的小姨子看的。然而,明明知道是这样,他还是很生气,心里堵得慌呢。
这个臭娘儿们,就不怕把门摔坏吗?他心里骂了一句。
他进了西屋,也没拉灯,在黑暗里久久地立着,像一只可怜的灯竖子。他摸出一支烟点了,狠狠地吸,吸了几口,觉得嗓子有点痒,想咳,又怕惊动了东屋的人,就憋住没咳。吸完一支,他又摸出了一支,点着了,却又把那点火星掐灭了。他不知该做些什么了,像笼子里的困兽,在黑暗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他不知五枝这会儿在做什么,她们睡下没有?睡下了,她们又该是个什么样子,五枝会挨着邻居的小姨子吗?他不敢往下想了,心里骂了自己一句,你这都胡想些什么呀,两个女人睡觉,你操的什么心?可是他对五枝又很不放心,担心她会做出些什么来。五枝会做出些什么来呢?
他觉得该提醒五枝一下了。
他靠近西屋的门边,清了清嗓子,对屋里说,五枝,你过来一下。
过了很久,五枝才磨磨蹭蹭出来了,像是怕他看到屋里的人,出来时顺便把门也带上了。看那样屋子里熄了灯,没有光亮跟出来。
五枝打了个哈欠,懒懒地问,喊我有事?
他心里一下来了火,却又不好发作出来,心说还装呢,睡得着吗你?他抓了五枝的手,把她拉到西屋,然后把门也关了。他开了灯,盯着五枝看,像看着一个陌生人。见五枝还穿着外衣,他脸上的凝重这才略略松弛了,缓和了。可他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五枝的衣扣松开了两颗,这使她的神情看起来有些暧昧。他心里的火又腾地升起来了,可是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伸出手来,帮她把扣子又扣好了。他认为这是对五枝最好的警告。
五枝懒懒地说,都要睡觉了,你这是干吗?
他忍不住骂了一句,你是我的女人,不能乱想,懂吗?
你这么凶,我想什么了?五枝说。
他一咧嘴,说,想什么你心里知道,这么吧,你和我在这屋睡。
你让她怎么看?说好了我和她做伴的。五枝眼睛睁得多大。
我知道你守不住了。
我怎么守不住了,你说呀,守不住什么了?五枝显得很委屈。
好像是自从邻居说了那个女人要住进来,五枝就显得不那么温顺了,不是昨天那个五枝了。他觉得五枝的嗓门大了,做事也不怎么扭捏了,这怎么能行呢。他有点后悔让邻居的小姨子来借宿了。从她迈进这个门的那刻起,这个家好像就乱了套,五枝不像个婆娘,他也不像个丈夫了。
你别忘了你是谁。他说。
我是谁?我不是你的女人吗?五枝的嗓门拔高了。
他不能不软下来,你小点声,你怕她听不到吗?
五枝不依不饶地说,是你凶嘛。
去吧去吧。他堵住了她的嘴。
五枝瞪了他一眼,倔倔地去了。五枝进了东屋,又把门关上了,好像还把插棍闩上了,很响的一声。他觉得那一响好像拍在了他心上,拍得很疼,他身体忍不住晃了晃,站不大稳的样子。五枝是进去了,他却不愿回去,但样子总得做做,他咳了一声,脚步很响地回了西屋。他当然晓得这是虚张声势,掩人耳目,一会儿他还会出来的。可是,他又不愿真的出来。他为什么要出来呢?一个人就不能睡吗?一个人就睡不着吗?
他立在黑暗里,他们的生活却过电影似的在他眼前亮了起来,像是一簇簇火苗,灼疼了他的记忆。他真有点恨自己了,为什么要遇到五枝呢,为什么要和五枝一起来到这个小镇?他不是早有对象了吗,树叶,那个叫树叶的姑娘。可是他偏偏遇上了五枝,而且决定要娶她。在那个城市,他们根本就结不了婚,那个城市的人们都盯着他们呢。不得已,他带着五枝出来了。他要和五枝追求他们共同的幸福。五枝其实不叫五枝,五枝成了他的女人,才叫五枝的。
五枝也是跟着老头子出来的。他真的很不愿意,这让树叶知道了,不定怎么伤心,怎么哭呢。树叶哭泣时声音细细的,肩头一耸一耸的,胸脯一起一伏的,真像是经了雨的树叶。记得有一次树叶被他弄疼了,就这么哭。树叶说,坏蛋,你不能轻点嘛。那是他们的第一次,他不想弄疼她,他很听话地说疼就下一次吧。他以为还会有下一次,下一次他一定要轻点,再轻点,决不弄疼她。可没多久他就离开了村庄。再没有下一次了。
那么五枝呢?五枝有过第一次吗?如果没有,那真叫遗憾啊。他只知道他和五枝不可能了。五枝是他的女人,可他知道五枝不会给他生孩子。他抱过五枝,摸过五枝,好像也吻过,可是他知道五枝不会像树叶喊疼的。他也想过让五枝疼,但终于没有。五枝也抱过他,抚摸过他,吻过他,五枝也没想过他会让她疼。在寒冷的冬夜,外面飘着雪,屋里的火炉熄了,他们紧紧地拥抱过,相拥着沉入了睡乡。或者是遇到了什么难事,有时是他遇上了,有时是五枝遇上了,他们也会紧紧地拥抱,彼此说些宽慰的话,抚摸着,这日子好像也温暖了。过得久了,他们彼此好像越来越分不开了,他疼五枝,五枝也疼她,真的是分不开了。他想,老头子见了五枝,这下该满意了。老头子对五枝说过,你得听艾国家的,他是你的男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女人。五枝越来越知道怎么做女人了,老头子却像一滴水一样消失了,蒸发了。一开始老头子还捎个信,问问他们过得怎么样,适应吗,生活有困难吗。现在却一点音讯都没了,不知是漂到了那个小岛,还是潜伏到了某个更隐密的地方,任他们怎么找都找不到了。他和五枝都骂过老头子,他让他们结了婚,让他们来到了这个小镇,却把他们丢下不管了。有什么办法呢,他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想过离开这个小镇,五枝也想过,然而终于没有,好像是习惯了这种生活,习惯了这个小镇,习惯了这样的厮守。就像镇上老磨坊里的磨盘和碾子,谁都离不开谁了。
他对五枝说,下辈子,我还娶你。
五枝说,下辈子我还嫁给你。
然而,邻居的小姨子却来借宿了,因为她的到来,五枝一下子像变了个人,变得魂不守舍了。甚至是有点急不可耐,只想跟着那个女人,只想守着那个女人,只想伴着那个女人。他真是有些想不通了,他们不是好好的吗?他们不是谁也离不开谁吗?可现在,他却拉不回五枝了。她硬是把他抛下了,砰地一声就把门关了。他呢,他不是忽然也变得怪声怪气的吗?他不是也想着邻居的小姨子吗?
他为什么要让她们睡在一起?
五枝这会儿在干什么?
他想自己真是糊涂,真是个糊涂虫啊,怎么做了这样的傻事。他在这屋子里待不住了,他出了门,想想又退了回来,脱了鞋,这才又出来了。
他轻手轻脚地走到了东屋门前,像一只猫。
里面好像没一点动静。
怎么会这样呢?他有点不相信。他不相信五枝会老老实实地睡在那个女人身边。五枝睡在那个女人身边了吗?
站得久了,潮湿的地气从脚底升起来,慢慢慢慢地顺着腿梁爬上来,他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了,想放个屁,却终于忍住了。他还想打个喷嚏,想想不能打,一伸手捂住了嘴。他觉得该去穿鞋了,要不然是站不久的,可或许是站得久了,困了,身体一摇晃,腿一哆嗦,就把什么碰翻了,可能是一只凳子,也可能是一只水桶。这就爆出一声响来,石破天惊地。
五枝出了声,谁?
他不知该怎么说了,他想说,猫。
他捏着鼻子学了一声猫叫。
他听得五枝嘟哝说,馋猫,该死的馋猫,都大半夜了,怎么还不安稳?
其实家里根本没养猫,五枝一定晓得他在偷听了。看来五枝还没睡,那个女人呢?她怎么没声音?
五枝又出了声,还在吧,回你的窝去。
他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贱。
可是,他不能不回去了。他知道不回去,五枝会出来的。五枝出来了就会跟他发火。五枝今天火气好像特别地大。他有点害怕了。看来五枝平时的温顺都是装出来的,或者是掩藏起来了,这个女人好像把五枝的火气都勾起来了。他原本就该意识到这一点,可多年的小镇生活却让他忽略了这一点。想到这里,他忽然想哭,他不知这该怨谁。
你真是个蠢驴,他骂自己。
像是在跟五枝怄气,他狠狠地倒在床上,用被子把自己捂了个严严实实。这床还是他们刚来时,从镇上的旧家具市场买的,很笨重,也很结实,两个人睡在一起发不出半点声响。后来他们觉得不时兴了,又换了张新的,旧的就放在西屋了。他们的亲戚都在很远的老家,早没了联系,也就从没有来镇上走动过。也许都以为他们在战乱中死了。战争像猛兽的嘴,不知吞掉了多少人,他们能幸免吗?没有亲戚走动,这床就闲置下来,闲了多少年他记不大清了。现在,他躺在床上,忽然觉得这床是异常的阔大,他一个人根本用不了。当初为什么要把这么大的床抬回家呢,真是可笑。他们又没有孩子,要这么大的床有什么用呢。
他努力强迫自己睡觉。他想五枝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去吧,看你能折腾出个什么样来。然而想是这么想,却还是怎么也睡不着,他躺在床上,心思却飘到东屋去了。五枝啊五枝,你千万别折腾出什么来,你别忘了你是谁。是啊,五枝是谁?他自己又是谁呢?你们为什么要到这个镇上来?这个问题忽然就冒出来了,把他吓了一跳。好多年了,他们早忘了自己是谁了,忘了来这镇上干什么了。只知道他们是这镇上安安稳稳的一对夫妻,有个幸福的家,要不镇长能把他们树为模范夫妻?
越是睡不着,脑子里越是生出许多想法,杂草似的疯长。他裹在厚厚的黑暗里,眼前却亮亮的,他看到了鱼一样光滑的女人的身体,闪着鳞光的女人的身体。他想到了树叶,黑暗里的树叶就是一条光滑的大鱼,在他怀里扭动着。他还想到了邻居的女人,邻居的女人好像对他很有意思,那双眼睛看着他时总是雾蒙蒙的,雾的后面是什么呢?他说不清。那是邻居的女人啊,他不能做出对不起邻居的事,也不能做出对不起五枝的事。他在黑暗里想过她几天后就不想了。人有时就得克制自己,该压抑的想法就得压抑,不该想的就不要去想,硬要想,硬要去做什么,那就会坏事的。
可现在邻居的小姨子来了。
她为什么要来呢?
五枝这会儿在干什么?他真是不放心。
他又爬起来,光着脚走了出来,站到了东屋门前。屋子里仍静悄悄的。似乎能听到那个女人均匀的呼吸声。五枝呢,他知道五枝很能睡的,有时候头一挨着枕头就睡着了。他为此没少笑话五枝,说她上辈子可能是头猪。五枝也笑话他,说他上辈子也是头猪,呼噜打得山响。五枝说,你打呼噜时,我真恨不得往你嘴里填些驴粪蛋,看你还打不打了。说着这些,他们就会笑,笑声像一道炊烟升起来,温暖着他们的日子。
屋子里却没有动静。
他在那里站了很久,觉得五枝可能真的睡着了,一颗心这才跌回了肚子。
他于是回到西屋,上了床开始睡觉,他觉得困得厉害,不好好睡一觉明天就没法去厂里上班。后来呢,他好像睡着了,他不知自己打呼噜没有。再后来呢,他好像飘进了东屋,不知怎么的就上了床,紧挨着邻居的小姨子睡了。他的手慢慢慢慢摸了过去,他触到了一条光滑的大鱼,鱼却忽然叫出声来。鱼的叫声很响,很尖,好像把他的手划破了。他猛地弹起来,摸了摸,身边什么都没有。但那声音却是真实的,尖利地从东屋飘出来。他蓦地意识到了什么,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会出什么事呢?五枝不是睡了吗?怎么会出事呢?
等他匆匆出了西屋,邻居的小姨子早已惊恐不安地奔向院子。这时候,院子的上空已经发白发亮了。他看到那个女人衣服穿得非常潦草,好像被什么绊了一下,她忽然跌倒了。他跑过去,想把她扶起来,那个女人又哇地叫出声来,一伸手捂住了脸。
离我远点,远点。邻居的小姨子说。
你究竟怎么了?
你老婆她不要脸,他怎么会是个……男的呢?那个女人哭泣着说。
不,不可能的,他对你怎么了?
流氓,你老婆是个流氓。
他又要问什么,五枝出来了。他看到五枝面如土色,脚上没穿鞋,衣服的扣子好像也系错了扣眼,显得驴头不对马嘴。
女人又叫了一声,爬起来就跑。
他知道坏事了,也没去追,直直地盯着五枝。
我实在忍不住了,她,她太好了。五枝结结巴巴地说,
他照着五枝的脸狠狠地抽了一下,都是你做下的好事,这下我们完了,彻底暴露了。
太阳升到中天时,他们逃到了几十里远外的一个小渡口,渡口边竖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几个血红的大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标语牌下是两辆三轮摩托车,几个穿白褂子蓝裤子的警察就在那里等着他们呢。
他知道这漫长的潜伏岁月就要结束了。
他搞不清这究竟怎么回事,真像个梦啊。他听得五枝说,对不起,都是我闯的祸,下辈子让我转个女的吧,我会好好服侍你。
他笑了笑,恍惚看到了那时候的五枝,一个英武的小伙子走在特务营的操场上,肩章反射着1948年秋天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