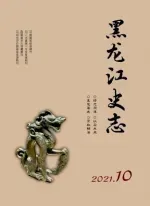方志是反映客观存在的镜子——认知方志学初论——泛地方志概念与新方志及新方志学思考札记
史天社
9年前,笔者提出“泛地方志概念”[1],指出:“地方志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新时期需要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看待它,研究它。从社会属性上对地方志重新进行认识,明确其研究记述自然、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的本质,以适应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今天,重新思考新时期现代化、信息化条件下方志的社会属性,思考构建以自然、社会客观存在为认知记述对象的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新方志学学科体系,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高度开拓方志的认知领域,重视方志对自然和社会认识过程及成果,提高方志活力及其社会文化知识品位,增强方志社会服务功能,对于促进地方志事业发展具有更加现实的重要意义。
一、传统方志概念
方志名称:在方志的发展过程中,有10多种文献、著述、著作与其有关,例如书、经、录、记、图经、传、略、乘、谱、考、集、编、薄、典、览、志等[2]。可以说,这些名称一度曾是方志的一类或是方志的别称。
“方志不是地方志的简称”,约在20世纪30年代后,有人开始将古代的“地志”、“方志”的称谓合并才有了“地方志”的名称,但在实际使用中,通用的仍是“方志”的原概念[3]。
方志的性质:历史上,人们曾将地方志书称作地理书、地情书、历史书、资料书、百科全书等等。
宋代以前,方志大都被列入舆地图经门类,视作地理专书。自宋代以后,就不断有人提出方志为史的见解,但并未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说明。章学诚继承前说,提出“志属信史”、“方志乃一方全史”等主张,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说明。
《方志百科全书》称:“方志,又称地方志、志书、志,是记述某一地方古今各个方面或某一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4]
《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
二、泛地方志概念
笔者提出的泛地方志,是指研究记述自然、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
按照泛地方志概念,地方志书的定义——是全面系统地研究记述一定区域内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客观性著述。
泛地方志概念的定义域:在这里,“方志”是一个大概念,其既包括“方志”、“地方志”,也包括“国家志”、“一统志”、“总志”,还包括类志书性质的其他著述著作等。用“方”来指代方志研究记述的主体及对象。所谓“方”,大指国家、民族、省市县区,小指企业、村组、家庭,也有一事、一人、一个组织的意义。方志姓“方”,还有因为它不“越界而书”具有特定记述范围的意义。方志名“志”,因为其质为“志”。之所谓“志”,志者性也,即一地之情、一地之性也。起码“志”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文化观念形态的志书著作作品;一是指研究记述形态的社会意识活动或社会修志工作(社会修志事业)。
就是说,“方志”的概念,一是指国家、社会组织、社会个人等主体对其所处的客观世界、现实社会乃至主观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与现状的研究记述活动(工作、事业);一是指这种研究记述的精神生产实践创造出来的观念产品——客观认知的著述志书等文化产品及由其所构成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
综上所述,就是宽泛意义上的完整的“方志”、“地方志”,笔者称其为泛地方志概念。
三、传统方志概念的局限
传统方志,是指以收集整理记载一地之历史认知成果为主的志书。其主要特征,一是收集编纂现有认知成果;二是收集辑录对历史认知的成果。
旧方志的志书,著述性不够,系统性不足,表象性往往大于实质性。其基本的编纂理念和原则是“忠于事实”、“言必有据”、“考证据典”、“述而不作”、“秉笔直书”、“生不立传”等等,往往拘泥于事实现象,就事记事,难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等问题。
因为方志是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成果,所以,方志便有了山经、水经、图经、地理书、物侯书、风俗记、人物传、国志、地志、专志等等种类。大约在萌芽期、早期乃至定型期甚至成熟期的方志,都是以记述人们对自然、社会乃至一切可以认知领域事物的意识成果为己任的。其基本特征是事以类分、直书记载、忠于史实。之所以说传统方志为“旧志”的原因,相对来看,主要是指这种方志记述活动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并不特指时间意义上的新与旧。
传统方志观念认为方志属于历史范畴,是历史性的地方志。实际上,方志记述的对象是自然、社会等等的一切客观存在,其社会属性、客观属性、意识属性等等大大超出了历史及历史学的范畴和意义。
传统方志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其对方志属性的认识上。关于方志的属性,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理解。过去的方志大家们都是从地方志自身特性来定义的,今天的学者使用逻辑学种属分类定义的方法,依然没有跳出就方志定义方志的圈子。比如,研究人的属性,如果从人的自身特性出发,就“人”来定义“人”,以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为标准,可以定义说:“人是高级动物”、“人会劳动创造”、“人会使用工具”、“人类有自己的语言”等等;如果从种属分类,人可以分为“男人”、“女人”,“大人”、“小人”,“好人”、“坏人”、“中国人”、“外国人”、“白人”、“黑人”等等;如果按照细胞、基因来分,人与人之间、与其他动物甚至物质之间的特性差异,就会无穷无尽。而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便一下子照亮了人类的整个历史。
方志在研究记述自然和社会存在中求实创新,使自己更加切近现实和客观事实,不断创造出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不拘一格的社会文化产品,方能保持旺盛的生命活力。据此要求来看,今天如果要说传统的方志理论、实践有局限的话,其表现在志书方面,片面强调“资料性”和“文献”式的“规范化”,强化“一本书主义”,人为设置了体裁樊篱;在学科方面,单纯“研究方志的产生和发展、性质和类别、特征和功能、编纂理论,以及整理和利用”,形成一个比较封闭的方志内部循环研究系统,是一个走不出去的迷魂阵;在编纂方面,把“现实”变成数字的堆砌和实例的总和,离开对“客观性现实”和“思想性历史”规律的把握;在工作方面,注重“过去”、看重历史、依赖资料,清规戒律、凝固范式、即此非彼,行政修志、摊派修志、关门修志,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产生不被重视、几十年修不出一部志书等被现实边缘化的问题和倾向。
对新时期地方志的社会属性没有深刻正确的认知,抱守传统的方志理念,便会丢弃《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的方志“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本质使命,在方志是“资料”、是“文献”、还是“著述”等外在形式问题上打转转,迷失方志研究记述的真正对象和标的,将方志目标囿于“一本书”上;将方志工作局限在志书编纂上;将方志领域开拓维系在“开发利用地方志资源”上;将修志体制机制桎梏在“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的“官职”、“官责”上;将编纂力量单纯依靠在方志专家身上。如此等等,这是新时期限制地方志事业不容忽视的一个关键问题。
四、方志的社会属性及提出泛地方志概念的依据
方志有历史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历史上,人们对方志的历史性认识得比较到位。方志的实践性更多地体现在其社会性之中。方志的社会属性,就是方志在整个社会及社会学中表现出来的质的规定性。方志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更要从它的社会属性来定性。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用哲学社会科学的观点,从社会属性来认识地方志,给它一个宽泛的新概念,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适应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及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需要,对于认识历史,研究现实,开拓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方志是历史和现实的一面镜子。其哲学依据——社会意识是社会客观存在的反映。
从方志的本源来看,方志作为研究记述自然、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观念形态,所记述的人、事、物必须是客观存在的,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方志的起源同一切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起源是一样的、同源的。方志的源头是人们认识事物、认识社会的一切知行活动。人们对社会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生活经历的理性认知或意识思维成果,都是人文社会学的源头,当然也是方志的源头。而人们认知活动的对象是自然和社会的客观存在,所以,方志是用意识的形式对一地之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照相”写真。
方志的社会本质是人们对自然演变、社会发展认识和实践过程及规律的归纳反映。
客观性,是方志的第一属性、根本属性。新方志崇尚资料性、科学性、思想性等等,都是由客观性衍生出来的。方志的所有其他属性皆由此派生而来。
从方志的类型来看,方志是一个综合的自然社会文化知识体系,是对特定地域内古今自然状貌、社会实践及认识的概括记述。
方志通过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记述一定地方的历史及现状,有研究性、学术性、综合性的意义。
首先,方志的记述,涉及到人们可以认识的所有领域。它既研究反映现状、研究反映历史,又研究反映理论和社会形态;既研究反映经济基础,又研究反映上层建筑,其特点是可以分门别类地纵向反映历史演变的连续性,又可以横向反映各个类目之间的有机关联,纵不断线,横不缺项,沿着事物发展的历史脉络,通过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相统一的记述著述,形成综合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用客观真实的事实,把现实事物的运动规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反映出来。
其次,方志的记述,涉及到人们研究的各个知识学科。一方面它把各学科的研究知识提炼汇总起来;另一方面它把各有关学科的知识综合起来,再用于在其他具体学科、具体领域的研究及实践。
总之,方志既是资料书、地情书,又是教科书、工具书;既是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文化著述,更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
从方志的功能和作用来看,方志是一座宝藏。方志是从人类社会一切知行活动中精炼萃取的精神成果。方志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及社会的历史过程的实际状况作为研究记述对象,不仅给社会、给后人提供经过提炼的金子一般的文献资料,而且,它自身更具强烈的厚德载物、经世致用的功能及作用。大家公认,方志有“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通过方志的功能更能看清其社会属性的本质。
方志的本质功能和作用在于其认知功能、意识功能和传媒功能,归纳起来就是服务现实的构建社会文化知识体系的功能。有“认知”才可“存史”,有“意识”才可“资治”,有“传媒”才可以“教化”,这便是方志作为社会存在而延绵不绝的内在依据,也是方志的神圣使命。
新方志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反映客观的主观意识形态属性非常鲜明,加之新方志记述的是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状况,其必将更加自觉地突出文化认知和文化传播功能。就是说,新方志是意识形态高层次的文化认知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软实力高层次上的文化事业建设,新方志内在具有文化知识意义上的质量价值标准要求及其高度自觉的倾向性。
从一定意义上讲,修志也就是在修史。从史与志的区别和联系来看,志是史的一种类型,史和志都是文化现象,同根同源,它们的社会属性是一样的,同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史要揭示社会、自然发展的历史规律,志一样也要反映社会现象和自然的演变规律。但志相对而言有更突出的广泛性,史取材于志,志包容着史,志是对史的表现形式的继承和拓展,史是对志的提炼、总结和升华。
今天的历史学,只能是一门整合的社会科学。方志同样也只能是一门整合的社会科学。在中国古代,人们对史学概念的解说所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是:史学是一门关于如何认识、叙述或编纂过去的事件的专门性、技艺性的学问。据瞿林东先生的研究,大体说来,中国古代“史”的含义经历了史官、史书、史事、史学的发展过程。后来它有了编纂学、文献学的内容;至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又赋予了史学以历史叙述技巧和历史认识方法等内容。瞿林东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5]蒋大椿定义“历史学乃是作为研究主体的历史学家通过一定的思维认识方式、手段与历史客体发生互动作用的历史研究这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即历史知识。”[6]吴泽说:“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7]可见,人们对历史、史学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因为,历史、史学的内涵在不断地扩展和延伸。同样,方志、方志学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扩展和延伸,人们的认识也在相应地提升。
有人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世界民族、国家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等,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历史运动事实和过程。方志研究的对象比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更为宽泛,涵盖了人们可以认知的一切客观、主观的现实存在领域及事物的历史与现状,所以,方志的整合性同样非常地突出。
方志与历史学一样,其存在的根本依据是其客观真实性。卢基阿努斯在《论撰史》[8]中讲过:“历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历史必须努力尽它的本分,那就是写出真实。”“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所以,在泛地方志概念中突出强调了体现方志社会本质属性的“客观性”著述的特征。这样的话,既然历史学可以确立,那么方志及方志学同样也就能够确立。
五、方志的基本规律
通过以上诸条对方志本源、方志类型、方志功能与作用、方志与百科知识和与历史学关系的研究探讨,可以得出了“两个概念”(即泛地方志概念、新地方志书概念)、两个规律(即方志演变基本规律、志书生产原理及生产规律),从而发掘泛地方志概念的巨大理论价值和意义。
方志演变基本规律:方志由多样性起源,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模式,这是方志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实现了由点到面的汇流、集纳过程;继而应该进入第二个阶段——打破第一阶段成熟固定的陈规,由程式化发展到更高层次的多样化。由此发展,方志逐步成为系统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成为帮助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知识工具,成为社会化修志的先导指南,使方志发展实现由面到点的新扩展,形成立体、多维的发展空间及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经过上述汇流、扩展两个阶段,方志在发展上实现一次质的飞跃,在实践上由必然王国奔向自由王国。
方志演变基本规律,是由方志反映自然、社会客观存在的社会属性决定的;是方志作为研究认知工具的本能体现。
志书的生产原理及生产规律:志书可以是历史著作,也可以是人文著作,还可以是经济著作、科学著作等等。甚至可以将一切类型的记载、反映地方特色的社会知识、自然知识的文化产品及其信息材料等等,都纳入地方志的内涵之中,然后创造出多种多样的体裁体例,通过多种载体进行记载和传播,增强其为历史及现实服务的功用。这就是志书的基本生产原理。
志书的生产历来都不是自发的,而是社会的、历史的和实用的。方志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社会修志、为社会修志、为后世修志。依据社会存在、按照社会需要修志,是志书生产的基本规律。
志书生产原理及生产规律,是由方志研究记述的客观存在对象的丰富性、多样性、生动性等决定的。“生活之树常青。”如何反映鲜活的生活,不可拘泥于固定的体例、规范和模式。否则,就会陷入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唯心主义的泥潭,就会僵化方志、窒息方志的生命。
六、新方志及其内涵
方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存在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作为社会客观存在,其具有特殊生命力和重要历史地位。所谓“新方志”,是在新时期对传统方志的开拓创新和继承发扬。新方志主要特征是,切近现实、与时俱进地认知方志所要记述反映的对象,用有意识的高度自觉来给现实存在“照相”、“画像”,形成积极主动地反映现实与历史的文化形态的知识产品,服务社会,服务当代和后世。
提出“泛地方志概念”和“新地方志”概念,是现代化、信息化、知识化社会形成和发展的需要及必然结果,是方志服务社会的客观要求及必然选择。
新方志,首先是指新编地方志,即新编的社会主义地方志,特别是指第二轮修志的尾声及以后将要形成的地方志。也就是所谓的“新时期”的地方志。
相对于传统方志概念,将泛地方志概念下的方志,称之为“新方志”。同样,将据此构建的方志学,称作“新方志学”。
新方志,狭义上是指研究记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程、规律及成果的文化形态的著述著作;广义上是指这种文化形态的著述形成体裁体例格式规范等等不拘一格体的新方志志书,构成系统的社会文化知识体系的社会文化活动、工作及事业。
新方志的时代背景,是指当前我国形成或正在形成的信息化、知识化、市场化、经济化、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大趋势;加快文化强国、文化强省建设的社会文明进程;文化融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核心软实力的崭新时期。
新方志的时代特征是,与当前的现代化同步地研究记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进程、规律及成果,形成不拘一格的新志书。相对而言,传统方志的基本载体是志书;新方志的基本载体是志书及其派生的各种相关著作著述。
新方志与传统方志两者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反映。但新方志有别于传统方志的根本点,就在于新方志内涵的哲学社会科学属性的增长和强化。新方志不断超越历史学的范畴逐步成为涉猎百科的新的知识体系。
狭义新方志概念与《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的地方志书的概念在研究记述对象上是一致的,但也有其他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一是狭义新方志概念定义的是“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的定义;《条例》定义的是“地方志书”,不能包括“地方志”的概念。二是狭义新方志概念认为“地方志书”是著述著作;《条例》认定“地方志书”是一种资料性“文献”。三是狭义新方志概念认为地方志及地方志书本质是“客观性”的著述;《条例》认定地方志书是一种“资料性”文献。比较而言,可见新方志定义更具哲学社会科学意义的规定性。
广义新方志概念的基本内涵,一是说明“方志”是研究认知性的记述活动;二是“方志”研究记述的对象是“自然、社会及其发展规律”;三是“方志”属于“社会文化”范畴,是对客观存在的认知活动及结果的归纳总结;四是“方志”自成“社会文化知识体系”,具有认知追求客观真实与记述汇聚百科知识的主动品质。
按照泛地方志概念的要求,新方志鲜明的研究和认知属性,使方志具有了认识事物的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工具性的作用和意义,大大增强了方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提升了方志在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乃至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七、方志学研究状况
我国以方志为研究对象的方志学,如果从清代的章学诚算起,也有近300年的历史。新编地方志30年间全国修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产生了大量的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方志学理论。广大方志学者在认真总结多年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修志的规律,努力将修志经验提炼到理论的高度,用来指导修志实践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修志工作的一项内容。
建立方志学的必要性。理论上的成熟是事业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当前,发展新时期的方志事业,迫切需要加强方志学研究。方志实践需要扩大到新的领域,没有学科理论的支持就显得十分窘迫。
方志学的定义。2010年4月,中指组召开的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会议认为:“方志学是研究方志领域矛盾运动的科学,主要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大方面,具体有方志的性质、功能、编纂、应用、管理,以及与编纂、应用对象相关的自然社会现象的对应研究等。”
方志学研究的困境。当前,方志学研究相对于方志编纂的实践,总体上仍显得比较薄弱、比较滞后[9],面临许多需要突破和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尽管方志理论的文章和专著几乎涉及到了修志的各个方面,但是,存在总体着眼点不高,多数文章是修志者的心得和体会,或者是经验和做法,可以直接提供给别人借鉴,却没有升华到理论的高度等不足。这是由于没有一致的理论研究方向和标准要求,没有明确的方志学总体规划目标要求的结果。
尽管《地方志工作条例》将推动方志理论研究列为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职责,但重实践、轻理论研究的问题普遍存在。许多地方志机构没有具体的落实措施,甚至没当成一回事儿。目前,做文章、搞理论研究似乎只是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
最大的问题在于至今没有理清构建方志学的思路和建立方志学科的目标途径。以致于在研究方志学问题中,出现将所有的理论问题甚至实践问题都想归入方志学之中的思维误区。
方志的涵盖面极广,实践性较强,方志学科应该处于高层次的指导地位,给修志实践提供哲学社会科学高度的指导思想和研究认识工具,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上发挥作用。指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方志学科,可以包容所有的修志体例、结构、范式、方法、标准以及所谓方志编纂学、审定学、管理学、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避讳学、出版学、应用学等等,那是天方夜谭。
方志的根本任务是出修志成果,这是中心,而绝不是出全各种各样的专用修志理论工具。务虚是为了务实。脱离务实的务虚方志学活动热闹非凡,却只会在历史的天空搞出玄而又玄的漫天迷雾。凭着现有的方志队伍,完成所谓方志学科如此庞大的、永无止境的务虚研究工程,可以说连起步的力量和可能都没有。
八、方志学科构建原则及前景
基本原则。一门学科的科学性的一般判断根据主要有两点:一是“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因为只要客观实在的东西,才可能有它内在的发展规律”;二是它“必须是旨在探讨对象发展规律的认识活动”[10]。据此意思,构建方志学必须把握两个层面的基本原则:一是始终明确当代新方志学,主要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一地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及其规律的科学;二是始终将探讨方志认知活动的着力点放在认知方志记述对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参考原则。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11]。人类的活动产生经验,经验的积累和消化形成认识,认识通过思考、归纳、理解、抽象而上升为成知识,知识在经过运用并得到验证后进一步发展到科学层面上形成知识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演进的知识体系根据某些共性特征进行划分而成学科[12]。《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主要依据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的本质属性或特征,学科的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学科研究的目的与目标等五方面进行划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的有关规定对于构建方志学科具有原则性的参考价值。
科学性原则。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科学”是在不同程度上正确反映事物的规律和特性。如果方志、方志学、方志学科,仍然只是将自身作为研究对象,自己研究自己,而不去研究自己记述的自然、社会客观现实,那就失去了科学性,那就是钻进故纸堆“自珍自艾”的烦琐哲学,由此建立的方志学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更无必要。
遵循客观原则。理论是实践的总结。意识反映客观,客观决定意识。正确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认识符合客观事实及其规律,就成了经验,继而上升到理论的层次,就成了定律、定理、真理。确立方志学科的科学性,其实就是不断地探索方志记述对象的发展规律,并且用以指导修志及方志理论学科的建设。这是其越来越符合方志反映记述对象规律的过程;是一边探索、一边符合现实社会存在的客观规律的过程;也是方志理论、学科内部各种要素及其配置不断合理化的过程。真正的理论并不深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谓真理,其实就是事实、就是生活,精灵古怪的“真理”就隐藏在事实、生活的细节之中。
科学理论指导原则。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正确的方志理论,本质上说来源于实践。但是,理论也可以来自理论,包括对旧方志学说的扬弃和借鉴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方志学尤其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成果,因为方志学本身与各种学科都有一定的联系或交叉、借鉴关系,更应该重视它的兼有其他理论土壤的营养和作用。
如何对方志的认识对象进行“观察”、“研究”和“把握”呢?主要有经验、认识、知识、理论、学科五种基本方式,五种方式都可以面对现实。所以,没必要将所有问题都一股脑地归入“学科”之中。
新编社会主义地方志,始终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可以说,我们的新编地方志是一个由此科学理论孕育催生的新方志,也是一个由此科学理论指导而不断发展壮大的新方志。马列主义科学理论是我们新方志的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重视马列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编修新方志的一条基本经验。当然,待到我们的科学的方志学真正建立起来的时候,会将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更好地坚持下去。那时,方志事业有了更强大的、更自觉的精神生命,一定会更加生机勃勃。
以科学理论指导就是要求我们加强理论的修养,坚持理论自觉,善于理论创新、升华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就是对规律的正确反映和阐明。因此,它能增强我们工作的预见性、驾驭性、主动性、原则性、精准性,从而提高科学化水平。这里有两个必须始终坚持的核心思想:一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这是我们党思想路线的精髓;二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这是十八大确立的指导思想,要贯彻到方志建设的各个方面。
科学制度保障原则。邓小平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科学化的重要内容就是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科学制度的保障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所以,在修志及理论学科建设实践中,要善于总结、提炼、规范,把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形式,并随着形势发展进一步调整、改进、完善做出修改,不断形成新的制度性规范,不断促进制度建设体系化、科学化。
科学方法推进原则。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是方法。方法问题非常重要。方法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方法是完成任务的途径。毛泽东曾把方法比作“桥”和“船”。好的方法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只有反映和遵循了客观规律的方法才会是科学的。对于方志工作及其学科建设来讲,要有针对性地设计抓手、平台和载体,通过合适的方式和路径,使国家意志、制度政策、学科要求、工作部署真正落地,就应讲究方法的科学性。科学方法,形式上是主观的,内容上是客观的。在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中,以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作指导,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方志学及方志学科建设,应该在遵循一般学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学术原则的基础上,将学科理论分为基础理论、制度理论、方法理论等不同层次,高度重视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方法创新,以这种“三位一体”的创新,保障和实现理论的创新及理论的应用。
依据方志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的本质属性,学科的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学科研究的目的与目标等标准,新方志学科应该定位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级综合学科。
主要原因是,新方志学具有研究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实状况的职能,其研究记述的领域范畴不仅可以涵盖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而且涉及人们可以认知的一切领域。新方志学主要与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档案学等同级学科相近或交叉;在应用学科意义上,新方志学的范畴更加广阔。
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方志学科属于人文与社会学科;二是方志学科属于历史学科,但是新方志超越历史,研究认知现实,具有宏观定性调查统计的社会职能、职责或意义;三是新方志使用的理性认知思维工具,具有哲学认识论的作用;四是方志涉猎百科知识,既汇总记述各种、各类知识成果,又使用这些知识去认知相应的自然、社会、行业、事物,兼具横跨专业领域的意义;五是方志学科研究的目的是给方志以客观真实的内容及一个切合实际的记述体例形式,具有极强的实践性、科学性和现实必要性。
九、认知方志学的基本构架
笔者将前文论述的新方志学定名为“认知方志学”。如果将传统方志学命名为“记述方志学”以突出其记述性的话,则在新方志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认知方志学”,重点突出新方志的认识现实、服务现实、开拓未来的特质属性,以保证志书更强的记述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传统方志的编纂,常常以收集资料作为认识事物的主要方法和手段,然后再依据资料确定篇目结构及内容取舍,被动性较强。资料全不全、对不对,是一个困扰、伴随修志始终的大问题。
新方志编纂,提倡用哲学社会科学及历史学等等学科的科学理论与方法指导认识志书的记述对象,首先是洞明历史,把握历史规律及事物规律,主动性地保证资料的真实和完整,保证志书的质量和文化品质。
认知方志学的学科构架。属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一级学科,由新方志和新方志史两个二级学科组成。
学科具有“学问”、“理论”、“知识”、“知识体系”等多种层次。方志本来就是一个学问。新方志构成知识体系,兼备学科的科学属性,它自然就是一个完整学科。
新方志在学科理论方面,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大部分。基础理论具体有方志的性质、功能、编纂等;应用理论具体有应用、管理、制度、规范、标准、方法、经验、典型等。
所谓新方志史,就是以方志研究记述客观存在的认识活动及其成果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问。之所以称其“新”,是因为新方志史不仅研究方志活动的历史规律,更是注重通过对方志及其成果的记述,真实反映方志记述对象的历史与现状、变化与规律,支持方志学贴近实际、结合实际,保持旺盛的繁荣发展活力。
至于当前方志学研究中学者们提出的所谓方志编纂学、审定学、管理学、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避讳学、出版学、应用学等以及方志批评、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等,都可作为新方志的内涵理论、制度、方法等层面的内容加以处理和完善,便可使它们化虚为实,发挥作用。其实,此类理论问题更多的是借鉴使用别的学科知识的问题。理论是个工具,通用工具是最佳选择,实在不行时方去配置专用工具。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也是一个技术和成本问题。
认知方志学构架的哲学和历史学依据。方志就是方志史。因为方志本来就是历史性的认知活动及其社会文化知识体系;同时,方志史本来就是认识活动的历史。由古往今来的方志所构成的方志史,就是认知性的历史。新方志史完全可以包含传统方志学的任务和内容。所以,认知方志学将其学科构架仅分为“方志”和“方志史”两个部分(二级学科)。
既然说“方志就是方志史”,那学科构架还要“方志史”干什么?方志和方志史之间的关系是,方志是方志史的根脉,方志史为方志提供“阶梯”和“支撑点”。方志就像一支征战四方的雄师,方志史就是它的粮草和大本营;方志就像一个耕耘农田的农夫,方志史就是他的粮仓和家园。有了这样的格局,方志才有依据,才能经得起历史性的追问和时代性的诘难。
认知方志学的实践依据。新编地方志没有建立完整的方志学科,照样完成了巨大的修志文化工程。新编地方志的科学性直接来源于社会实践。首轮、第二轮志书都是由熟悉情况的亲历者、亲为者参与编纂完成的,是社会化修志、众手成书的结果。当然,方志专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编纂《汶川特大地震陕西抗震救灾志》,一边抗震,一边修志,同步进行。结构志书没有什么深奥理论,只是按照灾害灾情—抢险救灾—社会赈济—灾后恢复重建的实际进程,收集编辑了500万字的资料长编,编写了260万字的初稿,几经修改最终完成106万字的志书,做到了精品要求。实践证明,生活才是教科书,实践才是真老师。以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的认知方志学,将认知活动、认知实践、认知要求等作为修志的“开山巨斧”,可以在客观存在中找到无比鲜活、恰当有用的方志学理论,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这就是修志的实事求是。
十、确立新地方志概念及新地方志学的意义
建立新方志、新方志学概念及体系,看似务虚,实在务实。这是一个“实学”问题。
新方志、新方志学概念及体系是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一个系统理论,是一个为用、有用的知识体系。泛地方志概念将方志的外延扩大到了人们可以认知的所有客观事物范围,给地方志事业以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生命力;新方志定义界定志书文化产品生产及管理事业的任务及功能,符合客观存在的发展规律的特质要求,保证了修志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将方志落到了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及社会科学的实处;认知方志学从理论工具方向入手,在泛地方志概念下,将方志及理论研究的内涵收缩到了可控、可用的程度,将学科构建成方志和方志史两个部分,增强了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对今后的修志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和意义。
新方志学适用于新编地方志进入第二轮结尾和持续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信息化、科技化、现代化、经济化、政治化、民主化等等。新方志学适用于古老的方志向现代方志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一本书主义”被打破,方志的发展从成熟走向再生;从体例、形式上发生多样化的变革;从方法手段上主要依靠信息化;成果载体形式上提倡不拘一格丰富多彩。
新方志及新方志学可以加深对地方社会存在的认知水平;提升方志的学术水平,将其从记述行为扩展到研究领域,提高方志的价值和作为能力;丰富志书的成果形式,壮大修志队伍和阵营;促进方志成果的开发利用,传承文明发挥更大的作用;开放方志的组织管理领域和组织机构形式,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修志工作。
结论。理论创新是对已有丰富理论资源的活化和相应理论困难的突破。所谓泛地方志概念、新方志、新方志学的提出,都是在传统方志、方志学的基础上和“襁褓”中诞生的。好比说,传统方志、方志学是一个老人经营着自己的家园;新方志、新方志学是他长大的孩子要去征战、去认识和收获关于自然和社会存在的一切知识财富。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方志时代的区分,同样道理,“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相信方志就这样简单一跃,便会迎来它全新、广阔、壮美的新时代。
[1]史天社.试论新时期地方志的社会属性——“泛地方志”概念的提出与思考.理论导刊,2004(4).
[2][3]王辉.什么是方志.中国地方志,2012(10).
[4]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5]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4).
[6]吴泽.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
[7]琉善.论撰史.章安祺,编.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 1 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8]朱佳木.关于加强当前方志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志,2012(12).
[9]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34.
[10][11][12]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2009)(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