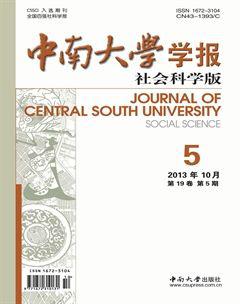金岳霖的外物观
苗磊
摘要:金岳霖认为外物是独立存在的,一方面是以朴素实在论的出发立场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批判唯主方式有关。从一时一地的官觉现象出发的这种唯主方式方式得不到真正的外物,而只能推理或建立外物,但最终推理或建立外物也是不可能的。唯主方式产生的原因是寻求立于不败之地的要求和无可怀疑的出发原则造成的,其最终也必然陷入无限倒退的深渊而不可自拔。金岳霖认为必须要超越人类中心观和自我中心观,肯定外物的独立实在性才能真正解决外物问题。
关键词:金岳霖;认识论;外物;唯主方式;无可怀疑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5?0080?04
外物是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历来研究认识论的哲学家无不要面对外物而给予一个界定,有的哲学家以为外物是不存在的,譬如彻底的唯心论者,有的哲学家把外物化进意识里,譬如贝克莱,而有的虽承认外物,但以为什么都是外物,甚至包括意识都是外物,譬如新实在论,当然也有分别承认意识和外物的,无论如何,必须要说感觉意识与外物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复杂的哲学命题,而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立场和争论也足够写一部哲学史了。本文主要探讨金岳霖对于外物的概念,以及他对推理或建立外物的思想根源“唯主方式”的批评,而且我们还将沿着“唯主方式”的内在理路的逻辑发展以找出其何以不能成立的理由,最后分析一下何以人们易于接受有感觉意识,而没有给予外物同样地位的内在心理机制。
一、外物的内涵
金岳霖关于外物的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金岳霖的《知识论》[1]这本著作中,在这本著作中,金岳霖认为外物要满足四个规定:第一,外物是“公”的,不是“私”的;第二,外物独立存在;第三,外物的形色状态是它本来有的;第四,外物在时间的绵延上具有同一性。第一条是规定外物的“公共性”,所谓公共,一方面是同一个外物不是仅仅能被一个个体所把握,另一方面是被把握的这个外物在不同的人那里被认为是同一个外物,而不是不同的外物。第二条是规定外物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包括4个方面:① 包括“独立存在”的概念;② 知道外物独立存在和如何知道外物独立存在不同;③ 如何知道外物独立存在简单,但是理解如何能够知道外物独立存在困难,而且是整个知识论所要讨论的问题;④ 外物的独立存在本身就有知识论上的某一种的假设。第三条规定知识论所探讨的外物主要是日常经验感觉范围内的外物,而不是科学研究中的外物,从这个立场出发,区分外物本身所固有的形色状态和人通过感觉把握得到的外物的形色状态不是一回事,而且前者不是人的感觉所赋予的。第四条规定外物不因其性质和关系的变化而改变其同一性,而且不仅外在于主体的物,包括外在于主体的“他人”或者“其他”是外物的东西,都具有同一性。
从这四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金岳霖的外物观是直接肯定外物的独立存在,这是其知识论的基本立场——朴素的实在论所决定的,站在朴素的实在论的立场上,不仅外物是存在的,而且感觉也是存在的,“有外物”和“有官觉”是金岳霖的知识论所出发的两个基本立场。不仅如此,这四个规定都是针对着“唯主方式”的外物观而言的,“唯主方式”并不一开始就承认外物的有,而是主张通过推论或建立出外物,这种知识论的出发方式正是金岳霖所批判的。
二、对唯主方式的批判
所谓“唯主方式”就是指从主观的或者一时一地的官觉现象出发。以这种方式作为认识的出发方式不仅会造成得不到真正的“非唯主的共同和真假”,也无法保证独立存在的外物。罗素对于外物的追问就是属于这种套路,他从怀疑论的思路出发,首先追问到底有没有外物这种东西,外物是否随我的感觉生灭而生灭,还是说外物仅仅是我幻想出来的东西,又或者仅仅是我梦中的东西,除了外物,还有“他人”,我们只是看到他人是有身体的,但是他人也是有心灵的吗,难道他人不会是一个没有心灵的身体吗?带着这种追问,罗素认为外物作为一个值得怀疑的对象,要展开对其追问就必须找到一个不可怀疑的、具有确定性的出发点。当然,他找到了,他认为这个出发点就是感觉材料,站在感觉材料的立场上,我可以怀疑我面前的桌子是否存在,但是我不能怀疑我看到的颜色和形状,这个颜色和形状就是感觉材料,感觉材料不仅适用于知觉,也同样适用于梦和幻觉,他说当我们梦见或者看见“鬼”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总会有“见”到鬼的形象,虽然我们的确坚持并不存在和鬼的形象对应的鬼的物理客体,但是“鬼”作为梦中或者幻觉中“见”到的感觉材料确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在罗素看来,在追问外物的过程中,感觉材料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是最基本的出发点。但是不是只有感觉材料,而没有外物呢?还是说这些感觉材料本身就是外物呢?罗素跟着这些问题继续追问外物。他举例说,如果我们看到的一个桌子仅仅只是感觉材料,而不是一个物理客体,那么盖上一块桌布,我们就只能看到桌布,桌子作为一种感觉材料就消失了,那么桌布便出于一种“奇迹”而在桌子原来的地方悬空了,这显然是荒谬的;其次,他还认为外物作为一种物理客体的存在,最大的原因在于外物的同一性,存在一个超越于个人特殊感觉材料之外和之上的共同的中立的客体,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追问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存在这样一个共同的中立的客体。关于这个追问,我们很自然就会得到一个答案,不同的人有着相似的感觉材料,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只要是在一定的地点,也会有相似的感觉材料,这就可以假定存在一个共同的持有的中立客体,它超乎与感觉材料之上与之外,从而构成了不同人、不同时间所产生的感觉材料的基础或原因。但是他接着说,这些推理都是在我们假定我们之外还有别的人的情况下得到的,但是我们实际上并不能保证我们之外还有别的人存在,从而以上论证的基础并不牢靠。那么接下来就要追问,能不能证明我之外还有别的人,还是说别的人只是我的幻觉,或者是存在于我的梦里,而这种假设在逻辑不是不可能,但我们也没有理由来证明它就是真的,也就是说,对于别人的存在我是没法证明其为假,也没法证明其为真的。罗素承认这是一个困难,最后他也只好求助于常识或者“本能的信仰”,他说:“从作为一种说明我们生活事实的方法来看,这个假设就不如常识的假设来得简单了,常识的假设是:确实有着不依赖于我们而独立存在的客体,这些客体对我所起的作用就是我们的感觉发生的原因。……我们本来就不是凭借论证才相信有一个独立的外在世界的。我们一开始思索时,就发现我们已经具有了这种信仰了:那就是所谓的本能的信仰在视觉中,感觉材料本身被人本能地信为是独立的客体,但是论证却指明客体不可能是和感觉材料同一的;我们永远部会对这种信仰产生怀疑。这种发型在味觉、嗅觉和听觉的事例在一点也不矛盾,只是在触觉中稍微有一点。然而我们还是相信的确有和我们的感觉材料相应的客体,我们本能的信仰并不因之而减弱。既然这种信仰不会引起任何疑难,反倒使我们经验的叙述简单化和系统化,所以就使人没有理由不接受它。因此,尽管梦境引起人怀疑外部世界,我们还是可以承认外部世界的确存在着,而且它的存在并不有赖于我们不断地觉察到它。”[2](15?16)罗素到最后也没有从感觉材料推出外物的存在,还是归结于常识和本能的信仰。金岳霖在批判以罗素为代表的唯主的出发方式来推论和建立外物的理论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一方面指出从此时此地的官觉很难推出“我”,即便推出“我”,“我”也只是此时此地的我,这个“我”没有多大用途,真正有用的是超越于一时一地的感觉内容又在时间上具有绵延的同一性的“我”,但是这样的“我”是无法从“唯主方式”的立场推出来的;另一方面,从“唯主方式”出发,也无法推出他人的存在。金岳霖认为从感觉内容无法推出他人和外物,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唯主方式”的哲学家以无可怀疑的原则为出发原则。
三、对无可怀疑原则的批判
所谓无可怀疑的原则就是追寻无可怀疑的命题为出发点,无可怀疑的命题也就是自明的命题或逻辑上不能不承认的命题,其目的就是为了求立于不败之地,无可怀疑不是要求怀疑者不能证明他所相信的命题为假,而是要求怀疑者无从怀疑起。罗素对于外物的追求的确是依据于无可怀疑的原则,他所说的感觉材料就是他当做出发点的无可怀疑的命题。而贝克莱的“感知即存在”和休谟的“只有感觉是真实”的推论同样是无可怀疑原则造成的结果。
无论科学研究还是哲学研究,求立于不败之地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都是可以理解并值得同情的,但是求立于不败之地是不是就一定要求追问无可怀疑的命题,二者似乎没有逻辑的必然性。在金岳霖看来,求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可以求助于无理由否定的命题,不一定必须求助于不能不承认的命题。无理由否定的命题也就是不能证明为假的命题,一般的真命题都是这类命题,譬如“1+1=2”“有地球”“我存在”这类命题都是真命题,我们不能证明其为假,但是无可怀疑要求证明其为真,要是自明的或者是逻辑上不能不承认的命题,也就是说不断地追问“为什么知道”,要提供辩护,也就是因为有这样强的要求,求立于不败之地被这类哲学家转换成了求无可怀疑的命题。既然求无可怀疑,肯定避免不了从怀疑出发,用排除法排除怀疑的对象是最自然能够延伸出来的理路。因此,在知识论的研究传统中,怀疑论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怀疑论一般都并非是彻底的怀疑一切,而是为了寻找无可怀疑的命题,寻求知道一个命题为真理由,或者说要求提供辩护。比较有代表性的怀疑论理论如阿格里帕论证,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求无可怀疑的论证,它不断地要求你提供理由来辩护你的主张,不断地提出“为什么”,这样一来,辩护就陷入了一个“无限倒退”;还有一个典型的怀疑论是笛卡尔的怀疑论,笛卡尔认为一切皆可怀疑,我们所看到、听到的、想到的一切都有可能是邪恶精灵制造的幻象,“邪恶精灵说”近代的版本是“缸中之脑”,二者都指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什么存在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所认为的存在的都是值得怀疑的,在逻辑上都有可能是不真实的幻象,因此最后笛卡尔提出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也就是说即便我可以怀疑那些所看所听所思是不真实的存在,但是我不能怀疑此刻我正在怀疑本身,因而我的思维活动本身是确定不移的存在,这样他也就找到了一个无可怀疑的命题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阿格里帕论证还是笛卡尔的论证,其本质上都是求一个无可怀疑的命题,其本质是都是求不断倒退式辩护,阿格里帕的论证是无限倒退的论证固然求不到一个无可怀疑的命题作为出发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实质上也是不成立的,正如金岳霖所言,这种“我思”只是笛卡尔自己的“我思”,只是相对于他个人的心理而言的,对于自己的“我思”,对于他人并不成立,然而笛卡尔对这种责难或许可以辩护,说每个人都可以“我思”,因而实质上这个问题在于“我怀疑”仍然在我的思维之中,我怀疑并不能保证我的思维存在,“缸中之脑”这个论证较之“邪恶精灵说”就更加注重了这个细节,也即我怀疑本身这件事并不能作为我思维存在的证据,它依然有可能是计算机的一段程序和指令,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缸中之脑”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这就如同阿格里帕的倒退论证一样,只要你提出来一个证明之见,他都会归之于链接着我大脑的那台计算机,而我是不知道这台计算机的存在的。从这两个典型的怀疑论的论证来看,沿着这种寻找无可怀疑的命题的理路是不可能成功找到无可怀疑的命题的,最终只能陷入无限倒退之中。因此,在金岳霖看来,寻求不败之地走向寻求无可怀疑的命题是必定是会失败的,哲学家完全可以放弃寻求无可怀疑的原则,而以不能证明其假的命题为出发点,因为这两种出发原则类似于法庭上原告与被告的关系,当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有罪时,被告就没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其无罪,只有原告提交证据证明被告有罪时,被告才会展开辩护,二者的责任和义务都是平等的。而且金岳霖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所从出发的命题大都是我们尚且没有工具证明其为真的命题,所以即便为了寻求不败之地也没有必要诉诸于无可怀疑原则,也即不败之地和无可怀疑原则作为出发原则来看没有逻辑的必然性。
四、有外物
求不败之地既然和无可怀疑原则没有逻辑的必然性,而且从无可怀疑原则出发必然导致唯主的出发方式,从唯主的出发方式是无法推论和建立出外物的,因而这条路子是不通的。在外物之有如何安排的问题上,金岳霖的方案就是直接肯定外物之有,一方面肯定外物之有作为一个真命题而言无法证明其假,也无法证明其不得不真,另一方面我们如果不从唯主方式出发,不坚持无可怀疑的原则,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接受外物之有这一命题,这就如同承认有知识为前提而展开知识论的研究一样,知识论研究并不以知识是有还是无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是肯定知识之有为一基本的立场,肯定外物之有也是一个基本的立场。但是尽管这样说,如果从习惯性的哲学思维出发,直接肯定外物似乎看来仍是一个独断性的判断,为了反击这种习惯性的哲学思维,金岳霖比较了有官觉和有外物这两个命题,也就是要回答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承认有官觉,而对于有外物则有分歧。有官觉和有外物得不到同等的待遇,主要还是由于无论是哲学家还是一般人,都会自热而然地承认:官觉总是在我的,而相对于官觉,外物总是在我之外的,外物即便与官觉同处于经验之内,官觉相对于外物而言是主体自身无法剥离的经验,而外物作为我的身外之物较之我自身的官觉而言,总是没有官觉这种亲切感,用金岳霖的话说就是我的官觉总是我拿它没有办法的事。所以,在追问何物存在的问题上,习惯性的首先承认官觉或者从官觉出发、从“我”出发,也是拿它没有办法的事。在这一点上,外物不可能享受与官觉同样的待遇,这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如果再坚持无可怀疑的原则,那么这种拿它没有办法的事,也就只能被接受为无可怀疑的命题,而“有外物”这一命题当然不可能享受这一待遇。但是金岳霖认为造成这种不同待遇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习惯性站在官觉者官觉的立场上,虽然我们不能不站在官觉的立场上,但是我们不能只站在官觉的立场上,只站在官觉的立场上,外物是得不到的。他要求我们对待外物,要站在外物的立场上,外物的立场和官觉的立场是平等的,如果我们承认有官觉,我们也必须承认有外物。虽然金岳霖对于外物之有绕了一圈仍然回到了立场的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认为他什么都没有说,他至少告诉我们外物之与官觉不平等地位的根源在于人们拿官觉本身是没有办法的,这里的“拿官觉没有办法”也不是一句遁语,实质上就是人类自身对于官觉不能轻易跳出“自我中心观”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又造成了人们不得不习惯性地以有官觉为一基本立场而忽略了给予其他命题以同样地地位,“唯主方式”就是根植于人们自身生理的局限性又循着这种局限性自然生成出来的思维方式。因此,对于“有外物”这样的命题必须以基本立场的形式给予一个基础地位,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唯主的出发方式,超越“自我中心观”,才能真正的解决外物之有的问题。
综而言之,我们看到在金岳霖的知识论中,外物是一独立存在的外物,是日常感觉中的外物,不是依靠推理或者建立而得到的外物,“唯主方式”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而求无可怀疑原则和立于不败之地作为出发立场既没有逻辑的必然性,而且还会掉进辩护的无限倒退的深渊。另外,金岳霖认为无论一般人还是哲学家,之所以习惯性地以为有官觉而不给予外物以同样的地位就在于我们很难跳出“自我中心观”的局限性,所以要真正地解决外物问题,就必须要跳出“自我中心观”,给予外物以存在论的基础地位。总的来看,金岳霖以“唯主方式”标画观念论者可谓是牢牢抓住了其软肋,而对于无可怀疑原则和立于不败之地的出发立场的分析,则具体地挖掘出了其内在的逻辑理路,同时指出“自我中心观”的局限性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展现其陷入歧路的源头,而在瓦解观念论外物观的同时,他也站在朴素的实在论的立场直接肯定“有外物”,这种以朴素的实在论对于西方观念论外物观的破与立,既是20世纪初期中国在认识论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也对于我们当下推进外物问题的研究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金岳霖. 知识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2] 罗素. 哲学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编辑: 颜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