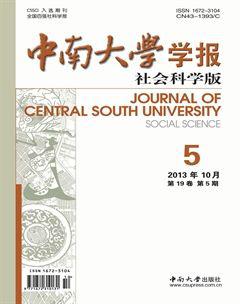“家园体验”与陶谢田园山水诗的文化差异
摘要:在处理人与自然及社会关系的诗学命题上,陶、谢的田园山水诗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性质:田园富于人间情味,与人的关系表现为和谐;山水则突出远离人寰的荒野性质,诗人游赏其间凸显出主客关系的紧张。这与其个性化的家园体验有关:陶在躬耕归隐的田园人生中重构价值依据,获得生命的安顿;谢则徘徊在山林与朝廷之间苦苦寻觅精神的归宿,在情理冲突中提炼出山水幽奇之美。正是这种家园体验的差异造成了田园、山水不同的审美风貌。
关键词:羁旅行役;陶渊明;谢灵运;田园诗;山水诗;家园体验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5?0169?07
陶、谢对举一直是古今文学评论的重要话题①,比较的焦点之一是田园、山水诗在艺术风貌和文化意蕴上的差异。论者多从陶、谢的家世生平、政治取向、哲学思想、审美旨趣等方面来解释这种差异,本文拟从“家园体验”的角度另辟一思路,最终仍落实到田园、山水诗的文本解读上。东晋以降山水思潮渐兴,士人行旅游览即是重要的助缘因素,围绕体验羁旅漂泊与渴望生命安顿这一情理激荡的两极运动,自然作为消解羁旅价值困境、补偿家园失落的重要因素而进入诗人的审美视野,山水就是这种文化心理积淀中家园呈现的最常见的意象形态[1](45?53)。家园感是虚灵的心理体验,它的获得不是廉价的、一蹴而就的,而需要个体反复不懈地亲证体认,这一心灵求索过程凝聚了诗人的独特生命感受,创作个性溶解在羁旅行程的山水观照中,无疑会增加山水美感的丰富性。在山水审美发轫的晋宋之际,陶、谢的田园山水诗奠定了山水(自然)最初的审美范型,这与其个性化的家园体验是分不开的。
一、晋宋之际的诗歌主题
晋宋之际是诗运转关的重要时期,除诗歌沿着自身发展规律在此时逼近发生新变的临界点外,政治时局变动和士人思想观念革新也是潜在的重要文化动因。士族门阀政治体系逐步崩溃解体、寒族势力兴起并最终窃据皇权开始主导权利分配、士族集团内部出现分化并在现实形势逼迫下不得不趋附新的皇权政府,种种矛盾的激化造成政局多故、社会动荡,个体的命运不由自主地牵连其中,常常蹈履危机、险夷难测,士人也就面临着如何处理出处去就、重新抉择人生价值的共同难题。东晋以来士族追求自然与名教合一的理想人格,也由于失去门阀政治依托和玄学思想根基而宣告破产,旧的思想观念受到挑战,刺激着时人从自身不同的思想背景出发思考着解决自我与现实矛盾的新出路。在这种类似的价值困境逼问下,家园体验意味着打破旧有的人格模式,寻觅和重建新的价值安顿方式,因而深刻地反映出诗人各自人生观的差异。同时,晋宋士人思想的矛盾交战,大大丰富了“情”的现实内容,诗性精神趋于复归,从而扭转了玄言文学中理尚玄虚、寂淡寡情的倾向,促使文学观念发生变化,诗歌创作也着力表达出复杂政治环境下的人生体验和理性沉思,再一次回到汉魏兴寄、建安风力的抒情轨道上来。钱志熙先生总结道:“晋宋之际文学的复兴,……作为纠正东晋玄言文学的一种重要的借鉴,正是超越东晋诗风,继承汉魏晋的抒情、缘事、言志的诗歌传统。”“在审美理想上的变化,……就是对于文学的形式与体物的方法的重视,诗歌的体物之功能与形式的美感逐渐取代其情、事、志而上升为主流,标志着艺术精神的变化。”[2](19)从诗歌内容的变化来看,陶渊明的田园诗与谢灵运的山水诗接踵出现,应是中古诗歌史上具有时代影响性的重大事件,尽管当时谢诗风靡一代而陶诗湮没不显,但从总体上看,田园山水诗的确在传统诗歌抒情、缘事、言志的范围外拓展了全新的表现领域,指示了诗歌未来的发展方向。陶、谢在体物尝试和形式美感上各有胜筹和缺憾,表明诗运转关之际诗人把握时代艺术精神的脉搏、草创摸索创作规律时的非同步性:陶诗体现了对魏晋以来抒情诗艺术性与思想性在玄学背景下的最后总结和最高融合,以田园风光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自然美与诗人的性情生活融为一体,陶诗的平淡风格尽管在当时不入主流,却具有时代超前性的美学意义;谢诗更倾向于将玄思与体物造型技巧结合起来,尽管他“解决了客体的发现问题,却没有解决客体主体化的问 题”[3] (210),但其创作实践体现了审美眼光下自然描写经验的巨大进步,确实指明了诗歌革新的新路向。在处理人与自然及社会关系的传统诗学命题上,田园与山水却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性质:田园富于人间情味,与人的关系表现为和谐;山水则突出远离人寰的荒野性质,诗人游赏其间开始凸显出紧张,不得不首先通过玄理体悟而非纯粹的审美体验来化解这种紧张。在自然的这两种分化形态中,陶、谢的生命实践与诗歌创作呈现出复杂错综的面貌,陶“居”于田园和谢“游”于山水的人生样态形成鲜明对比,寓于其中的家园体验也就有各自典型的意义。
二、陶诗的羁旅之叹与家园之思
陶渊明的出仕经历先后有五次,其中以三次入军政要员幕府的任职经历最为重要,卷入了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中[4](67)。作于晋安帝隆安四年(400)至义熙元年(405)的一系列公务行旅诗[5](208?215),记录了陶渊明仕宦经历中的思想矛盾和心态变化,集中展现了他黾勉功业、扬名立善的隐衷志愿,却又倍感身心羁绊,陷入了价值困境的深沉反思,由此引发向往田园归隐和家园安顿的渴望②。如他自己所总结:“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祭从弟敬远文》),羁旅浪游所带来的人生思考可以分剖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在价值实践上对出处进退的犹疑彷徨:
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一)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这是羁旅诗最典型的游于家国之间的抒情模式:一方面以侍亲友于的伦理温情逗引强烈归思,一方面又以阻风穷湖、川涂险远形容自身如孤舟漂泊的苦况,从而“空叹将焉如”有茫茫无所归止之感。这并非简单的仕隐矛盾的牢骚发泄,而是对末世求仕的价值实现之路的反复权衡。三次入幕前后陶渊明都有短暂的归隐经历,之所以隐而复出,除了亲老家贫、迫于生计的表面理由外,也暗示着他应时而出的用世之志。其所依从选择的幕主如桓玄、刘裕等皆是操控晋末政局、声威煊赫的重要人物,任职于其幕中正是期待“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希望能做出一番济世安民的事业。但随着政局变化和幕主个人私欲的膨胀与野心的暴露,陶渐渐觉察到投身政治不仅难有作为,且有蹈祸之危,无法切实安放其素所服膺的儒家情怀,因此每次入幕时间都极短并借故抽身而出。上述羁旅人生的沉重喟叹,隐然与田园隐处的宁静人生对立起来,显示出他在追询精神家园过程中的思考方向。
其二是在价值定位上对“素志”的反省校正、清醒认知直至自觉践行。陶渊明是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屡屡自述“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其十六)、“先师遗训,余岂之坠”(《荣木》),说明其“素志”所秉乃是诗书礼义的儒家仁学,这构成了其价值观的基石。他最初也是遵循时俗常例来从宦求仕的,尽管甫入官场即“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显示出质性自然、不喜拘束的一面,但此时毕竟对中国政治传统的负面根性理解尚浅,对士人传统的价值实现之路也未有根本的怀疑。投身军幕、习染政争的经历使他对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开始有了理性反省,羁旅漂泊经验加剧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也促使他对价值安顿的家园产生冥冥求索。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
“巽坎难与期”不仅指风水逆顺的羁旅境遇,还暗指对政途风波忧患难测的隐忧,田园静好的归隐之愿与人间事务的倦游之叹将诗人抛入取舍两难的境地。此前桓玄势力坐大于荆、江上流,与北府兵及司马元显父子所执掌的东晋傀儡政府之间的矛盾渐趋激化。陶任桓玄僚佐而奉命使都,对其时政局消息或有所知闻,因此在行旅中流露出矛盾的心理。随着桓玄与北府的矛盾公开化,陶进一步坚定了校正素志、投冠归隐的决心。《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云:“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此后桓玄篡晋,劫帝西迁,刘裕扫灭桓玄,携安帝反正,逐渐势倾晋鼎,而军阀派系斗争愈演愈炽。陶知世事不可为,乃将其心事表露如下: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壑舟,谅哉宜霜柏。(《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在当时政局动荡、道义隳颓的背景下,陶渊明对价值定位的思考发生了根本变化:平津仕途既难以走通,就不妨在田园衡茅之中固穷栖迟,保持自身如霜柏般坚贞的节操;不再如传统士人那样注重外在功业以实现自我价值,而转向了个体道德的体认和情志的满足,其思想来源之一是古代经典所记录传扬的仁人志士的道德感召。这种对于宦游仕进的厌倦拒否和养真立善的道德自觉表明,陶已经意识到在腐浊的官场人生和谲诈的政治攻伐之外,士人的精神生命还应别有寄托,须在更高的道义信仰层面确立自我的价值安顿,这便是“诗书敦宿好”所培育出的道统意识的自觉。“道统”指的是“士人文化中价值传承的系统,即‘德性之学之传统”[6](110),与“政统”——专制集权的政治权谋治术、意识形态传统相对。道统代表着儒家的文化理想,但常受到政统的挤压劫迫而蜕变为僵硬的政治意识形态,士人不得不屈从帝王威权而委身求仕,往往失去了以道义制衡专制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同时在士人的精神统系内,追求人格之高扬、精神之弘毅、道义之尊严的自觉意识一直潜存不灭,所谓“道尊于势”,乃成为士人精神血脉薪火相传的重要传统。东汉末士人群体以道义相高、以志节相尚,欲与政统一争知识与思想的话语权,但两次党锢之祸使士人群体精神趋于离散而转向个体自由与超越的探索,道统的承续转入了一种隐性的、迂曲的方式,即林泉隐逸对于政治的批判和道义的坚守。陶渊明身处晋祚鼎革、士风浇薄的板荡之世,军幕羁旅生涯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与道统对立的政统的存在,也进而认识到个体的生命价值和精神安顿须在士人历史文化生命的大传统中方能得到真正落实。这一思想转轨的自觉实践便是在田园隐逸人生中最终完成的。
三、陶渊明田园人生中的家园安顿
不同于羁旅中彷徨犹疑的漂泊心态和惶惶焉如的价值求索,陶渊明在归隐躬耕的田园生活中才真正找到心灵的归宿,与素朴自然的农村生活场景相融合而形成独特的田园人生境界。可从三个方面稍作归纳:第一,远离官场、疏离政治而守拙田园,为其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据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思考视角。明道、势之分,意味着定位人生价值的标准不在现实功利和参与政治,而在道德主体的圆满完善,在此修习过程中获得心灵的自由独立。《归去来兮辞》是与现实政治决裂、走向田园人生的伟大宣言,表达了对先前价值追求的否弃(“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和自主抉择命运的肯定(“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五柳先生传》则以“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箪瓢屡空晏如也”的自画像突出了淡泊自守的性情自足。陶诗屡述饮酒赏菊、乞食安贫,与农人话农事、与知己诉饥寒,皆印证着解脱外在价值束缚后对精神自由的自觉体认和真率呈现。萧统《陶渊明集序》赞其“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惟其抛舍了拘于仕隐出处的功利人生,才能站在超越政统的立场重新理解道统:如《述酒》、《赠羊长史》等抨击篡弑争夺的政治阴谋、歌颂守节不屈的古贤隐者,展示了士人以道义承传为根柢的公义良心;《桃花源记并诗》提出和平无争、良善无伪、无剥削无压迫的社会理想,彻底否定了自秦以来聚敛攻伐、天下无道的专制政治,也以富于诗意的审美意象勾勒出士人孜孜以求的精神家园;陶诗还重新发明了士志于道的精神传统,将个体的道德自砺和人格养炼以诗的形式揭扬出来。如真德秀评:“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揜。《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有曰:‘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渊明之智及此,是岂玄虚之士所可望邪?……又岂毁彝伦而外名教者所可同日语乎?”(《跋黄瀛甫拟陶诗》)[7](卷三十六)安磐也说:“汉魏以来,知遵孔子而有志圣贤之学者,渊明 也。”[8]陶诗的精神深度,正在于平淡无奇的田园生活中寄寓着彰显仁道大义、延续文化命脉的严肃主题。
第二,田园风光成为其化解人生矛盾、消解悲剧意识、将生命引向审美体验的重要因素。陶渊明思想中有浓烈的悲剧意识,《杂诗十二首》其二表露最显,“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历代解诗者以陶有易代之愤而独抱孤忠(吴师道《吴礼部诗话》)[9](584),其实此中孤独悲凉之感慨所系,不在一己之贵贱穷通与一朝一姓之轮替,而在节义大道的层面上思考士人生命价值的终极根据。面对“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悲剧现实,时人操行失守,谬无准的,“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感士不遇赋》)。陶最忧心关切的,乃是士人以道自立维系精神生命之传统的失坠,所以在诗中多次表达矫正时俗、指明大义的素志所在,“斯滥岂彼志,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拟古九首》其二)、“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七首》其四)。就个体的生存境遇而言,这种价值定位的悲剧性又与生死拷问缠结在一起,对有形之生命的觉醒珍视和本体探询,亦成为陶诗的重要主题。《形影神》组诗就是陶以“新自然观”来思考“安身立命之所在”的集中体现[10](223),是遵循玄学理路来解决人与社会、自然关系上由冲突走向和谐的独特见解[11](75?78),陶诗的理趣代表了玄学发展的最后总结。然而陶与东晋玄学名士最大的不同,是将玄理体悟落实为现实实践,在田园生活中拥抱自然、融入自然,将生活细节熔炼为审美体验,从而真正获得家园安顿。辞彭泽令后所作《归园田居五首》首章就展现了一幅鸡犬相闻的田家村朴之景,查慎行评:“‘返自然三字,道尽归田之乐,可知尘网牵率,事事俱违本性。”[12](1),指明陶脱却尘网樊笼后身心获得极大的解放。又如《饮酒》其五写采菊东篱下的悠然“真意”,也是与玄学言意之辨相符的,但给诗人提供归宿感的家园不是虚无难言的玄远之境,而是心远地自偏的“人境”,不是远离人寰的山林薮泽,而是与人交接相融的现实田园,“陶的‘人境具有最实在的实践性”、“是将嵇、阮提倡的合于老庄精神的绝对自由境界与现实人生结合的结晶”[13](190?191)。由于这种极强的实践性和现世品格,田园之美才显得浑厚深广而与诗人的性情相印相通,那些写景佳句才呈现出极富情韵的自然美感:“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时运》)、“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和郭主簿二首》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这种物我的交融映衬反映了其时自然审美意识的别样发展路向,与大谢山水迥然异趣。同时,生死的悲剧叹问也在田园风景中得以化解了,如《游斜川》因“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而会友同游,最后在“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的山水游赏中纵情散忧。有时田园景致又与饮酒所得的审美体验相交汇,如《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己酉岁九月九日》等,醉中的心灵解脱与自然观感涤荡了人生的悲剧感,而代之以一种人格升华的艺术显现,“是抗衡污浊现实的永恒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理想”[14](105),这也就是陶渊明田园人生中的精神家园所在。
第三,田园能够支撑陶渊明全部价值安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躬耕自足的生命实践。士人承担着道义的文化使命,但在现实政治形势和个体生存境遇中,口腹生计之患往往使道义承传蜕变为利禄之学,极易丧失独立抗争的立足支点,道也就只能在政治夹缝中委曲求全,由此延伸而来的思想胁迫和人格扭曲更是不可胜计。田园躬耕虽不足以抵抗政统对道统的全面钳制,却可使个体的生命在田园生产活动中获得实在的依托,从而解决出处矛盾和价值安顿问题。《劝农》:“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弗履。”即认识到儒门中人皓首穷经、不亲稼穑的固有缺陷,提出“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陇亩”的理想,使士人的人生视野不再只局限于经术治道而引向了一个全新的天地。陶集中《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皆详述躬耕的筋力劳苦和内心愉悦,道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的朴素真理,至此虚浮漂荡的人生方有现实的着落之处。黄文焕《陶诗析义》评:“躬耕之内,节义身名,皆可以自全,纵不能为颜子,不失为文人。”[15]躬耕对于士人立身处世的巨大意义,绝不仅是保身全生顾全节义,而是以曲线而积极的方式来实现道统在内心中的自觉坚守。《归园田居五首》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其中有对农耕生活极其真实的体验,而内中隐藏着坚定此志、自足无待的深意,深知渊明的苏轼感叹道:“以夕露沾衣之故而违其所愿者多矣。”无违的志愿就是审美生命中的道德升华和心灵体认。总之,陶的躬耕实践“将消极、冷性、懒散的隐士人生形态,转化为积极、乐观、勤生的田园人生形态;又将儒家道统置于一个绝对清净、自本自根的实践人生中”[6](124),这是陶渊明依托田园而构建价值依据、获得家园体验的一大创造,也是其诗富有人间情味、平淡自然而真淳厚朴的重要源泉。
四、谢灵运羁旅山水中的家园寻觅
与陶相比,自然山水在谢灵运诗笔下更多是山林气,而非田园气,这与其社会地位、生活经历、气质性情、思想倾向有关,也使其寓于山水中的家园体验判然有别。钱穆先生曾比较说:“田园中人,一面亲就自然,一面又能在人文陶冶中,乃始是理想人生。”“谢灵运诗:‘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写境精妙已极。王维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写景清绝之至。此两诗,一片天趣,却少世情。缺乏世情,终非最上乘的诗。亦非最上乘的人生。在此孤屿之上,空山之中,惜乎放不进人文圈。放进了人文圈,此自然圈之精妙清绝便会破坏消失。故不如陶潜与其他田园诗人所咏,能使人文圈与自然圈相得益彰,融成一体。”[16](12?13)钱先生的话极深邃精辟,道出了中国人在现实人生中安放精神家园的最上乘、最理想的状态,田园便是农耕社会中最富有诗意、最能承载文化理想的家园。而山水美的最初定位,则是以远离人际、缺乏世情的面貌来呈现的,刻意摒除世俗情味,正突出了山林作为诗人寄意精神超越之所的美感特质,是与庄玄精神相通的“天趣”。故早期山水诗境以精妙清绝、夐然孤迥为高,体现的是一种由凡入圣的精神追求,从大谢的永嘉山水到王维的辋川山水,都是循此思路的同一品格。
由此来看大谢的羁旅山水,一方面是远绝人寰寻访幽僻,以乏世情的孤傲姿态来化遣人间烦恼,企图寻找精神家园的安顿,另一方面又无法泯除现实政治功名的牵累和内心情理的激烈冲突,因而不断地自我放逐和苦苦寻觅,总是处在动荡漂泊的游旅生存状态中,暗示着家园体验的失败和幻灭。弃绝人间情味的代价,便是发现了山水的幽奇之美并以诗笔创造出谢氏的精妙山水诗境,这一悖论的求索即构成了大谢山水的内在基本矛盾。谢灵运早期的公宴、酬赠诗中已有山水描写的萌芽,如《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其渊源是建安诗人邺下群集、西晋诗人祖饯赠答以及东晋殷仲文、谢混等的宴游诗,山水背景尚未远离人境;永嘉之贬是山水诗正式形成的重要契机,借助行旅游览,诗人的足迹视野遂远涉荒僻之地,锻炼出幽峭奇险之景,施补华《岘佣说诗》云:“大谢山水游览之作,极为巉峭可喜。”[17](976)“巉峭”一语可谓精准评价。有论者指出:“此后在归隐始宁,征召赴京,二度归隐,外放临川时,行旅与游览更成为难以分割的模写山水的两种基本形式。至此谢客山水由宴游、特别是行旅诗中蜕出当无可疑。”[18](305)行旅作为山水诗创作动力的源头之一,实包含着在旅途中通过山水审美来满足涤洗烦累、寻求安顿的精神需要。初离都赴任之际,谢的赠答诗即流露出失路远谪、家园何在的怨愤,“如何怀土心,持此谢远度”,“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瓯越。解缆及潮流,怀旧不能发”(《邻里相送至方山》),怀愤寻幽一直是其此后羁旅中的情感主调,而这种追寻安顿的心理诉求也逐渐呈现在大量的山水游览和精细描绘中。如《过始宁墅》:
束发怀耿介,逐物遂推迁。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缁磷谢清旷,疲薾惭贞坚。拙疾相倚薄,还得静者便。剖竹守沧海,枉帆过旧山。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葺宇临回江,筑观基曾巅。挥手告乡曲,三载期归旋。且为树枌槚,无令孤愿言。
尽管诗中自陈逐物仕宦有违自己幽栖归隐的志愿,在诗末还许下任满还乡养老终死的誓言,但诗人内心并不平静,诗中铺陈在山水间沿洄登顿、顾盼踟蹰的所见所感,与首尾的述志自白相映衬,泄露了他心有不甘又幽愤难遣的隐衷。出守永嘉是受到权臣徐羡之、傅亮的排挤,也是谢氏家族在刘宋皇室权利斗争中失势的缩影,这对于心高气傲的谢灵运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打击,尤其是回到父祖经营归葬之所、代表了谢氏在晋世彪炳勋业的始宁故宅,这种复杂的情感便更是难以化遣。政治失意造成价值确认的失落,也暗示了家园的失落,山水不仅传达了挂帆沧海、山水登涉的行旅境况,也成为抚慰、化解诗人内心郁结的重要补偿因素。“白云”一联作为状景的迥秀之句为人称颂,不但取色鲜明,字眼清奇,还将诗人傲兀不群的性情襟抱烘托出来,陆时雍评:“语何悠旷,外有物色,内有性情,一并照出。”[19](卷十三)山水在这里就有了别样的意味,既是耳目感官所发现的新奇之景,也是情理转化、融情于景的重要媒介。赴任永嘉途中以及在郡内的山水游历,使大谢山水诗创作数量激增,佳句名篇焕然涌现,羁旅山水的抒情体势逐渐定型成熟,而追寻家园感的理悟思路也在不断强化。姑以其仕宦晚期的《入彭蠡湖口》为例:
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缀流温。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由于受到会稽太守孟 的参劾,谢不得不驰赴京师辩诬自赎,接着即被派任临川内史,这无异于受到监管和闲置,政争的险恶、仕途的挫折,都加深了他的苦闷。此诗以孤客倦游起首,历述洲岛回合、圻岸崩奔的行旅苦况,点出他此时千念万感的不平静心绪,苦苦思索着这个“难俱论”的悲剧性人生。“事多往”、“理空存”是诗人面对万古江山而发出的理性叩问,却得不到理性的回答,正如他在山水行旅中一直追问寻觅的,其实连他自己也恐怕说不清到底在追问寻觅着什么。结尾在夜色江景中透露出思乡归隐的浓浓忧思,尽管强作旷达,但仍表现出家园难觅的失落之慨。山水物色在此诗中既有阔大的外围空间,也有精致的细节描写,且与首尾灌注的郁勃不平之气相融汇,悟道的理语已自然交融在情景之中了。黄子云《野鸿诗的》评:“康乐于汉魏外别开蹊径,舒情缀景,畅达理旨,三者兼长,洵堪睥睨一世。”[17](862)这显示出大谢羁旅山水诗日渐老熟的特征,从拖着“玄言尾巴”更上一层进境。
在这些羁旅山水诗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谢灵运自觉地对山水追赏、冥赏,以获得审美愉悦和心灵的超脱。如初至永嘉郡的《晚出西射堂》:“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石室山》:“灵域久韬隐,如与心赏交。合欢不容言,摘芳弄寒条。”《游南亭》:“逝将候秋水,息景偃旧崖。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隐居始宁时的《田南树园激流植楥》:“唯开蒋生径,永怀求羊踪。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受召赴京时的《酬从弟惠连五章》其一:“岩壑寓耳目,欢爱隔音容。永绝赏心望,长怀莫与同。”《石门岩上宿》:“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这些反复出现的心赏冥悟,有的是发现山水胜景佳致时的欣喜自得与孤独自赏,有的是期待知己良友能共赏此刻的美景欢乐,有的还与慧远“庐山净土法门的观想修行方式一脉相承,具有神秘的性质”[20](79),显示出大谢在山水中向往净土感悟佛理的独特体验,总之是以一种向外寻求确证的心态来处理外物与内心、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希冀在宗教的或审美的体验中使自我摆脱烦恼,达到与外物和谐随顺的自由状态,这其实也是一种向往家园寻求精神安顿的表现。诗人因现实的挫折而自我放逐,企图抛舍一切系累挂碍而追求与道冥一的超越境地,他渴望获得理解和安慰,山水即被视作有灵的知己而与主体产生了精神交流,山水中的自然生机与生命辉光,照亮了久为世俗功利所窒塞的心灵,因此在那些刹那兴悟所获致的山水佳句中,诗人抓住了自然最深刻隐秘的天机与“道”,在审美体验中使自我的精神得以疗救,获得了暂时的止歇与安顿。与陶渊明的走向田园取径不同,他所选择的是“置心险远,探胜孤遐”的方式[21](540),在密林深谷、曲涧幽壑之中流连盘桓,通过超脱俗世是非利害、以定生慧的审美观照,把山水看作是净化心灵获得解脱的通道。因此,山水作为心赏的对象,就是要突出其杳冥迥深、远绝人境的性质,诗人深入山水行旅游览的过程,即是隔绝外界尘杂的侵扰,进入到一种冥神寂想、虚志抱一的心境之中,从而心灵由晦暗转为光明,现实得失的沉溺也变为人生真谛的豁然朗照,证成主体脱凡入圣的精神洗礼和自我超越。陈祚明说:“其钟情幽深,构旨遥远,以凿山开道之法施之,惨澹经营之间,细为体会,见其冥会洞神,蹈虚而出,结想无象之初,撰语有形之表,孟 生天,康乐成佛不虚也。智慧如此,所证岂凡。”[21](519)沈德潜也说:“前人评康乐诗,谓东海扬帆,风日流丽,此不甚允。大约经营惨淡,钩深索隐,而一归自然,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22](196)都指出谢诗内蕴深厚、思理曲折的特点,这也是他以山水观照体验家园感的独特方式,与陶诗的淡泊宁静大异其趣。
五、结语
谢诗中大致固定的心理流程可概括为:怀愤寻幽、耳目游观、悟理化情。首先是为摅泄积愤而构成行旅的动机,并指引着游览的方向;其次是全面调动耳目身心对山水作立体观照,刻意抉险搜奇、寻幽探胜,使家园寻觅的欲念凝冻在山水秀句之中,获得忧思的纾解和情绪的畅适;最后是由山水赏悟进一步提炼为理性的认知与顿悟,舍弃缠绕心头的俗累世情,达到“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的澄明境界。现实的激愤失意在此得到淡释,但所依托的玄佛义理并不能完全填补他的价值失落,所以只能反复投入山水中,不断地对人生秘奥和精神安顿作苦苦探求。由此情理显隐的诗思线索有时也会变得复杂,一方面固然使诗歌须以多层结构来组织安排情景事理,突破了建安以来较为简单的咏怀模式,使诗人的才性气质和诗艺技巧得以充分表现;另一方面也使主体与山水始终处在形神间隔的状态中,无法达到陶诗那样的物我交融,山水只被认作导泄郁愤、体认理悟的媒介,最终还是要将诗旨落实到那“畅神”的“理”或“道”上。大谢身上高门世族的符徽使他终难以跳出现实政治与功名追逐的网罗,深厚的才学与颖悟的哲思又使他在精神领域总保持着一种力求超越的应对姿态,这种矛盾深刻地影响着他对山水的观照态度,山水诗创作仍浮于对外在自然和表层人生的书写,并引向对形上问题的哲学思辨,但文学手段所负载的一系列反省思考并未能转化为一套适用的、成熟的人生哲学,从而成功地支配、引导、调适其内在精神世界,所以他一直都在寻找家园,踽踽不安,最终以弃市悲剧收场。《临终诗》:“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下泯。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其愧悔憾恨之情溢于言表,然亦终未能大彻大悟,所谓期待来生,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期待和抚慰罢了。反观在当时备受冷落的陶渊明,则通过田园躬耕、饮酒赏菊的人生实践形成了独特的处世哲学和价值体系,因此能在恬淡自足的田园人生里构建自身存在的意义,在汹汹乱世里树立了士人对精神家园孜孜以求的特异形象。陶、谢对待自然的眼光以及从其人生形态所衍化而来的田园、山水诗歌,折射出“居”与“游”、仕与隐等价值取向的扞格,唐人始调和仕隐对立,田园山水诗也渐趋合流了。
注释:
① 南朝至盛唐,陶诗不受重视,论者多以“颜谢”、“鲍谢”并举。杜甫始称“陶谢”以肯定陶及其诗的地位:“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夜听许十诵诗爱而有作》)、“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此后陶愈见尊崇,声名盛过谢诗。今人关于陶、谢的比较研究,自袁行霈《陶谢诗歌艺术的比较》(《九江师专学报》1985年第1、2期合刊)、孙敏强《陶谢山水田园诗差异论》(《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以后成果蔚然,专著则有马晓坤《趣闲而思远:文化视野中的陶渊明谢灵运诗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白振奎《陶渊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等,兹不详述。
② 还包括时地系年未确的《杂诗十二首》其九、其十、其十一,参见王国璎《陶诗中的宦游之叹》,《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 程磊. 羁旅山水与家园体验——论羁旅行役诗中家园感呈现的意象形态研究之一[J].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1): 43?45.
[2] 钱志熙. 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3] 张国风. 传统的困窘——中国古典诗歌的本体论诠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4] 袁行霈. 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A]//袁行霈. 陶渊明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5] 逯钦立. 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A]//逯钦立. 陶渊明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6] 胡晓明. 陶渊明与儒家“德性之学”[A]//胡晓明. 诗与文化心灵.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7] (宋)真德秀. 西山文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8] (明)安磐. 颐山诗话[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0] 陈寅恪.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A]//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 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11] 程磊. 论陶渊明的价值选择和生命境界——以《形影神》为例[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6): 75?78.
[12] (清)查慎行. 初白庵诗评[M]. 上海: 上海六艺书局, 1912.
[13] 傅刚. 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M].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
[14] 冷成金. 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修订版)[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5] (明)黄文焕. 陶诗析义[M]. 南京图书馆藏明末刻本.
[16] 钱穆. 双溪独语[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
[17] (清)王夫之. 清诗话[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18] 赵昌平. 谢灵运与山水诗起源[A]//赵昌平. 赵昌平自选集.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19] (明)陆时雍. 古诗镜[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李炳海. 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J]. 学术研究, 1996(2): 79.
[21] (清)陈祚明. 采菽堂古诗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22] (清)沈德潜. 古诗源[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