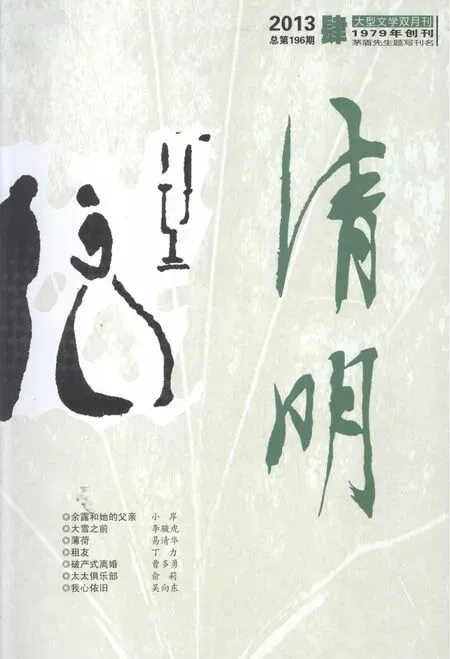口语化对新诗发展的革命意义与原创价值
杨四平
好诗不分新旧,不分中外,不分雅俗。大家公认的好诗,没有什么时代、民族、地域、题材、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区隔。尽管含蓄有含蓄的美,明白有明白的美;但是,人们总是倾向于大面积接受那些明白晓畅的诗,白居易和艾青的接受度要高于李商隐和穆旦的接受度。口语化与书面语化/共同语化/普通话化是诗歌发展历程中此消彼长的两极:口语化过于发达后,人们就要求书面语化,反之亦然。就百年新诗发展而言,口语化与书面语化是二元对立的。它们之间不存在价值等级上的优劣,而仅仅是审美趣味不同而已。不过,依据当初新诗的理想“我手写我口”来看,口语化似乎应该成为新诗发展的主流。
本期所选三位诗人的作品,在口语化态度和程度上不同。在谈他们的写作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楚,为什么新诗写作需要口语化?口语化对新诗写作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众所周知,艺术的本质与其说是创造,不如说是不断地发现和“给出”;艺术并没有给世界创造出新东西,而仅仅是把长期被忽视的东西呈现出来,用艺术之光照亮那些在黑暗中的事物。新诗写作既要面对几千年来的古典诗歌传统,又要面对新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诗传统”,也就是说,新诗写作要警惕那些司空见惯的语言、意象、象征、语境、氛围和内涵,使之陌生化。新诗与古诗最大的区别是,从以往的“字本位”转向“音本位”,从“文字中心”转向“声音中心”,从以书面语为主体转向以口语为主体。五四以来的“汉字革命”、“语文革命”和“文腔革命”既昭示了这种新诗语言的流变,同时也不断提示我们语言与思想的一体性,也就是说,对于新诗写作而言,语言既是工具性又是思想性的,即“器”与“道”合二为一。一句话,新诗写作的至高目标是“言文一致”,而口语化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方案。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目标出发,从指尖上的口语出发,评价本期的这些诗。
其实,这三位诗人的诗风差异很大。我之所以把他们放在一起来谈,是因为他们在对新诗语言的认知及处理上各有千秋,刚好体现了新诗诗人对“我手写我口”的理解和表现的差异性。如果单从对新诗语言的自觉程度来看,郁葱较为明显,徐春芳次之,而谢克强不明显。具体来说,郁葱的诗较好地体现了新诗语言的“道器观”。郁葱对词语比较敏感。尽管郁葱对口语与新诗的关系没有明确的表述,尽管他在这几首诗里反复提到的“词汇”与新诗语言,尤其是与口语化的新诗语言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我还是愿意从口语化的向度上来谈论郁葱在新诗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自觉的自觉”。而诗歌的这种不自觉就是它的自觉,或者说,诗歌的自觉也是它的不自觉。在《私密空间》里,郁葱关注“这些与身体有关的词汇”,“保留着,那些依然有热度的词汇”。也就是说,郁葱对种种具有生命体温、心跳和私密的语言始终保持着诗人独有的隐秘的激情。这些或那些“没有割舍”掉尘世冷与热的词汇,就是我们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活生生的生命密码和生存信息。它们抵御来自外在器物的、制度的和文化的规约、缩减和命名。它们总是以最感性的口语状态反抗着最理性的书面语状态,正如郁葱在《静静生长》里所说:“单纯,不经过大脑/那些有命运的词汇”。口语是最原始的,与时俱进的,也是最丰富和最活跃的;而书面语是第二手的、第三手的、第N手的语言,是固步自封的,也是永远落后于、少于口语的。“心口不一”是一种常态。我们“写”下来的东西永远少于我们“说”的东西。而且写下来的东西,被固化下来的思想,渐渐使人习以为常,使人心智变得麻木,因而缺少“敏感与痛感”,缺少哭泣与欢笑,就像郁葱在《欲望的注视》里所说,这种情况可能是一种“现实”,但不一定“真实”。其中的哲学意味较深,因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在此就不展开了。口语“单纯”,但不单调。口语一旦经过大脑处理成书面语,意味着它就死亡了,它的命运就终结了,同时,也就意味着新的口语要诞生了。我赞同郁葱在《经年》里讲的“简单,生活化/不停地被托起,不停地被淹没”。此乃口语命运的沉浮,而“简单,生活化”则是它的主宰。因此,郁葱呼吁诗人从文绉绉的书面语和标准统一的普通话/共同语回到“粗粝”的活生生的口语,从“文”走向“言”,最终实现言文统一。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口语不等于诗歌,口语本身不是诗歌,只是说,新诗语言的口语化是新诗写作的追求。我们必须对口语进行加工、转化、提炼,只有这样“诗化”的口语,才能具有郁葱在《日常的转换》里所说的“那种穿透力,简单纯粹”。显然,那些常常被人诟病的所谓的“生活流”的诗,“下半身”的诗和“口水诗”就是因为把口语混同于诗歌而变得十分的琐碎、乏力。不同于郁葱寻找与生命呼吸节奏同步的“词汇”,徐春芳的组诗《在大地上》专注于感伤性的浪漫主义。他把爱情视为一种圣洁的宗教般的信仰,就像当年沈从文要在湘西用文字“建一座希腊小庙”那样,徐春芳的这些诗力图筑起一座爱情的寺庙,他与他的爱人要在里面穿越时空、超越苦乐地“修习”爱情,把磨砺爱情当做自己一生的课业,从而使“爱的话语”熠熠生辉,使“我的爱轮回不尽”(《如梦令》),同时,也将以此阻止“仇恨的话语提起利斧”(《倾听或祈祷》)作为自己的担当。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徐春芳诗歌的主题词十分明确,因而他的这些诗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在新诗语言方面,他还是有一些自觉追求,一些不同于郁葱那样的新诗口语化的追求,那就是他的诗歌语言具有浓厚的书面语色彩。比如,《杨柳岸》以一句引语“是的,记忆的灰烬带着余温/泪水的珍宝闪耀在我的手心。”起始,其中还有像“蝉们”这样的欧化语言的复数,此外还有汉语成语如“永无休止”、“恍如隔世“、“两手空空”,以及对文言词语的大胆启用,这些新诗语言的书面化要是放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一定会被瞿秋白指责为“新文言诗”、新贵族诗。近年来,在文化全球化的冲击下,社会上涌现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潮,受此影响,诗坛上也出现了文化复古的诗象,除了一些明目张胆的“新文言诗”、“新古体诗”外,有一些新诗人写诗,在现代汉语的诗句中搀杂大量的古典文化和诗词里的“典故”,更有甚者,这些典故的“注解”居然在文字和篇幅上远远大于新诗本身,这种掉书袋的、假古董的、伪文化的所谓的新诗写作,明显走上了新诗的歧路,因为它们与“我手写我口”、“言文一致”的新诗理想背道而驰、渐行渐远。这是值得警惕的。谢克强的诗具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风格”,其中的理想主义至今依然鼓舞人心。《灯塔》、《路灯》和《墙上的钉子》具有互文性,都是写信仰及其可贵的坚守。谢克强的诗歌语言也是以口语为主体,但是经过了政治化、历史化和哲学化的激情处理,因而那种口语本来应有的原汁原味就被冲淡了。
我们应该避免对口语与新诗的关系做狭隘的理解,当然,也要避免把口语等同于新诗语言的错误理解,重新认识口语与新诗之间的“道器一体”观念,以及口语化对新诗发展的革命性意义和原创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