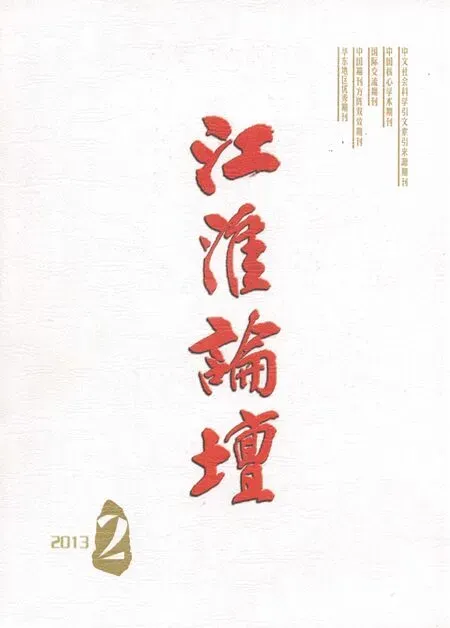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主导因素及其演变*
蔡长青
(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合肥 230601)
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主导因素及其演变
蔡长青
(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合肥 230601)
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先后有三种主导因素对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分别是文化权威、政治权威和市场权威。由于主导因素的变迁,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也随之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关于评价机制的主导因素及其演变的研究有助于对中国现代作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定位。
评价机制;文化权威;政治权威;市场权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往往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较大的变化,有时甚至是天壤之别。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文学史就是现代作家的沉浮史。这就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很难对一个作家进行全面而准确的评价。这种现象的出现从表面看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实际上,其背后还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显然离不开一定的评价机制。作家的评价机制是文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往往会决定一个作家的名望和文学地位。一般来说,作家的评价机制应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评价的作用。但由于现代中国的特殊情境,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常常处于动态的演变之中。既然评价机制发生了演变,那么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出现变化也在情理之中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因素是复杂多变的,但真正对评价机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主导因素只有三种:文化权威、政治权威和市场权威。由于这三种主导因素的变迁,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也随之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一
由知识分子参与并发动的新文化运动对后来的新文学作家的评价机制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由此产生的文化权威在“五四”乃至“五四”后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评价的主导因素。
毋庸置疑,“五四”是现代文人的黄金岁月。这场由文人发动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直接造就了一大批文化权威。何谓权威?詹姆斯·科尔曼有过非常精辟的论断,他说:“具有权威地位的人通常拥有大量资源,他寄极大的期待于使用这些资源,因此,如果不服从这种权威,后果将极其严重。”科尔曼的解释指出了权威的基本特征:一是拥有大量资源且处于核心位置,二是要主动使用这些资源。由此看来,“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郭沫若、李大钊、茅盾等人都曾先后成为文化权威。他们或指点江山,或激扬文字。他们往往站在社会制高点,振臂一呼,响者云集。这些文化权威们都毫无例外地关注和指导过新文学的发展。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尽管文化权威们对新文学的把握水平各异,甚至存在外行指导内行的嫌疑,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权威性。
文化权威们的巨大影响力不仅仅来自他们的核心位置,更来自他们手中的文化资源。“五四”时期的文化权威们往往会借助自己掌控的现代期刊来扩大其影响力。如陈独秀之于 《新青年》,鲁迅、周作人之于《语丝》,茅盾之于《小说月报》……新文化权威与现代媒体的相互结合对“五四”作家评价机制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五四”作家的出道与成名大都与这些媒体的推介有关。如《新青年》对于鲁迅,《晨报》对于冰心,《小说月报》对于丁玲,《创造》等创造社刊物对于郭沫若、郁达夫……此外,现代出版机构也加强了与文化权威们的合作,在推介新文学作家及其作品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如商务印书馆、北新书局、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开明书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说到新文化权威与现代媒体的结合,茅盾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茅盾1916年入商务印书馆工作。1920年受命改革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并把它变成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主要阵地。他不仅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1927年茅盾在《小说月报》发表了长篇论文《鲁迅论》,对鲁迅及其作品第一次作了全面评价,这也是现代文学史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作家论。由于论文作者和论述对象均为“五四”时期的文化名人,其权威性和影响力不言而喻。茅盾还对“五四”时期的其他重要作家如冰心、庐隐、许地山、徐志摩等专门做了评论。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学评论家,茅盾的作家论对这些作家的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四”时期形成的这种以文化权威为主导的作家评价机制,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作家的评价起着潜在的影响。
1935至1936年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显然是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全面检阅。为了扩大这套丛书的影响,赵家璧精心策划运作,特意邀请了当时文化界权威参与编写。蔡元培作总序。全书共十卷,分别由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朱自清、洪深、阿英编写。我们不难看出这一串名单的权威性。除了蔡元培应景式的总序外,其他十位文化权威直接参与了大系的编写工作。按照统一的编写体例和要求,每位编写者各负责一种文体,在编选具体作品之前,每人须完成一篇导言。无论是导言的撰写,还是具体作家作品的编选,都不可避免涉及对作家的评价。如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中就对弥洒社作家、狂飙社作家、新潮作家、莽原社作家、乡土文学作家等进行了凝练而准确的评价。在作品的编写数目上也能体现编选者对作家的的评价高低。郁达夫在《散文二集》中总共选取16位作家的131篇作品。其中,鲁迅24篇,周作人57篇。周氏兄弟占了一半以上,这也客观反映了当时文化界对周氏兄弟的推重。而郁达夫对鲁迅、周作人、冰心、朱自清诸作家的独到点评已成为经典。事实上,由文化权威们参与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已不仅仅是一部作品选集,同时也具备了文学史的初步特征。其中关于“五四”作家的评价和定位对后来的文学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不同于文化权威的形成,政治权威所依赖的不是文化资源,而是政治资源。以政治权威为主导的作家评价机制就是指借助政治权威的力量来决定或影响作家的评价标准。在现代中国,由于特殊的情境,政治对文学的介入已是不争之事实。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政治化不断加强的过程。大革命失败后,在经历短暂的低潮后,无产阶级文艺开始兴起并最终成为三十年代最有影响的文学思潮。“五四”时期的文化权威们不得不面临严峻考验并随之发生分化,或转向革命阵营,或转向自由主义阵营,或投向反动阵营。其实这种分化早在“五四”退潮时就端倪初现。随着政治权威的彰显,一种以政治权威为主导的作家评价机制逐渐形成。这种评价机制在“左联”时期起到了令人瞩目的作用,当然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的《讲话》进一步确定了这种评价机制,“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使之合法化、经典化。有了这个评价机制,我们就不难理解同是解放区成名的作家,赵树理和孙犁却在评价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是一个作家,丁玲的前后期小说创作却有天壤之别。而王实味的悲剧命运或许能找到一点原委。这种评价机制轻则影响作家的文学地位,重则影响作家的前途及命运。从延安时期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因这种评价机制而导致的文人苦难比比皆是。
说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政治权威,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周扬。无论从政治还是从文学角度,周扬出道都不算早。“左联”成立时,他还在日本参加左翼运动。1933年前他一直未能进入 “左联”的领导层。而当他成为“左联”领导后却仍然遭到以鲁迅、胡风等人的强有力的挑战,并因鲁迅的那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遭受重创,使其在文艺界的威性大大降低。应该说周扬是在非常失意的情况下奔赴延安的,没想到很快得到毛主席的信赖并被委以重任。这种知遇之恩使周扬没齿难忘。于是,当他编译《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时,就很自然地把毛放在马恩列斯之后。而对于毛主席的《讲话》他更是推崇备至,毫不怀疑地授受,不折不扣地宣传贯彻,并成为它权威的解释者、捍卫者。应该说此时的周扬已具备政治权威的身份。这种权威在1949年后进一步得到强化。尽管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他与郭沫若、茅盾一起成为大会引人注目的三巨头,但由于来自延安解放区的天然优越性,周扬实际上是执行文艺政策的最高领导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当时的作家,他已具备生杀予夺的权力。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重要文学事件中(如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我们都能看到他频频出现的身影。应该说周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家,他是代表政治家在行使“文艺总管”的职能。而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这个“文艺总管”还是较为满意的。1942年整风期间,毛泽东与丁玲交谈时说:周扬还是懂一点逻辑的,他的长处是跟党走。周扬也说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紧跟党走。正是依靠这种优势,周扬能够长期在文艺界担任权威的角色。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是中共文艺政策尤其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忠实执行者。他可以凭此向文艺界发号施令,甚至决定作家的地位和命运。总之,这种以政治权威为主导的评价机制曾深深影响了现代作家的命运。
三
市场因素对作家评价的影响由来已久。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市场对文学的介入愈加明显。但这种影响在现代文学诞生之初以及相当长的时间内的作用是有限的。由于现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特殊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因素在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中难以成为主导因素。市场权威真正主导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在经济领域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市场经济大潮开始冲击中国。这场变革的影响并非局限于经济领域,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确立,代表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需求的大众文化开始崛起。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政治权威相对淡化,传统的精英文化日益式微,市场权威开始彰显。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权威所带来的冲击几乎横扫一切,它对人们的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影响已成为无须争辩的事实。与文化权威和政治权威不同,市场权威并不体现为特定的人或力量,它主要体现为一种价值取向,即以市场为主导,以赢利为目的。市场权威评价一个作家的主要依据就是市场的认可度,具体一点就是其作品的销量(网络文学就是点击量)。市场权威一旦成为作家评价机制的主导因素,它就有可能对传统的文化权威和政治权威进行挑战,甚至是颠覆,从而对作家的评价产生影响。
说到市场权威对作家评价的影响,金庸显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金庸从事武侠小说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他已完成其主要代表作品。但其作品真正被大陆接受却在八十年代后,内地出版的第一部金庸小说是 《书剑恩仇录》,1984年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广州分社出版。不久,内地数十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其中《射雕英雄传》就出现7个版本。金庸的作品虽受读者认可,但当时的文学评论界几乎保持沉默。而大陆最权威的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还专门就金庸的小说来痛斥武侠小说的“泛滥”。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市场对金庸的追捧开始势不可当。北京三联书店正是看中了金庸作品的巨大销售市场和盈利空间,于1994年将金庸作品汇编成集进行捆绑销售,一经上市,便成为畅销书。2000年,三联书店再次根据市场需要,推出了金庸全集“口袋本”,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印数达到56000套。随着市场对金庸作品的认可,以严家炎、冯其庸、孔庆东、陈墨等为代表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并出版了相关学术成果,“金学”研究也蔚为大观。而各类高校开设的相关选修课也是丰富多样。其代表作品《天龙八部》的部分章节还进入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金庸开始成为文化热点人物,其文学地位也出现上升之势。1994年,王一川等著名教授在为20世纪文学大师排座次时,金庸名列第四,仅次于鲁迅、沈从文和巴金。同年,金庸被聘为北大教授。2004年的第三届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显示,金庸取代老舍成为了北京读者心目中的最爱。凤凰卫视“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在北大举行,金庸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从金庸文学地位的上升来看,市场因素显然起了主导作用,尽管其中少不了文化权威(以专家学者为代表)和政治权威(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的认可。由此观之,市场权威与文化权威、政治权威的关系有时是相当微妙的,它们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
但并非所有的作家都像金庸这般幸运,贾平凹在出版《废都》后就遭遇了无处容身的痛苦。在出版《废都》前,贾平凹的创作一直得到较高的肯定,但在《废都》出版后这一切发生了变化。这部作品的出版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它的出版激起了知识界的众怒,贾平凹和《废都》几乎遭到了不容置疑的讨伐。另一方面,《废都》自出版后一再畅销并被盗版,大有洛阳纸贵之势。据有关资料统计,《废都》公开出版应在150万册以上,而盗版却有1200万册左右。批评界的讨伐与大众的认可形成了奇特的文化景观。“《废都》现象”的背后实际上体现了知识文化权威与市场权威的交锋。而结果却是日益强盛的市场权威借助传媒的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影响了对这一现象的冷静思考。当然,市场评价机制是否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客观公正对待每位作家,已引起了当今学者的深深忧虑。“通过贾平凹《废都》被大量盗版侵权的事实,可以看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许多作家、文化人,在充分享受媒体时代、文化市场所带来的种种特权的同时,随时也都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受害者。”今天看来,此言不谬。由于市场权威的运作,有关《废都》的批判及评价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从而难以对作家形成客观公正的评价。
作为作家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理应对作家的创作及文学地位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能保证文学创作朝着健康和良性的方向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可悲地发现市场权威同样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冲击着为 “文学立法”的文学批评。不可否认,在滚滚红尘面前,仍有一些敢于坚守、敢于探索的批评家在默默耕耘,但这并不能整体上改变市场权威对文学批评裹挟这一客观现实。在市场权威的诱惑和紧逼下,文学批评很难保持独立品格。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的文学批评来看,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媚俗化倾向日趋明显,有的甚至沦为商业炒作的工具。尽管政治权威和文化权威仍潜在影响着作家的评价机制,但市场权威的主导作用已不容置疑。在这种评价机制下,作家的创作及地位往往由市场来确定。一方面,作家要靠市场来生存;另一方面,市场也需要打造自己的品牌作家和作品。作品是否畅销已成为作家、出版方和读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在其影响下,作家们很难成为“局外人”,他们不得不关注自己的作品能否适应当下市场、能否创造不错的销售业绩乃至能否成为畅销书而进入各种各样的排行榜。由于市场经济在当下中国的方兴未艾,再加上人们对市场权威的负面作用缺乏足够的清醒认识,可以预见,市场权威对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影响将更为深远。
中国现代作家的评价机制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并非体现为简单的直线进程。实际上,它常常体现为以一种因素为主导并与其他因素相互交织。在不同时期,这几种因素总是不同程度地进行排列组合,此消彼伏。这种复杂性在客观上造成了对中国现代作家评价的艰难。一般来说,作家的评价机制往往涉及多种因素。这里既有文学创作本身的因素,也有文学创作之外的因素。文学创作理应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因素。可是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来看,文学之外的因素受到了过分的强调。无论是文化权威、政治权威,还是市场权威,它们都不可能对一个作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定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评价一个作家的重要因素如审美标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除了一些小圈子如“京派”),以审美权威为主导的作家评价机制在现代文学史上从未被确立。也许,这正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因为这不仅是对作家的负责,也是对作品和读者的负责。
注释:
(1)就笔者所掌握材料,周扬作为政治权威影响现代作家地位和命运主要是在1949年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此期间,周扬作为党的文艺总管,几乎全部参与了较大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批判,直接或间接造成了许多作家的不幸。著名作家就有胡风、丁玲、冯雪峰、艾青等。
(2)根据中国期刊网统计:1980至1989年,关于金庸的论文仅有7篇。
(3)参见:王鹏《金庸小说,从江湖到庙堂》,《京华时报》2008年10月31日第17版。
(4)据贾平凹多年后的倾诉:“《废都》弄到那个地步”,“我在西安没法呆下去”,“一夜之间我成了流氓作家、反动作家、颓废作家,帽子戴得特别大。这期间好多人、好多事,给我写作和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参见:《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第215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5)参见:陈晓明《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及其他》,《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栾保俊《不值得评价的评价——〈废都〉读后感》,《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2期;户晓辉《裸体的〈废都〉》,《新疆艺术》1994年第2期。另外,李书磊、戴锦华、张颐武、李洁非、孟繁华、韩毓海、余世存等也都对小说进行了“严厉批评”。
[1][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85.
[2]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2-12.
[3]徐鹏绪,李广.《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66.
[4]孙国林.毛泽东与“党的文艺总管”周扬[J].党史博采,2006,(4):17.
[5]舒坦.金庸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J].文学教育(上),2009,(5):157.
[6]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文 心)
I206.6
A
1001-862X(2013)02-0171-005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作家评价机制的生成及演变”(11YJC751004)
蔡长青(1971—),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教育部资助武汉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