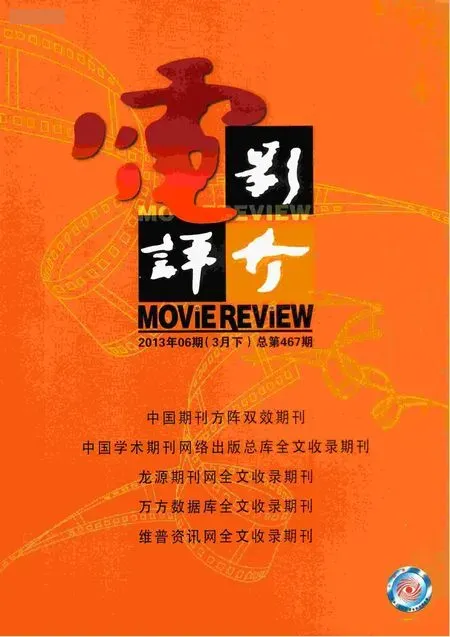现代人生存的多重困境—— 浅析《一次别离》
《一次别离》无疑是一部朴实无华却内蕴丰厚的电影,相对于中文译名的直白,该影片的英文片名"A Separation"似乎涵盖了更为复杂的多面意思。本文将对在纳德和西敏这对夫妻的离婚案中勾连出的移民与留守、婚姻与爱情、传统与现代、法律与道德等诸多问题进行浅析。
首先是对祖国“母体”的背离与否。纳德一家三口打算要离开自己的国家移民到对自己孩子成长与未来更好的国家。正如电影的开头西敏向法官陈述要带女儿出国的理由时说:“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令人惊讶的是法官问:“怎样的环境”?西敏却没有回答。西敏对移民这件事感觉最为强烈,她极力想要离开这个国家,而丈夫拒绝离开的理由是要照顾患上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我们不能否认西敏的这个决定多少带有利己主义色彩,这种利己主义色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必然是追求自我保存,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和存在的,人的本质决定人是利己的。”[1](P551)但是老人在影片中似乎带有一层象征意义,那就是他们的祖国,他们曾经试图背离的“母体”。在我看来这种主动对于“母体”(也就是自己祖国)的背离,看似是积极地追寻新的更加优越的生活,实则是对现状的逃离,虽然他们是自己国家的有着不错生活的中产阶级。影片中对于大的背景交代甚少,但影片最初在西敏和纳德打算离婚的法庭上,工作人员反问西敏“怎么确定移民的国家就一定对孩子有好处呢?”我们可以大胆假设,纳德的父亲,这位身患老年痴呆不能自理的老人根本不存在,那么移民之后,他们的生活会像想象中那样么?我觉得答案是否定的。正像是西敏质问纳德,“他还认识你这个儿子吗?”纳德说,“他不必认识我,只要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就可以了。”人身上的对于母体的依赖、眷恋是无法通过距离来剥离的,所以纳德对于自己的父亲和国家都还是怀有期待的,甘愿承担照顾父亲的重担。况且纳德一家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逃离了这个大的生存土壤、文化环境,他们可能会剔除自己的信仰以及信仰带来的生活习惯么?他们能够在另外一个环境中适应生存下来么?这似乎象征着整个社会要去否定自我要去重构自我,而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难以承受的阵痛。这种对于“母体”的“背离”,该去该留,本身就是一个生存困境。
其次是最为显而易见的分居。其深层原因是两人之间的隔阂。纳德不忍丢下身患重病无法自理的父亲而放弃移民,西敏在无法说服之后选择分居,乃至片末两人的离婚。剧中纳德与西敏发生的最为激烈的争论是如何处理与保姆瑞茨家的矛盾,西敏为了避免自己的女儿受连累,想要通过妥协退的方式。而纳德却十分坚持自己的原则,甚至对西敏大加指责“你一遇到什么事情,要么就是躲避,,要么就是妥协,你从没有想到迎上去解决它!”西敏偏于感性,她最为关心的始终的自己的女儿,而纳德却十分理性注重法律。这也许是男女处理问题的分歧。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好好的交流,正如西敏哭诉着“他连‘你别走,别这样,我不想离婚’这种话都没说过”,“好像十四年的夫妻生活都不算什么似的”,证明夫妻关系已长时间疏离。当西敏愿意卖车出钱去帮助丈夫时,换来的却是纳徳愤怒的指责,“我是说你为什么要插一手?”西敏再次留下泪水。由此可见西敏的出走,并非出于自私,而是于夫妻的隔膜与冷漠。影片中导演处处小心,保持中立,正像是西敏要求离婚时还强调自己的丈夫是个正人君子。破裂的婚姻更多的是两人长期疏于交流导致的隔阂。即使纳德安慰自己的女儿说“她会回来的”。影片中有一次纳德为自己的父亲洗澡,在浴室里他禁不住失声痛哭,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的痛苦与无助,只是他从不曾在自己的妻子面前流露。这里的“Separation”更像是他们夫妻之间的隔膜,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稀薄,移民问题、重病父亲大概只是冰山一角。无法与自我、他人、社会沟通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生存疑虑。现代人在心灵精神上的孤独、虚无、幻灭,这种扭曲是惊人的。这种畸形变形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社会的变异。这种精神困境不但是纳德和西敏的困窘,而是具有普泛化的,是存在于现代生活的角角落落的生存困境。
然后是纳德一家与保姆瑞茨一家的“鸿沟”。带着孕体和照顾小女儿的瑞茨需要早晨五点就起床然后坐车两个小时来工作。通过影片画面中瑞茨憔悴的神态,我们可以看到她作为一个普通的底层民众与纳德一家的差距。丈夫的失业、债务使得她不得不瞒着丈夫出来工作,这在伊斯兰教的教义中是不允许的。在瑞茨的丈夫哈德特因为她流产而控告纳德,气急败坏地出场以后,影片中透露出浓浓的辛酸气息。作为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家庭,经济破败物质匮乏是困扰他们的生存难题,他们需要一笔钱,这笔钱可以堵上债务,可是细想一下,抛去良心的谴责,即是得到了这笔赔偿,他们以后的生活就会有起色么?更何况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他们血液里积淀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胎记是不会允许他们逃离道德的谴责的。两个家庭的对立并非黑白分明,而是善恶不明。一切矛盾在此碰撞,所有阴暗面又被作者融合到一切普世价值和真善美中,结成一片朦胧无解的无法遁逃的生存之网。
最后是影片中暗含的一对矛盾,纳德代表的世俗世界的法律规则和个人道德,瑞茨代表的传统的宗教道德。除了上文中纳德指责妻子的妥协退让之外,影片中安排了纳德为女儿温习单词的细节,他告诉女儿即便会被扣分也要坚持正确的拼法,这里可以看出纳德是一个有原则坚持真理的人——他甚至不介意为坚持原则付出的代价,恰如西敏指责他不顾及女儿的安全执拗不赔偿瑞茨家一样。但面对法官的追问时,因为担心女儿和父亲无人照料,他却违心地说了假话。倘若他恪守道德便意味着将要遭受法律的制裁,所以他做出了向现实妥协的一种无奈选择。其后法官要求询问他的女儿,纳德并没有对女儿有太多的交代,没有试图想要女儿帮他圆谎。而后面对女儿的一再追问,他说出了真相。纳德处在道德与法律的纠葛中,法律中他能蒙蔽他人,道德中他却欺瞒不过自己和女儿。同样,瑞茨瞒着丈夫出来照料老人是违背宗教道德的,所以在为老人洗澡之前,她忐忑不安,不知所措,最后竟然打电话向宗教权威请教是否可行。这样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一个深受宗教熏陶,严守宗教禁忌的底层社会妇女身上。在这个信仰日渐淡薄的现代世界里,古老的宗教观依然顽强地延续着它的生命力。但是为了顾忌丈夫的感受,同时面对得到一笔赔偿为家庭解难的诱惑时,瑞茨不敢向丈夫坦白自己在流产前被车子撞过的事实,一边暗暗地受到道德的谴责,一边不得不接着把戏演下去。宗教最原始的根源来自自然,但是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适应社会的法律和道德难免会与宗教冲突。 这种道德的挣扎一直持续到纳德和西敏愿意出钱赔偿,才触及到她的底线。她道出实情的理由是害怕会招来可怕的诅咒。平民百姓的善良和诚实竟是出于对信仰的恐惧,或者说虔诚。绝对的信仰带来了绝对的恐惧,这本身也是互为矛盾。相对于纳德与西敏担心这件事情对于自己女儿成长会带来负面影响而言,这是多么的嘲讽。她的丈夫虽然是一位无力养家而自责的男人,但也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当瑞茨袒露车祸实情后,他想收下赔偿金并独自承担说谎的罪过。此时,在与宗教道德的冲突中,身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感以及被债主的逼迫最终占据了上风,但是面对不愿意违心发誓的瑞茨时,他的道德谴责和生活的承重负担交织碰撞。然而我们不该痛加指责,“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自私和人性是分不开的。”[2](P625)他的自私源于生活的困顿,影片中人的自私本性是被现实生活的困境催生出来的。
影片的结尾意味深长:女儿含泪,将向法官宣布选择父亲或者母亲,而男人和女人则走出审讯厅,两人之间隔着一道玻璃屏障,各自不安地等待。故事既然讲的是一次别离,那么几经波折之后,两人又重新回到了法官面前。纳德依旧是纳德,西敏依旧是西敏,互不妥协,离婚是必然的。梅特似乎已经明白,孩子总该接受大人的分离,就如同老人总有一天得接受儿女的离开一样。
结语
电影《一次别离》仅是如实地呈现了一个家庭生活中的故事,然而在这个平凡的生活缩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思所想所困扰的问题跟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人民一样。这个平凡的故事背后带有普泛化的意义,揭示了现代人类文明和现代人生的生存困境。人性的自私,信仰的挣扎,亲情的博弈,现实的贫苦,无论真相如何,双方都有各自的难处。片中没有所谓的正反面人物,每一个人都像是遁入了一个大网,挣扎于现实与良心的纠葛,人性的善与恶,并最终暴露出了人信仰道德界限之外的一面。生活还在继续,问题依旧存在。
[1]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荣震华、李金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P551
[2]休谟著. 关文运译. 人性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P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