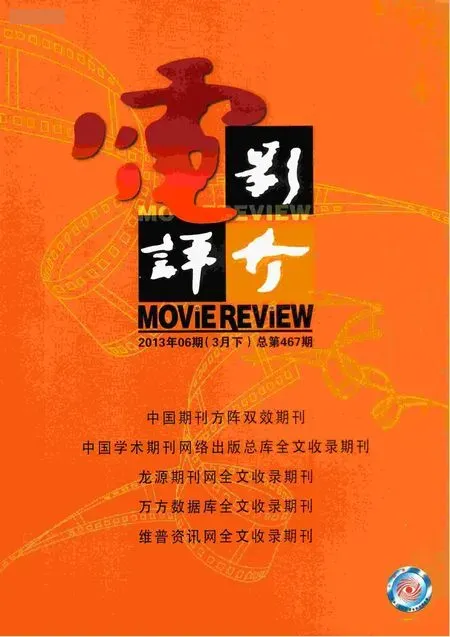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看人类精神信仰的价值
从片名不难看出,这是一部充满奇幻冒险风格的影片,它讲述了一个少年在海难之后如何与一只同船的猛虎结伴同行的故事。这样的故事通常情况下会被笼统地归纳为一个“成长”或是“友谊”的主旨。但是,影片峰回路转,虚实相间的地方在于:当作家和观众都以为派的故事以自己获救、老虎走进森林而终结时,成年派又提供给我们另一个故事,不同于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自己和老虎,第二个故事是全部以人物出场——水手、厨师、妈妈、自己,在小说家的推断下,他们分别对应了第一个故事中的斑马、豺狼、猩猩,而少年派居然是第一个故事中的老虎。成年派没有否认小说家的推断,只是问他喜欢哪个故事,得知对方喜欢第一个故事时,成年派说他看见了上帝。
李安的这部电影的主题当然不只是寓意深刻的精神分析,也不仅仅是通过那美轮美奂的3D效果而显示出的人与自然的神奇交响乐。所以,如果派的第二个版本的故事没出现,这部电影只能称之为精致,却格局不大,充其量是海洋版《荒岛求生》,人虎版《泰坦尼克号》,印度版的《鲁滨孙漂流记》,而在派讲述完第二个版本的故事后,电影情节急转直下,人物故事豁然明朗,草蛇灰线全部浮出水面,好比观众品了甘醇的酒,潜伏的酒劲此刻终于上脑,大家直呼后劲十足畅快过瘾。派的第一个版本的故事是派自己虚构出来的,而第二个版本才是真实发生的一切,而正是这两个版本的冲突与一致,使得《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充满了复杂深刻的哲学解读。这里面出现的哲学元素有:理性,欲望,宗教,克尔凯郭尔宗教的人,弗洛伊德的自我本我,科学,人的本质。
少年的派信奉多种宗教,他的父亲曾一语道破:什么都信等于什么都不信。此时的派貌似是宗教信徒,但严格意义上讲,他不是宗教信徒。他不过是看似虔诚却又一无所知循规蹈矩的人。在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眼里,这些人说到底不过是遵循着教规和仪式的伦理阶段的人,而宗教阶段的人,都是体验着人生的莫大痛苦,当痛苦到生活对他毫无意义,上帝就会降临。真正宗教的人,是“信仰骑士”,惟有信仰才能在荒诞偶然的存在中,仰天大呼“啊,请赐予我力量吧!”。在派遭遇了海上的一系列磨难后,他从理性的人变成非理性的个体,他的内心生活痛苦神秘,终于,当生活对他而言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另外一个意思上的神终于出现,派最终获救并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宗教的人。电影里少年的派吃饭时会祷告,中年派吃饭还在祈祷,这份祈祷和信仰却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一次升华。
当然电影里对宗教看似不敬的细节很多,派早期信仰基督教不过是和哥哥打赌敢不敢喝圣水。这样看起来,李安貌似是在某种意义上反宗教,实则李安是反宗教的宗教,反信仰的信仰。因为,电影结尾处,一个对于宗教无可无不可的信徒,尽管已经知道彼岸的极乐世界不复存在,但却在磨得九九八十一难后取得信仰的真经来。电影中,派与老虎在海面上敌对又共存这一段,派其实就是老虎,这一个故事可以有多种哲学解读,比方说派代表着人的理性,老虎代表着欲望与恶;我们也可以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派代表理性与常识的自我,老虎代表无道德无理性的本我,当人类恶的化身豺狗厨子吃掉斑马水手,杀死派的猩猩母亲后,派心中的恶被无限激发,他杀死厨子也吃了厨子。在此之前,派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类个体,影片中曾讲到过他小时候曾伸手喂老虎吃肉。而这之后,派的兽性以绝对优势地压倒了人性。但当派踏上陆地终于获救的那一刻,老虎头也不回的跑进了山林,这寓意着回到正常的人类社会,派心中的兽性也随之消失,他的理性回归,本我再次复活。那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善,恶,理性,还是欲望?我想李安试图告诉大家:人的本质不是善恶,人性中善与恶,理性与欲望并存,在某种关系下理性凸显,在某种关系下恶复活。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不过是那一系列关系罢了。
在片中,派与老虎,或者说人类的理性与恶经历了多个阶段,童年时的派意识不到老虎是恶,派此时还不代表理性。因为对于派而言,一个尚未接受人类教化的儿童身上自然性仍然占据主导,理性尚不显露。之后,派的父亲教育派,人类文明的痕迹在派身上越来越明显,派趋向于一个理性的人。救生船上,派扔下救生圈准备救漂浮物,却发现是老虎后,并不打算救老虎,于是片中出现派拿起船上的竿子打老虎,老虎却借助竿子的力量自己跃上了船。此时,理性对于恶是十分戒备的,理性拒绝着恶。当猩猩斑马豺狗都死去以后老虎曾一度掉下水,派打算用锤子阻止老虎上船,却不忍下手,最终拆下船上的木板救老虎上船。此时,理性与恶的界限开始模糊,理性与恶开始共存。派借助在动物园学习到的本领试图驯服老虎,理性控制驯服恶。暴风雨后,老虎奄奄一息,派也穷途末路,派抱起老虎轻轻安慰,此时,理性与恶相互依赖,共生共存,密不可分。上岸后,老虎离去,恶、欲望、兽性在人类的文明社会是被压制和掩饰的,派的理性回归,但是这个理性早已不是受人类文明教化的理性,所以派会为老虎的离去而伤心无比。总体而言,派与老虎,理性与恶经历了共存,驯服与依赖。
电影结尾处,派询问记者更喜欢哪个故事,记者回答说第一个版本,保险公司的日本代表尽管十分怀疑第一版本的真实性,却最终在报纸上刊登出了第一个版本,两个版本孰真孰假已经无关紧要,版本的对立消弭于看似不可一世的人与科学的无能为力中。至此,《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完成了两大哲学主题:理性的人——非理性的人——理性的人;信仰的存在——信仰的迷失破灭——信仰的重建;在这次奇幻漂流中,人与人类的信仰遭遇了一次奇遇,完成了一次升华。
[1]田卉群.《少年派的奇幻漂流》:2012年的《约伯记》[N].北京日报.2012-12-20(018)
[2]龚丹韵.《少年派》为何激起如潮解读热情[N].解放日报.2012-12-18 (008) [3]靳凯元.无解的主题—关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N].中国文化报.2012-12-06 (006)
[4]吴言.我们心中都有一只猛虎[N].华夏时报.2012-12-06 (021)
[5]储双月.少年派讲的是信仰故事[N].新华每日电讯.2012-11-30 (014)
[6]蒲波.“少年派”在3D奇幻中追索信仰的力量[N].中国艺术报.2012-11-3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