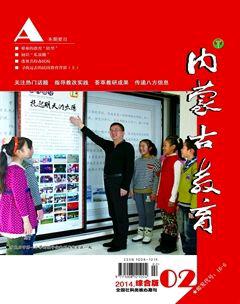漠南教育史上的丰碑
刘朝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清王朝腐朽黑暗的统治和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之下,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神州大地阴霾蔽日,满目疮痍;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称为漠南的内蒙古大地,更是贫困闭塞,民不聊生。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夏历戊戌年),喀喇沁右旗(现赤峰市喀喇沁旗)一代开明蒙古王爷贡桑诺尔布(1872~1931)承袭其父旺都特那木济勒的爵职,继任喀喇沁右旗多罗杜棱郡王、札萨克(执政),成为喀喇沁右旗第十四任札萨克、第十二代多罗杜棱郡王,人们称之为“贡王”。是年康有为等人发起了“戊戌变法”运动,这场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残酷镇压下以失败而告终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给贡桑诺尔布以深刻的影响。他立志革新旗政,发展实业,废除封建等级制度,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在贡桑诺尔布的革新举措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提倡科学文化,兴办新学,培养人才,开启民智。
●创办新学的前奏
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专制统治,长期对蒙旗采取愚民政策。朝廷明令蒙古族人民不准学习汉文和外文,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学习蒙文也得向喇嘛学习。在清王朝的严酷箝制下,蒙旗文化落后,经济萧条,广大农牧民陷于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的状态,世世代代为王公贵族、牧主地主、上层喇嘛等特权阶层输租服役,当牛做马。贡桑诺尔布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又受到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深知发展教育、开启民智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为了改变喀喇沁右旗贫穷落后的面貌,他把兴办教育当作革新旗政的首务,决心创建新式学堂,培养人才,在自己的领地上开一代新风。为此,他向旗民公布了兴办教育事业的训令:
查自古昔以来,不论何种民族,随着时潮的演变,都是由落后逐渐走向文明。例如汉族,虽然居住在中原地区,气候适宜,物产丰富,但在古代轩辕皇帝以前的时期,他们仍然是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在此后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很多英明皇帝和古圣先哲创造文字和文化,教育全体民众,才形成了现今的文明民族。西欧列强,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毫无例外地都经过了野蛮时期,但由于各国国王们的善于教养本国人民,才逐渐强盛起来。日本是一个东海岛国,在他们英明皇帝明治时代,周游各国,变法维新,振兴工业,数十年间,国富民强,比我们清朝这样一个大国还要强盛得多,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我们蒙古民族,在数百年前,成吉思汗崛起于漠北之地,席卷欧亚两洲,灭国四十;忽必烈薛禅汗,入主中原,数代相传。元顺帝失政中原,退居漠北,自此之后,日渐衰落,以至于目前的贫弱境地。这岂不是因为没有文化的原因造成的吗?本王父祖相承,历受大清皇朝的爵位和俸银,当此国家多事之秋,如不协助国家使民众习文练武,实在于心不忍。尤其是我旗蒙汉杂居,如果不提高蒙民的文化水平,则势必受到汉民的卑视和欺压。因此,于公于私,必须创建学校。协理台吉、官员、参领以及全体旗民,善体本王意愿,一体遵照。切切此令。
(邢致祥著,讷古单夫译《贡桑诺尔布传》,见《赤峰市文史资料选辑·喀喇沁专辑》。下同)
他从中原汉族的文明发展史和西欧、日本的强盛史,揭示了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对于民族进步、国家兴盛的重大意义;昭告全旗官员和民众:必须创建学校,发展教育事业,提高蒙古族人民的文化水平,这样才能改变蒙古族的积贫积弱状态,也才能在列强环伺的“多事之秋”为国家尽忠效力。训令形成于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其主旨显然在于强调创建学校、提高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对于振兴国家、民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贡桑诺尔布能将教育事业放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高度上认识,这种远见卓识应当受到后人钦敬。
贡桑诺尔布迅速将创办学校的计划变为行动。在他袭职之前,喀喇沁右旗只有为数寥寥的几处私塾。他登上统理一旗政务的札萨克郡王之位后,即在大营子村(今王爷府镇王爷府村)开设书塾一处,称为义学,招收附近村庄12名农家子弟入塾读书。他聘请塾师钱士林任教,教材为传统的读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四书、五经。因是义学,学生免费上学,学费、膳食费都由王府的管事处发给。贡桑诺尔布每年两次亲自测试学生成绩,对学业优等的奖给笔墨纸砚,以资鼓励。义学是旧式学堂,不能传授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培养新型人才,当然不是贡王办学的最终目的。据曾任王府官员的汪国钧所著《蒙古纪闻》记载,贡桑诺尔布在开办义学时,就有兴办新式学堂的打算,只是“民智未开”,怕旗民百姓对新学堂难以接受,加之经费困难,只好暂缓一步。
●创办崇正学堂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乘机大举入侵北京的事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逃到西安避难。清政府被迫与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八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再一次落入苦难深渊,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更加摇摇欲坠。为了挽救危局,原先极力反对变法维新的保守势力不得不接受变法的呼声。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慈禧太后正式宣布实行“新政”。是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4月21日,她又下令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划推行“新政”的专门机构,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又增加袁世凯)为参与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
清末新政的改革措施多与1898年戊戌变法相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1901年9月4日,清政府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清政府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此外清政府还要求各省筹集经费选派学生出洋学习,对留学生给予奖励。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等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的折子,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当年12月6日,清廷下谕设立学部,为专管全国学堂事务的机构。这些举措充分说明,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清廷不能不感到危机深重,迫切希望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培养各方面急需的人才,缩短与西方列强的差距,挽救国家危亡和自身统治。
贡桑诺尔布目光敏锐,怀着强旗富民、振兴国家和民族的雄心抱负,时刻把兴办新式学堂放在心上。他抓住清廷颁发新政诏令的良机,立即从1901年开始筹办新学,相继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开办了崇正学堂,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开办了守正武学堂和毓正女学堂。三所新式学堂的创办,在内蒙古开风气之先,取得了彪炳史册的骄人业绩。正如资料记载,当时内蒙古西部地区虽然有1902年初“绥远城将军信恪创办了为编练新军服务的绥远城武备学堂”,但是从总体上看,“蒙古各盟旗中最早兴办新式教育的是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分别见《内蒙古区情网-自治区志-清末内蒙古地区的其他新政-文化教育事业》和白拉都格其等《蒙古民族通史》第五卷,第73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崇正学堂的校址设在王府大院西边的一座院落里,这里是王府的旧址,俗称“西衙门”。从现存的一帧崇正学堂旧址照片上可以看到,学校房舍俨然,绿树成荫;前庭很广阔,正好用作操场。院内除教室、办公室外,两旁各建有4个储粮的圆仓。后院是球场,立有篮球架。据记载,校内还有宿舍、饭厅,有小型图书馆,设施一应俱全。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有这样一处王府旧邸设立学校,条件应属上乘。
为了筹建这所学校,1901年夏,贡桑诺尔布邀请浙江钱塘人陆韬来喀喇沁右旗王府,拟定学堂章程,包括课程门类、教学方法。当时正有日本人寿田龟之助和他的翻译小池万平来王府,贡桑诺尔布也请他们“帮同参酌一切章程”(汪国钧《蒙古纪闻》)。经过一年的筹备,新式学堂于1902年10月31日(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一)开学,原先办的义学并入了新学堂。新学堂起初名叫“养正学堂”,贡桑诺尔布亲任校长,派旗衙门协理希里萨拉(希光甫)为校务总办,负全责,管旗章京于瑞生、梅伦章京朝鲁(汪良辅,系汪国钧之父)、管旗章京衔海山、王府长史阿拉麻斯鄂其尔(赵鹤亭)为副总办,梅伦衔邢宜庭为教务主任。聘请陆韬和另一江南名士钱桐(江苏无锡人)为总教习;长安(邢宜庭)为汉文教员,富宝斋(包景文)、巴图敖其尔(伊宪斋,有梅伦职务)为蒙文教员。学堂总办和帮同总办参赞事务的副总办负责学堂的行政及经费筹措等工作。
新学堂开学的第一天,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开学典礼,王府衙门的高级官员都参加了这一盛大典礼。贡桑诺尔布登上讲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我身为王爵,位极人臣,养尊处优,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可是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因为我亲眼看到了我的旗民子弟入了新学堂,受到教育,将来每个人都会担当起恢复成吉思汗伟业的责任。
讲话之后,他濡墨挥毫,当众撰写了一副楹联:
崇武尚文,无非赖尔多士;
正风移俗,是所望于群公。
联语工整而有气魄,表达了对莘莘学子的殷切期望,显示了一代开明蒙古王爷培养人才、正风移俗、富旗强国的雄心壮志。陆韬、钱桐和教师们欣赏之下无不交口称赞。据马希《崇正学堂百年校史》一文记载,因为对联内有“崇正”二字,陆韬、钱桐和教师们建议把学堂名称由“养正学堂”,改为“崇正学堂”,贡桑诺尔布欣然采纳了这一意见。于是这所开风气之先的塞外新式学堂,就以“崇正”这一高雅隽永的校名载入了史册。学校命名为“崇正”,体现了贡桑诺尔布崇尚正道、培育英才、追慕时代新潮、拒绝腐朽和邪恶的办学理念,也蕴涵着对学生的训导、对教师的厚望。
接着,贡桑诺尔布又即兴赋诗一首:
朝廷百度尽维新,藩属亦应教化均。
崇正先从端士学,兴才良不愧儒珍。
欣看此日峥嵘辈,期作他年柱石臣。
无限雄心深企望,养成大器傲强邻。
诗中的“端士”,即端方正直的人。“儒珍”,语出《礼记·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诗中以席上的珍宝比喻古时儒者拥有的美善才学;自信今日崇正学堂将要造就的人才,一定无愧于古人。全诗抒写了兴办新学的意义和对学子们寄予的热切期盼,充分显示了贡桑诺尔布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造就国家栋梁,强国御侮的豪情壮志和远见卓识。崇正学堂的开办,开创塞外蒙旗兴办新式学堂之先河,犹如给闭塞的穹庐打开了一扇通向外界的窗户,为喀喇沁右旗带来了新鲜气息。
崇正学堂初办时,只有40名学生,主要是并入学堂的原义学学生、王府勋旧子弟和贡王的随侍人员。学生编为初级和高级两个班,课程设置有蒙文、汉文、日语、算术、地理、历史、修身、书法、绘画、音乐、体育等,每周上课五天半。贡王请陆韬编写了《喀喇沁源流要略便蒙》,由汪国钧(博彦毕力格图)译成蒙文,又责成两人编写了汉文四字句蒙旗地理教科书,一并作为乡土教材。汪国钧还撰写了《蒙文文法启悟》,以便于蒙文教学。(分别见玛希《汪国钧及其〈蒙古纪闻〉》和吴恩和等《贡桑诺尔布》)
在留存至今的崇正学堂学生合影上,当年那些由于贡王办学才有机会接触近代文明的蒙汉族子弟,身着统一校服,整齐列队;前排是龆龄学童,后排是少年学子,最后面是一排身着长衫、风度儒雅的教师。照片记录的这一瞬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崇正学堂的创办,是漠南草原上近代新型教育的滥觞,在内蒙古东部地区是破天荒第一次。贡桑诺尔布的历史功绩将永载于史册,为后人世代铭记。
崇正学堂创办之始,即遭旗内一些蒙古族上层人物和喇嘛的反对,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将来要废除私塾,毁坏庙宇,改成洋学堂。但是贡桑诺尔布办学态度坚决,这些人无可奈何。第二年,即1903年,为扩大学校规模,贡桑诺尔布下令从全旗招收少年儿童入学。因为旗民对前任札萨克郡王旺都特那木济勒(即旺王,系贡王之父)的凶残暴虐心有余悸,根本不相信王爷能为百姓办好事,对贡王动员各户送孩子入学疑窦丛生,加上反对办学的人极尽造谣惑众之能事,一时间掀起了轩然大波。造谣的人说什么“学堂和天主教堂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子弟一入学堂,不仅变成异教徒,还要送到外国去,后果怎样,那是很难说的”,等等。王府一些下层官员为了完成招收学生的任务,急于求成,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挨家逐户地去“号”学生,甚至动用差役抓孩子上学。这样一来,更增加了旗民的误解和恐慌,有的把子弟藏在地窖里躲着,有的给王府的官员、差役送礼、行贿,请他们“网开一面”,也有的把孩子送到庙上去当了喇嘛,或送到贵族家去服差役,甚至还有的人家舍家撇业,带着孩子远避他乡。
贡桑诺尔布再三派人下去宣传解释,没有效果。于是他接受幕僚的建议,下令:“今后对于送来学生的人户,免去户口税,并且给他们的门首悬挂上解除赋役的特许木牌,以资奖励。”(见贾荫生整理《崇正学堂》等)这样才陆续有人把子弟送进学堂。为了实现教育兴旗这一梦寐以求的理想,贡桑诺尔布不顾旗衙门财政困难,宁可减少王府的赋税收入,也要采取果断措施,鼓励青少年入学,保证学堂生源。这种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地位的精神,今天看来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同时,他还对学生采取了一系列优待措施:学生学习用品由学堂免费发给;学生的食宿问题由公费解决,走读生午间在学堂吃饭,住宿生在校食宿;毕业生公费保送升学或留学,不愿升学的留旗内任用,等等。由于采取了这些鼓励措施,入学的学生逐渐增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下层人家的子弟。很快,崇正学堂由两个教学班扩大到了4个教学班。学生年龄从7岁到20岁不等,学堂按学生文化程度,分3个年级进行教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学制逐渐完善,几年后增加到了6个年级,并增设了一个师范部,学制1~2年,以适应培养师资的急需。
崇正学堂从开办起到1912年,学生人数最多时达400多名,班级最多的时候发展到10个班,其中包括师范班、实业班(专学养蚕、纺织技术)各一班;毕业生累计达600多名。(同上)据汪国钧《蒙古纪闻》记载,到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崇正学堂“学生百二十人,蒙汉不分,无膳、学等费。学生每日在堂午饭一顿”;“寄宿生四十名,每日饭三顿,饭食为小米、咸菜、菠菜、豆腐煎汤。每星期吃荞面一次。五、八月节及孔子祭丁日吃白面馒头一顿”;唯“学生衣帽均归自备”。由此可见学生所受的优待和生活状况。对那时的农村孩子,这是很难得的。
不久,崇正学堂在王子坟(现辽宁省建平县三家乡新艾里村)和公爷府(现喀喇沁旗锦山镇)设立了分校,不过只办到1908年。
- 内蒙古教育·综合版的其它文章
- 育人:请从“规矩”始
- 高中课改四年间:成效与缺失
- 天生我才教语文
- 教苑新语
- 他刊速递
- 新闻资讯